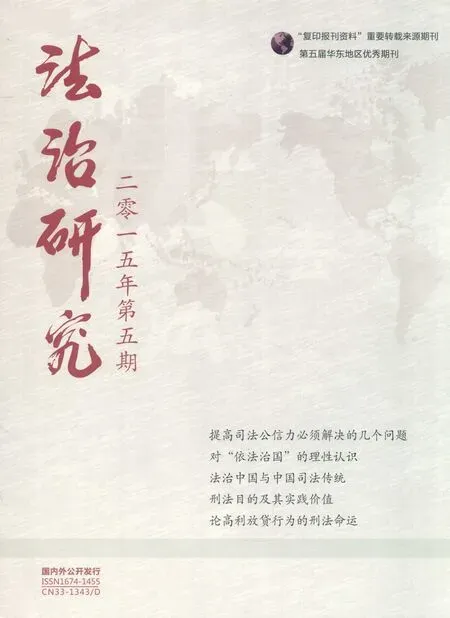人體器官犯罪中醫(yī)院的違法行為類型、刑事責(zé)任認(rèn)定與立法改革建議*
周振杰
人體器官移植在中國的歷史可以追溯至20世紀(jì)60年代。20世紀(jì)90年代之后,中國每年器官移植的數(shù)量,已居世界前列。據(jù)權(quán)威統(tǒng)計,雖然自2004年以來數(shù)量有所減少,但中國2006年的人體器官移植仍多達10000余例,高居世界第二。①See Huang, J., Mao, Y. and Michael, M.J. Government Policy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Lancet, 2008, 372(9654), pp. 1937-1938.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數(shù)十年來一直在無序中進行,而且因為系統(tǒng)地利用死刑犯的人體器官,飽受國際輿論的強烈批評。②See, for example, Foster, T.W. Trafficking in Human Organs: an Emerging Form of White-Collar Cri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1997, 41(2), pp.139-150.為使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走上法治化道路,國務(wù)院于2007年3月21日公布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在第3條規(guī)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不得從事與買賣人體器官有關(guān)的活動”,并具體明確了人體器官移植的原則與程序。為了保證《條例》的規(guī)定得以貫徹,2011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第37條將組織出賣人體器官、欺騙他人捐獻器官、摘除未成年人器官等行為納入了刑法調(diào)整的范圍。
雖然囿于《刑法》第30條“法律規(guī)定為單位犯罪的,應(yīng)當(dāng)負(fù)刑事責(zé)任”之限制性規(guī)定,目前尚不能追究醫(yī)院的刑事責(zé)任。但是,根據(jù)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4月24日頒布的《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條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單位實施刑法規(guī)定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刑法分則和其他法律未規(guī)定追究單位刑事責(zé)任的,對組織、策劃、實施該危害社會行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之規(guī)定,在醫(yī)院組織實施人體器官犯罪的場合,可以追究涉案自然人的刑事責(zé)任。因此,醫(yī)院可以實施什么樣的人體器官違法行為,涉案自然人可能根據(jù)現(xiàn)行刑法承擔(dān)什么樣的刑事責(zé)任,又應(yīng)該如何具體認(rèn)定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應(yīng)該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
一、醫(yī)院人體器官違法行為的具體類型
基于《條例》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在理論上可以將醫(yī)院可能實施的人體器官違法行為大致分為如下四種類型。第一,醫(yī)院違反上述第3條的禁止性規(guī)定,獨自或者參與組織出賣人體器官。在當(dāng)前實踐中,主要表現(xiàn)為醫(yī)院與非法中介互相勾結(jié),偽造供體與受體之間的血親或者親情關(guān)系證明文件,進行所謂的“親體移植”,這已經(jīng)成為了整個移植行業(yè)的潛規(guī)則。《條例》第10條規(guī)定,活體器官捐獻人的配偶、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nèi)旁系血親,或者有證據(jù)證明與活體器官捐獻人存在因幫扶等形成親情關(guān)系的人員可以接受活體器官捐贈。所以,此類證明文件可以成為醫(yī)療機構(gòu)中負(fù)責(zé)審查器官移植合法性的倫理委員會審查的書面基礎(chǔ)與應(yīng)付追責(zé)的盾牌。據(jù)統(tǒng)計,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fù)核權(quán)的當(dāng)年,全國肝移植中有近1/4來源于活體,這一比例在3年前只有0.32%。當(dāng)然,這其中絕大部分的移植手續(xù)都是虛假的。③參見朝格圖:《非法器官移植,醫(yī)院該當(dāng)何罪》,載《南方周末》2011年3月24日。在鳳凰周刊報道的一例肝臟移植中,收治患者的某醫(yī)院移植中心主治醫(yī)生教唆并安排患者家屬偽造供體移植資料,而所在醫(yī)院的倫理委員會不作任何實質(zhì)性審查,就心照不宣地許可了這一虛假的親體移植。④參見鐘堅:《大陸死刑犯器官移植演變史》,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fengmiangushi/2411.html,2014年12月28日訪問。從行為的整個過程來看,案中醫(yī)生的行為顯然并非是其個人行為而是整個醫(yī)院的有組織行為。
第二,不具備器官移植資格或者未經(jīng)合法科目登記,擅自進行人體器官移植手術(shù)。根據(jù)《條例》第11條與第27條之規(guī)定,醫(yī)療機構(gòu)從事人體器官移植,必須根據(jù)《醫(yī)療機構(gòu)管理條例》的規(guī)定,向所在地省級政府的衛(wèi)生主管部門申請辦理人體器官移植診療科目登記,否則可以根據(jù)《醫(yī)療機構(gòu)管理條例》給予行政處罰。但是在實踐中,為了謀取暴利,未經(jīng)申請登記而從事人體器官移植的醫(yī)院不在少數(shù),甚至像浙江省人民醫(yī)院、海南省人民醫(yī)院這樣的省級醫(yī)院在2012年都曾經(jīng)因為違法進行器官移植而受到行政處罰。⑤參見徐潛川:《揭開中國非法器官移植的驚悚黑幕》,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011/23/642066_320699284.shtml,2014年12月28日訪問。
第三,違反《條例》規(guī)定的具體倫理規(guī)范、技術(shù)規(guī)則與法定義務(wù),開展人體器官摘除或者移植手術(shù)。例如,根據(jù)《條例》第17條之規(guī)定,在摘取活體器官之前或者尸體器官捐獻人死亡之前,執(zhí)業(yè)醫(yī)師必須向所在醫(yī)療機構(gòu)的人體器官移植技術(shù)臨床應(yīng)用與倫理委員會提交人體器官的審查申請,后者在收到后,應(yīng)當(dāng)對人體器官捐獻人的捐獻意愿是否真實、有無買賣或者變相買賣人體器官的情形以及人體器官的配型和接受人的適應(yīng)癥是否符合倫理原則和人體器官移植技術(shù)管理規(guī)范進行審查,但是上述案例已經(jīng)表明,在實踐中倫理委員會不認(rèn)真履行審查職責(zé),甚至利用職責(zé)謀取利益的情況并不罕見。再如,根據(jù)《條例》第8條之規(guī)定,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獻其人體器官的,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捐獻、摘取該公民的人體器官。醫(yī)院違反死者生前意愿摘取或者竊取其器官,以及未取得死刑犯同意或者未經(jīng)死刑犯家屬同意,與非法中介甚至與司法機構(gòu)互相勾結(jié)摘取死刑犯器官的,都屬于這一違法類型。⑥在實踐中,醫(yī)院為了謀取利益與司法機關(guān)勾結(jié)買賣死刑犯的人體器官在內(nèi)部早已不是秘聞。參見陳齊、羅璐:《變賣死刑犯器官現(xiàn)象亟應(yīng)做出立法限制》,載《檢察實踐》2003年第5期。
第四,明知他人利用租用的醫(yī)療設(shè)施進行非法器官摘除或者移植手術(shù),為了獲取非法利益聽之任之。例如,在被稱為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人體器官販賣案的鄭偉等組織出賣人體器官案中,犯罪人鄭偉就曾經(jīng)租用徐州市某縣醫(yī)院的手術(shù)室進行腎臟摘除手術(shù)。雖然該醫(yī)院的業(yè)務(wù)副院長、主治醫(yī)生等曾經(jīng)懷疑過犯罪人行為的合法性,但是為了謀取利益,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積極參與。⑦參見孫思婭:《全國最大販賣腎臟案宣判15人摘腎51枚獲利千萬》,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08/22/c_126902645.htm,2014年12月28日訪問。在這種情形中,醫(yī)院其實是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產(chǎn)生人體器官被非法摘除的危害結(jié)果而放任其發(fā)生,構(gòu)成幫助犯。
那么,在上述四種不同違法行為類型中,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應(yīng)該承擔(dān)什么刑事責(zé)任呢?
二、涉案自然人可能觸及的罪名分析
在上述第一種違法行為類型中,醫(yī)院在供體與受體之間居間聯(lián)絡(luò),教唆、安排偽造患者親屬與器官供體之間存在親情關(guān)系的虛假證明材料,可能涉及的罪名有《刑法》第234條之一規(guī)定的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與第280條規(guī)定的偽造、變造國家機關(guān)公文、證件、印章罪,偽造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由于組織出賣行為是目的,偽造行為是手段,兩者之間存在牽連關(guān)系,在法律沒有特別規(guī)定的情況下,應(yīng)從一重處罰。所以,應(yīng)對參與的自然人以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定罪處罰。⑧根據(jù)《刑法》第234條,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chǎn)。而根據(jù)第280條,偽造國家機關(guān)公文、證件、印章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quán)利;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偽造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最高才處以3年有期徒刑。
在第二種違法行為類型中,醫(yī)院在客觀上無視《條例》規(guī)定的條件與程序,擅自從事人體器官移植,侵犯了被害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權(quán)利;在主觀上,醫(yī)院作為專業(yè)機構(gòu),對于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完全可以預(yù)見,但為了謀取利益積極追求其發(fā)生。同時,在被摘取人體器官者是受到脅迫或者欺騙的場合,醫(yī)院的行為毫無疑問具有違法性;在被摘取人體器官者為了經(jīng)濟利益而出賣自己的器官的場合,即使醫(yī)院能夠證明其是知情同意的,也不能否定自身行為的違法性,因為,一方面,基于上述《條例》第3條的禁止性規(guī)定,買賣人體器官的行為是違法行為,被害人無權(quán)對違法行為作出同意;另一方面,人體器官犯罪不僅侵犯了供體的健康與生命權(quán)益,也侵害了器官移植的合法秩序,被害人有權(quán)放棄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權(quán)益,但無權(quán)放棄公共法益。就如韓忠謨教授所言:“得承諾之行為是否阻卻違法,未可一概而論,應(yīng)視其侵害之法益是否有關(guān)公共法益,以及被害人是否有判斷力而出自真意,并對于該項法益是否得任意處分,參照法律之全體精神以判斷。”⑨參見韓忠謨:《刑法原理》,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頁。就此問題,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立場也非常相似。參見[日]山中敬一:《刑法總論》,成文堂2008年版,第199頁;Jacqueline Martine and Tony Storey. Unlocking Criminal Law, Hodder Education, 2007, p 278.無論受害人是否同意摘取其器官,是否已滿18周歲,是否受到強迫、欺騙,只要醫(yī)院是違法開展器官摘除、移植手術(shù),其行為就具有了可罰的違法性,對于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應(yīng)該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zé)任。
在第三種違法行為類型中,如果醫(yī)院在主觀上是故意違反《條例》規(guī)定的倫理規(guī)范、技術(shù)規(guī)則與法定義務(wù)進行器官移植手術(shù),并在客觀上造成了傷害或者死亡的結(jié)果,或者違法摘除死者的器官,應(yīng)追究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或者侮辱尸體罪的刑事責(zé)任;如果醫(yī)院是因為未盡到注意義務(wù),過失違反法定的規(guī)范、規(guī)則與義務(wù)進行器官移植手術(shù),并造成了客觀的傷害或者死亡結(jié)果,因為醫(yī)院違反義務(wù)的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存在可歸責(zé)的因果關(guān)系,其行為構(gòu)成過失致人重傷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相應(yīng)地,涉案個人應(yīng)承擔(dān)《刑法》第235條規(guī)定的過失致人重傷罪或者第233條規(guī)定的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責(zé)任。
在第四種違法行為類型中,醫(yī)院是以從犯的身份出現(xiàn),參與其中的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的刑事責(zé)任應(yīng)從屬于主犯的刑事責(zé)任,可以根據(jù)《刑法》第234條之一的規(guī)定對之定罪處罰。
三、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的認(rèn)定與量刑
既然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是醫(yī)院人體器官違法中的處罰對象,如何對他們進行具體認(rèn)定就成為了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就此,目前尚無司法解釋或者指導(dǎo)性案例。基于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與刑法謙抑原則,對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的認(rèn)定,從行為視角,應(yīng)遵循“危險原則”,即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的行為必須在客觀上具有導(dǎo)致危害社會后果的現(xiàn)實危險。這里包括兩種情形:(1)行為本身就具有的危險性。例如,D是肝臟移植的主刀醫(yī)生,其明知所要摘除并移植肝臟的對象可能是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仍然在所在科室的組織下,違反規(guī)則實施摘除與移植手術(shù)。(2)行為本身雖然不具有危險性,但是與其他行為相結(jié)合就產(chǎn)生危險性。例如,D是某醫(yī)院倫理委員會的秘書,負(fù)責(zé)器官移植倫理審查申請文件的整理與準(zhǔn)備。在準(zhǔn)備某次審查會議的資料時,故意不將證明供體E與受體F之間存在父子關(guān)系的證明材料(虛假材料)放入審查資料之中。在倫理委員會同時對多項申請開會審查之際,除了委員A之外,其他委員都沒有仔細(xì)審查材料的完整性就表示同意。A注意到了E與F的申請缺少證明文件,但是認(rèn)為在其他委員處,就沒有細(xì)究也表示同意。醫(yī)院也并沒有規(guī)定需要對審議材料與審議結(jié)果的復(fù)查制度。因此,E的腎臟被非法摘除與移植。在此場合,秘書D的行為本身并沒有現(xiàn)實的危險性,因為是否許可器官移植的關(guān)鍵在于倫理委員會的審查。但是,當(dāng)其故意行為與倫理委員會不認(rèn)真履行職責(zé)的行為相結(jié)合,就產(chǎn)生了導(dǎo)致危害結(jié)果發(fā)生的現(xiàn)實危險。
從行為人視角,應(yīng)遵循“知情原則”,即行為人在主觀上了解自己行為的性質(zhì)、后果及其危害性。具體而言,在故意犯罪的場合,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應(yīng)該知道自己的行為:(1)至少是部分為了醫(yī)院的利益而實施;(2)是作為醫(yī)院整體行為的一部分而實施,但并不要求行為人知道其他所有參與人的行為;(3)具有社會危害性。在過失犯罪的場合,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應(yīng)該知道自己的行為:(1)違反了其所承擔(dān)的法律義務(wù)或者業(yè)務(wù)規(guī)則;(2)醫(yī)院知道或者應(yīng)該知道這種違反的存在,并有義務(wù)采取而未采取措施予以預(yù)防、制裁;(3)具有社會危害性。
從上述原則出發(fā),對組織、策劃與實施者的認(rèn)定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根據(jù)行為人是否以自己的行為實現(xiàn)犯罪構(gòu)成要件事實,將參與人劃分為組織/策劃者與實施者,組織者與策劃者并不以自己的行為而是通過實施者的行為實現(xiàn)犯罪構(gòu)成要件事實;其次,根據(jù)是否提出具體的犯罪方案,區(qū)分組織者與策劃者,組織者通常整體負(fù)責(zé)犯罪行為的實施與參與人的分工,而策劃者通常提出具體犯罪計劃。如果某一行為人同時實施了兩項或者三項行為,以其中作用最大的一項行為認(rèn)定其身份,其他行為作為量刑情節(jié)予以考慮。例如,行為人同時實施了組織、策劃與實施行為,其中組織行為的作用最大,則在定罪環(huán)節(jié)認(rèn)定其為組織者,在量刑環(huán)節(jié)再考慮根據(jù)其策劃與實施行為適當(dāng)加重其宣告刑。
應(yīng)該指出的是,因為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刑事責(zé)任的落腳點仍然是單位的危害行為,而單位危害行為是通過具體個人的組織、策劃與實施行為實現(xiàn)的,所以“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與“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通常是相一致的。但是,與《刑法》第31條已經(jīng)將處罰對象限定為單位中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負(fù)責(zé)人員不同,上述全國人大常委的《解釋》并沒有規(guī)定組織、策劃、實施者必須是單位內(nèi)部的經(jīng)營管理人員或者工作人員,可以理解為只要是以組織、策劃或者實施的方式參與了單位危害行為即可,所以“組織、策劃、實施該危害社會行為的人”的范圍應(yīng)該大于“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⑩根據(jù)《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jì)要》規(guī)定,《刑法》第31條規(guī)定的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jīng)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聘任”、“雇傭”的用語表明行為人還是要與單位建立起合法的勞動關(guān)系。本文認(rèn)為,構(gòu)成《解釋》規(guī)定的組織、策劃與實施者,無需這一要件。例如,在醫(yī)院通過外部不法分子來聯(lián)系供體與偽造證明文件的場合,即使后者不是醫(yī)院的工作人員,也可以作為實施者被處罰。
對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當(dāng)然可以借鑒《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是否區(qū)分主、從犯問題的批復(fù)》(法釋[2000]31號)等司法解釋中關(guān)于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負(fù)責(zé)人員量刑的規(guī)定,根據(jù)各自在醫(yī)院組織實施的違法行為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jié)予以處罰。但是,如此做法不但過于原則化,難以操作,而且容易放縱那些站在犯罪幕后操縱、把持人體器官買賣的人,而從犯罪預(yù)防的角度而言,恰恰是這部分犯罪人最應(yīng)該被嚴(yán)懲。為了提高刑罰的威懾力與實現(xiàn)刑罰個別化,建議將對組織者、策劃者、實施者的量刑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根據(jù)其是否對于整個行為或者行為的某一階段起到支配作用,將組織者、策劃者、實施者分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前者是通過后者的行為實現(xiàn)犯罪構(gòu)成要件事實,而后者完全或者部分受到前者的精神或者行為制約。原則上,對于支配者的處罰應(yīng)重于被支配者的處罰。第二,在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內(nèi)部,進一步根據(jù)各自在危害行為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jié)分別進行量刑。
此外,在被支配者中,對于受支配者命令、指派甚至壓制而參與實施了部分人體器官違法行為的人員,也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責(zé)任,或者根據(jù)《刑法》第13條的但書規(guī)定認(rèn)為其行為情節(jié)顯著輕微,不構(gòu)成犯罪。?就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從期待可能性的角度作出解釋。例如,醫(yī)院院長指令辦公室職工與非法中介聯(lián)系,提供受體信息、收取款項或者偽造證明文件,在目前勞動權(quán)利保護不力的情況下,很難期待該職工冒著被調(diào)離崗位、降職、降級甚至開除的危險對抗違法指令。這也是司法實踐的立場。例如,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jì)要》明確規(guī)定,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lǐng)導(dǎo)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zé)任人員追究其刑事責(zé)任。總而言之,刑罰的鋒芒所向,應(yīng)該是那些對危害行為的發(fā)生、發(fā)展與結(jié)束起到全部或者部分主導(dǎo)作用的人。
四、改革人體器官犯罪立法的建議
(一)立法改革的必要性
在人體器官犯罪的整個犯罪鏈條中,摘除與移植是兩個至關(guān)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因為犯罪人的最終目的是將器官出賣給受體進行移植,以獲取高額利潤。如果摘除不成功,就談不上出售;如果不能夠移植,受體就不會購買。在這兩個環(huán)節(jié)中,醫(yī)院與醫(yī)生都起到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立法層面都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司法機關(guān)是根據(jù)《刑法》第225條規(guī)定的非法經(jīng)營罪打擊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的行為。雖然在實踐中并無醫(yī)院被追究非法經(jīng)營罪的案例,但畢竟留下了追究醫(yī)院刑事責(zé)任的途徑。《刑法修正案(八)》雖然將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的行為規(guī)定為獨立的犯罪,但是并沒有將單位列為犯罪主體。?在2010年12月20日對《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進行二次審議時,曾有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在有關(guān)人體器官犯罪的立法中增加對醫(yī)院或醫(yī)務(wù)人員入罪的內(nèi)容,規(guī)定凡是明確知道而違法犯罪的應(yīng)一律予以追究,并處沒收財產(chǎn)。但遺憾的是這一建議并沒有得到接受。參見趙秉志:《略論我國〈刑法〉新增設(shè)的人體器官犯罪》,載《法學(xué)雜志》2011年第9期。這在實質(zhì)上是免除了醫(yī)院的刑事責(zé)任,反而降低了對醫(yī)院的威懾力。對于涉案醫(yī)生而言,雖然他們在理論上作為自然人主體可以被追究刑事責(zé)任,但因為他們在實踐中通常是以受雇傭進行摘除或者移植的面目出現(xiàn),所以只能追究他們從犯的刑事責(zé)任。這明顯也難以反映他們在人體器官犯罪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正是因為立法上的缺陷,在執(zhí)法與立法階段,醫(yī)院與醫(yī)生都沒有受到應(yīng)有的處罰,這又反過來導(dǎo)致了人體器官犯罪有法難禁。就組織實施人體器官危害行為的醫(yī)院而言,在民事賠償之外,目前僅需要接受行政處罰,而行政處罰的力度不夠,存在放縱甚至鼓勵醫(yī)院進行違法之虞。例如,2012年浙江省人民醫(yī)院在沒有取得相應(yīng)資質(zhì)的情況下開展器官移植,僅被責(zé)令整改、罰款3000元,暫停心臟移植資質(zhì)5年。?同注⑤。相比較從人體器官違法行為中獲取的暴利,罰款的數(shù)額實在微不足道;該醫(yī)院既然敢于在未進行科目等級的情況下非法開展器官移植,暫停其心臟移植資質(zhì)可能也難以起到威懾作用。尤其是,實施違法行為的醫(yī)院在實踐中受到處罰很輕。例如,在2009年北京市司法機關(guān)查處的一例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的案件中,北京的數(shù)家醫(yī)院都深陷其中,但都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同注③。以至于有的評論大聲疾呼不能再放任醫(yī)院肆無忌憚地做非法器官移植的幫兇。?參見吳帥:《非法器官移植:醫(yī)院不能再做幫兇》,載《江淮法治》2011年第10期。
同樣的情況也見諸于參與人體器官犯罪的醫(yī)生。例如,在2006年發(fā)生的震驚全國的故意殺害、摘取乞丐人體器官的案件中,參與摘取器官的武漢與北京數(shù)家醫(yī)院的多名醫(yī)生非但沒有受到刑事指控,反而以證人的身份出現(xiàn)在訴訟程序中,而相似案例不在少數(shù)。?同注③。司法機關(guān)的不作為可以說幾乎完全否定了刑罰對參與人體器官犯罪的醫(yī)生的威懾力,因為“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不是刑罰的嚴(yán)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這種必定性要求司法官員謹(jǐn)守職責(zé),法官鐵面無私、嚴(yán)肅認(rèn)真,……如果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犯罪可能受到寬恕,或者刑罰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結(jié)果,那么就會煽惑起犯罪不受處罰的幻想”。?[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fēng)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版,第59~60頁。
此外,在現(xiàn)行立法模式之下,雖然實施危害行為的是醫(yī)院,但是僅能對涉案的自然人進行處罰。在政策層面,這不但是錯誤地將涉案個人作為了預(yù)防對象,而且給醫(yī)院留下了將犯罪成本外化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因為醫(yī)院只能被追究民事責(zé)任與行政責(zé)任,所以在整體上,即使涉案個人被定罪處罰,醫(yī)院本身及其他人并不會產(chǎn)生犯罪的恥辱感。如此,對于涉案醫(yī)院而言,會因為其內(nèi)部成員普遍將自己的違法行為中性化而產(chǎn)生認(rèn)同非法買賣、摘除、移植人體器官行為的犯罪亞文化。這種亞文化不但使得涉案醫(yī)院原來的成員心安理得地繼續(xù)實施違法行為,而且會使得新加入的成員不得不接受業(yè)已存在的價值觀與行為規(guī)范。
對于醫(yī)院群體而言,則會產(chǎn)生美國犯罪學(xué)家詹姆士·威爾遜和喬治·凱林提出的破窗效應(yīng)(Broken windows theory)。?See Wilson, James Q, Kelling, George, L. Broken Windows: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 available at 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org/pdf/_atlantic_monthly-broken_windows.pdf (accessed 18 January 2015).根據(jù)該理論,環(huán)境中的不良現(xiàn)象如果被放任存在,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例如,如果一幢建筑有少許破裂的門窗,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將會有破壞者破壞更多的窗戶。最終他們甚至?xí)J入建筑內(nèi),如果發(fā)現(xiàn)無人居住,也許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縱火。一堵墻,如果出現(xiàn)一些涂鴉沒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墻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一條人行道有些許紙屑,不久后就會有更多垃圾,最終人們會視若理所當(dāng)然地將垃圾順手丟棄在地上。在人體器官違法移植的場合,既然有先例證明實施非法器官移植能夠獲得巨大的利潤,而且即使受到處罰也不會對本身產(chǎn)生實質(zhì)影響,就會有大量的醫(yī)院效而仿之。
最后,隨著人體器官供需矛盾的加大,犯罪的經(jīng)濟驅(qū)動力將會增強,需要加大刑法規(guī)制的力度。因為器官來源短缺,我國每年器官移植手術(shù)僅有1萬余例,但是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超過100萬人。?衛(wèi)生部的統(tǒng)計顯示,截至2009年底,有超過65%的移植器官來源于死刑犯。See Huang, J., Millis, J.M., Mao, Y., Millis, M.A.,Sang, X. and Zhong, S. A Pilot Program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in China. Lancet, 2012, 379(9818), pp.862-866.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全面禁止將曾經(jīng)是主要器官來源的死刑犯作為移植供體來源,自愿器官捐獻成為了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yī)院協(xié)會人體器官獲取組織聯(lián)盟主席黃潔夫2014年12月4日在中國醫(yī)院協(xié)會OPO聯(lián)盟昆明研討會上正式宣布了這一消息。參見程姝雯:《明年起中國器官移植將全面停止死囚器官捐獻》,載《南方都市報》2014年12月4日。但是,我國的人體器官捐獻率僅約0.6/100萬人口,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從絕對數(shù)量上來講,在2013年之前,每年的器官捐獻僅有幾百例,2014年雖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也不過1500例,?參見程姝雯:《明年起中國器官移植將全面停止死囚器官捐獻》,載《南方都市報》2014年12月4日。與每年1萬例移植手術(shù)的需求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并未減少甚至是在增加;另一方面,移植器官的來源卻在減少。所以,移植器官的供需差距將會進一步加大。而供需差距的加大,意味著人體器官在黑市能夠產(chǎn)生更大的利潤。馬克思曾斷言:資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著被絞死的危險!人體器官犯罪帶來的利潤,又何止百分之三百。“要制服兇猛的獅子需要閃電,而槍聲只能使它激怒。”?同注?,第44頁。因此需要改變目前對醫(yī)院與醫(yī)生走過場式的處理方式,通過突出他們在人體器官犯罪中的作用,加大他們的責(zé)任,提高對孕育著風(fēng)暴的人體器官犯罪的懲治力度。
總而言之,醫(yī)院雖然在人體器官犯罪中占據(jù)著至關(guān)重要的地位,但是立法與司法并沒有對之給予充分的重視,就如有的觀點所言:“司法懲治的不平衡性是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犯罪日益嚴(yán)重的重要原因。非法買賣人體器官違法行為中存在組織者、供體、受體、醫(yī)院等多方關(guān)系,在以往的案例中,司法機關(guān)往往只是追究組織者的刑事責(zé)任,尚未有醫(yī)院受到責(zé)任追究,而醫(yī)院恰恰也是人體器官犯罪鏈條上的重要一環(huán),是承擔(dān)審查‘供體’身份、實施摘取行為的主要機構(gòu)。”?參見趙秉志:《略論我國〈刑法〉新增設(shè)的人體器官犯罪》,載《法學(xué)雜志》2011年第9期。所以,從犯罪預(yù)防的角度出發(fā),需要改革現(xiàn)行立法,將醫(yī)院與醫(yī)生作為重要的懲治與預(yù)防對象。
(二)立法改革的初步建議
從醫(yī)院違法行為的類型、醫(yī)院根據(jù)《條例》應(yīng)承擔(dān)的法律義務(wù)以及《解釋》的基本立場出發(fā),應(yīng)該在如下幾方面采取措施,完善現(xiàn)有人體器官犯罪立法。
首先,將單位列為《刑法》第234條之一規(guī)定的人體器官犯罪的主體。本條共涉及四個罪名: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以及盜竊、侮辱尸體罪。其中,將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規(guī)定為單位犯罪可能最容易接受,因為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設(shè)本罪之前,對于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的行為,司法機關(guān)是按照可以處罰單位的非法經(jīng)營罪來定罪處罰,而且上述《條例》第3條也明確將組織作為了禁止對象。將醫(yī)院列為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與盜竊、侮辱尸體罪的犯罪主體在立法上的主要障礙是相應(yīng)各條都只規(guī)定了無法適用于醫(yī)院的死刑與自由刑。因此,需要在相應(yīng)各條增加一款,或者在《刑法》第234條之一中增加一款,規(guī)定單位犯本罪的,處以罰金,對涉案個人根據(jù)上述規(guī)定處罰。?當(dāng)然,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在傳統(tǒng)上都被視為自然犯,能否由單位實施在理論上存在爭議。由于此問題已經(jīng)超出了本文的主題,所以不在此論述。
其次,針對上述第三種違法行為類型中過失犯罪的情形,在規(guī)定醫(yī)療事故罪的《刑法》第335條中增加一條,作為《刑法》第335條之一,增設(shè)器官移植審查失職罪,規(guī)定“醫(yī)療機構(gòu)不履行法定審查監(jiān)督義務(wù),致使人體器官被非法摘取、移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依照前條規(guī)定處罰”。本罪在客觀層面,表現(xiàn)為醫(yī)院等醫(yī)療機構(gòu)不充分履行上述《條例》第11條、第18條等規(guī)定的審查監(jiān)督義務(wù),導(dǎo)致人體器官違法行為的發(fā)生;在主觀層面,則表現(xiàn)為醫(yī)療機構(gòu)已經(jīng)或者應(yīng)該預(yù)見到自己不充分履行法定義務(wù)可能會產(chǎn)生危害后果,但是沒有采取合理預(yù)防措施,而導(dǎo)致了危害后果的發(fā)生。
再次,實施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等犯罪行為者,無論是醫(yī)院還是個人,通常都是為了追求金錢利益。但是如上所述,在《刑法》第234條之一規(guī)定的四個罪名中,僅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規(guī)定了罰金與沒收財產(chǎn)。從“只有能夠消除犯罪原因,才有可能論及有效的犯罪預(yù)防政策”?[日]大谷實:《刑事政策講義》,弘文堂1996年版,第85頁。的角度出發(fā),建議在《刑法》第234條之一增加一款,規(guī)定對實施本條規(guī)定之罪者處以罰金,沒收非法所得。
這里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如何防止醫(yī)院通過提高醫(yī)療服務(wù)或者醫(yī)療器械的價格將罰金轉(zhuǎn)嫁至患者頭上?如果這一問題不能有效解決,在人體器官犯罪中對醫(yī)院判處罰金就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不但不能對醫(yī)院形成有效威懾,反而增加了公眾的經(jīng)濟負(fù)擔(dān)。就如有的學(xué)者所言:“機關(guān)的任務(wù)是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zhuǎn),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對機關(guān)進行經(jīng)濟處罰,只能損害機關(guān)行使職能的能力,最終損害國家和人民自身的利益,因此,必然迫使國家追加對機關(guān)的經(jīng)費支出,這無異于國家把金錢從這個口袋裝入另一個口袋,沒有實際意義,也達不到懲罰教育的目的,而且有損于國家機關(guān)的威信”?左振杰:《論國家機關(guān)不能成為犯罪主體》,載《西安社會科學(xué)》2008年第26卷第4期。,作為公共機構(gòu)的醫(yī)院的場合,情況亦是如此。
就此,筆者建議在此類單位犯罪案件中增設(shè)單位緩刑制度,以避免上述負(fù)面效果。?法人緩刑制度在英美等國早已存在,并在避免罰金的負(fù)面效應(yīng)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See, for example, Fisse, B. Sentencing Options against Corporations. Criminal Law Forum, 1990, Vol.1, No.2, pp. 211-58. Wray C. A. Corporate Probation under the New Organization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Yale Law Journal, 1992, Vol. 101, No.8, pp. 2017-2042.我國《刑法》第72條規(guī)定的緩刑制度以自由刑為基礎(chǔ),僅適用于自然人犯罪。為了避免罰金的溢出效應(yīng),應(yīng)對犯罪單位不能支付或者通過特殊手段轉(zhuǎn)移罰金等情況,可以考慮在第73條之后插入一款,作為第73條之一,規(guī)定法人緩刑制度,即在認(rèn)為合適而且必要之際,法院可以向犯罪單位發(fā)出緩刑令,并規(guī)定如下一項或幾項條件:(1)提供補償;(2)設(shè)計并實施特定的措施減少其犯罪行為造成的損害并進行補救;(3)制定具體的政策、標(biāo)準(zhǔn)與程序預(yù)防類似犯罪的發(fā)生;(4)以法院確定的方式披露關(guān)于其犯罪與量刑等相關(guān)信息;(5)遵守其他法院認(rèn)為有利于預(yù)防犯罪或減少、補償其造成的傷害的條件。?鑒于本文的主旨是論述醫(yī)院的刑事責(zé)任與立法改革,關(guān)于法人緩刑制度的具體建議,筆者將另行撰文論述。
具體到人體器官犯罪的場合,如果法院認(rèn)為對涉案醫(yī)院判處罰金可能導(dǎo)致其經(jīng)營困難或者存在醫(yī)院通過提高醫(yī)療服務(wù)或者藥品價格轉(zhuǎn)移成本的可能性,則可以在認(rèn)定法院有罪的同時,對之發(fā)出緩刑令,要求其以金錢以外的方式對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親屬作出適當(dāng)補償,制定具體措施保證相關(guān)部門與醫(yī)務(wù)人員遵守器官移植法規(guī),充分履行法定義務(wù),并要求醫(yī)院履行相關(guān)的社會義務(wù),例如向特定患者群體提供義務(wù)醫(yī)療服務(wù)、醫(yī)療咨詢等。
五、結(jié)語
醫(yī)院在人體器官違法行為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質(zhì)疑的。一方面,醫(yī)院是器官移植的合法主體,不但承擔(dān)著審查器官摘取與器官移植合法性的法定義務(wù),而且承擔(dān)著具體摘取與移植手術(shù)的任務(wù);另一方面,醫(yī)院最熟悉受體的情況,如果缺少醫(yī)院提供的信息,供體與受體之間很難達成協(xié)議,犯罪行為就不會產(chǎn)生經(jīng)濟效益。因此,在幾乎將法人刑事責(zé)任延展至所有犯罪的英美法系自不待言,在大陸法系也已經(jīng)有許多國家就非法器官移植的行為處罰包括醫(yī)院在內(nèi)的法人。例如,日本1997年制定《器官移植法》第24條特別規(guī)定,在法人的代表人或者管理人,法人或者自然人的代理人、使用人以及其它從業(yè)人員,在與法人或者自然人相關(guān)業(yè)務(wù)方面實施該法規(guī)定的禁止性或者義務(wù)性規(guī)定之際,除了處罰行為人以外,對法人也應(yīng)判處罰金。
雖然在中國現(xiàn)有立法框架下,在醫(yī)院實施人體器官違法行為之際,可以刑事處罰組織者、策劃者與實施者,并追究其民事責(zé)任。但是,現(xiàn)有立法并不能真實地反映醫(yī)院在人體器官犯罪中的地位與作用,在人體器官犯罪能夠帶來的暴利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同時,隨著死刑犯不再被允許作為移植器官來源,在人體器官捐獻率較低的情況下,人體器官的供需矛盾將會進一步擴大,非法人體器官買賣將會產(chǎn)生更大的利潤,這也意味著將有更多的組織與個人會鋌而走險。因此,必須加大對人體器官犯罪的懲治力度。從整個犯罪鏈條來看,只有緊緊抓住器官摘取與器官移植這兩個主要環(huán)節(jié),將醫(yī)院與醫(yī)生作為重點預(yù)防對象,才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效果,因為與街頭犯罪不同,良好的醫(yī)學(xué)培訓(xùn)與醫(yī)療設(shè)備是完成人體器官犯罪的必要要件。
一言以蔽之,立法機關(guān)應(yīng)該將包括醫(yī)院在內(nèi)的單位列為現(xiàn)有人體器官犯罪的主體,突出其在整個犯罪鏈條中的作用,并針對實踐中醫(yī)院倫理委員會不認(rèn)真履行法定義務(wù),導(dǎo)致虛假“親情移植”泛濫的情況,在醫(yī)療事故罪之后,增設(shè)器官移植審查失職罪,促進醫(yī)院對器官移植與摘取的合法性進行實質(zhì)審查。與此同時,針對其背后的經(jīng)濟動機,立法機關(guān)應(yīng)該將罰金與沒收財產(chǎn)規(guī)定為人體器官犯罪的法定刑。此外,為避免罰金的溢出效應(yīng)與應(yīng)對醫(yī)院不能支付罰金等特殊情形,立法機關(guān)應(yīng)考慮引入法人緩刑制度,要求被告醫(yī)院履行一項或數(shù)項判決書具體載明的條件,以代替繳納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