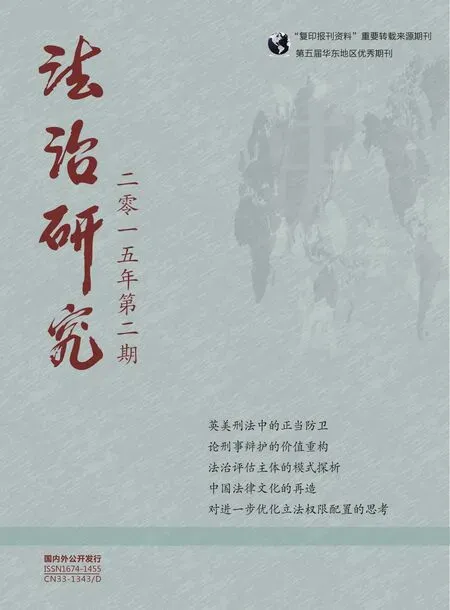環境刑法論綱
陳曉明
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關注的問題,環境問題的本質是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隨著科學技術和經濟的迅猛發展,環境問題也日趨嚴重。環境問題的蔓延及其危害的加劇,不僅影響和制約著各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而且對人類的自身生存也構成嚴重威脅。在環境問題日趨嚴峻、環保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人們不得不反思傳統的對待自然環境的態度與方式。
保護環境的目的在于保障人類自身的生存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此,世界各國刑法均規定了環境犯罪,以回應人類保護環境的訴求以及對自身利益的關切。近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在創造極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每年發生的環境事故極多,但真正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卻極少。究其原因,源自多方面,但其中我國現行的環境刑事立法,包括立法價值、立法模式、立法技術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應是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更好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環境保護領域的作用和如何借助刑法對環境犯罪進行有效規制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概念厘清:公害犯罪VS環境犯罪
與環境有關的犯罪早期普遍稱為公害犯罪。“公害”一詞源自日本,是借用英美法中“公共妨害”(Public Nuisance)一詞而創用。公害泛指各種因企業的生產活動而致環境污染或破壞從而造成公眾受害或遭受危害可能的狀況。因此,一般包括“公眾受害”、“環境污染和破壞”和“產業活動”三個要素。
公害犯罪首先出現于日本1967年制定的 《公害對策基本法》,隨后又出現于1970年制定頒布的《關于危害國民健康的公害犯罪處罰法》(簡稱《公害罪法》)。日本的《公害罪法》在形式上屬世界首例,在立法上也有一定突破,比如設立了針對環境的特殊因果關系推定原則以及實行雙罰原則等,但由于價值觀念的問題,該法僅以公眾的生命和健康作為保護對象,將處罰限定在危害生命和健康范圍內,沒有將環境法益納入其中。該法第1條即明確規定,本法的目的在于通過對在各種事業活動中所引起的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的公害行為的懲罰,以保護人體健康,防止公害。可見,公害僅指“人為活動帶來的環境污染以及破壞為媒介而發生的人和物的損害”,①[日]原田尚彥:《環境法》,于敏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結果是公害犯罪“囿于危害人體健康為處罰之法益保護范圍,而不及于自然環境保育之危害犯罪”②柯澤東:《環境刑法之理論與實踐》,載臺灣《臺大法學論叢》1989年第2期。。
隨著人們對環境問題認識的深入,逐漸認識到環境保護不能只停留在防范公害層面,而應對環境進行全方位的保護。因為環境各部分是一個互相聯系和依賴的整體,對于其中某個系統的損害,就可能影響其他系統,進而可能對整個環境造成影響。比如,有毒化學廢棄物的排放可造成土壤或水質污染和殘留,有毒化學廢氣逸散可被人類、植物、動物以及微生物直接或間接吸收,經由復雜與相互依存的構成分子,組成生物鏈循環網絡,彼此結合相互依存,再與非生物環境結合,可使整個自然生態環境遭受危害。這應驗了環保先驅貝里·湯瑪斯曾提出的生態學四大原理,即:(1)萬物相互關聯;(2)萬物皆有其去處(例如汽車廢氣看似消失,但其實是進入大氣并促成溫室效應);(3)最了解自然界的是其自己(例如許多看似“無用”的物種可能極有生態價值);(4)萬物皆有代價。③Berry,Thomas(1988),The Dream of the Earth.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p.67.可見,環境問題帶來的危害可能是全局性的和整體性的,它所侵害的不僅僅是人身或財產權利,更重要的是它破壞了生態平衡以及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因此,許多國家已將環境保護的政策由控制公害轉變到對整個環境的保護,由此環境犯罪也就應運而生。
環境犯罪并不是法律規定的某種具體罪名,而是一個集合性概念,是所有危害環境的犯罪的統稱。所謂環境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和非生物的組成,包括空氣和所有的大氣層、水體、土地,包括土壤和礦物資源、動物界和植物界,以及所有在這些組成其內部的生態關系。④鄭昆山:《從國際刑法會議抗制環境犯罪決議文,論我國環境刑法之檢討與展望》,載臺灣《律師雜志》1997年8月第215期。它們相互聯系,互相影響,共同組成了一個整體。環境犯罪的本質在于生態環境作為整體受到損害,破壞了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與安全,從而影響到人類的生存環境,而人類利益僅僅是作為生態環境中的一部分而受到侵害。
一般來說,環境犯罪包括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兩大類。前者是指有害物質在環境中擴散、遷移使環境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發生變化,進而對人類或其他生物產生不利影響的情況。比如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后者主要指人類的社會生產活動產生的有關環境效應,進而導致環境功能與結構的變化,從而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的情況。比如過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過度砍伐引起的森林銳減等以致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情況。
環境犯罪具有如下特征:
1.高科技性。環境問題伴隨著科技的發展而來,科技越發達,環境問題也越復雜。而且,環境問題的預測與評價也對科技具有高度依賴性。因為很多環境問題的作用機理涉及到專業技術,有些環境犯罪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厘清從污染到侵害的具體過程和作用機理。此外,環境刑法在立法過程中對于不同行為類型的環境危害評價也受制于科技領域的認知水平,而且在司法過程中的環境危害評估、因果關系的判斷也受限于科學上的認知與判斷。
2.經濟相關性。環境問題是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產物。環境犯罪不同于一般傳統犯罪,屬于現代型犯罪。大多數環境犯罪與經濟利益密切相關。人類在資源開發和利用以及生產活動中無時無刻不在產生環境問題。比如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為降低生產成本,獲取高額利潤,追求經濟利益,節省污染防治費用而排放未經妥善處理的廢水或任意丟棄毒性廢棄物等等。因此,環境問題實際上是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副作用與負面效應,是人類在實踐中主動創造出來的不可避免的伴隨性結果。因此,在經濟學上常被稱為“社會成本”,為此,德國法學界將環境犯罪視為經濟犯罪的一部分。
3.國際互動性。環境危害后果具有空間上的延展性,即全球性的特征。國際化、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整個地球和太空環境成為一個共享的公共資源平臺,致使環境破壞和污染所造成的后果在地域上會不斷蔓延,超越地理邊界和社會文化邊界的限制。因此,環境問題已成為一個超越國界的問題,可能引起國際性災難,并對全球的生態環境產生長遠的影響。
4.高決策風險性。環境問題通常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許多環境上的危害行為往往是在經年累月后才被發現。如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生態失衡、環境污染等都要經歷一定的潛伏期,即從行為發生到結果的顯現要經過很長一段時期;而且危害結果出現后,又往往不會立即消失,危害長期持久地存在。同時,對環境影響的評估與預測、環境質量標準的設定也受制于科技水準及企業的技術能力。因此,涉及環境問題的決策具有濃厚的風險意味。
5.高利益沖突性。環境問題涉及多種利益沖突,比如價值沖突、行業沖突和代際沖突等等。環境問題自始就表現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質,直接或間接將地域間、產業間、利益團體間以及抽象或具體的價值之間的沖突緊緊聯系在一起。在這種整體連帶的背景下,環境的相關決策就涉及復雜的利益權衡,需要統籌兼顧各種利益。
6.高度行政依附性。環境刑法對于環境行政法律規范具有高度的依附關系。環境問題不僅涉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而且涉及到不同世代間的資源分配,甚至還涉及到如何看待生態環境的觀念問題,因此無法以單純禁止的形式進行,而是帶有濃厚的政策意味。環境政策是國家應對環境問題的策略與手段,而環境刑法是落實環境政策的一種工具。盡管環境問題的應對措施日趨多元化,但由環境問題的特點所決定,行政規制目前仍是最基本和最適合的環境管制手段。因此,對環境質量標準的設定及企業行為的規制,經濟發展與環境危害的利弊權衡,多元利益沖突下各方利益的統籌權衡,都必須由政府主導。環境刑法對于環境政策的從屬性意味著環境刑法必須建立在行政法規基礎之上,其行為的違法性判斷、責任主體等都需要依賴于行政法規才能加以確定,刑事制裁只不過是行政規劃一連串程序中最末端的一個環節。
公害犯罪與環境犯罪主要區別在于:
1.范圍不同。公害往往僅限于企業或工業生產活動對民眾生命和健康造成的損害,比如生產有毒、有害食品被稱為食品公害,生產不良藥品被稱為藥品公害等等;環境犯罪無此限制,只要是人類活動即可。
2.保護對象不同。公害犯罪從刑法保護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功能出發,以民眾的生命、健康以及財產作為保護的對象,希冀通過對人的基本權利保護來達到對于環境保護的目的。環境犯罪則是將水、土壤、空氣等環境要素納入環境中而對環境的整體進行刑法保護,也就是說打擊環境犯罪著重保護環境生態系統自身,并不要求該行為與人類利益存在任何聯系便可證明刑事制裁的正當性。⑤趙秉志、王秀梅:《環境犯罪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頁。
3.保護法益不同。公害犯罪侵害的法益僅限于傳統法益,即人類的健康、生命或財產法益等,而不及于可能入罪化之行政犯或環境法益在內。⑥鄭昆山:《論我國環境犯罪防制之道》,載臺灣《東海法學研究》1995年第9期。所以,是否導致了民眾生命健康受損,或者是否已使民眾的生命或健康處于危險狀態是判斷公害犯罪成立與否的標志。而環境犯罪是把侵犯環境利益作為環境違法行為入罪的條件。誠如臺灣學者林山田所言,“環境刑法所保護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體法益或財產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謂之‘環境法益’,由于生態環境之破壞,將足以導致生命、身體或財產之危險,故以刑法保護環境法益,亦屬間接地保護個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法益”⑦轉引自王秀梅:《臺灣環境刑法與環境犯罪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1999年第3期。。
由此可見,公害犯罪的設立是希望通過直接保護人類利益而間接保護環境生態,而環境犯罪的設立則是希望通過直接保護環境利益來間接保護人類自身。兩者的不同除了范圍的不同,即公害犯罪實際是環境犯罪的一部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價值觀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對法益認知的不同。環境犯罪將環境整體作為一個具有獨立價值的法益予以保護,是對傳統法益保護觀念的突破,充分反映了人類對環境價值認識的變遷。
二、立法價值:現實經濟利益VS可持續發展
價值,從哲學范疇來說,是指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積極意義或客體的有用性。⑧張文顯:《法學基本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頁。實際上就是指滿足人和社會需要的一種屬性。價值取向受制于社會制度、社會環境、歷史文化、個體意識等多種因素,這里既包括社會條件等客觀因素,也包括功利、情感、道德等主觀因素。所以,價值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調整、充實與豐富。價值決定著人們的思想取向和行為選擇。因此,價值也決定了有關環境犯罪的立法與司法。
(一)傳統發展觀與可持續發展觀
環境刑事立法的最根本難題在于“規范需求”本身牽涉到兩種相沖突的價值取向,即追求現實經濟利益還是可持續發展。當然這兩種價值并不完全對立和抵觸,但在規范價值選擇時,偏向一種價值實際上自然會影響另一種價值,保障一種價值勢必會損害另一種價值。因此,立法時首先必然面對價值選擇和預設問題。
在傳統的發展模式下,基本的目標就是物質財富的增加,也就是追求現實的經濟利益。在這種信念的驅動下,“為什么發展”和“什么是好的發展”等一些有關價值論的問題卻往往被忽略。因此,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于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缺乏全面而長遠的認識,專心致力于追求經濟的高速成長,把破壞和污染環境為代價的局部、現實的經濟利益作為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否有利于經濟發展成為一切工作的評價尺度。
環境危害往往都是發生在促進經濟發展的生產活動中,被視為謀求經濟發展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而且,環境危害由于受害者眾,缺乏危害的直接性和直觀性,倫理色彩不強,難以激發公憤,所以,往往不僅能為政府所寬容,同時也能為社會公眾所忍受。因此,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發生沖突時,基于眼前經濟利益的考慮,人們往往傾向于前者。優先發展經濟的政策一方面確實會給經濟帶來發展,但同時也會因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從而導致環境污染事件頻發成災。生產的高速發展以及經濟主義的算計,就會促使人們置環境危害于不顧,久而久之就會造成人與自然的高度分裂,其結果是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最終會導致人類自身生存的危機。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出現過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沖突,是發展經濟為主,還是保護環境優先成為許多國家艱難的選擇。日本早期對公害沒有警覺而任其發展,致使戰后的日本環境遭到極大的污染和破壞,在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下,日本經歷了從“經濟優先”(1967年《公害對策基本法》)到“環境優先”(1970年《公害對策基本法》)的發展過程。
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發展,環境問題給人類帶來的危害日益凸顯,并造成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諸多危機。人們開始認識到,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今天,在由人類自己親手制造的環境危機面前,人類面對的主要任務已經不再是物質生活的富足,而是如何使發展能持續下去并讓后代能夠生存下去。于是,人類開始重新審視環境危害問題,并以新的視角去探索和創新環境保護機制。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聯合國在20世紀80年代從環境與自然資源角度提出的關于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主要包括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作為一種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觀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資源、人口等諸多領域的全新的理論體系,是在人類生存與發展面臨巨大的環境壓力與威脅的背景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是一種以人為主體和中心的發展觀,它確立的是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和諧相處的觀念,追求的是自然環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要解決的是人類無限發展的需求和自然資源有限性的基本矛盾”⑨傅華:《生態倫理學探究》,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頁。。可持續發展“既要有滿足人們的普遍需求的發展,又要有約束性的限制以保證持續,即必須兼顧發展與持續,兼顧需要與限制,是發展與持續的統一,滿足需要與實現限制的統一”⑩陳昌曙:《哲學視野中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頁。。
可持續發展觀與傳統發展觀的不同在于:傳統發展觀所追求的目標是單一的、有限的和現實的,它過于關注人類自身的利益,對自然的利益關心不夠;過于關注當代人的利益,對后代人的利益缺乏考慮。而可持續發展觀跳出了“人類自我”的圈子,所追求的目標是全面的和長遠的。就環境保護而言,它強調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時應有限度;就經濟發展而言,它強調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發展的最基本任務;就人的生存發展而言,它強調既要解決好同代人之間的生存發展問題,又要解決好上代人與下代人之間的生存發展問題。因此,可持續發展觀不再純粹地割裂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兼顧這兩種關系,“旨在促進人類之間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世界與環境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王之佳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頁。。可持續發展觀凝結了生態學、經濟學以及環境學的思想精華,是人類在面臨生態危機的形勢下對傳統發展觀作出的一次重大調整。這種理念不僅應當成為現代各國完善環境法體系的長遠目標,而且理應成為環境立法和環境實施中應當具體體現的一項基本原則以及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的價值觀。?金瑞林、汪勁:《中國環境與自然資源立法若干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二)可持續發展理念下的刑法價值追求
作為一種現代發展理念,可持續發展觀提出以后,就以其強大的生命力滲透到生態學、經濟學、社會學、科學技術等社會的各個領域,法學也不例外。可持續發展觀要求環境刑法突破過去只重視短期利益和人身利益保護的局限,在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沖突時拋棄短視的價值取向,著眼于長遠利益和生態利益。因為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科技等發展的根本所在,其他方面的發展最終都要歸結在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上。
可持續發展觀決定了環境刑法的基本目標是保護包括環境利益與人類利益在內的生態環境整體利益,維護人與環境的和諧。具體來說包括下列三個方面:
1.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觀清楚地表達了必須重新認識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及人與自然的聯系方式,主張重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公平要求將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羅伯特·科林:《關于環境種族主義、環境公平和環境正義法律文獻評論》,載呂忠梅:《環境資源法論叢》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頁。它把人與自然視為一個整體,不僅重視人的生存與發展,也重視環境對人類的重要性,尊重生態環境的獨立存在價值。因為人類與自然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惠共生的關系,人類必須尊重與善待自然。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實質是指人類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應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應是和諧相處而非相互競爭的關系,所謂“人本取向”與“環境取向”應是一種取舍與比重的問題,而非處于完全對立的狀況。實現這種和諧完全取決于人類是否能夠尊重環境生態規律,并進而能夠維護環境生態利益。
2.維護人類的基本利益。可持續發展觀在一如既往地關注當代人利益的同時,也強調保障后代人利益,其基本要求是當代人在滿足自身發展需要時,還要保證后代人也能夠有機會滿足他們的利益需要,即要求當代人對后代人負責,發展經濟一定不可將潛在的環境享受成本轉移給未來的世代,決不能超越生態系統的負荷能力求發展而斷送后代人的生存發展機會。這也是為了實現代際公平,誠如美國學者魏伊絲所言:“作為物的一種,我們與現代的其他成員以及過去和將來的世代一道,共有地球的自然、文化的環境。在任何時候,各世代既是地球恩惠的受益人,同時也是將來世代地球的管理人或受托人。為此,我們負有保護地球的義務和利用地球的權利。”?[美]魏伊絲:《為了未來世代的公正:國際法、共同遺產、世代間公平》,汪勁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頁。
3.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為了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必須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發生。人類必須利用環境,利用天然資源始能生存,但是經濟、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環境和自然資源條件的制約,如果人類毫無節制破壞環境或耗盡自然資源,有朝一日就會受到自然環境的報復。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取決于生物及物理定律,人類經濟開發必須服從這些自然的界限,才談得上可持續發展。因此,人類必須合理開發利用,也就是人們在開發利用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過程中,要把開發利用與保護結合起來,應當根據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特點適度進行開發,在開發利用過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產生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浪費,以提高資源的再生補給能力,實現資源可持續利用,促進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
總之,環境刑事立法既要有生態的觀念,又要有經濟和社會觀念,要注意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協調社會、經濟發展,把人類活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限制在最小范圍內,維護生態平衡,促進和保障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因此,環境刑事立法的基本目標應是多元的,要兼顧多方面利益。
三、立法目的:事前預防VS事后治理
立法目的是法的價值理念的集中體現與直接表達,是法的價值理念的外化。任何刑事立法都要實現特定的社會目標,也就是要發揮積極解決社會問題的作用,而不是一般地解決刑法的懲罰性問題,因為所有刑法規范的存在都不是為了存在而存在,而是為了某個目的而存在。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人類對于各種危險的掌控及預測能力不是越來越強,而是越來越薄弱,對于未來的危險也越來越難以提前做好準備。環境問題已經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境遇和生活體驗,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危機應對理念和治理模式,因此,刑法的目的也應適時進行調整。
傳統應對環境問題的方式是事后治理。西方國家過去大都走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整治”,“先開發、后保護”的道路,相關國家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主要是因為環境犯罪具有完全迥異于普通犯罪的特質,其危害范圍大且難以估量,而且具有長期性和隱蔽性,更為重要的是危害后果一旦發生,具有不可逆的特點,損失將無法挽回。比如,現代科技所引起的廢氣、廢水、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嚴重的環境問題,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已大大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環境問題,甚至已超過了環境的承載負荷能力以及自然界和人類的自我修復能力,從而長期或永遠使生態不能復原,致使后代去承受惡果。通過治理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會有所改善,但是代價高昂并且無法根治。
由于事后補救已達不到刑法保護的目標,因此,國家治理環境問題的方略就應當有所調整并采用不同于傳統犯罪的對策。國家作為公共利益和社會安全的維護者,一方面必須創造有利于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推動社會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卻又不能無視環境問題帶來的各種危害,必須建立適當的防范和預防機制,以對環境問題作出適度地回應。這就決定了刑法的工作重心應有所調整,即從事后懲治轉向事前預防,從原先僅扮演對于法益侵害的事后處理的角色,逐漸轉變為以預防功能為主的主動角色,也就是防范措施的提前。透過這樣的轉變,可以盡可能減少和阻止環境問題的發生,切斷環境問題通往實害之路,表明刑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防止災難或不幸,從而保障社會的安全。所以,“今天的刑法不僅是對侵害的反應,而且它還有這樣的任務:使保障社會安全的基本條件得到遵循”?[德]烏·金德霍伊澤爾:《安全刑法:風險社會的刑法危險》,劉國良編譯,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3期。。在今天各國的刑事立法中,提高刑事立法對預防犯罪的有效性已成為現代刑事立法的發展方向。?張明楷:《刑事立法的發展方向》,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4期。防范危險應是刑法在現代社會的一項重要的功能,作為國家管理的一種手段,刑法不能無視國家危險控制和防范的需要。這就是說,刑法不能僅僅是對侵害的被動反應,還應作為危險控制的工具,積極承擔起保障經濟發展和環境安全的重任,因為 “保障安全始終是政府對其公民最重要的承諾,對威脅生命、健康、財產的因素予以排除也是政府的基本任務”?[德]漢斯·沃爾夫等:《行政法》(第一卷),高家偉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30~31頁。。
毋庸諱言,刑法的預防導向會導致刑法適用范圍的擴張,可能引發與傳統刑法基本價值產生沖突的疑慮。在預防危險機能的引導下,環境犯罪的不法已經從具體的實害轉變為可能的損害,從原來法益侵害為原則轉變為法益危險為原則,從有法律始有犯罪的消極層面轉變為有危害必有刑法的積極層面,致使刑法在某些情況下由最后手段性變為最先手段性。雖然這種方式能使刑法成為安全保障法并能對新的類型犯罪進行積極活用,但如此一來,不僅犯罪范圍被擴大,而且造成以實害為中心的刑法消解,代之以懲治行為人的單純違反規范的行為,從而與刑法的謙抑性產生沖突。
確實,刑法不能僅僅具有防范的功能,還應有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保障人權的機能。因此,有必要對環境刑法與傳統刑法進行調和,找出刑法的合理界限,并在各種機能間取得適度的平衡。為此,一方面,為了防范環境問題,可以提升刑法的工具性價值,適當運用刑罰前置化的立法方式,以確保刑法機能最大限度的有效性,因為如果刑法不能適度地發揮社會安全的維護機能,也有喪失正當性的危險;但另一方面,在適用刑罰前置化的同時,也應防止刑法機能的無限擴大,盡量避免刑罰的不當擴張和矯枉過正,防止刑罰過剩化。因此,環境刑事立法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以在人權保障與環境安全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
(一)相當性原則
制定環境刑法是為了保障生態的安全,而保障生態安全既不能以犧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為代價,也不應以民眾的基本權利受到過度損害為代價。在動用刑罰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各種利益的沖突,在存在雙方或多方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就有了諸利益之間價值的衡量判斷問題,因此,環境犯罪的建構應作損益衡量。所謂損益衡量就是要對利益與危險以及犯罪建構所預防的危險和建構后可能產生的新危險進行比較,不僅要考察行為給社會與民眾利益帶來的可能損害,還應考慮行為給社會和民眾帶來的利益;不僅要考察因犯罪建構給社會帶來的安全利益,還要考慮因犯罪建構可能給民眾帶來的基本權損害。通過衡量和比較的方式尋找國家介入的時間點。當然,利益衡量并不屬于精準無誤的科學法則,而是一種抽象的價值判斷,因為社會的進步以及生命、自由乃至生態環境等無法用經濟價值來換算。
通常,刑法所欲保護利益的重要性程度以及保護利益受到損害的危險程度應是主要的考量因素。利益的重要性程度越高、受損害的可能性越大,保護的必要性也就越高。總而言之,應適度地允許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但如其對社會和民眾利益的可能損害明顯超出合理范圍,就應當予以禁止。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例,國家一方面基于生產發展的需要不應對開發單位作過度限制,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生態環境保護和當地居民的人格權和生存權,也就是要均衡兼顧經濟開發利益與環境生態價值。在保證環境生態與生活質量的前提下,允許有限度開發,而禁止毫無節制的亂采和亂伐,以防止發生無法承受的危害后果。
(二)典型性原則
環境犯罪建構應是一種動態性和漸進性立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動態過程。鑒于環境危害大多情況下并非一個現實的危害,犯罪建構應當有所節制,保持適當的靈活性和彈性,現階段只應將一些典型的、社會有共識的環境危害行為納入刑法的規制范圍,就是說,只能將可能對社會危害重大,對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形成典型危險性的行為納入法律的范疇。
刑法要堅決避免“現象立法”,不能因為現實社會中出現某些特別現象時,立刻就以危險犯的立法方式將之規范。只有那些經過長期社會生活經驗檢驗的形成了普遍共識的典型危險行為才應該入罪,以具備正當性。所謂典型危險行為是指具有高度實害可能性的重大危險行為。污染環境或破壞生態行為之所以典型,就在于現實世界的無法把握和控制,從而可能的危害具有不可預測性。典型危險行為的判斷和確定是其中至為關鍵的問題。判斷的依據主要是環境危害行為的性質,看其是否可能造成嚴重的或者不可彌補的后果。對這些行為,即使發生事故的概率很低,但在無法排除危害可能性的情況下,也應當有所防范,以避免給社會和民眾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所以,應當根據環境危害行為性質確定防范的強度和選擇相應的措施,屬于典型行為的,納入刑法調整范圍,對于現階段無法把握的,或者可由民事或行政領域處理的風險,都不納入刑法規范之中。
(三)規范化原則
實現環境保護和人權保障平衡的關鍵在于環境危險行為的規范化,也就是將危險通過法律規范標示出來,并以實施特定行為所產生的象征標示作為刑法發動的條件。賦予環境危險行為規范性意涵,不僅可以藉由合法與非法二元符碼,預先標明犯罪的標準,從而提供清晰而穩定的可罰性界限,而且可以明確相關行為人的責任,確保環境危險行為可以成為歸責的基礎。規范的確立是歸責的起點,而歸責又以規范效力的預設,建立起國家為了預防危險而作出干預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如前所述,環境刑法具有高度的行政依附性,環境問題的特殊性使得行為違法與否、程度如何的判斷都無法脫離與行政規范的聯系。因此,在規范化問題上完全可以借助行政法規,即“以行政法規規定的標準”作為對危險判斷的依據,比如只要投棄、排放的毒物或其他有害物質超出行政法律規定的標準,即認為事實上危險已經產生,也即行政法規確定的標準或限制,成為判斷刑事不法的核心。通過這種立法方式,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另一方面又使立法者得以隨時針對環境的改變、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觀念理念上的變化作出靈活的調整,使刑法可隨著行政法規,迅速對環境問題作出回應,達到保護環境之功效。
四、立法策略:行為取向規范VS結果取向規范
傳統法治理念指導下的刑法是一個自我完結而封閉的體系,重結果而輕行為,重實害而輕預防,因此,法益的實際損害是犯罪的實質要件并以此作為可罰性的界線,因而所建立的是一個以實害為基礎的實然刑法體系。將刑法定位于對犯罪的被動反應位置,反映在環境刑事立法中,就是將環境犯罪設置為實害犯,即把環境危害行為是否侵犯人的某種權益以及侵犯的程度如何作為評價是否構成犯罪的標準,也就是要對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造成實際損害作為環境犯罪成立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造成重大實際危害結果而僅存在造成重大實際危害結果的危險,則不構成犯罪。這就導致刑法反應的時機滯后,對于環境問題的防范,不免力有不逮。一個以實害為基礎的實然刑法體系,是無法滿足刑法對環境應然保護要求的,如果等到實害發生,則重大的損害已無可彌補。為防止這種不可彌補局面的發生,刑法就要改變“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思路,在策略上進行重新調整,以彌補先前的不足。
為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以行為為取向將環境犯罪設定為危險犯類型也就成為必要,這意味著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污染環境或破壞生態的行為,即使沒有造成嚴重后果也構成犯罪。危險犯并不關注個案中所發生的危險結果,而是注重行為的種類,或者說危險犯強調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本身的性質,并不注重該行為所引起的外界變動。危險犯的“危險”并非由個別行為去觀察,而是基于大量的觀察,從經驗上顯示,某一類行為易造成被保護法益之實害,便認為這一類行為帶有一般危險性?東茂:《危險犯的法·性質》,載臺灣《臺大法學論叢》1995年第1期。,也就是通過事前的判斷直接將該類行為擬制為危險行為。因此,當行為人一旦實施該類行為的時候,在法律上就可以認定其有危險結果的發生。所以,就環境犯罪來說,對于污染環境和破壞環境行為的犯罪性的確定,并不必直接對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等法益造成侵害或對環境生態的現實破壞,而是根據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以及人類以往的經驗,僅需根據行為的性質加以確定。
對危險犯而言,行為方式本身即是可罰的,雖然沒有造成實害,卻制造了客觀危險,誠如學者所言,“在這些犯罪當中,犯罪分子的行為已經把行為客體帶入了危險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特定財產的損害還只是一種偶然性,盡管如此,刑法還是要對行為人施以刑罰,這是因為行為人客觀上促使了這種危險狀態的形成”。?薛曉源:《法治時代的危險、風險與和諧——德國著名法學家、波恩大學法學院院長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教授訪談錄》,載薛曉源:《當代西方學術前沿研究報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頁。因此,行為的可罰性基礎不再以實害為核心,而在于行為人主觀上的不法意志與客觀上的典型危險行為。之所以這樣設定是因為環境危害行為的后果具有不可恢復性和不確定性,為了預防實害的發生,就有必要對這種行為加以禁止而直接入罪,也就是通過事前的判斷直接將該類行為與危險加以連結并規定為犯罪行為。這樣的設置可以對法益作前置性的更周密和更有效的保護,加大對環境以及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保護力度,從而彌補法益保護上的不足和漏洞。因此,德國刑法學家赫爾佐格曾指出:“危險刑法不再耐心等待社會損害結果的出現,而是著重在行為的非價判斷上,以制裁手段恫嚇、震懾帶有社會風險的行為。”?轉引自林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5頁。
如前所述,將環境犯罪設置為危險犯是刑法功能性轉向的產物,這與我國傳統的立法指導思想確實有所不同,也改變了我國長期以來環境犯罪屬于結果犯的規定。我國的刑法思想向來以結果為本位,這種立法模式雖然縮限了刑法的懲罰范圍,但從預防違法犯罪角度來說,在立法層面上就打了折扣。刑法為了更有效地保護人類的環境生態安全,控制環境風險,其介入點必須提前。最佳的環境問題防范應是在危害還沒有發生,而有發生之虞的時候,或甚至僅有預見可能性時,就已經予以排除。因此,基于刑法的預防需要,對環境危害行為提前干預就成為必要選擇,對其予以刑罰處罰也就成為必然,這有助于從源頭上遏制環境危害行為,防患于未然。
當然,將環境犯罪設置為危險犯并不意味著結果無價值,造成的實害應當作為加重要素考慮。這樣的立法例在國外也十分常見,如日本《公害罪法》第2條第1款規定:凡伴隨工廠或事業單位的企事業活動而排放有損于人體健康的物質,給公眾的生命或身體帶來危險者,應處以3年以下的徒刑或300萬日元以下的罰金;該條第2款則規定,犯上款之罪而致人死、傷者,應處7年以下的徒刑或500萬日元以下的罰金。2003年修訂的《德國刑法典》第325條也有類似的規定。此種立法方式不僅可以發揮刑法的預防作用,而且也考慮到環境犯罪危害程度上的差異。因此,環境刑法規制和防范既包括已造成的實害或者已經高度現實化的危害,也包括環境危害行為可能引起的慢性危害和遠期危害。
以結果為取向的實害犯要求對法益產生實際危害結果才成立犯罪,危險犯則要求存在造成重大實際危害結果的危險即成立犯罪,也就是說刑法評價或者非難的對象從行為的結果轉為行為本身,即由結果本位轉向行為本位,行為不法將作為刑事不法的核心,行為本身被加以無價值判斷。行為不法不注重行為是否產生實害或實際危險的結果,而是立法者針對各種在性質上具有典型危險性的行為,從根本予以禁止以杜絕危險的實際發生,其不法的內涵在于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主觀上表現出了對法的敵對意識。結果不法之規范重點在于通過控制行為程度,防止實害以達到保護法益之目的。兩種規范是基于不同層次與目的而產生:前者是規范一般性的危險,旨在避免漏洞;后者則是針對特定的危險而設計,以強化對犯罪的懲罰。兩者相比,實害犯較之危險犯顯然將環境危害行為的處罰時間推后,處罰的范圍也較危險犯收窄。實害犯雖然強化了刑法的懲罰功能,但卻弱化了刑法的預防功能。
立法上以行為為取向實際上是一種刑罰前置的立法方式,不要求任何實害結果,只要求行為人的特定行為。如此不但使行為人更容易入罪,而且也大大擴張了刑罰的范圍。這一轉變會在維護安全與保障自由之間產生一定的沖突,因而引起了人們對這種立法方式正當性的疑慮。應當說,環境犯罪的建構是基于環境問題的威脅。鑒于刑法所具有的防范功能,將刑法的適用范圍作一定程度的擴張是有正當性和必要性的。在現代高度發展的社會里,環境安全的任務越來越難以實現,人類不能不依靠刑法去建構更安全的社會,刑法也就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成為一種防范危險的工具,而刑罰前置化的立法是實現其目標的一種方式。之所以采用這種立法方式,主要是基于下列幾方面考慮:
第一,基于犯罪預防目的的需要以及對于預防技術上的需求。從現實情況來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生態環境的嚴重污染和破壞,但是與之相對應的,卻是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案追究甚少,環境保護步履維艱。前置化的設置就是要讓刑法提前介入,以把環境危害制止在萌芽狀態,盡可能減少環境危害的發生。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發表的《里約熱內盧環境和發展宣言》第15項原則指出,“為了保護環境,國家應依據其能力廣泛地采用預防性方法。當有重大或不可恢復之損害威脅時,缺乏充分的科學確定性不應作為延后透過成本效益方法以防范環境惡化之理由”,從而使預防上升成為國家義務。為此,歐盟在1992年《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公約》中就確立了“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當環境污染威脅風險未被證實但卻有可能出現時,即使環境污染危害之犯罪尚未發生,只要風險是可預測的,縱使不知或不確定損害是否會發生,國家都有義務防制此風險,并采取必要性的預防保護措施。?Ben Bore,Ross Ramsay and Donald R.Rothwell (1998),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aw in the Asia Pacific,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Ltd,pp.9-12.既然保護環境已成為一項國家義務,在危險來臨的時候,國家就負有預防或降低危險威脅的責任,有義務為保護環境而用立法來排除造成危險的各種因素。因此,可以說,對環境問題采用預防原則是國家履行保護義務的實踐方式,通過預防以善盡自己的保護義務。
第二,強化刑法對社會公眾生態保護的規范指引功能,把刑法規范塑造成為“行為控制導向”的行為控制工具。刑法將環境犯罪設置為危險犯,并將從生活經驗中累積而知的具有典型危險行為予以規范化,并借此彰顯一種警示作用,就是要從預防的角度向民眾傳達訊息,特別是給領導者以警示,表明環境危害行為需要特別提防,在工作中應保持高度警惕。其意義在于強勢地貫徹刑法規范的行為指導功能,強化刑法規范的宣示作用和規制機能。德國刑法學家雅各布斯就認為,刑罰是一種維護法規范的威嚇手段,借由刑罰的威嚇效應,達到尊重規范的目的,并從對破壞規范者的處罰,強化社會大眾的規范意識,以達規范信賴之目的。?轉引自柯耀程:《變動中的刑法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頁。通過刑法規范的引導作用,使社會大眾形成新的規范意識,形成新的社會倫理秩序,在社會生產生活中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適當的防范措施,以實現保護環境的目標。
第三,避免舉證上的困難,減輕追訴機關在舉證上的負擔。在司法實務中,環境犯罪往往面臨取證困難、因果關系及責任分配難以確認等問題。危險犯是將危險通過某些特定行為標示出來,并以實施特定行為所產生的象征標示作為刑法發動的條件,就是說只要實施了法定的構成要件行為即構成犯罪。不要求結果,因此也就無需證明因果關系,大大減少了證明難度。這就有助于克服在不確定實害范圍中判斷和認定上的困難,強化刑法的實用性。因此,危險犯的設置不僅能為人類環境提供更周全的刑法保護,而且能有效避免環境犯罪建構上的偏差以及刑法適用中的困難。當然,單純為了訴訟上的便利采用此種方法不夠正當,其前提是此種行為對社會危害重大,對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形成典型的危險性。如果對此類行為還要等到實害發生,則重大的損害將無可挽回,刑法的提前介入就是為了避免這種不可挽回局面的發生。因此,國家動用刑法對付這種具有典型危險性的行為并不過當,它“把制定法看作一種用來對付當下問題的資源,也就是為了該制定法的未來著想”?[美]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頁。。另外,通過這種實體上的安排,還具有活化刑法的功能,可以與刑事訴訟相互呼應,以有利于訴訟上的貫徹。如果在訴訟上不能被實踐,從刑事政策上來說就是無用之物。?張麗卿:《刑法新探索》,臺灣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85頁。
五、現行刑法規范:調整VS創新
合理運用刑法規制與懲戒環境危害行為已成為學界和社會的一種共識。但是,是在傳統刑法框架內對環境犯罪進行若干“調整”,還是在傳統刑法框架外進行“創新”是人們面臨的一個新的課題。我國在這方面也進行了一些嘗試。比如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就進行了修改,擴大了適用范圍,降低了入罪條件。這種修改雖有積極的一面,但是,由于環境犯罪迥異于傳統犯罪的特質,這種修改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環境保護的作用有限。
縱觀我國的環境刑事立法,雖歷經修改,仍然存有以下主要問題:
第一,沒有體現環境刑法的立法價值。環境安全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居于基礎性地位。但是目前的相關立法缺乏生態保護意識,過于考慮人類自身以及眼前利益,對生態利益的保護考慮不足,更不用說后代人的權益。因此,也就根本無法體現環境立法保護法益的重要程度,嚴重弱化對社會公眾生態保護的規范指引功能,導致環境保護的力度不夠。
第二,沒有確立獨立的環境犯罪保護法益。現行刑法將保護法益局限于以人為中心的人身、財產、安全等傳統法益,沒有直接保護環境法益,沒有確立維護生態平衡、保護環境利益、正確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法律目的,這顯示出環境保護只是規范手段,不是規范目的,未能反映環境刑法的特質。
第三,關于環境犯罪的規定過于注重對環境犯罪侵害人身、財產法益的保護,而忽視了對環境利益、生態利益的保護,主要表現在將犯罪設置為結果犯和情節犯,這說明我國刑法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性還不明確,不注意通過直接預防方式保護環境,只注意通過懲罰犯罪的方式間接保護環境。這種立法模式屬于一種間接保護的性質,無法起到刑法在保護環境方面“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第四,在環境犯罪的具體規定方面,環境犯罪的范圍過于狹窄,許多對于人類長期生存發展具有決定作用的環境要素沒有納入刑法保護的視野。環境刑法采用了最狹義的環境概念,未能涵蓋《環境保護法》所提出的全部自然環境要素,未能將諸如草原、濕地、自然保護區等自然環境要素包括在內。?趙秉志、陳璐:《當代中國環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載《現代法學》2011年第6期。而且,環境犯罪的認定,仍然沿用傳統的刑法模式,因果關系、主觀罪過等并沒有考慮環境犯罪的特殊性,導致了司法實踐中環境犯罪的實際認定過少與嚴重危害環境行為蔓延呈明顯反差的局面。
綜上,環境刑事立法如果還是停留在傳統的法律模式中,不僅現有的環境刑法規范無法得到很好的實施,而且環境刑事立法本身也受到制約,難以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而從根本上進行完善。環境刑事立法必須走出傳統的立法模式,應高度重視對環境生態利益的保護,確立環境法益在環境犯罪所侵犯的法益中的主導性地位,并體現在相應的刑法規范中,如此才能發揮防范環境風險,保障環境生態安全的作用。為此,對環境刑事立法無論是在價值取向上還是在犯罪建構上都應有所突破。
(一)環境犯罪構成要素
1.法益和對象。保護法益是各國刑法的共同目標和基本任務。法益保護既是刑法的機能,也是刑法存在的根據。法益侵害是犯罪的本質所在,因此,法益的侵害與否就成為行為入罪化的實質標準和刑罰的正當性基礎。法益的存在不僅決定了立法上刑罰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決定了司法上處刑的合理性,同時也說明剝奪犯罪人權利的正當性。國家運用刑罰手段懲罰犯罪,就會對法益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刑法被定位為法益保護法。
關于環境刑法的保護法益,學界歷來有傳統法益和現代法益之分。前者以人本主義為基礎,認為法律功能的實現依賴于對人類利益的保護,因此保護的法益都純粹是與人(當代人)直接相關的利益,如生命、健康、財產等,生態環境等只能處于間接或者附屬的保護地位。后者則超越人本主義范疇,以生態學為基礎,以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為價值訴求,將環境法益納入刑法的保護范圍并作為其首要保護目標。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是因為環境問題的持續惡化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人們認識到環境要素具有獨立的保護價值,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能附屬于人類利益。否則,無助于對環境的保護,從長遠來看反而會有害于人類自身。
在現代社會,環境保護的價值訴求已經不是僅僅保護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也不是通過對人身和財產的保護間接地保護環境,環境保護的價值訴求在于對人類自身存在的保護。此外,環境刑法還有更深一層意思,即環境資源在當代和后代之間的分配問題,基于此一考量,環境刑法所保護之對象不應直接以當代民眾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之保護為限,還應包括空氣、土壤、水等環境要素以及其他自然生態、野生動植物等。因此,環境刑法不能僅限于保護人自身的利益,還應保護環境利益。
所謂環境利益是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及其在此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破壞環境行為侵害客體所蘊含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是通過侵害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狀態,損害他人或整個人類的生存權和生活質量來體現。”?趙秉志、王秀梅等:《環境犯罪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頁。從法律的規范目的來看,任何法律都無法脫離人的利益,甚至純粹的環境利益也不例外,之所以保護生態環境,主要是考慮到人類長久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因為生態環境本身具有絕對的價值。環境利益不僅包括人類利益,也包括自然利益。水、空氣、土壤、植物、動物等與人類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的環境要素都是環境利益的組成部分,都應成為環境刑法的保護對象。
環境問題造成的危害具有不確定性,但其損害的法益確是存在的,只不過是一種不確定的法益,因為在將環境犯罪設置為危險犯的情況下,對民眾的生命、健康以及生態環境等造成的是嚴重的不確定性威脅,行為人無論在客觀上還是主觀上對于法益侵害的范圍也難以判斷和控制。因此,這種法益可稱為普遍性法益,它脫離了個人法益的內容,是比個人法益更前端的社會性利益,以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以及生態環境作為保護對象,甚至不限于當世之人,還把后代納入保護范疇,因而具有現代性、復合性、公益性、大眾性和隔代性的特征。
2.主客觀要素。在主觀上,行為人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過失。但是,環境犯罪主觀方面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的復雜情況。就故意而言,是一種對危害的范圍不確定的故意。行為人對其可能的危害無法作出判斷和控制。因此,這種故意與對行為的認知是相結合的,認識到行為的性質也就認識到危險的存在,就是說行為人只要認識自己的行為屬于法定的典型危險行為,其也就存在危險的故意,行為人具有危險的故意表明其主觀上存在不法意志。應當提到的是,環境危害行為不要求實害,但是不排除實害。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不能只對實害負責,還要對不確定范圍的危險結果負責。因為行為人無論對實害還是危險均存有故意,如果行為人單純只對實害負責,就不能完整評價行為人的不法意志。就過失而言,主要是指行為人在有注意能力的情況下違反注意義務。比如,有的行為人在行為時實際上已經感受到危險的存在,卻忽略了危險的實質存在而冒險實施的情況。
在客觀上,刑法將環境犯罪設定為危險犯,實際上就是要以具體的行為形態界定不法的內涵,也就是運用“典型行為模式”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明確標定其處罰范圍,即只要查明符合構成要件行為即可,因為該行為即代表危險的存在。由于立法技術的限制,刑法中不可能羅列所有典型的環境危險行為,因此,可在環境犯罪的構成要件中設計一定數量的行政從屬要件,依附環境行政法規來決定環境行為的刑事不法并借助行政規范證明行為的客觀危險性。其中,關鍵性要素有兩個,一是“違反行政法規”,二是行為人負有“預防環境損害之義務”。前者的目的在于確定危害程度及可能性,比如 “毒物”、“有害物質”等都需要根據行政法規確立的標準加以認定。國家為了保護環境,都會規定相應的環境標準。行為人如果超越此標準,表明其公然蔑視法律法規,置公眾利益不顧,即使無法預見可能的損害后果,但其違法性已十分明顯。環境標準應根據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并結合環境的承受能力與經濟發展的需要、人類和生物的生存需要與生活需要之間的關系加以設立。后者的目的在于確定行為人違反了法規范所承載的法定義務,凸顯行為人對法益和法規范的敵視態度,以此確立處罰的正當性。
(二)環境犯罪的歸責
環境犯罪的重新建構必然引出責任歸屬問題,誰來承擔責任往往是一個難題。由于環境犯罪的固有特性,使得侵害何種法益以及侵害的程度和范圍往往難以確定,而且在證明上更是困難重重,因為環境危害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達到科學上所要求的確定性,從而導致傳統的因果關系相當理論在環境犯罪中無法勝任,使得因果關系認定在環境犯罪追訴中,成了一項特別的難題。?許玉秀:《水污染防治法的制裁構造——環境犯罪構成要件的評析》,載臺灣《政大法學評論》1992年第45期。實踐中,環境危害行為往往都發生在生產活動中,并且為集體所為,因此,司法實踐中會出現責任主體模糊和缺位,沒有人來承擔責任的問題,正如美國學者費希爾所言,“正當威脅與災難看起來變得更加迫近和明顯時,它們同時又從證據、義務和政法體制企圖捕獲它們的夾縫中溜走”?轉引自周戰超:《當代西方風險社會理論引述》,載人大復印資料《社會學》2003年第9期。。
鑒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情況,真正應該承擔刑事責任的應是環境危險的制造者,因為“欲使責任有效,責任還必須是個人的責任。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不存在任何由一群體的成員共同承擔的集體責任,……如果因創建共同的事業而課多人以責任,同時卻不要求他們承擔采取一項共同同意的行動的義務,那么通常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即任何人都不會真正承擔這項責任”?[英]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99頁。。也就是說,責任只有明確到個人才會真正得到落實,否則就會導致共同的不負責任。因此,承擔責任的主體范圍不能也不應泛化,因為“責任主體越多,每個責任主體承擔的責任就越小,而且容易造成相互拉扯,責任模糊,無人真正負責的怪現象,導致真正的責任主體缺位和虛位”?[德]烏爾里希·貝克:《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關于人類生存、社會結構和生態啟蒙等問題的思考》,王武龍譯,載薛曉源、周戰超編:《全球化與社會風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頁。。
環境危險的制造者實際上就是環境危險行為的決策者,因為危險源于人的決策。決策者之所以對危險決策的可能后果承擔責任,主要原因是:首先,決策者擁有權力,對規避危險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和選擇負責。在現代社會,決策者必須具有高度的責任意識,對可能的危險發生進行審慎地評估和預測。危險雖然難以預測,但仍然存在著發生征兆和預警的可能性。因此,行為人在決策時,面對危險問題,必須對各種可能性進行審慎評估。行為人如果已經明確認識到后果的必然性,而且后果無法彌補,就不應作出決策。即使某些決策是在良好的愿望下作出,但是如果出于錯誤判斷或武斷產生了事與愿違的后果,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這仍然不能排除決策者的責任。
其次,決策是行為人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決策實際上是對不確定事物和社會價值的整合過程。行為人應當依據自身的經驗和現代科技,探尋可能的危險源,充分考慮危險的普遍性和可能性。現實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危險往往是由于行為人的人為疏失,甚至故意行為造成。比如,有的決策者實際上在決策時已經感受到危險的存在,卻忽略了危險實質存在的狀況,或者在主觀考量下基于利益博弈,濫用權力,寧愿作出可能導致危險發生的決定。正是因為危險威脅能夠或已經被感知和認識到,并隨著人的決策而來,因此,風險可以被歸咎于責任人。
那么,如何判斷行為人存在故意或疏失?實踐中,要看行為人在決策時是否遵守了必要程序,是否采取了適當的認識方法,并盡其注意義務。德國學者奧森鮑爾就認為,預測是對未來事實的描述,是蓋然性判斷,對未來事實的描述并不存在真實性和正確性的標準,僅存在注意程度的要求。預測內容可能存在錯誤,但卻同時適法地存在,錯誤并不必然導致不法,預測本身意味著合理錯誤的伴隨。?轉引自陳春生:《行政法之學理與體系(一)》,臺灣三民書局1996年版,第186~187頁。因此,如果決策者踐行了必要程序,即使發生了當時條件下無法判明的危害,也很難讓其承擔責任,考察的重點在于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是否有明顯的人為疏漏以及嚴重恣意和濫權等情況。其次,考察決策者是否可以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間作出選擇以及選擇的余地有多大。如果別無選擇,就很難將責任歸咎于決策者。這是責任原則的基本要求,因為“對于沒有回避可能性的行為事實的處罰并無預防意義”?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上),臺北元照出版發行公司2006年版,第424頁。。再次,現代社會的決策絕非過去單純幾率性的評估,還必須體認到未來的無限變化。所以,決策者對隱蔽、潛藏的副作用不得視而不見。例如,自然生態資源的開發可以帶來一定的經濟利益,但同時也可能導致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浪費。如果過度開發就會引起水土流失、旱澇災害頻繁等情況,特別是在一些極端惡劣條件下會造成泥石流等災害,對當地民眾的人身和財產造成嚴重的威脅,因此,決策者就應當對開發的規模和程度等進行仔細評估,不得濫墾、濫建和濫伐。所以,決策者是否應承擔責任就應考慮決策者的決策空間和過程等因素。決策者不得盲目作出決策,否則,就應承擔法律責任。
總之,趨利避害應是決策的基本法則。但是,現代社會的每項決策涉及的問題龐雜,不可能完美無缺,無法完全排除危險,因此應當允許一定程度的危險的存在,哪怕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現代社會所應當避免的是那些嚴重不負責任,或者一意孤行,堅持錯誤的價值取向,罔顧民眾生命和健康以及環境生態的價值的非理性決策。因此,只有在決策者具有失察、失職、失誤的情況,或者為了片面地追求某種利益而故意地選擇承擔危險,以至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下,才應承擔法律責任。通過歸責,可以喚起決策者 “作為一個整體的行為主體的危機意識,從而為防止人類的共同災難的出現尋求一條出路”?甘紹平:《應用倫理學前沿問題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