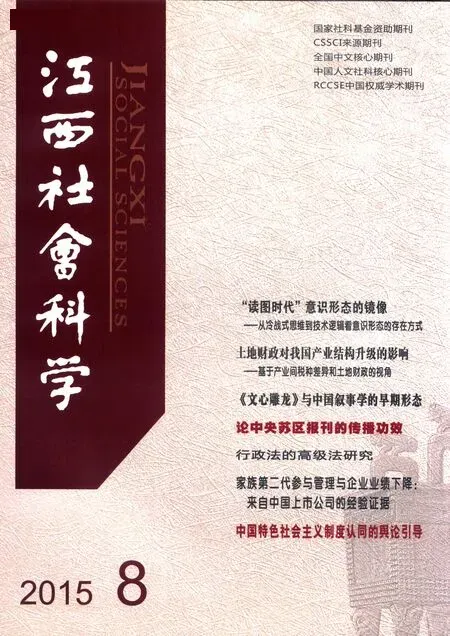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實施與得失鏡鑒
■陳小紅 易花萍
一、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及其功能
民國時期的語言文字規范主要以“憲法性法律文件”、“令”、“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存在。從功用上看,“語言文字規范”和一般法規現象一樣,具有“社會作用”和“規范作用”。其“社會作用”主要體現為“建立和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規范作用”主要體現為一種“指引”作用,其次是“教育”作用,“教育”是為了更好地“指引”。
(一)社會功能
1.建立和穩定社會秩序,同時體現語言文字規范的“社會性”和“群眾性”
首先,表現在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是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提出的,順應了社會的客觀形勢,起到了挽救危亡、穩定民心的作用,漢字革新無疑具有“建立社會新秩序”的作用。如“國語”的制定,時值民國新建,建立一種新的國語,倡導語言統一,是勢之所然,更是建立社會新秩序努力的反映。“建設民族共同語”,是中國從政治、經濟等領域向現代型民族國家邁進的需要,更是正面臨民族生存危機的民族所急需的民族向心凝聚力、文化整合力的資源。
其次,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是由民眾發起和推動的,是順應民心的,具有廣泛而堅實的“群眾性”,因而不會引起騷動,具有“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具體體現為:(1)由群眾自愿、自覺發起,并推動。例如“切音字”是由王照、盧戇章、芝乃宣等首倡;“國語羅馬字”是由錢玄同吳稚輝等發起的;“拉丁化新文字”是由旅蘇的共產黨人吳玉章、瞿秋白、林伯渠等興起的。無數先賢為此也自覺地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在各種語言文字規范方案的制定過程中,只有促成方案更加合理的不同聲音,而沒有騷動事件。(2)定位于推廣、普及漢字的大眾化和全民性目標。把語言文字當作工具,以便于民眾快速和容易地識字學知識和增加智慧為目標,是近代語言文字規范的目標。例如,“切音字”方案雖然林立,但它們具有“易”(如盧戇章的“新字”,“雖一生未入孔了門,亦能無師自識漢字”[1](P28))、“簡”(如王炳耀的“拼音字譜”,“以最簡之筆畫作字……聲母一筆,韻母一筆,每字獨二筆”[2](序)、“捷”(如蔡錫勇的“傳音快字”,“一筆連書,可代數字”,“一人可兼數人之力,一日可并數日之功[3](凡例)”)的優點。
2.追求民族振興與富強
鴉片戰爭的失敗,驚醒了腐朽帝國“天下朝儀”的迷夢,也讓部分有識之士產生“逐出人國”的深刻焦慮,于是,以外求獨立、內求富強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式民族主義思潮彌漫于晚清社會各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變革思想成為近代中國思想的主流。為尋求拯救之道,知識分子從自己專業的角度檢討得失,他們把漢字落后列為國家貧弱挨打的總根源。他們痛陳漢字缺點:認為漢字繁難,導致百姓不易掌握,教育不能普及;因為語言文字分離導致識字率低下和民智無法開啟;因為語言不統一,所以“上下內外”不通,全國一盤散沙。裘廷梁說,“有文字為智國,無文字為愚國;識字為智民,不識字為愚民;地球萬國所同也。猶吾中國有文字而不得為智國,民識字而不得為智民,何哉?此文言之為害也。文與言判然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為兩千年來文字一大厄也。”[4](P120)在科教救國的時代語境中,吳稚暉認為普及初等教育是救國的根本方法,而應急的拼音字母是普及教育的具 體 步 驟[5](P102)。至 于 拼 音 文 字 是 否 就 能 救 國,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總之,不管是激進還是漸進的文改家都把漢字改革當成尋求文化振興的妙策良藥,文改成了“愛國保種”與否的試金石。
即使是以西方文字作為文字改革與立法的權威標準、文化上向西方看齊以使國家富強,但這并不是說不堅守民族立場。它不僅表現在他們的文字改革與立法始終著眼于民族振興的目標,更表現為他們的文字改革與立法活動中始終貫注的民族主義情結,始終堅守民族的邊界。正如提出《盛世元音》方案的沈學認為,中國文字“最拙”,歐洲列國之富強是因為有“羅馬之切音字”,因而中國的文字“有不得不變之勢”;但同時又認為,決不能“遽變”。[6](序)提出《拼音字譜》方案的王炳耀主張,語言文字方面應學習西方,但主要是學習其理念和方法,而反對采用外國字母來拼讀漢文。但為了堅守“國基”,“漢文”仍應存,“方音”不能滅,以“參求本國字體為體,變于己不變于人”為改革之方針。[2](序)
(二)規范功能
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的最大特點是文字體系經歷了巨大變革,經歷了從方塊體系到拼音化的嘗試,以及從繁體到簡體的轉化,這是前所未有的。對于這種創新和改創,頑固勢力和守舊守力必然阻撓;為此,新法需要做大量的“告知”工作,即“指引”作用,而“告知”功能的行使仰賴于宣傳和教育工作。也就是說,近代語言文字規范的“規范作用”凸顯為“指引”作用和“教育作用”。“指引”民眾在革命動蕩年代如何快速有效地使用漢字,是配合近代革命宣傳的迫切需要。“指引”作用是第一位的,“教育”是為了更好地“指引”。當然,我們強調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的“指引”作用,并不是否定它的其它“規范”作用;“指引”的內容,顯然也是“評價”和“預測”當時人們使用漢字是否合法的標準。
二、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生成機制
語言文字規范的生成動因包括三個維度,一個是“社會環境”維度的,一個“漢字本體”維度的,一個是“意志”維度的。
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生成動因以“社會環境”因素最為突出,其次是“漢字本體”因素,“意志”因素相對較弱。
(一)“社會環境”維度
“社會環境”維度首先凸顯的是“思想”因素。例如,在“啟蒙思想”的啟發下,“民”被確認為國家政治的主體,而且把民族振興的希望寄托在“民”的普遍的理性覺醒和達到“智”的境界基礎之上;他們以“開民智”為導向,著眼于“農夫販豎”、“婦人孺子”的識字學知識,主張讓“農、工、商、兵”等下層民眾都有受教育的機會[7]。受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無政府思想”的影響,崇尚世界主義,認為文化不存在民族和國家的界分,作為文化之一部分的文字當然也是這樣,基于此,提出了“萬國語”、“世界語”的方案。在“歐化主義思想”的入侵下,他們把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和發展樹為最高價值目標,在堅持新文化方向的同時,對來自外國、外族的各種形式的侵略保持著高度警惕和堅決抵制的態度;這種思潮的結果是,主張歐化的同時保持漢字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對漢字拼音化有阻力。
其次是“政治”的因素,主要表現為語言文字工作基本上與政治斗爭和社會運動緊密結合。如“切音字運動”時值中日甲午戰爭和變法維新運動,中國面臨著被世界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統一國語”在于,當時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想觀已經由清末狹隘的大漢族主義轉換到多民族共存的國家建制思想,而中華民國建立之時就以“五族共和”明志于世,但蒙藏各族語言和漢地各有不同,因此在語言上處理這種民族關系顯得非常關鍵;另一面,政府方面認為蒙藏之人既是中華民國國民,當然得熟習“國語”,所以建構一種全民族的共同語,加強所有國民的民族性建構乃是國語運動的應有之義。[8](P1053)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民眾識字運動官方宣傳材料中,我們也看到:大眾的識字與否被認為與訓政能否成功、民族精神能否振起,與世界各民族能否處于平等之地位、三民主義能否實現直接掛鉤。[9](P31)
再次是“經濟”和“軍事”等因素。近代是中華民族“落后”和“挨打”的時期,異國入侵、軍力疲軟,民眾的生存是第一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不可能產生專門和系統的語言文字規范法。相反,八國聯軍的侵華,一次次的喪權辱國賠款,讓中國人淪為下等民族,生活舉步維艱,徹底失去了尊嚴,停止了反抗,外交、軍事、政治、文化全面繳械投降,中國傳統文化遭到空前浩劫,因而將漢字作為重點討伐對象,廢除漢字的呼聲也就不絕于耳。當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因而時人寄希望于通過“統一國語”加強地方軍閥對整體的認同,實現全國的統一。倪海曙認為,“連年內戰,使當時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到政治統一的需要,于是許多人又都從統一上著想,這種意識反映到語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與國語運動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轉變成了‘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他還說:“方今南北紛爭,憂國之士力謀統一,但統一南北,非先聯絡感情,則言語之效力乃大。”[1](P89)
(二)“漢字本體”維度
首先,漢字體系本身的局限是語言文字規范法規和標準出臺的重要原因。他們認為漢字筆畫多、難認、難識、難學是漢字的局限,因此有必要改革現有漢字體系。盧戇章認為:歐美強國“切音為字、字劃一律、字劃簡易”,而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下字之至難者”。[10]錢玄同說:“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這是有新思想的人們都知道的”。譚嗣同號召“盡改象形文字為諧聲”;[11]蔡元培認為“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徑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12]陳獨秀也說:“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魔窟,廢之誠不足惜”;[13]魯迅認為,“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14]“拉丁化新文字”的創設就是為了改革現有的繁難的漢字體系、使漢字更加簡易、更加方便和更加容易使用;也正因為拉丁化新文字具有簡單易學的特點,適于在廣大勞動群眾中流傳,因此獲得了很大的廣泛性和群眾性,被當成了“掃盲”和推行漢字“大眾化”的工具。
其次,近代語文運動把漢字當作配合革命宣傳的工具,語言文字規范化的目標定位于“便利”、“簡捷”和“通用”的“器具觀”。清末民初以來的歷次漢字變革及立法,不論口號、做法有多大的出入,但核心目標始終沒有發生變化,就是文字必須簡化到老百姓會寫會讀、會認,語言必須做到言文一致、口手如一。文字改革及規范推動人士從文字角度意識到中國文字具有不適應于“多數人”的弊端:“不患無上等少數人之教育,所患者,無教多數人之教育耳。何謂教少數人之教育?漢文西文是也。何謂教多數人之教育?以語言代文字,以字母記語言是也”。他們認識到人民的文化水平決定著國家的強弱,“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15](P7)他們把語言當作工具,認為語言是人類交際的符號,要想建立人類祖國,必須建構這個大家庭的共同語。
再次,體現為近代語言文字規范化致力于語言文字體系本身的改革和進步。從1900年至1911年,已知的切音字方案有20個,如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田廷俊的《數目代字訣》、力捷三的《無師自通切音官話字》、陳虬的《新字甌文七音鐸》、李元勛的《代聲術》等。這些方案有一個最大特點:隨著人們對文化以及文化與“強國”的關系之認識不斷深化,語言文字改革在這一時期主要被置于民族新文化建設的框架下進行,因而語言文字改革的思考和活動已從過去更多地著眼于其外在的政治、社會等方面作用和功能發揮,轉移到越來越多地致力于語言文字體系本身的改革和進步。
(三)主觀性“意志”
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的主觀性“意志”因素相對較弱,但由于它是由民眾推動的,難免也打上語言文字規范提倡者們主觀意志的烙印。例如,錢玄同的“簡化漢字”主張與他的歷史哲學思想有關系。他深諳春秋公羊之學,把天下歷史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世之說,認為世界化的“國語羅馬字”是“太平世”的初步,現在中國社會還只是個“升平世”,還離不開漢字,須就漢字作一些形體的改良和聲音的幫助[16];而后,在張勛復辟丑劇事件后,受到刺激后,他又提出“廢除漢字”的激烈主張[17](P1682);之后,受20世紀涌入中國的“以世界大同作為普世價值”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18],又提出“萬國新語”、“世界語”的主張。
另外,受由于時代和認識的局限,近代語言文字規范方案有主觀意志性的一面。例如,民國政府的“老國音”采用投票的方式決定標準音,這是多種語音的機械相加得到的一種雜燴音,以這種語音為標準音的共同語是一種“折衷南北,牽合古今”的人工創造的語言,主觀性太強。而“Esperanto(世界語)證明,人工創造語言是可能的,但是人造語言的流通性和生命力無法跟自然語言相比”。[19](P44)因為活方言有它的社會基礎,有幾千萬人在那兒說著。還有一個最現實的問題:用一種活方言作標準,當地的人可以馬上做教師;人造語言的師資很難落實。
三、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的實現與失效
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實現”的重要原因歸于社會各界力量的支持,如“國家的有力支持”和“群眾的積極參與”。
(一)“國家的有力支持”,表現為“國家公權力干預”的合適及合理
解放戰爭時,在革命區,以政府的力量大力普及新文字是前階段新文字得以推廣的根本原因。例如,為了給新文字運動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1940年12月25日邊區政府頒布《關于推行新文字的決定》規定:從1941年1月1日起,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41年“五一”頒布的《政府施政綱領》第14條規定:“繼續推行消滅文盲政策,推廣新文字教育。”邊區教育廳更是將推廣新文字教育作為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號召全邊區干部、群眾努力學習新文字[20]。他們配合著新文字掃盲,在延安成立了新文字協會,編印了《新文字報》,又出版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新文字課本》《新文字講話》等讀物,還出版了《瑪利亞的故事》《列寧的故事》等兒童讀物;綏德、隴東、關中等地成立了新文字協會的分會[21]。也就是說,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和區域內,國家以政權的力量強力和規模地自上而下推行新文字,其努力變成了真正的現實[22](P317)。
(二)“群眾的積極參與”表現在尊重民意、考慮民眾的利益和需求
如在語言文字規范方案的制定過程中,反復召開會議、征詢集體意見。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產生前,從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一年時間,就開了22次討論會;“注音字母”產生前也是反復召開會議,“讀音統一會”上鼓勵大家提出字母方案,如“偏旁派”、“符號派”、“羅馬字母派”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各種方案的設計者各執己見,雖然爭論了兩個月卻沒有結果,但有所啟發,在魯迅及許壽裳等的提議下,最后決定采取審音用的“記音字母”定名為“注音字母”,并議決《國音推行方法七條》。
民國時期語言文字規范受挫、并最終“失效”的因素可歸結為四個方面。
1.實踐中偏離了群眾路線
“實踐中偏離了群眾路線”是民國時期“國音政策”執行不久就失效的關鍵原因。讀音統一會審定“老國音”的會議時,原計劃參會人員有80人,但由于“各省代表,遠省既憚路遠,又多不重視,故不樂費款;有僅派送一人者,且有自至閉會尚未送一人者。”[23](P53)實際到會者僅是計劃人數的一半略強。這樣,參與會議的代表面自然大打折扣,而審定的所謂“國音”又只是這些專家們折衷的結果。一個群眾基礎如此薄弱的審音結果,在正式執行之前也沒有在社會上予以試行并廣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老國音”隨著使用它的注音字母方案頒布實施,1918年遂成為統一國語的語音標準。這種語言政策在極小的學術圈子里制定而成,也沒有經過反復試驗和廣泛聽取群眾意見,不為群眾所接受在所難免。
2.行政干預過程中政治傾向過于濃厚,實用性重視不夠
解放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以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作為自己的革命職責,新文字的產生和推行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過于深厚[24]。例如,因賦子新文字太多的政治內涵,政府在新文字冬學課本的內容和課程的配備上,都過多地強調了政治內容而忽視了文化識字功能。而就新文字運動本身來說,識字掃盲運動本身也是一項群眾運動,是抗戰動員的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加強大家對于革命和戰爭的認識,而不是出于民眾自身追求知識的要求。[25]另一方面,其教育普及的對象是廣大農民群眾,但其教育內容卻遠離鄉村民眾的一般生活和習慣。
文字改革在性質上歸根到底不同于政治運動,我們不能用過于強烈的政治功利性替代文字改革所必須注重的實用性,陜甘寧邊區新文字運動濃厚的政治色彩,加上新文字的不實用,是民眾對拉丁化新文字產生懷疑和排斥的最主要的原因。
3.方案制定過程中語言事實未被充分重視
舉例而言,民國政府的“老國音”采用投票的方式決定標準音,是一種由多種語音的機械相加得到的一種雜燴音,這種語音比任何一地藍青官話的語音更缺乏內部系統性。這種以方言語音融合而成的方式確立標準音的做法明顯違反了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原則。民族共同語是以政治、經濟集中地區的方言作為基礎,逐漸吸收其他方言中的可取成分而成的…這個形成的民族共同語不論在語音、語法、詞匯任何一方面一定都是以作為基礎的方言做骨干而絕不會以其他方言作骨干,當然更不會以各個方言共同作骨干的。[26](P21)。吳稚暉等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成員確立標準音的辦法是融合,不是擴展,是違背事實的,其生命力必然不長。
4.執行過程中經費短缺
史實可知,民國23年11月,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39次常委會通過了黎錦熙所提的《漢字注音銅模,應由國家鑄造推行案》。民國24年1月26日教育部便召集談話會討論決定撥款委托商鑄的事項,3月5日的第202次行政院會議上通過了教育部呈送的《委托上海中華書局代鑄漢字注音銅模,并繕具合同草案,請準在本年度教育文化費第一預備費項下動支二萬元,俾資周轉案》,但由于國民政府支持注音漢字銅模鑄造的資金過少,導致了成品注音漢字銅模在全國分布過于集中的局面:一套寄運給北平的國語會,其他四套集中派銷給上海的商務、中華、世界、正中四大書局。當戰亂降臨時,大部分毀于戰火之中,這自然造成了注音漢字出版物的印刷困難,也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注音識字這項利國利民的語言規劃事業的物質基礎。1930年時教育部雖然頒布了《各省市縣推行注音符號辦法》,規定凡兒童和民眾的漢字讀物字旁都必須一律加注音符號,但是具體落實起來,無法實現,全國各地出版的為數不少的民眾讀物絕少見有注音符號,而書商們出的注音符號傳習小冊,也竟不見有給民眾用的,甚至連教育部審訂的小學教科書和銷行較廣的兒童民眾讀物,也不照文件辦事[27](P20)。故至1935年時,所能見到的成績便只是小學僅國語課本生字注音,民眾則偶爾提示,略資點綴,實際上不發生效力,法律所定亦漸等于具文[28](P133)。
四、語言文字規范化有效實施的當下思考
(一)語言文字規范有效實施的前提是語言文字規范和標準本身是科學的、正義的和尊重實際的,同時法規和政策應該具有一定穩定性
首先,語言文字規范和標準本身應該科學,而不是主觀意志的和偽科學的。“二簡”方案之所以失敗,就在于簡字多是主觀臆斷的和敗筆的,例如將“泰”簡化為“太”、“彩“簡化為“采”、“座”簡化為“坐”、“賬”簡化為“帳”、“藍”簡化為“蘭”、“歧”簡化為“岐”、“戴”簡化為“代”、“齡”簡為“令”等。其不科學性在于:一是被簡化的簡化字與另外一個簡化字具有重疊,造成了語義功能疊加;二是輪廓字和草書楷化字等破壞了中華漢字一貫的方塊字結構,違背了漢語言文字發展的事實與規律;三是二簡方案正值十年動亂結束,人們都愿意穩當,不愿意再亂了,“文革”之亂結束一年就出臺一方案,這種標準的出臺會讓人視為是權力尋租的手段。也就是說,法規和標準的出臺應該為人民考慮生活的便利與實踐應用的價值。
其次,語言文字規范和標準的科學性和正義性應當建立在實事求是基礎之上,是符合實際的和群眾能夠接受的。要說的最典型的當下例子是“林陰道”的“陰”字。記得讀書時代,老師通常以“說文解字”的方式,強調無“草”不成“蔭”,同時也認為,“林蔭道”有形象地遮蓋的意思,而“林陰道”似乎傾向于背陽,故認為“林蔭道”更能形象表達“綠林遮蓋”的語義。但事實上,在國家語委1985年12月推出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中為了區別達隱蔽、封賞等意思的“蔭”,將“樹蔭”、“林蔭大道”中讀第一聲的“蔭”都改成“陰”。也就是說,該規范已經存在快二十年了,但90年代在校接受早期教育或更早接受早期教育的人面對該規范字時,無比驚詫,在網上引發了熱烈爭議,這里面自然存在標準是否合理和能為群眾接受的問題。
再次,良性的語言文字規范和標準要具有一定穩定性和連貫性,不能過快更替,朝令夕改,否則會失去威信和被接受的基礎。舉例而言,1955年12月發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但隨后不久,1956年3月又發布了《修正〈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內“阪”“挫”二字的通知》,恢復“阪”、“挫”二字的規范身份;20世紀80年代,《簡化字總表》(1986年10月10日發表)和《關于發布〈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的聯合通知》(1988年3月25日發布)中又重新認定了26個字的規范身份;1993年《關于“镕”字使用問題的批復》又恢復了“镕”字的規范身份;2013年頒布的《通用規范漢字表》,再次審核異體字,認為“鐓、鰌、虠、刬”應繼續按異體字處理。如此頻繁地更換規范和標準,會讓人無所適從,不敢相信規范和標準,降低規范和標準的威信。
(二)語言文字規范工作從政治目的出發沒有生命力,基于社會應用出發的語言文字規范更具科學性
近代“切音字”運動和“漢語拼音化”的目的主要是通過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喚起民眾,救國圖強。它是政治性的,忽視了語言文字的客觀規律,其后果在于:第一,政治目的強的語言文字規范讓人感覺任務性明顯、御用性強,因而可能影響民眾的主動配合力和接受性,影響語言文字政策法規和標準的傳播力;第二,由于政治的指向,在學術性的語言文字規范化活動中,必然會出現指導思想的錯誤,錯誤的指導方向自然不可能帶來正確的發展路徑,實踐也證明,中國走漢語拼音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第三,一旦政治活動追求的政治目的不能實現或崩潰時,活動自然也就瓦解而歸于失敗了。
語言文字規范是社會的,它脫離不了政治等因素,但賦予語言文字規范太強的政治性內容沒有生命力。當代“二簡”方案就是因為政治性太強而導致失敗。語言文字規范一方面要順應國家建設與發展的形勢,另一方面要盡可能地淡化政治色彩,更多地從語言文字的實用性出發,立足于語言文字“本體規律”和“社會需要”,最大可能地發揮語言文字的交際功用,才可能取得更好的實施效果。[29]
(三)“政府推動”是語言文字規范化工作開展的外在動力,“社會演進”是語言文字規范化工作開展的內在要求,二者應該良性互動,促進社會和諧
國家的重視和扶持,官方的重視,政府的積極干預,是語言文字規范化實施的有力保障。近代國語運動首倡于民眾中,但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它不可能得以實施和推廣。例如,國民政府曾擬大規模推行簡體字,但因戴季陶等人強烈反對,1936年便下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解放戰爭時期,在對待實行新文字以掃盲問題上,因教育部拒絕實驗新文字,故而新文字運動沒有大的發展,直至后來教育部換人,各方呼吁,最后在“文學革命”的推動之下,才勉強得以正式公布。
但尊重民俗民意,發動民眾廣泛參與,也是語言文字規范化工作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政府控制”思路太強,未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是當下語言文字規范工作的一個局限,導致語言文字規范傳播面受限,也不被群眾理解,很難開啟民眾自覺的語言文字規范意識。[30](P185)良法是大家向往的目標,法的實施效果最終體現為相關主體對法的服從程度。作為一種理性遵從,它需要讓民眾覺得自己是主人翁,并使民眾成為權利的主體;同時,應該讓社會各界廣泛參與成為推動語言文字規范工作的極大力量,發揮民間社團、學者和民眾的合力。
(四)語言文字規范化工作的實施效果,不只取決于政策法規自身的完善程度,也取決于政策法規的社會環境,以及執行者的素質和社會風氣、社會心理等因素
首先,語言文字法規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受經濟條件的制約,經濟狀況的好壞不僅影響著立法活動和執法活動,也會影響人們的守法活動,人們在采取什么方式守法的問題上,受當時的社會經濟因素制約。如果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能使人們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方式和手段滿足自己基本的社會需要,那么人們就比較愿意安居樂業,自覺守法,否則,人們就可能沖破法律束縛,采取非法手段來獲得個人需要。人們能否依法享用權利和履行義務,并不只是取決于個人的主觀愿望和要求,還要看社會是否提供了這方面的物質保障,否則,守法只能是紙上談兵。只有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公民才能真正享用各項權利并履行各項義務。語言文字規范化活動的實施必須要有合理的經費,沒有最起碼的國撥經費作保障,文字規范這類上層建筑的工作很難取得進展。[31]
其次,唯有穩定的政局,語言規劃者才有時間和精力來關注和制定語言規劃;唯有安定的環境,語言規劃接受者才能安居,才能接受和執行語言規劃。無論是語言文字的創制和選擇,還是語言地位的篩選和確定,還是語言習得的開展和落實都需要安定的社會環境和穩定的政局。動蕩的社會,慌亂的人心,任何規劃都不可能有機會落實和實現。同樣,語言是民族的象征,民族文化的載體,科學合理的語言規劃會促進語言的發展,民族的融合,必然促進國家的安定和民族團結。
再次,語言文字規范化工作的有效實施有賴于公民信仰和法律規范意識的提高。真理的取向和認可往往在于個體的集體表達之后才能全面顯現;法高于一切,源自他們內心深處本真的希望法能夠成為維持秩序的一種權威訴求,讓法純凈地運行,成為指導一切的規則。盧梭說過:“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它每天都在獲取新的力量,它形成了國家的真正的憲法,當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時候,它可以復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個民族的精神。”[32]法律的實現依賴于社會成員對法制的自覺信任和普遍維護,法制觀念和法律信仰是實現法制的內驅力。沒有對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礎,任何社會都不能邁進法治社會的門檻。
[1]盧戇章.新字初階序[A].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2]王炳耀.拼音字譜[M].拼音文字史料叢書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
[3]蔡錫勇.傳音快字[M].拼音文字史料叢書本.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199.
[4]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A].近代史資料[Z].北京:中華書局,1963,(2).
[5]吳稚暉.吳稚暉先生全集[M].臺灣:中國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編輯出版,1969.
[6]沈學.盛世元音[M].拼音文字史料叢書本.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
[7]栗萬鐘.蒙學堂宜立章程說[N].湘報.第142號,1898,(8).
[8]蒙藏教育應注重語文[A].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新編民國法令大全[G].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9]宋恩榮.晏陽初全集第1卷[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10]盧戇章.一目了然初階[M].北京:中國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
[11]譚嗣同.仁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12]蔡元培.漢字改革說[J].國語月刊第一卷第7期,1922,(8).
[13]詩探索編輯部.詩探索[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2).
[14]魯迅.關于新文字[A].魯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雜文[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5]佚名.清末文字改革文集[C].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16]盧毅.錢玄同與近代語言文字改革[J].重慶社會科學.2007,(5).
[17]錢玄同.錢玄同日記.第4冊[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8]汪林茂.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義與文化運動[J]學術月刊,2007,(10).
[19]周有光.周有光語文論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20]邊區政府重申前令,保障新文字合法地位[N].解放日報,1941-09-18.
[21]晉冀魯豫新文字運動[N].解放日報,1942-07-19.
[22]董純才.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2卷[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
[23]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目錄[M].上海:上海書店,1990.
[24]吳玉章.新文字在切實推行中的經驗和教訓[N].解放日報.1941-12-16.
[25]王元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的新文字冬學運動[J].抗日戰爭研究,2009,(3).
[26]中國語文雜志社.漢族的共同語和標準音[M].北京:中華書局,1956.
[27]黎錦熙.國語新文字論[M]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
[28]倪海曙.注音識字簡史[M].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會語文現代化(第一輯)[G].上海:知識出版社,1983.
[29]易花萍.古代語言文字規范法有效實施歷史鏡鑒[J].北方論叢,2012,(12).
[30]易花萍.語言文字規范法治秩序構建[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
[31]張國慶.現代公共政策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32](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