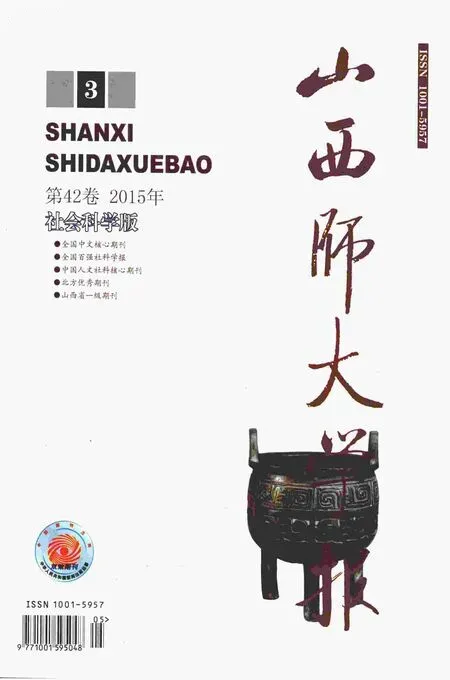1990年代工業改革題材小說懷舊敘事審思
----以張宏森的《車間主任》為中心
薛 月 兵
(山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4)
1990年代工業改革題材小說中的許多作品反映了國企改革的困境及工人群體的生存境遇,表現出強烈的回到革命史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情緒。此種懷舊情緒在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同時高揚著道德理想主義的旗幟,表達了工人群體在現實困境中尋找精神家園的強烈渴望,以及通過“左翼”精神的復興確立自身文化認同和歷史合理性的努力。然而,將過去道德化和理想化,“家園”意識形態及“左翼”精神的復興在解決工人群體現實困境方面有著明顯的不足與欠缺,而且在全球消費文化語境中存在著被消費意識形態捕捉而被商品化的危險。以張宏森的小說《車間主任》為個案,探討此一時期懷舊敘事的策略、存在的問題及所應進行的文化審思無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一、懷舊的概念及類型
在西方,“懷舊”(nostalgia)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瑞士醫生霍弗爾在1688年的一篇醫學論文中提出的。英語“nostalgia”由希臘語“nostos”(返鄉)和“algia”(懷想)構成,主要是指士兵返回故土的愁思。“懷舊”一詞起初是在病理學層面上使用的,中經心理學階段,最終被納入到社會學以表達某種文化情懷。美國社會學家斯維特蘭娜·博伊姆認為:“懷舊向往的定義就是所渴望的那個原物的喪失,以及該原物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位移。”[1]5就中國而言,從公元前6世紀的孔子時代開始,“懷舊”就成為中國文學的母題,表示回到某段時光和某個地方的強烈渴望,總在社會出現不和諧、斷裂、巨變、異化的時刻綻出,執迷地述說著對于宇宙和諧、社會烏托邦和人性健全的幻想。
19世紀末期,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性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尋根,借用美國社會學家羅蘭·羅伯森的概念將其稱為“存心”懷舊。主要表現為兩種類型:其一,在民族志中的原始神話、巫術儀式以及在前工業時期較少受現代文化浸染的邊陲地帶尋找民族文化之根;其二,對于被現代性排斥的階層而言,表現為在該階層曾經輝煌或高度發展的時期尋找文化之根。羅蘭·羅伯森指出:“出于某些目的,把從政治上鼓動的懷舊看作以下兩者的混合產生的考慮是適當的:從實際的和潛在的民族精英這方面來看,他們意識到了民族整合的需要;同時,因‘國際社會’的壓縮,民族認同受到相對化的威脅。”[2]218與這種出于民族整合及認同的需要進行政治上鼓動的“存心”懷舊相比,“存在型”懷舊則是現代社會對前現代社會文化資源的再利用,抑或對前現代文化的體驗式消費。在全球消費文化語境中,因民族文化同質化的焦慮而進行的“存心懷舊”可能最終被“存在型”懷舊所捕捉。此外,美國社會學家斯維特蘭娜·博伊姆將懷舊分為“修復性”懷舊和“反思型”懷舊兩種類型。“修復型”懷舊是指通過對過去之物(如紀念碑、教堂)的修復,使其作為一個民族輝煌過去的實證性力量,從而完成民族象征和文化的構建。“反思型懷舊”則是目睹現代文明的諸多弊病對“精神家園”的回望,并意識到過去的建構性、回溯性及非本真性,進而生發出強烈的主體精神與批判性,在形式上表現出“挽歌”和“諷喻”的特征。綜合二者的懷舊理論可以看出,“存心”懷舊是一種政治實踐;“修復型”懷舊是這種政治實踐的文化舉措,目的是持續文化認同的同一性;“反思型”懷舊則是認識到過去已不可返,側重于對現實的審視與反思;“存在型”懷舊則是消費語境中對文化的體驗式消費,是一種為了消費而進行的懷舊,潛存著對上述三種懷舊的解構與涵化。
盡管羅伯森和博伊姆的懷舊理論是在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層面展開的,然而其理論也適用于1990年代工業改革題材小說中懷舊敘事的研究。其實,中國現代性(啟蒙主義、工具主義、物質主義)的發展往往伴隨著政治維度上的“存心”懷舊和文化層面上的“反思型”懷舊。近代歷史中出現的“中體西用”派就表現出強烈的“存心”懷舊色彩,而上世紀30年代出現的“京派”則代表了在鄉土中國的回望中對現代性的反思。不論是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抑或師陀的“果園城”,都具有家園即將逝去的挽歌情調。同樣,1990年代的工業改革題材小說也是反撥1980年代西化思潮的政治實踐及文化反思。首先,隨著全球范圍內資本的擴張,國有企業不得不面對跨國資本的滲透及跨國投機的風險。其次,各種體制外經濟實體的大量涌現導致國有企業競爭的激烈化。同時國企改革中腐敗、尋租等現象進一步惡化了企業的困境及工人群體生存境遇。再次,在全球消費主義、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的沖擊下,傳統的、革命史中的價值觀念解體,工人群體面臨著文化認同的危機。新興階層的崛起在加大貧富差距的同時,與工人群體的沖突不斷加劇。由此,面對20世紀90年代改革進程中引發的諸多矛盾與困惑,工人群體產生了回到革命史,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強烈渴望,體現了對過去的挽歌及對現實的反思。然而,在消費主義的文化語境中,不論是“存心”懷舊的政治實踐抑或“反思型”懷舊的文化審視,都可能被納入到消費意識形態的框架中被“存在型”懷舊所消解。
1990年代工業改革題材小說中出現了大量的懷舊小說,如榛子的《且看滿城燈火》,肖克凡的《最后一個工人》、《最后一座工廠》,張國擎的《斜陽與輝煌》,季宇的《灰色迷茫》,趙德發的《繾綣與決絕》,劉醒龍的《生命是勞動與仁慈》(又名《無家可歸》),張宏森的《車間主任》,等等。作為改革時代的文學書寫,這些小說反映了轉型期中國改革的困境及其承受者在文化方面的蛻變。然而,最集中和最深刻地表現上述四種懷舊類型相互滲透和交疊的是張宏森的《車間主任》。這部小說書寫了在全球消費主義和新興階層圍困中工人群體的尷尬境遇,既包含著對現實境況的反思,也包含著對過往時代的精神提取。其懷舊的策略既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文化資源,又提供了對懷舊敘事進行審思的樣板。
二、懷舊敘事的表現及策略
張宏森的《車間主任》以瀕臨倒閉的大型國企“北方重型機械廠”為敘事空間,刻畫了社會轉型中工人群體對革命史尤其是毛澤東時代道德理想和精神風貌的守望,流露出強烈的時代懷舊情緒。以車間主任段啟明為代表的工人群體堅守著那個時代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相互扶助的優良傳統。然而,這些與革命史及中國五六十年代的道德理想聯系在一起的集體風尚,卻在市場經濟的進程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尷尬與屈辱。如小鼻涕在為父親看病時遭到醫生無情的奚落和譏諷;程全懲治惡少楊子江反被拘留;郭燕燕在楊子江的脅迫下,為了尊嚴投河自盡;劉義山下崗的妻子遭到不法商人的詐騙,等等。小說展現了工人群體在與市場經濟、消費時代的文化錯位中的無奈與嘆息、憤怒與迷惘,并引發了回到革命時代的強烈渴望與對毛澤東時代的“存心”懷舊。然而,這種“存心”懷舊本質上是一種時間政治,其中包含著將過去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傾向,旨在通過將過去理想化而為工人群體提供溫馨的精神家園。
除了對革命史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存心”懷舊,《車間主任》還敘寫了工人群體在“存在型”懷舊中所遭遇的文化圍困與符號暴力。市場經濟的勃興引發了社會的轉型及各階層的分化與重組。代表既得利益的新興階層因其在經濟上的優勢,必將把他們的文化欲求通過媒體表達出來,從而使部分媒體成為其文化欲求的倡導者。然而,消費意識形態的興起不僅侵蝕和消解了傳統的階級區分,而且工人群體的向下流動及消費能力的匱乏使其文化訴求被忽視和遮蔽。《車間主任》中出現的媒體文化,如“憂傷迷惘”的《霧里看花》,“俗不可耐”的《大花轎》,街頭秧歌的伴奏曲《擁軍花鼓》,“粉飾太平”之聲的《今兒個真高興》,星級酒店大堂內“幽雅”的琴聲,“全是資產階級牛奶,沒一點無產階級的糧食”的書籍,對于工人群體而言是異質的。這些媒體符號既與向下流動的工人群體的情感相隔膜,又在特定的情境下形成了對工人群體的文化圍剿和符號暴力。當參加完劉義山火化儀式,懷著悲痛心情的工友們面對大街上傳來的《今兒個真高興》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懣與無奈。此種媒體的中產情調和娛樂化傾向對經濟上貧困、政治上弱勢、文化上孤立并對前景充滿困惑和焦慮的工人群體形成了巨大的挑釁,引發了工人群體對疏離的和異己的媒體文化的深深敵意。這種疏離的和異己的感受在強化工人群體階層意識的同時,使其成為消費社會中充滿敵意的被排斥的存在。
現實的失敗感與媒體文化的圍困使工人群體生發出強烈的抗爭意識,而這種抗爭又是在話語的、象征的層面上進行的。《車間主任》中除了“程全”將反抗付諸行動外,車間內其他成員希冀通過“左翼”話語進行象征性的文化抵御,以消弭現實處境的尷尬與焦灼。小說中反復回蕩的“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深深的海洋”、“三套馬車”等紅色革命歌曲的高亢旋律,也營構著這種文化抵御的悲壯氣氛。同時,革命歷史小說中的敘事元素,如“血書”、“遺物”、“臨終囑托”成為革命史中的工人階級與市場轉型中的工人群體精神延續的策略與方式。這些“左翼”話語表達的正是工人群體現實的、文化的困境以及通過懷舊重塑其作為一個階層的文化認同感。究其根源,“左翼”話語是工人群體在現實挫敗感中,修復和重建“溫馨共同體”的努力以及尋找并證明其歷史合理性的嘗試,是“確認自己處在一個強大的歷史空間和族群文化之中,擁有一些可以充分應對變化的傳統資源,自己是這一傳統中一分子,憑著凸顯和夸張這種文化傳統與民族歷史的方式,人獲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3]544在此過程中,革命文學中的貧窮革命化、同情道德化、暴力合法化也成為工人群體修復自身歷史合理性的負面文化心理。
然而,工人群體所懷戀的光輝歲月及作為溫馨共同體的毛澤東時代是無法返回的,僅僅是其在艱難的現實境遇中對過去的想象性重構。在集體失語的境遇中,工人群體深刻地意識到在時代與社會的轉型中革命史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輝煌已經逝去,使此一時期的懷舊敘事表現出“反思型”懷舊的特征。然而,向市場主體的轉身必然是沉重的,因為工人群體必須在斷裂的意義上與過去告別,并引發了強烈的認同焦慮,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工人群體在與新興階層的創傷性體驗中通過創造性地利用消費文化,借用表達新興階層文化欲求的媒體符號來表達自身的現實處境。究其實質是“左翼”文化傳統在當下的延續,是工人群體在其文化傳統視域中對當下媒體文化的審視與反思。其二,向下流動的工人群體對日益中產化、娛樂化的媒體文化表現出強烈的傾慕,借自其他階層文化欲求的媒體符號既表達了工人群體加入全球文化消費的渴望,也意味著主體性的匱乏及對現實苦難的象征性撫慰。由此,工人群體的象征性符號抗爭與全球媒體文化符號之間表現出既抗拒又迎合的復雜形態:抗拒表現為借用媒體文化以反媒體文化的策略,亦即通過工人群體對生活的感知和體認對抗著消費社會淘空歷史與現實所營造的“神話”;迎合表現在工人群體在消費社會中建構主體與尋求抱慰的文化選擇,這種文化選擇在閹割其反抗性的同時也標明了回到過去、走向未來的尷尬處境。
綜上所述,《車間主任》的懷舊敘事策略表現為在時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工人群體對過去的想象與重構,目的在于通過“左翼”精神的復興修復其文化認同與身份的同一性。然而,這樣一種重建文化同一性的努力在全球消費文化語境中遭到了媒體文化的圍困與排斥。工人群體通過懷舊抵御消費文化的圍困,但是過去已不可重返;希冀加入消費文化,但又處于被排斥的位置。《車間主任》寫出了工人群體回到過去和走向未來的尷尬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認同危機。然而,過去的烏托邦及當下的消費意識形態都是以主體性的匱乏和懸置為代價的,簡單地依附于過去的重建抑或加入到消費意識形態之中,都不是工人群體解決困境的應然方式。重要的是,工人群體如何在現實的困境中重建自身的主體精神,如何在對過去的精神尋找中提升自身適應現實的能力和實踐感。同時,懸置工人走出困境的主體重建,將過去理想化、現實苦難化的敘事策略,以及對已逝之物的道德同情和情感追憶,是否潛存著商業寫作的可能性?
三、懷舊敘事的問題及反思
《車間主任》中的懷舊敘事高揚著道德理想主義的旗幟,表達了對毛澤東時代的深情追憶。但是,將過去道德化、理想化并非中國擺脫現代性困境的應然方式。因為此一時代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政治化的文化模式已經在歷史中證明了自身的局限及不合理性。本質上,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也僅是一種“歷史的想象物”,是對已逝的特定歷史進行選擇性提取和選擇性構建的文化行為。其在歷史深處除提供特定的精神文化資源外并不能指明中國社會的前行方向。懷舊敘事的文化功用就在于通過回望過去對現代性的前行方向進行審思。對“過去”歲月的懷舊是在體認“過去”對“現在”深層形塑的基礎上,探尋超越現實的文化因子和精神能量,對未來的預言則是將推動現實的文化因子和精神能量納入到未來的視界中。簡單地回到過去抑或走向未來都可能因其對歷史的想象和對未來的虛構而走向為歷史而歷史的犬儒主義及為未來而未來的烏托邦維度中去。此一時期的懷舊敘事表現出來的道德理想主義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具有反思現實的、未來指向的超越性品格。道德理想主義的懷舊情緒在表達烏托邦美學的同時,潛存著將國人所應有的現代精神向度拉回到革命時期甚至是傳統文化的向度中去,而且在對“過去想象物”的懷戀中斬斷了通向未來的進階。
進而言之,將過去道德化、理想化是一種典型的“家園”意識形態。這種“家園”意識形態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就世界而言,整個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就表達了現代性語境下重建家園的渴望;就中國而言,文學對家園的回望和追憶亦是其永恒的母題。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迫切地希望退回到過去的精神體驗中,這一方面說明了現實變革與人自身的承受能力之間的激烈碰撞;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人的惰性以及趨樂避苦的本能,反映出不敢直面也不能直面、只求退避和自保的怯懦心態。”[4]358由此,懷舊植根于人類對消逝、變革、動蕩、苦難、死亡的恐懼,是對孤獨、焦慮等本真困境的逃避,是人性的怯懦以及對家園的穩定感、安全感、連續感的渴望與追尋。從20世紀80年代“改革小說”中的“家園意識”,到90年代“工業改革題材小說”中的“家園已失”,再到新世紀“底層文學”中的“家園重建”,都伴隨著對“家園”的深切渴望。然而,“‘共同體的追尋’——尋找認同的故鄉——是‘人類境況’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類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一樣,這條道路上也遍布著荊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5]17就此一時期的懷舊敘事而言,簡單地依附革命史的、消費文化的認同盡管潛存著新的歷史經驗生成的可能性,但缺乏現實轉向的基礎。工人群體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社會轉型與變遷中重建自身的主體精神,以及激活過去、開辟未來的必要性。與上世紀80年代初的“改革小說”相較,90年代的“工業改革題材小說”中對家園深切的渴望在表達濃重的“家”的意識形態的同時,恰恰懸置了改革開放初期“上城”、“出國”敘事中的個體精神和開拓意識。
法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對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種種政治狀況進行深入的反思后,認識到全球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文化所導致的共同體的離散,提出了“尋找政治”的口號。這種“尋找政治”在此一時期的懷舊敘事中表現為“左翼”精神的復興。如果將張宏森的《車間主任》納入到“工業改革題材小說”的發展脈絡中進行考察,從《喬廠長上任記》建構“現代性神話”的開拓性實踐到《大廠》分享工人群體在改革困境中的艱難;從《車間主任》對毛澤東時代的回想與追憶到曹征路小說《那兒》中對“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的期盼與熱念,始終伴隨著對革命史中“左翼”精神的尋找。臺灣學者林毓生就指出:“從‘五四’后期開始一直到‘文革’結束,中國歷史的過程,基本上,是由強勢左翼意識形態統攝的民族主義激情所形塑的。它使得人的精力與干勁迸發出來——其強度與濃度在世界史少見。”[6]568同樣,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新的社會困境和現實苦難在改革進程中的出現又再次激活了工人群體“左翼”精神的復興。此種“左翼”傳統成為工人群體應對現實困境、構建自身主體性的重要精神文化資源。說到底,對“左翼”精神的尋找是現代性困境的承受者對現代性進行抵抗的政治行為,是通過“懷舊”對過去時代精神的復興,是對現代化進步觀念的質疑和對工業化線性時間的破除。然而,此一時期的懷舊敘事仍潛在地包含著左翼話語在革命史中的負面因子,如將苦難道德化,將同情政治化,將暴力合法化。因而如何在對左翼精神的提取中規避其在原有語境中的負面效應,并將“左翼”精神納入到現實層面的改革中,是這一時期懷舊敘事所昭示的重要文化向度。
盡管此一時期的懷舊敘事表征著對現實的審視與反思,卻也有意無意地在消費社會中體現出“存在型”懷舊的傾向。主要表現為通過將工人群體的生存境遇苦難化賺取讀者同情的眼淚;通過“左翼”精神的復興將社會重新階級化滿足讀者情感宣泄的渴求;通過將過去重構為精神家園迎合讀者懷戀過去的集體無意識。這種“存在型”懷舊模糊了精神文化產品和消費文化產品的界限,前者是以人為中心,關乎人的解放、自由,旨在激發主體的能動性、創造性、超越性;而后者則是文化工業中激發、滿足大眾欲求、用以消費的文化產品。與“存心”懷舊不同,“存在型”懷舊是大眾的、體驗的、消費的,“存心”懷舊是回溯的、批判的、生產的。本質上,“存在型”懷舊旨在撫平快節奏生活中人們與現實的緊張關系,并使之獲得一份內心的寧靜。正如詹姆遜在論述懷舊電影時所指出的:“一般說來,懷舊電影同后現代主義傾向很協調,它試圖生殖關于往昔生活的形象與類象,因而——在真正的歷史真實與階級傳統日趨弱化的社會環境之中——為消費而生產某種虛假的過去,不僅以之作為一種補償和替代,而且也是作為一種移置。”[8]461—462這一時期的懷舊敘事甚至表現出以消費為目的而生產、虛構過去的不良傾向。在這種刻意生產的虛假過去中表達的正是現代市場中的營銷理念,也即通過超現實的想象,關于“過去”的形象不斷激發人們消費過去的沖動與激情,表現出濃厚的消費拜物教特征。因而,這種對“過去”的消費抹除了過去、現在、未來向度中所包含的能動的、建構的能量,削弱了建立在文化同一性基礎上主體的批判、反思的能力,懸置了文學自身的美學精神及超越性品格。由此,在全球消費主義文化景觀中,這一時期懷舊敘事中的“尋找政治”也被納入消費的意識形態之中,成為消解和弱化后發現代化國家信念和價值的文化因子。
[1] (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懷舊的未來[M].楊德友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0.
[2] (美)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與全球文化[M].梁光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4] 趙靜蓉.懷舊——永恒的文化鄉愁[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5]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M].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M].上海:三聯書店,2011.
[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陳清橋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