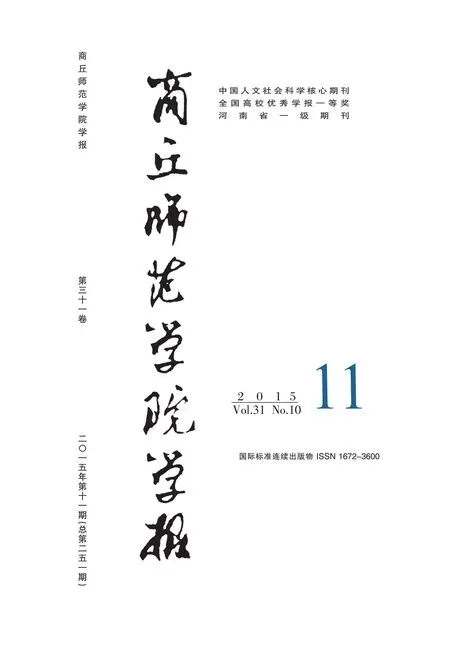嚴復政治學思想新論
王 秋
(黑龍江大學 哲學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嚴復政治學思想新論
王 秋
(黑龍江大學 哲學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嚴復從天演論出發論及政治學,認為以亞里士多德和盧梭為代表的政治學理論在國家類型劃分和國家治理體制問題上存在重大問題。他從國家演化動力的角度將國家分為基于保護共同利益的真正國家、基于同種同祖的宗法國家、基于同宗教信奉的宗教國家三種。他認為“自由”或“專制”程度根本上取決于國家面臨的內憂外患程度,真正國家的政治治理并非取決于多數人的自由或是少數人的專制,而是在于是否有基于公理與民意的根本法律。
嚴復;政治學;天演;內籀
《政治講義》一書反映了嚴復對政治學的系統思想。本文從方法論選擇、國家分類及其旨趣、自由觀念的正名、對專制政治之新的解釋及其與憲政的關系等方面論析嚴復政治學思想的新意所在。
一、從歷史術、天演術、比較術論政治學的變革
嚴復認為,中西傳統的政治哲學主要是奠基在對天之理解之上,天在上,地在下,由此而論及人之尊卑貴賤,而日心說則打破這種天地之上下觀念,進而抽空了以此論尊卑貴賤的世界觀基礎,導致“三百數十年之間,歐之事變,平等自由之說,所以日張而不可遏者”[1]1241。在嚴復看來,導致近代政治變革的理論動因,就是聯系十分緊密的天演論、歷史方法和內籀方法。
在論及政治學與歷史關系時,嚴復指出:“蓋二學,本相互表里,西人言讀史不歸政治,是謂無果;言治不求之歷史,是謂無根。”[1]1243嚴復援引西方成語之本意并非僅僅意在強調歷史學與政治學之緊密關聯,而是要由此推論歷史方法在政治學近代轉型中的重要價值。他認為,傳統政治學是從心學或自然公理談論政治問題,而從歷史研究政治是西方近代政治學的新形態。
從歷史學科的發展看,嚴復認為,歷史學科不斷發展,近代隨著專門史的不斷分化和獨立,最終普通史演化成政治科學,并且從歷史學演化而出的政治學能夠見到政治演變之因果關系,而這是歷史的可貴之處。他說:“史之可貴,在以前事為后事之師。是故讀史有術,在求因果,在能即異見同,抽出公例。”[1]1243由此,嚴復認為,歷史方法在內籀術(歸納法)的基礎上可以實現對歷史、政治演進的因果關系的探究,近代政治學之所以成為科學,就是因為對歷史方法和內籀之術的運用。
嚴復強調了歷史方法、天演方法、內籀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歷史方法是占據基礎地位的,此種論述方式之下,嚴復實現了對中國歷史方法的重新激活,駁斥了流行于20世紀初期關于政治學理論的一些見解,對當時中國人流行的政治觀念進行了批判性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推演出自己最具政治演變公例的結論。
二、從國家類型的新劃分到政治新公例的推演
嚴復認為,國家是政治學研究的首要對象,而對國家進行分類,則是辨別異同、獲取政治規律的基本途徑。因此,嚴復在推出自己的政治規律理解之前,按照歷史方法的要求,先對前人諸如亞里士多德、盧梭等人的國家分類法進行了批判性分析,并按照天演論的觀念,對國家進行新的分類,由此闡發自己對政治演變之公例的新觀念。
亞里士多德按照掌握著國家治理權力的多寡,將國家分為獨治、賢政和民主三種類型。在嚴復看來,這種方式與古希臘的“壤地極小”的“市府國家”的現實相適應,而與近代的地域更為廣闊、組織更為復雜的“邦域國家”不相適應。盧梭亦存在此種問題,故而導致其民約論的政治思想似是而非。
嚴復從“天演涂術”講求政治,認為在天演程度較低的階段,天的要素(宗法或宗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導要素,至天演程度較高,則人為要素(主要是共同利益的維護)對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導性作用更為明顯。按照推動國家演進主導要素的差別,嚴復將國家分為基于保護共同利益的真正國家、基于同種同祖的宗法國家和基于同信奉宗教的神權國家三種。這種劃分克服了亞里士多德三分法不適用于邦域國家的弊端,并且將國家演進的動力要素和國家演進程度的高低有機結合在一起,因而,在解釋政治問題時更有普遍效力。此外,嚴復還著重分析了“惟以壓力”結合的第四種國家形式。他認為,此種國家以強力“并兼”主導政治運行,是國家演進的無機體狀態,因此,程度更低,為非自然演進之國家,注定要被歷史所淘汰。嚴復在此表達了對高度專制的政治統治的批評,并指明其必然被取代的命運。
在此基礎上,嚴復還發出政治改革的呼聲:“是故除非一統無外,欲為存國,必期富強,而徒以宗法、宗教系民者,其為輕、重之間,往往為富強之大梗。于是不得不盡去拘虛,沛然變為軍國之制,而文明國家以興。證以東西歷史,此說殆不可易也。”[1]1265他認為,必須改變中國以宗法和宗教管理國家的傳統形式,向追求富強、維系共同利益的“軍國之制”發展。這種政治改革之關鍵在于“參用民權”,而“參用民權”之程度決定了政治的“自由”和“專制”程度。因此,嚴復對當時流行的“自由”和“專制”兩大政治概念進行了正名和學理辨析,并由此確立了自己對政治問題的獨特理解。
三、從對“自由”的正名到對“專制”政治形式的辨析
嚴復認為,民權自由的程度和政治專制的程度是緊密相關的,對于自然演進的國家而言,民權的自由度或者專制的程度往往取決于國家現實政治的需要。
在嚴復看來,自由的基本含義是“惟個人之所欲為”,而政治作為管理之術,是要“個人必屈其所欲為,以為社會之公益,所謂舍己為群是也”,因此自由與政治是相矛盾的,如何使二者相互調劑,是“政治家之事業,而即我輩之問題也”[1]1279。
嚴復認為,那種強調自由根源于種族的觀念是錯誤的,征諸歷史,他認為普魯士從種族上來說是條頓種族,從宗教信仰來說,是路德改宗的新教。但是,普魯士在18世紀的政治體制則是專制體制,與同為條頓民族和路德新教的英國、美國的政制有所差異。通過對自由概念進行正名和征諸歷史的方式,嚴復認為“民權自由”之多寡要看是否符合國家政治治理的現實需要——國家面臨的外患程度。如果政治治理違反了這種需要,就會有亡國的危險。
嚴復指出:“今所立公例系云:凡國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內治密,其外患淺者,其內治疏。疏則其民自由,密者反是。雖然此是大例,至于他因為用,而生變例,亦自有之。”[1]1292嚴復對“民權自由”利弊的分析,是按照天演程度和歷史演進的原則進行的,指出了“民權自由”多寡與國家面臨外患程度的緊密關系。這一論述有其明確的現實指向性。當時的中國正處在資本主義列強殖民程度不斷加深的歷史條件之下,因此,嚴復認為此時中國的憲政改革要以實現富強以維系社會的共同利益為首要目標,而不能將民權自由作為憲政改革的中心,“自由或不自由的評判標準在于政令簡省就是自由。而次政令必須建立在立憲的議會制度上,讓人民的意愿得以表達,并且根據法典節制的權力,不使其濫用權力”[2]219。
在論述了“自由”之于政治治理的利弊關系之后,嚴復進一步對“專制”的國家形式進行了辨析,并且指明了“專制”的國家形式所具有的現實性。他認為,“專制”的現實合法性可以通過兩個方式獲得論證:一是征諸歷史,二是政治學說的比較辨別。
通過征諸歷史,嚴復指出專制的政治體制雖然并非國家的長治久安之本,但卻往往是應對危機的有效手段。他說:“往者吾論自由,終乃揭言自由有不必為福之時;而今言專制,又云專制有時,且有庇民之實……但須知民權機關,非經久之過渡時代,民智稍高,或因一時事勢會合、未由成立。而當其未立,地廣民稠,欲免于強豪之暴橫,勢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權,以付諸一人之手,使鎮撫之。此其為危制,而非長治久安之局固也,然在當時,則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矣。”[1]1305-1306在嚴復看來,專制體制是政治體制發展的過渡性環節,并且民主政治的實施程度與民眾的素質密切相關。對于20世紀初期的中國而言,民智、民德、民力都亟待提高,因此,他認為政府應當在教育、宗教文化乃至政治權利方面加強管理,而不是抽象片面地實行自由和自治。嚴復對西方的民主自治理論雖然有所向往,并且高度肯定將自治程度作為衡量政治治理程度的標準,但現實政治操作層面,嚴復則強調較高程度的自制和全方面的代表制度只適用于民智程度較高、地域較為狹小、人口數量也較少的國家。而對于當時的世界來說,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的地域和人口狀況,都不宜實行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制的“代表制度”。因此,他認為從民約論生發的代表制度和自治管理固然有其重大意義和價值,但不宜過度美化,并且對其所能達到的政治效果也不宜過高估量。
在嚴復看來,專制政治無論是得益于天命論的合法性庇佑,還是得益于宗教的合法性庇佑,其之所以能夠存在并且取得民眾支持,根本上是取決于民心所向。通過對專制國家形式的論述,嚴復強調了政治管理只有符合天理、符合民意,才是專制國家形式得以長期存在的真實基礎。民權之“自由”程度或國家之“專制”程度都取決于國家所面臨的外患程度,以及政治治理合乎科學和民意的程度。
嚴復從萬物自然演化的觀念出發,通過訴諸歷史經驗和比較歸納方法,對國家類型進行重新劃定,并在此基礎上對自由觀念和專制政治制度進行了不同于西方政治學和當時中國流行的政治觀念的解讀,反映了嚴復在政治公例尋求上的新探索,以及對中國政治變革的理論回應,其思想依然具有值得深思和探索之處。
[1] 王栻.嚴復集:第5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2]劉桂生,林啟珍,王憲明.嚴復思想新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李安勝】
2015-08-30
黑龍江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重點課題“中國近代教育思想研究”(編號:GBB1213030)。
王秋(1979—),男,黑龍江雙鴨山人,講師、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哲學研究。
K25
A
1672-3600(2015)11-004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