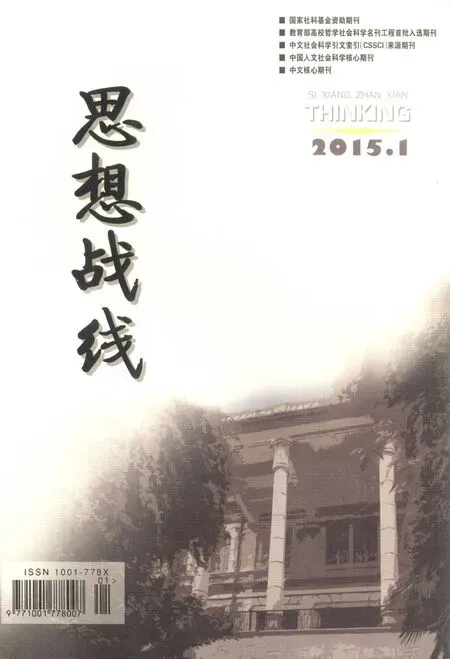破解我國當代鄉村治理困境的文化路徑
李 婭
“鄉村治理”一詞最早于1998年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政治學者提出。隨著研究視域的拓展,“鄉村治理”在“村民自治”升格為“村治”后延伸而來。正如賀雪峰精煉的界定:“鄉村治理是指如何對中國的鄉村進行管理,或中國鄉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
一、我國當代鄉村治理困境
目前我國鄉村治理所遇的困境,主要是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內生權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衡。即在國家權力的引導下,鄉村社會缺乏內在發展動力,鄉村治理能力較低。具體而言之,稅費改革后的中國鄉村社會呈現出“國退民進”的過程,國家權力從顯性層面退出了,但是依舊在鄉村治理中產生隱性影響。例如村黨委會是國家政權在基層的代表;再如《村民委員組織法》文本規定鄉鎮與村委會的關系為“指導與被指導”,但由于權力行使的慣性,加之稅費改革后的鄉鎮政府擁有分配惠農資源的權力,最終文本規定的指導、協商關系被異化為“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除此之外,鄉村社會的內部力量相對薄弱,極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自我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我國當代鄉村治理過程中,國家政權的角色已從前臺轉移到幕后,但不可能完全退出,鄉村治理必須倚靠國家政權的主導。正如徐勇教授曾言:“單靠脆弱的小農是難以支撐一個龐大的農村現代化體系的。”①徐 勇: 《關于支撐農村現代化體系問題的思考》,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49139/49143/3779138.html,2005—10—18。同時,“現代國家是不可能放棄,也不應該放棄對鄉村社會的管制,這是因為,如果沒有國家強制性的影響,傳統農業不可能走向現代農業。”②劉 濤、王 震:《中國鄉村治理中“國家—社會”的研究路徑——新時期國家介入鄉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7年第5期,第60頁。因此,當代國家政權隱性滲入鄉村治理是必要的,破解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內生權力失衡的困境只能從后者入手,即充實鄉村社會的內部力量。
二、文化破解我國當代鄉村治理困境的機理
鄉村社會內部力量的充實離不開鄉村本土文化的滋養。這里所言的文化,不僅僅局限于擁有某種載體的具象文化,也包括鄉村治理過程中文化的環境和氛圍。接下來,將從文化與鄉村治理存在的內在機理出發,探討文化路徑選擇的可行性。
文化與鄉村治理的互動關系可以分解為兩個方面:第一,文化是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經過數千年的歷史積淀,每個鄉村地域范圍內都形成了獨特的鄉村文化,這個文化具有粘合一定鄉村地域內的社會成員的功能,使得他們在地緣基礎上形成一定的歷史文化認同感,并且是“自愿認同”而非“強制性認同”,最終穩固了鄉村治理的社會心理基礎。第二,鄉村治理為文化發揮應有之效提供了平臺。目前,當代中國鄉村治理的現實用“木桶短板理論”最能詮釋。鄉村民主政治在制度、政策等工具理性的助力下有所成效,市場經濟的高速運轉也帶動了鄉村經濟的發展,然而相比之下,鄉村文化仍在蹣跚而行。正因為當代鄉村治理出現結構性缺陷,這為鄉村文化功能的發揮提供了新的契機。總之,鄉村文化與鄉村治理是歷史進程中的適應性聯系,無法將它們割斷而視之。從文化的視角破解當代鄉村治理困境不僅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須的路徑。
三、文化破解我國當代鄉村治理困境的方式
事實上,不僅城市社區與鄉村社會存在較大的異質性,而且不同地域的鄉村社會也各有其特點,無論是經濟水平、傳統習俗、民族構成,抑或地理環境等,都是非均質的。因此,筆者無法從文化的視角提出一條萬能的破解我國當代鄉村治理困境的操作路徑,只能在思想上拋磚引玉。
(一)關注傳統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銜接
傳統文化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概念,其內容并非一成不變,畢竟社會歷史在不斷地前行,當下的現代文化經年累月之后也將被視為傳統文化。那么,如何對接傳統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這是我國當代鄉村治理過程中的重要立足點。誠然,盡管傳統鄉村文化經過歷史的沉淀,但仍有與現代文化難以接軌的成分。只有深度挖掘傳統鄉村文化中的優秀因子,改造其中拒斥現代文化的成分,才是傳統鄉村文化“吐故納新”的基本思路。同時,現代文化也有優劣之分,并不是所有的現代文化都能夠為國家治理所用。在我國當代鄉村治理背景下,銜接傳統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過程中,必須摒棄現代文化中的負向因子。簡而言之,傳統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對接、融合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并非傳統鄉村文化單方面地靠攏現代文化,而是保留二者的優良成分為我國當代鄉村治理構建新的文化格局。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銜接,并不是一種具象的、可視的文化載體互換行為,而是傳統意識吸納現代價值的抽象過程。
(二)因勢利導鄉村宗族組織
我國當代鄉村社會中,宗族組織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但傳統功能尚未完全消逝,它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產生正負兩方面的影響。首先,宗族組織作為傳統權威的代表,已然能夠獲得族內成員的認同。正如有的學者所肯定:“事實上,在調解鄉村社會糾紛方面,在社區公共秩序尤其是基于道德層面的人倫秩序維持中,宗族可能比村級政權組織的作用來得更為有效。”①龔志偉:《和諧與沖突:社會變遷中宗族復興與鄉村治理的關系解讀》,《理論與改革》2006年第1期,第67頁。換言之,宗族組織能夠憑借自身的道德力量解決部分鄉村事務。另外,宗族組織還經常承擔各類宗族活動,此類宗族內部公共行為能在精神層面滿足其成員的心靈寄托,不使他們在現代化進程中喪失內心歸屬感。其次,宗族組織也不可避免地與鄉村治理發生沖突。宗族組織是一個以姓氏、血緣和地緣為基礎而構建的共同體,它必定要追求、實現和維護本宗族的利益。在鄉村地域范圍內,能夠滿足宗族利益剛性需求的途徑無外乎村干部的選舉。可見,宗族組織也是消解鄉村治理過程中民主與法制理念的潛在動因。總體而言,宗族組織對鄉村治理具有穩定秩序的積極功效,也有威脅民主化進程的消極影響,如何趨利避害?筆者認為國家應當引導宗族組織的良性發展。既憑借其宗規族約凝聚鄉村社會,又加強國家民主法治理念的下滲,日漸消解宗族組織的負面影響。
(三)加強鄉村文化與鄉村經濟的融合
鄉村治理過程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共同聯動的社會行為,從文化視角破解我國當代鄉村治理困境是鄉村文化對鄉村政治發展需求的回應,在這個過程中,文化也必然要與經濟有所互動,才能為鄉村治理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事實上,當代的文化與經濟是一種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新型關系,只有兼具文化內涵與經濟價值的物品才具有持久性的競爭力。鄉村文化與鄉村經濟之間的關聯亦遵循此邏輯。因此,我國當代鄉村治理過程中,加強鄉村文化與鄉村經濟結合的方式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另外,我國目前面臨復雜的國際文化競爭形勢,西方強勢國家利用各種手段將其文化意識輸入他國,企圖弱化他國的文化價值,擴大本國文化的影響范圍,甚至有意成為全球主流文化,最終控制世界話語權。因此,我國當代基層治理不僅要重視鄉村文化,更要發揮鄉村文化的經濟價值,提高鄉村社會內部的生產力,進而以強勢的經濟力量反作用于鄉村文化,推動鄉村文化再度發展,如此循而往復,構建鄉村文化與鄉村經濟的良性互動機制。
結束語
前文提出的關注傳統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銜接、因勢利導鄉村宗族組織、加強鄉村文化與鄉村經濟的融合等具體的文化路徑,三者之間并非孤立而行,甚至更多時候是兩者或者三者融合并行。本文基于文化視角提出破解我國當代鄉村治理困境的路徑選擇,意在提升鄉村社會的治理能力,進而推動國家現代化治理之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