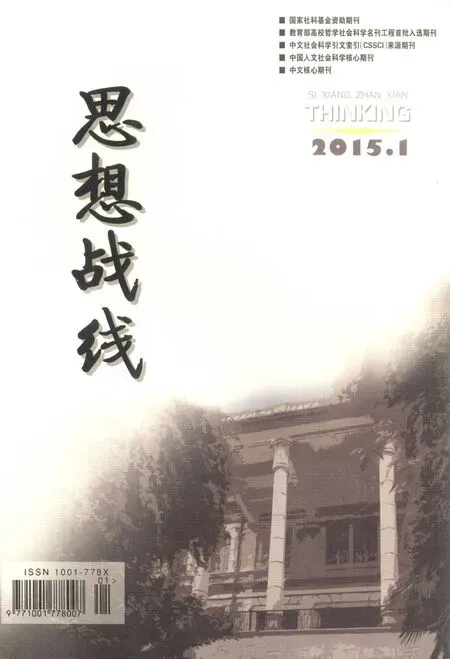中藥意義系統與現代建構
——以“東北野山參”為例
王修曉,孫曉舒
中藥意義系統與現代建構
——以“東北野山參”為例
王修曉,孫曉舒①
作為一味獨特的中藥,真正意義上的東北“野山參”已幾近枯竭,目前市場上銷售的“野山參”乃為大規模生產之物。現代山參之“野”伴隨著一個意義建構過程,屬于一個非常有趣的人類學研究問題。通過對當代“東北野山參”生產、流通以及消費的社會生命史考察,可以發現,中醫思想對東北野山參的意義建構是現代“野山參”延續社會生命的文化動力,由此導致山參之“野”的文化意義不斷地被建構和再生產。在“野山參”的社會生命史中,生態資源、國家制度、民間行為、社會需求與市場行為形成一個相互聯結的聯動模式。
“野山參”;中醫文化;意義建構;物的社會生命史
一、物的人類學
嚴格意義上的東北野山參是指產于中國東北地區、在自然環境中生長,沒有任何人為干預、生長于林下的人參。在清朝末期,東北野山參幾近枯竭,實物形式的東北野生人參幾近消失。其后,民間多用人工培育的方式種植人參。因其生長環境和種植方式的差異,與真正的野山參不可同日而語。有趣的是,“東北野山參”的概念一直延續至今,市場上每年銷售和消費的“東北野山參”規模之大,遠遠超過東北長白山山脈的確存的少量野山參。*據訪談中一位專家介紹,這種“純野山參”每年的產量在20千克左右,曬干后不到10千克。本文以現代“東北野山參”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其社會生命史的全程追蹤和考察,揭示現代山參之“野”的意義建構過程,以及背后的文化動力與實踐邏輯。
人類學向來都是研究“人”、“人性”及“文化”的學問。*莊孔韶:《人類學通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導言。“物”并不是人類學研究的常規論題。然而,人類學對“物”的研究并非局限于“物”本身,而是透過“物”的物質表象,透視“物”背后的文化含義,進而試圖回答兩個問題:“物”如何傳達社會關系?如何經由“物”來理解文化或社會?*林淑蓉:《物/食物與交換:中國貴州侗族的人群關系與社會價值》,載黃應貴《物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年,第212頁。早在西方人類學發展的初期,莫斯(Marcel Mauss)就出色地闡述了蘊含在禮物交換體系中的復雜社會意義:物品通常被賦予所有者的精神特質、靈魂,送出禮物的同時,也是將自己的精神特質送了出去。*參見[法]馬塞爾·莫斯《禮物》,汲 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在與涂爾干(Emile Durkheim)合著的《原始分類》中,莫斯進一步指出,社會的分類決定了事物的分類,社會并不單純是分類思想所遵循的模型;分類體系的分支也正是社會自身的分支。*參見[法]馬塞爾·莫斯,[法]愛彌爾·涂爾干《原始分類》,汲 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列維—斯特勞斯(C. Levi-Strauss)從結構主義的立場出發,認為莫斯人與物不分,只停留在處理現象的表面,忽視了背后深層次的交換關系。他認為,交換才是社會的再現和繁衍的機制,是超越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可以被客觀地加以研究,進而揭示不同類型社會的運作機制。*參見[法]列維—斯特勞斯《圖騰制度》,渠 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馬克思揭示出“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認為“商品”之所以神秘,并不在于它的使用價值,而在于它的“形式”表面上看似簡單、平凡,實際上卻“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89頁。
人類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把上述思路做了充分的延伸和推進,認為“物”的意義蘊含在它們的形式、用途和軌跡之中,所以我們必須跟隨“物”本身,通過對“物”的社會生命軌跡分析,才能充分把握、理解和解釋與之相關的人的行為。他把這種分析視角稱之為“方法論上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5.這就是“物”的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things)。
這種理念被西敏司(Sidney W. Mintz)在《甜與權力》一書中充分運用。他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用糖的歷史作為例證,力圖證明西方資本主義的崛起,除了其內部的發展驅動之外,還有殖民地經濟(甘蔗莊園及制糖產業)等外生變量的巨大貢獻。通過翔實的史料,西敏司向我們展示了糖是如何從最初的奢侈品和身份表征,隨著資本壓榨和產業發展,逐漸變成一種大眾廉價必需品的。借助“物的人類學”方法論, 西敏司將現代日常生活中再常見不過的糖,放到一個更深遠的歷史進程中考察,*[美]西敏司:《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朱健剛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揭示出物的內在意義與日常生活相關聯,是個人為自己及周圍人的行為賦予的意涵;而其外在意義則與社會組織、體制、權力等相關聯,是“社會組織與族群造成的改變帶來的影響”。*[美]西德尼·W.明茨:《吃》,林為正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7頁。
通過分析布農人對物的傳統分類觀念,黃應貴探討了他們對不同物種的認識、接受與創新的過程。布農人把自然物看成與人密切相關的東西(比如水稻),而通過特殊“知識”或“工藝技術”所創造出來的物,則是沒有主體性的客觀的物,如茶葉。對兩類農作物的劃分,不僅影響了布農人的生產活動,同時還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黃應貴:《物的認識與創新:以東埔社布農人的新作物為例》,載黃應貴《物與物質文化》,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年,第379~448頁。張光直倡導研究飲食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food),*陳運飄,孫簫韻:《中國飲食人類學初論》,《廣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指出中國人具有獨特的飲食文化,其中最為核心的即“食品也是藥品”。我們認為,一個人所吃食物的種類和數量與他的健康密切相關,機體的運行遵循著基本的陰陽原則,體內陰陽不平,可以吃特定食物來調節體內的陰陽失衡。陳有平也認為,食用適當的食物有助于人保持身體的平衡或恢復平衡狀態。*Chen JY,“Chinese health foods and herb tonic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vol.1,no.2,1973,pp.225~247.這種觀念使得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關注滋補品和保健品。蔣斌從中醫思想和中國文化入手,以燕窩為研究對象,借用阿帕杜萊的“方法論上的拜物教”,探討燕窩在中國社會和文化體系中的位置,以及人們用怎樣的修辭和語言來建構燕窩的意義。他發現,燕窩之所以能夠成為可欲的(desirable)消費品,其背后依賴的是知識的斷層和阻絕。*蔣 斌:《巖燕之涎與筵宴之鮮——沙撈越的燕窩生產與社會關系》,載張玉欣《第六節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2000年,第383~425頁。
人類學對食物的研究并沒有將話題和研究對象局限于食物,而是將食物放置于更加廣闊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視其為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一部分。因此,歷史、政治、權力、宗教、意識形態、觀念信仰、經濟制度、生產方式等諸多文化因素都可以用于分析飲食文化。*參見[英]約翰·安東尼·喬治·羅伯茨《東食西漸:西方人眼中的中國飲食文化》,楊東平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美]尤金·N.安德森《中國食物》,馬 孆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美]馮珠娣《饕餮之欲》,郭乙瑤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上述研究脈絡較好地呈現了人類學對“物”的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分析視角。本文將延續這種分析路徑,以“東北野山參”為對象,考察其在生產、流通和消費三個環節的意義建構和再生產過程。
二、“東北野山參”的文化意涵
在中國文化體系中,“東北野山參”絕非通常意義上的中藥或補品,它的身上承載著近乎神圣的文化意蘊。在中醫體系中,任何一味藥都有自身獨特的藥性,藥性理論又是建立在中醫陰陽五行思想基礎上。中醫典籍這樣判斷人參的藥性:
有如人參,或謂其補氣屬陽,或謂其生津屬陰……不能定其性也。余曾問過關東人,并友人姚次梧游遼東歸……與《綱目》所載無異……云人參生于遼東樹林陰濕之地……秉水陰潤澤之氣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發之為三稏五葉,陽數也。此苗從陰濕中發出,是由陰生陽,故于甘苦陰味之中饒有一番生陽之氣……不獨人參然,凡一切藥,皆當原其所生,而后其性可得知矣。*王咪咪,李 林:《唐容川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第534頁。
這段文獻告訴我們:1.藥物與其生長環境遵循相生相克的原理。人參的生長環境是陰濕的,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存活,說明它自身屬陽;2.藥性與陰陽五行密切相關。人參是三稏五葉,三和五都是陽數,所以人參的藥性屬陽。
此外,古代醫家觀察到某些藥物的形狀與人體的器官相似,于是就聯想到這些藥物可能具有治療與其形態相近的人體器官病變的作用,這被通俗地闡釋為“吃什么,補什么”。*至于人參的實際功效,現代中醫學者張效霞認為,中藥的藥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取象比類”來的。他將取象比類原則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1.同聲相應;2.同形相類;3.同色相通;4.同類相召;5.同氣相求;6.同性相從;7.性隨時異;8.性隨地異。參見張效霞《回歸中醫》,青島:青島出版社,2006年,第321頁。清人張志聰著《本草崇原》云:“(人參)其年發深久者,根結成人形,頭面四肢畢具……稟天宿之光華,鐘地土之廣濃……故主補人之五臟。”*張志聰:《本草崇原》,劉小平點校,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年,第1頁。美國人類學家尤金·N.安德森(E.N.Anderson)對中藥“取象比類”所產生的藥效解釋為交感巫術,認為“補”是一個自圓其說的文化體系,是經驗主義事實和心理作用的共同結果。*[美]尤金·N.安德森:《中國食物》,馬 孆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頁。
中醫根據生長環境、生長季節、生長規律和植物本身的習性來判斷中藥藥性。人參的生長季節和生長規律、習性基本上相同,故產地便成了判斷人參品種的重要標志。歷代文獻中也多以產地作為區分人參“品牌”的重要標準。
各地所產人參的優劣等級并非固定不變。自唐代以來,產于山西上黨的上黨人參始終被醫家奉為最好的人參品牌,其中又以紫團人參為最優。*該排名背后,有著深刻的文化意義。清代學者陸烜在其著作《人參譜》中給出了如下解釋:“上黨,今山西潞安府。天文參井分野,其地最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居天下之脊,得日月雨露之氣獨全,故產人參為最良。紫團山即在潞安府東南壺關縣境,尤為參星所照臨者也。”參見陸 烜《人參譜》,轉引自蔣竹山《清代人參的歷史:一個商品的研究》,花蓮:“國立”清華大學,內部資料,2006年,第40~47頁。隨著過度采挖的進行,上黨人參在明朝便不見了蹤跡,遼參便躍居人參榜首位。*謝肇淛在《五雜俎》中寫道:“人參出遼東上黨最佳,頭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李日華在《紫桃軒雜綴》中寫道:“人參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今人參惟產遼東東北者,世最貴重。有私販入山海關者,罪至大辟。高麗次之,每陪臣至,得于館中貿易。至上黨紫團參,竟無過而問焉者。”轉引自蔣竹山《清代人參的歷史:一個商品的研究》,花蓮:“國立”清華大學,內部資料,2006年,第48~50頁。人們認為人參會隨著帝王之氣轉移。*據《晉書·石勒別傳》記述,出生于上黨地區武鄉的石勒(274~333),在其園圃中栽有人參。“初勒家園中生人參,葩茂甚盛”。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人參栽培記錄。石勒于319年稱趙王,建立后趙,應驗了人參“王氣所鐘”的說法。參見許嘉璐《二十四史全譯:晉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年,第2323~2361頁。遼東是清王朝興起之地,是“王氣所鐘”、“地氣所鐘”,遼參自然便被認為是最好的人參。
從各產地人參等級排名的歷史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參等級差序的建立與變遷,更多地依靠文化解讀和意義生產。簡單來說,文化的建構與解釋左右著人們對人參品種的喜好。在清朝,中國人對人參的功效深信不疑,東北人參更是受到醫家、病人的熱衷追捧。傳教士杜德美神父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一現象:
……中國許多名醫就這種植物的特征寫下了整本整本的專著,他們對富貴人家開藥方時幾乎總要加入人參……中國醫生們宣稱,人參是治療身心過度勞累引起的衰竭癥的靈丹妙藥……它能大補元氣……還能使老年人延年益壽……我服用了半支未經任何加工的生人參;一小時后,我感到脈搏跳的遠比先前飽滿有力,胃口隨之大開,渾身充滿活力,工作起來從沒有那樣輕松過……。*[美]杜赫德:《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2卷,鄭德弟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50~51頁。
實際上,早在杜德美之前,另一個法國傳教士李明便在1696年巴黎出版的《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中提到過人參在中國的良好聲譽:“在所有的滋補藥中,沒有什么藥能比得上人參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李 明:《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郭 強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77頁。
一般人參即有如此神奇功效,長年吸取天地靈氣的野山參,更應該是“起死回生”靈丹妙藥。故而,“野”這個概念,便引起上達天子下至百姓的無限遐想。
人參在滿語里叫做“奧爾厚達”,“奧爾厚”意思是“草”,“達”表示“首領”、“頭人”,所以“奧爾厚達”是百草之王的意思。單純理解,“野山參”是指從種子落地生根、到整個植株的生長過程均在野生狀態下完成,沒有任何人工干預的、生長于深山密林中的人參。但是,縱觀廣義的人參生命史,“野”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朝代的更迭而不斷變化。
在清朝之前,人們挖采的人參絕大多數都是嚴格意義上的“野山參”。但經過亂采濫挖,產量急劇下降,與此同時,需求卻有增無減。在巨大利益的驅動下,清政府采取增加參票、擴大參場的方式,增加挖參的人手,開發新的參源地,以保證東北野山參的產量。但這種行政主導的產業開發政策卻加劇了野生人參的滅絕。于是,人工栽培出來的非野山參便開始出現。
對于民間人工培植人參,清政府的態度是堅決禁止。乾隆四十二年(1779年),清政府下令:“至收買秧參栽種,以及偷刨參秧貨賣等弊,即將此等人犯嚴拿究辦,一律治罪。”*《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33,乾隆四十二年條,轉引自叢佩遠《東北三寶經濟簡史》,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年,第151頁。道光十三年(1833年)史料記載,吉林地區“不法之徒往往布種栽秧,實為參務之害”。*《清宣宗實錄》卷230,轉引自叢佩遠《東北三寶經濟簡史》,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年,第155頁。嘉慶八年(1803年)正月二十四日的上諭云:
人參乃地靈鐘產,如果山內有大枝人參原應照例呈進,尚實無此項大參,不妨據實聲明,何必用人力栽養,近于作偽乎。況朕向不服用參枝,但揆知物理,山內所產大參,其力自厚,若栽養之參即服用亦不得力。*《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8冊,第27頁,“嘉慶八年正月二十四日”。轉引自蔣竹山《清代人參的歷史:一個商品的研究》,花蓮:“國立”清華大學,內部資料,2006年,第168~169頁。
從嘉慶皇帝的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統治者認為用野生的人參較人工培養的人參藥力更大。清政府之所以對人工栽培人參嚴厲禁止,是因為統治者認為,人參的珍貴之處就在于它是天然的地靈,如果不是在純天然條件下生長出來的人參,便是在用人工造假了。
到了現代,國家規定的野山參概念和等級制定,時有改變,總的趨勢是界定標準逐漸放寬。關于野生人參最早的國家標準是成文于1984年的《七十六種藥材商品規格標準》,只是簡單明確“野生者為‘山參’,栽培者為‘園參’”,沒有涉及野生“山參”的具體評估指標。*國家醫藥管理局,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七十六種藥材商品規格標準》國藥聯材字(1984)第72號文附件,054條關于“人參”的表述,http://wenku.baidu.com/view/3147b4a4b0717fd5360cdcba.html。1995年、2000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同樣沒有規定具體的野生范疇。
真正對人參經濟有決定性影響的質量標準是在2002年出臺的國家標準《野山參分等質量》(GB/T18765-2002)。該標準指出,野山參系自然生長于深山密林下的野生人參。這個分類標準等級更加細化,且增添了理化指標,在人參經濟產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標準只規定了野生人參的自然生長環境,沒有規定播種方式,也沒有規定生長年限,所以野山參的概念范圍進一步擴大,導致市場混亂,各種類型的山參名目繁多、歸類混亂、難以區分。*婁子恒等:《野山參市場的基本情況及規范市場的幾點建議》,《人參研究》2003年第3期。2003年10月27日,國家標準委參照國家參茸中心的《野山參分等質量》國家標準修改建議,發布農輕函[2003]88號文,將野山參的定義修改為:“自然生長于深山密林下的野生人參或‘林下籽’,經過若干年后能完全體現野山參特征的可視為野山參”,*具體而言,是把從種子時期就已經生長于深山密林下的人參,不管是人工播種還是自然播種的,都界定為野山參;而將人參的秧苗移種于深山密林間的人參則視為移山參。參見http://www.foods-info.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8063。此標準從種植方式上明確區分了野山參與移山參的特點。該質量標準極大地促進了“林下籽”的生產。此時已經收獲了林下參的農戶從中獲得巨額效益,有效帶動了其他農戶的生產行為。
縱觀各種國家標準,我們不難發現,國家機構對于“野山參”、“山參”的判定標準在逐漸降低、放寬。其后果是導致大量人工播種的林下參進入中藥市場,充當“野山參”,參農用人工種植的方式制造“野山參”,也逐漸被默許和認可。
三、“東北野山參”的現代生命史
我們把“東北野山參”的“物的生命史”劃分為生產、流通、消費三個階段(分別對應“物”、“商品”和“補品/禮物”三種社會形態),關注處于不同生命階段的“物”對于相應行動者所承載的不同意義,并用遼寧撫順清原滿族自治縣的甲屯村、河北安國中藥材市場和浙江杭州三個田野分別作為“東北野山參”的生產地、流通地和消費地。
野山參的聲譽價值從清代一直延續到了現在。野山參在大眾心里仍舊是一味帶有神奇色彩的中藥,在中藥材和禮品市場上依舊十分搶手。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場。所以,在野山參的原產地——東北,農民開始采用人工的手段,生產全新意義的“野山參”。筆者主要發現兩種“野山參”的人工生產方式。
遼寧省清原滿族自治縣甲屯村的參農們種植“林下參”的歷史由來已久。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甲屯就有農民開始人工種植人參。W家從1984年開始嘗試在野生山林里種植人參。10多年后第1次挖參,就賣到了1.8萬/斤的價格,之后更有在1年內單靠賣人參就收入了27萬元。這種巨大的經濟利益,帶動了甲屯村民種植人參的熱情。現在,甲屯大部分農民都在自家承包的林地中種人參。
在W家人和其他村民們的認識里,林下參就相當于野山參。原因主要有兩個:1.種下去的人參種子是野生的人參種子,生長出來的人參自然就是“野生人參”;2.更重要的是,林下參完全模擬人參的自然生長環境,不采取任何人工干預方式,就算種下去的是園參的種子,經過10年、20年的野外馴化,經過自然選擇后長成的人參,也就帶有了園參所不具備的“野性”,跟真正的野山參也就沒什么區別了。此外,人參種植帶來的巨大利益,也讓甲屯村村民們進一步堅定林下參就是野山參的信念。
與甲屯地處長白山余脈、三面環山的地理優勢不同,秋窩棚村地勢較平緩,只有一部分臨山,林地較少。黃土廟村則沒有一塊林地,全部是耕地。但是,受甲屯成功經驗的誘惑,農民還是會想方設法種植人參。他們想到的辦法是在自家菜園里種“缸參”。在沒有條件種植林下參的地方,村民積極創造“野生”的條件,模仿林下參生長的環境。
用水缸作為種植人參的容器,原因非常簡單。水缸中裝的是從山上取下的適合野山參生長的土壤,缸壁能夠保證缸中的土壤與外界土壤隔絕,保證人參只生長在山上的土壤中。顯然,人們認為,只要能夠在野生的土壤中完成整個生長過程,那么,人參也就吸收了土壤中的“野”,變成和林下參一樣的“野山參”了。
缸參這種種植方法充分折射出人們對“野”的概念詮釋。不難看出,缸參的出現,完全是人為的操作。為人參提供營養的土壤是人為從山中取下,隔絕在水缸之中的,就連光照也經過了人為的加工,透過大棚才能照射進來。但是,村民卻相信,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出來的人參就是野山參。也就是說,人們認為“野”是可以復制、可以制造的。
如果說,生產階段對“野”的建構還有源可溯,那么流通階段的包裝和人為加工,則充滿了重重迷障,令人更無從考證了。通常來說,作為禮品的人參需要進行層層包裝,才能夠作為“野山參”出售。產自東北的各種人參就是在安國這樣的中藥材市場搖身一變,變成禮品、保健市場中的“野山參”。
商戶對禮品人參的包裝主要分為4個步驟。第1步是刪選,參商通常會選取個頭較大,主根完整,沒有傷殘,蘆頭長,須子多、長,五形俱全的人參。這個環節有很多貓膩,部分商家會對人參做些手腳,如將蘆頭接長、在人參上刻出表示年老的紋路、把須子加長等。最簡單方法是用“502”膠水黏合。第2步是對將人參的主體及根須固定在貼著紅色(或黃色)絨布的紙板上;第3步是將人參裝入各種精美的包裝盒。包裝盒的材質多樣、花樣繁多,有些包裝盒的價值甚至超過其中的人參,向消費者傳達稀有、珍貴等意義;第4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鑒定。鑒定過程主要依靠網絡進行。網上的各種鑒定機構,基本上都是在沒有看到人參實物的情況下做鑒定。被檢驗的每1支人參會獲得獨一無二的鑒定證書、編號、鑒定報告、封條等。消費者根據人參的編號可以在網絡上查到相應的信息。除了這種外包的網絡鑒定,筆者還發現不少商家干脆自己來做“山寨檢驗”。他們認為,這樣既節省了成本,又為消費者帶來了實惠。
不難看出,流通領域是“野山參”意義建構與價格生成的關鍵階段。市場管理局的C主任認為,對于人參而言,“賣的(人)稀里糊涂,買的(人)也稀里糊涂”。也就是說,買賣雙方并不注重人參的實際品質和藥用效果,作為一個禮品,最重要的是外在的“符號”和賦予其身上的意義。所以,外包裝、盒子、鑒定證書等等外在附加因素,往往比包裝里的人參本身還要重要。通過對人參的各種包裝,藥商們除了給人參附加更多的價值,也把文化意義、概念符號附著人參之上,從而不斷生產和再生產人參的“野”性。此時的人參,已經不再作為一味中藥出現,而是被當成禮品來消費。消費者需要的,正是山參之“野”的概念與意義。
江南地區是東北人參的主要消費市場。我們在杭州和寧波的田野調查發現,江南地區對“東北野山參”的消費,主要分為兩種方式。杭州人講究冬至進補,認為冬至是一年當中人體陽氣最弱的時候,趁這個機會要給體質羸弱的人進補。很多人選在冬至以后到杭州市的各大中醫館去抓藥,一直喝湯藥到立春。杭州市著名的幾大中醫館,如胡慶余堂、方回春堂、承志堂等,都集中在吳山廣場邊的河坊街上。每到冬至,這些醫館里便人頭攢動,排隊看病抓藥。我們發現:1.“進補”在杭州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從長身體的孩子,到成年人,再到老人,都有進補的習慣;2.“進補”具有較強的季節性和針對性。按照中醫的說法,冬天人體的陽氣最弱,應當“藏”。民間形象地把進補和流汗聯系起來,認為進補之后不流汗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3.“進補”講究時效和禁忌,要在合適的年齡段補,年幼的孩子進補效果適得其反;4.強調“本真性”,認為與低廉的價格相比,藥品的“本真性”更加重要。
在“進補”觀念的影響下,人參成了杭州人家中常備的補品,幾乎人人的知識儲備中都有關于人參吃法與效果的知識,并且根據經驗總結出相關禁忌。無論是怎樣的吃法,食用人參的消費者幾乎都相信人參的神奇效果,并能夠敘述出于親身經歷或者聽說過的人參救命的故事,并對人參的療效深信不疑。
作為禮物的人參,其流動方向是自下而上的,即由社會層級、地位較低的人群流向社會層級、地位較高的人群。在饋贈禮物時,人參傳達的是“健康”、“尊敬”、“長壽”、“孝心”等祝福和特殊含義。既然是作為禮品,消費者對人參的外包裝、鑒定證書等外在附加的意義要求也就比較高。如閻云翔在《禮物的流動》中提到的,杭州人也實行策略性的禮物饋贈,來維系社會網絡的運作。筆者在調查中發現,某些具有特定意義的禮物只能(或者說,只合適于)出現在某一個禮物圈中,即便禮物本身的價格并不貴重。人參便是這樣的禮物。
與清朝相比,人參作為禮物的流動范圍變得狹小了。禮物的流動方向也發生了變化。原來能夠平級流動甚至自上而下流通的人參,現在只適合于自下而上流動。即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使得人參只適合在特定的禮物圈中流動,超出這個禮物圈,便會對收禮者造成回禮的壓力。
有意思的是,在江南這個“東北野山參”的主要消費市場,消費者對山參之“野”的本真性沒有過多的糾結。這或許是因為人們大都清楚,純正的野山參早已變得可遇不可求,或者對于遙遠的產地和復雜的中間銷售環節無能為力。只是因為文化和傳統的慣習,使得人們還近乎無意識地延續著祖輩們流傳下來的消費和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附著于物品身上的符號和價值體系,在特定的情境下,是可以脫離于物本身而獨立延續的。
四、討論與結論
本文以“東北野山參”為研究對象,以“物的生命史”為線索,探討人們對“東北野山參”這味特殊中藥的意義建構方式和過程。
在《甜與權力》中,西敏司認為糖的消費和傳播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體系發生了權力變遷,甚至是文化的改變與更替。我們卻發現,根植于中醫思想和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意義體系,先于“東北野山參”經濟產業鏈條的出現與發展。在這里,文化變成了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無論是作為藥物還是食物,東北野山參在中國傳統飲食、中醫文化中都占據著相當重要和主流的地位。人參的藥性、藥效在中醫思想體系中有一整套完整的解釋體系。醫家運用陰陽五行的理念,根據東北野山參的生長環境、自身形態等因素,判斷人參的藥性;用“取象比類”思想判斷人參的藥效。雖然歷代醫家對人參藥性、藥效的判定并沒有一致的說法,有的甚至完全相反,但是所有說法均以中醫文化、思想、信仰為背景。病人接受的并非僅僅是藥物,還有其背后一整套的中醫邏輯思維體系。也就是說,病人消費“東北野山參”時,是以接受中醫思想為前提的。
在現代社會,狹隘意義上的東北野山參資源幾近枯竭,但打著“東北野山參”旗號的各種人參依舊活躍于市場。說明消費者消費的不僅是“東北野山參”的實物,而是更加看重其背后承載的文化意義。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認為,在消費體制的引導下,人們對物品的追求已經不再局限于物品本身的性能(即使用價值)了。物品所承載的符號與意義才是現代人們消費物品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物的消費不是對物的占有和消耗,而是指向符號的消費。在消費社會,消費行為已經成為一種純粹的象征行為。*參見[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本文研究的“野山參”之“野”便是被消費的符號、意義。“野山參”的使用價值已經不再重要,單單一個“野”字已經足以成為人們消費人參的真正原因。因此,以實體人參為基礎,“野”成了生產者生產商品時惟一需要追求的目標。無論是種植“野山參”的參農,還是負責包裝、加工“野山參”的藥商,都在積極地制造、建構“野”這個意義和符號體系,供消費者消費。人參作為中藥的藥效及藥性,卻很少被關注。由此,“野山參”的一整套經濟鏈條宣告完成,“野”的文化意義與價格逐漸被制造、加工,最終被消費。
總之,中醫的文化和理念衍生出對“野山參”的需求,進而刺激參農想盡辦法用人工手段制造“野山參”。同時,在國家政策與經濟利益的雙重推動下,“野”的概念認知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于是才有林下參、缸參以及各種網絡鑒定和“山寨檢驗”的出現。可以說,對中醫藥文化的信任與推崇,深深地推動了人們對“野山參”的需求,進一步促進整個“野山參”經濟的繁榮。在這個過程中,有幾個因素值得我們關注,即文化理念、國家制度、市場行為與社會需求。筆者認為,只有把這四個要素看作一個聯動模式,才能把握和理解“東北野山參”的意義建構和再生產過程。人類學對于物的研究目的也正在于此,即通過物來反映和理解社會文化。
(責任編輯 陳 斌)
王修曉,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博士(北京,100871);孫曉舒,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博士(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