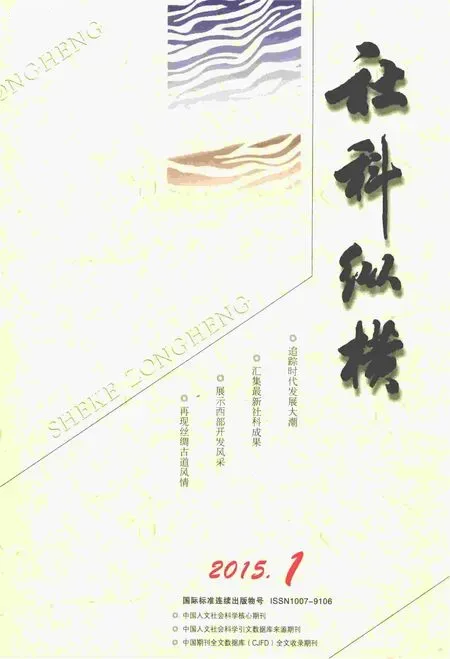尼采形而上學思想中的人化和非人化的矛盾——以海德格爾對尼采的解釋為線索
章 林
(安慶師范學院政治學院 安徽 安慶 246001;南京大學哲學系 江蘇 南京 210023)
在海德格爾對尼采的解釋中,無論是在虛無主義本身中,還是在作為虛無主義之克服的永恒輪回的思想中,存在者整體和人的關系都以緊張的形式凸顯出來。虛無主義標志著“一切最高價值的自行貶值”,也就是說傳統形而上學通過一個超感性領域來規定包括人在內的整個感性的存在者的做法失效了。因為這些超感性領域最終不過表明自身是源于人的構建,也就是說形而上學乃是“擬人論”,而海德格爾認為尼采自己的強力意志學說最終卻是對存在者整體最為極端的人化。同時,在作為對虛無主義之克服的永恒輪回學說中,尼采要求對存在者整體的非人化,而它將作為“最大的重負”要求人們在每個瞬間都要超越自身,從而對人進行了最終的規定。
上面的敘述將尼采思想中的某種困境標識了出來:一方面,尼采試圖從存在者整體中獲得對人性的新的規定;而另一方面,對存在者整體的解釋卻又必須依賴人來完成。由此出發,尼采要求對存在者整體的“非人化”,通過這種非人化,他可以按照自然本身來規定人,將人自然化;與此同時,尼采最終在其強力意志的形而上學中實現了對存在者整體的極端的人化。尼采思想在海德格爾那里表現出來的人化和非人化之間的矛盾,在現代其他思想家那里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現了出來。在洛維特那里就表現為永恒輪回中“宇宙學”因素和“倫理學”因素之間的矛盾,而這種沖突和人化和非人化之間的矛盾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表明了一個共同時代的困境。
對在尼采思想中出現的人化和非人化問題的探討甚至可以說構成了海德格爾尼采解釋的一條隱線。人化和非人化的問題對海德格爾來說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和海德格爾對主體性形而上學的克服聯系在一起的。尼采的困境標識著海德格爾自己的困境:如何在主體性形而上學之外為人性提供新的規定,既然對存在者的人化看來是如此的不可避免?這種主體性的形而上學在其自身的歷史中走向了虛無主義,而尼采對它的克服最終卻是以對存在者整體最為極端地人化結束。強力意志在本質上是一種無規定的狀態。
海德格爾對人化和非人化的思考是和他對主體性形而上學的克服聯系在一起的,而這種克服又是為了給在現代那里“無家可歸”的人尋求棲息之所。在這種克服中,顯示了一個真正思想家運思之艱辛。海德格爾由存在者整體和人的關系走向存在本身和人的關系,并將其規定為:人是存在的看護者。而存在本身是絕對超越的。存在之真理最終為人提供了棲居之所。
一、尼采思想中的存在者整體的人化和非人化之間沖突的顯現
海德格爾對于尼采思想中的矛盾的展現是和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歷史的理解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在對尼采的思想的形而上學特征進行了詳盡地闡釋之后,也即在整個形而上學歷史中對尼采的思想進行定位之后,在權力意志和永恒輪回之間,以及在永恒輪回自身之中,一個本質性的問題顯現了出來。從時間上看,這個問題是在海德格爾對尼采思想的闡釋過程中產生的,并且規定了他后來對尼采的思考。
我們以海德格爾的一段論述作為起點:
正是在形成永恒輪回思想的那個時期里,尼采最堅決地力求在思想上達到對存在者整體的非人化和非神性化。尼采的這種努力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他這個時候正在消退的‘實證主義階段’的一個余音。這種努力有它本身更深的來源。惟因此,才可能出現以下情況:當尼采在強力意志學說中要求一種對存在者的最高人化時,他很快就不得不放棄上面這種努力,被逐入似乎與此努力互不相容的對立面之中了。[1](P345)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海德格爾認為尼采的強力意志學說是一種對存在者的極端的人化,而永恒輪回則是尼采在“最堅決地力求在思想上達到對存在者整體的非人化和非神化”時期的思想,也就是說永恒輪回標示著尼采對存在者整體非人化的堅決要求。但是由于海德格爾注意的是尼采思想作為形而上學的統一性,所以兩者之間的矛盾被套上了模棱兩可的“似乎”。可以看到,在后面對尼采思想的解釋中,這種對“人化”和“非人化”的思考,即便不是被當作主題來探討,也總是若隱若現地暗含于其中。可以說,對海德格爾來說,尼采的這種對存在者整體的人化和非人化的思考絕不僅僅是一種無關緊要的想法,這種思考直接關涉到尼采以及海德格爾自己其思想的處境。這種人化和非人化之思是隨著虛無主義以及由之帶來的危機一同出現的,而海德格爾之所以將其標示出來,是因為尼采的這種思考是和他的存在者整體以及其存在之思是一致的。
二、傳統形而上學對存在者的人化
尼采對存在者非人化的要求是虛無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虛無主義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以前的那些超感性領域自行崩潰了,而這些超感性領域在傳統的形而上學中,規定著整個感性領域。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它們作為存在者的存在規定著全部存在者,包括人(存在者整體和存在者的本質以及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之間的關系)。但是,隨著在虛無主義那里一切超感性領域的失效,尼采也就將整個形而上學的歷史解釋為“謬誤的歷史”①。對于尼采的人化思想,海德格爾如此概括到:
所謂“人化”既包括根據一個創造者的決定對世界的道德解釋,也包括根據一個偉大的工匠(亦即造物主)的活動對世界的相應的技術解釋。但“人化”也包括一切把秩序、劃分、美、智慧強加于世界的做法。所有這一切都是“審美的人性狀態”。當我們把‘理性’歸于存在者,并且斷言世界是合理性地發生的,乃至于接受黑格爾的那個命題——“凡是合理的就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時候也就有了“人化”。不過,即使我們把非理性設定為世界原則,那也脫不了是一種人化。同樣地,在存在者中也并不含有某種自我保存的本能。[1](P342)
在尼采那里,對世界的人化不但包括將美、善、理性等加入其中,也包括將一種非理性加入其中。海德格爾后一句話無疑是說尼采對叔本華的批評,叔本華和克爾凱郭爾一樣,他們自己的理論是以黑格爾的體系為參照物的,叔本華畢生之事就是將黑格爾理性的世界轉變為一個非理性的世界,這個世界的本質就是自我保存的本能,盲目地求生存的意志。而對尼采來說,這種對世界的“非理性化”,同樣也是一種“人化”:
把“自我保存感”歸于存在【指存在者整體(海德格爾加)】!何等荒唐!把“欲與無欲的追求”歸于原子!”[1](P342)
前面說過,尼采對世界“非人化”的想法是和虛無主義一脈相承的。在“虛無主義”那一節中,我們就論述了虛無主義是和那些各式各樣的,處在感性世界之上的超感性世界的失效聯系在一起的。而尼采的“人化”的思想無疑是對形而上學歷史,對他來說,也就是“一段謬誤的歷史”的解釋,也就是說,傳統形而上學中的超感性的東西都是人自己加諸存在者整體之中的,這種超感性是就我們前面說的,以柏拉圖的哲學為隱喻的整個的歷史的解釋。和海德格爾從形而上學自身的邏輯(其中包括存在者整體和人的關系)出發去思考這段歷史不同,尼采則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對這段歷史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尼采這樣說道:
一種統一性,某種‘一元論’形式:而且由于這樣一種信念,人就處于對某個無限地優越于他的整體的深刻聯系感和依賴感中,那就是神性的樣式……‘普遍的幸福要求個體的投身’……但是看哪,根本就沒有這樣一種普遍!根本上,人已經失去了對他自身價值的信仰,如果沒有一個無限寶貴的整體通過人而其作用的話;這就是說,人構想了這樣一個整體,為的是能夠相信他自身的價值。[1](P695)
也就是說,尼采認為傳統形而上學,這段“謬誤的歷史”,完全是出于人自己的構造,為了是能夠“相信他自身的價值”,所以人們才將諸如真、善、美之類的東西放進一個普遍的整體之中。所以就這方面來說,虛無主義乃是一種近乎啟蒙的力量,和柏拉圖讓人們在感性的‘虛假’世界之外看到一個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正好相反,虛無主義讓人們看到自柏拉圖始,整體形而上學世界的虛假,人們構造了這樣一個世界是為了能夠更好地生活在其中。尼采“非人化”的思想在這種虛無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說傳統的形而上學通過對存在者整體的“人化”,而這種人化反過來對人自身進行規定的話,那么尼采的“非人化”就拒斥了這種可能性,也就是說存在者整體或者存在者的存在不再能夠對存在者包括人進行規定了。②為了防止對存在者的人化,尼采說:“相反,世界的總體特征永遠是混沌。”[1](P341)
三、尼采對存在者整體的非人化的要求
海德格爾認為這種“非人化”的思想對尼采來說是“獨一無二的”:
防止對存在者整體的籌劃中發生的種種人化現象,這對尼采來說是多么重要,而關于作為混沌的世界的主導觀念在尼采那里又是多么獨一無二地始終起著支配作用,這一點最清晰地表露在那個甚至在他關于輪回學說的筆記中也再三出現的短語中:‘我們要提防’。其意思就是說,我們要堤防,不可把我們某個任意的觀念,我們的一種能力強行置入存在者之中。[1](P343)
尼采的“非人化”和“非神化”思想在海德格爾那里以一種理論的清晰性表達出來,而這種對存在者非人化的要求在他們之后的思想家那里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就海德格爾的后學而言,我們僅舉加繆和洛維特為例。盡管他們表述的方式各不同,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一樣的。
馬爾庫塞稱加繆的《西緒福斯神話》是直承尼采的遺響,這篇影響甚大的隨筆探討的問題甚是明了:“荒誕是否要求死亡,應該在一切思想方法和一切無私精神的作用之外,給予這個問題以優先權……關于自殺的思考使我有機會提出我感興趣的唯一問題:有一個一直到死的邏輯嗎?”[2](P628)加繆稱之為“荒誕的推理”。我們應該看到加繆這里討論的從荒誕出發一直到死的邏輯,已經不是叔本華的從世界的生存意志的本質一直推到人應該自殺的邏輯。因為在后者那里,盲目的生存意志是作為世界的本質的,而在加繆那里,荒誕并不是所謂的世界的本質——“荒誕產生于人類的呼喚和世界的無理沉默之間的對立”。[2](P640)所以,甚至是和叔本華相反,荒誕感首先就表明世界不再給我們的行動提供任何依據了,世界對人來說始終是“沉默”的。加繆說:“有兩件事是確切無疑的:即我對絕對和統一的渴望而這個世界又不可能歸結為一個理性的和合乎常理的原則。”[2](P675)
加繆的荒誕來源于世界的沉默本身,在他那里也是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也就是世界(海德格爾總是將其“翻譯”為存在者整體)不再對人的呼喚提供任何回答,不再對人的行動提供任何規定。從這點說,加繆和尼采是一致的。在尼采那里,傳統形而上學所規定的存在者存在和人之間的聯系就已經斷裂了,人被置入一個混沌的、無限生成的世界中。而且尼采時刻提醒人們不要犯“人化”的錯誤,也就是不要在存在者中置入自己的東西,以便讓這個世界變得更“人性”,這種拒斥本身就表明了現代人這樣的一個信念——以前的“人化”的世界是一種幻象,世界乃是自在的在人之外的,任何想從世界中獲得某種東西的做法都是一種自我欺騙,世界不能給人提供任何東西。這在洛維特那里,就被清楚地表達為:“世界和人之間的分裂”。
可以說在現代哲學那里出現的同傳統形而上學的斷裂乃是世界和人之間關系的破裂的表現。這個破裂乃是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因為尼采的目標不是毀滅而是建筑。也就是說,尼采的目標是在一個傳統的人性所賴以建于其上的整個機制業已失效時,為新的人性尋求根據。在虛無主義這一點上要求對存在者的非人化是一種誠實的表現,因為在這里,世界和人成了漠不相關的兩極,我們不再能從世界(存在者整體)那里來獲得對我們自身的規定了,像在柏拉圖那里的理念世界、基督教的上帝、或者近代那里作為理性的統一的世界那樣指導著人的行動那樣。對世界的“非人化”也就是對世界的“非神話”,也就是在超感性領域不再能夠對我們的行動形成規定,這一方面是超感性領域的失效,另一方面是指超感性領域的虛構性,也就是說這種超感性的價值是人自身投放進去的,然后又作為一種客觀性來規定我們。
四、尼采對存在者人化的要求
但是在力求對存在者“非人化”之時,海德格爾告訴我們尼采又要求對存在者極端的人化。海德格爾引用到:
把世界‘人化’,這就是說,越來越覺得我們就是世界的主宰——(海德格爾,第344頁)[1](P344)
同樣的說法我們在《強力意志》中還有許多,我們試舉一段:
到后來,人在事物中除了重新發現自己的入藏品而外再也不會發現任何東西。——這種再發現,自稱科學。入藏品包括——藝術、宗教、愛情、自豪。有兩群人,——就算是兒戲,人們也應當繼續前進——,應當有勇氣去做這兩種人。——一種人司職再發現,另一種人——我們這一種——司職入藏
對存在者人化和非人化的思想在尼采的思想中同時都可以找到,海德格爾是從其對形而上學的內在統一性出發去解釋尼采的,這種解釋下的尼采的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是權力意志和永恒輪回的統一,是存在者存在的本質和存在者整體的存在方式的統一,是傳統的“essen”(本質)和Existense(實存)的統一。但是在這種主導性的解釋之外,海德格爾還是直面了尼采思想中的矛盾。這種矛盾在不同的人那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但是他們很多都是和在尼采思想中出現的世界(存在者整體)和人之間關系的破裂相聯系的。
也就是說,在虛無主義這一點上出現了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抉擇:一個是認識到存在者本身是不會給予我們任何東西的,我們從存在者那里發現的任何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加進去的。對存在者非人化的要求因此也就是要“直面世界本身”。這個世界是擺脫了真善美,擺脫了一切人性化的東西的“混沌”,它同時就要求我們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對我們自身進行規定,這種規定是和整個傳統形而上學的方式不同的,也就是不再從世界中尋求某種東西來規定我們自身;另一個就是上面引用的那一段所說的,知道世界本身是沒有所謂客觀的、普遍的真實,而這種真實又最終能夠規定我們。從存在者那里發現的任何東西都是虛假的,因為它們都是我們創造的,但是在我們知道了這一切之后,我們更應該將我們自身的東西放到存在者中去,去實現對存在者最為極端的人化。后面一種是在存在者整體和人的關系已經斷裂之時,卻明確地回到存在者整體,以便“繼續前進”。
五、作為問題核心的人的本質的規定
尼采非人化的要求是和虛無主義的邏輯一致的:傳統形而上學通過在感性世界之上構建一個超感性的世界并最終規定感性世界,尼采認為這種傳統的形而上學對存在者整體的解釋是一種對存在者的“人化”,也就是說是人自己將那些東西放進存在者整體中的。而非人化的要求表明了一種決心,這種決心是和啟蒙精神一致的,也就是要活在一個自然的、真實的世界中。其實和傳統形而上學中的人們努力按照他們信以為真的世界那樣生活一樣,在虛無主義的啟示中,在上帝已死的時代里,尼采力求按照一個失去“本質”的世界去生活,這同時也就是不再依賴于存在者整體去生活,因為任何對存在者整體的解釋都是一種人化。根據海德格爾的解讀,尼采的“去人化”的世界乃是“混沌”,而這種混沌也就是強力意志的永恒輪回。至此,海德格爾不得不發問:難道永恒輪回作為存在者整體不又是一種對存在者整體的人化嗎?因為“任何一種關于存在者的觀點,尤其是關于存在者整體的觀點,都已經作為通過人而帶來的觀點而與人相關聯。這種關聯的來源是人。”[1](P349)海德格爾接著推論:“但是,如果說世界解釋不可避免地包含著人化,那么,任何想把這種人化非人化的努力,都是毫無希望的。因為這種非人化的努力本身只不過是人的一種努力,從而說到底還是一種潛在的人化。”[1](P351)面對這種看似不可避免的人化,海德格爾說:
因此,我們對于那種認為本身不可克服的人化的本質性態度也有如下兩種:要么我們勉強接受這種人化,并且活動于那個不相信一切的、但求安寧而無所作為的懷疑者的虛假優越感中;要么我們使自己努力遺忘這種人化,從而認為這種人化已經被消除了,以此方式獲得我們的安寧。[1](P67)
我們不知道海德格爾在這里參照了哪些原型,尼采似乎的確采取了第二種方案。但是與它不同的是,尼采并不是要遺忘這種人化,而是自覺地活動在這種人化之中。因為尼采明確地說:“我們職司入藏”。尼采的那段格言無非是說,人們在世界種除了發現自己已經藏進其中的東西外再也發現不了其它的東西,這些東西我們知道在尼采那里指的是所謂的真實的東西,真、善、美皆囊括其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為了“繼續前進”,也就是說為了不在這種囊括一切的人化中懷疑、無為至死,人們要么繼續在世界中從事“科學發現”,這在尼采那里是“求真理的意志”使然;要么“職司入藏”,這是尼采的夫子自道,也是按照“權力意志”來行事。在尼采那里,真理意志是權力意志的一種,不過是后者墮落的形式。這樣看來,有意識的進行人化是尼采的首選,也就是按照權力意志的本質來生活,有意識地將一些東西放進世界中,并在這個世界中繼續生活下去。所以尼采要對世界進行“徹底的人化”。但是在徹底的人化的同時,尼采也同樣要求對存在者的非人化,并且時刻提醒自己堤防對存在者的人化。
尼采這種在人化的同時又要求非人化,或者說在非人化的同時又乞求人化的矛盾態度是尼采既將永恒輪回視為一種物理的事實,又將其視為一種倫理學的信仰一致的。但是在它們之間并不具有一種嚴格的一一對應的關系,它們之間的一致性來源于一個共同的處境:如何在傳統形而上學之外去重新規定人性?非人化的要求正是在以“擬人化”為本質的形而上學之外去規定人性的努力,而這種努力很快就走向了徹底地人化;而作為一種倫理信仰的永恒輪回可以視為尼采在對對存在者整體的真理的認識之外,完全通過人自身的信仰去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又同時要求一種宇宙學的事實為根基。
人化和非人化的思想最終指向了存在者整體和人的關系問題。海德格爾之所以將人化和非人化的思想從尼采的思想中提出來進行詳細地探討,這無疑是和海德格爾對存在者整體和人的關系的思考相關的。
海德格爾將目光聚焦在存在者整體和人的關系這一問題上,而這個問題最終以人化和非人化之間兩難的困境表現出來。海德格爾認為尼采盡管已經要求對存在者整體的非人化,但是他的強烈意志的形而上學最終是對存在者整體極端的主體化。由此出發,人的并沒有獲得新的、與傳統形而上學完全不同的規定。而海德格爾自己則將人視為存在的看護者,這是和主體性形而上學完全不同的對人的規定。而關于海德格爾的存在之思以及其基于存在對人的“本質”進行重新規定的路徑則是另外一個話題。
注釋:
①在《偶像的黃昏》“‘真實的世界’如何變成了寓言”篇中,尼采自己以其格言的方式對歷史進行了解釋,這段歷史在尼采那里是“真實的世界”如何一步步地成為寓言,也就是如何一步步地失去對感性的世界,也就是非真實的世界的規定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海德格爾那里就是形而上學如何在其自身內一步步達到其主體性的顛峰,從而遺忘存在的過程。這篇的副標題就是“一段謬誤的歷史”。尼采:《偶像的黃昏》,周國平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第26頁。
②我們一直是從尼采對歷史的解釋出發來思考問題的,而對歷史的解釋,我們又是從存在者整體和人的關系出發來進行的。就在尼采對存在者整體“非人化”的要求而言,尼采的“認識論”也是與此完全一致的。
[1][德]海德格爾.孫周興譯.尼采[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法]加繆.郭宏安等譯.加繆文集[M].譯林出版社,2000.
[3][德]尼采.張念東,凌素心譯.權力意志[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