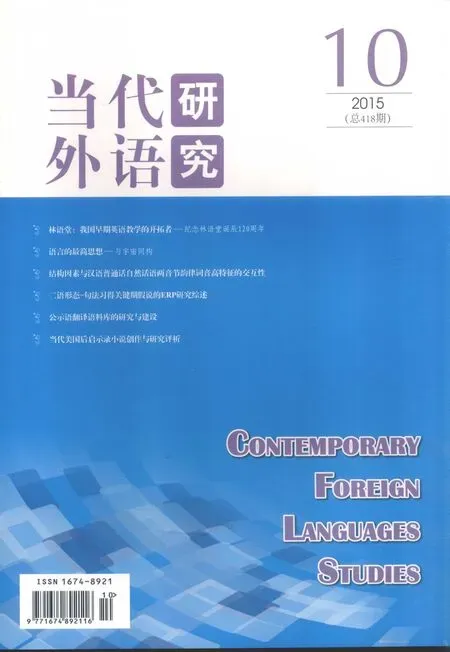戴·赫·勞倫斯短篇小說中的意象觀
邵珊 何江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210016)
戴·赫·勞倫斯短篇小說中的意象觀
邵珊 何江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210016)
戴·赫·勞倫斯的短篇小說有一個明顯特征,即用意象創(chuàng)作。勞氏意象表征了貫穿短篇小說始終的主題支離人。根據(jù)兩者間的對應程度,勞氏意象可分為直指主題和半指主題的意象,前者豐富了傳統(tǒng)意象的內(nèi)涵,后者擴大了傳統(tǒng)意象的外延。同時,勞氏意象是以視覺為主,集聽覺、觸覺、嗅覺甚至動態(tài)因素為一體的雜糅意境,充分激發(fā)了讀者的抽象感知。勞氏意象多重觀感的匯聚流動形成了一動一靜兩個能量渦旋,對現(xiàn)代社會進行了一次從歷時到共時的透視。勞氏能量渦旋記錄了社會效應由外而內(nèi)的轉(zhuǎn)化過程,并揭露了支離人產(chǎn)生的根源,即現(xiàn)代化的解構(gòu)性使巨大的消極物質(zhì)能量變?yōu)楸l(fā)性的精神能量,無處宣泄,引發(fā)現(xiàn)代人精神世界的分崩離析。
戴·赫·勞倫斯,短篇小說,意象,渦旋
戴·赫·勞倫斯一生寫有七部短篇小說,并在其中成功塑造了支離人(the disintegrated individuals)形象。所謂支離人,即指處于西方現(xiàn)代文明重壓下或飽經(jīng)戰(zhàn)爭暴力摧殘后被異化,以支離破碎的心理狀態(tài)孤立生存的現(xiàn)代人。描摹形形色色的支離人是勞倫斯短篇小說最突出的主題。其中有些人物的支離破碎是直接顯現(xiàn)的:《狐》(The Fox,1920/1922)中的“瑪琪在兩性關(guān)系中性別角色錯亂”;《上尉的玩偶》(The Captain’s Doll,1923)中的“亞歷山大在婚姻中無法履行男性角色且被操控擺布”;《瓢蟲》(The Ladybird,1923)中的“迪翁尼斯因被摧毀了男性氣質(zhì)而瘋狂無助,而戴夫妮在婚姻中壓抑窒息”;《烈馬莫爾》(St Mawr,1925)中的“路易莎不安于自我被壓抑,桀驁焦慮”,而“萊科雖安于自我被壓抑,內(nèi)心卻備受煎熬,焦慮不安”。另外一些人物的支離破碎在矛盾中顯現(xiàn):《小公主》(The Princess,1925)中的“多莉自詡為公主高高在上卻為世人所厭棄,是個丑小孩般的存在,只能在無性婚姻中尋求慰藉”;《女孩與吉普賽人》(The Virgin and the Gipsy,1930)中的“伊薇特看似受寵實則為家人所憎恨厭棄”;以及《逃跑的雄雞》(The Escaped Cock,1928/1929)中的“‘他’(即耶穌)重生后放棄了救世使命,陷入存在與生存意義虛無的泥潭,是個行尸走肉般的存在”(邵珊、何江勝2014)。支離人形象是對普通人外表平靜完好而內(nèi)心卻創(chuàng)傷迷惘的概括,外表與內(nèi)心間的張力既使得支離人的言行舉止間滲透出異樣的空洞和絕望,又是支離人形象能量與活力的源泉。
“作為意象派詩人一員的勞倫斯”(Drabble 2005:515)不僅在詩作中奉行它的創(chuàng)作原則,還成功地將意象融入短篇小說中。“意象可以是任何東西,它可以是一副速寫、一個插畫、一段評論、一句格言警句,也可以是印象主義,甚至是詩以外的其它文類(prose)”(Pound 1915:349,轉(zhuǎn)引自Hakutani 1992)。勞倫斯筆下的意象并不局限于“狹義上象征文學作品的某種事物”,還包括“作用于感官上的抽象意境”(Abrams 2004:121)。勞氏意象既豐富多樣又和諧統(tǒng)一,他在每部短篇中都創(chuàng)造出一個主導意象:《狐》中的狐貍、《上尉的玩偶》中的玩偶、《瓢蟲》中的瓢蟲、《烈馬莫爾》中的烈馬、《小公主》中的小公主、《女孩與吉普賽人》中的寵兒,以及《逃跑的雄雞》中雄雞。這些意象表征了不同情形的支離破碎,根據(jù)意象與主題支離人的對應程度,勞氏意象可分為兩類:直指主題的意象,即較全面概括支離人的意象,如狐貍、玩偶、瓢蟲和烈馬;半指主題的意象,即僅提煉矛盾的支離破碎中矛盾一方的意象,如小公主、寵兒和雄雞。
直指主題的意象是對直接顯現(xiàn)的支離破碎的正面描摹,并通過類比豐富了傳統(tǒng)意象的內(nèi)涵;半指主題的意象是對在矛盾中顯現(xiàn)的支離破碎的襯托,并通過反語擴展了傳統(tǒng)意象的外延。同時勞氏意象還具有雜糅的意境,直指主題的意象形成的動態(tài)意境和半指主題的意象形成的靜態(tài)意境充分激發(fā)了讀者的抽象感知,完善了從支離人到意象的投射。勞氏雜糅意境的能量都因共性而互相吸引,形成能量渦旋。兩個渦旋一動一靜,從歷時到共時對現(xiàn)代社會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透視。
1.勞氏意象的內(nèi)涵和外延
勞氏意象立意新穎,意蘊豐富,“擺脫了傳統(tǒng)意象的一般性特點”(薩克文2009:129),是對傳統(tǒng)意象內(nèi)涵的豐富,也是對其外延的擴展。傳統(tǒng)意義上,狐貍是一種弱小、狡猾、善于隱藏的動物,也可指狡詐的人;玩偶是微縮的人形玩具,是傀儡,也指被操控擺布以取樂于人的人;瓢蟲(ladybird or ladybug)這個詞起源于中世紀,“人們謹以這種昆蟲獻給圣母瑪利亞,并稱它們?yōu)槭ツ钢x,是圣母的象征”(Britanica 2010);烈馬是溫和馴服的動物種群中桀驁不馴的另類存在,也可指桀驁不馴的人;公主指身份尤為高貴的皇族直系女性;寵兒是某個社會單位或群體中備受寵愛和關(guān)注的人;雄雞通常是雞群里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唯一雄性,“雄雞啼叫在基督教文化中象征著覺醒、耶穌復生……宣告精神上的黑暗和絕望之終結(jié)……也象征勇敢”(丁光訓、金魯賢2010:719)。勞氏意象中直指作品主題的意象沿用了傳統(tǒng)意象的能指范圍,即狐貍、玩偶、瓢蟲和烈馬原本都可以用來指人,它們的“非一般性”在于使傳統(tǒng)意象的內(nèi)涵多樣化、具體化。而半指主題的則沿用了傳統(tǒng)意象的所指內(nèi)容,即公主、寵兒和雄雞都保持著傳統(tǒng)的意義,它們的“非一般性”在于使傳統(tǒng)意象的外延擴大化。無論是對傳統(tǒng)意象內(nèi)涵的豐富還是外延的擴展,勞倫斯都以新的視角引領(lǐng)著讀者體驗一場細膩而傳神的文字盛宴。
直指作品主題的勞氏意象既脫胎于傳統(tǒng)意象,又與其迥然不同。勞氏狐貍是迷幻誘人而又注定死亡的,既符合傳統(tǒng)狐貍的弱小狡猾,又因注定死亡而不同。勞氏玩偶既是惟妙惟肖的,又是被倒置而無力的,既符合傳統(tǒng)定義之被擺布的人形玩偶,又因被倒置而不同。勞氏瓢蟲既是私密而瘋狂的,又是沉重而壓抑的,它符合傳統(tǒng)圣母圣子間的親密感,又因瘋狂和毀滅而不同,同時它符合圣母被無限弱化的附屬地位,又因自身的不情愿與被壓抑而不同。勞氏烈馬既是桀驁不馴的、會傷人的,又是順從的、焦慮不安的,它一方面符合傳統(tǒng)的桀驁抗爭,又因?qū)δ行缘膮拹憾煌涣硪环矫嫠蠝仨樂N群的順從壓抑,又因時時爆發(fā)的焦慮而不同。
直指作品主題的勞氏意象是對直接顯現(xiàn)的支離破碎的正面描摹,其內(nèi)涵與支離人的境遇性質(zhì)相同。勞氏狐貍的迷幻誘人、注定死亡與瑪琪在同性、異性關(guān)系中的搖擺不定和附屬地位是同質(zhì)的。玩偶與亞歷山大的極度相似和被倒置的無力狀態(tài),是對他在婚姻和社會生活中被妻子操控擺布的“惟妙惟肖的模仿”(939)①。瓢蟲作為家徽“由家族女性親手縫制……繡在襯衣衣領(lǐng)內(nèi)側(cè),緊貼著皮膚”(1073),傳達了圣母圣子間的血肉相連的私密感,表征著流淌于迪翁尼斯血液中的男性氣質(zhì);而“繡在帽子內(nèi)側(cè)……類似諺語中帽子里飛進蜜蜂意指瘋狂”(1073),則體現(xiàn)迪翁尼斯被摧毀了男性氣質(zhì),內(nèi)心狂亂而無助。同時瓢蟲作為寶石頂針“戴在手上很重……這種沉沉的感覺,她[戴夫妮]一邊縫紉,一邊想著自己的丈夫”(1080),通過指向圣母在圣父與圣子間不可或缺卻被無限弱化的附屬地位,表現(xiàn)戴夫妮在婚姻中的壓抑窒息。烈馬的桀驁不馴、會傷人的特征與路易莎對社會禮教的抵觸抗爭,以及對像萊科一樣被馴化男性的厭惡逃避是同質(zhì)的。而被圈養(yǎng)的烈馬終究會像其它的馬一樣溫順恭謙,與萊科雖然“是一匹烈馬”(1061),野性卻時刻被壓制,永遠也無法爆發(fā),而“焦慮不安”(1113)的境遇是同質(zhì)的。
類比實現(xiàn)了從支離人到勞氏意象的投射,透過意象可以清楚地透視支離人,而支離人的種種境遇也使得勞氏意象具體而豐富。“類比是為了顯示兩事物相似的一種比較,通常是為了說明(通過與人們熟知的事物間相似性的比較,來說明不為人熟知的事物)或論證(力圖說明對比的兩事物間,適用于其中一個的原則也同樣適用于另一個)”(李正栓2006:384)。勞倫斯通過重點渲染支離人境遇和意象事物之間的相似性,使人們將后者性質(zhì)自然地轉(zhuǎn)嫁到支離人身上,從而產(chǎn)生相應的投射:瑪琪像狐貍一樣錯亂多變;亞歷山大像玩偶一樣受人擺布;迪翁尼斯像諺語中的瓢蟲一樣瘋狂無助及戴夫妮像代表圣母的瓢蟲一樣壓抑窒息;路易莎像烈馬一樣桀驁不馴及萊科像被圈養(yǎng)的烈馬一樣野性被壓抑而焦慮不安。類比的使用使支離人形象與日常生活經(jīng)驗和事物相聯(lián)系,消除了支離人形象的陌生感,也賦予老生常談的日常事物以不同的解釋,令人耳目一新。
半指主題的勞氏意象沿用傳統(tǒng)意象的所指內(nèi)容,卻顛覆其能指范圍,將意象所指投射在與傳統(tǒng)能指完全相反的范疇,而新能指范疇是對支離人境遇的概括。在勞倫斯筆下,高貴美麗的公主被用來指代丑小孩(changeling),而丑小孩是民間傳說中在嬰兒時期被仙女偷換后留下的孩子。丑小孩具有不受歡迎、是替代品的性質(zhì),是對多莉為世人所厭棄、只能在無性婚姻中尋求慰藉的處境的概括。深受人們寵愛關(guān)注的寵兒被用來指代吉普賽人,而吉普賽人歷來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是被排斥厭惡的流浪者。由于這些被排斥、游離的性質(zhì),吉普賽人是對伊薇特為家人所憎恨厭棄、被邊緣化的處境的濃縮。充滿活力生氣、斗志昂揚的雄雞被用來指代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肉體存活而精神死亡的代名詞。由于肉體的活力和精神的無力,行尸走肉是對“他”復活后放棄了救世使命、陷入生存意義虛無的泥潭的處境的象征。
半指主題的勞氏意象的新能指與傳統(tǒng)能指間的對立是主題矛盾的縮影。公主與丑小孩間的對立,是對多莉自詡高高在上,事實上卻為世人所厭棄而只能在無性婚姻中尋求慰藉這個主題的濃縮;寵兒和吉普賽人間的對立,是對伊薇特看似是家里和主流社會的寵兒,實則為家人所憎恨厭棄,是個被邊緣化的吉普賽人的主題的概括;而雄雞和行尸走肉的對立,是對“他”復活后肉體充滿旺盛生命力,卻放棄了救世使命,從而陷入生存意義虛無的泥潭的主題的濃縮。
反語(irony)實現(xiàn)了意象和其對立事物間的投射,其通過將處于對立的兩者轉(zhuǎn)換為對等關(guān)系而擴大了傳統(tǒng)意象的外延。“反語作為修辭……特征是說與真實意圖完全相反的話”(Kierkegaard 1989:247)。作者利用欲說之事與所述之實之間的張力,實現(xiàn)一種欲蓋彌彰的效果,從而建立對立雙方的投射關(guān)系。所謂小公主,喻指多莉自詡的冷漠疏離的貴族姿態(tài),而丑小孩作為替代品帶有勉強和不盡如人意之感,象征多莉在兩性關(guān)系中被閹割的處境。多莉身上所表現(xiàn)出的嫌惡世人與被世俗關(guān)系遺棄的對立,變相顯示了她作為不合時宜存在的支離破碎。所謂寵兒,是伊薇特那些道貌岸然、“卻彼此憎恨的家庭成員們”(1260)為了掩蓋她被遺棄的真實處境而營造出的假象。同時流浪、被遺棄的處境傳達了伊薇特內(nèi)心的真實的感受,反映了她的挫敗與壓抑。雄雞旺盛的生命力喻指“他”被動獲得的生命,而行尸走肉的生存狀態(tài)象征了“他”生存意義的虛無。當一個神之子否定了為人類救贖的使命,“他”的存在就成了一種悖論,存在的事實凸顯了意義的虛無。反語將原本格格不入的事物和意義聯(lián)系在一起,使二者相斥相生,建立了處于張力中的和諧。
2.勞氏意象的雜糅意境
勞倫斯在創(chuàng)造文字盛宴的同時,還以雜糅的意境為讀者營造了一場華麗的感官盛宴。勞氏意象突破了傳統(tǒng)意象單純的視覺性,并不局限于“對某種事物或場景的視覺再現(xiàn)”(Abrams 2004:121),而是一種以視覺為主,集聽覺、觸覺、味覺、嗅覺甚至動態(tài)因素為一體的雜糅意境。透過意象的折射,讀者對支離人的認知由平面直觀上升到立體會意,而折射的基礎(chǔ)是意象與支離人間直接或間接的共性。因此雜糅的意境充分激發(fā)了讀者的抽象感知,完善了從支離人到意象的投射。
直指作品主題意象的意境大多是動態(tài)的,以變化交錯的視覺畫面為主,并伴隨其它感官感受及抽象感知。勞倫斯用細節(jié)描述和典故引用構(gòu)建能激發(fā)全方位感官感受的雜糅意境,影射支離人的境遇。作者筆下的狐“是魔鬼……總在她們(瑪琪和女友)眼皮子底下偷家禽……讓她們氣惱……溜得太快,根本捉不住”,又經(jīng)常“在草叢中悉索潛行,若隱若現(xiàn)”(1006-1007),一旦現(xiàn)行總會讓瑪琪陷入“白日夢、半催眠中”(1008,1009,1010,1013,1022)。這些關(guān)于狐的細節(jié)描寫營造出迷幻效果,作用于視覺、聽覺以及抽象感知的動態(tài)意境,暗指瑪琪與女友間模糊曖昧,卻令其不滿的性別角色。夜晚的夢魘中,瑪琪“順著狐貍的歌聲拼命追逐,卻被狐尾掃中,被烈火灼燒”(1015),看見“女友躺在棺材里,只能以狐皮覆身”(1031),而“最終死去的狐被倒吊著……被剝?nèi)テっ保?031-1032),營造出作用于視覺、聽覺和觸覺的動態(tài)意境。追逐灼燒的細節(jié)影射瑪琪內(nèi)心對兩性關(guān)系的渴望,而死亡、剝皮則暗示她在兩性關(guān)系中注定無法實現(xiàn)自身想要的性別角色的結(jié)局。玩偶“穿著緊身的蘇格蘭呢子褲……是蘇格蘭人”,和“可憐的玩偶頭朝下、雙臂無力的聳拉著”(939)這些描述創(chuàng)造的意境偏靜態(tài),主要作用于視覺。前者象征高原人堅毅、豪邁的性情,后者影射壓抑亞歷山大真實性情的婚姻狀態(tài),并暗示著他在兩性關(guān)系中始終支離破碎的結(jié)局。“幾百年來,瓢蟲一直繡在[迪翁尼斯的]家族帽子內(nèi)側(cè)”,“一個正常的世界業(yè)已毀滅……讓我[迪翁尼斯]像瓢蟲一樣瘋狂吧”(1073),這些細節(jié)創(chuàng)造出了作用于視覺和抽象感知的動態(tài)畫面,暗示著迪翁尼斯男性氣質(zhì)的錯亂顛倒和他在瘋狂的世界里做一個沒有意義的存在的命運。同時戴夫妮陷入與丈夫不愿親熱和與情人迪翁尼斯不能親熱的兩難處境,只能作為一個“處女般貞靜的存在”(1106),和“你[戴夫妮]無論生死,都是瓢蟲[迪翁尼斯]在夜間的妻子”(1105,1108)的意境是靜態(tài)的,主要作用于視覺,暗示了戴夫妮作為被閹割的存在的遭遇。烈馬對于路易莎來說,是個“魔鬼”(1121),散發(fā)著“黑色的、隱形的火焰”(1119),卻又“像一個從黑暗中張望的神祗……散發(fā)著白色的、刀鋒般的冷冽”(1121),這種黑白交錯、有形與無形雜糅、魔鬼與神祗共存的矛盾修飾法創(chuàng)造出作用于視覺、觸覺和抽象感知的動態(tài)意境,暗示著路易莎桀驁不馴的內(nèi)心及對文明世界壓抑人的自我的外部抗爭。對萊科來說,烈馬“存在于一個希臘英雄們、包括希波呂托斯在內(nèi)……的時代”(1124),并“充滿力量……蠢蠢欲動,伺機報復”(1121)。神話典故的運用將烈馬塑造成一個破壞者,一匹摔死神之子的馬,這種意境是動態(tài)的,主要作用于視覺和抽象感知,影射萊科倍受壓抑自我的煎熬的內(nèi)心以及焦慮不安的處境。
勞倫斯還通過明喻將雜糅意境與支離人境遇間的暗示影射變?yōu)閷嵲谥干妗!懊饔魇且环N……對比較之物與被比之物間共性的衡量……通過使用鮮明的意象來表現(xiàn)兩者間常識之外的聯(lián)系——比較通常不能比較的事物間的相似性”(Israel et al.2004:124)。以細節(jié)描述和諺語典故引用影射支離人的關(guān)鍵,在于它們所創(chuàng)造的意境畫面盡管多變甚至抽象,卻緊緊圍繞著意象事物的內(nèi)涵這個核心,是對意象事物內(nèi)涵的立體化:無論狐貍在白天時的詭詐飄忽還是夜夢中的被屠戮,都反映了瑪琪在兩性關(guān)系中的搖擺錯亂;玩偶被扭曲倒置的畫面反映了亞歷山大在婚姻中被操控擺布的處境;瓢蟲在瘋狂的世界中飛行的畫面,反映了迪翁尼斯被摧毀了的男性氣質(zhì);瓢蟲夜間是妻子、白天像處女的畫面反映了戴夫妮在婚姻中壓抑窒息和被閹割的狀態(tài);烈馬無論是像魔鬼散發(fā)黑色火焰,還是像神祗充滿冷冽氣質(zhì)的畫面,都反映了路易莎桀驁不馴及對文明世界壓抑人的自我的不滿;烈馬像破壞者般報復的畫面,反映了萊科倍受自我壓抑的煎熬,從而焦慮不安的內(nèi)心。同時,意象事物的內(nèi)涵與支離人之間是類比的,具有同質(zhì)性,因而意境與支離人之間是同質(zhì)而不同類的關(guān)系。這種共性確立了文字描述和視覺及其他感覺所呈現(xiàn)的氛圍間的投射,促成了支離人和意境間前者像后者的明喻關(guān)系。
半指主題意象的意境主要是靜態(tài)的,以特寫畫面為主,以調(diào)動讀者的抽象感知為輔。作者通過靜與動、具體與抽象間的張力,象征意境與支離人境遇間的矛盾沖突,以激發(fā)讀者的抽象感知。在勞倫斯筆下,有的意境在和諧中隱晦地透露出矛盾之處,即主體畫面是對主題中矛盾的某一方的具象化,卻又在細節(jié)上隱晦地透露出矛盾的另一方:小公主多莉“像從畫兒里走出來的美人”(1227)、“像無性別的仙子”(1229)和“像永不結(jié)果的花朵,裝腔作勢、格格不入”(1228)。作者用美人、仙子、花朵表征公主所傳達的美麗優(yōu)雅和高貴身份,形成了靜態(tài)的華美畫面,而無性別、不結(jié)果的被閹割感是滲透于畫面中的抽象感知,因而意境隱晦的矛盾在于華美精致總是伴隨著被閹割感。有些意境是和諧統(tǒng)一的,畫面僅體現(xiàn)主題中矛盾的一方,與主題另一方的支離人境遇形成鮮明對照,而二者的矛盾沖突調(diào)動了讀者的抽象感知:如伊薇特“活得有些沒心沒肺”(1259),“總是心不在焉的樣子”(1262),“年輕、柔美的臉上透露出絲絲剛愎任性,顯得有些冷酷”(1272)。這組人物特寫主要是靜態(tài)的,玩世不恭、冷酷疏離是伊薇特身為一個寵兒所流露出的特質(zhì),而她作為支離人的真實處境被轉(zhuǎn)化為“自負……對主流社會嘲諷質(zhì)疑”(1272)的吉普賽人形象。玩世不恭、冷酷疏離的寵兒姿態(tài)和憤世嫉俗卻被邊緣化的吉普賽人形象間的鮮明對比是對矛盾主題的模擬,兩者間的對立激發(fā)了讀者的抽象感知。雄雞“側(cè)著頭,傾聽著來自陌生世界里未知同類的挑戰(zhàn)聲”、“并以響亮的啼鳴應戰(zhàn)”和“它上下?lián)潋v、全力掙扎”(1320)。這組特寫是動態(tài)的,意在調(diào)動讀者的視覺、聽覺,而“他”作為支離人“對重生感到厭惡”“充滿幻滅”(1324),行尸走肉式的處境反映了精神和肉體上的靜滅狀態(tài)。斗志昂揚、不屈不撓的形象將雄雞宗教意義上的特質(zhì)動態(tài)化、具象化,與支離人內(nèi)心肉體的靜滅間的對立形成了對矛盾主題的立體化。
勞倫斯通過暗喻實現(xiàn)意境與支離人境遇間相斥相生的對應關(guān)系,將由反語實現(xiàn)的文字上的對立對等轉(zhuǎn)化為抽象感知的對立對等。“暗喻源于兩者(即比較之物和被比之物)間相通的日常體驗……選擇性地將一個領(lǐng)域的觀念投射在另一個領(lǐng)域上……即創(chuàng)造兩個領(lǐng)域間的共性”(Israel et al.2004:124)。作者或是利用意境中隱晦的不協(xié)調(diào)感與支離人境遇的矛盾感間的同質(zhì)性,或是直接利用意境與支離人境遇間的矛盾沖突間蘊含的同質(zhì)性,創(chuàng)造性地將靜態(tài)或動態(tài)的感官感受轉(zhuǎn)化為抽象感知,完善從意象到支離人的投射,而矛盾沖突始終是這種投射不變的核心。美人、仙子和花朵是無性別和不結(jié)果的,華美畫面與被閹割感間的矛盾,與反語所實現(xiàn)的多莉看似是小公主實則為丑小孩的矛盾是同質(zhì)的,暗喻利用這種同質(zhì)性將文字領(lǐng)域的體驗投射在感官領(lǐng)域上。而對于單純的意境,暗喻則實現(xiàn)了由內(nèi)在世界至外部畫面的投射:如伊薇特外表玩世不恭、冷酷疏離而內(nèi)心卻自信自負的意境,體現(xiàn)了表里不一的對立,與伊薇特看似是寵兒實則被嫌惡、是被排斥的吉普賽人的處境間的對立是同質(zhì)的。又如,斗志昂揚、不屈不撓的外在畫面和被動幻滅的內(nèi)心間的對立,與“他”肉體充滿生氣而內(nèi)心卻死氣沉沉間的對立是同質(zhì)的,暗喻正是藉由這種同質(zhì)性,將文字上的矛盾統(tǒng)一轉(zhuǎn)化為抽象感知的對立統(tǒng)一,完善了由支離人到意象的投射。
3.勞氏意象的能量渦旋
無論是直指主題的意象,還是半指主題的意象,雜糅意境對讀者感官和抽象感受的調(diào)動都是意象能量與活力的體現(xiàn)。“意象是一個(觀感)匯聚的節(jié)點或集合;它(意象)必然會成為渦旋——一個各種觀感因不斷產(chǎn)生、凝練、回歸而生生不息的循環(huán)”(Pound 1914:469-70),而且“形成渦旋的意象充滿了能量”(Hakutani 1992:47)。每個勞氏意象都是匯聚多重觀感的集合,充滿了能量與活力,而每組意象的意境都因擁有相似的性質(zhì)而互相吸引,產(chǎn)生流動。同時能量因流動而融合凝練,釋放出新的渦旋。直指主題的意象間的共同能量體現(xiàn)在視覺上色調(diào)的變化和感官上動靜間的過渡,意境在這兩方面的融合凝練釋放出的渦旋是一段記錄現(xiàn)代文明歷時演變的動態(tài)短片。半指主題的意象間的共同能量體現(xiàn)在視覺層面和抽象感知層面始終奉行的矛盾感上,即兩極間的相斥使渦旋充滿了爆發(fā)性的力量,而其相生是種限制爆發(fā)的力量,給渦旋蒙上了一層平靜的外表。這個看似平靜實則洶涌的渦旋是對現(xiàn)代社會解構(gòu)性的共時記錄。
直指主題意象間的共同能量體現(xiàn)在視覺上色調(diào)的變化和感官上動靜間的過渡。這組意象像黑白膠片,有的意境畫面黑白分明,是動態(tài)的。如白日夢中狐貍迷離而疏遠,時隱時現(xiàn),夜夢中狐貍被追逐、灼燒、剝皮、死亡。有的意境畫面黑白相間、時動時靜。如瓢蟲在白天貞靜如處女,黑夜時卻瘋狂而毀滅,以及烈馬是黑色的魔鬼,卻像神祗散發(fā)著白色的光芒,像英雄充滿力量卻又躁動不安、伺機報復。還有的意境是空濛且靜止的,如玩偶是被倒置的,四肢無力地聳拉著。這組畫面有從黑白分明到黑白相間再到空濛的灰色的變化特點,和從動到時動時靜再到完全靜止的特點。意境在相似的色調(diào)和動靜兩方面拼貼融合,生成了由黑白分明到空濛灰色、由動而靜的能量渦旋。
直指主題意象間所形成的由黑白分明到空濛灰色、由動而靜的能量渦旋,是一段記錄現(xiàn)代文明歷時演變的動態(tài)短片。其色調(diào)變化力圖體現(xiàn)現(xiàn)代化由啟蒙時的艱難求存到繁榮壯大再到疲軟的軌跡。白與黑、動與靜都是好和壞的代名字。黑白分明的色調(diào)形成記錄了現(xiàn)代化作為歷史必然在發(fā)展初期的先鋒性和進步性,與其在封建勢力的統(tǒng)治下艱難求存形成鮮明對照。黑白相間則記錄了在迅速發(fā)展的中期,現(xiàn)代化全面改造社會生產(chǎn)力的好和對人性逐漸產(chǎn)生異化作用的壞糅合共存。空濛灰色則記錄了后期現(xiàn)代化在推動生產(chǎn)力飛躍方面的遲滯疲軟和將現(xiàn)代人徹底變成支離人的弊端。同時,渦旋的動靜轉(zhuǎn)換記錄了現(xiàn)代化效應由積極向消極的演變。“動”記錄了現(xiàn)代化從萌芽到巔峰的上升過程,以及伴隨生產(chǎn)力的飛躍而來的物質(zhì)財富激增。“靜”記錄了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入平穩(wěn)期后,生產(chǎn)力失去激增魔力所導致的遲滯疲軟,以及伴隨現(xiàn)代化對人生存意義的解構(gòu)而來的支離破碎。
半指主題意象間的共同能量體現(xiàn)在視覺層面和抽象感知層面始終奉行的矛盾感上。勞倫斯所描摹的現(xiàn)代社會似乎是“善”的體現(xiàn):從視覺來看,現(xiàn)代人像公主、像寵兒、像雄雞;從抽象感知來看,伴隨公主身份的崇高地位和美麗精致,伴隨寵兒身份的玩世不恭和萬眾矚目,以及雄雞所傳達的旺盛斗志和生氣勃勃是主體。然而相反的“惡”才是作者真正想傳達的社會現(xiàn)實:從視覺來說,現(xiàn)代人其實是丑小孩、是吉普賽人、是行尸走肉;從抽象感知來說,被閹割感、被邊緣化和死氣沉沉才是隱晦卻又真實的感受。無論是視覺還是抽象感知,作者都在差異最大化的兩級間建立對等關(guān)系,這使渦旋充滿了爆發(fā)性的力量,而對等給爆發(fā)性的力量掩上了一層平靜的外表,因而形成一個看似平靜實則洶涌的渦旋。
半指主題意象間所形成的看似平靜實則洶涌的渦旋是對現(xiàn)代社會解構(gòu)性的共時記錄。現(xiàn)代社會的解構(gòu)性是伴隨現(xiàn)代化進程而來的,人的生存意義的消解造成了人的客觀實在與意義虛無間的悖論。傳統(tǒng)觀念上人的存在是先驗宗教價值的體現(xiàn),而現(xiàn)代化的進程是一個人被物化的過程。當賦予人一切行為以意義的上帝被證偽了,人的存在就不再具有了先驗的價值,人改造客觀世界的行為也不再具有高于行為本身的意義,而僅僅是為了行為而行為,即人從一種價值自在體淪為純工具性的存在,陷入了存在與意義虛無的泥潭。無論是意象的視覺效應還是抽象感知方面,美好外在和殘酷內(nèi)在間的強烈反差是對現(xiàn)代人陷入了存在與意義虛無的概括。因而,這個能量渦旋象征著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不斷加劇的存在與虛無的悖論,渦旋平靜的外表象征了現(xiàn)代人的客觀實在,而洶涌內(nèi)在象征了生存意義的不斷被消解。現(xiàn)代人是一群頂著光鮮靚麗的外表而內(nèi)心荒蕪殘缺的支離人。
4.結(jié)語
勞倫斯通過直指主題意象和半指主題意象所形成的兩個能量渦旋一動一靜,截然相反,并從歷時到共時對現(xiàn)代社會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透視。直指主題意象的能量渦旋是對現(xiàn)代社會外部世界演變的概括,無論其色調(diào)變化還是動靜轉(zhuǎn)換,都按時間軸的推移,記錄了現(xiàn)代化進程中消極效應打破積極效應的壟斷不斷顯現(xiàn)自身的過程。而半指主題意象的能量渦旋則是對現(xiàn)代人內(nèi)在世界的描摹,是懸置了時間概念后,對身處同一社會的整個人群的透視,并透過靜態(tài)的表象挖掘現(xiàn)代人分崩離析的意識形態(tài)。
同時,從歷時渦旋能量的由動到靜,到共時能量渦旋的由靜到動,記錄了社會效應由外而內(nèi)的、動—靜—動的轉(zhuǎn)化過程。靜態(tài)是能量對接的中間環(huán)節(jié),也是社會效應由外而內(nèi)的關(guān)鍵。當直指主題意象的渦旋的社會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失去了外部擴張的積極效應后,其破壞性的力量不再被壓制,由外而內(nèi)作用于人身上,即能量從外部世界流入現(xiàn)代人的體內(nèi),轉(zhuǎn)化成一種使人支離破碎的精神能量。巨大的消極物質(zhì)能量變?yōu)楸l(fā)性的精神能量,無處宣泄,引發(fā)精神世界分崩離析,是現(xiàn)代社會解構(gòu)性的根源。
勞氏意象是一種揭露現(xiàn)代文明解構(gòu)性的創(chuàng)作實踐。意象手法的成功不僅僅在于豐富的感官效應,更在于對當下社會的審視和對現(xiàn)代人生存處境的探究,是通過世界來看人,也是透過人來看世界的嘗試。這種努力使得勞倫斯的短篇超越了小說抒情、敘事的功能,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性質(zhì)。
附注
①文中勞倫斯作品的引文均選自Lawrence(2005)。所引中譯文均為筆者自譯,下引此作僅注頁碼。
Abrams,M.H.2004.A Glossary of Literature Term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ritannica.2010.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Z].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Drabble,M.2005.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kutani,Yoshinobu.1992.Ezra,Pound,Yone Noguchi,and imagism[J].Modern Philology1:46-69.
Israel,M.,R.H.Jennifer,&T.Vera.2004.On simile[A].In A.Michel &K.Suzanne(ed.).Language,Culture,Mind[C].Stanford:CSLI.123-35.
Kierkegaard,S.1989.The Concept of Irony,with Continual Reference of Socrates(Hong V.Howard &Edna H.Hong ed.&tran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wrence,D.H.2005.The Selected Works of D.H.Lawrence[M].Hertfordshire:Wordsworth.
Pound,Ezra.1914.Vorticism[J].Fortnightly Review573:469-70.
丁光訓、金魯賢.2010.基督教大辭典[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李正栓.2006.英國文學學習指南[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薩克文·伯克維奇.2009.劍橋美國文學史(第5卷)(馬睿等譯)[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邵珊、何江勝.2014.戴·赫·勞倫斯短篇小說中的“支離人”研究[J].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68-72.
(責任編輯 玄 琰)
I106.4
A
1674-8921-(2015)10-0067-05
10.3969/j.issn.1674-8921.2015.10.012
邵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現(xiàn)代文學。電子郵箱:nuaashaoshan@126.com
何江勝,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現(xiàn)代文學。
*本文為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青年科創(chuàng)基金資助項目(編號NR201403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