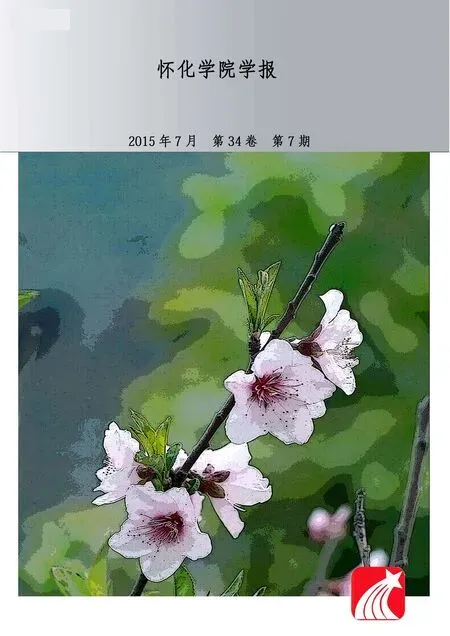“合同履行費用過高”適用研究
(西南政法大學 民商法學院,重慶401120)
一、問題的提出
由于植根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契約必須嚴守”、“法鎖”等理念,我國《合同法》在違約責任章中亦將繼續履行①作為補救合同的首選措施。同時,《合同法》第110條②還對非金錢債務的繼續履行規定了3種除外情形,以期獲得制度與邏輯上的完滿。但始料未及的是,在紛繁復雜的具體案例面前,《合同法》第110條第2項中關于“履行費用過高”的除外規定卻無法大放異彩。
有關履行費用過高的規定存在先天性缺陷:(1)履行費用過高因缺乏具體的認定標準,其結果無疑拓展了法官遐想的空間,致使法官可能濫用自由裁量權;(2)無故摒棄故意違約、債權人的特別保護等考量因素,以經濟合理性來判斷違約方是否應繼續履行,未免太過功利;(3)在特定案件中,經濟利益并非合同目的的終極追求,合同目的所承載的除了物質利益外,尚包括無法量化的精神權利、精神享受等,而此時,若僅以合同履行費用過高為由排斥違約方的繼續履行,不僅踐踏當事人的真實意志,漠視合同特殊目的之保護,而且也很難對守約方進行公平救濟。而更進一步的問題在于:(1)在合同糾紛中如何權衡故意違約、債權人的特別保護、履行費用過高等因素,以決定是否繼續履行;(2)如何認定合同的特殊目的及特殊合同目的是否僅著眼當事人的精神利益;(3)履行費用過高是否應當絕對地排斥強制履行責任方式的應用;(4)若允許強制履行,則應具備哪些適用條件等。諸此問題,筆者將在下文進行系統闡述與邏輯展開,希冀對司法實踐能有所裨益。
二、困境與出路:履行費用過高的認定難題及制度辨析
關于履行費用過高的認定標準,理論界非但未形成一致論調,反而眾說紛紜。如顧全認為,履行費用過高,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1)債務人的履行成本與債務人的收益不對等,在經濟上不具有合理性;(2)債權人的收益與債務人的履行成本之間的不對等;(3)如果履行時間過長,也不適合強制履行;(4)當違約方繼續履行合同所需的財力、物力已超過合同雙方基于合同履行所獲得的利益時,應允許違約方解除合同,用賠償損失來代替繼續履行[1]。葉昌富認為,強制實際履行是一種違約的補救方式,因此這一方式是否適用,應考慮其經濟合理性,如果在經濟上極不合理,不但對當事人有害無利,對于社會也是一種浪費,此時大可不必適用強制實際履行[2]。王洪亮認為如果履行所必要的費用與債務人給付利益之間的關系嚴重不成比例的話,仍然要求債務人履行,不利于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也有違誠實信用原則[3]。再如Reinhard Zimmermann認為履行費用過高的比較標準可以有二,既可以是與另外一種補救履行所需費用相比(相對不合理),也可以是與債權人通過該特定的強制履行所獲得的利益相比(絕對不合理)[4]。可見,學界對履行費用過高的認定標準模糊不定,且主要考慮經濟合理性。
而反觀司法實務界③,對履行費用過高的認定標準亦莫衷一是。實務者大多基于社會觀念、自身經驗、價值判斷、經濟分析等方法來確定履行費用是否過高。而在部分案例中,法官直接援引《合同法》第110條第2項中關于履行費用過高的規定來駁回當事人一方要求繼續履行合同的訴訟請求,用損害賠償等救濟措施來代替合同的強制履行。于是,囿于履行費用過高具體認定標準之艱難,法官在具體適用時大都對此避而不談。
誠然,撇開具體的認定標準,我們仍可基于一般社會觀念、價值判斷、經濟分析、審判經驗等方式粗略地認定履行費用是否過高,繼而促成合同糾紛的迅速解決,且在大部分案件中亦能實現判決公平。然而,將莊嚴而神圣的裁判說理路徑托付給飄忽不定的認定標準和近乎誤打誤撞的現實可能,不僅難以實現裁判結論的穩定和個案公正,而且在理論與邏輯上亦難謂周延與完滿。更顯要命的是,若僅僅因為合同履行費用過高就武斷地終結合同的繼續履行,則在如下案例中必然讓《合同法》第110條第2項有關履行費用過高之規定所殘缺的存在合理性喪失殆盡。
在案例一中,就比較法而言,縱然能確切地證明繼續履行的費用過高,但若B 屬故意違約,則在美國法上可以依據“修復費用”計算A的損失,判令B賠償,其結果與強制履行④相同(類似代替執行)。實際上,此類案件中應綜合權衡的因素頗多,除了經濟因素外,還包括應否懲罰故意違約?應否保護債權人的特別需要[5]610?進而,在類似案件中,絕不能再隨心所欲地通過適用履行費用過高的規定來無理放逐合同的繼續履行。
在案例二中,由于C僅支付了1 000元定金,理性的經濟人E基于效率違約⑤的理念,同時援引合同履行費用過高的抗辯,必將鎮定自若地拒絕履行合同,雙倍返還定金即可。與此同時,若C 欲向E主張其他賠償,則E 還將證明C所受損失的舉證責任無情地附加給C 自身,但此時C 難謂遭受了經濟上的損失。因此,有理由相信,即便最后對C 有其他賠償,也更多地僅具有象征意義。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本案C 與E 簽訂合同絕非僅僅是為了取得鉆戒的所有權,至為重要的目的在于攜鉆戒向D求婚,并收獲極大地精神愉悅和人生最珍貴的記憶。此外,E 對自己的遲延交貨亦有過錯,對C的特殊合同目的更是知情。誠然,本案中法院強制E 履行因需要較長時間而不具實益,但并不意味著強調C的特殊合同目的無意義。此時,若一意孤行地支持拒絕履行,則必然會摧毀C的期待利益,放縱E的違約故意,助長不誠信和引發道德風險,反叛“一諾千金”的處事真諦,最終將使C為E的故意違約買單。
綜上,合同的履行費用過高存在認定難題和規制缺陷,須以《中國民法典》⑥的編纂為契機,對之進行理論審思與制度甄別。同時,僅以合同的履行費用過高來判斷合同是否繼續履行的做法誠不可取,我們還應審查合同是否具有特殊目的、違約人是否存在故意、應否保護債權人的特別需要等因素。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過分倚重經濟效益,必然變相慫恿商人不擇手段地逐利,進而引發嚴重的信用危機和社會問題,扭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若違約方存在故意且守約方能對此加以證明,則應對違約方進行懲罰,即便履行費用過高,也應強制履行⑦。至于合同的特殊目的及保護債權人的特別需要等問題,將在下文展開論述。
三、甄別與完善:債權人的特別需要與合同特殊目的論
(一)概念難題:何謂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至關重要。合同目的在對重大誤解和根本違約的認定上起著決定性作用,實乃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終極追求,集中彰顯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合同法》第60條、第62條、第94條、第148條、第166條等處多次提到合同目的,但縱觀整部《合同法》,其并未對合同目的進行說明,進而引發概念與適用難題。
就比較法而言,英美法系國家的學者在談到契約之要件時,認為其必須以發生法律關系為目的[6]5-6。日本學者認為債的目的在于給付,而給付分為五種:“特定物的轉讓、種類債權、金錢債權、利息債權和選擇債權”[7]21-26,其中選擇債權并不限于經濟目的。盡管前述國家在表述合同⑧目的時的稱謂與我國的表述略不一致,但其本質含義卻是如出一轍,且它們都認為合同目的并不局限于經濟利益抑或經濟目的。
“銀行說是上級行卡了規模,另外也覺得這筆貸款有風險。我向銀行解釋過,這家大企業信譽良好,回款及時,不會拖欠我們的款項,而且我自己企業的回款賬戶可以放在銀行,還有什么擔心的呢?但銀行還是說不行。我覺得銀行在風險評估手段上可以更靈活一些,仔細調研,不要一覺得有風險就干脆不做貸款了。”顧繼宏說。
就國內學界而言,有學者認為,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是指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所追求的目標和基本利益不能實現[8]289。通過反對解釋可知,合同目的即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時所追求的目標和基本利益。亦有學者認為,合同目的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通過合同的訂立和履行,期望最終得到的東西、結果或者達到的狀態[9]。還有學者認為合同目的可以分為“一般目的”與“特殊目的”,前者指雙方當事人各自欲實現的經濟利益目的,它應當得到執行;后者則指出于特殊需求或者動機而產生的目的,必須是明示的、明知的或顯而易見的[10]220-224。
綜上,合同目的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時所欲追求的目標和利益,其并不限于經濟目的,尚包括精神權利、精神享受和其他特定目的。
(二)甄別難題:厘清關聯內容
誠如前述,《合同法》并未對合同目的進行界定,進而導致司法適用上難題。現實的問題是,合同目的的適用在審判中依賴法官的解釋與運用實乃權宜之計。同時,囿于法官法學素養和審判經驗的良莠不齊,必然使類似案件的裁判結果不一致,甚至大相徑庭。而更迫切的問題還在于合同目的與合同動機、附隨義務等究竟有怎樣的關聯,如何對之進行甄別和厘清,以避免理論的混亂。
就合同目的與合同動機而言,筆者認為合同動機內在表現為需求,外在表現為誘因;而合同目的則表現為對預期追求結果的實現。在案例二中,C欲買鉆戒在戀愛十周年紀念日向D求婚即為合同動機,最終C按時取得鉆戒的所有權,并將之送給D且求婚成功和收獲巨大精神愉悅則為合同目的。當然,在有的案件中合同目的與合同動機是難以區分的,只有結合法理、判例、慣例等進行綜合認定。
而附隨義務是指當事人基于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的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合同目的與附隨義務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合同目的對附隨義務的確定具有決定作用。
(三)適用難題:特殊合同目的之認定
筆者贊同將合同目的分為一般目的和特殊目的的做法。同時,筆者認為特殊合同目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精神利益、精神權利、精神享受⑨等內容,案例一中發包人A的預期目的即為著例(其為經濟利益),此外,債權人的特別需要也可納入合同的特殊目的,如此便可實現對守約方抑或債權人的充分保護。
然而,正義的天平誠不可無端傾斜。當事人的特殊目的必須在合同中進行明確約定(未在合同中明示,若有證據進行確切證明亦可),以合理保護違約方抑或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在《霍依與上海中興汽車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2002)滬二中民四(商)終字第576號)的判決中,二審法院法官雖也認為上訴人(原審原告)買車的目的是作為“夫妻相識十周年紀念禮物”,其與一般的合同目的大不相同,理應受到法律保護,但最終判決并未支持上訴人的這一主張,理由就在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并未在合同中對此進行約定,被上訴人亦未預見其違約會帶來如此嚴重之后果。此時,若法院支持上訴人的這一請求,必將踐踏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僭越居中裁判的法官角色。因而,筆者對二審法官的做法亦深表贊同。
綜上,在具體司法實踐中,面對合同特殊目的認定的問題時,應首先甄別當事人對特殊目的在合同中是否有明確約定,對方當事人對此是否知悉并預見后果(只要對方知悉且簽訂了合同,就應推定其已預見后果);若在合同中未進行約定而守約方能舉出確切證據對此進行證明亦可;若既未對合同特殊目的進行約定又未能舉示證據完成證明,則對守約方的請求將不予支持。此外,在對合同條款的理解發生分歧時,有關合同目的(尤其是特殊目的)的條款應具有優先效力,其有助于保證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和合法權益,促使合同的全面履行。
四、規制與發展:強制實際履行之適用條件論
(一)前提論
筆者對合同履行費用過高所生質疑與批判的目的絕非在于顛覆《合同法》第110條第1、2、3項之規定。同時,毋庸置疑的是在大部分案件中履行費用過高的規定確實能簡化法律關系,化解合同糾紛,提高訴訟效率,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存在合理性。而筆者唯一憤懣不平的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僅僅因為合同的履行費用過高就斷然拋棄合同的繼續履行(守約方自愿放棄繼續履行的除外),轉而采取損害賠償等救濟方式,漠視守約方的特殊合同目的與特別需要,致使履行費用過高的規定殃及無辜、誠信、滿懷期待的守約人。事實上,在守約方未支付定金或未與違約方事先約定違約金,加上守約方自身很難證明其遭受了損失,遭受了多大的損失時,守約方的利益難以得到合理救濟,況且在此種情況下,單純的經濟利益并不重要,特殊的合同目的才至為關鍵,若此時仍固執地排斥繼續履行,必定會對守約方造成難以承受之痛。因此,本文是以此為基點進行邏輯展開的,其亦為后文論述的邏輯前提。
(二)要件論
誠如前述,《合同法》第110條第2項中關于履行費用過高的規定由于欠缺具體的認定標準,未考慮違約人的故意、合同的特殊目的等因素,致使其存在先天缺陷和適用難題。筆者認為,履行費用過高并不絕對排除合同的強制履行,而在此條件下,如何規定強制履行的適用條件抑或構成要件以助推其掙脫現行規定的羈絆,誠值研究。
筆者認為即便合同履行費用過高仍應適用強制實際履行的要件應包括如下內容:
1.違約方存在故意
誠然,我國《合同法》是秉承無過錯責任之理念來構建違約責任的,質言之,只要違約方存在違約行為,則無論違約方是否具有過錯,都應承擔包括繼續履行在內的違約責任。而此處之所以規定違約方應存在故意這一要件,實為提高履行費用過高背景下仍適用強制實際履行的準入門檻,增強違約方擔責的正當性(在不存在合同特殊目的,僅有違約方故意且繼續履行對守約方極為重要的情形下更是如此)。若因不可歸責于違約方的事由導致違約行為發生時,絕不可再適用強制履行,應訴諸其他救濟措施。須注意者,違約方存在故意與適用強制實際履行并非充要條件關系,即故意違約并不必然適用強制實際履行(有時可能考慮其他因素),強制實際履行也非僅有故意違約的緣故,有可能是基于合同的特殊目的保護。
2.存在特殊合同目的
如前所述,若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對特殊合同目的進行明確約定,且對方當事人知悉此一目的并能預見違約所帶來的非同尋常的損害后果,則即便履行費用過高,仍應支持守約方要求強制履行的訴訟請求,守約人應負擔證明特殊目的存在的舉證責任。至于在此情形中,強制履行與諸如損害賠償等替代救濟措施、情勢變更、意外事件等的邊界為何,尚待進一步研究。
3.強制履行仍屬可能
首先,若合同事實上或者法律上不能履行,債務的標的不適合強制履行,則即使違約方存在故意、合同存在特殊目的、債權人有特別需要,我們仍應果斷放棄繼續履行,轉而采取損害賠償等救濟措施,畢竟法不強人所難。其次,不可否認的是在部分特殊合同目的場合,強制履行似乎沒有太大實益,如在案例二中,只要超過5月20日履行,即構成合同特殊目的不達,此時應在計算守約方損害的時候將合同特殊目的考慮在內,至于具體的賠償額度,誠不可一概而論,應結合具體案例靈活確定。再者,實際上只有合同的特殊目的所承載的利益足夠巨大時,強制實際履行或進行損害賠償才具有意義,比如有關合同特殊目的的常見例子是異地戀者于情人節在網上為戀人買花,因為賣方的原因而未能按時送花,導致戀人感情出現裂痕,此時買方卻只能索回訂花時所支付的價款(如果提前支付的話),很難謂尚存在繼續履行和主張其他損害賠償的可能。
(三)小結
綜上所述,在合同履行費用過高的情形下并不必然排除強制履行抑或繼續履行的適用,而此時強制履行的適用條件為違約方存在故意、合同有特殊目的、履行仍屬可能,須注意者,此三項要件并非要同時滿足,而是在具體案件中可參照適用。
五、結論
《合同法》第110條第2項中關于履行費用過高的規定存在認定難題,其一刀切地排除繼續履行的做法極不合理。在決定合同是否繼續履行時,除了考慮合同的履行費用是否過高外,還應斟酌違約方是否存在故意、合同是否載有特殊目的、是否蘊含當事人的特別需要等因素。進而,履行費用過高并不絕對排除守約人要求強制實際履行的權利。在目前編纂《中國民法典》的大背景下,我們應對合同履行費用過高之規定進行理論甄別與制度完善,以期對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能有所裨益。
注釋:
①有學者認為繼續履行與強制實際履行同義,僅是提法不同,但繼續履行這一字面含義卻不能體現蘊藏其中的國家強制色彩,故該學者推崇并采納強制實際履行這一表述,參見:葉昌富《論強制實際履行合同中的價值判斷與選擇》,載《現代法學》2005第2期第152頁,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繼續履行除了包括強制履行外,還應包括守約方請求違約方履行,而此種履行并不帶有國家強制且此種履行請求較強制履行更具有普遍的意義,因為通常情況下守約方在違約方違約后應首先請求違約方繼續履行而非徑直訴諸法院或仲裁機關請求強制違約方履行。事實上,違約方并非都如“老賴”那般不堪,在守約方請求繼續履行合同時,有的違約方會積極配合履行,最終實現合同目的。故筆者認為繼續履行是包括強制履行的,二者存在差別。
②《合同法》第110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錢債務或者履行非金錢債務不符合約定的,對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事實上不能履行;(二)債務的標的不適于強制履行或履行費用過高;(三)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
③筆者在北大法寶司法案例中檢索“履行費用過高”關鍵詞,篩選出的案例與裁判文書共484例,其中合同糾紛409例。在如何認定履行費用過高這一問題上,大都采取模棱兩可的曖昧做法。
④須注意:強制履行與強制執行、直接強制有本質的區別,不可混用。強制執行乃緣于違約方對法院強制履行判決的拒不執行,而直接強制為強制執行的一種執行方法。
⑤大約在10年前,學界曾對效率違約展開過熱烈討論,并形成諸多學術研究成果。最終的結果是我國依然堅持將繼續履行作為補救合同的首選,但適當借鑒了效率違約的某些理念。參見:孫國良《效率違約理論研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年第5期;唐清利《效率違約:從生活規則到精神理念的嬗變》,載《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等。
⑥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編纂民法典,標志新一輪的民法典編纂工作正式揚帆起航,民法學界亦是斗志昂揚。目前,正在進行《民法總則》的征求意見稿工作,接著將著手制定民法分則部分,預計2020年左右會出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民法典》。
⑦強制履行發生在法院判決階段,有可能被寫入生效判決的主文,成為強制執行的依據。如前所述,若違約方對此判決拒不執行,則法院將會進行強制執行,依《民事訴訟法》理論,強制執行包括直接強制、間接強制(包括代替執行和執行罰)。此處,切不可將強制執行等同于直接強制。當然,若最終履行不能,則應提高對守約方的賠償額度。
⑧在民法學說史上,亦曾有過“合同”與“契約”的區別。契約為個人法上法律行為之典型,合同行為為團體法上法律行為之典型,同時,從字面上看契約的概念比合同更確切。但新中國成立后,基于時代變革的大背景,契約一詞逐漸被合同所取代,時至今日,在中國大陸從國家立法到日常用語,已普遍接受了“合同”這一概念,在我國臺灣地區等地仍然適用契約一語。參見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版,第310—311頁;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頁。
⑨須注意:此處因合同特殊目的不達所遭受的損害與因合同違約所遭受的精神損害并不相同,眾所周知,《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并不承認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由于前者為當事人雙方所明知且已成為合同條款,違約方對違約之后果亦有所預見,當事人理應受其約束,在合同特殊目的不達時,此部分應計入損害賠償的計算,而不能僅僅因為其或多或少承載了精神利益,就以違約不支持精神損害賠償為由進行駁回,否則守約方的利益必將暴露于外。
[1]顧全.合同法上強制履行的適用條件分析[J].人民司法,2012 (24):31.
[2]葉昌富.論強制實際履行合同中的價值判斷與選擇[J].現代法學,2005 (2):155.
[3]王洪亮.強制履行請求權的性質及其行使[J].法學,2012(1):112.
[4]Reinhard Zimmermann.The 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102 (2005).
[5]韓世遠.合同法總論 (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6]楊楨.英美契約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7][日]我妻榮.債法總論(新訂)[M].東京:巖波書店,1991.
[8]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2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9]馬忠法.“合同目的”的案例解析[J].法商研究,2006 (3):123.
[10]王信芳.民商事合同案例精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