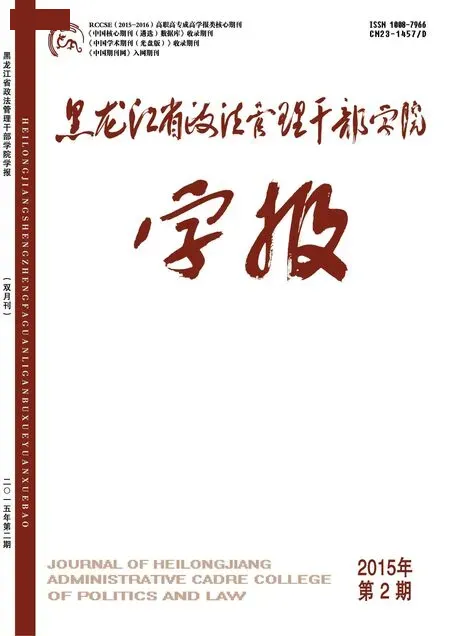基層司法過程中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根源及解決
魏丹
(四川大學法學院,成都 610065)
基層司法過程中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根源及解決
魏丹
(四川大學法學院,成都 610065)
當今中國的法治障礙主要表現為民間法與國家法的沖突,這一矛盾導致民眾普遍不信任裁判結果,降低民眾對法律的確信。民間法與國家法的沖突首先源于不同的經濟基礎,但隨著農村經濟市場化,矛盾的關鍵因素集中于不同的法律文化,國家法屬于“形式的理性的法”,民間法是“實質的非理性的法”。二者各有優劣,國家法與民間法的融合便于開啟中國法治夢的理想圖景。著眼于二者呈現的不同法律文化,明確二者在中國法治路途上可相互補益,最后提出具體措施,樹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思維,適用區際法律沖突法緩解國家法與民間法的矛盾,培育法官理性的裁判思維,發揮陪審制的作用,增加裁判語言的說服力,提高法律解釋的可接受度。
國家法;民間法;形式的理性;實質的非理性;中國法治夢
在世界各國均熱衷于競爭的時代,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人開始尋求中國在全球性結構中的話語權,法學家們也竭力探尋中國法學參與“話語權爭奪”的可能性,努力實現中國法治夢。在這個角逐的過程中,民間法逐漸踏入法學家們的視野,中國法學研究者試圖采用民間法,利用中國本土資源創造中國特色法治夢。另外,中國法治發展道路上,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也加深了中國法學者對于二者急切的探索和研究,其現實沖突主要體現在國家法的裁判結果越來越不能滿足民眾的有效期待性。
一、國家法的窘境
法律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法律是指法的整體,它包括由國家制定的憲法、法律、法令、條例、決議、指示、規章等規范性法律文件和國家認可的慣例、習慣、判例、法理等”[1]。制定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及其各部門、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省級政府。狹義的法律僅限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之法。該意義上的法律定義與蘇力國家法(國家制定法)雷同。自此,不難窺探這一定義的“理論基礎是法律是一種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這種工具來規制社會”[2]5。反復推敲上述理論,其違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包含法律),上層建筑反映并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固有關系,夸大法律的作用,并試圖利用法律規制人們進而“形成社會”、“統領經濟”。其揭露中國當今法治/法制①民間法是相對于國家法而存在的概念,以國家法概念的存在為前提,其理論性的前設是一種“法律多元”觀念。關于“民間法=非正式制度=本土資源”的論點請參看田龍飛《本土資源與法律多元——重讀蘇力之〈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載《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7年第2期。建設道路存在重大缺陷。
縱觀世界各國法制建設道路歷史,各國實踐經驗也適當地例證了中國當今法制建設模式“入不敷出”,罕見成就。法國革命如火如荼,革命成果涵蓋了一系列法治原則,首倡人權,但令人不得不反思的是,法國革命者的“成就遠較……他們自己最初想象的要小。……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中繼承了大部分的感情、習慣、思想……”[3]“歐洲大陸各國之所以能夠法典化,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歷史久遠的羅馬法傳統和其哲學的理性主義傾向”[2]44。
再者,即使忽略馬克思關于法律的理論,舍棄他國經驗教訓,中國司法基層頻繁發生法院判決無法實質解決人民內部糾紛,不能滿足民眾對法律的期盼,如秋菊的困惑和受虐待母親的無奈(控告兒子,母親可以免受虐待,但是依照國家法,兒子將被判入獄,這是母親極不愿意的;若不起訴兒子,自己又要忍受兒子的虐待)等,國家法與民間法沖突這一事實無法磨滅,這一矛盾成為中國實現法治的軟肋。終究,法律(此處不包含民間法)不可能規定一切,法治也有缺陷,比如它的保守型,滯后性,有限性,并且法治精神前提中人是不可信的假設局限性等。
二、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
(一)國家法與民間法沖突的經濟②法學界熱衷區別“法治”與“法制”,二者確存較大區別,然通說認為,不論“法制”還是“法治”,都需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法律規范為基礎,本文一概同一視之。根源
蘇力先生描述的民間法遇②可以有效緩解司法基層中法律與經濟基礎的沖突,遺憾的是,民間法并沒有被國家有效接納,尚未納入中國“法律”。國家法是改革開放后國家急速引進西方法制,吸收西方法律文化衍生的人為果實,其很好的凸顯了中國勵志與國際接軌的思維,方便中國在經濟交往,政治交流中與世界對話,更是中國盡快建立市場經濟的強有力的武器之一;而民間法,即“在社會中衍生的,為社會所接受的規則”[2]45,則是中國本土法律文化和經濟繁衍的自然果實,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開辟實現中國夢的新路徑,在中國實現中國法治夢,更有利于強化中國特色。若此路探索成功,將有利于中國提升“話語權爭奪”的可能性。本質上,二者源于截然不同的經濟基礎,國家法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民間法源于中國五千年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隨著時代變遷,中國對于農業經濟繁榮的關注,小農經濟已然逐步市場化,農業經濟廣泛參與市場競爭。
(二)國家法與民間法沖突的法律文化根源
民間法通過人們反復博弈和適用而被證明是有效的,人們還保留著中國本土法律文化。中國國家法滋生于西方市場經濟的土壤,但在西方,國家法的定義異于中國,它涵蓋了習慣法、判例法等。國家法最初是為實現經濟貿易的預測性,方便交易者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穩定經濟秩序,因此,很多法律,特別是民商法,直接取源于已然形成的民間交易習慣。在市場經濟中,這種法律建立的假設前提是,人是理性的人,人們為了增強法律預測性,設立并且遵守一系列法律規則。所以,國家法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出來的思維模式或者法律文化,其類屬于韋伯所謂“形式理性”的法律“理想類型”。“形式理性”法律需要滿足如下條件:(1)法官可以將抽象法律適用于具體案例;(2)邏輯分析抽象法律并以之認定具體事實;(3)抽象法律具有邏輯性,自成一套完整體系;(4)法律不關注不能通過理性分析得到的事務;(5)抽象法律行為的標準必須是一般理性人可以達到的標準。相反,如果立法或者司法過程中不是采取理性方式衡量行為的活動在形式上是非理性的。而民間法在法律發展歷史的潮流中,韋伯將之歸于“實質的非理性”,即“立法和司法的具體決定是在倫理、感情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下,而不是根據一般規則做出的”[4]。賀衛方教授將民間法歸為“卡迪司法”,闡釋中國本土法律是“實質的非理性的法”,例如中國人注重天理人情高于法律,天理人情高度不確定導致判決者可以翻云覆雨,糾紛處理很少考慮規則[5]。
(三)國家法與民間法在中國法治夢中的地位
臺北張偉仁先生對于賀衛方教授的結論有所質疑,認為那是中國學者“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確實絕少深入的探究,僅僅用外國的觀點和語言,去審視和討論中國的司法和法學,泛泛地,但是很武斷地加以批評”[6]。中國當代法制建設35年,幾乎在零基礎上實現“質的飛躍”,全方位吸收西方法律制度,如歐美法理學理論,蘇聯刑法體系,德日民法思維方式,等等,速度之快;自上而下的法制建設模式,國家大批量立法,一方面“教育”中國民眾,普及西方法律,另一方面利用國家強制力保證該實施,來勢之猛,導致中國法學建設倍受鄧先生所謂的“現代化范式”①“現代化范式”是相對于“革命史范式”的一個史學概念,通過羅榮渠、張開沅、許紀霖等學者的發展,其開啟了研究中國史學的新紀元。支配,“這種‘范式’不僅間接地為中國法制/法律發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且還致使中國法學論者意識不到他們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7]。鄧先生之所以得出如此結論,因為在他分析并批判了張文顯、姚建宗等教授主張的“權利本位論”、中國各個部門法研究人員倡導的“法條主義”、梁治平先生提倡的“法律文化論”以及蘇力教授推舉的“本土資源論”后,得出結論:這些理論實質上都受西方“現代化范式”的支配,“權利本位論”和“法條主義”直接接受這種范式的改造,“法律文化論”和“本土資源論”以“現代化范式”為標準來定義中國文化,推演而定西方法律是“現代化”的,而中國本土存有的“法律”②筆者認為,此處中國本土的“法律”,即民間法究竟是否能被定義為法律尚待探討,且不說前文所述的法律在中國的廣義或者狹義,都難以將民間法包含其中,因為其未由國家制定,也從未得到國家法律上的認可,并沒有作為裁判依據。另一方面,“晚近以來,法律更傾向于意指一種將法律秩序、指導法官和行政官員的權威性材料以及司法和行政過程全數考慮在內且將它們構成一個論題——即政治組織社會系統規制人際關系的材料和過程——的知識或研究”(羅斯科·龐德《法理學》,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此定義意味著法律的制定或者認可主體必須為政治組織社會,所以很難確定的定義民間法屬于“法律”。部分民間法似乎具有法律功能,可以納入司法審判程序,比如摩梭族的婚姻體制,還有所謂的“阿夏”婚,雖然國家法禁止,但是根據民間法,這些地方還保留傳統婚姻體制,這種民間法在實際審判當中其實已經默認為“合法”,而另外一些民間法,例如民間嫁女所謂“嫁妝”僅作為民間習俗對待,不為婚姻成立的必要程序,“嫁妝”不能成為訴訟請求。本文限于討論中國法治建設,所以將民間法局限于可以作為“法律”的范圍,而不可作為法律的民間法,它們或為道德范疇,必然當道德規范待之,或作為其他(尚待研究),亦當區別對待,建立多元的糾紛解決機制,比如調解,仲裁等。是“傳統的”,甚至將“現代化范式”作為判斷正義的標準,強壓甚至全盤否定中國本土法律資源。
事實上,中國傳統司法者均遵照“法有規定必遵循,法無規制參照類似已判案件”的司法方式。若法律已經明文規定,有具體遵照的可操作程序,司法者按部就班遵照即可,
根據已有法律判案極為便利,何樂而不為呢?司法者們都會尋求捷徑。其次,遵循規則,完全固守法律無法順應日新月異的新事物、怪事件,法律具有其本身的滯后性。另外,將天理人情置于國法之上裁判并不必然導致裁判的不確定。所謂天理人情,即公平正義和常識理智,是一般理性人均予以認可且作為人類判斷是非的一般性標準,比如,民法常采用交易習慣確立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而國家制定法確容易被執法者濫用,因為執法者和立法者均屬于權利階層,并且此權力階層無法有效反映所有甚至大多數人民的心理判斷標準。
筆者認為,中國的民間法更適合歸入“實質的非理性”,這主要是與西方法律的“形式理性”對比得出的概念,因為在法律發展史上,韋伯將其發展進程表述為“形式的非理性的法→實質的非理性的法→實質的理性的法→形式的理性的法”[8]。并且,中國當代學者對于民間法存在爭議的是民間法屬于實質的非理性的法還是實質的理性的法,但形成共識:民間法不同于由西方引進的形式的理性的國家法。最后,筆者需要強調的是,國家法與民間法雖千差萬別,但從上文不難得知,理性與非理性不宜判斷優劣,它們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國家法與民間法相互補充的優勢可見一斑。國家法為實現中國法治夢奠定了法治基礎,而民間法則可為中國法治夢增添中國特色,民間法源于中國本土文化,為中國法制的“話語權爭奪”提供了無限資源,有助于增強中國實現中國法治夢的自信心。在司法實踐中,合理處理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可以有效解決社會糾紛,增強民眾對法律的確信,進一步實現中國的法律信仰。
三、司法中有效解決國家法與民間法沖突的路徑
既然民間法有如此意義,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具體在司法中合理對待民間法呢?
首先,樹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思維。因為法律可以多元,“法律多元的研究指出了法律與社會生活方式之間的密切關系,有助于打破統一的法律模式的觀念,和世界單線近代的觀念”[2]49。訴訟并非唯一的糾紛解決機制,仲裁可以有效解決商事主體的合同糾紛并且有效保護當事人商業秘密,調解也可以節約司法成本并且將緩解沖突。
適用區際法律沖突法緩解國家法與民間法的矛盾。司法過程中,忽略國家對民間法不重視這一因素,國家適用民間法的主要障礙來自中國疆土遼闊,民族眾多,各地方民間法具較大差異,若適用民間法,勢必導致各地區適法不一致。雖然從歷史發展來看,法律的差異是過渡時期,統一是趨勢,但現實中國確實處于這一法律矛盾期,所以有必要利用區際法律沖突法緩解這一矛盾。中國歷史中亦出現類似做法,如《唐律疏議》“諸化外人,同類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這里“本俗法”可概括為民間法,而“法律”即相當于國家法的唐律。亦可模仿美國關于區際法律沖突的解決方法,首先深入學習研究中國各地區民間法,按照一定標準,如民間法的活動性,可接受性,可塑性,權利義務的分配性,合理性等[9],區分可以轉化為法律的民間法和不可轉化的民間法。隨后,組織法官學習可以轉化為法律的民間法,節約成本的方法是任命當地法官。法官適用民間法的過程中,需要一系列程序法和實體法為支撐,比如在全國各地民間法代表的廣泛協商下,制定全國統一的區際沖突法,各地區再根據全國區際沖突法制定自己的沖突法。另外,充分發揮半官方機構和民間機構,如法律協會和法學者的力量,擬定法律重述,協調國家法與民間法。
培育法官理性裁判思維,堅持倫理性和技術性的統一。既然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在司法領域中具體體現為公民與法律人腦海中的“法”的概念不一,國家法更側重技術性,而民間法更關注倫理性。“這種對交流載體持有的不同認知,造成主體間溝通的障礙,大大消弱了裁判的說服力”[10],所以法官應以人權為紐帶,造就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橋梁。兩者沖突之時,法官應當在不違背公平正義的前提下以退為進,充分發揮民間法的效用。促進國家法與民間法相互交融的過程中,法官要保證所有的審判都應當具有教育意義,教育法官及其他法律人接受民間法,教育民眾了解國家法。
發揮陪審制的作用。中國當今法官是國家法的代表,為平衡國家法與民間法,作為民眾代表的陪審團發揮著重大功效。“陪審制度一方面將人們擁有的各種見解和社會上流行的不同觀點融入裁判;另一方面也使得法官的一部分思維習慣進入所有公民的頭腦,使得裁判結果的道義力量加大”[10],并利用上文所述“轉化為民間法的法律”充實合議內容,增強法官和民眾對裁判結果的預測能力。
增加裁判語言的說服力,提高法律解釋的可接受度。國家法和民間法在很多價值上具有同一性,比如追求公平、實現互惠、保障自由等。二者沖突有時只源于用語的差異,因此提升法官的語言表達能力,深入淺出詮釋國家法,方可有效平衡國家法與民間法。
[1]高其才.法理學[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5.
[2]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3][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4][德]馬克斯·韋伯.法律與經濟(下)[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7.
[5]賀衛方,孫笑俠,等.法律人之治——法律職業的中國思考[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6]張偉仁.中國傳統的司法和法學[J].現代法學,2006,28(5):59.
[7]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13.
[8]白中林.韋伯社會理論中的“中國法”問題[J].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7,25(3):186.
[9]謝暉.論民間規范司法適用的前提和場域[J].法學論壇,2011,26(3):51-53.
[10]方海明,范莉.司法過程中的法律與民意——以刑事司法為視角[EB/OL].無錫:無錫法院網,2010[2014-01 -10]. http://w x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 php?id=650.
[責任編輯:李 瑩]
DF59
A
1008-7966(2015)02-0108-03
2014-10-12
魏丹(1989-),女,四川遂寧人,2013級法律碩士,主要從事民商法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