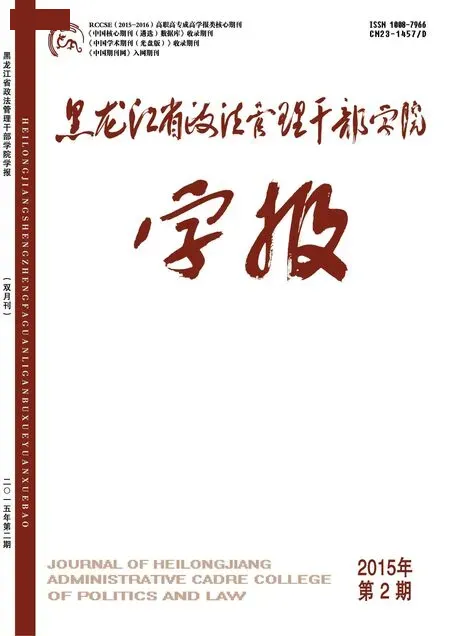“激憤殺人”刑事立法之提倡
劉杰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上海200042)
“激憤殺人”刑事立法之提倡
劉杰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上海200042)
“激憤殺人”行為與普通故意殺人行為相比,在主觀可責難性上更小,為了給刑事辯護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以及具體的適用標準,提倡“激憤殺人”的刑事立法具有必要性。“激憤殺人”是指由于受害人暴力、侮辱等重大過錯行為,導致行為人處于激憤或者情感強烈壓抑的情況下實施的故意殺人行為。“激憤殺人”的適用較輕刑罰的淵源以及他國的立法經驗都為“激憤殺人”的刑事立法提供了可行性。對于“激憤殺人”的立法路徑,宜采用條文修改+立法解釋的形式。
激憤殺人;激情殺人;立法解釋;刑法修正案
“激憤殺人”是司法實踐中比較常見的故意殺人行為。“激憤殺人”的主觀惡性比一般的故意殺人行為的主觀惡性要低,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也較之更低。因此,理論界偶有聲音提倡《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中應通過立法明文規定“激憤殺人”。然而,在《刑法》中設置“激憤殺人”的條文,一方面要考察對其規制有無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要尋找其合適的立法路徑,是采用單設“激憤殺人罪”的形式還是將其設置為故意殺人罪中的一個情節都是需要討論的問題。本文正是從這兩個角度展開論述,以期能為“激憤殺人”的刑事立法提供可借鑒的思路。
一、“激憤殺人”立法具有必要性
“激憤殺人”行為與一般的故意殺人行為在客觀方面具有一致性。然而,不同于一般故意殺人行為,“激憤殺人”無論是主觀惡性還是人身危險性較之普通殺人行為都較低。因此,本文認為,“激憤殺人”行為屬于《刑法》第232條規定中“情節較輕的”規定。但是,仍有必要在《刑法》中設置“激憤殺人”的條文。
(一)為刑事辯護提供法律依據
“激憤殺人”是比較常見的故意殺人行為,律師在該類案件中為當事人進行辯護,通常是認為該類行為符合《刑法》第232條中的“情節較輕的”規定。然而,我國《刑法》中并沒有明文規定“激憤殺人”,所以,律師在為當事人進行辯護時通常都顯得沒有底氣,法官在審理該類案件的大部分時候也沒有魄力將該類殺人行為適用“情節較輕的”規定。另外,由于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激憤殺人”的行為,所以,即使法官想要適用《刑法》第232條中“情節較輕的”規定,但是,什么行為屬于“激憤殺人”,什么行為不屬于“激憤殺人”,就顯得含糊不清。因此,我們就有必要在《刑法》條文中明文規定“激憤殺人”行為。一方面,為律師辯護、法官審判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另一方面,為適用“激憤殺人”的規定提供具體的、可操作性的標準。
(二)主觀有責性小于普通殺人行為
“激憤殺人”的主觀有責性部分阻卻,確實具有單獨規定之必要。之所以要對“激憤殺人”單獨規定,是考慮到“激憤殺人”與一般的故意殺人行為不同,若要適用一般的故意殺人罪條文,對“激憤殺人”行為選擇“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不能體現刑法的目的。犯罪成立包括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與有責性。“激憤殺人”的行為當然符合故意殺人罪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的要素,但是,在有責性層面上,由于被害人具有重大過錯,行為人是基于“激憤”實施的殺人行為,可見,“激憤殺人”的行為的責任有部分阻卻。因此,在《刑法》中單獨明文規定“激憤殺人”具有法理依據。
二、“激憤殺人”的概念梳理及條文設置可行性
首先,需要明確“激憤殺人”的含義,并將其與“激情殺人”相區別。“激憤殺人”是指由于被害人存在暴力、侮辱等重大過錯,而使行為人陷入激動憤怒、失去控制狀態下的殺人行為。而“激情殺人”則是指行為人在認識和控制能力降低的狀態下實施的殺人行為[1]。區分“激憤殺人”與“激情殺人”非常有必要。“激憤殺人”與“激情殺人”存在交集,可以說,“激憤殺人”是特殊情形的“激情殺人”。不同于“激情殺人”,“激憤殺人”在主觀罪責上具有部分阻卻,對其適用刑罰應當降格適用,而一般的“激情殺人”適用《刑法》第232條的死刑則沒有問題。例如2010年的藥家鑫案件是典型的“激情殺人”案,但并非是“激憤殺人”。藥家鑫眼見被害人記下他的車牌號,一時沖動連砍被害人十幾刀。這里被害人記號碼的行為顯然不能認定存在過錯,藥家鑫因為被害人記號碼而砍殺被害人,在主觀上顯然沒有減少罪責。“激情殺人”的起因很多,而“激憤殺人”的起因只限于被害人存在重大過錯導致行為人陷入激憤狀態。因此,法院在審理該案時,對藥家鑫適用死刑沒有問題。至于律師聲稱藥家鑫是所謂的“激情殺人”,雖然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在刑罰的適用上顯然也只能是無能為力。
其次,本文認為,在《刑法》中明文設置“激憤殺人”的條文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來源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刑法》中明文設置的“激憤殺人”的條款可以作為“注意規定”。《刑法》條文中有法律擬制與注意規定之分。“為了防止司法工作人員混淆《刑法》的有關規定,或者忽略一些應該按照犯罪或按照某種具體犯罪處罰的情形,立法者方才通過設置注意規定條款對基本規定進行解釋或補充,這就決定了注意規定必然具有補充主要規定不足之功效”[2]。筆者認為,在《刑法》中明文設置“激憤殺人”的條文,可以使其成為注意規定,目的是為了要提醒司法工作人員,在審理故意殺人行為時,要區分“激憤殺人”與一般的故意殺人行為。“激憤殺人”屬于故意殺人行為中情節較輕的行為,一方面,要避免動輒適用死刑;另一方面,對行為人的故意殺人行為,應當適用本條后段“情節較輕的”法定刑。
第二,“激憤殺人”條文的設置有據可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10條規定:“嚴懲嚴重刑事犯罪,必須充分考慮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對于事先精心預謀、策劃犯罪的被告人,具有慣犯、職業犯等情節的被告人,或者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處罰、在緩刑、假釋考驗期內又犯罪的被告人,要依法嚴懲,以實現刑罰特殊預防的功能。”第22條規定:“對于因戀愛、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犯罪,因勞動糾紛、管理失當等原因引發、犯罪動機不屬惡劣的犯罪,因被害方過錯或者基于義憤引發的或者具有防衛因素的突發性犯罪,應酌情從寬處罰。”通過以上兩條規定可以看到,“激憤殺人”的設置在立法上符合先前的立法旨意。
第三,無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有很多國家規定了類似于“激憤殺人”的條文,可為我國《刑法》明確設置“激憤殺人”條文提供借鑒。在大陸法系國家中,諸如《希臘刑法典》第299條故意殺人罪中,第二款規定“如果行為是在激情的支配下決意和實施的,處有期懲役”;《奧地利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76條規定了因通常可以理解的劇烈的情緒激動而殺害他人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萄牙刑法典》第133條規定了“如果殺人者是受可理解的激動情緒、憐憫、絕望或者具有重要社會價值或者道德價值的動機所支配,可以明顯地減輕其責任的,處1-5年監禁”的減輕殺人罪。在英美法系國家中,諸如英國《1957年殺人罪法》第3條規定,“如果在謀殺罪的指控中,存在著陪審團能夠查明被告人受到挑釁而喪失自我控制能力的證據,陪審團就應該確定,被告人面臨的挑釁是否也足以使正常的人實施被告人所實施的同樣的行為。在確定這個問題的實施,陪審團應該按照自己的看法,來考察當時被告人面臨的言行的所有內容對正常人的影響”。《加拿大刑事法典》第232條規定,“因突然挑釁致使情緒激憤而實施殺人行為的,本來可能構成謀殺的有罪殺人,可以降級為非預謀殺人。錯誤行為或者侮辱足以使通常人喪失自制能力,而被告于情緒激憤后沒有時間冷靜下來而突然行為的,該錯誤行為或者侮辱為本條規定的挑釁”。可見,在立法中規定“激憤殺人”是當今大多數國家的選擇,具有一定趨向性。在《刑法》中規定“激憤殺人”條文有助于我國刑法同世界接軌,也符合歷史的潮流。
三、“激憤殺人”之立法路徑分析
在刑法條文中明文規定“激憤殺人”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幾種路徑。
路徑一,單獨設置“激憤殺人罪”。即采取《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第232條之后增加一條,作為《刑法》第232條之一,設置“激憤殺人罪”。例如規定《刑法》第232條之一:“激憤殺人的,處……”
路徑二,采取《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第232條罪狀。例如規定《刑法》第232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受害人過錯引起行為人陷入激憤或者情感強烈壓抑狀態情況下實施‘激憤殺人’的或者有其他較輕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路徑三,采取《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釋的形式,修改《刑法》第232條的罪狀,同時用立法解釋來解釋“激憤殺人”的含義。例如:1.修改《刑法》第232條罪狀為: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激憤殺人”的或者有其他較輕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頒布立法解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2條的解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況,討論了刑法第232條的含義,對其中的“激憤殺人”,解釋如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2條所稱“激憤殺人”,是指由于受害人暴力、侮辱等重大過錯行為,導致行為人處于激憤或者情感強烈壓抑的情況下實施的故意殺人行為。
筆者認為,“路徑三”較前兩者路徑更為合適。“路徑一”與“路徑二”都是歷次《刑法修正案》所采用過的“立法技術”,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是在此處,“路徑三”更能保持體系性與簡潔性。
首先,“路徑一”的形式在“立法技術”上欠妥。自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一)》頒布以來,我國開始通過《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從《刑法修正案(一)》到《刑法修正案(八)》,歷次《刑法修正案》增加條文比較常用的方式就是在某條之后,增加該條之一,規定相似行為的刑罰,正如“路徑一”的形式。例如,《刑法修正案(一)》中,在第162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162條之一:“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刑法修正案(三)》中,在刑法第120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120條之一:“資助恐怖活動組織或者實施恐怖活動的個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刑法修正案(八)》中,在刑法第17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17條之一:“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可見,刑法在對新的行為進行規制時都是采用“路徑一”的形式,即在相關條文之后增加一條作為該條之一。然而,從歷次的修改可以看出,“路徑一”在條文之后增加之一的形式只適合對不同的行為進行規制時所采用的立法技術。簡言之,《刑法》條文之間的核心區別除了侵犯的法益不同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實行行為不同。而“激憤殺人”并不是與故意殺人互斥的行為,“激憤殺人”可以說是故意殺人中情節較輕的一種情形,與普通故意殺人最主要的區別是在殺人的起因及主觀內容上。因此,之所以不宜采用“路徑一”的形式,是因為通過增加“激憤殺人”新條文的“立法技術”有違該“立法技術”的適用情形。而并不是像某些學者所說的,“不像有些國家那樣,將‘激憤殺人’另行規定為一個法條,主要是因為我國刑法已經有了四百多條,再增加會使我們的法條過于龐大,內容本身就有關系和交叉的,不需要再另行規定”[3]。總之,采用《刑法修正案》在《刑法》第232條故意殺人罪之后增加《刑法》第232條之一的形式并不是十分妥當。
其次,“路徑二”的形式與本罪條文的用語不是特別協調,不符合《刑法》條文應力求簡潔性的要求。《刑法》作為法律規范,要處理好條文簡介、精確和表意明確之間的矛盾關系。“法律語言最好是確切的,簡潔的、冷峻的和不為每一種激情行為左右的。最好的法律文本是出色的文學作品,它們精確合適的語詞模塑出一種世界經驗,并幫助我們通過同樣精確得富有美學意義的語言模式,把人類的共同生活調控到有秩序的軌道上。”[4]《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見,對于“故意殺人”的行為規制,《刑法》條文十分精練簡潔。如果采用“路徑二”的方式,修改《刑法》第232條的罪狀,也即在條文中詳細規定“激憤殺人”及其本質、特征,容易造成條文的冗長,使該條文在體系上顯得前后不協調。
最后,“路徑三”的形式具有合理性,能夠保持條文之間的協調性與用語的簡潔性。“路徑三”是通過條文修改+立法解釋的形式對“激憤殺人”的情形進行立法,一方面,通過《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第232條故意殺人罪的罪狀;另一方面,通過立法解釋來闡明“激憤殺人”的具體含義。該做法具有如下優勢:一是能夠保證刑法的體系性不被破壞。正如上文所述,“激憤殺人”與普通故意殺人最主要的區別是起因以及主觀上可歸責性大小的不同,因此,在同一條文中進行規定而不是增加新的條文,有利于保持刑法的體系性。二是能夠做到語言的精練。《刑法》作為法律規范,其條文應簡潔精練。在第232條中規定“激憤殺人”的情節,在立法解釋中具體闡釋“激憤殺人”的本質、特征以及成立條件,有助于保持第232條條文的簡潔性,不至于造成“故意殺人”的規定很簡潔,而“激憤殺人”很冗長的情形。三是能夠與“嚴重情節”的規定形式相一致。由于《刑法》第13條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因此,我國《刑法》分則中并沒有規定與“情節嚴重的、情節特別嚴重的”相對稱的“情節較輕的、情節顯著輕微的”情形。但是,修改罪狀為“激憤殺人的或者有其他較輕情節的”,與“情節嚴重的”條文更加對稱、協調。四是能夠保證“法定刑”的合理銜接。如果在《刑法》第232條之后增加一條規定“激憤殺人”,難以處理“激憤殺人”的刑罰尺度,因為,在《刑法》第232條之后的第233條規定的是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為“死刑或者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在兩條文中間增加一條規制“激憤殺人”,那么法定刑的區間就很難規定。五是“路徑三”能夠使“激憤殺人”不至于與“情節較輕的”相重疊。可以說,“激憤殺人”是故意殺人罪法條中“情節較輕的”一種情形。路徑一的規定,顯然導致《刑法》對待同一行為采取了二次規制。
綜上,本文認為,采取“路徑三”的形式規制“激憤殺人”較“路徑一”、“路徑二”更為妥當。“路徑三”的形式能夠更好地照顧到“立法技術”、《刑法》的體系性、以及《刑法》條文用語的簡潔性要求。而“路徑一”和“路徑二”則分別在立法技術的使用上、與刑法體系的協調性上有不協調之處。
四、結語
《刑法》作為法律規范,本身應當力求簡明扼要,同時達到條文明確的要求。因此,是否應該通過刑事立法的形式將“激憤殺人”明文規定進《刑法》條文中就引起了諸多討論。通過本文的論述,筆者認為,在《刑法》中明文規定“激憤殺人”行為具有必要性,也具備了可行性。同時,為了兼顧刑法條文的精簡性,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第232條故意殺人罪的罪狀,增加“激憤殺人”的注意規定;采用“立法解釋”闡明“激憤殺人”的具體含義,這種方式最為妥當。
[1]鄒兵.論激情犯罪的刑事責任[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4,(5).
[2]劉憲權,李振林.刑法中的法律擬制與注意規定區分新論[J].北京社會科學,2014,(3).
[3]駱瓊,鄭元健,高飛.“激憤殺人”的立法建議與分析[J].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4,(2).
[4][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M].鄭永流,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93.
[責任編輯:李洪杰]
DF612
A
1008-7966(2015)02-0044-03
2014-12-25
劉杰(1989-),男,安徽池州人,2013級刑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