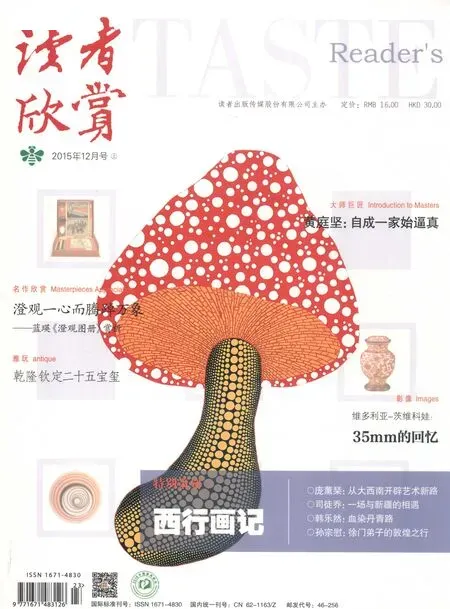如何在一幅畫前掉眼淚(上)
如何在一幅畫前掉眼淚(上)
廖廖·專欄
我們常常為一部電影、音樂劇或小說而感動流淚,卻難以為一幅畫感動流淚。通常的解釋是,電影、音樂和小說的情節讓人更容易有代入感,我們的情感隨著跌宕的劇情和變換的節奏而醞釀、起伏、轉折、傾瀉。而當我們擠在熙攘的人潮中看一幅畫,目光停留在畫上不過幾秒或幾十秒,沒有前戲,沒有高潮,也沒有結局,簡直秒射。
其實,如果一幅畫能夠激起我們強烈的情感,我們也可以給它腦補一個千回百轉的故事,就像“同人文”干的那樣。18世紀的藝術愛好者就是那么干的,當時的藝術評論家會為一幅傷感的浪漫主義作品而落淚,甚至會在評論中虛構出畫中主角的年紀、生平、戀情,乃至心理狀態—18世紀的腦補技術不亞于今天的“同人文”作者。
重點在于,今天的我們認為為一幅畫而腦補一個故事進而感動自己是一個淺薄的舉止。藝術評論家教育我們,欣賞一幅畫應該保持理性,而不能涉及個人情感。藝術家也不會創作感動人的作品。達·芬奇在《論比較》中說,畫家不會流淚,因為眼淚嚴重擾亂了內心的情緒。
藝術教育讓我們不能在一幅畫面前輕易流露情感。我們的理論家認為,哭泣是情緒失控的表現,失控意味著不能“理解”作品的“真正意義”,而在一幅畫前感動落淚就意味著無知、原始和膚淺。在藝術評論家看來,欣賞一幅畫的唯一正確道路就是秉持客觀的立場與冷靜的態度,思考它的技法、構圖和藝術家意圖,分析其在藝術史中的位置。
藝術評論家對一幅畫有著理性而嚴謹的分析公式,他們的畫評是寫給藝術史的,而不是寫給喜歡這幅畫的人看的。理論家們以自己看過無數作品而驕傲,他們因為掌握藝術史的話語權而傲慢,卻從來不會說自己為一幅畫而感動流淚。藝術于他們而言,仿佛一門外語或者一項運動,只需背熟所有知識,熟練運用技術與公式。
并不是說藝術史無用,如果沒有藝術史的知識,我們無疑是新時代的文盲—視覺審美上的文盲。今天的中國文青其實“文藝的成色”并不高,至少大家對藝術史并沒有系統的認識。隨著文藝知識的普及,我們會讀越來越多的書,逛越來越多的畫展,我們的眼睛會慢慢變成專業的器官。我們面對一幅畫時,那些強烈的感情、好奇的探尋、懵懂的真摯,都會隨著藝術史知識的加深而逐漸減弱、消失。不再有幻想,只有分析;不再有憧憬,只有解讀;不再有神秘,只有對比。迷人的顏色,要作象征符號的解讀;動人的線條,要理解為隱喻的標簽。我們“誤讀”一幅畫的風險越來越小,直覺和想象力卻越來越遲鈍。就像一個初涉云雨之事的后生,雖然技巧不足,但勝在熱情有余。當有朝一日技巧嫻熟,他會發現自己的熱情早已淡薄。
隨著書單越來越厚,純真慢慢成為傳說。藝術史的知識澆滅了我們的天真與熱情。旁人的經驗、注解的標簽,影響著我們的情感與觀感。這是藝術史對藝術開的玩笑,這是藝術為知識付出的代價。當我們還在懵懵懂懂的時候,當我們被告知“一幅畫的價值不在于讓人感動”之前,倘若能擁有在一幅畫前感動流淚的經歷,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
對于藝術品來說,觀眾的感受也構成了它的一部分,盡管藝術家與評論家可能不以為然,但是一件藝術品應該不介意觀眾的感動的淚水為它增添新的價值。一幅畫不僅意味著拍賣價格與歷史地位,還有令人感動的價值。(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