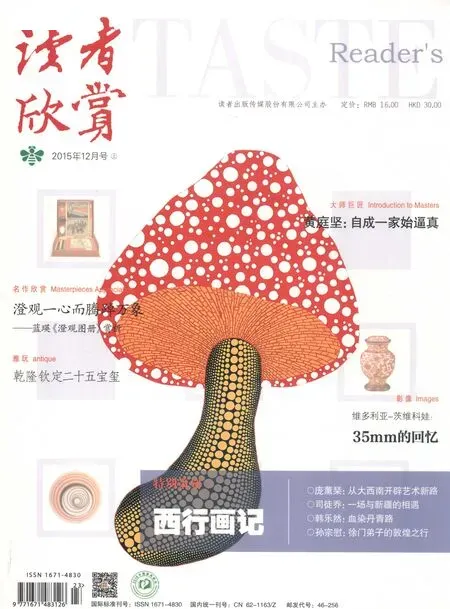孫宗慰:徐門弟子的敦煌之行
文靜一
孫宗慰:徐門弟子的敦煌之行
文靜一
1942年陰歷元宵節前,我趕到青海塔爾寺,主要為看塔爾寺廟會,因塔爾寺廟會以元宵節最盛,蒙藏各族信徒來此朝拜,近10萬人。不信佛教的及漢族、回族也有很多人來此,主要為做買賣或觀光。我則對各民族的生活服飾等感興趣,故畫了些速寫。后來我就學習用中國畫法來畫蒙藏人生活。速寫稿比較詳細,也有憑記憶畫成油畫“藏族舞蹈”之類的。
—孫宗慰
機緣巧合赴敦煌
孫宗慰1912年生于江蘇常熟,本來的小康家境因一些原因而中落,他在親友資助下勉強才讀到高中畢業,隨后在南京市的一所小學謀了一份教職。從小喜歡繪畫的孫宗慰一直在為了自己的夢想而努力,1934年,孫宗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學美術系,并成為徐悲鴻的學生。此時的徐悲鴻剛從法國回來,正著手在國內美術教育界建構他所主張的現實主義寫實語言體系。這也就是人們一直認為的,孫宗慰在藝術上一直追隨徐悲鴻體系,被視為徐門弟子的代表者的原因。
抗日戰爭爆發后,南京中央大學于1938年遷到重慶。孫宗慰也隨校入川,在戰事流離中完成學業,并留校擔任了助教。3年后,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把他和繪畫大家張大千轟動文化界且毀譽參半的敦煌之行聯系在了一起。
1941年春,張大千碰到了時任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的呂斯百,張大千告訴呂斯百自己計劃去敦煌探訪千佛洞,并想找一個有繪畫寫生能力的助手同行。呂斯百想到了系里的年輕助教孫宗慰,便向張大千推薦。張大千曾為中央大學藝術系短期授課,對學生時期的孫宗慰印象頗好,聽呂斯百提起,也覺得他是極好的人選。在呂斯百的動議和安排下,孫宗慰停薪留職一年,追隨張大千開始對敦煌壁畫進行臨摹與研究工作。孫宗慰的西行,“雖晚于趙望云,但早于大家熟悉的吳作人、董希文”。他也因此機緣,成為中國西北少數民族繪畫題材的開拓者之一。
因為孫宗慰帶著大量的畫具,所以他沒有同張大千一起乘飛機到蘭州,而是先取道成渝公路,而后從成都換乘火車到西安。而從西安往蘭州的一段路只能靠步行、搭車和騎驢并舉,這樣在戰火中走走停停,他用了兩個月時間才到達蘭州。西行途中雖然經歷曲折,孫宗慰卻也收之桑榆,一路和西北的少數民族同胞有了更日常的接觸和觀察。一向對普通人生活狀態感興趣的孫宗慰,被蒙古族、藏族的邊地風情深深吸引,畫出多幅國畫和油畫,日后都成為他的代表作。
西北之行的臨摹與研究
到敦煌后,孫宗慰的工作比較繁重,包括摹繪壁畫、寫生彩塑,對洞窟外的景致也做了大量寫生,以便對照著為洞窟編號。學西畫的孫宗慰第一次系統地接觸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對敦煌壁畫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留下一批精彩的寫生臨摹稿。這段經歷,在他此后大半生的繪畫中都留下了痕跡,一些重要作品尤其國畫,多是根據這批臨摹稿來進行重新創作。他在敦煌期間的工作細節,除了當年的日記有錄,還可從他多年后在“文革”中寫的《交代我與張大千的關系》里看到許多。如在1968年11 月22日的一份材料中,他這樣記述從敦煌返回青海塔爾寺的:
1942年陰歷元宵節前趕到青海塔爾寺,主要為看塔爾寺廟會,因塔爾寺廟會以元宵節最盛,蒙藏各族信徒來此朝拜,近10萬人……我則對各民族生活服飾等感興趣,故畫了些速寫。后來我就學習用中國畫法來畫蒙藏人生活。速寫稿比較詳細,也有憑著記憶畫成油畫“藏族舞蹈”之類的。在塔爾寺住了約三個月,要為張大千整理畫稿,收集寺內建筑上的裝飾紋樣。工作之余則向喇嘛畫工學習從制作畫布、顏料到畫后裝幀等方法及壁畫方法(以期與敦煌佛畫傳統相近)。
1942年5月底,孫宗慰和張大千在蘭州作別,張大千獨自返回敦煌繼續臨摹和研究,孫宗慰則按照原先和學校的約定回去復職。因碰上山洪暴發,車票難求,孫宗慰在蘭州被困三月余才回到重慶。不過,就是在這段被迫滯留蘭州期間,他潛心整理了自己的敦煌臨摹勾線稿及青海塔爾寺寫生稿,并完成了油畫“藏族舞蹈”等作品的初稿。
孫宗慰的西部之行為他帶來了藝術創作方面的山洪似的爆發,而這些作品從藝術價值上來看也是相當值得稱贊的。孫宗慰的這些西行題材作品,也使徐悲鴻大為驚嘆。
1942年秋,孫宗慰從蘭州回到重慶后不久,徐悲鴻受中英庚款董事會委托在重慶磐溪籌建中國美術學院,即決意聘孫宗慰為副研究員,當時同被聘為副研究員的還有畫家吳作人、張安治、李瑞年、陳曉南和馮法祀等。1945年,孫宗慰在重慶舉辦“西北寫生畫展和個人作品展”,徐悲鴻親自題寫前言,文中贊弟子:“以其寧郁嚴謹之筆,寫彼伏游自得、載歌載舞之風俗,與其冠履襟佩、奇裝服飾,帶來畫面上異方情調,其油畫如藏女合舞,塔爾寺之集會,皆稱佳構。”
西北之行成就人生精彩
1945年,孫宗慰在重慶舉辦西行個展,時任《大公報》主編的王凡生為其作品《駝牧》題寫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所為者何?求其自我”,這大概算得上是對孫宗慰西行繪畫的點睛了。
經西行歷練,在同時代人里,孫宗慰已經顯現出他的獨特畫風,而西部之行可以說是孫宗慰繪畫生涯的轉折點,也是頂峰,誕生了一套完整的蒙藏風情圖卷。油畫《冬不拉》和《駝隊》,分別完成于西行途中的1941年、回到重慶后的1943年,其繪畫方法的不拘,表現出他在現實主義寫實語言架構中的突破。“這其中有一批專畫背部形體的作品,每幅僅一人,背對畫面,而形體的微妙和服飾造型的豐富,都使作品擺脫了簡單的寫生狀態而引發了想象空間。如在“蒙藏生活圖”系列中的《集市》《背影》《對舞》等作品里,或‘西域少數民族服裝系列’,都采用了這種類似于中國畫中‘留白’的處理方式。”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吳洪亮評價。
西北之行是孫宗慰人生的精彩一頁,不僅在他的畫里留下了奔放的線條與熾烈的色彩,也讓他回到美院許多年以后,還保留著使用藏族碗筷、冬天戴狐皮藏帽的習慣。
“西畫的辦法是告訴一個藝術家如何畫所見,古法則是告訴藝術家如何畫所知。在創作中可以發現,孫宗慰的視角極其復雜,他不是定點視角,他的視角似乎很漂移,這種漂移來自于中國古法里的‘游觀’,他不是畫他所見,而是畫他所理解的世界。”
包括徐悲鴻在內的許多老一輩油畫家,都有一段“從洋到土”的藝術歷程。曹星原說:“徐悲鴻后期的土油畫確實很不好,可他實際上是在找一些東西。”或者說那是一種本地化嘗試,“他們都在追求一種信念,油畫要畫出‘我’的精神。我究竟怎么去表現我?今天再回頭看,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哪個油畫系的老師敢站出來說,我敢跟孫先生比書法、比線條、比造型能力?”
1946年,徐悲鴻接任北平藝專校長,孫宗慰又獲聘為副教授,也進入他創作的第二個高峰,《打粥》等國畫代表作即出在這一時期。1955年,以原北平藝專為基礎成立的中央美院再次進行院系調整,孫宗慰被調到中央戲劇學院,參與建立舞臺美術基礎教學體系。這以后,政治環境的劇烈變化,加上個人的身體病痛,孫宗慰漸漸疏離于美術界的主流語境而被淡忘,除了教學中示范的戲裝人物寫生,甚至少有人知道他的西行經歷以及他曾畫過那么多獨具個性的油畫、國畫作品。對于孫宗慰而言,西行亦成為他此生不可或缺的一段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