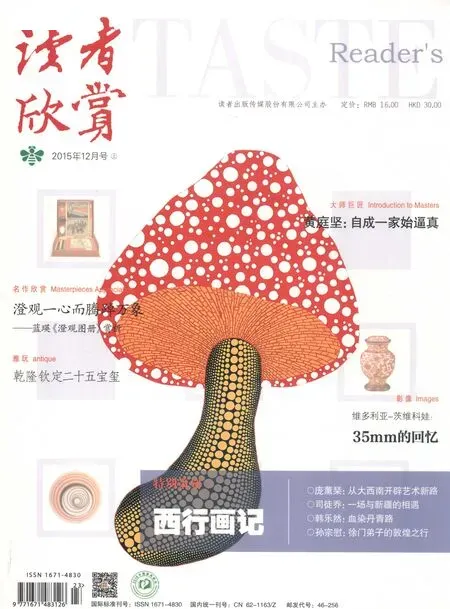西行畫記
供稿/中國美術館
西行畫記
供稿/中國美術館
藝術家從畫室走向寬闊的天地,
以文化的自覺探索出一條具有民族本土風格的藝術道路。
這是一張大大的路線圖。
圖中的路線從重慶到成都,到西安,到廣元,到天水,到蘭州,到武威,到西寧、張掖、敦煌、哈密、烏魯木齊、伊寧、庫車、喀什、于田,又至貴陽、安順……
這是一群清貧的藝術探險家。
“到西部去!”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們懷著理想,從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重慶出發,堅定地踏上西行之路。
1943年,說走就走
西部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但近代以來因為地理上的遙遠偏僻和交通不便,長期未受到足夠重視。20世紀30年代初,從平津想要到達西北,必須取道內蒙古、嘉峪關才可;而從內蒙古到哈密的路途,非得要由駝運完成,條件之艱苦、地域之閉塞可想而知。因而,20世紀30年代以前,普通民眾心目中的西部文化想象,是異域文化強烈反差所引發的不適應感,或行者把自己想象成漂泊者而引發的流亡情結。
20世紀30年代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西南、西北遂成為重鎮。大批文化人隨之西遷,針對文物的西南西北考察研究也相應展開,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川康古跡考察團、大足石刻考察團以及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藝術家們經歷了動蕩時代下文化格局的分流與聚合,內心經受震動并完成向現實的艱難轉型。有志的藝術家并沒有被淹沒于時代的漩渦之中,他們將自己的藝術追求放在川、黔、甘、寧、青、新等廣闊的西部山水之間,深入那里民族生活的現實,追尋傳統之源。“到西部去!”一代中國藝術家將古來通向西部的刑罰之路、流放之路、冒險之路,踏成一條面壁投荒之路,一條艱難而又充滿奇遇的探索發現之路,一條中國藝術家的成長之路。
1943年,對于這些藝術家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9月,遭受喪妻之痛的吳作人,萌發了旅行寫生的念頭。他從蘭州啟程,搭乘開往星星峽的“羊毛車”車隊,開啟“絲綢之路”的旅行。在酒泉,他遇到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和新西蘭進步友人路易·艾黎,遂邀二人同行。戈壁夜宿,一路顛簸來到敦煌后,吳作人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考察臨摹。第二年6月,他入西康,在打箭爐的體驗生活中畫出名作《打箭爐少女》。隨后,他又赴康青公路、西康北部草原,越過5000米的安帕拉山,過甘孜、玉樹,歷時8個多月返回成都。這段考察邊區生活、描繪民族風情的西部之旅,讓他畫下大批速寫、油畫、水彩—由這些素材整理加工的創作,就有100余幅。
如今年輕人總想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要論說走就走,誰也比不上被徐悲鴻譽為“感覺色調為中國當代最敏感之人,又有靈動之筆,供其縱橫馳騁”的司徒喬。時任重慶軍委會政治部設計員的他,1943年隨重慶軍委會政治部前線視察團的西北視察組進入西北,結果只見到一處抗日前線,遂決定描繪西北風光。重慶-西安-武威-張掖-嘉峪關-星星峽-哈密-迪化-阜康-烏蘇-精河-霍城-伊犁-鞏哈-焉耆-庫車-阿克蘇-喀什-莎車-葉城-墨玉-和田-皮山-洛甫-于田—歷時兩年的“旅行”,留給司徒喬和中國美術史的是280余幅作品。1944年,他在《新疆獵畫記》中記載的,都是“打獵”的心得。
在中國的傳統藝術中論起“打獵”,西南亦是豐饒之地。1939年,龐薰琹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苗族語言學的芮逸夫一起,研究西南少數民族傳統藝術。歷時3月,深入貴陽、花溪、龍里、貴定、安順等80多個苗寨,詳細觀察記錄不同地區苗族的衣裝服飾,為中央博物院搜集民族服飾和繡片600多件。1940年,他根據搜集到的資料和記憶,重拾畫筆,用工筆、水彩、白描等方式創作《盛裝》等作品。
/20世紀40年代,國民政府組織有關專家到西部考察,涉及實業、史地、科學、文物藝術等領域。影響較大的有:1942年政府經濟部組織的西北工業考察團;1943年國民黨中央設計局組織的以羅家倫為團長的西北建設考察團等。諸如鐵路、公路、水利、農業、畜牧、墾殖、工業、礦業、衛生、教育、民族等各方面的專家紛紛出動,走進西北五省。于此前后,針對藝術歷史文物的西南西北考察研究也相繼展開。如1940年教育部組織的以王子云為團長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1941、1942年間,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組織的川康古跡考察團;1945年,顧頡剛、馬衡等組織的大足石刻考察團;特別是1944年成立了以常書鴻為主任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將敦煌收歸國有,推動了對敦煌藝術等西部傳統文化藝術的整理保護研究工作。除了有組織的考察外,伴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云集于西部的藝術家更加關注現實,紛紛走出畫室,深入到邊疆與少數民族地區,在西部一邊考察研究,一邊沿途寫生。由此開啟了20世紀40年代中國美術新的篇章。/
旅行仍未停歇
“作品既富,而作風亦變,光彩煥發,益游行自在,所謂中國文藝復興者,將于是乎征之夫。”徐悲鴻當年曾這樣評述吳作人的西部之旅,而這又何嘗不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這一批藝術家的藝術經歷與成果。他們通過寫生或臨摹,從中國傳統藝術中認識到具有東方和本土特征的造型體系,特別是從藝術上“發現”了敦煌,也從民族地區的風土人情中獲得了嶄新的體驗,在作品中注入了活潑清新的氣息,給繪畫史留下了邊陲瑰麗的自然風光和多民族的生活畫卷。藝術家從畫室走向廣闊的天地,以文化的自覺探索出一條具有民族本土風格的藝術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廢除農奴制,進行民主改革,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歷史性巨變。美術創作上也涌現出一大批表現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的偉大歷史變革和時代建設以及新型社會關系下西部嶄新精神風貌的美術作品,它們構成了西部美術的重要內容和主要形態。而在改革開放初期,美術家敏銳地意識到這一新生的契機,一部分畫家延續第一代畫家的路線,堅持深入西部地區的生活中創作,用平實、樸素的現實主義手法記錄新的時代條件下少數民族生活的變化和他們的思想情感,將精神內涵的探求與表現高原人的生命激情融為一體,以期將文化的力量熔鑄進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之中。不過,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