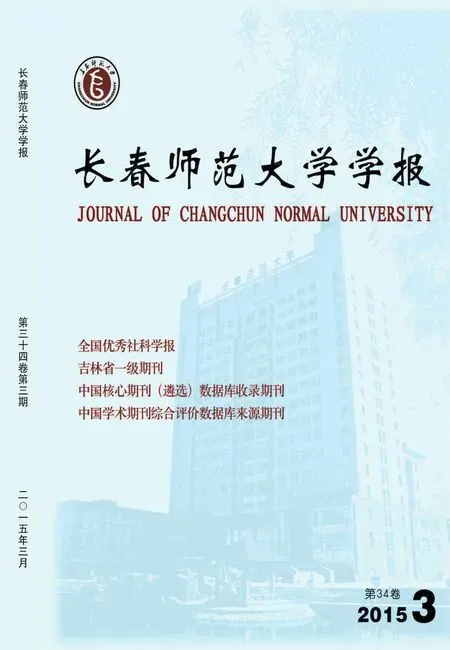汪曾祺小說的“空白”之美
劉瑀婷
(吉林出版集團時代文藝出版社,吉林長春130062)
我國文學研究者對汪曾祺小說中多次出現“空白”這一主題作過許多探討。有研究者將汪曾祺小說“空白”的思想動機與道家思想中的衍生理論相結合,認為在文學藝術創造中通過使用“空白”手法能對小說的敘事表達產生較大的包容性,為作者提供更為自由的創作空間,同時也能讓讀者從“空白”表述中獲取更寬闊的故事聯想平臺。
一、汪曾祺與其小說創作
汪曾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幼年時期就受到文化的熏陶與訓練,對文學作品的賞析與創作功力十分深厚,能夠將熱烈的文學感情通過流暢的文筆表達出來,在其小說中含有大量的“空白”。他曾說,“我認為一篇小說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作的。作者寫了,讀者讀了,創作過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寫盡了,要留有余地,讓讀者去捉摸,去思考,去補充。……短篇小說可以說是‘空白藝術’,辦法很簡單,能不說的話不說。這樣一篇小說的容量就會更大,傳達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許,勝人多多許。”[1]汪曾祺的部分小說敘述鋪墊過少,使整個故事發展情節看似不完整。這一代表性十足的個人創作手法讓讀者能夠從作品中感受到印象派描述手法對小說藝術美創作的重要性。“空白”是小說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對所描述的情景或情節的即時感想,代表了作者內心最深處的情感表達。汪曾祺小說中“空白”手法的運用雖使故事情節表現模糊,卻使情感表達得更加深入。
讀者的閱讀過程是對文學藝術的享受過程。小說的創作者通過大量的創作技巧為讀者營造出一定的藝術感受環境與氛圍,讓讀者獲得對現實的感悟。汪曾祺小說中多次使用的“空白”創作手法,為小說營造了虛與實共存的環境,讓小說的內涵和韻味顯得更為深厚。小說“空白”的部分并不是說內容不存在,而是希望通過此類情節描述讓讀者擁有更多的想象空間。
二、汪曾祺小說中的“空白”
從現代敘事學角度看,小說中敘事空白的出現始終與敘述話語之間存在較為緊密的關系。敘事話語規則一般包括三個要素,即狀態、語式以及結構。汪曾祺小說中的“空白”表達將這三個要素展現得淋漓盡致。
從敘述語式角度看,一般小說具有兩種不同的敘述表達方式。一種是按事件發展順次描寫,在小說結尾點出文章主旨。另一種是倒敘或插敘,中間通過補足的方式完整、豐富小說敘述,最后再點出文章主旨。這兩種表達方式都是作者通過文字描寫、語句表達對作品深層意味闡釋的途徑和過程,其中還摻雜有作者的思維邏輯環節。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首先要把握作品的邏輯思維發展順序搞清楚,并進行線索探求,才能最終明白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很多敘事作品中的描寫與敘述內容并不完全同步,讀者需要主動參與到敘述發展之中,而非一味地被動閱讀,才能夠真正感受文章主旨及其邏輯發展的寓意。這種“不完全同步”,主要是指作品中文字描寫與語句敘述的省略性空白,兩者之間的推理邏輯是完整的。由于其“空白”美學的追求,一般要通過大段旁白描寫內容后,才緩緩引出其內涵,也就是在全部內容包袱拋出后,再做主旨強調與歸納[2]。
“空白”創作的巧妙之處在于能夠為小說的故事情節營造一個虛、實共存的環境,讓作者在描述某個故事情節或人物事件時能夠通過一定的寫實技巧讓虛化的描述足夠鏈接上下文,使“空白”與“寫實”互相對應,完整地展示了故事的情感表達與主旨內涵,給讀者以足夠的想象空間來思考故事中沒有直接寫明或闡述的思想與內涵。汪曾祺對小說故事的敘述建立在事實情節的基礎之上,又十分善于利用“空白”的特別設置讓其呈現“隱形”狀態,讓讀者的文學感受得到更高層次的升華。汪曾祺在《天鵝之死》中大肆利用“空白”創作手法,向讀者呈現了時間與空間交錯的意境。在《橋邊小說三篇·茶干》中,作者把列醬園的老板連老大的經商理念條條列舉,中間并沒有穿插其他多余的解釋,可謂是“一片空白”。而在《幽冥鐘》中也沒有書寫任何有關故事情節的片段,而是通過大量的語句文字來對故事的氛圍進行描述與渲染。在這些所有的“空白”作品中,汪曾祺都沒有將整個小說的前后發展結果作出詳細的解釋和闡述,也沒有直接告知讀者故事中人物之間的現實關系,只是通過只言片語向讀者提示小說故事的主線發展概況,讓讀者根據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在內心聯想故事情節發展方向,并體會其作品中的情感表達。
三、汪曾祺小說中文學之美的體現
第一,小說語言極具流暢性,文字運用富含詩意與韻味。
汪曾祺對語言文字的研究造詣深厚,其小說文風樸素、結構發展流暢。在讀其小說中常常可以同時感受到誦讀散文、詩歌般的意境享受。汪曾祺說:“我以為小說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和作者的情感都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這樣才能形成小說。”[2]這正是汪曾祺自成一派的獨特小說風格。
第二,小說作品純粹質樸,結構情節淡而不散。
汪曾祺小說并不以情節曲折、敘述精彩取勝,而是通過故事情節之間的巧妙穿插吸引讀者,當中免去了很多故事背景的銜接與過渡,通過“空白”創作使小說主題更加突出。
“空白”描寫手法是汪曾祺駕馭文學語言能力的重要體現,他覺得語言的美“不在字面上所表現的意思,而在于語言暗示出多少東西,……古人所以‘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因此,汪曾祺的小說,在描述過程中免掉了冗長的小說背景鋪設,在小說結構上表現出一些“殘缺”的空白部分。例如,在《異秉》中的情節設計,張漢與王二對話,王二表示自己的“大小解分清”異秉。在小說的最后直接寫道:“原來陳相公在廁所里,這是陶先生發現的。他一頭走進廁所,發現陳相公已經蹲在那里。本來,這時候都不是他們倆解大手的時候。”[3]戲劇化的小說結尾處理讓上下文之間出現了一種無形的關聯性,而中間省去了許多故事情節的詳細交代以及小說人物的心理特征描寫等,都是一種“空白”的描寫手法。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明顯地感到小說交代過程中的“空白”缺口,同時也明白“空白”并沒有導致閱讀不連貫、情節脫軌,并能夠在大量的空白之處充分發揮自己的聯想與思考。
第三,小說創作結構多元,情節自由,故事結局設計精巧而開放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其小說故事結構、發展十分隨意而灑脫。例如在《安樂居》中的結尾處:“安樂居已經沒有了。房子翻蓋過了。現在那兒是一個什么貿易中心”。當讀者還對“安樂居”的一個個人物消失而有所失時,敘述內容突轉,只剩下一個“貿易中心”,讀者開始遐想“貿易中心”的模樣,故事戛然而止。
四、結語
“空白”最初是在中國國畫創作理論中提出,其內涵主要是強調畫作的虛實結構。汪曾祺小說中的“空白”沿用這一理論,達到虛實共存的效果,使小說的表達富有藝術感,并充滿含蓄韻味。
[1]汪曾祺.蒲橋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366,367.
[2]汪曾祺.橋邊小說三篇[J].收貨,1986(2):143
[3]汪曾祺.汪曾祺小說經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