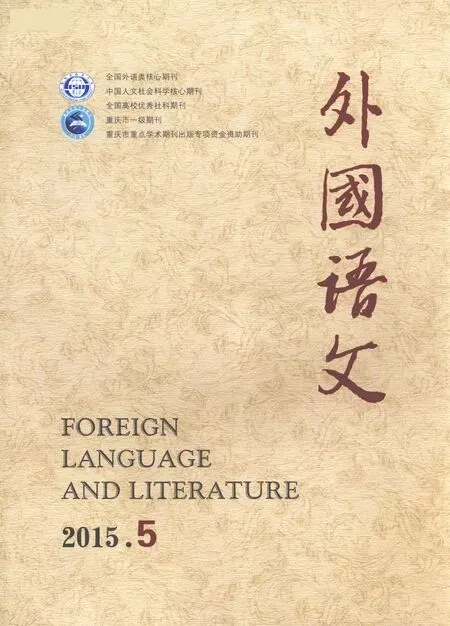我們為什么要學習語言哲學
江 怡
(北京師范大學 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北京外國語大學 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北京 100089)
當代哲學家將“意義、真理、語言用法、語言能力”等視為語言哲學的核心問題,因此學者將語言哲學溯源至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曾被視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認真討論語言問題的哲學,洛克、萊布尼茨、休謨等哲學家都對語言做了深入討論,亦可被視為現代語言哲學的先導者。但它作為一門新興的、獨立的哲學分支學科卻是出現于20世紀初,試圖通過分析語言問題來理解思想和世界。該學科的主要創始人是德國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弗雷格、英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羅素以及維特根斯坦等人。語言分析哲學在20世紀西方哲學特別是在英美哲學中占據主導地位,對當代哲學中的其他分支學科以及整個人文學科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語言哲學研究在我國哲學界也已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特別是近30年來得到了長足發展,與國外基本上達到了同步程度。可喜的是,近十年來,它在我國語言學界和外語學界也得到了關注,不僅許多高校外語學院開設了語言哲學課程,并培養該專業方向的研究生,而且還成立了“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在外語類雜志上發表語言哲學論文,出版了年刊《語言哲學研究》和以語言哲學研究為主題的學術著作。這表明,語言哲學已進入我國的語言學界。中國的語言哲學研究雖發展勢頭喜人,但與國內外研究相比,尚有差距。本文旨在澄清語言學界和外語界對語言哲學的一些誤區,使其能受到更廣泛的接受和深刻的理解。本文將重點論述的是語言哲學的性質、任務以及研究方法,最后是我們為什么要學習語言哲學。
1.語言哲學是什么?
當代哲學家對“語言哲學”的定義五花八門,一般認為它與英美哲學中的分析哲學密切相關,或者說,它就是分析哲學的直接后果。因為分析哲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就是語言,主要關注“語言意義、真理、邏輯”等話題。也有哲學家把以語言作為研究核心的哲學思想都劃歸為語言哲學,由此出現了所謂的“廣義語言哲學”;與之相對,英美分析哲學就是“狹義語言哲學”。前者還可將現代歐陸哲學家們對語言的討論也納入其中。
當代西方哲學是現代哲學的產物,是哲學家們借助于現代形式邏輯而形成的一種哲學分析方法。弗雷格當算第一人,他首倡形式化分析命題結構的方法,且區分涵義與指稱等。由于英國哲學家羅素和達米特的工作,這一方法逐漸為后人重視。正如達米特(Dummett,1996:14)所指出的:“他在哲學史上提出了第一個對思想、句義及其構成語詞的合理說明。誰要想通過分析語言意義而去分析思想,他就要無可選擇地以弗雷格所確立的基礎為出發點。”達米特還據此認為,弗雷格確定的語言哲學研究原則就是,“只有通過分析語言才能達到對思想的研究”。
當代哲學中發生“語言轉向”且直接促成了語言哲學出場的,嚴格來說當從維特根斯坦開始,并經由維也納學派在哲學領域中大加推廣所致。他在《邏輯哲學論》(Wittgenstein,1961:4.0031)中大膽宣稱“一切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且明確指出:(1)語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2)未來哲學的綱領就是對命題的邏輯分析;(3)哲學的消極任務就是要消除毫無意義的形而上學,積極任務則是澄清命題記號的性質;(4)對經驗現象的語言描述做出邏輯分析;(5)符號系統的研究就是對邏輯真理的闡明。他認為,“邏輯命題的特征是,人們單從符號就能知道它們為真,而這個事實本身就包含著整個邏輯哲學。”(Wittgenstein,1961:6.113)這些論述對20 世紀20年代的維也納學派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成員在維氏那里找到了表達他們思想的恰當方式,并以此作為整個邏輯實證主義思想的基礎和出發點。
根據當代哲學家們的各種理解,可大致將語言哲學歸結為以下幾個主要原則:
(1)研究語言就是研究思想。由于弗雷格的工作,哲學家們逐漸認識到把握語言的過程就是把握思想的過程,而只有通過對語言表達式的結構及其構成方式的分析,才能理解語句的基本內容。或者說,要理解作為認識活動的思想,只能通過分析語言表達式的結構。這種觀念直接構成了蒯因后來提出的“語義上行”的觀念。
(2)研究語言就是研究意義。自從弗雷格以來,意義研究成為語言哲學的核心內容,意義與指稱、意義與真理、意義與證實、命題形式與命題內容等問題成為語言哲學討論的主要話題。隨著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學派的發展,考察日常語言的實際用法也成為語言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這使得言語行為、合作原則、會話含意成為后來哲學家們討論的熱點。
(3)研究語言就是研究人類活動。由于維氏在《哲學研究》中把語言游戲作為哲學討論的重要話題,哲學家們越來越關注作為人類活動組成部分的語言活動及其特征,試圖通過對日常語言活動的考察揭示語言活動的社會性質。奧斯汀、塞爾、斯特勞森和格萊斯等人的語用學便是這一思潮的產物。
(4)研究語言就是研究世界。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主要以語言的形式表達出來,正是基于語言、思想與世界的三角關系,哲學家們愈發強調語言在認識世界的活動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蒯因明確指出,我們對語言的理解其實就是對世界的理解,因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接受一種科學系統是一個語言問題,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接受一種本體論是一個語言問題”(Quine,1953:14)。這就意味著,任何對世界的理解其實就是對語言的理解。
由于作為哲學分支的語言哲學來自現代英美哲學中的語言哲學思想,因此論述語言哲學的學科性質就只能從現代哲學中去尋找。然而,作為一門獨立的哲學分支,甚至在某些哲學家看來可稱作“第一哲學”的語言哲學,它仍然有自己的獨特問題和領域。根據陳波的歸納,語言哲學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1)語言、世界、心靈、認知、思想等之間的復雜關系;(2)意義論、指稱論、真理論,以及對意義和指稱的語用學研究;(3)意義模糊性、隱喻等等(Lycan,1999,陳波譯,2011:3)。萊肯則把莫里斯提出的關于語言學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直接視為語言哲學的主要內容(同上:170)。國內著名學者陳嘉映(2003:5)在他的《語言哲學》中對語言哲學給出了自己的理解,“語詞是概念的最高形態,但概念考察并不限于考察其最高形態,因此不宜把哲學等同于語言哲學,而應把語言哲學視作與科學哲學等并列的一個哲學分支,雖然這個分支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他認為,語言哲學還應包括“專名與可能世界、語詞內容、隱喻與隱含、語言與現實”等內容,這些都涉及到把語言哲學視為一門哲學分支學科的問題。
我們認為,語言哲學作為一門哲學分支,的確具有不同于其他哲學分支的特征。首先,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把語言視為研究的主要對象,這是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所不具有的。表面上,這個特征似乎與語言學研究相似,但語言哲學研究語言與語言學研究語言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把語言視為理解思想與心靈最為重要的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或把語言看作人類與世界保持互動關系的主要途徑;而后者卻主要把語言視作一種符號系統,并以實證的方法來研究語言的語形、語義和語用。可見,語言哲學是從哲學的角度分析語言符號和語言現象,強調語言與人類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系,而語言學則是從經驗科學的角度處理語言的符號表征,突出語言自身的內在特征。
其次,語言哲學抓住了語言與思想的內在聯系,試圖通過揭示語言的意義而展現思想內容,其重要的哲學意義在于:思想表達成為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通過對語言表達的解釋和理解去把握思想內容,這也是其他哲學分支所沒有的。
再次,語言哲學還把意義問題與真理問題密切聯系起來,強調只有解決了真理問題才能真正解決意義問題,通過對真理問題的說明而達到對語言的理解,這也是語言哲學的一個明顯特征。“語言與實在、語詞與世界”等的關系構成了語言哲學討論的重要話題。這表明,語言哲學不僅具有認識論意義,更是在形而上學層面揭示了實在的終極意義。
一切哲學研究的目的似乎最終都是為了對世界有所理解,但不同哲學分支領域中采用的方式卻各不相同,或者說,正是由于這些方式的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的哲學領域。語言哲學對世界的理解主要是以研究語言的方式進行的,這就使得語言哲學不僅在研究方式上不同于其他哲學分支,而且對待世界的態度上也有了重要區分:語言哲學對世界的解釋完全是建構性的,即世界是按照我們對語言的解釋而建構的。
了解到語言哲學的這樣一些特征,也就能理解語言哲學作為一門哲學分支的性質。
2.語言哲學能做什么?
通常情況下,一門學科的性質就規定了它的任務;知曉了語言哲學的性質,就能知曉語言哲學的基本任務,也就能知曉語言哲學能夠做什么。
弗雷格認為,分析概念的用法是理解語言意義的重要步驟,因此區分“概念詞”與“對象”以及根據句子的形式要求去解釋思想內容,應當是哲學研究的主要工作。他提出的“概念文字”的確為后來的語言哲學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對“涵義”與“指稱”的區分又直接導致了意義理論的深入發展。可以說,弗雷格的工作正是在規定任務的意義上開創了現代語言哲學。
真正為語言哲學提出明確而又具體任務的是維特根斯坦,他在《邏輯哲學論》上對語言所做的邏輯分析其實就是對語言哲學任務的明確規定。這個任務包括:
(1)要對語言表達形式給出限定性說明,解釋語言表達式在何種意義上可以描述世界中的事實情況。他給出的說明就是關于語詞與對象、命題與事實之間一一對應的“圖像論”,即可通過設定語詞與對象、命題與事實的對應關系,揭示語言與世界在邏輯上的對應符合關系。
(2)以真值函項說明基本命題的一般形式,由此說明所有命題的一般形式。這就為命題的構成方式給出了方向性解釋,由此建立了關于命題的真值函項理論。
(3)通過對意義概念的說明,解釋了思想如何成為有意義的命題,并借此確立了思想表達的語言范圍,即語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不僅把思想的可能性限定在語言范圍內,且還把所有可說的東西看作是可以思想的東西。這樣,凡是不可說的東西就只能通過顯示而揭示其意義了。由此可見,維氏為我們明白闡述了語言哲學的主要任務。
后來的日常語言哲學派對語言現象的精細分析往往被視為語言哲學的又一典范。雖然他們的分析方法顯示了語言分析的明顯特征,如通過對日常語言中的語詞用法分析去說明語言活動中的心理機制,但這種方法也帶來顯而易見的弊端:如他們過分關注日常語言中某些語詞的具體用法,缺少對語言機制的深入剖析,更不愿意從語言與世界的關系上理解語言的性質;又如他們強調了對語言用法的描述,卻忽略了對其做出解釋,更沒有從整體上理解語言活動,常使人有“見樹不見林”的感覺。這甚至直接導致后來的哲學家對語言哲學的一般性批評,語言哲學甚至被指責為“零打碎敲、毫無實質價值的工作”。
從上可見,語言哲學的研究方法無外乎以下兩種:一是形式化的邏輯分析,其結果導致了對語言結構的重新構造,忽視了日常語言的實際使用;另一是對日常語言用法的細致分析,其結果造成無法從整體上把握語言的意義。根據當代語言哲學家們的實際研究情況,本文擬將語言哲學任務大致歸納如下:
(1)語言哲學研究就是要更好地了解語言的實際作用,以便能通過掌握語言用法從而進一步理解語言使用對于認識活動的意義。
對語言實際用法的描述始終是語言哲學學家們研究語言的主要內容。這種描述基本上是經驗性的,主要考察日常語言使用中的各種具體情況,包括一些非語言現象與語言活動之間的關系。當然,這種描述也是規范性的,要對各種語言使用情況(即語境)從理論上給出總結和歸類,以便確定不同語言使用情況的特征。弗雷格確定的語境原則不僅是對命題形式的意義規定,更是對語句使用具體情況的考察。蒯因提出的意義場理論更是根據科學命題的意義而得出的結論。
不僅如此,描述語言的實際用法是為了更好理解語言的使用對于認識活動的意義。人們的認識活動是通過感知世界而產生的,最終通過語言表達來完成。認識活動的最終結果就是我們得到了關于世界的知識。人類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并掌握它們,取決于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并掌握用于表達這些知識的語言。要很好理解并掌握語言則取決于對語言實際用法的了解,以及能否正確地使用這些語言。
正是基于對語言用法與認識結果之間關系的這種理解,語言哲學就要詳細描述語言的實際用法,包括語言的構成方式即語法描述以及語言的具體使用情況。當然,這種描述與語言學的描述有很大不同。語言學側重于實證,而語言哲學則更多地反思了語言現象,以能理解語言實際情況與人類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要認識語言活動的一般規律,就要把握語言活動的性質。
(2)語言哲學研究要給出對語言意義構成方式的明證,由此表明一種語言在何種意義上可以是有意義的。
這種明證的前提一定是經驗性的,而非推論性的。所謂“推論性的明證”是指,根據已有信念和知識確保現有明證是可靠的。但對于意義構成方式的明證而言,這種推論性明證又是不可取的,因為這種明證完全是根據我們對現有語言的理解,其本身也構成了這種明證的一部分,而不是說這種明證是根據我們的理解而推出的結果。換句話說,我們關于語言意義構成方式的明證,正是我們對現有語言的充分理解。因此在這種意義上,這種明證只能是經驗性的。
這里所謂的“意義構成方式”是指,語言的意義必須以某種方式加以說明。按照達米特的說法,它應適用于所有語言。正如塔斯基提出的語義學真理定義一樣,對意義構成方式的說明必須能為合理解釋語言意義提供了一種內容上恰當、形式上正確的意義構成條件。所謂“內容上恰當”,就是要對意義內容給出合理的說明,符合認識論上的意義說明;所謂“形式上正確”,就是能夠對意義獲得方式給出形式上的規定,保證從形式上就可以判定意義說明的有效性。
當然,所有這些都表明:一種語言在何種意義上是有意義的。蒯因認為,這里的“有意義”應當指能為使用它的人所理解和掌握,且能產生相應的結果。所以,語言哲學研究在處理意義時并不是要對意義本身給出獨立于語言使用的說明,而是能給出語言意義條件的說明,包括形式的和非形式的條件。這樣的意義理論才具有普遍性。同時,這樣的意義理論也并非一種關于意義的理論,而是一種關于語言如何有意義的理論。
(3)語言哲學研究要通過研究語言揭示人類與世界的互動形式。
在人類與世界的交往中,語言是最為重要的途徑。這種重要性首先表現在語言是表達人類理解世界的簡單而又便捷的形式,語言的使用又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因此人類對世界的理解絕大部分都是通過語言表達完成的。同時,語言的重要性還表現在語言具有的意義特征,它是根據語言使用者對語言的使用而變化的。這就增加了語言活動的復雜性、多變性以及意義的多樣性。人類通過復雜多變的語言與世界打交道,甚至可以說,人類在語言中不是與世界打交道,而是與語言自身打交道,最終是與自己打交道。因此,研究這種復雜多變的語言現象,就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人類與世界的互動關系。
語言學也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人類與世界的關系,在這種意義上語言學與語言哲學的目的一致。應當說,現代語言學正是哲學家們重新思考語言性質以及運行機制的結果。所以我們經常說,語言學產生于語言哲學,兩者不可分割,這不僅指語言學對語言哲學的依賴,而且還指語言學本身就構成了語言哲學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迄今為止我們無法清楚地區分“語言哲學”(philosophy of language)與“語言學哲學”(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或“語言的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的主要原因。我們現有的區分更多的是歷史的,而非學理的(Vendler,1957,陳嘉映譯,2002:9)。
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在處理人類與世界的關系上,語言學與語言哲學之間仍然存在重要差別,否則我們就沒有任何必要區分這兩者了。我們認為其間最主要差別在于:語言哲學要外觀世界,通過研究語言更深入地理解世界;而語言學則要內觀語言,試圖通過語言與世界的關系更好地理解語言本身。這或許表明了語言哲學作為一門哲學分支與語言學作為一門經驗學科之間的區別。這里的“外觀”就是要從語言研究出發去觀察和理解世界,而“內觀”則主要就語言本身進行描述和解釋。理解了這兩者的區別,便可更好地理解語言哲學的主要任務。
從上分析可見,語言哲學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對世界的理解,以致對人類自身的理解。基于這個目的,語言哲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分析語言意義的構成方式、語言活動的一般規律以及語言活動與非語言活動之間的復雜關系,來說明語言及其活動對人類活動的意義。這完全是一種概念性、反思性的研究活動,但卻對具體的語言研究起到了方向性指導作用。
3.如何研究語言哲學?為何學習語言哲學?
談到語言哲學對語言學的指導作用,或許我們會想到哲學觀念對一般活動的指導作用。的確,語言哲學作為哲學的分支當然會對語言活動產生一定的指導作用,但這種指導有時并非是直接的,如同學習了哲學不一定就知道如何去行動一樣。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觀念要轉換為群眾的物質力量,必須首先為群眾所理解和掌握;同樣,語言哲學對語言學研究的指導作用,也需要語言學家們首先對語言哲學的理解和掌握,這種理解和掌握的過程,就是學習語言哲學的過程。
如何學習和研究語言哲學,這涉及如何學習和研究哲學的問題。雖然某些哲學家把語言哲學看作第一哲學的觀點并不為所有哲學家都接受,但語言哲學與一般哲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卻是大家公認的。這主要是因為語言哲學重在通過分析語詞概念,來理解和解釋語言意義,進而達到對世界的理解,這與一般哲學的工作性質完全一致,即哲學是為了清晰論證和說明我們的所思所想,辨析概念意義顯然有助于理解世界概念,因此,在這種意義上學習和研究語言哲學,就是在從事哲學研究工作。既然如此,在這一過程中就需要掌握一些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1)哲學需要學會從經驗到理論、從常識到思辨的上行之路。我們常說哲學要超越經驗,這樣才能進入抽象的哲學領域。語言哲學作為一種哲學研究,首先就需要超越經驗上的語言現象,能從語言現象中發現具有普遍性的語言性質和規律。當然,超越經驗并不是脫離經驗,哲學的歸宿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經驗,這才是哲學的真正完成。正如黑格爾所說,“哲學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確認思想與經驗的一致,并達到自覺的理性與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達到理性與現實的和解”(黑格爾,1980:3)。學習哲學的唯一道路就在于從具體的生活和實踐中去體會其中所蘊含的真實思想。同樣,學習語言哲學的唯一道路就在于從具體的語言活動中發現語言現象背后的語言性質。
哲學還需從哲學回到生活和實踐的下行之路,這就意味著,語言哲學必須最終要回到語言的經驗活動,從經驗中驗證普遍規律的正確性。
(2)哲學思維的特性在于抽象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因此,哲學的研究方式就只能是概念性、論證性和非結論性的。哲學的抽象就是一種通過概念之間橫向的邏輯關系來自我限定的抽象。這是因為,“在極高度抽象的情況下,概念的內涵被提煉到了極其‘純粹’的普遍性程度,以至于如果不用與它相對應的另一個概念來比照和限制,就無法界定和顯現它所要表達的特殊內容。這種通過概念之間的橫向關系來自我限定的理論特征表明,哲學的抽象始終是一種力求在最大限度上把握事物最普遍特征的理性創造,并不是一種無所節制、隨心所欲、脫離現實的想象和臆造。有了這樣最高程度上的抽象概念,人類才能夠在最具普遍性意義的層次上思考那些最具普遍性的問題,以能從總體上把握世界,而不必一一回答每個個別的問題”(李德順,2011:22)。語言哲學中討論的主要概念同樣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如“意義、指稱、真理、世界、可能性、必然性、意向性”等,語言哲學家們試圖通過對這些概念的討論獲得對語言活動以及語言的一般性質的理解。
我們知道,哲學的批判活動通常是通過論證的方式對一切科學和常識的前提提出追問和質疑。哲學批判不同于其他批判(包括科學批判)的一個主要之點就在于,日常批判是形而下的、日益走向具體實證化的批判,而哲學批判則是形而上的,即對構成對象或思想的前提和根據的批判。思想的前提和根據就像“一雙看不見的手”,盡管它在最終意義上決定著思想發展的方向和道路,但在常識和經驗科學的視野中它卻是隱而不顯的。“構成思想的根據和原則雖然深深地‘隱匿’在思想的過程和結果之中,但它作為思想中‘看不見的手’和‘幕后的操縱者’,卻直接地規范著人們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孫正聿,1998:176)。哲學批判恰恰在于把這雙“看不見的手”展現出來,讓它從“幕后”走向“臺前”,由“操縱者”變為“表演者”,并在“理性”舞臺上為自己辯護。這就是哲學論證的功能。語言哲學也正是通過邏輯分析和概念分析的方式,以追問合理性的論證從而獲得對語言現象的更一般性解釋,并對已知的語言描述給出前提批判。
哲學批判是一種在邏輯上最具徹底性的批判,其徹底性還表現在,它的批判矛頭不僅是“對外”的,即針對一切外部對象和已有概念及成果,同時也“對內”,針對批判者的思想自身。這就是哲學的反思性特征。這種反思性特征決定了哲學不可能終結對一切問題的回答,相反,“哲學問題一開始就是人類所面臨的永恒問題——它不僅本質上就是人類生活中所產生或出現的最根本問題,而且也是基于人類生活形式在某個層面上的相似性來思考全人類的共同問題。哲學問題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如古希臘哲學家所思考的很多問題仍是當今哲學家繼續思考和探究的問題”(馬爾霍爾,2007:1)。這就使得哲學研究不會對哲學問題得到最終結論性的回答,“我們甚至可以把哲學史想象成是一個(長命的)人在一段一段的時間里‘接著’想下去,后人接續前人,‘不斷地’做下去”(葉秀山、王樹人,2004:17)。這種非結論性的研究方式恰好是哲學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源泉。
(3)哲學研究的基本思考順序是從“時間在先”轉向“邏輯在先”,從時間上的“順序思考”轉向“從后思考”。這里所謂的“時間在先”,是指對象依據時間序列中的先后次序;所謂的“邏輯在先”,是指從邏輯上看事物的本質及其相互聯系,關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根據和條件,把握處于“優先”地位的對象之本質和普遍聯系。從性質上看,“時間在先”是經驗科學的視野,體現的是科學的解釋框架;“邏輯在先”是哲學的視野,體現的是哲學的解釋框架。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根據外在時間,前者依據時間,而后者超越時間,這正是哲學得以成立的根據和理由,是哲學特有的思想層次和思考路徑。從“時間在先”轉向“邏輯在先”,實質上就是從科學視野轉向哲學視野,這對于語言哲學來說具有重要意義,是從作為經驗科學的語言學轉向作為哲學分支的語言哲學研究的必經之路。
哲學研究中的“邏輯在先”并不意味著無視歷史的時間順序,而恰恰是從對象的歷史生成意義上來把握其時間順序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從后思考”。這種思考方法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提出來的。他指出,“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馬克思,1972:92)可見,所謂的“從后思考”就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和結果”出發,通過“由果溯因”的逆向運動來把握事物本質及其發展的內在邏輯。當然,在運用“從后思考”方法時必須把握限度,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現在與過去的差別,不能把現在的理論觀念不加區別地簡單套用到過去。
一旦掌握了哲學研究的這些基本方法,就可以把它們運用到語言學研究當中,由此便可理解語言哲學對于語言學研究所具有的重大指導意義。
[1]Dummett,M.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Quine,W.V.O.From Logical Point of View[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3]Wittgenstein,L.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London:Routledge,1961.
[4]澤諾-萬德勒.哲學中的語言學[M].陳嘉映,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5]陳嘉映.語言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6]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7]李德順.哲學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8]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孫正聿.哲學通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11]威廉·G·萊肯.當代語言學導論[M].陳波,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12]葉秀山,王樹人.西方哲學史:第1卷[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