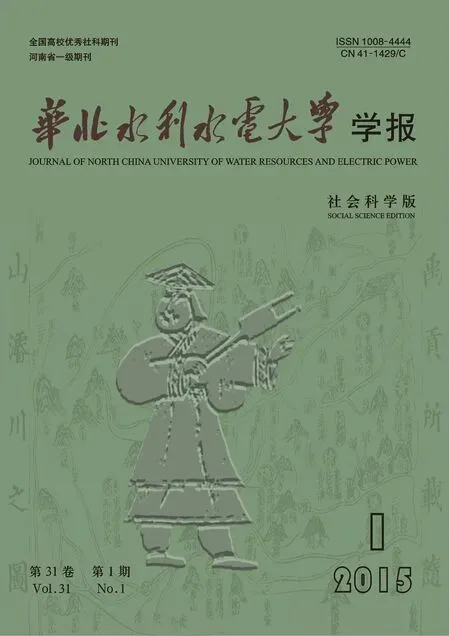社會科學哲學的語境論進路
陳肖東
(大連理工大學哲學系,遼寧大連116023)
當代社會科學哲學是連接社會、科學與哲學的橋梁,其研究方法在不斷地探索和更新,以尋求該學科的持續、健康發展。從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進路上看,邏輯經驗分析、歷史分析、實踐分析逐漸淡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主流,在經歷語言轉向和解釋學轉向后,社會科學哲學也逐步實現向修辭學轉向。社會科學哲學的修辭學轉向也被稱為20世紀繼語言轉向和解釋學轉向后的人類第三次理智運動。
修辭學的大量運用,實質上開啟了社會科學哲學的語境論進路。因為,人類在描述社會歷史的“故事”時,都是以語言作為基本符號,語言受個體的差異、語境的差異、研究者的情緒等影響很大,即使是敘事性的研究進入,都會造成事實與解釋的巨大差異,因而,此時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帶有語境的。這種語境觀念在思維領域滲透的同時,一種語境論世界觀逐漸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發展中顯現出來。無論是以語境實在為特征的本體論立場,以語境范式為核心的認識論路徑,還是以語境分析為手段的方法論視角,語境所具有的元理論特征,使人們已經不能把語境論僅僅局限于使社會科學哲學融合起來[1]。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方法需要擺脫“科學效應”的影響,讓社會科學哲學使用修辭學,以消除“科學效應”帶來的差異,走出辯護主義者的科學哲學與非理性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的科學哲學之間的二難選擇的困境。
一、“科學效應”對傳統社會科學陳腐、刻板的統治
19世紀以來,“科學效應”風靡西方的科學界。為了讓社會科學成為“科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嘗試了在研究中引入科學的方法。當時關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主流思想的基本主張是:把有關人類事物的規范知識(社會科學)與文學和修辭學(文學批評)區分開來。1929年,哲學領域的重要學派——維也納學派,在成立時發布的宣言中,再次強調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科學取向:“他們闡述的科學世界觀的主要理論要素是經驗、實證和對語言的邏輯分析;同時,把這些分析分別應用于算術、物理學、幾何、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2]于是,在科學方法的奠基下,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具備了初步的規模。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注重力求還原的敘事
“科學效應”是一種研究方法,意在引導讀者形成適當的態度,以確立社會科學家的精神氣質[3](P269)。這種效應來自于表現形式,而不是被表現的事物。在“科學效應”的影響下,研究者的敘事都是用語言和不斷變化世界創造那種“事實”,這種“事實”要成為人們公認的“觀點”,而又不能是一種觀點。大量的時間、地點、人物等客觀的因素撰寫其中,而修辭等主觀性較強的因素均被傳統社會科學排除于體系之外。在這種情況下,還原主義原則,貫穿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始終,社會科學的“事實”力求的客觀,將所有主觀因素拒斥于研究之外。
(二)強調可逆性的論證
傳統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者同樣注重論證的可逆性,這使得很多社會科學向著自然科學的方向發展。如《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指南》的頒布,就讓心理學這門從哲學脫離出來的學科,逐漸從論辯性的探究變成了實驗性的報告,敘述者、被敘述者以及運用的結構逐步從研究中僵化起來。《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指南》逐步成為行業的標準,無論是研究者或是從業者都必須遵守《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指南》制定的規范。《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指南》的規則實際上會使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喪失在許多極為重要的社會科學雜志上發表的資格,在這些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其科學效應是必不可少的。而在《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指南》制定的規范下,研究結果的突出特征是:材料是結構的內在組成部分;沖突和沒有答案的問題很少出現;所有的參考文獻都具有同樣的形式和地位……這標志著從論證向沒有經過論證的實驗主義的退卻。
(三)重視對事件的邏輯分析
亞里士多德是邏輯之父,自他開始,后人便習慣性地把邏輯作為“思維的工具”。在傳統社會科學研究中,研究者注重運用狹義的邏輯方法,這種邏輯在嚴格性、抽象性、邏輯性、系統性方面幾近苛刻,研究者在苛刻的方法下尋求歷史、社會、文化等內在的邏輯性。但是這種研究卻往往沒有達到研究者的預期效果,邏輯學的三段論并不適用于所有的“感性”的社會科學案例,邏輯學的充足理由律中的兩大律令:(1)理由必須真實;(2)從理由能夠推出結論。這兩條看似簡單,但是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并不容易做到。
二、對“科學效應”統治的批判和反思
當“科學效應”在世界浪潮中逐漸消弭之際,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者也發出了批判的聲音,人們發現了雖然受到這條效應制約多年后,社會科學的研究并沒有進入“科學”的行列,反而讓自身的發展失去了生機。
(一)絕對的還原只是“虛幻”
研究者擔心,如果把社會科學理論化,那么就會造成人們的注意力從實在方面移開,失去“實在論”,而過度強調方法則社會科學將虛而不實。例如:社會學家把握“大屠殺”無疑不同于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的理解。社會學家側重該事件對社會結構、社會進步等的影響;政治學家側重該事件對政治格局、階級斗爭等的影響;歷史學家側重對事件的屠殺過程(起因、經過)等客觀事實的記錄。人類學家側重該事件對人類思想進化和涌現出的一些領導人等的記錄;他們都力圖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制造出某種具有強制性的論點,但是因為所持立場的不同,表述出來的研究結果也大相徑庭。
除了立場的不同,研究工具的不同也會形成不同的研究結果。社會科學一般使用的研究模型是將觀察理由(觀察者)與現存世界通過具有重要作用而又與理由和世界均無關系的中介系統(觀察工具)結合起來。
例,觀察者:我;觀察工具:思(故我);觀察對象:在。
雖然世界是客觀存在的,因為觀察者使用的觀察工具(核心)的不同(宏觀、微觀)等(例如伽利略的望遠鏡),他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世界有很多節點,它可以被切割成許多小碎片),也導致了觀察者心靈的分離性和個性心理結構的產生。
(二)深陷無法調和的“兩難”
實證主義還主張用“明顯的”數字語言來記錄經驗性的現代事實。例如,19世紀30年代,有關編號方式或者毋寧說從有關數字化事物中做出歸納的辯論,都成功地運用了統計學。統計學的大量運用,催生了許多“數字化的事物”,而這些事物無不成為“對愚蠢的數字所表現出來的乏味而無聊的炫耀”[4](P25)。以經濟學家為代表,他們希望達到一種純科學的境界——一種能夠精確地加工計算的模型世界,其中不管是論證還是講故事都不妨礙對原理的證明。人們作為精于計算的經濟主義,運用更多的計算,結果導致對模擬和模型的過分依賴,以及政策制定中的華而不實。
實證主義視域下的社會科學面臨著兩難的發展困境。研究社會科學并堅持科學實證的方法,這樣可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獲得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此時它已經不再是社會科學,而成為“內在一致”的學科。否則,研究社會科學并使用非實證主義的方法,社會科學會形成自身的特色,但是會成為諸多個人主觀因素達成的暫時一致,缺少客觀性和科學方法,被自然科學排擠。
三、溫和的轉向
在經歷了艱難的摸索之后,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多種新的轉向。一種重生意義的新的美學科學已經出現,它對人類的知識和真理進行考察,把它們視為我們在世界上的有限位置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錯誤,它所使用的工具是我們自身所形成的。理查德·哈維·布朗(Richard Harbey Brown)花費了20年時間發展了一種具有詩歌文體形式,介于實證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個對立概念之間的社會學。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也致力于將社會科學帶回美學和道德科學領域,他堅持認為歷史及社會科學的復興只能來自該領域之外。維柯(Vico)的觀點認為人類創造歷史,人類選擇歷史。
(一)語言轉向
美國當代歷史哲學家漢斯·凱爾納(Hans Kellner)認為,社會科學家的職責并不是平鋪直敘地述說這一故事,相反,“曲解故事”成了一種解讀社會和構造歷史的方法。也就是說,史料不再是歷史寫作的基礎,這個基礎變成了文本的語言結構。同時,由于作者的寫作必須依賴語言,但作者通過自己的語言構成的文本,并不見得等同于作者的內心意圖,也不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對象。社會科學亦是如此。
(二)解釋學轉向
在解釋學的觀點看來,任何一種社會科學理論解釋都不可能是對理論文本的純客觀解讀,其中必然存在著科學家共同體的先存觀念、先存知識和先存方法的引入問題。因此,任何一種科學理論解釋都只是附著在特定語境基底上的產物,不同的語境基底必然會形成不同的科學解釋體系。解釋學會側重分析社會學描述中的隱蔽的“內在一致性”。社會科學得以保存,正是因為對不確定的客體(過去發生的事件、社會構成、經濟交易、政治勢力等)按照隱蔽的一致性(默認的社會共識)進行“命名”(概括社會事件),使這些現象作為研究的對象而保存下來。可以預言,若沒有這種一致,在其現有形式上所謂社會科學事業將會崩潰。解釋學正是找尋和解讀這種“內在一致性”的途徑。
(三)修辭學轉向
用比喻修辭來組織社會科學研究素材的四種方式是:“隱喻本質上是表現的(representational),轉喻是還原的(reductionist),提喻是合成的(intergrative),而諷喻則是否定的(negational)。”[5]我們可以這樣大致地來理解隱喻的四種類型在歷史意識和歷史寫作中的實際體現。隱喻,它所建立的是兩個對象之間的類比關系。我們在歷史著作中常常看到,以植物的生長、繁茂和衰敗來類比一個民族或文化的興衰起落,或者以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意象來表述個體或民族經歷危機而重新煥發活力的歷程。轉喻,其特征是把整體還原為部分,如將對殖民主義的個別抵抗行為視作給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賦予了意義,視作某種普遍現象的代表。又如以伏爾泰一生言行作為啟蒙運動的人格化身。提喻,與轉喻相反,其運作方向不是從部分到整體,而是從整體到部分。由“一切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或“一切歷史都是貴族的靈床”(帕雷托)這樣對全部歷史的意義做出判斷的命題出發,一切個別事件或事件組合都由此得到理解并獲得其意義。諷喻,對于某種關于歷史的判斷采取懷疑主義或犬儒主義的否定態度,以展示出與之相反的意涵[6]。一旦我們接受了這種修辭學轉向,我們就會在我們一向擁有的同一基礎上做出道德決定,因為我們不可能是我們已經所是的那個樣子了。而接下來研究者面臨的問題是,這種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如何使人相信?
(四)心理學轉向
心理學轉向是繼語言轉向之后,科學哲學在其理論發展和演變過程中呈現出的又一重要趨向性特征,是人類哲學理性的又一次進步。對于當代意義理論進行了認知分析,展示出在語言外衣下融合語義和意向已成為當代意義理論的必然走向,心理認知與語境分析方法的結合成為科學哲學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趨勢,從而證明了對心理認知的語境說明已經在整個科學哲學的解釋中顯示出令人矚目的啟示性意義,鮮明地映射出科學哲學研究對心理認知因素分析的依賴性。
四、結語
運用語境論的隱喻思考與模型化方法,不僅能夠使科學進步過程中的微觀的邏輯結構與宏觀的歷史背景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且能夠使基本的內在邏輯的東西在歷史的發展中內化到新的語境當中,從而使語境在自然更替的同時,不僅完成了理論知識的積累與繼承的任務,同時也揭示出更深層次的世界機理。因此,語境生成論的科學進步模式既不會走向相對主義,也不會走向多元真理論,相反,它既能夠包容相對主義的某些合理成分,又能夠堅持實在論的立場。
[1]郭貴春.隱喻、修辭與科學解釋:一種語境論的科學哲學研究視角[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2]成素梅.科學哲學的語境論進路及其問題域[J].學術月刊,2011(8).
[3]斯蒂芬·P·特納,保羅·A·羅思.社會科學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4]漢斯·凱爾納.社會科學哲學:“另見文學批評”——介于事實與比喻之間的社會科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5]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6]彭剛.敘事、虛構與歷史——海登·懷特與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型[J].歷史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