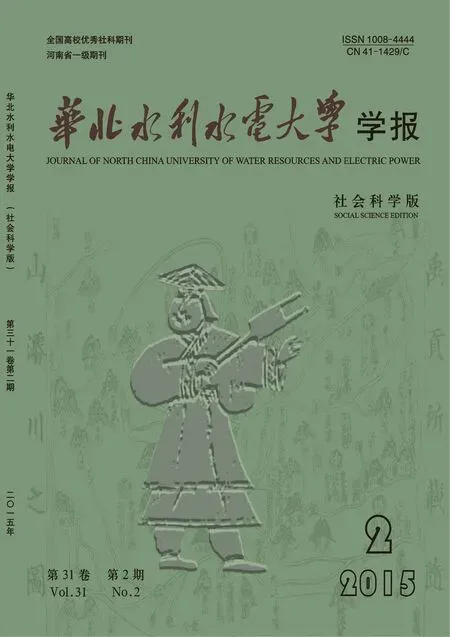論湖南衛視綜藝節目的后現代主義特性
馬俐欣
(鄭州大學文學院,河南鄭州450001)
近年來娛樂節目如日中天,稱霸熒屏。湖南衛視更是將節目準確定位在青年人這一娛樂生力軍上,成功打造了一系列綜藝節目,如《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爸爸去哪兒》《我是歌手》《花兒與少年》《百變大咖秀》等。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每一檔由湖南衛視打造的綜藝節目都能引起全國范圍內的熱烈討論與瘋狂追捧,使得湖南衛視成為娛樂界難以撼動的大佬。在湖南衛視的風光之下,就連央視的綜藝節目也黯然失色。國家廣電總局于2011年7月專門召開了“關于防止部分廣播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座談會,10月下旬正式頒布“限娛令”,要求各地方衛視在17∶00至22∶00黃金時段,娛樂節目每周播出不得超過三次。即便如此,也沒有真正削弱娛樂綜藝節目的強大影響力。湖南衛視綜藝節目成功的背后,到底蘊含著怎樣的文化心態?反映了現代人怎樣的心理機制?筆者將從后現代主義視角進行分析解讀。
一、精英化的消解與大眾化的盛行
《快樂大本營》是一檔嘉賓訪談游戲型的綜藝節目,邀請兩岸三地的知名藝人進行訪談、游戲。《花兒與少年》以七位明星相互結伴窮游歐洲為題材,記錄這群平日衣食無憂、萬眾矚目的人,在陌生而拮據的條件下的生活狀態。《爸爸去哪兒》是一檔親子戶外節目,節目挑選了五組精英家庭,分別由爸爸帶著年幼的孩子進行五次旅行,五位精英男士還原到爸爸的角色,親自擔起照顧孩子衣食住行的責任。《天天向上》是一檔禮儀公德脫口秀節目,用輕松幽默的方式傳播中國千年禮儀之邦的文化。《我是歌手》是一場全國頂級歌手對決真人秀,歌手服從淘汰制的規則進行競演角逐。《百變大咖秀》則是集表演、音樂、時尚為一體的明星模仿秀大賽。這五檔節目代表了湖南衛視綜藝節目的最高成就,同時也是當下國內綜藝節目的縮影。
在形形色色的節目背后,涌動著一股后現代主義浪潮。在后現代主義的場域中,文化不再專屬于精英和少數天才人群,而應該是大眾的、日常的。湖南衛視的綜藝節目,恰恰牢牢把握了這一準則,節目內容都比較貼近生活、貼近觀眾。節目將位高權重者與卑微貧賤者、偉人與無名之輩、智者與愚夫結合到一起,消除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距離。這些欄目里有眾多的明星出現,但并不刻意地追求明星效應。節目中出現的名人們不再是聚光燈下的焦點,他們褪去了光環;也不再富有,要像平凡的大眾一樣面臨基本的生計問題,甚至面臨激烈的社會競爭。他們在節目中斗嘴、揭短,頻頻犯錯、失誤,與平日光鮮亮麗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央視著名主持人倪萍調侃搭檔趙忠祥生活中極其摳門,導演王岳倫不知道如何給女兒扎馬尾辮,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此外,主持人作為綜藝節目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風格也由嚴肅刻板向平易近人轉變。與以往的綜藝節目不同,湖南衛視的主持人形成了個性獨特的主持風格。何炅與汪涵善于制造歡樂、融洽的氣氛,穩重而不失幽默,睿智而不失風趣;謝娜敢于犧牲自己高雅的形象,運用夸張、搞怪、出丑等方式娛樂大眾……他們為了滿足觀眾、取悅觀眾,不單以傳統的表情微變化和聲音的抑揚頓挫取勝,而是在主持的過程中隨時變換角色,以表演的形式隨時準備進入情境,坐下、趴下、躺下。
后現代思潮影響下的綜藝節目展現出對精英文化的解構和顛覆。在節目中,繁瑣的日常生活取代了理想與信仰,人們所共有的柴米油鹽、喜怒哀樂被搬上了熒屏。精英的介入不是為了進行高高在上的指導,而是站在大眾的立場,認同大眾的生存方式和價值觀念,用平民化的思維和語言來揭示大眾的生存狀態,從而在精英文化的反叛和主流文化的一體化趨勢之外,形成大眾自己的話語權利——即關注現實的、當下的日常生活,從彼岸的烏托邦理想回歸到生存、人事關系、金錢、時尚、娛樂等俗事中來。
不能忽視的一點是,當代中國文化是一個多元的、相互獨立又相互妥協的文化。在中國,后現代主義是與多種文化觀念混雜在一起的。因而在這些綜藝欄目中,那種顛覆性的后現代主義文化往往是與主流文化共存的,即不僅僅是“下里巴人”,也還有“陽春白雪”,國家主流意識與純粹娛樂搞笑的節目常常共處于同一平面上,這也體現了后現代主義對不同文化場域的疊加能力。
二、娛樂化、狂歡化特征明顯
后現代主義對綜藝節目的顯著影響即是放大了節目的娛樂性質。
首先,話題的娛樂化。傳統綜藝節目最常選擇的話題即是音樂與影視。音樂、影視以其多變的風格給人以視覺和聽覺上的沖擊與享受,最能達到活躍現場氣氛的效果。節目組或是邀請娛樂界的歌星影星進行訪談,或是對音樂與影視進行模仿,或是讓頂級歌手進行同臺較量,以期獲得最大的收視效果。然而湖南衛視的系列綜藝節目,在常規娛樂項目之中插入了紛繁多姿的娛樂話題,任何事情都可以隨即拿來消遣逗樂。比如在《快樂大本營》中,身高、體型、吃相、廚藝、旅行箱內收納的物件、臥室床頭書的選擇等私人話題都屬于談話的范圍。部分受邀嘉賓也深諳此道,擅長進入自我嘲諷的模式,例如袁珊珊在網友“袁珊珊滾出娛樂圈”的怒罵聲中,自己示范“滾”的動作,以娛樂的方式化解潛在的矛盾沖突。
其次,語言的娛樂化。后現代文化的發展方式是“語言游戲”,即在一個談話的語境中,說話者處于一個“知者”的地位,而聽話者則處于一個同意或反對的地位。綜藝節目所擅長的也正是這種語言游戲的手法。一句話可以任意聯想出一個或多個話題,語言是無序的碎片,可以根據大眾的口味重新組合與闡釋。為了盡量保證節目的真實感,湖南衛視的綜藝節目往往不經彩排,制作人只提供大致思路而不進行細致演練,節目中的語言多是心之所想、脫口而出,具有很強的隨機性與無序性,為觀眾呈現出一個全新的戲謔的話語世界。
最后,敘事方式的娛樂化。電視以視覺形式來表達大多數的內容,使得電視節目的錄制采取了帶有娛樂色彩的敘事模式。在錄制過程中,主持人把握節目進程,常常以懸念的方式吊人胃口,為了保證收視率,答案的揭曉也往往以荒誕的手法呈現;主持人與幕后工作者想方設法設置各種“沖突”,即挑起主持人之間、主持人與嘉賓自身的“沖突”,使得節目中充滿尖銳性和戲劇性。后期制作也是節目不可或缺的敘事環節。綜藝節目作為一種娛樂方式,是對現實世界進行處理之后的虛假世界,制作者將視頻素材拼接在一起,采用對比、回放、特寫等方式,再配上的歡樂或煽情的文字和音樂,從而達到讓觀眾歡笑、哭泣或目瞪口呆的目的。比如在《爸爸去哪兒》中,田亮嚴厲地教育哭泣的女兒,而節目制作人刻意回放了他前期聲稱自己溫柔的話語,連播三次“我是一個慈祥的爸爸”,前后巨大的反差使得觀眾們哄堂大笑,欲罷不能。
具有后現代主義特征的娛樂節目逐漸淡化了主流文化,它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教授某些知識,而是純粹地為了娛樂而娛樂,通過玩耍和快樂的參與過程帶給人們感官上的愉悅,從而減壓放松,這使它徹底消解了高基調的主題承載,解構了傳統審美模式,推崇娛樂至上,將娛樂節目回歸本真。后現代主義所表露出的狂歡與激情,最早應來自古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精神”。酒神象征醉狂、激情、音樂、想象、本能、生命。后現代主義思想通過對“酒神精神”的發揚來表現對生命的肯定和張揚,對生命的激情與狂歡,目的在于擺脫理性與法則的束縛,達到生命的解放與完滿。
三、后現代主義影響下的綜藝節目所暴露出的問題
(一)過分追求娛樂,導致節目難以傳達有益的價值觀
這一點在《百變大咖秀》這檔明星模仿秀節目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在《百變大咖秀》中,主持人每期模仿一位經典熒幕人物形象(如趙雅芝版白素貞、傅藝偉版妲己、李明啟版容嬤嬤等),同時,受邀嘉賓也以模仿某位公眾人物的形式在舞臺上進行才藝展示。模仿重形似而輕神似,常以反串、惡搞等夸張形式引人捧腹大笑。導演對模仿者的挑選似乎只取決于他有沒有廣泛的知名度,能不能憑個人能力逗樂更多的觀眾。至于明星的模仿是否比民間模仿高手還到位,明星模仿的意義在哪里,沒有人說得明白。就連身為主持人的何炅也笑著調侃說,“我也不知道這個節目的定位和意義在哪里”。此外,綜藝節目為了突出娛樂性,滿足觀眾的心理需求,往往設計一些明星們不擅長的游戲環節,以明星的笨拙、失敗顛覆他們平日高高在上的形象。觀眾在對明星善意或惡意的嘲笑中獲得心理上的滿足,然而人們在一笑了之之后并沒有任何其他收獲。
我們的文化已經開始采用一種新的方式處理事務,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了表現一切的形式。電視一直保持著一成不變的笑臉,不但為我們呈現娛樂性的內容,而且將所有的內容以娛樂的形式表現出來。后現代主義文化消解了崇高的意義,試圖開辟多元的文化境界,但是后現代主義的無信仰、反傳統、顛覆性也帶來了虛無的色彩,淡化了人們對于文化價值的追求與理想信仰的堅守。
(二)后現代娛樂節目具有明顯的后現代復制文化的特征,缺乏創新性
湖南衛視的多檔娛樂節目如《爸爸去哪兒》《我是歌手》《花兒與少年》引自韓國,《百變大咖秀》引自西班牙,原創性很低,它們的類型、模式、內容,甚至連語言都是原封不動地復制而來;自詡原創的《快樂大本營》也多多少少帶有臺灣綜藝節目《康熙來了》的影子,近年來也逐漸陷入了重復的囹圄之中,娛樂段子老梗新用,游戲環節大同小異,難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此外,《爸爸去哪兒》《我是歌手》《花兒與少年》《百變大咖秀》之類的節目雖然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觀眾,但由于節目形式的固定套路,很容易造成觀眾審美疲勞,使得它們難以形成長期的品牌節目。
中國現階段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后現代主義也伴隨著多種思潮融入文化熔爐之中。后現代主義打破了中國長時間僵化的思維模式,推動了轟轟烈烈的娛樂時代。然而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使得我們不得不理性地面對它所帶來的一切。從湖南衛視這一娛樂領軍衛視入手,研究其特色綜藝節目,能夠使我們更準確地把握當下大眾文化脈搏,及時挖掘其中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從而為文化事業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