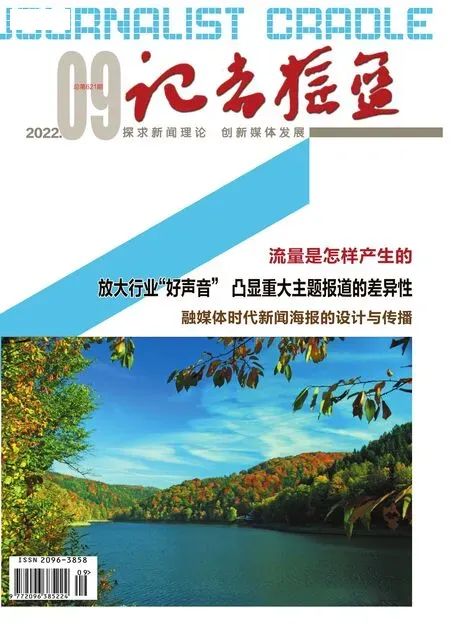從“交叉學科”到“平臺性學科”:“新文科”語境下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芻議
□王 偲 李 薇
“新文科”建設提出已近三年,學界對“新文科”的來源、特點、建設途徑等進行了大量的討論。總體來看,“新文科”的提出旨在從學科建設標準、學科分析框架、學術古典主義傳統(tǒng)以及知識生產(chǎn)方式四個方面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人文社會科學的突破與超越;中國語境下的“新文科”建設本質上是一項由國家和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系統(tǒng)性工程,強調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派。
本文擬從新傳播研究這一概念入手,關注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對當前人類社會發(fā)展而言的重要性,并借助學者劉海龍?zhí)岢龅摹捌脚_性學科”概念,強調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的學科特征從“交叉學科”到“平臺性學科”的轉移,分享筆者對“新文科”建設背景下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改革的思考,以求教于國內專家同行。
一、新傳播研究
“新文科”建設的核心在于“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模式,做強一流專業(yè),建設一流課程,培養(yǎng)一流人才”等方面,“新文科”建設最核心的工作仍然是對人的培養(yǎng)。那么,“新文科”的發(fā)展就不能僅以知識應用為導向,而是要將知識生產(chǎn)與教學育人相結合,重拾傳統(tǒng)文科擅長的啟蒙與批判,聚焦于中國的本土化實踐,通過研究我國的自身特質與社會關切,促進人與社會的聯(lián)結,發(fā)揮大學教育的教化功能。
在幫助建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有效聯(lián)結方面,傳播至關重要。但是進入新媒體時代以后,我國傳播研究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仍習慣基于原有的傳播研究思維定式,尤其是“大眾傳播”研究思維定式研究新媒體。這種思維定式表現(xiàn)在專業(yè)設置上,就是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仍開設在新聞傳播學院中,新媒體還是被作為繼報紙、廣播、電視后的一個并列類型。而這種看法忽略了新媒體技術的發(fā)展對人類社會產(chǎn)生的強烈沖擊,以及對自現(xiàn)代大眾傳媒時代以來形成的傳播理論與范式的顛覆:
第一,盡管“新媒體”一詞被廣泛使用,但是至今尚未形成關于“新媒體”的標準且統(tǒng)一的定義。學者彭蘭指出,“新媒體”一詞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有不同的含義,它既可以指傳播介質層面,也可以指傳播形式與手段層面,還可以指傳播機構與平臺。“新媒體”很難被定義,并非是一個嚴謹?shù)母拍睿鼉A向于一種通行的說法,不能簡單粗暴地將其和報紙、廣播、電視并列。
第二,“新媒體”這種說法在字面上容易讓人誤解,似乎“新媒體”與傳統(tǒng)媒體之間的差異就是時間的新舊和先后上,卻忽視了新媒體本身對傳播的顛覆。傳統(tǒng)的大眾傳播研究是一種以傳播符號為主的研究,忽略了媒介的物質性及人的身體對傳播的影響。而新媒體技術的發(fā)展,特別是虛擬現(xiàn)實(VR)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的運用以及5G 技術支持下“萬物皆媒”時代的來臨,人們需要能夠理性地理解和對待參與傳播的“物”以及人與機器、人與社會的關系。而這些新媒體傳播研究中的熱點卻是傳統(tǒng)大眾傳播研究視角的盲點。
對此,有學者呼吁借助新媒體時代的技術去蔽,開創(chuàng)“新傳播研究”,促使傳播研究的符號與物質再度匯合;讓“傳播”這個概念回歸到更廣泛、更一般的交往概念,既包括物、精神構成的人與非人的連接網(wǎng)絡,也包含了傳統(tǒng)的交通觀念;在這種觀念下,交通、物流、流行疾病等都能夠作為新傳播研究的對象。
基于此,“新文科”語境下的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需要生產(chǎn)幫助理解人與社會關系的新范式與新視角的知識,幫助學生建立與新媒體社會的有效聯(lián)結。同時,在新傳播研究觀念下,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要深化學科的交叉通融,擁抱其他學科,亦需要重新思考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二、再議交叉學科
學界一般認為,“新文科”一詞源于美國。2017年,美國施拉姆文理學院提出“新文科”概念,強調不同專業(yè)的學生打破學科界限進行交叉實踐與跨學科學習。
而當前我國的“新文科”則源于2018年。黨中央要求“高等教育要努力發(fā)展新工科、新醫(yī)科、新農(nóng)科、新文科”。2018 年 10 月,“六卓越一拔尖”計劃 2.0 中首次增加人文學科;2019年10月《教育部關于一流本科課程建設的實施意見》中強調“新文科”建設要“體現(xiàn)多學科思維融合、產(chǎn)業(yè)技術與學科理論融合、跨專業(yè)能力融合、多學科項目實踐融合”。加之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的“人文社會學科危機”,跨學科、文理交叉成為對新文科內涵與特征的主流解讀。就這個層面而言,“新文科”被視為對傳統(tǒng)人文社會科學的升級與超越。
結合“新文科”這一概念在美國和我國的起源不難發(fā)現(xiàn),跨學科與技術似乎成為催生“新文科”改革的兩個關鍵詞。但是這兩個詞與“新文科”之間仍存在需厘清之處。
其一,于美國而言,“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在1926年就出現(xiàn)了;我國亦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重視跨學科問題,《未來與發(fā)展》雜志1985年第1期發(fā)表了關于《跨學科學》的論文。因此,不能將“新文科”的特征僅局限在跨學科或學科交叉融合上。
其二,“交叉”這種說法容易引起“邊緣化”的歧義。人文與社會科學大類中的其他學科如哲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等也經(jīng)常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但這些學科都不是邊緣學科。交叉可以形容“新文科”的特點或者產(chǎn)生的新的研究領域,但不容易突出“新文科”的重要性。
其三,技術的發(fā)展與變革是促進“新文科”改革的重要背景與工具。我國的“新文科”建設高度重視技術要素。2018年,《關于提高高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yǎng)能力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yǎng)計劃2.0 的意見》一文中指出“全媒化”是第一培養(yǎng)目標。這要求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對內實現(xiàn)專業(yè)各門課程之間通融,對外與其他學科跨學科交叉,幫助學生建立包括技術適應、技術賦能、技術批判在內的技術思維。
在這一點上,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的發(fā)展與我國“新文科”建設產(chǎn)生積極的呼應。一方面,“新文科”改革的實踐與推廣離不開新媒體傳播;另一方面,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始終對技術,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區(qū)塊鏈、虛擬現(xiàn)實等技術保有高度的敏感和密切的聯(lián)系,“媒體”與“技術”不再僅僅是專業(yè)學習的特定概念,而是技術迭代的載體與社會變革的動力。
但是除了技術驅動,我國“新文科”建設還需考慮自身的社會情境,概括地講是新時代對“新文科”的要求。有學者認為我國“新文科”概念與新技術推動、新需求產(chǎn)生、新國情要求都有關。“新文科”建設是由國家和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系統(tǒng)性工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下,隨著中國的大國崛起,中國要在世界舞臺上傳遞中國聲音、凸顯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智慧和力量。
比較中美兩國關于“新文科”概念的闡釋,對中國語境下的“新文科”而言,技術不是外在的“新文科”改革的工具,而應成為內在要素。物聯(lián)網(wǎng)技術和5G 技術使得“萬物皆媒”的時代來臨。傳播不再是新聞與傳播學科的專屬,而是更廣泛的一般交往。對各領域融合產(chǎn)生的綜合性問題需要運用多元的研究視角和知識來探討。新聞與傳播學科不能簡單借鑒其他學科知識,而是需要從自身的視角去研究更廣泛的傳播問題。新聞傳播學擁抱其他學科時,其他學科也在走向新聞傳播學。
那么,再用交叉學科形容新聞傳播學科,尤其是其下屬的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稍顯不準確。對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的理解應從“交叉學科”向“平臺性學科”轉移。
三、平臺性學科
按前文所言,網(wǎng)絡與新媒體不應是學科交叉產(chǎn)生的邊緣專業(yè),而應有潛力成為平臺性學科,不僅吸收其他學科的優(yōu)秀成果,也能融入其他學科中,展現(xiàn)出較強的適應性。學者劉海龍認為,平臺性學科能為其他學科提供研究理論、假設和數(shù)據(jù),幫助其他學科借助平臺性學科的視角解決其自身的研究問題。
當前,網(wǎng)絡與新媒體作為平臺性學科需要思考的重點問題是,作為平臺能夠為其他學科提供什么樣的“基礎設施”。新媒體并非簡單地與傳統(tǒng)媒體并列,網(wǎng)絡與新媒體的發(fā)展使得新聞傳播業(yè)態(tài)以及傳播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變革。對新媒體的研究,在關注新媒體信息與符號傳播的同時,也需關注新媒體中的物質與人的流動。比如有學者對數(shù)字勞動的起源、發(fā)展作了詳細的梳理,還有的學者認為融媒體生產(chǎn)不只關乎媒介融合,更強調人的身體的感官重組與直覺再造。網(wǎng)絡與新媒體在向其他學科開放的過程中,亦不斷獲得新的知識。
傳播地理學的發(fā)展或可為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作為平臺性學科如何向其他學科提供能量這方面提供借鑒。
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地理學“文化轉向”與傳播學“空間轉向”相互碰撞,產(chǎn)生“媒介與傳播地理學”這一跨學科交叉領域,從多個方面挑戰(zhàn)了人們關于媒介和空間的傳統(tǒng)觀念,拓展了研究媒介和空間的思維與方法。大致地看,西方地理學共有四種研究媒介與傳播的主要路徑,分別是交通地理學、文化地理學、非表征地理學和虛擬地理學。19世紀,古典地理學的社會有機論思想為一百年后傳播學的產(chǎn)生打下了重要的思想根基。社會有機論認為郵政、報紙、電報等構成的信息傳播系統(tǒng)對人類社會而言就像人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一樣協(xié)調和控制各種資源。而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傳播”概念中“信息交流”和“物理交通”兩個內涵開始分野,傳播學轉向以符號內容為中心的研究,地理學則逐漸放棄信息傳播而主攻物理交通。直到20世紀90年代新文化地理學的興起,地理學家的研究目光才再度落回人類的現(xiàn)代都市生活,一系列有關文化地理的研究重新審視了媒介的作用,并以媒介為研究路徑分析地方與空間的意義生成。當前,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發(fā)展、賽博空間和網(wǎng)絡虛擬環(huán)境里的人類交往與社區(qū)體驗以及電子地圖的普及與發(fā)展,地理學的研究開始超越虛實界限。傳播地理學認為,如果將媒介放在現(xiàn)實的場景實踐中,則媒介與訊息不再涇渭分明。這對交叉學科的啟發(fā)在于:一般認為交叉學科只能在多個學科的邊緣做修補,而鮮有通過交叉向原學科的中心發(fā)起挑戰(zhàn)。跨學科的意義不僅是跨越原本存在較多差異、互相比較獨立的學科,更要在學科之間建立起關聯(lián)的網(wǎng)絡。不僅保持住原學科各自的特色,也努力促進學科內部的整合,不斷推動學科之間的交流與對話。這或應成為“平臺性學科”建設最重要的意義。
本文建議以“平臺性學科”認識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的課程設置、培養(yǎng)路徑、行政系別劃分等。學者黃旦在《試說“融媒體”:歷史的視角》一文中援引新媒體研究領域專家穆爾的話指出:新媒體還在發(fā)展,以傳統(tǒng)媒體為參考體系思考新媒體似有其必要性;但不應過多聚焦于研究二者的相似性上,而是要思考數(shù)字傳媒獨有的特征。
四、結語
隸屬于新聞與傳播學的網(wǎng)絡與新媒體是具有顯著新文科色彩的專業(yè)之一。自我國提出新文科建設以來,網(wǎng)絡與新媒體如何抓住新文科建設的機遇發(fā)展自身,已有大量的討論。本文未把網(wǎng)絡與新媒體在新文科建設背景下的專業(yè)課程設置、建設路徑作為重點討論對象,而是建議轉換思考該專業(yè)定位的思路。
結合新傳播研究,本文建議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不只是多學科交叉的邊緣匯聚,而是能夠形成新的中心。它不僅需要引入來自其他學科的知識與方法豐富自身,而且更有潛力成為平臺性學科,為其他學科提供養(yǎng)分,以幫助自身和其他學科共同發(fā)展。
網(wǎng)絡與新媒體專業(yè)可稱為新文科建設在微觀和中觀層面的一個實踐;而在宏觀層面,未來或可進一步思考的是,新文科的發(fā)展建設在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校發(fā)展建設中處于怎樣的位置。對新文科發(fā)展建設依托的中國情境,亦需要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