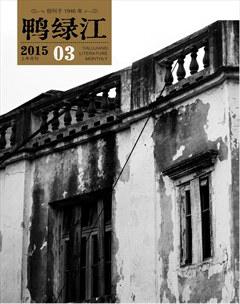五車間
朱日亮
五車間是462路汽車的終點站。這地方位于老城的郊區,除了五車間找不到一個醒目的標志物。五車間廠房高大,差不多有三四層樓高,所以462路汽車站名就把五車間用上了。
客車廠在城里,因為地方狹窄,又因要擴大規模,就在郊區建起了五車間。原打算全廠都搬到這邊來,后來下來個文件,不搬了,所以五車間和總廠不在一起。雖不在一起,五車間卻是廠子的龍頭老大。五車間是客車廠總裝車間,是客車廠最重要的車間。一輛車有上千上萬個零部件,進入五車間之前,它們都是散著的,是一個一個鐵疙瘩鐵片子。進了五車間,它們就合到一起了,變成一輛漂亮的大客車。當年客車廠生產的大客車,全國各地馬路上都見得到,有藍色的,黃色的,綠色的。東邊的鎮江徐州,南邊的廣州海南,西邊的成都烏魯木齊,北邊的佳木斯滿洲里,都跑著客車廠的大客車。那時,提起客車廠,沒有誰不知道。如果你說是五車間的,聽到的人會眼珠子發藍,恨不得立馬把閨女嫁給你。全國有名的國營大廠,哪個人不羨慕?只要說到五車間,就給人一種朝氣蓬勃的感覺,說的人精神,聽的人也精神。
客車廠全稱叫黎明客車廠。客車廠生產客車,這是一定的。如果你認定客車廠只能生產客車就大錯特錯了,老客車的人都知道,廠子還能生產軍車,就是那種軍用卡車。只要上面紅頭文件發下來,就會有一輛接一輛綠色的軍用卡車從五車間開出去,據說,連越南和朝鮮的大山里也跑著客車廠的軍用卡車呢。
現在,五車間已經不是一個車間了,它是一座巨大的空房子。不光五車間空掉了,墻外的家屬房也漸漸空掉了,只剩下王進山一個人。這一天,王進山坐在一根工字鋼上,像一條老狗一樣看著空曠的五車間。在王進山的眼中,車間里除了一部老掉牙的車床和埋在地面上的鋼軌之外什么也沒有。車間的窗子早就沒有玻璃,看著就像一個老嫗的眼睛;水泥地面斑斑駁駁,就像一幅一幅破碎的地圖。風從窗子刮進來,刮進幾片黃了邊的樹葉子。王進山揀起一片葉子放在嘴里咬著,這哪里還是五車間?分明就是一片廢墟。五車間沒了,說不定哪天,連這座空房子也沒了。現在,五車間屬于顯達房地產公司,十年前顯達公司就把五車間買下來了,不光買下了五車間,車間里的設備也一起買下來了。十多年了,顯達公司并沒在這兒蓋房子,就這么把五車間空著,空得周遭長滿了荒草,車間的屋頂上也長了草。
當年,五車間可是好大一片地方,車間里的設備頂呱呱。除了這座車間,外面還有一個籃球場,那是區里唯一的燈光球場,國家青年隊還在這里打過比賽呢,廠區還有一個露天的游泳池,現在,那個游泳池成了一個爛泥塘。
王進山進廠就在五車間當學徒。他當的是維修鉗工,那是一個讓人羨慕的工種。鉗工們屁股蛋子上吊著工具袋,袋子里面插著鉗子扳子螺絲刀,走起路來晃晃當當,那真是要多威風有多威風。王進山十五歲進廠,二十一歲就帶了徒弟。那天,主任把他叫到辦公室,指著兩個女的說,大王,新分來兩個徒工,你帶著她倆。這兩個徒工一個是高云,一個就是他的前妻春剛,那時當然還沒有前妻那一說,那時她倆還不到十六歲,兩個人都是頂花帶刺的黃花閨女。
女的?王進山沒正眼看那兩個女的,心里罵道,娘的,老子命不好。滿心不樂意地把兩個丫頭片子領進維修班。沒想到高云和春剛在維修班一干就是幾十年。
兩個小女子第二天上班時穿上了工作服,怪去了,那工作服就像為她倆定做的一樣。進了車間,幾百號人都看傻眼了,這不就是車間墻上的宣傳畫?宣傳畫上就有那么兩個女一男,雄赳赳氣昂昂的,她倆和畫上的女子一模一樣!
王進山也傻眼了,長到二十一歲,他就沒見過這么打眼的女孩子。客車廠二十六個車間,一萬八千多號人,女職工占了小一半,他就沒見過這等人才。不過王進山心里有小九九,好看不是真本事,好看多半是樣子貨,就像墻上的宣傳畫,誰也不能把畫揭下來當飯吃。
沒想到這兩個丫頭片子哪個都不是省油的燈。那個叫春剛的,本來已經考上市里的機械學校,可她硬生生沒去。她老爹是客車廠的,她早就想進廠子了,上了機械學校也未必能分到客車廠,有這樣的好機會她當然不能放過。另一個叫高云的,也是人托人才分過來的。高云在中學就是響當當的人物,是全市學生的頭,聽說小學時還給鄧小平獻過花呢。
兩個女子萬沒想到,剛進廠就分到五車間,那可是五車間啊。在五車間當鉗工,走到哪兒都是尖子,五車間的鉗工組,在全國技術比賽中拿過第一呢。她們認定老的就是好的,滿心跟定一個老師傅,學得一手鉗工的好武藝。都說車鉗鉚電焊,給塊金子也不換。五大工種里鉗工是一頂一的全能,五大工種里沒有鉗工干不了的,鉗工好比體操里面的全能,春剛和高云不知道,師父王進山雖然年輕,但他就是那個全能冠軍李小雙,不過這是后話。
有一次車間書記對王進山說,你這名字和一個將軍一樣,他也叫王近山。王進山說,少給我灌米湯,我哪里比得上人家,人家是將軍,我就一鉗工。話是這么說的,王進山可是狠狠自豪了一把,心里自傲著呢。跟將軍他是沒法比,但在五車間,在維修班,沒有誰他不敢比,客車廠里面訪一訪,有誰不知道五車間王進山?王進山是五車間的王,車間里那些鐵塊子鐵片子螺釘螺母鉗子扳子車床沖床銑床就是他的兵。
王進山是大個子,也不是太高,他是顯個那種人,車間里人都喊他大王。現在五車間的老人不叫他大王了,叫他老王,年輕的,叫他老王頭,更年輕的,干脆就不認識他。現在,王進山很少能看到五車間的人了,只要有紅白喜事他都去,只要見得到,火葬場他也要趕過去。
怕自己迷糊過去,王進山站起來,吐掉嘴里的樹葉,圍著五車間轉起來。往上看,五車間頭上是鋼灰色的天空,一大片云彩被風撕扯得支離破碎。往下看,蒿子又長高了,蒿草甚至伸進了窗子,蟈蟈在草叢里長一聲短一聲地叫,那叫聲本來挺好聽的,王進山卻聽得心煩,他把眼睛掠過那些蒿草。五車間的墻體是耐火磚砌的,上面有很長很長的標語,字體已經看不清了,但王進山還能念出來,就是閉著眼睛也能念出來。
職工們一起洗澡,一起打籃球,一起去食堂,一起會戰加夜班,一起打架。大客車一輛一輛從五車間開出去,幾十年的事情放電影一樣在眼前打轉。那時加班不加工資,頂好的是補幾斤糧票,工人們也不怎么計較。沒想到在一次會戰加班的夜里,王進山和一個女子擦出了火花。
夜里的五車間像一座輝煌的宮殿。
有一天,騷猴子來了,還拿來一瓶酒。騷猴子在五車間當了三十年車工,當年這家伙因為偷看女工洗澡,差點被廠子開除。那天喝著酒,騷猴子說,大王,你說我看見誰了?王進山說,誰啊?騷猴子說,你猜。王進山說,你都六十了,經見過的人成百上千,誰知道你說的是誰?騷猴子說,我看見高云了。王進山一陣心跳,拿杯子遮住臉說,她呀,她不是在沈陽么?騷猴子說,回來了,跟兒子過不到一塊兒,一個人回來了。王進山輕描淡寫地說,找個老頭不就得了,干嗎回來?騷猴子說,我也這么說呢,她要找好找,哎,你沒看見,高云現在還她娘的腰是腰,屁股是屁股,奶子還是翹的,說四十也有人信呢。王進山說,你個老猴子,又犯騷勁了。嘴上說騷猴子,心里卻是一陣騷動。騷猴子說,我倒是想犯,騷心有,騷勁沒有了,我問你,當年你是不是和她有一腿?王進山說,說實話?騷猴子說,當然說實話,我跟你就說實話。我偷看女工洗澡,差點被廠子開除。王進山說,你活該。騷猴子說,我不是看女工洗澡,我是看高云,看看還不行嗎?許你繞山放火,不許我屋子點燈?王進山說,還有臉說,你把燈點到人家女澡堂了。騷猴子說,說實話我恨死你了,我恨不得你讓大客車撞死,好事都讓他媽你霸著,五車間兩個大美人都他媽的喜歡你。現在我也恨你,恨你是恨你,我他娘的恨你還喜歡你。你技術好,我是車工,你車件比我車得還地道,不過你小子別得意,除了你,我騷猴子誰也不服。王進山說,老皇歷,別提了,喝酒。騷猴子說,老皇歷?我就樂意翻老皇歷,五車間那時多熱鬧,比現在電影明星還火,還熱鬧,操,那肉皮子,白,緊實,說,你和她有沒有一腿?
騷猴子總是說話跑題,跑題是跑題,最后卻是萬變不離其宗,那個宗就是女人。王進山明白騷猴子又犯騷勁了,也明白那“白”和“緊實”說的是誰,說就說吧,騷猴子也就是過過嘴癮,酒喝到這份上,王進山也憋不住了,他說,差一點。
真就差那么一點。那天,王進山把高云送到衛生所,醫生給高云打點滴。醫生說,車間里那么熱,女孩子又不能像你們男人那樣光膀子,小高是中暑了。
高云真中暑了,不過一瓶子點滴打進去,高云就醒了。見到王進山,她問,誰送我來的?王進山說,我。高云坐起來說,我要回家,你送我。大黑夜的,一個女孩子,中了暑又是他徒弟,王進山只好送高云回家。高云家里一個人也沒有,門剛關上,高云一下抱住王進山。
騷猴子問,上床了么?王進山說,沒上。騷猴子酸酸地說,到嘴的肉你沒吃?說死我也不信。王進山說,不信就不信。
還是那句話,就差那么一點了,讓高云緊緊抱住的王進山已經暈了頭了。一個女孩子這么樣抱住你,你還有什么不明白,還有什么可說的?高云身子熱得燙人,王進山也熱起來,身體上的所有零部件全都嗷嗷地鼓噪,他也緊緊地抱住高云,情勢已然勢不可擋了。就在那一刻,王進山看到了高云工作服上的工牌,15號,他想起,有一個人的工牌是16號,想起那個人,王進山放開了高云。
高云狠狠剜了一眼王進山,捂著臉跑進屋里。幾十年了,王進山總忘不了高云那一眼。
隔不幾天,王進山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手機一拿起來他就知道是誰了。他說,你是高云。高云說,我還沒說話,你咋知道是我?王進山說,聽喘氣就聽出來了。高云說,你出來吧。
高云在一家小館子里等著王進山。高云一點沒顯老,騷猴子眼睛花了,看女人卻是一點不花,王進山想起騷猴子那句話,眼前的女子果然腰是腰屁股是屁股,兩只奶子果然是翹著的。看著王進山坐下來,高云說,你沒刮胡子。王進山說,忘了刮。高云說,我才不信你忘了呢,早先會戰加夜班,你還把胡子刮得干干凈凈呢。王進山說,又不是會戰加夜班。高云說,下次來把胡子刮干凈,你就當是加夜班。
王進山說,去哪兒加班,做夢吧,你多久沒去五車間了?高云說,兩年了。王進山說,兩年沒去?你可真狠。高云說,不想去。王進山說,再不看你就看不著了。高云說,不想看。王進山說,沈陽可是大城市,在那兒過得咋樣?聽說你兒子在那兒有買賣?高云淡淡地說,開個網店,房子買了,車也有了,還是嚷嚷沒意思,你說,他們年輕輕的都沒意思,我有什么意思?
酒一沾,高云的臉紅了,眼睛也亮了,從那眼睛中,王進山又看到了他熟悉的浪勁兒,還有寂寞。他想,喝酒有壞處,也有好處,酒不做假人就不做假,比方現在,幾杯下去高云又成了以前的高云。他看著她說,跟兒子過不到一塊兒吧?高云說,也不是,我在沈陽一個熟人也沒有,悶死了。王進山說,悶?扭秧歌,跳舞,扭起來跳起來就不悶了,現在時興跳舞。高云說,我才不跳呢,讓那些騷老頭子摟著抱著,惡心死了。酒進肚,王進山說話也放肆起來,說,老牛吃嫩草,不讓老頭抱,讓小伙抱啊?高云在桌子下面踢他,瞪著一對桃眼說,煩人,又說,有臉說別人,你還抱過我呢。高云那一腳把他的情緒踢起來了,王進山也被高云帶入了港,有些神往地說,是抱過,那天會戰加夜班你暈倒了,我抱你去的衛生所。高云說,你還記得衛生所么?王進山說,那還能忘?咱廠子衛生所是全市最好的衛生所。高云說,現在我也不相信你抱過我,我覺得那像做夢。忘沒忘,春剛懷你兒子就是在衛生所查出來的,全市第一臺B超呢。王進山說,別提B超,也別提他。高云說,為什么不提?你說他傻?傻也是兒子,說不定哪天他就會回來呢。王進山說,屁,回來?十多年了,五車間賣給顯達十多年了。高云說,顯達是炒地呢,要不是賣給顯達,黎明不會犯病,不犯病他就不會走。王進山說,和那有屁關系?高云說,有關系,我說有關系就有關系,黎明是在五車間長大的。看王進山攏起眉頭,高云突然笑起來,笑得滿臉飛紅。王進山問她,你笑什么?高云說,聽說有個女人五十歲還生了孩子。王進山說,怎么扯到生孩子了,你信那鬼話?高云說,鬼話?電視都播了,那女人五十一了。王進山說,電視也說鬼話。高云突然生氣了,站起來說,這鬼話那鬼話,我看你就是個鬼話。
王進山看著高云,明白她用的是激將法,但他還是繞山繞水地說,真忘了,你也奔五十了。
把話說到這份上,這家伙還在繞,高云忽閃著一雙桃子眼,對王進山說,大王,我不跟你講廢話,你要是不煩我,我今晚就跟你去五車間。王進山被高云逼得發慌,岔開話題說,顯達公司說在五車間蓋樓,十多年也不蓋,一大片地就那么空著。高云白他一眼,說,你盼它拆掉啊?王進山悶悶地說,有一個單口相聲,說的是夜里樓上把一只鞋扔在地板上,樓下的人等啊等,等他扔另一只,樓上就是不扔。高云說,你就是樓下那個人,我知道你,你不是盼他扔,你是怕他扔。王進山說,也不是,鞋扔了,也就死心了。
高云說,別啰嗦你的五車間,說句痛快話,你煩我不?王進山臉紅到脖子上,悶聲悶氣地說,我沒說煩你。
他怎么會煩她呢,他從來就沒煩過她,要不是春剛,他說不定會娶她。不到三年,高云和春剛腳跟腳出了徒,那當然是名師出高徒,她們也像他一樣屁股上掛著鉗子扳子螺絲刀,像他那樣晃晃當當走路,像他那樣解決車間和廠里的疑難雜癥。高云本來有機會去長春一汽,不知道為什么她沒去,結婚不到兩年她就離了,誰也不知道她為什么離婚,不知道她為什么喜歡帶著孩子自己過。這么多年,五車間流傳很多涉及她的花花事,但是誰也沒見過那花花事里的男人。
高云放下酒杯,說,走,跟我去打車。
夜晚的五車間不再燈火輝煌,看著就像一只受傷的野獸,黑洞洞的窗子就像野獸的眼睛。兩人一腳高一腳低地圍著車間繞了兩圈,高云問他,總裝設備和機加設備怎么都沒了?王進山說,讓他們賣了。高云說,不看了,難受。王進山說,告訴你,地上的五車間是沒了,地下還有一個五車間,五車間地下的管道能繞全城十圈。高云說,一百圈也得賣掉。王進山索然地說,不想看你就回去。高云由悲轉喜地說,你的意思是不讓我回去?王進山盯著她不吭聲,高云看到了一口白牙。
在床上,高云擁著王進山說,我是不是做夢?王進山說,做夢?人要總是在夢里就好了。高云說,你真不嫌我老啊?我五十了。王進山說,要說老,我比你還老。高云說,你是男人。兩人再不說話,話都用行動替代了。
高云把一條光腿搭在王進山身上,意猶未盡地說,大王,我城里有樓,兩小室,你若是同意就搬過來。王進山想也不想地說,不去,想搬你搬過來。高云說,爛草叢,爛泥坑,我搬過來,你讓我喂蚊子啊?王進山說,怕蚊子有驅蚊香,車間院子里艾蒿比人高,那東西熏蚊子最好用了,比驅蚊香還頂用。高云說,蚊子咬也罷了,這里不能上網。王進山說,上網干什么,找老頭啊?五車間傳你不少花花事,你有沒有他們說的花花事啊?高云說,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我倒寧愿有,死了也不冤枉。姓王的,我過年就五十了,走到這一步你還拿捏我。王進山說,我真不是拿捏你,我還要看著這房子呢。高云騰地站起來,一個字一個字地蹦著說,王進山,你就死在五車間吧。
又過了一年,五車間還是沒拆,王進山還在這里看著這座空房子。拆是沒拆,顯達公司在這里立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顯達房地產開發公司工地。看樣子五車間還是要拆。一個雨天,騷猴子又來了,帶了一瓶白酒兩只豬腳。喝酒時,騷猴子說,娘的,一看那狗牌子老子一點胃口沒有。王進山明白他說的是顯達那牌子,說,沒胃口你喝酒。騷猴子說,五車間要是拆了,462路站點還叫五車間么?王進山說,不叫五車間叫什么?騷猴子說,保不定就不叫五車間了。王進山說,只定叫五車間,叫別的,誰能找得到啊?騷猴子說,你又犟,犟一輩子了還犟。王進山悶頭喝酒,再不說話。騷猴子說,想起以前的五車間,血都往上涌,你說怪不,我現在總想以前的事,越往前的事,越他娘的記得清楚,眼前的事卻一點不記得。你說,這日子是過好了還是沒過好?廠子黃了,白米飯也吃膩了,樓高了,人也懶了,我他娘的也越來越迷糊了。
騷猴子比王進山晚幾年進廠,年紀卻比他大幾歲。王進山看著騷猴子,人沒回憶就成傻子了,不光騷猴子,人都活在記憶里,他王進山也一樣。就這么一年,騷猴子老了,騷猴子成了真正的老頭子了,原來那股騷勁剩得差不多了。
高云再沒來找他,把手機也關掉了。騷猴子說,高云又去沈陽了,兒子在沈陽給她找了個老伴,那老頭六十五,比高云大十五歲,是金杯集團的高工,退休還開五千多呢。這女人找來找去,還是找個造汽車的。高云生了個鬼精兒子,給老媽找老伴,輕松把老媽蹬了。王進山說,精個屁,老媽老媽,老媽就是老媽子,我看他不精,他傻。
那天夜黑,五車間突然來了兩個人,他們是開著一部帶掛卡車來的。開車那人給王進山遞了一支煙,說,老哥,我是騷猴子的表侄,有個事和你老商量。王進山說,你說你說。那人說,顯達公司就要扒房子了,明年就要在五車間起樓。王進山聽出那人話里還有話,說,有話你就說吧。那人說,這房子里的破爛顯達肯定不要,地里埋著的破鐵軌,還有那爛車床,你老合幾個錢小侄我拉走。王進山說,合幾個錢?那人說,憑你說。王進山說,一分錢不要。那人驚喜地說,那我拉走了。王進山說,那可不行,這地方一塊磚你也不能動。那人說,這里早就不是五車間了,顯達不會要這些爛鐵塊子,他們要的是地皮。王進山說,我說不能動就不能動。那人說,你老真是死心眼,你就是一看堆的,管那么多干嗎。另一個人說,顯達給你多少錢?一千還是兩千?你說個數。說話時那人掏出一打錢,都是一百一張的新票。王進山斜眼看著那打錢,那兩個人也不錯眼珠地看著他。王進山說,我說過,一分錢不要。那兩個人明白碰上犟眼子了,后說話的那人笑笑,把錢收起來,說,那算了,不麻煩你了。
兩個家伙走后,王進山憤憤地罵起來,騷猴子,打起五車間主意了。又給騷猴子打電話,騷猴子說,他們騙你呢,外甥我有,我哪有什么侄子,我從出生就是獨哥一個。轉轉眼珠子,又說,五車間誰不知道?黃攤子了也人人都知道,你也是犟眼子,破鐵塊子,賣也就賣了,當酒錢了,你還當那是你的五車間啊,不是了,那地方現在是顯達公司。王進山啪地放下電話,心里說,顯達就是個屁,老子寧可不喝酒!
王進山一萬個沒想到,高云和春剛都喜歡他。先前她們還有些看不起他,后來她們發現,廠子里出了什么疑難雜癥都找王進山,王進山就像專治疑難雜癥的老郎中。這家伙不光技術好,干起活也特瀟灑,摔摔打打的,叼著煙卷,眼睛瞇瞇著,心不在焉似的,手里的活卻是又快又好。王進山籃球也打得棒,五車間籃球隊從來都是全廠的冠軍。
滿徒之后,高云和春剛都留在了維修班。這兩個女子,一個蔫,一個浪。一個總是甜甜地喊他師傅,另一個很少喊他,卻是一步不離地跟著他,他說,鉗子,她就遞他鉗子,他說扳手,她就遞他扳手。這另一個就是春剛。和高云比起來,春剛就是一個悶屁,和她待上一整天,也聽不見她說一句話。
王進山還是讓春剛悶住了。春剛平時不聲不響,那年春節加班卻放了一個響屁。午夜時食堂給大家加餐,書記說,你們是不是五車間的,就這么悶著頭過年啊?騷猴子說,書記帶頭,你給大伙唱一段。書記說,我嗓子比脖子還粗,我給你們找一個人替我唱,春剛啊,你來唱一段。書記這么一說,工人們都起哄,書記是亂點鴛鴦譜,大伙偏就喜歡這樣亂點鴛鴦譜,誰叫人家長得好技術也好呢。想不到起哄聲中,春剛站起來了,只聽她唱道:
小路的李子樹刮破了裙腳,
姑娘手舞足蹈往家跑。
過了石橋鋤頭掉在河里她也不知道,
只是一個勁地往家跑,
姑娘的心事誰也猜不著。
這女子唱的是誰?是她自己嗎?看她那亮晶晶的眼珠子,那紅撲撲的臉蛋子,她是唱她自己。春剛的嗓子不好,還有一點跑調,可她這么一唱,把王進山唱傻了,也唱明白了,穿著16號工裝的春剛,在王進山眼里一下子變成了女神。
和春剛結婚是在“五一”,高云沒來,騷猴子說她去沈陽了。不過新房卻是高云幫著收拾的,新房里掛滿王進山和春剛的獎狀,那幅結婚的大照片,也是高云逼著他倆照的。那天工人們都來鬧洞房,騷猴子拉住王進山說,大王,你小子喜上加喜啊,五一節,入洞房,好事都讓你占了,說,你是不是五車間的?王進山說,廢話。騷猴子說,五車間的人都是狠家伙,夜里你猛勁干,干得狠生小子,生不出小子你就不是五車間的。
不用王進山發狠,春剛比他還狠,夜里一上床,春剛的兩條白腿就把王進山箍住了。從此以后,白天,王進山是春剛的師傅,夜里師傅成了丈夫,只要到了床上,春剛的兩條白腿就會箍上來。怪不得白天話少,這女子把勁都留在晚上了,她是人蔫心不蔫啊。王進山高興春剛這么箍著他,高興是高興,時不時地他會想起一個人,那人是高云。高云和他在一起會是什么樣,也像春剛這樣拿腿箍著他么?想到高云,王進山會狠狠罵自己:王進山,你娘的騎著馬還找馬,你就是一牲口。
五車間墻外,廠子蓋了幾趟平房給職工當宿舍,撥了一間給王進山和春剛,兒子就是在平房里出生的,現在,平房里的住戶都搬走了,沒有住戶,電話線網線有線電視都給掐了。
干得狠果然生小子,而且是當年媳婦當年孩。王進山給兒子起名叫黎明,和廠子同名,那時候職工們都這么給孩子起名,什么李建設,王衛星,劉躍進啦。黎明九歲還不會說話,走路也東倒西歪的。衛生所查不出毛病,市里的醫院也查不出毛病,高云說,去沈陽查,我表哥在中國醫大。廠子給王進山派了一輛吉普車,王進山抱著黎明,春剛和高云跟著去了沈陽。診斷很快就做出來了,黎明是智障,醫生說,九歲的黎明只有一歲的智商。
春剛哭成了淚人,她哭,高云也跟著哭。
黎明睜開眼睛看到的就是五車間,長到十七歲沒離開過五車間。五車間的院子是黎明的天堂,書記特許一條,小黎明可以在五車間院子里玩。五車間的工人們都認識黎明,黎明也認得五車間所有的職工。黎明不會說話會笑,誰喊他的名字他都笑。騷猴子和鉗工班的人給黎明焊了一輛三輪車,黎明騎不了兩輪的自行車,只要出屋子黎明就會騎著三輪車去五車間,黎明不光是王進山的兒子,黎明也是五車間的兒子。
騷猴子又來了,一照面就說,想不到我還真有一個八竿子打不到的侄子,這包玉溪煙就是他孝敬我的。說著話,把玉溪煙撕開,扔一支給王進山。王進山說,那天來的就是他吧?騷猴子說,不是他,是他朋友,他讓我捎話給你。王進山說,什么話?騷猴子說,五車間那些破爛讓他拉走,他打一萬塊錢給你。侄子答應騷猴子,事成之后,另外打給他兩千塊。兩千是個什么概念?可以給兒子交半年社保了,還能余下點煙酒錢。
騷猴子說,我侄子不敢騙我,你同意,錢先打你,一萬塊啊,有這一萬塊,滿天下找黎明也夠你用了。王進山聽得一怔,心也咚咚跳起來,騷猴子知道他的痛處,騷猴子專捅王進山的痛處。
黎明不到十六歲時春剛得了胃病,一年以后,黎明失蹤了,春剛的胃病成了胃癌。
騷猴子走前放下一句話,成不成你都給我個電話。如果這時候高云在就好了,王進山愿意和高云商量這件事,普天之下沒有怕錢咬手的,一萬塊,的確不少了,一萬塊到手他就去找黎明。五車間就在他眼皮底下,這座空房子他說了算,顯達公司要的是五車間的地皮,他們不要五車間,那些爛磚塊子爛鐵塊子爛車床都不要,現在,那些爛東西屬于王進山,只要他開口。那幫人就等著他開口。
五車間歸顯達公司那天,公司一個副總找到王進山說,老王,你是老王吧,我們需要一個看院子的人,你給我們看院子吧,一個月給你開一千塊。王進山說,我還沒到退休年齡,為什么讓我看院子?那個副總說,不看院子,你就回家。回家,回家不就是退休么?若是回家他和五車間就一點瓜葛也沒有了。王進山問,這院子要閑起來么,不生產汽車啊?副總說,我們不生產汽車,我們什么也不生產,我們只管蓋房子,這里要蓋高層。
王進山沒回家,他成了五車間的更夫。
騷猴子等了一個月也沒接到王進山的電話。那天,等不及的騷猴子把電話打給王進山,他打了一天,王進山手機一直是忙音。騷猴子氣得摔掉手機,狠狠罵道,王進山你個犟驢,你就是個犟驢。
王進山沒騷猴子說的那么犟,可是他就是打不了那個電話,把騷猴子電話忘記就好了。怪了去,他的記憶越來越差,腦子里卻忘不了騷猴子的手機號,那一串號碼像蚊子一樣在他腦子里嗡嗡亂飛。
尋找黎明的傳單貼遍了大半個東北,黎明還沒找到。有一天,城郊的一條小河里發現了一具死尸。王進山扶著春剛跌跌撞撞趕了過去,看到那具尸體,他腿一軟,一下子跪了下去。那人眼睛都爛沒了,只剩兩個黑窟窿。但那個人不是黎明,警察很快做出結論,根據骨齡判斷,那是一具老人的尸體。
王進山明白,黎明不會回來了,黎明一定死在了他鄉,這年頭一個智障活得下來么?
那具尸首讓春剛魔怔了,她認定尸首就是黎明,她說,頭沖著五車間,黎明是想回家。自那以后,廠子給她辦了提前退休,她從來不出屋子,成年累月穿著那件16號工作服,胳膊套著套袖,手上戴著白線手套,就像上班一樣。再后來,她死了。
自從當了五車間的更夫,王進山不再回家,對他而言,家就是五車間,五車間就是家,睡到哪兒他都是一個人。每天他都摟著一條木棒睡覺,這一晚,王進山把木棒扔掉了,他在心里說,五車間跟我有什么關系,一毛錢的關系也沒有,偷吧,搶吧,賣吧,老子不管了,老子睡覺。蒙蒙朧朧中他做了個夢,夢見黎明回來了,可是黎明找不到五車間了,五車間被大卸八塊,夷為平地了,王進山一下嚇醒了,睜眼一看漆黑一團,他被人蒙住眼睛,手和腳也被捆住了。他想,我得罪誰了?隨即他聽到汽車馬達聲,還聽到車間里傳來叮叮當當的響聲。王進山明白,有人來偷五車間了。
有人來偷五車間了。手和腳動不了,身子還能動,王進山像魚一樣一打挺坐起來,他拿牙咬繩子,嘴被他咬出了血,繩子終于讓他咬斷了。站起來的時候,他差一點跌倒,但他沒忘順手抄起那條木棒。他悄悄躲在一個角落,眼前的一幕讓他呆住了——那臺車床已經被裝到卡車里了,十幾個人正在挖地上的鐵軌,鐵軌痛得吱吱呀呀亂叫。血一下涌進了王進山腦袋。
他拎著棒子走過去,沖著那幫人吼道,誰讓你們來的,都給我住手。
先頭,那幫人驚呆了,后來發現就他一個人,就把他圍起來,圍是圍起來,沒有誰真敢下手,這邊一個,那邊一伙,兩邊都僵著,其實他們都是帶了家伙的,鍬鎬撬杠都在手里攥著呢,那都是致命的鐵家伙。領頭的正是那天開車的人。他一看這樣不行,這么僵下去事情就泡湯了,沖上去就是一棒子,他一下手,就都下了手。王進山只覺得被冰涼冰涼的什么糊住了眼睛,再后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幫人看著打死了人,一個一個跳上車跑了。
在沈陽,金杯那個退休高工約高云第二次見面,老工程師花白頭發梳得一絲不亂,他對高云印象不錯,這女人真是個女人。話沒說一句,高云的手機響了,電話是騷猴子打來的,他說,高云哪,你快回來吧,王進山出事了。
醫院是區里的醫院,區醫院收費比市醫院便宜。
天亮時,王進山被蟈蟈叫醒了,摸了摸頭,他摸到一手黏糊糊的東西,眼睛看不到,心里明白那是血,也明白他還沒死。手機還在身邊,他掙扎著打了120,只說了“五車間”就又死過去了。
現在,王進山躺在四人一室的病床上,滿腦袋纏著繃帶,腿上也打了石膏,他左腿折了。他睜開眼睛就看到高云。王進山說,你怎么來了?高云說,廢話,我怎么就不能來?高云打開一聽罐頭,喂他吃桃子。王進山愛吃桃子。高云說,顯達公司送來五百塊錢,還讓你留著醫藥費票子,公司給報銷,我把票子替你收好了。又說,現在給錢,以前是給獎狀,以前,發你一張獎狀你就不知道姓啥了。王進山說,以前的人都傻。高云說,一個傻,兩個傻,都傻?王進山說,別說那些了,我問你,錢是誰送來的?高云說,騷猴子,騷猴子報案了,警察抓走了他侄子,顯達公司也是騷猴子找來的。王進山說,你怎么知道的?高云說,騷猴子悔得想撞墻,他不敢見你,給我打的電話,他侄子是顯達公司的保管。王進山說,到處都是內鬼啊。高云說,你是真犟啊,命值錢還是那些破爛值錢?又不是你家的,你管他內鬼外鬼?
王進山說,不管了,管也管不了,你不是找老頭了么?高云說,幫我拿主意啊?正想聽聽你的意見呢,說吧,你啥意見?王進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想嫁你就嫁。高云點了他一下,說,嫁你個腿。王進山說,我現在可真就剩一條腿了。
王進山從醫院回來那天,顯達那個副總又來了,他對王進山說,過幾天我派鏟車來這里平地,然后挖地基蓋房子。我看你這人挺踏實,你若是同意,你接著看工地,月薪給你漲一千,加上先前那一千你就開兩千了。
王進山說,鏟車來,我就不干了。副總說,為什么不干,你怕錢咬手啊?王進山說,這幾天我還干,還是那話,鏟車來我就不干了,你另外找人。副總奇怪地看著王進山,王進山明白他是啥意思,他的意思是王進山不識抬舉。
隔不幾天,幾輛大鏟車開進五車間,幾個司機跳下來圍著五車間轉了一圈,踢踢這兒,踢踢那兒,又跳上車開走了。王進山明白,五車間這樣的耐火磚,一般的鏟車鏟不動,這種耐火磚得用炸藥崩,一般的炸藥還不行,得用強力炸藥。
那幾天王進山一直胃痛,腿也痛。那天早晨他拄著木棍出來曬太陽,聽說曬太陽補鐵補鈣。從462路站點走過來一個人,那人搖搖晃晃向五車間走過來。他覺得那人眼熟。王進山拿手遮著眼睛問自己,這是誰啊?很少有人來五車間了。
那人走到他跟前突然站住了。
是黎明。
王進山腦袋轟一下子炸了。
黎明是靠記憶找回來的,他先是想起了五車間,他對民政局的人比畫著說,五車間有那么高,他拿眼前一幢四層的高樓比畫著,他還做出游泳的姿勢,意思是那地方有個游泳池。接下來他告訴他們,那地方生產大客車,他指著馬路上的公汽比畫。他又告訴他們,那地方是汽車站點。想到五車間,想到大客車,黎明的記憶一下子復蘇了,他還在五車間放過風箏呢,五車間外面有好大一塊空地,最后他竟然神奇地寫了一組數字462,黎明就這么一點一點地找回了五車間。
黎明變了,他不再是小伙子模樣,胡子老長,頭發亂得像團草,身上是一處一處的傷,有的傷還青著,有的傷結了痂,痂上又結了疤。黎明還是不會說話,但他會比畫,只要他比畫,王進山一下子就明白。問他這么多年是怎么過來的,他卻不會比畫。
黎明穿一套破爛工裝,看著就像一個剛剛干完活的車間工人。
顯達公司很快拉來一車強力炸藥,一整天,他們圍著五車間打眼裝藥。他們走到哪兒,王進山像頭瘸狼一樣跟到哪兒,他想,炸吧,老子就當這是在做夢,要炸你炸,炸沒了,我還有黎明。
黎明搖搖擺擺地跟著他,也像狼一樣盯著打眼裝藥那些人。
騷猴子最后一次來,看見王進山,啪啪掄了自個兩記耳光。王進山說,你這是干啥?騷猴子說,我他媽的不是人,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要不是我,你折不了這條腿。王進山罵道,你他娘的哪壺不開提哪壺。從小賣店買了兩袋散裝白,喝酒的時候,騷猴子看著黎明光喝酒不說話。王進山說,你就來這兒喝悶酒啊?騷猴子說,大王,黎明是不是你兒子?王進山說,當然是。騷猴子說,你有幾個兒子?王進山說,廢話。騷猴子嘆了一口氣,說,你還知道你就這么一個兒子啊?你這個人,只為你自個兒考慮,從來不為黎明考慮。
王進山氣惱地說,來這兒說混話,我怎么不為黎明考慮啦?騷猴子說,黎明二十幾啦,二十七二十八了?王進山說,二十八虛歲。騷猴子一拍桌子,說,你還知道黎明二十八了,明白嗎,你和你兒子缺個女人!王進山腦袋一下子大了。騷猴子又說,五車間眼看就沒了,你還守個什么勁兒?趁這機會,把五車間那些沒挖出來的爛鐵塊子折騰出去,去鄉下給黎明找個閨女,也算你當了一回老子,人家高云也等著你呢。
眼前的騷猴子越來越模糊,看著不像騷猴子,像一團霧,黎明卻是越來越清晰,王進山看得清兒子那硬硬的胡茬兒,黎明二十八了,黎明可不是二十八了?
不光騷猴子,第二天高云從沈陽打來電話,她說,王進山,你到底是啥意思?王進山想,高云是要他口供呢,忽地想起騷猴子缺個女人那句話,答說,你不是又去沈陽了么?問我啥意思,啥意思你知道。高云說,我不知道。王進山心說,我真就等著你呢,我碰上了難事等你商量呢。嘴上卻硬氣地說,你不就是要口供么,老子又沒去沈陽,別看折了一條腿,人還在這兒戳著呢。
高云罵道,屁口供,你等著,回去我打折你那條腿。
責任編輯 ?李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