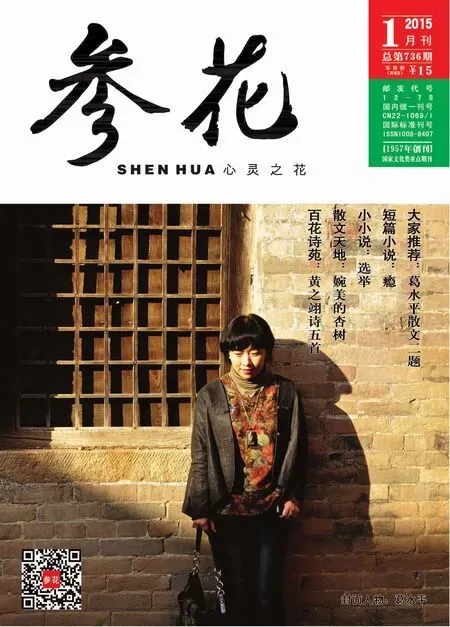凄絕南朝第一僧
◎周春華
凄絕南朝第一僧
◎周春華
世人太過于希求生命的長度,而忽略了生命的亮度。即使年逾百歲,倘若默默無聞,終歸是與草木同朽而已;如果能夠在短暫的生命中,涂抹出多姿多采的色彩,則一刻何當不就是永恒呢!蘇曼殊在短短的三十五個寒署中,仿佛就像一顆璀璨的慧星,劃過幽暗的夜空,發出絢麗的光芒,令人為之目眩神移,歌詠贊嘆。而他出神入化的天才智慧、憂傷國時的志士抱負、放蕩不羈的浪子行徑與返璞歸真的僧人意念,使他成為一個多才多藝、豪氣干云、為所欲為、逃避現實的奇人怪僧。

蘇曼殊(1884—1918)
蘇曼殊,原名戩,字子穀,小字三郎,后更名元瑛,改字子谷。“曼殊”一詞源自佛經,原本菩薩名,即文殊,常侍釋如來之左,而侍智慧。蘇曼殊出家后就以“曼殊”作為了自己的法號。
1884年9月28日,曼殊出生在日本橫濱。父親蘇朝英原籍廣東中山,是個旅日華僑,是時在橫濱英商萬隆茶行做買辦,但是母親是誰至今一直未有定論。曼殊從小就體弱多病,備受家人歧視與虐待。1892年,父親生意失敗,回到家鄉。1895年,為了生計,曼殊就隨化緣和尚贊初法師在六榕寺出家,為“驅烏沙彌”。后因犯佛門戒律,被逐出寺院。1898年,他跟隨表兄林紫垣東渡日本,求學于橫濱,入華僑主辦的大同學校。期間曼殊戀愛受挫,不堪打擊,回到廣州白云山蒲澗寺當了“門徒僧”。但是不出三月,無法忍受苦行僧的生活又還了俗。很快他又回到了橫濱大同學校學習,后考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
1903年,曼殊轉入成城學校研究學習軍事,并參加了革命團體青年會,投入到了革命救國的行列。曼殊的革命行為,遭到了林紫垣表兄的反對,斷其經濟援助。曼殊生活無著,只得輟學回國。在國內,曼殊親歷“蘇報案”的發生,加之其個性孤僻,痛感身世有難言之隱,選擇了逃避,決意斬斷塵網,出家為僧。于是又回到廣東惠州慧龍寺出家,后在海云寺修禪受戒。最終因他仍是奈不住“青燈古佛、芒鞋破缽”之苦,逃回了香港。此后他往返于蘇州、上海、長沙、南洋、香港、日本、杭州、南京等地,從事寫作、辦報、繪畫、教書、游學等活動,編織出奇特浪漫、傷感悱惻的人生。
曼殊的確是一個天生的才人,過目成誦的老生常談,用在他身上似乎特別的恰如其分。他并沒有花費太大的工夫,便能盡得中華文字的瑰奇與精妙;更像是走馬觀花似的匆匆一過,亦能擷英拈蕊般的獲取“英、法、日、梵”文的精髓;他在文學、藝術、哲學、佛學上也有精湛的造詣,已足超越古人,杰出當世的。
曼殊很早就與柳亞子、章炳麟等人交游,后經柳亞子推薦加入了南社。

蘇曼殊南社入社書
曼殊的翻譯、詩作、小說、繪畫等,都有極高的成就,特殊的經歷形成了他獨特的創作風格。他集壯懷激烈與放蕩不拘于一身,既出家,也隨時還俗,在清末民初的文藝領域中,成為一個“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頂尖人物,是“南社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奇才怪杰。
早期的蘇曼殊,思想比較激進,屬于辛亥革命時期首先覺醒的那一部分知識分子。他積極鼓吹以排滿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相當突出的。他翻譯拜倫的《哀希臘》和印度小說《娑羅海濱遁跡記》,其用意就是以希臘和印度滅亡的歷史教訓,喚醒國人,起來推翻滿清統治。“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別人的祖宗為祖宗”的喪失國格人格的無恥行為,他深惡痛絕,滿懷悲憤地說:“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嗚呼廣東人》)表現了他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嶺海幽光錄》中他極力頌揚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明末愛國將領的鄭成功,客死他鄉的朱舜水等,目的都是為了喚起人民的民族感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就是革命,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具體表現。
曼殊在日本參加“抗俄義勇隊”的革命組織時,寫下了《以詩并畫留別湯國頓二首》:“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海天龍戰血玄黃,披發長歌覽大荒。易水簫簫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詩句中反映了他強烈的反清情緒,以及蒼勁悲壯的愛國熱情。辛亥革命的失敗,給曼殊以極大的刺激,思想陷入了苦悶彷徨之中,流露出看破紅塵,逃避現實的頹廢感傷的情緒。此時他多有抒寫個人身世之感,抒發男女情愛的詩篇,其中《本事詩》最突出,“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等詩句表現詩人凄涼孤獨的心境,折射出欲愛而不能的復雜心情。《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詩中有云:“契闊死生君莫問,行云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詩人把內心的郁悶,孤苦的心情,淋漓盡致地表露了出來。曼殊是南社的重要詩人,以寫清逸的抒情小詩見長,他的詩在當時和后世都產生過一定影響。現在收集到他的詩作只有一百余首,絕大多數是七言絕句,而言情篇又占十分之九。曼殊的詩作無論哪一類題材,格調基本是低沉的,以纖麗綿眇的風格,表現幽怨凄惋的感情,在藝術上可以說是受李商隱和龔自珍的影響較多。曼殊意欲通過幽悠哀怨的情調,抒發其胸中的積郁,打動讀者的肺腑。所以,章士釗說他“小小詩篇萬匯情”,高天梅說他“二十八字含馀音”,良非虛語。
曼殊的小說創作大多采用第一人稱口吻描敘的記體形式,這是最適合他的文學個性的表現手法。因為其常痛感自己身世的坎坷孤零,曾寫下《斷鴻零雁記》《繹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等多部小說,這些小說在當時是與鴛鴦蝴蝶派的風格一致的,也開了近現代浪漫主義小說的先河。曼殊大凡接觸到婚姻自由的主題作品,都充滿濃厚的感傷,男女纏綿悱惻終以悲劇告終的愛情經歷,構成了曼殊的小說對舊世界批判的一個重要部分。其次,部分記體小說的主人公或為三戒俱足、袈裟披身者,或經歷磨難,終皈佛門者。但他們注定不能成正果,在佛俗之間徘徊彷徨,既信佛理,又不忘俗情。構成了曼殊的小說對世事無常表現出的無可奈何以及皈依佛門后又無法忘卻世俗情愛的矛盾心理的特點。像長篇小說《斷鴻零雁記》,她的影響是最大的,也是多部小說中寫得最好的,其中某些情節有著曼殊本人生活的影子。男主人公三郎,家道衰微。其未婚妻雪梅被繼母迫嫁富室,三郎憤而為僧。后來,三郎東赴日本尋找生母,與姨姐靜子相遇。三郎之母屬意靜子,三郎對靜子也不無戀戀之情,但終因皈依佛法,割斷情絲,潛逃回國。其時,雪梅已絕食而死。本以為是幸福甜蜜的戀情到后來卻以悲劇而告終,這是一段多么纏綿悱惻、凄婉感人的經歷啊!
曼殊的繪畫堪稱一絕,把中國畫法、西洋畫法與東洋畫法熔于一爐,而又能不為任何成法所拘泥,以其胸中空靈,目中無物的秉性,加上卓而不群,遺世獨立的精神,故而下筆落紙無不清秀典雅,疏落有致,而風格迥異,意境深遠,處處都表現出他淡泊的人生和幽雅的態度。曼殊生性酷愛美術,幾乎是無師自通,有人說他的繪畫風格是融合了東洋畫風的淡雅與南宋畫家馬致遠的空靈悠遠,表現出一種高逸清奇的神韻。曼殊曾贈柳亞子夫人鄭佩宜紈扇一柄,紈扇上畫有一條堤,一石橋,六七株疏柳,帶著風的樣子;一扁舟,兩燕子,神情疏朗,寥寥幾筆,高寡淡秀,尤見其曠,頗有不食人間煙火之感,正是曼殊代表之作也。

1912年6月蘇曼殊贈鄭佩宜的紈扇
后期的蘇曼殊,思想日趨消沉,悲觀厭世,頹唐自傷,寄情酒色,經常混跡于歌樓妓院,以“斗雞走馬”(舊時的一種賭博游戲)為快。作為南社的重要詩人,蘇曼殊參與南社的社務和社內的重大活動是不多的。他之所以成為南社的重要詩人,除了曾與柳亞子、高天梅、陳去病等南社詩人一起,以詩篇鼓吹革命,表現愛國主義思想外,更多是因為他在翻譯、詩詞、小說、繪畫等方面對當時的影響和藝術上取得的成就。關于蘇曼殊,柳亞子先生也曾自嘆“文采風流我不如”,稱他是“凄絕南朝第一僧”,評他的詩“好在思想的輕靈,文辭的自然,音節的和諧。總之是好在他自然的流露”。
所以縱觀蘇曼殊的一生,既有革命進取的一面,也有消極頹廢的一面。造成這種性格是多方面的,起初他只是狷介孤傲,不隨俗流而已,到了民國成立袁世凱的竊位盜國、軍閥割劇的昏暗局面、張勛復辟的丑陋鬧劇,各種勢力之徒趨之若騖,曼殊既不愿隨波逐流,又無力挽瀾救世,遂陷入了一種感傷的心境而不能自拔;于是呼一反常態,借醇酒、美人、詩文、禪理來麻醉自己,進而演變成一種逃避現實,甚至類似于一種自虐的行為,意欲快速的毀去皮囊,獲得真正的解脫。
“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殘時花已空”,1918年5月2日,“曼殊和尚”終因全身病痛,特別是腸胃病尤為嚴重,治療無效而溘然長逝。
(責任編輯 馮雪峰)
周春華,男,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博物館副館長、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