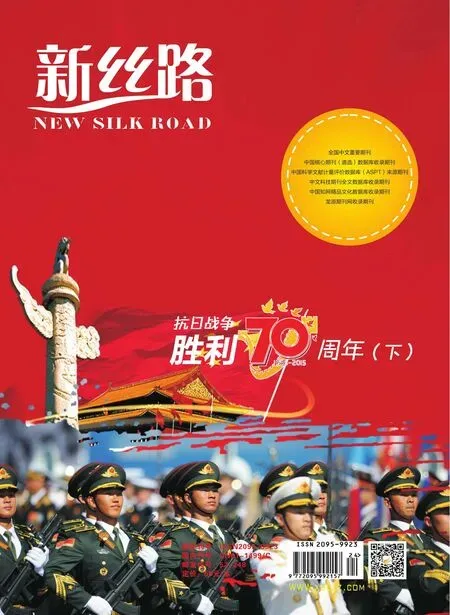探索穆旦詩歌的現代主義思想
孫海波(西北大學文學院 陜西西安 710127)
探索穆旦詩歌的現代主義思想
孫海波(西北大學文學院 陜西西安 710127)
現代主義思想使穆旦的詩歌成為中國現代詩歌中的奇異風景。詩歌評論界和文學史界對穆旦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足以和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等齊名的一流的詩人。古典詩歌表現溫情脈脈的美好理想,穆旦詩歌穿透美麗溫情的表象,向人們展示世界赤裸殘酷的真實本質。古典詩歌中詩人是群體的代表,傳達普遍的愿望和理想;穆旦詩歌則強烈突出了個體內心體驗,并揭示人們注定要不斷痛苦掙扎的命運。
穆旦;現代主義;自我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穆旦的詩歌卻與傳統涇渭分明。傳統文學追求意境創造,追求天人合一,穆旦卻背棄了傳統,走出人類的伊甸園,揭開世界的“摩耶之幕”。世界上只剩下了一個孤獨的主體,像西西弗斯一樣頑強而又徒勞地對抗一切,感受心靈上的顫抖戰栗,痛苦哀傷。他以孤獨痛苦的自我個體對抗一切,完成不可能完成的自我救贖的任務。
穆旦的詩歌創作開始于30年代他在天津南開學校讀高中之時,少年的他在那時已流露出早熟與早慧的特點,在詩中表達了對現實苦難的關注和對人生哲理、宇宙奧秘的探求。1935年,穆旦考入清華大學,抗戰爆發后又隨校來到昆明,進入西南聯大,開始顯示出自己獨特的詩歌才華。穆旦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接受了系統的現代主義思想,受到西方現代主義詩人的影響。他結合自己的現實體驗,寫出了許多現代主義的詩歌,創造出一個獨具特色、激蕩人心的精神世界。下面,筆者從傳統世界的失落、個體內心體驗的凸顯、痛苦掙扎的人生命運等幾個方面分析穆旦詩歌的現代主義思想。
一、傳統世界的失落
穆旦詩歌給人最顯著的刺激就是他展現了一個與傳統文學截然不同的世界圖景。他的眼光像鋒利無比的剃刀,掃除一切浮華,穿透溫潤的肌膚,深入骨髓,道出其中的秘密。他把人帶到了一個陌生、矛盾、危險、殘酷但又無比真實的世界中。赤裸裸的真實那么刺眼,讓人心驚膽寒,激發起讀者生死存亡的本能欲望。他的詩歌中沒有傳統意境的寧靜和諧可以使人在其中安歇,找到精神的歸宿;沒有美麗的景物、優美的旋律、溫馨的情感。有的只是直面人生的冷漠、孤獨、無奈和痛苦。
在《蛇的誘惑》小序中作者說:“創世以后人住在伊甸樂園里……人受了蛇的誘惑,吃了那棵樹上的果子,就被放逐到地上來。”這是《圣經》中的古老傳說,然而作者“覺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現。這條蛇誘惑我們,有些人就要被放逐到這貧苦的土地以外了”。上帝曾給人伊甸樂園,但人偷吃禁果有了知識,被逐出樂園來到屬于自己的大地上;而現在作者卻要更加深入認識自己,走出這貧苦的大地,失去任何依托,要孤獨地自己生存了。“呵,我覺得自己在兩條鞭子的夾擊中,/我將承受哪個?陰暗的生命的命題……”在新的世界中人們將無處可逃!蛇的第一次誘惑使人類被逐出伊甸園,但還有安身立命的土地;蛇的第二次誘惑使人類又被逐出貧苦的土地,無立身之所。蛇的第一次出現是人類的自我覺醒,從虛幻的伊甸園來到現實生存的土地上;蛇的第二次出現是詩人個體的覺醒,擺脫貧苦的土地,來到現代主義的世界中,面對“陰暗的生命的命題”。
沒有了上帝,沒有了樂園,甚至沒有立足的大地,世界將會怎樣?穆旦擺脫現實的迷惑,不再心存幻想,不再贊美愛情、謳歌生命,摒棄了溫情、浪漫、理想。他看透世界、人生以及生命,深刻體驗荒誕、悲劇、殘忍的本質,并講出這些真理,呈現出一個非理性的世界。
詩人在社會紛繁的現實表象后發現了陰謀與混亂,但他冷酷的洞察力并沒有停留在對“現時”社會的抨擊、批判上,而是進一步指向對人類歷史終極真相的追問,詩人的身分不僅是一個現實的搏求者,也是一個廣闊人生的探險者。現代主義的世界便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及古典主義的世界截然不同。在一般人的思想中,生命、春天、愛情、人生總是美好、幸福的,人們滿懷熱情、勤奮勞作就能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在穆旦看來卻恰恰相反。
對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謬性的艱難開掘,使穆旦詩中的“自我”形象地呈出高度緊張的現代特征。人們歌頌春天,陶醉在繽紛的色彩和馥郁的芬芳之中,可穆旦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本質。他在1942年的《春》中寫道:“如果你是醒了,推開窗子,/看這滿園的欲望多么美麗。”詩人在花團錦簇后面發現了生命的本質:欲望。這正是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叔本華所強調的:“世界和人自己一樣,徹頭徹尾是意志,又徹頭徹尾是表象。此外再沒有剩下什么東西了。”詩人振聾發聵的語言揭示觸目驚心的本質,讓讀者看清生命的痛苦和掙扎,來到欲望的無底深淵之前,戰戰兢兢,無限驚異、眩暈和恐懼。
愛情是詩歌的永恒主題,給人無盡的美好幻想,是苦難人生的慰藉。穆旦的詩歌中也有燃燒的愛情,但沒有纏綿和傾訴,沒有希望和白日夢的幻想。在1942年《詩八章》中穆旦說:“那燃燒的不過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們相隔如重山。”燃燒是什么?在許多詩人的篇章中,愛情的火焰常放射出最美的光芒,璀璨奪目,給人永恒和神圣的意味。但穆旦認為“那燃燒的不過是成熟的年代”,不過是生命發育成熟后的欲望要求,詩人說:“即使我哭泣,變灰,變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愛情不過是偶然的游戲,人不過是上帝玩弄在手里的玩偶,沒有一點自由,更談不上什么永恒和神圣。沒有什么“心有靈犀”,人和人之間“永遠相隔如重山”。
二、個體內心體驗的凸顯
世界和人生是虛幻、荒誕的,是充滿痛苦的悲劇,那么人能夠在哪里生存?拋棄這樣的世界和人生,還剩下什么?只剩下孤獨的自我。現代主義詩人將探究的目光轉向自我、轉向內心深處。現實的世界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人必須要在內心中尋找真實,尋找生存的依托,哪怕是用痛苦來對抗虛無。“這種尋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現代主義的追求脫離了藝術,走向心理:即不是為了作品而是為了作者,放棄了客體而注重心態。”
穆旦詩中的思想含量很大,很多詩句甚至類似于抽象的思辨,但這樣的詩句卻能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不安,其原因在于詩人常常將心靈的活動轉化成身體的感受,將觀念外化為具體的身體感知或生理意象。穆旦于1940年寫了一首詩,名字就叫《我》:“從子宮割裂,失去了溫暖,/是殘缺的部分渴望著救援,/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里……/永遠是自己,鎖在更深的絕望里/仇恨著母親給分出了夢境。”誕生就是一個荒誕的悲劇,被拋到荒野上,一個絕望的世界上。孤獨、殘缺、荒誕、絕望,這是現代主義最主要的思想情感。自我成為整個宇宙的中心,是生存的根基,除此之外則是虛無。所以,怎能不探索自我來尋找真實的意義?
在1976年創作的《聽說我老了》這首詩中,詩人這樣寫道:“人們對我說:你老了,你老了。但誰也沒有看見赤裸的我,只在我深心的曠野中,才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穆旦珍愛“赤裸的我”,在“深心的曠野中”,“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詩人一生都在探索自我內心世界,從自身來觀照人,1977年2月26日,穆旦因病去世。他是徹底的現代主義者,始終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他遠遠超越了他的那個時代。那些意氣風發的壯志豪情,或幸福快樂的頌歌贊曲,在這樣的詩句前顯得何等淺薄、蒼白、愚昧和虛偽。
穆旦對詩歌中語詞的選擇,詩行的展開模式中也處處滲透著“張力”意識。閱讀他的詩作,讀者會發現他十分偏愛從對立、矛盾的地方著筆,通過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的較量,形成詩歌曲折深入的表現力。譬如:“在過去和未來兩大黑暗間,以不斷熄滅的/現在,舉起了泥土,思想和榮耀。”(《三十誕辰有感》)
個人感受的凸顯是現代主義的重要特征。穆旦的詩歌中有對個體生存的虛無、荒誕之感的直接闡述。在早期詩歌中,穆旦就認為人們正在遭遇一個新的時代,必要經歷一番風雨、水火的洗禮。他在1939年的《從空虛到充實》中寫道:“我知道/一個更緊的死亡追在后頭,/因為我聽到了洪水,隨著巨風,/從遠而近,在我們的心里拍打,/吞噬著古舊的血液和骨肉。”死亡的洪水吞噬了古舊的世界,現在到處充滿了死亡,人要永遠面對著死亡,這是人的宿命,不管愿意不愿意。
如果說知性與感性的結合,是現代詩學的一個理想,那么“用身體來思想”則是其具體的方案,穆旦的寫作成功地實現了這一點,驗證了詩歌想象力對現實、觀念、感覺的重新組織能力。“真理和犧牲”不再神圣、崇高偉大,而且因為虛偽、狂妄和欺騙,所以讓人更深地低下“懺悔”的頭。那么人應當怎么做呢?穆旦于1947年創作了《我歌頌肉體》,這讓人不禁想起美國著名民主詩人惠特曼的一首詩《我歌唱那帶電的肉體》,他“歌唱帶電的肉體”,因為“這些不僅是肉體的構成和詩篇,也是靈魂的構成和詩篇”。惠特曼的詩歌充滿了理想和激情、信心和力量,要擁抱、享受和創造世界。然而穆旦詩歌中的肉體卻與黑暗、彷徨聯系在一起,甚至讓人哀憐:詩人在這個世界上終于找到了依托。穆旦寫道:“我歌唱肉體,因為它是巖石/在我們不肯定中肯定的島嶼。”肉體是“被壓迫的,和被蹂躪的”,但唯有肉體是“肯定的島嶼”,是生存的基石,“因為光明要從黑暗里出來:/你沉默而豐富的剎那,美麗的真實,我的肉體。”而“思想不過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護它所要保護的”。在這個世界上,人如何拯救自己?思想其實不可靠,或許肉體能告訴我們自己的存在,肉體承受著黑暗、壓迫和蹂躪。
三、痛苦掙扎的人生命運
對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謬性的艱難開掘,使穆旦詩中的“自我”形象地呈出高度緊張的現代特征。人生不過是一個無奈的過程,而且永不得安歇。上帝死了,人獨自支撐這個世界,盡管那么脆弱無力,孤獨無援。在1941年的《潮汐》中,詩人極大地突出自我,自我成為主宰,成為神,而這個神是異教的神,與希望、夢想、安寧和幸福背道而馳:“看見到處的繁華原來是地獄,/不能夠掙脫,愛情將變成仇恨,/是在自己的廢墟上,以卑賤的泥土,/他們匍匐著豎起了異教的神。”顛覆了一切,但要以血肉之軀,泥土一樣的身軀,承擔這坍塌了的世界。這“異教的神”即是現代主義的“自我”。
自我的分裂殘缺不只是詩人主觀的心理感受,它更是不斷的自我剖析、自我質問。《蛇的誘惑》以“人受了蛇的誘惑”,吃了智慧之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這一宗教故事為象征性背景,描述了一個青年在現代生活中虛弱彷徨的心理感受,外部環境描寫與內心獨白的交替閃現讓人聯想起艾略特的名詩《普羅甫洛克情歌》。
穆旦以自我扛起所有的一切,扛起整個世界:“他樹起了異教的神”!
宗教中的“神”給人信仰,當一切是虛幻的假象、是痛苦和失敗時,唯有信仰能給人勇氣和力量,給人繼續生存的理由。“他樹起了異教的神”,穆旦信仰的對象不是崇高偉大的上帝,而是一個真實、弱小但要求生存的自我。所以更需要信仰!信仰自我!以自我來支撐生存的世界,哪怕是無限的痛苦和悲哀。
現代主義詩人始終探索自我,咀嚼自己的痛苦。在1976年的《智慧之歌》中,詩人寫道:“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它的碧綠是對我無情的嘲弄,/我咒詛它每一片葉的滋長。”詩人自己支撐著世界,自己又能怎樣?1976年的《自己》是對詩人一生的回顧和總結,但每小節的結束,詩人都在做這樣的表白:“不知那是否確是自己。”現代主義者永遠在尋找自己,卻又永遠找不到自己,飽嘗無盡的痛苦,卻絕不欺騙自己。
對于自己詩歌中的現代主義思想,穆旦有清醒自覺的認識。在1940年的《玫瑰之歌》中,他用三個小標題大致描繪了自己的思想歷程:“一個青年人站在現實和夢的橋梁上”、“現實的洪流沖毀了橋梁,他躲在真空里”、“新鮮的空氣透進來了,他會健康嗎?”他探尋新的生命,走進一個充滿困惑和痛苦但真實的現代主義世界。在《玫瑰之歌》中他說:“我長大在古詩詞的山水里,我們的太陽也是太古老了,/沒有氣流的激變,沒有山海的倒轉,人在單調中死去。”他用最深刻的思想展現新的世界,用最強烈的情感激蕩、震撼古老的心靈,用最堅硬沉重的語言建造了紀念碑,指引人們走向新生:“然而我有過多的無法表現的情感,一顆充滿著熔巖的心/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顆冬日的種子期待著新生。”
這就是穆旦的詩歌,“他樹起了異教的神”!王佐良稱贊穆旦的詩歌創作是“去爬靈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一件在中國幾乎完全是新的事”。穆旦的詩歌確實是高聳、險峻的山峰。這山峰白雪皚皚,寒氣逼人,重云積聚,爆發刺眼的閃電和震耳的雷鳴!這山峰是讓人驚異的景象,象征著激蕩、悸動和戰栗的現代主義思想。
[1]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沖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33.
[2]彼得·福克納.現代主義[M].鄭羽,譯.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88:58.
[3]丹尼爾·貝爾.文化:現代與后現代[M]//王岳川.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7.
[4]穆旦.蛇的誘惑[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