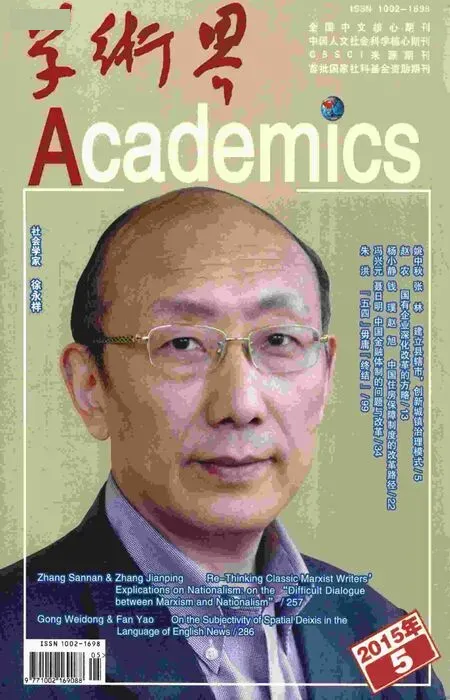新時期農(nóng)民啟蒙的經(jīng)濟理性面相〔*〕
○ 李衛(wèi)朝
(山西農(nóng)業(yè)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西 太谷 030801)
一、農(nóng)民啟蒙與經(jīng)濟理性
改革開放開創(chuàng)的持續(xù)至今的歷史轉(zhuǎn)折年代是謂“新時期”。在這一時期的歷史脈絡中,“農(nóng)民”包含著豐富的含義,既是一種職業(yè)概念——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又是一種身份概念——“鄉(xiāng)下人”,還是一個階級概念——與工人階級相對,更是一個文化概念——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承載者。盡管陸學藝先生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將農(nóng)民劃分為農(nóng)業(yè)勞動者、農(nóng)民工、雇工、農(nóng)民知識分子等多個階層,〔1〕但由于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特有的戶籍制度等原因,農(nóng)民作為多重含義的概念仍然繼續(xù)存在,農(nóng)民仍被站在農(nóng)民之外的人們視為“小農(nóng)”,認為他們所從事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往往是非理性的。與之相反,我們站在農(nóng)民的立場,認為生活在底層社會的農(nóng)民既是一個基本生存的維持者,更是一個最大利潤的追求者,“農(nóng)民在生存困境的長久煎熬中世代積累傳承下來并使其家系宗祧綿延不絕的豈只是理性,那應該稱為生存的智慧”。〔2〕這種“生存智慧”正是農(nóng)民的理性選擇在經(jīng)濟生產(chǎn)活動中的具體體現(xiàn)。就此而言,我們提出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就是其根據(jù)所處社會的經(jīng)濟制度、生產(chǎn)方式、義利觀念、文化背景、個體權(quán)利、道德規(guī)范、交往方式、市場范圍等,在經(jīng)濟生產(chǎn)活動中綜合考慮做出的,有利于自己以及家庭乃至共同體的生存安全、最大利益、最大效用的理性選擇。但是,由于受落后的生產(chǎn)方式、人多地少的困境、“水深齊頸”的生存狀態(tài)、社會經(jīng)濟制度的限制、農(nóng)民個體政治權(quán)利的少寡、宗法共同體的心理控制、血緣親緣地緣關(guān)系的作用、傳統(tǒng)義利觀的影響等諸多因素的束縛和制約,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長期處于一種潛在和模糊的狀態(tài)。
新時期以來,隨著社會經(jīng)濟政治制度的轉(zhuǎn)型,農(nóng)業(yè)政策的逐步調(diào)整,農(nóng)民在經(jīng)濟、政治、文化方面的權(quán)益逐步擴大,農(nóng)民逐漸從外部環(huán)境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生產(chǎn)活動范圍得以拓寬、生產(chǎn)方式得以提高、自主生產(chǎn)經(jīng)營得以保障,其經(jīng)濟理性才得以逐漸從潛在走向顯在,從模糊走向明晰,全面迸發(fā)涌現(xiàn)出來。正如秦暉所言:“只有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農(nóng)民作為交換行為的主體擺脫了對共同體的依附,他們的理性才能擺脫集體表象的壓抑而健全起來。”〔3〕從家庭承包責任制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從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到外出務工,再從外出務工到理性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中國農(nóng)民一步步地突破各種外部環(huán)境的制約和束縛,逐漸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潮中找準自己的定位與目標。這一過程一方面得益于外部環(huán)境的改變,另一方面也是農(nóng)民勇于運用自身經(jīng)濟理性進行抗爭的結(jié)果,“他們在尋求生存的過程中,不僅在有意無意之間改變著行為規(guī)則和制度約束,改變著資源的組合方式,而且也在不斷地反觀自己的行動,反省這些行動的后果”。〔4〕這兩方面相輔相成,共同促進了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解放與發(fā)展。
從啟蒙的視角出發(fā),新時期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從潛在走向顯在、從模糊走向明晰、全面迸發(fā)涌現(xiàn)出來的過程正是農(nóng)民啟蒙的過程!正如康德所言:“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經(jīng)別人引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aude(敢于知道)!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5〕由于經(jīng)濟生產(chǎn)活動在歷史上受到各種外部桎梏的束縛,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被“蟄伏”,因而農(nóng)民就處于“不成熟狀態(tài)”。新時期以來,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從“集體表象”的壓抑、生產(chǎn)方式的制約、各種制度的束縛、傳統(tǒng)義利觀念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在不斷調(diào)整的農(nóng)村政策的指引下,農(nóng)民開始敢于在自己的經(jīng)濟生產(chǎn)活動中運用理性進行選擇,從而逐漸地走出“不成熟狀態(tài)”。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新時期農(nóng)民在經(jīng)濟生產(chǎn)活動中逐漸趨于合理的理性選擇恰恰正是農(nóng)民啟蒙的過程!
我們的探討從此開始。
二、“等意交換”——傳統(tǒng)“生存理性”的回歸
誠然,傳統(tǒng)宗法性質(zhì)的村落共同體在歷史上對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生活形成了一定的控制,抑制著農(nóng)民個體思維的發(fā)展,阻礙著農(nóng)民個體理性的運用,并使農(nóng)民處于“神秘”的共同參與之中。但是,村落共同體同時給予農(nóng)民逃避競爭、分化、風險、動蕩的“保護”,使農(nóng)民對其形成了一定的依賴。這就是秦暉所言的宗法共同體對農(nóng)民的束縛與“保護”。〔6〕建國之后,在以社會主義為內(nèi)容的價值取向的支配下,人民公社制度的實施,一方面將農(nóng)民從宗法共同體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用集體指令替代了農(nóng)民個體的理性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農(nóng)民的自主權(quán)(比如農(nóng)民到農(nóng)業(yè)以外進行就業(yè)受到限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對歷史進行清算和總結(jié)的同時,以人民公社制解體為開端的農(nóng)村社會改革逐步展開,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平等的土地再分配,“競爭機制”的引入,相對平等、開放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建立等等,為農(nóng)民提供了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結(jié)構(gòu)”。自主生產(chǎn)經(jīng)營權(quán)利的獲得,使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得以復萌,他們開始靈活自主地選擇多種多樣的經(jīng)濟生產(chǎn)方式。由于相對比較落后的生產(chǎn)方式,在“生存理性”的支配下,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活動不得不再次向村落共同體回歸,尋找合理的生產(chǎn)合作方式,尋求村落共同體對其經(jīng)濟生產(chǎn)活動的保護。但是,這種回歸并不是一種倒退,而應該是螺旋式的上升,是一種理性的回歸,這種回歸是擺脫宗法控制之后的理性選擇,是一種超越式的回歸!從農(nóng)民啟蒙的角度而言,這正是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在被壓抑或被替代之后的重新釋放。
在村落共同體范圍內(nèi),為了追求生產(chǎn)過程中的代價最小化,人民公社制度廢除的傳統(tǒng)“搭伙”“搭套”“伙種”等以交換生產(chǎn)力內(nèi)容獲得農(nóng)業(yè)利潤的方式再次在農(nóng)村社會出現(xiàn),多個家庭之間展開互助合作,進行勞動力與勞動力、勞動力與畜力、畜力與畜力、畜力與農(nóng)具之間的交換,代耕、幫工、伙養(yǎng)役畜、共同租種、共同雇工等成為改革開放之初農(nóng)民耕種的主要形式。這種既不等時又不等量更不等價的交換,從經(jīng)濟利潤的角度來看,當然是“不劃算”的,但是從當時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而言,卻正體現(xiàn)了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狡黠”。因為“能不能,或者說會不會參與這種交換,對當事者來說,它意味著你是否能夠獲得合作機會和實現(xiàn)經(jīng)濟利潤的合作伙伴。”〔7〕對于農(nóng)民而言,在既有條件下備全畜力與農(nóng)具是一種多余的開支,因此他們需要的是在“伙種”中創(chuàng)造那種需要畜力或農(nóng)具時便能夠借到的自信。傳統(tǒng)的義利觀念在此仍然發(fā)揮著重要的功能,要實現(xiàn)一戶家庭之“利”只有在維護了多戶家庭的合作經(jīng)營之“義”中才能得到實現(xiàn),舍此之“義”則無一己之“利”!因此這一時期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表現(xiàn)為“文化意義很強的‘等意交換’”,或謂之“道德靈魂的交換”。〔8〕這是傳統(tǒng)村落共同體文化的回歸與復興,是血緣、地緣關(guān)系在農(nóng)民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中的作用的再次發(fā)揮,這也同時證明了雖然土地實現(xiàn)了家庭承包責任制,使用權(quán)歸個人所有,但在生產(chǎn)過程中農(nóng)民仍然能夠理性地進行著有序的組合。
雖然在村落共同體范圍內(nèi)進行著“等意交換”的合作生產(chǎn)方式,但是,經(jīng)歷了“餓怕了”的年代,在具體的生產(chǎn)過程中,農(nóng)民仍然保持著齊全的耕作模式,這塊地種糧,那塊地植棉;坡地栽薯,山地種樹;夏季收糧,秋季收豆;家家養(yǎng)豬,戶戶種菜……“窮怕了”的農(nóng)民小心翼翼地利用天時、地利條件,經(jīng)驗性地經(jīng)營著那幾畝薄田,維系著家庭的生活和地位尊嚴(臉面)!同時,為了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農(nóng)民開始嘗試性地采用科學的“間種”“套種”方法,選擇化肥、農(nóng)藥等先進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這種“內(nèi)向型”開發(fā)土地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其根本是為了達到“吃喝穿不求人”的目的。這就是所謂的農(nóng)民“生存理性”的延續(xù),是在農(nóng)民個體自主權(quán)利相對擴大、農(nóng)業(yè)科技水平逐步提高的背景下“生存理性”的進一步發(fā)展!
從農(nóng)民啟蒙的角度而言,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之所以得到釋放,主要得益于農(nóng)民、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政策的調(diào)整,這是農(nóng)民運用經(jīng)濟理性的前提。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正確處理了公與私的關(guān)系,原來被納入到集體、國家的農(nóng)民的“一己之私”獲得了合法的身份,“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極大地刺激了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釋放。這種經(jīng)濟理性首先直指農(nóng)民及其家庭的生存,即如何維持保障一家人的生活!這是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直接關(guān)乎農(nóng)民在其村落共同體范圍內(nèi)的地位與尊嚴。其次,選擇何種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以規(guī)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可能出現(xiàn)的各種風險,是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所要面對的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直接影響著農(nóng)民的生存保障。再次,如何取舍傳統(tǒng)的義利觀念,是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所要面對的又一個抉擇甚至是比較痛苦的抉擇,這個抉擇對于農(nóng)民實現(xiàn)自身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之初乃至更長的一段時間,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正是在這些繁雜的問題面前進行著權(quán)衡比較,亦步亦趨地走出“不成熟狀態(tài)”。但是,隨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科技化水平的提高,人多地少問題的凸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邊際報酬逐漸趨零,農(nóng)民這種“內(nèi)向型”向土地求生存的理性選擇再次陷入困境,這就迫使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必須突破向土地求生存的選擇,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之外尋找出路。
三、離土不離鄉(xiāng):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傳統(tǒng)生存理性的首次突圍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農(nóng)民為了能夠在“弄夠口糧之外能有閑錢”所尋找的第一個出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異軍突起”在當時的理論界引起了巨大的熱情,很多人由此找到了中國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的獨特模式,認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為華夏民族從農(nóng)業(yè)社會轉(zhuǎn)向工業(yè)社會提供了可以依托的微觀社會組織基礎”(甘陽語),既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的競爭原則,又符合中國的社會制度以及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而且繼承了傳統(tǒng)家族文化的精髓,體現(xiàn)了中國“群社會”的本質(zhì),是真正體現(xiàn)中國特色的社會發(fā)展之路。〔9〕對于這種高調(diào)評價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論點,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這些高調(diào)唱響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論點由于急切地試圖提出“非西方的現(xiàn)代化道路”,都存在明顯地把個別案例普遍化和理想化的傾向,〔10〕“離土不離鄉(xiāng)”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等級身份制”問題,而身份制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內(nèi)部的地緣關(guān)系、宗法關(guān)系、依附關(guān)系更阻礙了現(xiàn)代企業(yè)文明的形成。〔11〕關(guān)于這場爭論,無需再多著墨,歷史已經(jīng)給予了雄辯的回答。如果允許我們?nèi)ヒ庾R形態(tài)地從農(nóng)民自身來分析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異軍突起,可以說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農(nóng)民在改革開放之后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空間之后,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一次突圍。
農(nóng)業(yè)的過密化始終是中國兩千年歷史上制約農(nóng)民的亙古問題。就地興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農(nóng)民在改革開放之后獲得了棄農(nóng)務工經(jīng)商自由進行反農(nóng)業(yè)過密化的理性新選擇,這種選擇是農(nóng)民作出的不得已而為之的“并非最次”的被迫選擇,“不過是農(nóng)民在原有城鄉(xiāng)格局和工農(nóng)體制下迫不得已的創(chuàng)造”。〔12〕在人多地少、農(nóng)業(yè)邊際報酬逐漸趨零的現(xiàn)實制約下,為了掙得一些現(xiàn)金以補生活之急,創(chuàng)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在離土不離鄉(xiāng)的基礎上“為擴大鄉(xiāng)親們的就業(yè)機會”和“為本鄉(xiāng)本土增加福利”,而不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擴大鄉(xiāng)親們的就業(yè)機會”和“為本鄉(xiāng)本土增加福利”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勝利,說明了農(nóng)民創(chuàng)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仍然是將傳統(tǒng)的功義觀念置于首要的地位!
“重農(nóng)輕商”“重本抑末”是中國兩千多年形成的重要觀念。“士農(nóng)工商”的等級排序使農(nóng)民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農(nóng)本”思想和“輕工”“輕商”的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農(nóng)民的擇業(yè)視野非常狹窄,基本上不愿也不能從事種植業(yè)以外的行業(yè),副業(yè)也只有少數(shù)精明的農(nóng)民在小心翼翼地從事,當然就不會明白比較收益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jīng)濟社會的轉(zhuǎn)型,為農(nóng)民棄農(nóng)務工經(jīng)商創(chuàng)造了寬松的外部環(huán)境,頭腦靈活的農(nóng)民很快意識到了“種田不劃算”,于是突破重本抑末觀念的桎梏,大膽從農(nóng)業(yè)轉(zhuǎn)向務工、經(jīng)商,在鄉(xiāng)村的土地上創(chuàng)辦了屬于自己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這是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對傳統(tǒng)“重農(nóng)輕商”“重本抑末”觀念的突破!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的古訓使農(nóng)民形成了重土安遷的生活習慣,對于中國農(nóng)民而言,但凡有生路,誰愿舍棄自己家鄉(xiāng)故土安靜平穩(wěn)的生活背井離鄉(xiāng)?但是,一方面要執(zhí)守安土重遷觀念,另一方面又要突破農(nóng)業(yè)過密化的現(xiàn)實困境。為了合理解決這一矛盾,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再次發(fā)揮了其創(chuàng)造性——就地創(chuàng)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離土不離鄉(xiāng)”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既實現(xiàn)了農(nóng)民棄農(nóng)務工經(jīng)商的追求,又滿足了農(nóng)民安土重遷的習慣。因此,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異軍突起是農(nóng)民面對安土重遷與農(nóng)業(yè)過密化的兩難困境中所進行的一次偉大創(chuàng)造!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本土性以及“為擴大鄉(xiāng)親們的就業(yè)機會”和“為本鄉(xiāng)本土增加福利”的目標,注定了其建立、發(fā)展和生產(chǎn)、運營必然具有先天的血緣、親緣、地緣關(guān)系的特性,而這與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模式必然會產(chǎn)生沖突與矛盾。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先天的血緣、親緣、地緣關(guān)系與后天的市場經(jīng)濟關(guān)系里尋找動態(tài)的平衡,冀圖在血緣、親緣、地緣關(guān)系規(guī)則與市場規(guī)則的交融過程中,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血緣、親緣、地緣關(guān)系的注重,這也是這一時期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選擇的又一特色!此外,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運營過程中卻未能意識到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自然資源的重要性,這充分證明了這一時期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異軍突起既不是出自政治領袖的意志,也非來自經(jīng)濟學家的頂層設計,只不過是鄉(xiāng)土中國的現(xiàn)實生存困境迫使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對傳統(tǒng)的一次突圍而已。從農(nóng)民啟蒙的角度而言,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發(fā)揮一方面是為了在經(jīng)濟生產(chǎn)活動中尋求更大的空間,但另一方面,經(jīng)濟理性的運用又會受到來自傳統(tǒng)觀念的阻撓,在既有的條件下,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不可能一下子實現(xiàn)質(zhì)的飛躍,往往會在這兩者之間尋求妥協(xié)。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就是這種妥協(xié)的結(jié)果。正因此,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命運必然多劫。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江南沿海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紛紛遭遇如何優(yōu)化配置資金、技術(shù)、勞動力和資源,如何減少或降低污染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如何參與更激烈的市場競爭等等難題時,內(nèi)陸的農(nóng)民在失敗的痛苦中驚醒,他們的經(jīng)濟理性再次實現(xiàn)突圍,放棄“離土不離鄉(xiāng)”的誘惑,勇敢地涌向城市,在全國范圍形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進城務工隊伍!
四、離土又離鄉(xiāng):進城務工——傳統(tǒng)生存理性的再次突圍
我國經(jīng)濟體制轉(zhuǎn)軌、社會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和工業(yè)化、城市化迅猛發(fā)展,為農(nóng)民向城市流動轉(zhuǎn)移就業(yè)創(chuàng)造了體制條件和就業(yè)條件;城鄉(xiāng)壁壘的松動,使農(nóng)民走出土地進城務工成為可能。伴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逐漸建立和完善,商品流通領域的逐漸擴大,農(nóng)民物質(zhì)生活資料的滿足漸漸從依靠土地轉(zhuǎn)向依賴市場。但由于工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剪刀差還沒有完全去除,農(nóng)業(yè)的比較效益明顯低于工業(yè),這就必然導致農(nóng)民在有限的土地上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所能夠獲得的“現(xiàn)錢”是有限的,“種田不劃算”成為所有農(nóng)民的真切感受。雖然政府也在積極推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升級換代,推廣新品種、扶持新項目等等,但由于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周期長,往往容易陷入蛛網(wǎng)循環(huán)〔13〕之中,這就給農(nóng)民引進新品種帶來了極大的風險,而與之相對,這種風險在無所謂生產(chǎn)周期的勞動力市場上卻不存在。既然進城務工能夠獲得比單純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較高的比較效益,農(nóng)民當然選擇放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而進城務工。如果說“離土不離鄉(xiāng)”就地進入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務工還受到傳統(tǒng)重本抑末、安土重遷觀念的影響和束縛,那么,“離土又離鄉(xiāng)”的進城務工則意味著傳統(tǒng)重本抑末、安土重遷觀念的坍塌。
1990年代,農(nóng)民負擔總體呈上升趨勢,年均增長幅度都超過同期農(nóng)民收入增長幅度。再加上農(nóng)村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不徹底、財政體制不完善、管理與監(jiān)督體制不完善等原因,地方政府借機亂攤派、亂收費,日益加重了農(nóng)民負擔,導致農(nóng)民不堪重負。〔14〕當農(nóng)民附著于土地增收致富無望的時候,身邊通過進城務工經(jīng)商致富的農(nóng)民給他們提供了又一條“離土又離鄉(xiāng)”的致富路徑——拋地進城務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農(nóng)民選擇進城務工既是農(nóng)民對繁重的稅費負擔的一次反抗,同時又是農(nóng)民實現(xiàn)增收致富的又一次理性選擇!
農(nóng)民進城務工并不像有些學者所擔心的那樣是盲目的、無序的甚至是可怕的。為了提高進城務工的安全和降低失敗的風險,他們進城是有其自身的運作機制和規(guī)律的,即“親戚帶親戚,老鄉(xiāng)帶老鄉(xiāng)”。有研究指出,親緣、地緣關(guān)系網(wǎng)絡是農(nóng)民傳遞信息的渠道和進行流動決策的依據(jù),在這種人際關(guān)系連帶型的流動中,農(nóng)民能夠很快找到工作安頓下來,并在新環(huán)境中形成共同生活的親緣、地緣關(guān)系群體,成為他們持續(xù)流動、改善生存境遇的重要依托。“以親緣和地緣為主的人際關(guān)系所形成的網(wǎng)絡支持了整個的流動過程,從而使流動的不確定性和流動者的不安全感大大降低”。〔15〕這種在農(nóng)民進城務工過程中形成的“關(guān)系型網(wǎng)絡”,也是農(nóng)民的理性選擇,是將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中對家族群體的依賴關(guān)系搬遷至進城務工之后的新生產(chǎn)生活環(huán)境,以將自己進城務工的代價和風險降到最低。就此觀之,農(nóng)民進城務工既是對傳統(tǒng)的突圍,同時又是對傳統(tǒng)的繼承和延伸。
從農(nóng)民啟蒙的角度而言,正是由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比較效益低下、稅費負擔日益加重,刺激了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再次突圍。這次突圍同時還得益于農(nóng)民對現(xiàn)代化都市生活的向往與追求,以及對傳統(tǒng)重本抑末、安土重遷觀念的舍棄。農(nóng)民啟蒙正是在現(xiàn)代性與傳統(tǒng)的緊張中不斷推向前進的。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傳統(tǒng)對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影響是深遠而持久的,農(nóng)民啟蒙正是在對傳統(tǒng)的突圍和繼承中發(fā)展著。
五、商品生產(chǎn)——市場理性的崛起
在大批農(nóng)民背井離鄉(xiāng)進城務工的同時,仍有部分農(nóng)民堅守在土地上,從事著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耕作,維持著中國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這些勞作在土地上的農(nóng)民,其經(jīng)濟理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刺激下,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與轉(zhuǎn)型,逐漸從傳統(tǒng)自給自足的生產(chǎn)轉(zhuǎn)向商品生產(chǎn),突破了傳統(tǒng)狹隘的市場意識、商品意識和消費觀念,實現(xiàn)了中國農(nóng)民歷史上的最大轉(zhuǎn)變。這是堅守土地的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巨大轉(zhuǎn)型,是新時期以來堅守土地的農(nóng)民最具革命性的變化。
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在農(nóng)村的逐漸建立,堅守在土地上的農(nóng)民逐漸打消了“餓肚子”的顧慮,開始從原來家家戶戶“少而全”的生產(chǎn)模式轉(zhuǎn)向“多而精”的生產(chǎn)模式,從為保障自家生活的種植模式轉(zhuǎn)向為迎合市場生產(chǎn)的商品種植模式,有些頭腦靈活的農(nóng)民甚至放棄了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耕作,開始在土地上從事養(yǎng)殖業(yè),以賺取更高的經(jīng)濟利潤。在市場里尋求更大的利潤成為堅守土地的農(nóng)民的首要目標。這是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艱難地突破傳統(tǒng)義利觀念之后的痛苦抉擇。傳統(tǒng)的小農(nóng)意識和小生產(chǎn)意識逐漸退卻歷史舞臺,市場意識和商品意識逐漸在農(nóng)民心里慢慢萌發(fā)、成長并茁壯起來,其消費觀念也從“節(jié)衣縮食、精于倉儲、守財如命”漸漸轉(zhuǎn)向追求財富增長與生活水平改善。
與此同時,在改革開放之初頗為興盛的傳統(tǒng)“搭伙”“搭套”“伙種”等生產(chǎn)方式已逐漸失去蹤影,多戶家庭一起生產(chǎn)勞作的轟轟烈烈的勞動景象已成為歷史記憶,那種既不等時又不等量更不等價的交換被一切以金錢來衡量的等價交換所代替。傳統(tǒng)血緣、親緣、地緣關(guān)系也逐漸褪色,父子之間、兄弟之間、親戚之間、鄰舍之間的那種脈脈的親情、人情、友情,逐漸被冰冷的金錢、利益沖蝕得消失殆盡,傳統(tǒng)“義以為上”的“等意交換”在80年代回歸了一段時間之后又再次消失。市場力量持續(xù)沖擊著村落共同體,農(nóng)民的經(jīng)營生產(chǎn)對于村落共同體的依賴大大減弱,即使轟轟烈烈的新農(nóng)村建設運動也很難將農(nóng)民凝聚在村集體周圍,只顧自家埋頭致富使村落共同體文化一步步走向蕭條。
農(nóng)民啟蒙首先指向現(xiàn)代性,在現(xiàn)代性的指引下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革,這種變革是伴隨著農(nóng)民文化價值觀念的轉(zhuǎn)變而逐漸實現(xiàn)的。市場經(jīng)濟的推進將競爭、進取、冒險等現(xiàn)代文化價值觀念熔鑄進農(nóng)民的文化心理,但同時又對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形成沖蝕,“義以為上”的義利觀、村落共同體文化、親情人情友情等本應該保留的傳統(tǒng)也消失殆盡。正如賀雪峰所言:“現(xiàn)代性不僅在器物層面,而且在觀念(靈魂)和邏輯層面,在根本的行為動力和人生目標上面改造和重塑中國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這一次不只是粗疏地掠過傳統(tǒng),而是細密地改造和改變傳統(tǒng),是徹底地消滅傳統(tǒng)。”〔16〕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現(xiàn)代性走向帶來了新的希望,但同時又帶來了新的困惑;傳統(tǒng)的流失促進了農(nóng)民的進步,但同時又讓農(nóng)民感到了些許的失落。在中國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變遷的過程中,現(xiàn)代的逼近、傳統(tǒng)的流失究竟是中國農(nóng)民、農(nóng)村之幸還是不幸?
六、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經(jīng)濟理性的成熟趨向
2006年農(nóng)業(yè)稅的全面取消、2008年的金融危機、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土地流轉(zhuǎn)制度的實施、農(nóng)村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升級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影響著進城務工的農(nóng)民開始大批地離城返鄉(xiāng),形成了所謂的農(nóng)民工“返鄉(xiāng)潮”。如果說90年代農(nóng)民大批進城務工經(jīng)商形成的所謂“民工潮”是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做出的選擇,是生存理性的突圍,那么,今天的“返鄉(xiāng)潮”也是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的選擇,是農(nóng)民“對自己所擁有的資本、對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再認識以及對生活的滿意度等各種經(jīng)濟因素和非經(jīng)濟因素”〔17〕進行理性比較分析的結(jié)果,是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趨于成熟的表現(xiàn)。
在城鄉(xiāng)二元體制下,戶籍制度永遠是進城務工農(nóng)民心頭隱隱的痛,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民的“城市夢”都將因為現(xiàn)行的戶籍制度而夢碎城市。但城市的務工生活使農(nóng)民具有了觀察、分析與預測市場的能力,并培養(yǎng)了他們在技術(shù)上的一技之長,使農(nóng)民獲得了文化資本;辛勤的勞動與節(jié)儉的生活為農(nóng)民積攢了微薄的積蓄,使農(nóng)民獲得了經(jīng)濟資本;通過血緣、親緣、地緣和私人等關(guān)系在城市里務工生活逐漸形成了農(nóng)民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使進城務工農(nóng)民獲得了社會資本。當他們由于年齡原因在城市的工作空間日顯狹仄,“城市的過客”心理使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以及城市生活的滿意度會逐漸降低,這些資本的擁有為他們再回到鄉(xiāng)村生產(chǎn)生活提供了一定的自信。由此可見,一方面是城市工作生活空間的狹仄和城市夢的破碎,另一方面是相對安逸的農(nóng)村生活以及自身所積累的資本,在這種理性權(quán)衡比較下,一些農(nóng)民開始理性地返回家鄉(xiāng),運用自己在城市所積累的資本進行創(chuàng)業(y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城務工農(nóng)民的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是他們在對城市生存空間與鄉(xiāng)村生活的滿意度以及自身資本進行比較分析基礎上的理性選擇,盡管這種選擇帶著一種無奈的酸痛,但畢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并非最次的選擇。
進城務工農(nóng)民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的這種理性選擇,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未來中國農(nóng)村社會的發(fā)展趨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楊團認為,農(nóng)村的各種社會問題現(xiàn)在已經(jīng)基本“見底”,農(nóng)村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已經(jīng)成為普遍現(xiàn)象,農(nóng)村人口的社會結(jié)構(gòu)造成了農(nóng)村的必然衰落,農(nóng)村現(xiàn)有的生產(chǎn)力跟整個中國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越來越脫節(jié),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的現(xiàn)象。亟待改觀的農(nóng)村形勢必然使中國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形成一個返鄉(xiāng)的高潮,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于農(nóng)村長于農(nóng)村的第一代農(nóng)民工,他們在城市務工二十余年,耳濡目染社會發(fā)展,成為農(nóng)村骨干的可能性最大,他們的返鄉(xiāng)會帶動農(nóng)村社會、經(jīng)濟、文化力量的回升。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進城務工農(nóng)民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正順應了中國農(nóng)村社會的發(fā)展趨勢。
進城務工農(nóng)民的“返鄉(xiāng)潮”給予我們一定的警醒,我們應該以一種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農(nóng)民啟蒙的終極指向,也許讓農(nóng)民回歸土地才是農(nóng)民啟蒙的根本目的。當然這種回歸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應該是經(jīng)現(xiàn)代性啟蒙之后的超越式回歸。回歸之后的農(nóng)民將會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將會創(chuàng)造一種全新的文明樣態(tài)!
七、不是結(jié)論的結(jié)論
新時期以來,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理性經(jīng)過了從生存理性的回歸——“等意交換”到生存理性的兩次突圍——“離土不離鄉(xiāng)”與“離土又離鄉(xiāng)”,再到市場理性的崛起——商品生產(chǎn),最后在農(nóng)民的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中逐漸趨于成熟,而這一系列的變遷,無不與國家政策的調(diào)整有著緊密聯(lián)系。所以,未來要推動農(nóng)民啟蒙和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持續(xù)變遷,對于政府而言,“就必須從改變限制農(nóng)民選擇范圍的外部條件著手”,調(diào)整農(nóng)民、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政策,從政治上賦予農(nóng)民更大的權(quán)利,從經(jīng)濟上給予農(nóng)民更大的選擇空間,保障農(nóng)民最大限度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尤其是經(jīng)濟理性的自由。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政府是農(nóng)民啟蒙的主要外在推動力量!此為其一。
其二,從農(nóng)民啟蒙的內(nèi)在推動力量而言,新時期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變遷是農(nóng)民突破自身對于步出“不成熟狀態(tài)”的懶惰和怯懦的過程。傳統(tǒng)農(nóng)民早已習慣于在“保護者”為他們設定好的軌道上“安逸”前行,他們從不考慮去爭得“安逸”之外的自由,并且認為步出“安逸”是非常艱辛甚而危險的。新時期以來,隨著社會的急速轉(zhuǎn)型,傳統(tǒng)那條“安逸”的軌道開始轉(zhuǎn)向,農(nóng)民終于開始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掙脫“不成熟狀態(tài)”這副腳梏,開創(chuàng)另一種全新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新時期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變遷其實就是一個農(nóng)民運用理性發(fā)現(xiàn)自身的過程。他們不再做既定規(guī)約下的義務工具,不再在既定的規(guī)約中尋找自己存在的意義,開始掙脫既定規(guī)約勇敢追求自身的幸福生活,開始從自身去尋找生存的價值和意義。這就是農(nóng)民啟蒙的要義!
其三,新時期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變遷與中國傳統(tǒng)之間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啟蒙是對傳統(tǒng)的批判還是對傳統(tǒng)的挖掘?這個問題自18世紀西方的啟蒙開始就引起了不同的爭議,有人認為傳統(tǒng)可以作為一個毫無根據(jù)的成見而被拋棄,也有人認為啟蒙之于傳統(tǒng)“不是去破除那些普遍的成見,而是運用他們的睿智來發(fā)現(xiàn)貫徹于其中的隱藏的智慧”。〔18〕而從新時期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變遷,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農(nóng)民啟蒙一方面應該是運用理性對隱藏在傳統(tǒng)(成見)中的智慧進行發(fā)現(xiàn),并且讓這些傳統(tǒng)(成見)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理性延續(xù)下來;另一方面,對那些建立在迷信基礎上的傳統(tǒng)則要通過啟蒙加以消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對于農(nóng)民而言,傳統(tǒng)的蛻變是一個比較痛苦的選擇過程,并且受現(xiàn)代化負面的影響導致不該流失的傳統(tǒng)的被祛除,導致在新時期農(nóng)村社會變遷過程中相應地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比如道德的滑坡、親情的淡漠、義以為上的淪喪、競爭導致互助的淡化等等,這些都是在未來農(nóng)民啟蒙中應該重視的問題。
其四,新時期農(nóng)民經(jīng)濟理性的變遷是“中國農(nóng)民一步一步地通過自己有目的的行為,逐漸地改變著行為規(guī)則和制度約束,改變著資源的組合方式”,〔19〕市場經(jīng)濟理性漸趨成熟、小農(nóng)經(jīng)濟“盲目性”逐漸弱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農(nóng)民當然地將現(xiàn)代化作為追求的目標,但是,現(xiàn)代性的危機在城市生活的肆虐,卻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未來農(nóng)民啟蒙的指向。今天,我們不應該再執(zhí)迷于“現(xiàn)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誤區(qū),應該跳出現(xiàn)代化的西方模式,依托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開創(chuàng)現(xiàn)代化的中國模式。當前,中國正處于歷史的拐點,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過一百年的萎縮在今天的真正崛起,給中國,給農(nóng)民,給啟蒙以新的希望與使命!
注釋:
〔1〕陸學藝:《“三農(nóng)論”——當代中國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民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417-424頁。
〔2〕郭于華:《“道義經(jīng)濟”還是“理性小農(nóng)”——重讀農(nóng)民學經(jīng)典論題》,《讀書》2002年第5期。
〔3〕秦暉:《傳統(tǒng)與當代農(nóng)民對市場信號的心理反應——也談所謂“農(nóng)民理性”問題》,《戰(zhàn)略與管理》1996年第2期。
〔4〕〔12〕〔19〕黃平:《從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到外出務工》,《讀書》1996年第10期,第70、66、69-70頁。
〔5〕康德:《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回答:什么是啟蒙?》,施密特編:《啟蒙運動與現(xiàn)代性》,徐向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頁。
〔6〕秦暉、金雁:《田園詩與狂想曲——關(guān)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北京:語文出版社,2010年,第124頁。
〔7〕〔8〕釋然:《文化與鄉(xiāng)村社會變遷》,《讀書》1996年第10期。
〔9〕王穎:《新集體主義:鄉(xiāng)村社會的再組織》,北京:經(jīng)濟管理出版社,1996年,內(nèi)容提要。
〔10〕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jié)與90年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第78頁。
〔11〕秦暉:《“離土不離鄉(xiāng)”:中國現(xiàn)代化的獨特模式?——也談“鄉(xiāng)土中國重建”問題》,《東方》1994年第1期。
〔13〕所謂蛛網(wǎng)循環(huán)是指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市場上的周期性波動。由于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周期長,其決策依據(jù)現(xiàn)時銷售價格刺激下產(chǎn)生的預期,而實際市場價格卻取決于前一周期的生產(chǎn)規(guī)模。
〔14〕曹錦清通過對中原地區(qū)農(nóng)民的調(diào)查,在《黃河邊的中國(增補本)》一書中翔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原農(nóng)民負擔加重的狀況。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增補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
〔15〕郭于華:《傳統(tǒng)親緣關(guān)系與當代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社會變革》,《讀書》1996年第10期。
〔16〕賀雪峰:《最近十年農(nóng)民的理性化進程》,http://www.snzg.cn/article/2007/0904/article_6850.html。
〔17〕周霞:《回鄉(xiāng),還是留城?——對影響農(nóng)民工理性選擇的因素分析》,《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18〕施密特:《啟蒙運動與現(xiàn)代性(導論)》,徐向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頁。
- 學術(shù)界的其它文章
- 我國國有企業(yè)利潤分配制度的歷史、現(xiàn)狀及其完善
- 中國住房保障制度的改革路徑
- 國有企業(yè)深化改革的方略
- The Spiritual Evolu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Archetype“the Fictitious Land of Peace and Happiness”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Archetype“the Wilderness”in American Literature
- Natural Ethics,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turn —— On the Ecological Society Thoughts in Tao Te Ching
- Validity Evaluation of the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Market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