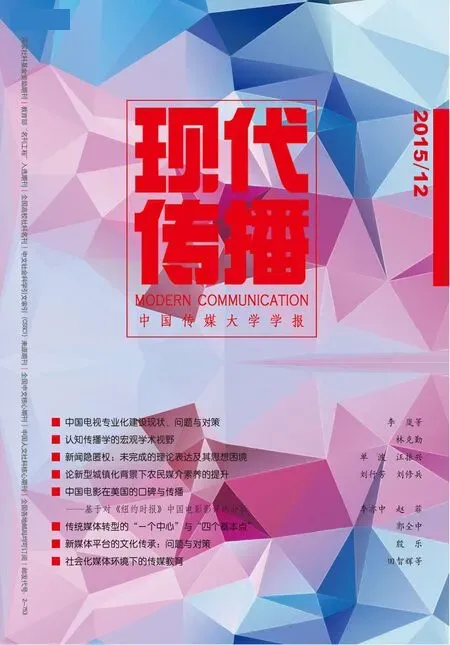批判學派的“另一副面孔”和傳播研究的“第三種可能”*
——洛文塔爾傳播理論解讀
■ 甘 鋒
批判學派的“另一副面孔”和傳播研究的“第三種可能”*
——洛文塔爾傳播理論解讀
■ 甘 鋒
面對傳播研究中經驗學派與批判學派爭執不下的理論困局,洛文塔爾通過轉換研究對象和思維方式,“在文化社會學領域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從而開啟了批判學派與經驗學派長達七十多年的沖突與融合,進而打造了批判學派的“另一副面孔”,揭示了傳播研究的“第三種可能”。洛文塔爾的傳播研究既堅守著批判學派的整體觀念和批判立場,又與經驗學派一樣重視實證研究和科學方法。他把經驗學派漠不關心的文藝傳播問題納入到傳播研究領域,并通過廣泛的經驗研究驗證其理論分析的有效性,從而有力地促成了具有批判色彩的傳播研究的人文主義范式。洛文塔爾開創的從文藝角度出發理解傳播的本性和意義,推進傳播研究的“人性”維度、批判觀點和人文主義精神的研究范式,對更好地理解正在發展中的、作為一門學科的傳播學具有重要意義。
洛文塔爾;傳播理論;批判學派;經驗學派;文藝傳播
傳播學經驗學派與批判學派是傳播理論在美國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逐漸形成的價值取向根本對立、研究方法截然不同的兩種研究范式。1941年,拉扎斯菲爾德首次撰文分析了這兩種研究范式的區別并將其分別命名為“管理的研究”和“批判的研究”。1977年,詹姆斯·柯倫等人編著的《大眾傳播與社會》進一步突出了二者的區別并將這兩個學派對立起來。而1985年國際傳播學會在夏威夷召開的以“典范對話”為主題的年會則激發了人們對兩大學派不同研究范式及其理論后果的熱烈討論。美國經驗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多元社會,因此只要協調多元利益之間的平衡便會有益于社會的發展,因而其從事的傳播研究多是一種鞏固當前社會模式的可量化的經驗研究。加之,其研究多接受政府資助或工商業贊助,因此帶有濃厚的實證色彩和商業氣息,這在促進應用研究的同時也嚴重限制了其研究的范圍和理論價值。而開創了批判傳播研究范式的法蘭克福學派卻與之有著不同的社會觀和方法論,在批判學派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事實上有利于資產階級自身的統治,其社會制度和傳播體制使大眾傳播有可能成為統治者控制大眾的工具,因而傳播研究應該通過社會哲學思辨對其進行批判從而為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服務。面對傳播研究中兩大學派爭持不下的理論困局,洛文塔爾通過扭轉研究立場、轉換研究對象、轉變思維方式,“在文化社會學領域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①從而開啟了奠基于實用主義傳統之上的經驗傳播研究與奠基于人文主義傳統之上的批判傳播研究這兩大學派長達七十多年的沖突與融合,進而打造了批判學派的“另一副面孔”,揭示了傳播研究的“第三種可能”。
一、阿多諾與洛文塔爾:批判傳播研究的“兩副面孔”
在現代大眾社會中,大眾文化與大眾傳播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大眾文化是以大眾傳播為途徑來實現的,而大眾傳播也已成為大眾文化的組成部分。因此,以大眾文化為研究焦點的法蘭克福學派就不可避免的要關注大眾傳播問題。無論他們直接探討的是何種學術問題(媒介變遷與文藝轉型、新媒介與現代性抑或電子媒介與流行音樂等等),無論他們選取的是何種研究資料(早期影像、現代音樂、高雅文學抑或通俗藝術等等),對于本雅明、阿多諾、洛文塔爾等批判理論家來說,對藝術問題的傳播學闡釋都不僅僅是為了孤立地研究特殊的文化現象,“它還力求把人類生存最有價值的一些證據置于社會學框架之中”。②事實上,“他們所有的藝術理論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問題的基礎上:即藝術如何體現它的社會批判的姿態。”③因此,當20世紀 30年代中期霍克海默、阿多諾、洛文塔爾等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流亡到美國發現“權威主義在美國的出現帶有與歐洲不同的偽裝形式,是一種更緩和的強求一致的方式,這在文化領域可能最有成效”④時,將其在德國初步建立起來的批判傳播研究范式應用到對美國文化傳播問題的研究上,就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理所當然的研究議題。
眾所周知,對文藝傳播媒介知識譜系及其文化邏輯的考察是法蘭克福學派藝術研究和傳播研究的焦點,但是對于大眾傳播的態度,批判學派不但與經驗學派分歧嚴重,就是在其內部,批判理論家們也一直爭論不休。爭論的一極是以阿多諾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主流成員,他們對大眾媒介持消極悲觀的批判態度,認為文化工業以大眾傳播技術為手段,把藝術變成商品,在創造虛假需要的同時達到了意識形態控制的目的。可以說,對大眾媒介與藝術傳播問題的批判性研究和對“實證主義的過分的經驗論偏見”的針鋒相對的批判是其與生俱來的基因。在批判理論的指導下,以霍克海默、阿多諾等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開辟了一條與美國經驗學派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徑。在阿多諾看來,美國經驗學派所采取的把文化現象轉換成量化數據的非中介方法,是大眾文化物化特性的典型體現。馬丁·杰伊認為正是“這一前提使他與以嚴格運用定量方法著稱的拉扎斯菲爾德的‘管理研究’的合作從一開始就不能成功。”⑤嚴格恪守批判理論立場的阿多諾曾經公開宣稱:“要將我的思想轉變成那些傳播研究的術語,就如同要把圓的畫成方的一樣不可能。”⑥這就是當時在美國社會科學界廣為人知的法蘭克福學派傳播研究的“第一副面孔”。爭論的另一極是特立獨行的本雅明,他極力鼓吹大眾媒介潛在的進步力量,雖然他也對傳統藝術的蛻變感到惋惜,但還是肯定了新興傳播技術及其派生的藝術形式和大眾文化。本雅明的激進形象也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但是,法蘭克福學派還有“被不公平地冷落的另一副面孔”,即洛文塔爾運用批判理論進行文藝傳播研究時所建立的批判傳播理論。
與阿多諾和本雅明的極端態度相比,洛文塔爾顯得較為清醒冷靜,他既看到了大眾媒介的技術潛能、美學潛能和認知潛能,因而沒有像阿多諾那樣消極悲觀;也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對大眾媒介的應用所帶來的問題,因而沒有像本雅明那樣積極樂觀。當面對現實生活中的電子傳播媒介時,他似乎與阿多諾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比如,他十分贊同阿多諾的流行音樂批判,“阿多諾花費了大量精力去論證包括但是不限于廣播和唱片的電子復制技術導致的嚴肅音樂的變形。我不是音樂社會學家,但是關于藝術作品和藝術演出的社會框架之間的必要關系,我還是知道一些,通過推論我必須假設被播映的莎士比亞的恐怖情形比得上阿多諾所說的音樂聽力的變形。”⑦面對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工業的迅速發展,他也承認:“傳播技術對于藝術家的完整性而言,已經成為了一種武器。我正在思考卡夫卡、喬伊斯和普魯斯特,在某個方面,他們是難以接近的,但這種‘難以接近’恰恰是他們的目標。對于抽象畫而言,也是如此。但是資本主義社會有一個大胃,我們總是低估它所能吸收和消化的東西。”⑧由此可見,洛文塔爾與阿多諾一樣對大眾傳播在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有著清楚認識的。
馬克·波斯特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媒介批判非常不滿,他寫道,“面對第一媒介時代的社會批判理論……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運作進行了條分縷析而鞭辟入里的探討。然而考察媒介時,則淪為攻擊和謾罵”。波斯特批評“阿多諾除了其自以為是的權威之外別無任何經驗基礎可言”,⑨也許是有其道理的,但是以此作為批判法蘭克福學派的論據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因為洛文塔爾的傳播研究不但有著堅實的經驗基礎,而且對大眾傳播持有較為客觀辯證的態度。尤其是當他把大眾傳播放到一個既定的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以仔細辨別文學與大眾傳播的關系時,他的態度就不再像阿多諾那樣激進。比如他在研究英國十八世紀的文學變遷問題時,就收集了大量關于文學媒介的數據,并采取定量方法對其進行了經驗性分析。這使他認識到媒介技術條件對于藝術生產的革命性潛能,他不但認為媒介技術不應為文化的衰落負責,反而建議研究“大眾媒介本身所固有的內容和價值”。⑩在這一點上他似乎又轉向了本雅明,而遠離阿多諾。由此可見,洛文塔爾對待媒介的態度是非常辯證的,他既不像本雅明那樣對大眾媒介抱有樂觀的和革命的烏托邦情懷,也不像阿多諾那樣持悲觀的和激進的批判態度。通過對歷史中的大眾媒介和文藝傳播問題的研究,洛文塔爾使法蘭克福學派的傳播研究呈現出了“另一副面孔”。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在堅持批判理論立場的同時,對美國經驗研究的有益成果進行了批判性吸收,這使他的傳播研究擁有更為豐富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
將洛文塔爾和阿多諾與美國經驗學派的合作情況略加比較,這一點便可一目了然。洛克菲勒基金會聘請阿多諾研究無線電音樂的消費和效果問題。這是阿多諾到達美國后在拉扎斯菲爾德的幫助下獲得的第一個科研項目,他非常重視這次近距離觀察和研究美國流行音樂的機會。但是在研究中,堅守批判理論的阿多諾發現,他根本無法接受拉扎斯菲爾德用經驗學派的實證技術來檢驗其關于廣播音樂研究結果的做法。他批判性的觀點和毫不妥協的姿態最終導致洛克菲勒基金會撤銷了對他的資助。福特基金會當時聘請洛文塔爾研究的是電視傳播問題。在拉扎斯菲爾德提供的研究團隊的支持下,洛文塔爾大量借鑒經驗方法來研究通俗藝術和文化的大眾傳播現象,他的研究成果不但得到拉扎斯菲爾德和美國文化公共政策委員會的肯定,羅伯特·默頓甚至贊譽他的研究是“綜合了歐洲理論立場和美國經驗研究方法的少數幾個經典范例之一”(11)。在拉扎斯菲爾德看來,如果批判理論能夠融入到大眾傳播研究的洪流中,就一定能夠做出更大貢獻。顯然,他是將批判理論作為經驗研究的一種補充來看待的。洛文塔爾則正相反,盡管他接受了拉扎斯菲爾德的資助,愿意采用經驗方法來進行傳播研究,但他是將經驗研究作為批判理論的一種補充予以借鑒的。拉扎斯菲爾德的經驗研究之所以對他有著特別的吸引力,可能是由于他看到雙方存在著極富潛力的合作前景;也可能是出于他當時特別的社會政治處境——“洛文塔爾和其他流亡學者一樣,不得不依靠有權勢的個人和組織的影響和慷慨捐贈”(12)。阿多諾的情況似乎有所不同,在與拉扎斯菲爾德的合作失敗之后,他就和霍克海默離開紐約,搬到洛杉磯說德語的移民聚居區了。作為社會研究所的主要負責人和核心理論家,他們擁有相對充足的資本繼續從事資本主義和文化工業的理論批判研究。但是洛文塔爾卻不得不繼續留在紐約,“在拉扎斯菲爾德充滿了經驗主義研究氛圍的應用研究局費力地工作”,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工作經歷和克服理論沖突的努力“使他的研究成為批判理論和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最美好的聯姻”(13)。洛文塔爾把經驗科學的實證性與理論研究的人文性辯證統一起來對文化傳播問題進行綜合研究的理論觀念和研究范式,不但拓展了傳播理論的研究空間,而且揭示了美國傳播研究的第三種可能。在此之后不久,洛文塔爾就被美國之音聘為研究部主任,成為當時美國規模最為龐大的一支大眾傳播研究隊伍的負責人,也正是在美國之音的學術生涯奠定了他作為美國大眾傳播研究專家的學術地位。
哈羅德·拉斯韋爾認為洛文塔爾的研究之所以極具張力和創造性,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同時采取了定性的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并且吸收了二者之所長”(14)。與法蘭克福學派“第一副面孔”相比,洛文塔爾對大眾媒介及美國經驗學派的態度確實更為理智也更加辯證:他既批判經驗學派缺乏哲學和歷史維度的還原論傾向,也希望用經驗方法來豐富、矯正并且支持它的理論假設。他站在批判的立場上開放地吸收一切優秀的文化資源,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實際上,“把經驗方法與社會科學的批判目標相結合,把嚴肅的實踐與價值意識理論結合起來”(15)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科林·斯巴克斯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采訪時強調指出:“在未來幾年里,中國的大學如果想要最大程度地提高社會科學研究的質量,應該在這方面多做努力。”(16)
二、吸收的前提:洛文塔爾對經驗傳播學派的批判
任何對已有理論的真正借鑒和吸收都要從批判性的清理開始,洛文塔爾的傳播研究也不例外。盡管相比阿多諾而言,他大量借鑒和吸收了經驗學派的有益成果,并且贏得了美國社會科學界的承認和尊重,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與經驗學派的合作就一帆風順,事實上,他也和阿多諾一樣飽受經驗學派的折磨。這一點阿多諾看得很清楚,“我讀到了你論述通俗雜志的論文,我非常喜歡它……我知道你面對的問題,一方面你要堅持我們的理論興趣,另一方面則要以拉扎斯菲爾德能夠忍受的方式來處理材料。”(17)洛文塔爾的研究盡管在當時就贏得了羅伯特·默頓等美國社會科學家的充分肯定,但是“拉扎斯菲爾德仍然以他典型的經驗主義-實證主義方式”指責洛文塔爾的批判立場。更加令人沮喪的是,他的很多作品由于堅守實證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批判理論或者缺乏經驗主義者所要求的“經驗性數據”而無法發表。比如《恐怖的原子人》“因經驗性數據太少”而被《美國社會科學》雜志退稿,施拉姆在再版傳播理論經典文獻時刪除了洛文塔爾的論文等都是典型案例。這種篩選行為本身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征兆,它很可能反映了當時美國主流傳播研究界對洛文塔爾的批判傳播理論的態度,或者說它反映了傳播學經驗學派與批判學派的理論分歧。正如漢諾·哈特所說:“作為第一流傳播研究文獻的編輯,施拉姆的行動復制了拉扎斯菲爾德對傳播研究的理解,包括不愿意包含傳播研究的批判觀點,這種觀點依靠歷史的力量和文化條件。當傳播研究走出學術領域進入市場時,它開始聚焦于機構的需要和興趣。”(18)
眾所周知,傳播學經驗學派的研究項目幾乎都來源于政府、工商業或者基金會等社會機構,由于此類資助有著很強的實用目的,導致經驗學派逐漸形成了注重經驗事實(通常被限定為可測量、可統計的信息資料)、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傳播效果為重心的研究范式。這不但使其研究范圍受到嚴重限制,而且喪失了傳播研究所應有的歷史語境和哲學參照維度,甚至于對傳播所固有的交流理解問題和文化價值問題都視若罔聞。而傳播的本性與意義、人類的自由與解放等法蘭克福學派所關注的問題恰恰是經驗學派的量化研究所難以解釋的。因而,試圖以廣泛的經驗研究來彌補批判理論之不足的洛文塔爾必然會先對經驗學派進行一番批判,才可能從中汲取有益的成果。在與經驗學派進行合作與對話的過程中,他基于批判理論著重從以下幾方面對美國的經驗研究進行了批判。
第一,經驗研究是一種缺乏價值導向的市場研究。傳播學經驗學派以市場數據作為研究起點,試圖將事實與價值分開,以期調和大眾傳播研究與有關機構之間關系的做法,在洛文塔爾看來,其實質是對權威的承認和對權力的妥協,就其客觀后果而言,不但不可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理解和人的自由與解放,反而起到了維護當前的統治與管理模式的作用。美國經驗學派的傳播研究“把自己局限在定義非常清晰的課題上,如內容分析、效果研究、受眾分層、媒介內部以及媒介之間的關系等”,這種以市場數據作為理論起點、只關注數據處理技巧的經驗研究缺乏必要的社會理論基礎,其結論不可能是真實的。因為對任何與人相關的社會現象的研究都不可能離開研究者的生存環境和價值取向。“調查研究并非一定要從一張白板開始不可。要弄清楚的首要問題是需要對羅列在數據表中的數據進行破譯和讀解。”(19)更何況大眾傳播機構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制度,它是無法脫離文化意義和價值構成的。對于經驗學派這種回避、掩蓋甚至參與社會控制的傳播研究模式,洛文塔爾進行了毫不含糊地批判,“從最終的分析來看,社會研究只不過是市場研究,它是一種權宜之計,是讓不情愿的消費者狂熱消費的工具”,(20)“他們之所以要進行經驗研究實際上僅僅是為了錢,而不是為了研究對象”。(21)
第二,經驗研究缺乏所研究現象的歷史語境。經驗學派的傳播研究“經常聚焦于心理經驗和行為結果,忽略了大眾媒介更廣泛的歷史語境和社會語境”,(22)在洛文塔爾看來,這與植根于具體的歷史語境、著眼于社會整體的批判傳播研究范式實在是相去甚遠。對于經驗學派的量化研究方法,他質疑道:“現代社會科學對于現代社會文化的處理已經達到什么程度?研究工具已經高度精確,但是這就足夠了么?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已經成為一種實用的禁欲主義。它和一切外在力量的糾纏劃清界限,在一種嚴格保持中立的氛圍中興旺繁榮。它拒絕進入意義的領域。”(23)“對于經驗研究者而言,現象好像是在某個精確的時刻被囚禁在現實中,研究者這個時候只要用他們的手術刀對準它就行了。”(24)但是對于批判傳播研究來說,所有對傳播理論家有效的經驗都不應當還原為實驗室的受控觀察,因為傳播研究總要包含歷史內容,應該從歷史可能性的角度觀察它們,他舉例說:“不同的政治和哲學陣營都在具體語境中研究社會現象——這種語境即現代報紙與中產階級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解放史之間的關系。以對出版界的研究為例,研究現代報紙,如果沒有意識到歷史的框架,那么在這個詞的確切涵義上,這項研究是毫無意義的。”(25)由此可見,歷史參照維度是洛文塔爾進行傳播研究的重要坐標。
第三,經驗研究缺少人性內涵與人文關懷。由于美國經驗學派未能認識到大眾傳播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制度,導致其拒絕對關于傳播的人性內涵等人文主義領域的問題進行探討。洛文塔爾指出,在經驗傳播學派利用個性為大眾傳播服務的過程中,精神的交流和經驗的共享等傳播所包含的人性內容都被遮蔽了。“當個體出現在傳播媒介中時,他被陰險地與他的人性隔離了。大眾傳播在開發個性的每一個過程中,都依靠個體自治的意識形態的支持來為大眾文化服務。”(26)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交往、理解基礎的傳播就被大眾傳播“附庸化”了。對于以效果研究為中心的經驗傳播學派而言,傳播活動更多地被視為傳播作用于接受者的過程。換句話說,作為個體之間創造性互動過程的傳播觀念,在經驗傳播研究的闡釋框架中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受眾的觀念。人們對傳播內容的理解、對傳播活動的參與被簡化為對大眾媒介做出被動的回應。如此一來,經驗學派就把大眾傳播研究的范圍局限在大眾媒介活動領域內了。
第四,經驗研究忽視了傳播的功能研究。在徹底批判了經驗傳播研究缺乏必要的社會理論基礎和哲學歷史維度、喪失了人文精神關懷的研究立場后,洛文塔爾進一步指出了經驗學派的全部研究都奠定在錯誤的前提上,“對于大眾媒介研究來說,理論的起點不應當是市場數據。經驗研究一直錯誤地假設,消費者的選擇是決定性的社會現象,我們應該對此展開深入分析。但第一個問題是:在社會的總體進程之中,文化傳播的功能是什么?”洛文塔爾將美國社會科學家所進行的“經驗研究”界定為市場研究,認為它僅僅表現了一種無中介的反應,而沒有對潛藏在文化現象下面的社會功能和心理功能進行詳細審查。他指出:“研究不應該限于狹義的心理學范疇。它們的目的更在于查明社會整體中的客體要素在大眾媒介中是怎樣被生產和再生產的。這就意味著不能把‘大眾的趣味’作為一個基本范疇,而是要堅持查明,這種趣味作為技術、政治和經濟條件以及生產領域主宰利益的特定結果,是如何灌輸給消費者的。”(27)洛文塔爾對傳播的人性內涵和文化功能的強調,使批判傳播研究得以糾正經驗學派“把語言和傳播僅僅作為信息技術概念”(28)的狹隘的傳播觀念。
盡管洛文塔爾對美國經驗學派進行了嚴厲地批判,但是他并沒有像阿多諾那樣陷于歐洲傳統不能自拔,與之不同的是,他采取的是批判吸收的策略:在批判經驗研究的同時,試圖改變其邏輯起點,借鑒其研究方法,拓展其研究范圍,將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同時引入到傳播研究中。正如道格拉斯·凱爾納所言:“批判理論杰出的辯證法體現在它的理論結構中融入了經驗研究方法。”(29)
三、“哥白尼式革命”:傳播研究的“第三種可能”
洛文塔爾傳播研究的辯證之處主要體現在,它既堅守著批判學派的整體觀念和批判立場,又與經驗學派一樣重視傳播研究的科學方法和對數據的經驗性分析。他在把經驗學派所定義的大眾傳播效果問題置于社會整體和歷史語境之中、站在批判理論的立場上從價值與意義的角度進行研究的同時,又把經驗學派漠不關心的文藝傳播問題納入到傳播研究領域,并通過廣泛的經驗研究驗證其理論分析的有效性,從而有力地促成了具有批判色彩的大眾傳播研究的人文主義范式,相對于傳統的批判學派與經驗學派而言,可說是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路徑。羅素·伯曼就此評論道,洛文塔爾“保持了堅定的批判立場,植根于具體的歷史語境。在這樣的語境中,文化成為一種審美文化,藝術則呈現了人類活動的獨特特征。”正是對藝術的傳播學研究使“洛文塔爾扭轉了當時的研究立場,在文化社會學領域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30)如果羅素·伯曼此言不虛,洛文塔爾像康德一樣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革命”,(31)那么這場革命是怎么發生的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洛文塔爾能夠開辟美國傳播研究的第三條道路呢?
首先,洛文塔爾始終堅持“理論力場”的學術理念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他堅決拒絕那種將各種見解和方法按照等級進行排序的做法,在他的傳播研究中,批判理論和經驗方法等“一系列變化著的因素組成了非總體的并置關系”,在這種動態的并置關系中,“他把第一流的歐洲傳統社會思想的知識興趣和對美國社會科學的新洞見融為一體……‘在保持人文學科的社會學觀點之時,從人文主義出發進行社會學研究,這樣做,能夠將西方精神的交融性導向一種全新的認識’。”(32)洛文塔爾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不但與他個人的學術特質有關,更與其獨特的實務經歷和學術視野密切相關。他在回答杜比爾關于他為什么“比阿多諾更容易與拉扎斯菲爾德合作”的問題時說:“對我而言,把理論的、歷史的觀點和社會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經驗研究結合起來是更容易的……這與我的職業經常與具體事務打交道,并且要求我去處理具體事情有很大關系。作為一名教師和社會工作者,我深陷研究所的實際事務之中,包括財政和管理事務,因此我比阿多諾要更關心社會現實。這一點最有可能反映在我們的學術行為上。”(33)誠如馬丁·盧德克所指出的,“盡管洛文塔爾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批判理論的框架之中——他幫助建立并且發展了批判理論;然而洛文塔爾注重實際的傾向也是非常明顯的,這種傾向使知識分子的愛好改變方向,返回到現存社會環境的軌道上。對于洛文塔爾而言,思想的可能性總是意味著在現存環境范圍內的思想。”(34)此外,移民到美國也拓寬了洛文塔爾的研究視野和研究領域,美國的大眾文化曾一度取代了歐洲經典文藝,成為他的研究對象和數據庫。而他與經驗學派合作研究美國大眾文化的學術經歷,尤其是擔任美國之音研究部主任的實務經歷,使他認識到批判傳播理論要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界的尊重和認可,就必須進行廣泛的經驗研究以說明其理論研究的充分性和科學性。因此,他既反對沒有經驗研究的空洞的理論推論,也反對沒有理論指導的盲目的經驗主義研究。總之,“洛文塔爾跨越國界的學術活動不但擴展了他的理論視野,而且為其建立新的學術體制做出了重要貢獻。”(35)
其次,從哲學層面看,根本原因在于洛文塔爾對批判理論的獨特理解和運用。對于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來說,批判理論既是從事研究的根本立場和出發點,也是一種研究方法,“其本身是一種植根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辯證的社會理論”(36)。對于這種嚴格界定,在洛文塔爾的內心深處,恐怕是持有保留態度的。他曾多次指出:“批判理論并不是一系列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運用的理論。”(37)在進行傳播研究時,他更多地是把批判理論作為一種面對所有文化現象都將采取的批判姿態,而非一套固定的方法論,這就使他的研究具有了批判性地吸收經驗研究方法的可能性。比如,給他帶來了巨大聲望的《通俗雜志中的傳記》之所以能夠同時贏得傳播學家和批判理論家的交口稱贊,就是因為他是站在批判理論的立場上采用經驗主義方法通過對發表在美國兩家流行雜志中的通俗傳記的數據統計、計量分析和內容分析,才令人信服地闡明了美國傳記主人公從“生產偶像”到“消費偶像”的轉變過程,進而敏銳地揭示了美國社會正在步入消費社會的歷史發展趨勢。作為通俗藝術傳播研究的一篇經典文獻,《通俗雜志中的傳記》所開創的批判理論與經驗方法互相融合、相互支撐的研究范式已經成為傳播研究的一種基本模式。
最后,相對于美國經驗研究的局限性而言也是最重要的,洛文塔爾是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出發進行傳播研究的——“要了解傳播的意義,我們最好轉向象征性表達領域,即藝術領域和宗教領域”。(38)洛文塔爾的這一轉向不但開創了傳播研究的全新視角和思維方式,而且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也都不再局限于原有框架,從此以后,數量龐大的文藝傳播資料以及文藝研究理念、方法就被引入到傳播學研究中,這種從研究對象、思維方式到研究范式的全面更新,極大地彌補了當時美國主流傳播研究中的許多不足。可以說,自從傳播學在美國誕生以來,“從基于文學或者哲學根源的文化或者社會決定性的角度出發對傳播本性進行的討論,是極其少見的,洛文塔爾則是個例外,他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39)盡管傳播研究理應對文藝傳播現象作出闡釋,“但是傳統傳播學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卻無法將文化中的藝術現象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40)。在洛文塔爾看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作為藝術的文學……是個體的創造物,并且是個體以自身身份進行的體驗。因此,它距離社會科學家的興趣點好像很遙遠。”(41)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當時美國的傳播研究主要聚焦于大眾傳播的效果研究,并且特別強調研究的實用性和實證性,對于缺乏實用價值和難以量化研究的藝術傳播活動自然也就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
扎根于批判理論、積極援引文藝研究補充支撐傳播研究的洛文塔爾則深信,把批判理論和實證研究方法應用到藝術傳播現象上將會駕起一座溝通二者的橋梁,這使他的藝術傳播研究與堅持歐洲批判傳統的人文主義者和堅持美國實證傳統的經驗主義者形成了鮮明對照——不但突破了傳播學經驗學派遠離藝術的禁忌,運用傳播學方法揭示了歐美藝術轉型之謎,而且站在批判理論的立場上對美國的大眾文化進行了實證研究,“形成了一種包括辯證思維在內的理論上的傾向性”,(42)從而推動美國傳播研究在理論上獲得突破性進展。從中不難看出洛文塔爾的傳播研究與美國經驗學派的一大區別:即文學藝術是否是理解傳播的必要條件。對于洛文塔爾來說,要理解傳播的本性及其對人類的意義,就必須研究文學藝術,因此他力求通過文藝傳播研究,將傳播理論從美國經驗學派的限制中解放出來,這不但擴大了傳播學的研究領域,而且影響了它的理論指向。在這樣做時洛文塔爾就推進了傳播研究的“人性”維度、批判觀點和人文主義精神,而這正是其所開創的批判傳播理論之于美國傳播研究的獨特意義和重大貢獻。
總之,洛文塔爾的傳播研究不僅繼承了歐陸的哲學傳統和人文主義范式,深深地植根于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對美國實證主義的尊重,批判地吸收了美國經驗學派的一些研究方法。歐美這兩大看起來難以調和的學術傳統經過洛文塔爾的綜合,不但使他成功地打造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第二副面孔”,而且揭示了傳播研究的“第三種可能”。雖然很長一段時期,洛文塔爾的批判傳播理論及其人文主義研究范式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隨著人們對傳播人性內涵的日益關注,以人文主義理念與綜合方法研究和闡釋傳播現象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逐漸得到了證明和肯定。洛文塔爾開創的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出發理解傳播的本性和意義,進而綜合批判理論、傳播理論和文藝理論對傳播現象展開跨學科研究的人文主義范式,對我們更好地理解正在發展中的作為一門學科的傳播學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30)Russell Berman.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Theory and Society Vol.15,No.5,1986,p.792.
②⑩(19)(20)(23)(25)(27)(41)洛文塔爾: 《文學、通俗文化和社會》,甘鋒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8、29、25-26、26-27、31、2頁。
③ 楊小濱:《否定的美學》,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8頁。
④ 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72.
⑤ 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222.馬丁·杰伊在《辯證的想象》一書中詳細地引述了阿多諾與拉扎斯菲爾德之間充滿火藥味的通信,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1996,pp.222-224。
⑥ 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曹靜生、黃艾禾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有研究者認為,阿多諾之所以拒絕接受經驗學派的理念和方法,“關鍵是心理學的視角遮蔽了他在傳播學意義上的思考,或者他壓根就沒有從嚴格的傳播學角度思考過這一問題。而缺少了傳播學意義上對無線電廣播的界定和分析,他的思考無論如何都不周全。”趙勇:《整合與顛覆:大眾文化的辯證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頁。
⑦(17)(42)Leo Lowenthal.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eorists,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89,p.58,p.131,p.251.
⑧(21)(24)(34)(37)Leo Lowenthal.An Unmastered Pa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29,p.144,p.144,p.239,p.77.
⑨ 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范靜曄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頁。
(11)Barry Katz.The Acculturation of Thought:Transformations of the Refugee Scholar in America,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3,No.4,p.746.
(12)(39)Hanno Hardt.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Essays on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London:Routledge,1991,p.157,p.92.
(13)(22)John Durham Peters,Peter Simonson.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Key Texts,1919-1968.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p.89,p.89.
(14)Harold Lasswell.Personality,Prejudice,and Politics,World Politics Vol.3,No.3,1951,p.407.
(15)奧利弗·博伊德、克里斯·紐博爾德編:《媒介研究的進路——經典文獻讀本》,汪凱、劉曉紅譯,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16)科林·斯巴克斯:《中國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現狀與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3月11日。斯巴克斯是從70年前拉扎斯菲爾德區分的“管理的和批判的傳播研究”的不同之處談起的。他認為,從拉扎斯菲爾德起直到今天,“管理”研究在美國大學里就十分盛行,并且“中國學術界對大眾媒體的研究也是追隨著這一傳統的”。但是70年前處于邊緣位置的“批判”研究,現如今在美國的大學里,卻逐漸受到重視,然而“這一研究在中國大學里還相當薄弱”。他認為:“這兩個理論分支的研究人員可以并且也應當在一起并肩工作,這兩者對于一個健康的社會科學團體來說缺一不可。”我國于2012年推出的以“多學科交叉融合、各行業協同創新”為主要特色的“2011計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體現了對這一科研理念和方法論的認同。
(18)(28)(32)Hanno Hardt.The Conscience of Society:Leo Lowenthal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ummer 1991,p.76,p.78,p.68.
(26)(38)Leo Lowenthal.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84,p.292,p.291.
(29)(36)Douglas Kellner.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New German Critique,No.4,1975,p.138.
(31)所謂“哥白尼的革命”,指的是哥白尼在天文學領域所做出的具有革命性的轉變,主要在于思維方式和研究主體與對象關系的轉變。哥白尼假定觀察者旋轉從而提出“日心說”假說,使主客關系發生根本轉變;他證明了日出之類日常感官經驗是不真實的,從而使思維方式轉向超越經驗的方向。康德按照哥白尼的思路,假定對象必須符合認識,從而將研究對象從客體轉向主體的認識能力,使思維方式轉向超越經驗的方向,最終確立了先驗論。先驗方法在美學領域的運用,使康德得以超越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為美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學理基礎。詳見拙作《康德“哥白尼式革命”與當代美學轉型》,《云南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從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的轉換和先驗方法的確立及運用的角度看,洛文塔爾轉換研究對象、轉變思維方式,進而確立批判傳播理論的做法,被譽為“哥白尼式革命”似乎并不算太過。
(33)Leo Lowenthal.An Unmastered Pa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41。就個人工作經歷而言,洛文塔爾與阿多諾最大區別可能在于,阿多諾一直是一名純粹的學者,而洛文塔爾卻承擔了大量的行政事務,從在歐洲擔任猶太難民咨詢委員會委員、社會研究所第一助手、《社會研究雜志》主編、社會研究所代理所長、社會研究國際學會主席一直到在美國擔任戰爭情報局分析師、美國之音研究部主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預算委員會委員、社會學系主任等等,這些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職務既鍛煉了他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也養成了他關注現實問題的習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了他從事學術研究的理念和方法。
(35)Gertrude J.Robinson.The Katz/Lowenthal Encounter:An Episode in the Creation of Personal Influence,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08,No.1,pp.76-96.(2006)。格特魯德·羅賓遜認為拉扎斯菲爾德/默頓的管理研究和洛文塔爾的批判研究不僅被過分簡化了,而且二者的歐洲思想淵源及其移民到美國后的互相學習都未能得到充分承認,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
(40)隋少杰:《藝術:在文化傳播中生成》,《山東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作者系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社科處副處長)
【責任編輯:張國濤】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方當代文學傳播理論的多維透視”(項目編號:14BWW005)、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3YJA76001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