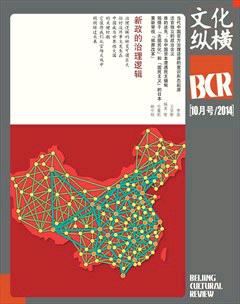搖擺于“去國民化”和“國民主義”的日本
[日]倉重拓
在距東京只要四個多小時飛行距離的北京,如今大約有一萬多的日本人生活在中國人當中。只看外貌難以判斷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但只要聽上幾句話,絕大多數日本人還是不難被辨識出來,因為日本人說漢語有獨特的音調。如果您突然碰到“日本鬼子”的后代怎么辦?也許您會有點兒尷尬,其實呆在中國的日本人同樣尷尬,雖然我們也都是很普通的一個老百姓,不太像抗日片中的軍國主義分子,但毫無疑問,我們是他們的后代,承襲著他們的血脈。
對當代在華日本人來說,上世紀的侵略戰爭并不是切身經歷的事情,因此在談到戰爭責任時實際上很多人認為是事不關己的。雖然二戰之后的日本社會以和平主義的名義思考日本的戰爭責任,但除了一部分戰爭當事者或者和平活動家之外,認真思考這些問題的日本人確實很少。為了確立中目之間的真正信賴關系,當代日本人正視侵華戰爭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大前提。那么,在戰爭記憶濃厚的中國生活著的在華日本人如何面對侵華戰爭責任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但難以回答的問題。在此需要說的是,這里談到的觀點和感受只代表筆者個人,不能代表在華日本人,可以說僅僅一個“80后”在華日本人對本國近現代史黑暗面的反思。筆者期望中日年輕一代為推進上一代人未完成的事業而共同努力。
戰爭賠償與經濟援助
為了討論日本侵華戰爭的責任,首先要回溯一下中日邦交正常化,看看當時中日兩國政府如何處理日方戰爭責任的問題。這里比較重要的是跟戰爭責任密切相關的戰爭賠償問題。根據1972年9月29日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之第五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毋庸置疑,中方放棄戰爭賠償權不意味著戰爭責任問題的圓滿解決,日方的戰爭賠償以經濟援助的名義,通過有償和無償的方式補償間接進行。日方往往批判中方對“政府開發援助計劃”(ODA)及其對中國經濟發展作用的認識不足,實際上中方也似乎沒有積極地公布日方的貢獻,給予日方很多借口批判中方不領情行為。但在此更重要的是日元貸款那樣的經濟手段能否解決戰爭責任那樣的倫理問題,如今中日關系的情況證明,只靠經濟手段好像難以建立中日兩國之間的信賴關系,無論多少日元投向于大陸,都難以感動中國人。
建交時期的日方領導對這一點認識還比較明確,像大平正芳外務大臣那樣,通過戰前參與侵華政策充分認識日方罪行的日方干部,不會輕率地將道義上的戰爭責任跟經濟上的戰爭賠償混為一談。眾所周知,恢復邦交以來的中日關系是被經濟因素所引導過來的,在這一點上需要中國市場的日方和需要日本援助的中方的利益也曾經完全一致。不過很明顯,在中國已經超越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現狀下,原來的中日經濟關系也不免經歷結構性的改變。因此,渡過了蜜月期的經濟性中日關系也碰上了障礙,以經濟優越為前提的戰后日本人之中國觀也開始動搖了。從經濟的角度只能分析極為復雜的中日問題之一部分,因為它不能解釋當代日本人為何對中國經濟發展抱有復雜的心情。站在重視經濟利益的立場來說,損害中日經濟關系的事情沒有任何道理。不過,他們往往忽略被經濟基礎一直壓抑的上層建筑,即形成東亞近現代史的“國民”(nation)概念的存在。
戰后日本與“去國民化”
中日恢復邦交時,中方在日方的戰爭責任問題上采取了極為寬容的態度,不僅放棄了戰爭賠償,而且把全部的戰爭責任歸為所謂“少數軍國主義者”,從而基本上免除了日本國民的侵華戰爭責任。比如,周恩來總理在歡迎田中角榮首相宴會上的祝酒詞很具有代表性,他主張日本人民也是跟中國人民一樣的受害者,接下來說道“中國人民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1972年9月25日)。可以說,這種判斷源自冷戰時期的高度政治判斷,以將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為目標。不過,其中也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及其邏輯內在的國際主義性質,它本身是國民主義的對立概念。二戰結束之后,全世界深刻反思引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強烈的國民主義(法西斯主義),在共產主義迅速普及的情況下,國民意識逐漸被階級意識代替,筆者暫且將在冷戰時期政治社會結構下出現的對國民意識的壓迫和否定簡稱為“去國民化”。
在此筆者所注意的是,二戰之后日本舉國積極參與“去國民化”這一過程所導致的意外后果是作為戰爭責任主體的日本國民之消失。“國民化”主要是通過學校和家庭的宣傳給予個人一種歷史主體性的過程,“去國民化”就是這一過程的逆轉,即從學校和家庭中完全消除這種歷史主體性而消滅國民意識的過程。如果多加注意當代日本人對本國國民史(時代區分上相當于近現代史)的反應就會明白,他們不僅對本國史缺少基本的知識和興趣,而且對“國民”這個歷史主體本身不知所云。因此無法理解中國國民對本國百年屈辱史的憤怒,甚至對反日游行的愛國活動感到害怕、驚訝。在這種情況下,當代日本人難以意識到自己的另外一個身份,即跟侵華戰爭有關的日本國民身份。
在二戰之后的中日關系史上,立足于共產主義或者人道主義的觀點來譴責本國政府的日本人應該不少,不過筆者擔心這些人往往將自己身份置之度外而進行空虛的批判,不知這種言行能否跟中方建立真正的信賴關系。但在日本戰敗至恢復邦交的一段時期中存在過認真思考日本國民戰爭責任的思想潮流,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思想家竹內好等組織的研究會“中國之會”。該研究會在戰后日本的中國研究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雖然其規模較小,通過其會刊《中國》將內容充實的各種文章提供給全國讀者;不同于自稱客觀中立的學術團體,它在其會刊上提起了例如“東亞同文書院”和“日本的社會主義者與中國”等專題,積極重溫在戰后日本社會被忽略的各種核心中日問題。正如在其臨時規定第六條“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思考中日問題”所明確表達的那樣,可以說“中國之會”是針對已經失掉歷史主體性及與其密切相關戰爭責任意識的戰后社會而出現的。但可惜的是,竹內好以中日恢復邦交為轉折決定解散該團體,后來在日本再也未出現過這種嘗試。
當代日本與國民主義
歷史的諷刺是,雖然在戰后日本社會里否定國民性的思想情緒仍然存在著,但“去國民化”的嘗試似乎完全失敗,并且其后果非常嚴重。正如安倍政權獲得日本老百姓的廣泛支持,如今日本社會里出現了明顯的右傾化現象,即根本否定戰后日本理念的草根性國民主義的抬頭。可以說,現在日本在戰后“去國民化”狀態和戰前“國民主義”狀態之間搖晃。那么,安倍政權的支持者們愿意以日本國民名義面對日本侵華戰爭的責任嗎?這些自稱愛國者的人們當然不敢承擔戰爭責任,因為對他們來說日本侵華戰爭本身并不屬于光榮國民史,就是說他們只能接受正面的、浪漫的、干凈的國民史。在他們眼里,無法看到沾滿血跡的東亞近現代史及其根本原因的日本國民主義,他們所崇拜靖國神社的“英靈”為何派到中國大陸,最后作為臭名昭著的侵略者被保衛祖國的愛國者們殺掉,這種重要背景也被忽略了。endprint
很明顯,上述所論的戰爭責任主體的問題不能通過庸俗的國民主義來解決,因為從為祖國而戰的圣戰的概念和戰爭責任的概念無法并存。在全球時代的國民國家(Nation-State)體制上,以媒體報道為緯、以國民歷史為經的國民身份在各國濃厚地存在著;它不同于埋沒在日常生活中的個人身份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同時能夠把他個人跟旁邊的他者聯起來而成立國民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不承認個人和本國的錯誤,積極地掩蓋壞事,站在個人身份上完全忽略或者隱藏國民身份的過去,這種“去國民化”的努力也不會有結果。國民主義對此會有一些批判,但它的毛病及其危害遠遠超過戰后日本的“去國民化”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到處充滿國民主義色彩的日本,“去國民化”的病狀同時并存,他們現在開始抱有對祖國日本的國民感情,但仍然對中國的愛國心感到反感。對中方來說,日方的這種矛盾心理應該很難理解,但筆者希望中方對此表示一定的理解,因為如今一旦在中國發生抗議日本的愛國行為,通過日本媒體刺激日方的國民主義,其針對日方反應的報道會再次刺激中方的國民主義,所以我們需要充分意識到這種對抗國民主義(Counter-Nationalism)惡循環的風險。
家族史的現實性
當然,我們在此無法回避另一個難題,即個人能否代國家謝罪的問題。在與侵華戰爭受害者的交流過程中,筆者逐漸理解了他們沒有要求這位年輕日本人替先輩抱歉的意思。筆者也試圖用委婉的方式表達一些歉意,但后來感覺這樣做也不太合適,因為筆者沒有資格代表國家或者加害者個人,如果擔任公職還是跟加害者有一些關聯的話,表示歉意也有一定的道理。當然也被拒絕過,但這些尊敬的老人愿意與一位日本年輕人見面,用慈愛的聲音給我講當時的事情,筆者對此已感到十分感激,不敢多言而保持沉默,只能感謝他們的接待。
筆者記得很清楚,比筆者大一個甲子的姥爺去世之前講的話,姥爺的存在在筆者的中國認識形成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1943年在東京的大學念書時,一位文藝青年被征去當兵,作為大日本帝國海軍下士兵去中國廈門,被分配到以擊落美軍航空部隊為任務的炮兵部隊。筆者想,作為海軍士兵分配到港口城市和作為陸軍士兵被分配到中國內陸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從心里感謝姥爺沒有被派到內陸。帶有傳統日本男子漢風格的姥爺,很愛跟我一起喝酒講講過去的事兒。我記得他驕傲地講擊中美軍飛機的情景,但關于他對當地人的待遇,除了跟他友好的一位富裕華僑之外沒有言及。現在無從知道,作為當時侵犯中國臭名昭著的日帝分子之一,他在廈門曾否犯過無法告訴愛孫的事情。我只知道的是,姥爺在去世幾個月之前的一天晚餐上,我大膽地提問他怎么看那場戰爭時,姥爺很認真地回答說“對于那場戰爭,我感到很抱歉,陛下也應該想的一樣”。姥爺在其人生最后一段時刻給孫子留言,對被他和同事們徹底蹂躪的中國國民表示歉意。
雖然在該文里主要討論的是國民史的脈絡,不過筆者認為通過家族史思考戰爭責任也許是更具體、現實、可靠一些。九一八事變以來,對中國人來說,這些鬼子們應該是一大批不可原諒的侵略者。但對在華日本人來說,來華之后重新認識在日本已被忘卻的這些歷史存在,也相當有意義。有趣的是,在抗日片中的主要壞人“日本鬼子”似乎已經變成在當代中國社會里最親近的日本印象,在華日本演員矢野浩二受歡迎一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還有如電影《南京!南京!》那樣,描寫一位日本士兵受到良心的譴責而自殺過程的作品也開始出現。可以說,作為“人”的日本士兵之出現也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中國國民對日本侵華戰爭看法的微妙變化。作為當代在華日本人之一,筆者當然對此有些好感,不過同時感覺最近歷史片,包括抗日片往往過于簡單化和娛樂化。回顧中國現代史就會明白,現實的皇軍比虛構的鬼子殘暴得多,將那一段歷史如實再現的話,恐怕無法在商業上成功。
在華日本人與戰爭責任
如上文所述,假如說中日關系已經開始從經濟時代轉向國民時代,而且目前日本在侵華戰爭責任問題上維持又曖昧又無禮的態度的話,在這種情況下,在華日本人到底應該怎么應對呢?一些中國朋友們同情地問過筆者,“中日關系已經變成了這樣,那你們在華日本人怎么辦呢?”這個提問點中了要害。這就是我們在華日本人自己要去認真思考的問題。尤其是2010年以來圍繞釣魚島歸屬問題中日之間發生一系列的糾紛之后,戰后穩定的中日關系受到前所未有挑戰的情況下,在中國長期逗留的日本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在華生活,其中不少已經正式回國,這些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過,建交以來逐漸建立起來的中日友好傳統也必須要繼續下去,我們不應該忘記當時為此盡力的“掘井人”及其成就。可以說,在華日本人面臨思考自己存在意義的關鍵時刻,他們需要一邊維持戰后中日友好的理念,同時站在當代日本人的立場上批判地分析中日關系的核心問題。當然,雖然日方也可以批判中方,但在缺少對自己充分認識的情況下,對對象的批判也往往缺少建設性,因此在華日本人也首先需要搞清楚自己的歷史位置,然后作為正視日本國民史的日本人才能跟中方一起討論上世紀的問題。
筆者的根本問題意識在于跟中國國民能夠交往的作為歷史主體日本國民之不在。極端地說,在中日問題上日方只有日本政府和各種個人來討論該題,也許有人會提問如今熱鬧的日本國民主義者如何,不過這種人的言論證明他們不理解國民史的兩面性,只求又正面又光榮的一面,完全忽略占日本國民史大部分的悲劇性內容,只不過是一種宅男化的國民現象,這里不會出現能夠跟中國國民對話的日本國民。筆者在這里所說的日本國民包括從親自殺害無辜中國國民的“日本鬼子”到對中日建交盡力的“掘井人”,它應該是這種不分善惡的國民綜合體,不應該偏向于一個方向而排除其他因素,這樣做才能真正以史為鑒地解決“去國民化”的矛盾。筆者認為,在當代日本人當中最合適于思考實踐這些問題的就是在華日本人,因為他們來華之后才能意識到當代日本人的認同感和中國觀之間的必然關系,從而從“去國民化”和“國民主義”這兩個極端日本思想潮流的束縛中擺脫出來,成為面對日本侵華戰爭責任的歷史主體才能獲得中方的尊重,最終在中日兩國之間能夠確立真正的信賴關系。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