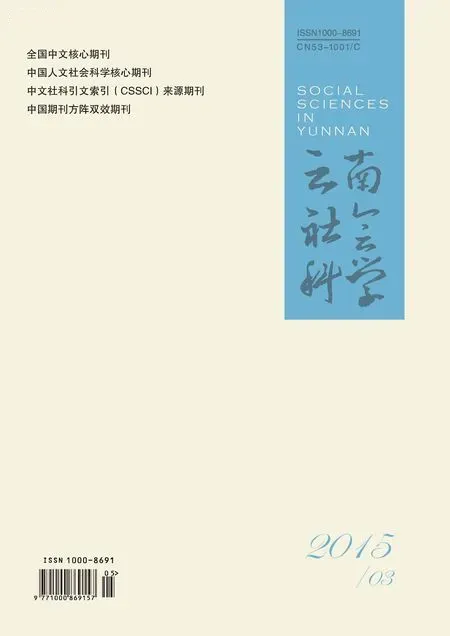展示的秩序:現(xiàn)代博物館空間的拜物幻象
18世紀(jì)晚期以來(lái),博物館日漸成為一種新的城市時(shí)尚。公共化是現(xiàn)代博物館區(qū)別于自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以來(lái)的珍寶館或私人收藏室的重要標(biāo)志。其中,1753年大英博物館的成立和1793年盧浮宮的對(duì)外開(kāi)放是這一民主浪潮最為顯著的代表。現(xiàn)代博物館的誕生,使藏品的所屬性質(zhì)發(fā)生了根本的轉(zhuǎn)變,即由私人走向公眾;與之伴隨的是,博物館空間中的視覺(jué)結(jié)構(gòu)和權(quán)力關(guān)系也進(jìn)行著調(diào)整,如藏品分類(lèi)、空間布局、視覺(jué)功能等。以托尼·本內(nèi)特(Tony Bennett)為代表的諸多博物館研究者援引福柯對(duì)19世紀(jì)初期知識(shí)型的考察,認(rèn)為現(xiàn)代博物館如監(jiān)獄、軍隊(duì)、醫(yī)院一樣,代表著古典知識(shí)型與現(xiàn)代知識(shí)型的變更。所不同的是,博物館翻轉(zhuǎn)了上述空間的可見(jiàn)結(jié)構(gòu)和表征方式。它面向一個(gè)偌大的市民群體,或者說(shuō)回溯性命名的、未有分化的國(guó)家公民,其主要功能不是隔離而是融合,通過(guò)物的秩序化展示,使博物館觀眾成為“合法”的主體。這是知識(shí)化的身份意識(shí),也是欲望化的自我指認(rèn)。博物館對(duì)物的展示發(fā)揮著教育功能,使進(jìn)入空間的觀者在身體的穿梭和視覺(jué)的游蕩中,發(fā)現(xiàn)“人”的進(jìn)化史以及自我作為普遍的大寫(xiě)的人的一員的優(yōu)越。然而,這個(gè)普遍性以及總體性的人,卻是博物館的分類(lèi)和排列所形成的幻象,因?yàn)槊褡鍞⑹潞蛧?guó)家意識(shí)形態(tài)已內(nèi)嵌到了表征過(guò)程中。主體化的過(guò)程,既是自我與他者的區(qū)分,也是自我內(nèi)部的劃分。前者是殖民的、階級(jí)的,后者則是趣味的、自我管理的。這就是說(shuō),通過(guò)空間中的物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個(gè)體成為主體,即成為國(guó)家的、殖民的、資產(chǎn)階級(jí)的、男性的主體。
現(xiàn)代博物館空間,這一現(xiàn)代性的文化景觀,通過(guò)看與被看的辯證結(jié)構(gòu),進(jìn)行知識(shí)生產(chǎn)和主體建構(gòu)。在眾多類(lèi)型,如自然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民族博物館等中,美術(shù)館的重要性在于,它凸顯也同時(shí)遮蔽了博物館關(guān)于人和國(guó)家的神話。美學(xué)作為一種去政治化的話語(yǔ),它重新規(guī)定了物的可見(jiàn)性,以及主體對(duì)物的觀看方式。于是,藝術(shù)變成了物的形式語(yǔ)言,準(zhǔn)確地說(shuō)是博物館使物如此這般顯現(xiàn)自身的原則。而物的藝術(shù)化既是現(xiàn)代博物館的展示技術(shù),也是其所要達(dá)成的一種非意識(shí)形態(tài)的效果。通過(guò)擴(kuò)展自身的范圍,藝術(shù)概念容納了原始物品,使之變成具有美學(xué)特征的藝術(shù)品,藝術(shù)史也就成了現(xiàn)代博物館的新的人類(lèi)學(xué)形態(tài)。雖然非西方他者仍舊被置入了自然與文明、低級(jí)與高級(jí)的種族主義話語(yǔ)系統(tǒng)中,但通過(guò)藝術(shù)之名,這些物似乎得到或分享了類(lèi)似西方藝術(shù)品的價(jià)值。
在物的轉(zhuǎn)換過(guò)程中,現(xiàn)代博物館通過(guò)拜物幻象實(shí)踐著價(jià)值的銘寫(xiě),賦予物一種藝術(shù)的價(jià)值。于是,物超出自身被升華了,成為具有意義深度的創(chuàng)造物,對(duì)它的欣賞是文化和趣味的象征。這不僅就主體自身而言,從更大層面來(lái)看,博物館對(duì)物的貯藏、保護(hù)、陳列具有展示國(guó)家形象的重要功能。
一、視覺(jué)的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yàn)
對(duì)于19世紀(jì)的視覺(jué)的文化史而言,博物館與拱廊街、博覽會(huì)、百貨公司、游樂(lè)市集等是相互建構(gòu)的,它們形成了一種視覺(jué)無(wú)意識(shí),移動(dòng)的目光與展示物的想象性關(guān)系。本雅明所揭示的“不準(zhǔn)觸摸”的原則,是人與物之間的新規(guī)范。物的使用價(jià)值退到幕后,在欲望化的觀看中,展示成了一種新的價(jià)值,交換價(jià)值的顯現(xiàn)需要借助于它而被推崇。
本雅明說(shuō),“世界博覽會(huì)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之地”①瓦爾特·本雅明:《巴黎,19世紀(jì)的首都》,劉北成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3年,第13頁(yè)。,歐洲人不僅傾巢出動(dòng)去看商品,他們也去博物館這個(gè)新的公共空間中觀看物。在一種經(jīng)驗(yàn)的、類(lèi)比的意義上來(lái)說(shuō),這是與博物館有關(guān)的拜物幻象,尤為突出的表現(xiàn)為藝術(shù)品的拜物教。跟博覽會(huì)的娛樂(lè)性質(zhì)相比,博物館更為嚴(yán)肅,具有某種儀式的氛圍。雖然博覽會(huì)和博物館都是人群的聚集地,但博物館的儀式感與禁止性相關(guān)。從前屬于王室的私人收藏室變成了國(guó)家的公共機(jī)構(gòu),民眾得以進(jìn)入其內(nèi)部,分享對(duì)物的視覺(jué)上的占有。然而,物保持了它自身的嚴(yán)肅性,博物館內(nèi)部的一系列展示技術(shù)用于防止人群對(duì)這些珍貴物品的僭越。現(xiàn)在,權(quán)力的顯現(xiàn)不是通過(guò)物的不見(jiàn)和對(duì)人群的屏蔽,而是以可見(jiàn)的方式,博物館將權(quán)力以藝術(shù)化的姿態(tài)展示著。
現(xiàn)代博物館作為公共景觀,伴隨觀者性質(zhì)的變化,物的擺置和空間秩序也發(fā)生了改變,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觀者的位置;一是,博物館的功能。
在博物館由私人向公眾的轉(zhuǎn)變中,影響物的收藏和擺置的不再是個(gè)人的好奇心,而是對(duì)物的秩序化展示。這體現(xiàn)在空間布局,它必須敞開(kāi)、容納、引導(dǎo)和管理人群,而1851年英國(guó)舉辦博覽會(huì)時(shí)新建的水晶宮就成為這一空間的典范。在某種程度上來(lái)說(shuō),現(xiàn)代博物館對(duì)玻璃展柜的運(yùn)用,是與拱廊街和博覽會(huì)的櫥窗相得益彰的——形象直觀。即使那些沒(méi)有被安置在玻璃展柜中的物或藝術(shù)品,仍舊是以一種類(lèi)似的形象直觀的方式讓自身客體化,與觀者保持一定的距離。面對(duì)物,觀者通過(guò)它們?cè)谝曈X(jué)關(guān)系中的客體化,確認(rèn)自己作為觀察者的主體位置。而博物館內(nèi)的空間被改建,以減少其他因素對(duì)這種看與被看的主客關(guān)系的干擾。其中,墻面背景的設(shè)計(jì)、光線的調(diào)控、玻璃展柜的造型和標(biāo)簽文字的寫(xiě)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之相應(yīng),心理研究在博物館的空間設(shè)計(jì)中也發(fā)揮著一定的作用,這意味著物的展示具有了一種人的尺度,以確保物能更好地向人顯現(xiàn),易于被觀者感知。因此,秩序不只是形式上的美觀要求,它內(nèi)在的是一種空間和視覺(jué)的經(jīng)濟(jì)學(xué)。不僅關(guān)涉物,還關(guān)涉人,準(zhǔn)確地來(lái)說(shuō)是人對(duì)物的感知。通過(guò)秩序化的建構(gòu),博物館以視覺(jué)形式,在物的展示中向觀者傳遞知識(shí)。
秩序,借用福柯的話,“既是作為物的內(nèi)在規(guī)律和確定了物相互間遭遇的方式的隱蔽網(wǎng)絡(luò)而在物中被給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視、檢驗(yàn)和語(yǔ)言所創(chuàng)造的網(wǎng)絡(luò)中;只有在這一網(wǎng)絡(luò)的空格,秩序才深刻地宣明自己,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默默等待著自己被陳述的時(shí)刻。”②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xué)考古學(xué)》,莫偉民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1年,前言第8頁(yè)。現(xiàn)代博物館對(duì)物的展示潛藏著某種敘事,使物在系統(tǒng)中獲得定位。秩序組織起整個(gè)敘事,使空間時(shí)間化以順應(yīng)這種敘事的發(fā)展;同時(shí),時(shí)間空間化則意味著時(shí)間的變化通過(guò)空間或地點(diǎn)的分隔得以外化自身。這種秩序隱而不見(jiàn),它的不可見(jiàn)卻給予了物的可見(jiàn)性以支撐。在一定程度上,空間的封閉性與秩序的系統(tǒng)性的相似作用在于,讓展示中的物成為一種全景式的景觀。
秩序規(guī)定了物的展示,也規(guī)定了人群對(duì)物的觀看方式。在與物的相遇中,觀者的感知內(nèi)化了展示的秩序,他們不僅需要辨別物是什么,還要在物的并置中去發(fā)現(xiàn)它們的意義。區(qū)別與前現(xiàn)代博物館對(duì)稀奇和怪誕之物的迷戀,現(xiàn)代博物館不再是獵奇的場(chǎng)所,而是通過(guò)秩序化的展示建立了以物為中心的認(rèn)識(shí)論。博物館與全景畫(huà)、全景文學(xué)的共同之處就在于,關(guān)于世界的科學(xué)觀點(diǎn)。其中,人不只作為主體存在,也同時(shí)作為客體被感知。而現(xiàn)代博物館的功能,對(duì)物的整體化的展示,是通過(guò)視覺(jué)活動(dòng)進(jìn)行理性的啟蒙和教育。
現(xiàn)代博物館的拜物特征與這種物的認(rèn)識(shí)論有關(guān)。秩序掩藏了自身的人為性,造成物的自然呈現(xiàn)的幻覺(jué)。事實(shí)上,正如美國(guó)的博物館研究者史蒂芬·康恩(Steven Conn)所指出的那樣,“博物館展覽的設(shè)計(jì)者在系統(tǒng)地安排展品的同時(shí)也就創(chuàng)造了這些展品的價(jià)值。”③史蒂芬·康恩:《博物館與美國(guó)的智識(shí)生活,1876—1926》,王宇田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2012年,第24頁(yè)。現(xiàn)代博物館存在著一種價(jià)值誤認(rèn),對(duì)于商品拜物教來(lái)說(shuō),商品形式掩蓋了人類(lèi)勞動(dòng)在創(chuàng)造價(jià)值方面的作用,賦予物與物的交換一定的合理性。博物館的展示形式同樣造成了價(jià)值的誤認(rèn),那些物神般的物或藝術(shù)品,它們的價(jià)值是一種文化的效果,由博物館的符號(hào)編碼系統(tǒng)給予。
那么,展示秩序所依賴(lài)的知識(shí)體系提供了怎樣的全景式敘事呢?
現(xiàn)代博物館以物品為中心的展示依賴(lài)于人類(lèi)學(xué)所提供的歷史框架,具體而言是,達(dá)爾文的進(jìn)化論思想。也就是說(shuō),博物館的教化功能,通過(guò)物來(lái)認(rèn)識(shí)世界以及認(rèn)識(shí)人自身,是一種人類(lèi)學(xué)的知識(shí)空間。它使得包羅萬(wàn)象的物都被整合在一個(gè)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鏈條中,轉(zhuǎn)喻性的物的并置是這種敘事的形象語(yǔ)言。如開(kāi)篇所說(shuō),現(xiàn)代博物館代表著19世紀(jì)的新的知識(shí)型,即于現(xiàn)代知識(shí)型,“人是什么”其核心問(wèn)題之一,博物館在一定程度上也回應(yīng)了這個(gè)問(wèn)題。它以秩序化的展示勾勒人的進(jìn)化歷史,并賦予觀者主體的位置,去感知和理解人之為人的歷史過(guò)程。
在這個(gè)知識(shí)空間中,通過(guò)進(jìn)化論的敘事,人得以認(rèn)識(shí)世界和人自身。知識(shí)的傳播依賴(lài)于物的展示,作為實(shí)證的客體,進(jìn)化的秘密據(jù)此獲得自明性。在知識(shí)與物體之間存在著的拜物式的誤認(rèn),博物館制造了顛倒的幻象,使展示秩序賴(lài)以建立的知識(shí)和理論基礎(chǔ)避免了反思。博物館以人的秘密為基礎(chǔ)來(lái)展開(kāi)它的編碼系統(tǒng)的構(gòu)想,在對(duì)進(jìn)化觀念的感知中,人既是認(rèn)知的客體,又是知識(shí)的主體。對(duì)起源的回溯和物的編碼都圍繞著“人”的揭秘,進(jìn)化論提供了一個(gè)平面化的圖景,使得人不僅作為觀看者、認(rèn)知者,也作為一個(gè)由物到人的歷史想象的接受者。
敘事的展開(kāi)依賴(lài)于博物館中的視覺(jué)關(guān)系和知識(shí)條件。借助建筑本身的空間結(jié)構(gòu),對(duì)物進(jìn)行分類(lèi)和組合,而秩序建構(gòu)賴(lài)以成立的知識(shí)基礎(chǔ)卻是透明的。物的集中、分散、連接和顯現(xiàn)被空間化,博物館成了一種中立性的媒介,而已然被給出的知識(shí)卻又等待著觀者的發(fā)現(xiàn)。通過(guò)對(duì)物的觀看,發(fā)現(xiàn)自己的主體位置,也在物的展示中去客體化地感知人的歷史,并且只有通過(guò)物,關(guān)于人和世界的知識(shí)才能被發(fā)現(xiàn)。知識(shí)的訴求,是現(xiàn)代博物館區(qū)別于博物館前身諸種空間的主要標(biāo)志之一。知識(shí)不只是一種要達(dá)成的主體效果,它也構(gòu)成了空間本身的儀式感,使博物館與一系列現(xiàn)代展覽現(xiàn)象,如拱廊街、百貨公司、博覽會(huì)等區(qū)別開(kāi)來(lái)。
本雅明在關(guān)于巴黎的現(xiàn)代性研究中曾指出,“恰恰是現(xiàn)代性總在召喚悠遠(yuǎn)的古代性。這種情況是通過(guò)這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和產(chǎn)物所特有的曖昧性而發(fā)生的。曖昧是辯證法的意象表象,是停頓時(shí)刻的辯證法法則。這種停頓是烏托邦,是辯證的意象,因此是夢(mèng)幻的意象。商品本身提供了這種意象:物品成了膜拜對(duì)象。”①瓦爾特·本雅明:《巴黎,19世紀(jì)的首都》,劉北成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3年,第21-22頁(yè)。博物館作為一種新的城市景觀,也提供了辯證的意象,通過(guò)物的秩序展示,進(jìn)化論建構(gòu)了關(guān)于人的宏偉構(gòu)想——人是更高級(jí)、先進(jìn)、文明的產(chǎn)物。知識(shí)的烏托邦,以現(xiàn)代性的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和展示技術(shù),將古代納入到現(xiàn)代人的視野之中。物的拜物特征就在于它的曖昧的可見(jiàn)形式,即使之可見(jiàn)的具體的、歷史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隱藏了自身蹤跡,而博物館作為治理機(jī)器的意識(shí)形態(tài)功能也被物的景觀所遮掩。
二、空間中的身體規(guī)訓(xùn)
現(xiàn)代博物館通過(guò)物的展示傳播了人和世界的進(jìn)化知識(shí),秩序就呈現(xiàn)在物的分類(lèi)和進(jìn)化的時(shí)間鏈條中,以及觀者與物之間的視覺(jué)行為中——知識(shí)的內(nèi)化。然而,秩序同樣表現(xiàn)為博物館空間對(duì)身體的規(guī)訓(xùn),或者說(shuō)治理。秩序,既是物在空間中的擺置及其潛藏的進(jìn)化論敘事,也是一種空間治理術(shù),通過(guò)身體的規(guī)訓(xùn)來(lái)實(shí)踐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主體構(gòu)想。這意味著,展示的秩序包含物和主體兩個(gè)方面的相互作用。對(duì)參觀者而言,他們對(duì)物的看,已然是一種省略:主動(dòng)觀看者亦是被看的對(duì)象。
羅蘭·巴特關(guān)于埃菲爾鐵塔的寫(xiě)作,揭示了建筑空間中主動(dòng)與被動(dòng)交織的視覺(jué)結(jié)構(gòu)。從某種程度上來(lái)看,埃菲爾鐵塔作為19世紀(jì)最為著名的城市景觀之一,代表著某種現(xiàn)代性的視覺(jué)原型。現(xiàn)代博物館與之相似的是,在目光的集合中,在自身景觀化的同時(shí),人群也成了景觀。巴特寫(xiě)道:“當(dāng)我們望著它時(shí),它是一件物體;而當(dāng)我們?nèi)ビ斡[鐵塔時(shí),它就變成了一種目光,并因此構(gòu)造著作為其注視對(duì)象的、既伸展于又收攏于其腳下的巴黎。”②羅蘭·巴特:《埃菲爾鐵塔》,李幼蒸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3頁(yè)。觀者與被看物之間的流動(dòng)關(guān)系,是對(duì)建筑物空間的自反性說(shuō)明。這旨在揭示,人群不僅作為觀看者被構(gòu)想,他們也是空間中被看的景觀。
對(duì)現(xiàn)代博物館而言,觀看不只是知識(shí)行為,更為重要的是,他者的目光具有“監(jiān)察”和“管理”的功能。通過(guò)看與被看的交織,觀者被置入了空間的權(quán)力秩序中。他們必須調(diào)整自己的行為符合空間對(duì)主體發(fā)出的要求——秩序化。這既體現(xiàn)為一些強(qiáng)制性的措施,例如,著裝的規(guī)范、排隊(duì)的準(zhǔn)則、物品的寄存等,進(jìn)入博物館內(nèi)部后,觀者行為更依賴(lài)于目光的治理術(shù)。它的作用方式是將觀者暴露在被看的情景之中以完成自我的管理。
監(jiān)獄,和博物館一樣,都是現(xiàn)代知識(shí)型的代表。前者依據(jù)邊沁的全景敞視主義建構(gòu)了空間內(nèi)部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無(wú)論目光來(lái)自某個(gè)具體的人還是一個(gè)空位,個(gè)體總是被看的。因?yàn)榭磁c被看是結(jié)構(gòu)化的,想象性的作用于被監(jiān)禁者。但是,博物館并沒(méi)有一個(gè)全能的視點(diǎn)位置,可以將人群納入其中。如果說(shuō)監(jiān)獄提供了一個(gè)垂直的視覺(jué)結(jié)構(gòu)的話,那么,博物館則具有平面化的空間性質(zhì)。這與物的展示的效果有關(guān),時(shí)間的空間化使得物的鋪陳是一種線性的漸進(jìn)鏈條。建筑本身造成了空間的不透明,柱廊和隔間的存在,打斷了視線的無(wú)限延伸。不過(guò),在一定的空間段落中,監(jiān)獄的透視關(guān)系也被引入,使管理者盡可能地看到展示物和逗留的、穿行的人群。碎片化的目光畢竟不能勝任監(jiān)獄瞭望塔的視覺(jué)功能,對(duì)于個(gè)體的規(guī)訓(xùn),需要借助于空間中的他者目光。這就是來(lái)自人群的目光,個(gè)體不僅被物包圍,還被目光所包圍。從這個(gè)角度來(lái)看,現(xiàn)代博物館與羅蘭·巴特筆下的埃菲爾鐵塔更為相近,它在世俗化的層面,把看與被看的相互性變成一種普遍的存在狀態(tài)。
鐵塔克服了看與被看的分裂,與瞭望塔的功能位置有所不同,后者更為突出了個(gè)體處于絕對(duì)主體目光之下的被動(dòng)狀態(tài),前者卻賦予了一種相互性,即被看的存在境況作用于人們的觀看行為。看與被看的交織,目光在主動(dòng)與被動(dòng)的權(quán)力兩極中流動(dòng)不居,觀者也在客體和主體位置之間搖擺轉(zhuǎn)換。埃菲爾鐵塔與監(jiān)獄瞭望塔一樣有著總體化的視角,對(duì)于博物館而言,總體化的視角既是由現(xiàn)代學(xué)科的知識(shí)視野提供的,通過(guò)物的秩序化展示使世界和人都變成科學(xué)觀念下的風(fēng)景;又是由目光的辯證法所形成的,而看與被看不只是人與人的外在關(guān)系,更是自我內(nèi)部的我—他結(jié)構(gòu)。
博物館作為意識(shí)形態(tài)國(guó)家機(jī)器,通過(guò)物的展示發(fā)揮詢(xún)喚功能,使個(gè)體接受空間的權(quán)力秩序完成主體化的過(guò)程,這涉及主體的知識(shí)啟蒙和身體規(guī)訓(xùn)。
博物館不僅闡釋了人的秘密,還建構(gòu)了人的標(biāo)準(zhǔn)。在此,知識(shí)和權(quán)力是合一的,內(nèi)在于博物館對(duì)主體的塑造。在《詞與物》中,福柯指出現(xiàn)代知識(shí)型不同于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和古典時(shí)期的知識(shí)型,其標(biāo)志是人的誕生。被納入知識(shí)的視野的人,既是知識(shí)的客體,又是知識(shí)的主體。現(xiàn)代博物館在實(shí)現(xiàn)這一轉(zhuǎn)換的過(guò)程中,發(fā)揮著啟蒙和教化的作用,但其功能的實(shí)現(xiàn)是和19世紀(jì)眾多的娛樂(lè)機(jī)構(gòu)相競(jìng)爭(zhēng)的,這意味著,博物館需要在差異性的運(yùn)作中,標(biāo)識(shí)自身的可參觀性。作為現(xiàn)代性的整體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的組成部分,博物館在分享類(lèi)似拱廊街、百貨公司、博覽會(huì)以及市集的奇觀技術(shù)的同時(shí),有著自身特殊的權(quán)力作用方式。而在大學(xué)還未取代博物館之前,它是重要的知識(shí)媒介。
本內(nèi)特指出,博物館對(duì)“人”(Man)的建構(gòu)由一系列相互交織的演化系列,如地質(zhì)學(xué)、生物學(xué)、人類(lèi)學(xué)和考古學(xué)等,這是當(dāng)下社會(huì)等級(jí)最為明顯和可感的表述方式。①Tony Bennet,“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p.45 -46.進(jìn)化論有效地組織起連貫、清晰的敘事,賦予物品可確定的編碼意義。而人則是一種帶有目的論色彩的文明產(chǎn)物,當(dāng)觀者在物的鏈條中發(fā)現(xiàn)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時(shí),自身也分享了進(jìn)化的價(jià)值。不僅如此,對(duì)于人類(lèi)自身而言,低級(jí)向高級(jí)的發(fā)展仍在繼續(xù),觀者既是作為“人”,更是作為現(xiàn)代西方人而享有了某種權(quán)力。因?yàn)橹R(shí)和權(quán)力總是密不可分的,對(duì)于現(xiàn)代博物館而言,知識(shí)作為一種權(quán)力的產(chǎn)物,也參與到權(quán)力的再生產(chǎn)中,維持和鞏固社會(huì)的權(quán)力秩序。
權(quán)力的再生產(chǎn)體現(xiàn)在博物館對(duì)主體的詢(xún)喚中。在此,存在著一種拜物的幻象,通過(guò)空間的儀式營(yíng)造,物顯現(xiàn)自身的方式似乎自然而然,但作為已然被言說(shuō)的對(duì)象,知識(shí)化的物發(fā)揮著意識(shí)形態(tài)的功能,參與到主體的詢(xún)喚。展示中的物總體性的建構(gòu)了關(guān)于人的知識(shí),及其中所包含的權(quán)力,觀者在物的表象中看到了一個(gè)理想形象,并通過(guò)目光的交織,與他者身份相互映射,確證自己作為“人”的優(yōu)越位置。
但是,在建構(gòu)普遍的“人”的概念的同時(shí),其本身潛藏著諸多的偏見(jiàn)。與觀者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一樣,博物館雖然強(qiáng)調(diào)自身的公共屬性,向不同階級(jí)和性別的觀者開(kāi)放,但在這一同化表象下則存在著區(qū)分的運(yùn)作。既表現(xiàn)為博物館關(guān)于“人”的敘事,也表現(xiàn)在觀者的身體規(guī)訓(xùn)中。如英國(guó)社會(huì)學(xué)者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所說(shuō):“現(xiàn)代公共博物館不只涉及儲(chǔ)存藏品,而是關(guān)于知識(shí)、身份文化的等級(jí)秩序以及發(fā)展歷程等重要現(xiàn)代概念的展示臺(tái)。”②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當(dāng)代“可參觀性”的生產(chǎn)》,馮悅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154頁(yè)。在博物館的知識(shí)表述中,物的展示與殖民擴(kuò)張密切相關(guān),通過(guò)原始和現(xiàn)代的區(qū)分,進(jìn)化的觀點(diǎn)抹除或消減了它的暴力性。展示物的粗陋與簡(jiǎn)單是對(duì)原始民族的形象修辭,這些異域的他者作為歷史的遺跡存在,所要證明的是西方現(xiàn)代國(guó)家及其民眾的文化優(yōu)勢(shì)。在理想主體的構(gòu)想中,不是所有個(gè)體都能獲得代表文明頂點(diǎn)的身份位置,博物館作為意識(shí)形態(tài)國(guó)家機(jī)器,它對(duì)主體的塑造是以資產(chǎn)階級(jí)男性為典范的。因此,博物館借由物的秩序化展示,不僅要在民族和國(guó)家的層面上區(qū)分自我與他者,更要在社會(huì)內(nèi)部區(qū)分自我中的異己者,并試圖把他們都改造成符合意識(shí)形態(tài)規(guī)范的主體。
主體化的過(guò)程需要借助自我的治理或監(jiān)察來(lái)完成。為了占據(jù)理想化的身份位置,個(gè)體不得不使自己與之保持一致。個(gè)人以服從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主體要求的形式建構(gòu)自己的身份意識(shí)。通過(guò)模仿資產(chǎn)階級(jí)的行為舉止和生活趣味,參與到現(xiàn)代博物館塑造主體的權(quán)力作用中。這與觀者的被看狀態(tài)是密切相關(guān)的,也就是說(shuō),個(gè)體的主體化過(guò)程總是已然發(fā)生的(always-ready)。而博物館作為一種詢(xún)喚機(jī)器,當(dāng)它(實(shí)在的或想象性的)成為人們身體經(jīng)驗(yàn)的組成部分時(shí),無(wú)論進(jìn)入其中與否,它的展示秩序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主體的建構(gòu)。這是資產(chǎn)階級(jí)化的、理性的、自我監(jiān)察的,代表著19世紀(jì)以來(lái)新的生活方式和態(tài)度。
阿爾都塞指出:“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永遠(yuǎn)存在于一種機(jī)器及其實(shí)踐中。這種存在是物質(zhì)的。”①路易·阿爾都塞:《意識(shí)形態(tài)與意識(shí)形態(tài)國(guó)家機(jī)器(一項(xiàng)研究筆記)》,見(jiàn)斯拉沃熱·齊澤克、泰奧德·阿爾多諾等:《圖繪意識(shí)形態(tài)》,方杰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164頁(yè)。現(xiàn)代博物館對(duì)主體的塑造不僅借助建筑自身的物質(zhì)性,更重要的是展示物的物質(zhì)性。通過(guò)現(xiàn)代博物館的視覺(jué)技術(shù)建構(gòu)了升華的物的表象,物成為信仰和崇拜的對(duì)象。通過(guò)觀看、靜思、想象、理解、反思等行為,物向觀者呈現(xiàn)自身的同時(shí),也通過(guò)物質(zhì)性傳遞進(jìn)化的知識(shí)。關(guān)于物的知識(shí),調(diào)動(dòng)了觀者對(duì)物及其價(jià)值的認(rèn)同,這卻是一種拜物式的誤認(rèn)效果,讓觀者遺忘了意義生產(chǎn)的現(xiàn)實(shí)機(jī)制,投入到物的想象關(guān)系中。在主體化的過(guò)程中,知識(shí)的啟蒙和教化作用,是以欲望化方式作用于個(gè)體對(duì)物的信仰。因?yàn)樗峁┝艘粋€(gè)理想的人的位置,具有合法性和權(quán)力的主體。屈從于這個(gè)位置所聚合的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yǔ),有關(guān)國(guó)家、民族、階級(jí)和趣味等,個(gè)體陷入物的符號(hào)體系,將物誤認(rèn)為某種意義的實(shí)體,也將主體化誤認(rèn)為主動(dòng)獲得權(quán)力的方式,而不知自身已參與到意識(shí)形態(tài)機(jī)器對(duì)個(gè)體的規(guī)訓(xùn)中。
三、藝術(shù)品的凝視美學(xué)
博物館研究者大衛(wèi)·穆雷(David Murray)在《博物館的歷史和用途》一書(shū)中指出現(xiàn)代博物館的兩個(gè)顯著特征是專(zhuān)業(yè)化(specialisation)和分類(lèi)法(classification)。前者指19世紀(jì)興起的一系列專(zhuān)業(yè)博物館,如地質(zhì)博物館、自然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美術(shù)館等;分類(lèi)法則是指博物館通過(guò)物品的組織安排,讓某種關(guān)于世界的科學(xué)觀點(diǎn)可被理解。在這些專(zhuān)業(yè)博物館中,拜物幻象在美術(shù)館中達(dá)到了高潮,即通過(guò)美學(xué)的原則,圍繞藝術(shù)品形成了一種去政治化的觀看方式。而這早已被現(xiàn)代博物館普遍借鑒,使物品的展示不僅是秩序化的,還要符合藝術(shù)的要求。現(xiàn)代博物館的儀式氛圍,就與藝術(shù)化的形式有關(guān)。因?yàn)樗囆g(shù)以及藝術(shù)品在法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布爾迪厄所說(shuō)的文化慣習(xí)中,通過(guò)高雅/低俗等對(duì)立式建構(gòu)了自身的價(jià)值。
美術(shù)館的誕生和成型是一個(gè)漸進(jìn)的過(guò)程。盧浮宮作為第一座現(xiàn)代性的公共美術(shù)館,它為此后的美術(shù)館建設(shè)提供了典范,如西班牙的普拉多美術(shù)館和美國(guó)大都會(huì)藝術(shù)博物館。與19世紀(jì)初期眾多美術(shù)館的成立或?qū)ν忾_(kāi)放相應(yīng)的是,美學(xué)方面的理論研究在18世紀(jì)晚期已有重要發(fā)展。其中,康德于1790年發(fā)表的《判斷力批判》一書(shū)奠定了美學(xué)的基本學(xué)科性質(zhì)。他提出的審美判斷的四個(gè)契機(jī),即無(wú)利害的快感,無(wú)概念的普遍性,無(wú)目的的合目的性和無(wú)概念的必然性。這些規(guī)定意味著審美或趣味的問(wèn)題更加注重主體的心智能力(通過(guò)分離和凈化建構(gòu)理想的審美態(tài)度)以及對(duì)象的形式因素。美術(shù)館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康德美學(xué)的對(duì)應(yīng)物,因?yàn)椋悦佬g(shù)館為代表的現(xiàn)代博物館通過(guò)展示技術(shù)將擾亂人們觀看物品的因素盡可能去除了。視覺(jué)變得尤為重要,它不僅是直觀形象的感性器官,也具有把握內(nèi)在敘事的理性能力,還在空間對(duì)人群的規(guī)訓(xùn)和管理中發(fā)揮著重要的意識(shí)形態(tài)功能。與其他類(lèi)型的博物館不同的是,美術(shù)館強(qiáng)化了審美鑒賞的純粹性,視覺(jué)的其他功能都服從于直觀。這就是說(shuō),與內(nèi)化低級(jí)到高級(jí)、原始到文明的觀念相比,更重要的是肯定物的美或藝術(shù)價(jià)值。
如前所述,現(xiàn)代博物館對(duì)物的展示具有某種拜物的效果,仿佛物具有某種自足性,在轉(zhuǎn)喻和隱喻的語(yǔ)言鏈條中,自我呈現(xiàn)世界和人的秘密知識(shí)。同樣的癥候也存在于美術(shù)館中,并且是以藝術(shù)品拜物教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lái)。不只藝術(shù)品作為新的拜物對(duì)象被賦予極高的文化價(jià)值,美術(shù)館自身也成了拜物的對(duì)象,這既與建筑本身的形貌有關(guān)(在新建過(guò)程中美術(shù)館常常被構(gòu)想為城市的藝術(shù)地標(biāo));也是指它在藝術(shù)評(píng)價(jià)、知識(shí)傳播、趣味建構(gòu)等方面的作用。
美術(shù)館在命名“藝術(shù)”品使之升華為無(wú)價(jià)之寶時(shí),功能的產(chǎn)生有其歷史語(yǔ)境,而非空間本然的神秘力量。本內(nèi)特指出,“只有現(xiàn)代主義的到來(lái),美術(shù)館空間才假定了自身的價(jià)值性,它賦予藝術(shù)品一個(gè)分離的和自治的幻象,并要求觀者做出回應(yīng)。”①Tony Bennet,“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p.45 -46.也就是說(shuō),美術(shù)館的拜物幻象是在藝術(shù)實(shí)踐、美學(xué)理論和觀者鑒賞等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藝術(shù)自治的美學(xué)觀點(diǎn)就與這種相互作用密切相關(guān),并凝結(jié)在美術(shù)館的具體空間建筑之中。它代表著一種與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美與藝術(shù)的世界,其中,藝術(shù)品是與任何實(shí)用的功能相分離的。
本雅明在《巴黎,19世紀(jì)的首都》中指出,藝術(shù)自治的幻象是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構(gòu)想。他說(shuō)道:“異議者反對(duì)藝術(shù)屈從市場(chǎng)。他們集合在‘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旗幟下。從這個(gè)口號(hào)中產(chǎn)生了‘總體藝術(shù)作品’的概念,試圖使藝術(shù)脫離技術(shù)的發(fā)展。用于慶祝這種藝術(shù)的嚴(yán)肅儀式與讓商品大放光彩的娛樂(lè)是相反相成的。二者都脫離了人的社會(huì)存在。”②瓦爾特·本雅明:《巴黎,19世紀(jì)的首都》,劉北成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3年,第23頁(yè)。美術(shù)館成了藝術(shù)的庇護(hù)所,使脫離了商業(yè)與技術(shù)的純粹概念得以展示和實(shí)現(xiàn)自身。然而,藝術(shù)自治并不如它所宣稱(chēng)那樣,表征去政治化的審美態(tài)度和創(chuàng)作自由,實(shí)際上,藝術(shù)的純粹性已然包含了意識(shí)形態(tài)的訴求。這主要表現(xiàn)為對(duì)殖民歷史的遮蔽、階級(jí)的區(qū)分和國(guó)家形象的建構(gòu)。
首先,美術(shù)館對(duì)藝術(shù)純粹性的營(yíng)造,包括藝術(shù)品的展示和主體塑造兩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其核心是視覺(jué)的美學(xué)化。這就意味著,主體對(duì)藝術(shù)品的看不是隨便一瞥,需要在凝視中形成美的循環(huán),即藝術(shù)品作為美的客體,自我則是能夠感知藝術(shù)之美的審美主體。這一能力是文明教化的結(jié)果,美術(shù)館在塑造審美主體的過(gu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作為一種公共機(jī)構(gòu),它為觀者接觸藝術(shù)品提供了便利,普通大眾也可從中獲得審美體驗(yàn)。而美學(xué)或藝術(shù)方面的傳記和理論則幫助觀眾理解作品的藝術(shù)價(jià)值,掌握美的知識(shí)和鑒賞方法。美學(xué)化的視覺(jué)是歷史的產(chǎn)物,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其呈現(xiàn)方式在不同條件下也有所不同。對(duì)于美術(shù)館而言,它是主導(dǎo)性的視覺(jué)結(jié)構(gòu)。因?yàn)樗囆g(shù)的純粹性(無(wú)功利、無(wú)目的、無(wú)概念等)要求一種與之相應(yīng)的凝視來(lái)鑒賞藝術(shù)品,甚至是從非藝術(shù)品中發(fā)現(xiàn)其形式的美。布爾迪厄稱(chēng)之為“純粹的凝視”(pure gaze),它“能夠按照藝術(shù)品所要求的方式(亦即自在和自為的,以形式而非功能)來(lái)理解藝術(shù)品……與純藝術(shù)目的所促成的藝術(shù)生產(chǎn)者的出現(xiàn)密不可分,因而也與一個(gè)自主藝術(shù)場(chǎng)域的形成密不可分”③皮埃爾·布爾迪厄:《純美學(xué)的歷史起源》,見(jiàn)福柯、哈貝馬斯、布爾迪厄著:《激進(jìn)的美學(xué)鋒芒》,周憲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48頁(yè)。。
其次,這種純粹的凝視在其他博物館或者說(shuō)廣義上的人類(lèi)學(xué)博物館中,同樣影響著觀者對(duì)物的觀看。當(dāng)然,它只是作為一種觀看的可能,而非空間的主要功能訴求。雖然美術(shù)館也是一個(gè)知識(shí)化的空間,如藝術(shù)史在展品安排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但最為影響深遠(yuǎn)的是,它建構(gòu)了審美的純粹凝視。這成為物的一種可見(jiàn)方式,為其他領(lǐng)域的分析提供了視覺(jué)原型,它的意識(shí)形態(tài)性就表現(xiàn)在純粹凝視對(duì)歷史、階級(jí)和權(quán)力的遮蔽中。
例如,現(xiàn)代博物館的展品來(lái)源及其秩序安排等,都或明或暗地帶有殖民色彩。在空間敘事的建構(gòu)中,展示的秩序受到進(jìn)化論觀點(diǎn)的影響,所有的人類(lèi)族群都被放置在由過(guò)去到現(xiàn)在的時(shí)間鏈條中加以度量和比較。那些來(lái)自非西方的人類(lèi)學(xué)物品就成為建構(gòu)自我文明形象的重要證物。博物館以靜態(tài)的表征方式將這些物所指示的非西方族群固置在人類(lèi)文明的初級(jí)階段,美國(guó)博物館學(xué)者珍妮特·馬斯汀(Janet Marstine)曾評(píng)述道:“作為殖民化空間,博物館自然將‘原始’種類(lèi)歸為隱喻性的死亡——非西方文化處于拘禁的發(fā)展?fàn)顟B(tài),冰凍在時(shí)間的洪流里。”④珍妮特·馬斯汀編著:《新博物館理論與實(shí)踐導(dǎo)論》,錢(qián)春霞、陳穎雋、華建輝、苗楊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2008年,導(dǎo)言第17頁(yè)。
對(duì)于博物館敘事所依賴(lài)的普遍的歷史觀點(diǎn),其中潛藏的殖民等級(jí)結(jié)構(gòu)已遭到博物館研究者以及其他學(xué)者的批評(píng)。但是,許多博物館以藝術(shù)和美的形式將這些人類(lèi)學(xué)物品變成了藝術(shù)作品,并要求觀者以審美的態(tài)度做出回應(yīng)。康恩指出:“將某一物品看作是人類(lèi)學(xué)的一部分現(xiàn)在已然成為一種文化上的不尊重,而其中所暗含的假設(shè)便是‘美術(shù)’代表著人類(lèi)文化等級(jí)中的頂點(diǎn)。”⑤史蒂芬·康恩:《博物館與美國(guó)的智識(shí)生活,1876—1926》,王宇田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2012年,第274頁(yè)。為了克服這種文化政治上的偏見(jiàn),美和藝術(shù)成了一種補(bǔ)償?shù)拇胧Mㄟ^(guò)賦予那些原始物品藝術(shù)之名,被貶抑的他者族群也就獲得了文化上的贊美。這使得博物館的藝術(shù)品拜物教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化幻象,當(dāng)來(lái)自異域的某物被指認(rèn)為藝術(shù)品,或者被要求以美學(xué)化的視覺(jué)所觀看時(shí),它就超出了自身的物質(zhì)性被高估了。博物館是這一升華發(fā)生的儀式場(chǎng)所,仿佛具有某種“點(diǎn)石成金”的神秘力量,將物的美學(xué)形式顯現(xiàn)了出來(lái),而且只有通過(guò)博物館的展示,這些物品的藝術(shù)價(jià)值才得以實(shí)現(xiàn)。
去歷史的美學(xué)態(tài)度,使得這些被收羅來(lái)的物品成為國(guó)家形象的宣傳,當(dāng)博物館以保護(hù)和弘揚(yáng)藝術(shù)的口號(hào)來(lái)掩飾帝國(guó)主義的擴(kuò)張史以及將物品帶離原初語(yǔ)境所造成的意義誤讀時(shí),現(xiàn)代西方國(guó)家試圖通過(guò)藝術(shù)品的收藏和展示,進(jìn)行文化和政治上的宣傳。藝術(shù)品成了新的拜物對(duì)象,并參與到博物館尤其是美術(shù)館的拜物幻象生產(chǎn)中,在藝術(shù)品將美術(shù)館神圣化的同時(shí),美術(shù)館又把藝術(shù)品本身神圣化了。通過(guò)它們的相互建構(gòu),諸多抽象概念如藝術(shù)、國(guó)家、民族等通過(guò)藝術(shù)形象的方式被呈現(xiàn),借由美術(shù)館以及藝術(shù)品的物質(zhì)性,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主體的規(guī)訓(xùn)得以具體地展開(kāi)和進(jìn)行。
人類(lèi)學(xué)物品的藝術(shù)化,是博物館權(quán)力配置的效果,隨著物的意義編碼的轉(zhuǎn)變,此前那種物的認(rèn)識(shí)論,也由對(duì)知識(shí)和理性的強(qiáng)調(diào)變成了關(guān)于美的趣味的培養(yǎng)。這同樣導(dǎo)致了觀者內(nèi)部的分化。藝術(shù)和趣味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本——高雅與低俗的對(duì)立,與資產(chǎn)階級(jí)和勞動(dòng)階級(jí)之間的對(duì)立是平行的。博物館不僅展示了等級(jí)化的物,也通過(guò)目光的辯證展示了參觀人群的差異。除了穿著和行為等外在因素外,等級(jí)的區(qū)分更為重要的表現(xiàn)為對(duì)不可見(jiàn)的“藝術(shù)”的把握。
正是不可見(jiàn)的“藝術(shù)”使得展示中的物或藝術(shù)品被藝術(shù)地感知和欣賞。但是,物的藝術(shù)意義對(duì)于所有觀者而言,不都是可見(jiàn)的或無(wú)差別的感知現(xiàn)實(shí)。在藝術(shù)的可見(jiàn)化的視覺(jué)結(jié)構(gòu)中,精英和大眾成了難以調(diào)和的一組對(duì)立,前者以其所享有的文化優(yōu)勢(shì)往往成為后者的效仿對(duì)象。博物館提供了一個(gè)展示性的空間,在建構(gòu)了物的展示秩序的同時(shí),還建構(gòu)了階級(jí)和文化的等級(jí)差異,并為主體塑造提供了知識(shí)和審美的范型。
結(jié) 語(yǔ)
西方現(xiàn)代博物館的興起有著特殊的文化背景,是18世紀(jì)晚期以來(lái)一種新的城市經(jīng)驗(yàn),在與百貨商店、游樂(lè)市集、博覽會(huì)等現(xiàn)代設(shè)置的競(jìng)爭(zhēng)中,博物館明確了自身的功能,即通過(guò)物的展示傳播知識(shí)與藝術(shù)。作為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國(guó)家機(jī)器,它借助物的奇觀向觀者發(fā)出詢(xún)喚,而處身于這一空間也就意味著進(jìn)入了秩序?qū)ξ锏木幋a和身體的規(guī)訓(xùn)中。觀者不僅要感知物本身,更重要的是在物的排列中發(fā)現(xiàn)秩序賴(lài)以建立的知識(shí)意志——進(jìn)化論的人類(lèi)學(xué),以及當(dāng)下所具有的文化優(yōu)越地位。這既是博物館傳達(dá)給觀者的科學(xué)知識(shí),又是一種“人”的權(quán)力。雖然現(xiàn)代博物館面向所有市民開(kāi)放,并提供了關(guān)于普遍的人的進(jìn)化觀點(diǎn),但這個(gè)大寫(xiě)的人卻有著內(nèi)在的等級(jí)意涵,它不僅涉及階級(jí)和性別的區(qū)分,也包含族群和國(guó)家的區(qū)分。然而,美或藝術(shù)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抵銷(xiāo)或轉(zhuǎn)移了博物館在主體建構(gòu)中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偏見(jiàn)。與視覺(jué)的美學(xué)化(人類(lèi)學(xué)物品的藝術(shù)化和主體的審美化)相應(yīng)的是,博物館成了一個(gè)藝術(shù)自治的空間,并以藝術(shù)品拜物教的形式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博物館在物的展示中所產(chǎn)生的拜物幻象。
隨著社會(huì)發(fā)展,博物館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受到挑戰(zhàn),不過(guò)無(wú)論如何博物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景觀。面對(duì)博物館研究者對(duì)現(xiàn)代博物館的諸多批評(píng),如殖民問(wèn)題、性別問(wèn)題、精英主義等,關(guān)于博物館的轉(zhuǎn)型的討論是20世紀(jì)末開(kāi)始成型的新博物館學(xué)的重要課題。雖然對(duì)博物館的具體構(gòu)想還存在著較大的爭(zhēng)議,但在多樣性的拓展,如虛擬博物館、女性博物館和大學(xué)博物館,以及平等對(duì)話的吁求等方面已展開(kāi)了相應(yīng)的實(shí)踐和探索,博物館的形式和功能也將不斷變化。
- 云南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死緩適用的實(shí)然標(biāo)準(zhǔn)— —以213個(gè)刑事指導(dǎo)案例為基礎(chǔ)的實(shí)證分析
- 危機(jī)中的云南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
——以云南文山谷拉鄉(xiāng)布央語(yǔ)為例 - 漢籍《玉匣記》“六壬時(shí)課”之納西東巴文譯本述要
- 替代性“女人交易”
——從訪談再論自梳女的身份選擇與家庭結(jié)構(gòu) - 大湄公河次區(qū)域邊界效應(yīng)的實(shí)證研究
——以中泰、中越數(shù)據(jù)為例 - 農(nóng)戶參與合作社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陜西省楊凌示范區(qū)的數(shù)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