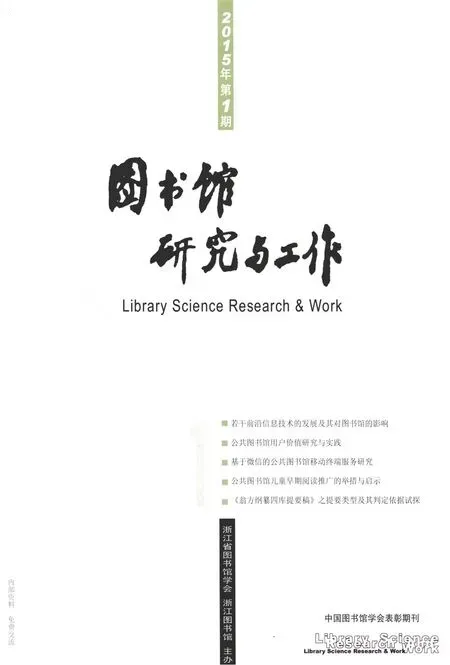《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之提要類型及其判定依據(jù)試探
許超杰
(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41)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以下簡稱“翁稿”)是翁方綱任職《四庫全書》館分纂官時所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初稿,共計千余則。《翁稿》對于研究《總目》編撰史、分纂稿與《總目》定稿之間的關系、分纂官與總纂官在《總目》編撰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有重要價值。但對于《總目》編撰來說,《翁稿》所包含的一千余則提要并不是處于同等地位,不同類型的提要稿是不同編撰時期成果的體現(xiàn)。要深入研究《翁稿》及《總目》編撰史,需要對《翁稿》進行分類。在此筆者試對不同類型的《翁稿》予以區(qū)分,并提出相應的判定標準。
1 《翁稿》所收提要及其類型
學界對《翁稿》分類的研究甚少,筆者目力所及,似只有張升先生有較為系統(tǒng)的論述。張升《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構成與寫作》一文認為《翁稿》寫作的對象主要包括兩方面的書籍:一是初辦之書,即四庫館初次分派給各纂修官首先辦理的圖書,由其擬寫提要并提出初步的處理意見。此為翁氏作為四庫館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的主要工作。二是分校之書,即四庫館臣擬定的應抄、應刊之書,在抄寫、刊印之前需要再次校勘一遍。即《翁稿》所涉及的書籍可分為初辦書籍和覆校書籍兩部分。①
張先生將翁方綱所校辦之書分為初辦書籍和覆校書籍無疑是正確的,但并不能將提要稿也相應地徑稱為初辦提要和覆校提要。我們知道無論是翁方綱為初辦書籍所撰的提要還是其他分纂官所撰的提要稿,都要經過總纂官的審定。若此提要稿大旨無誤,則雖仍會有所修改,然多為字詞、文句,無關宏旨,此可稱為初辦提要。若分纂官所撰提要稿不合于總纂官之看法,則多需要重改、重撰,這種重改、重撰之后的提要稿只能稱為修改提要。②《翁稿》中所錄的提要稿也不應該完全是初辦提要,很大一部分應該是不同時期的修改提要,這部分提要稿若稱為初辦提要就難免給人以誤解。是以,筆者認為將《翁稿》所收提要稿分為初辦提要、修改提要、覆校稿三部分較為合適。
2 初辦提要及其判定依據(jù)
張升說:“四庫館擬定的抄、刊之書,在發(fā)抄、刊印之前需要再校勘一遍。”〔1〕這些“指定的抄、刊之書”,即張先生所謂的分校之書,是指在發(fā)抄、刊印之前由分纂官覆校一遍的書籍,相應的這些書的提要稿就是覆校稿。覆校稿主要是校勘書籍之內容,間亦會對原提要稿作補充。關于覆校稿的判斷依據(jù),張升先生《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構成與寫作》一文已言之甚詳,筆者并無補充,不贅。在此,筆者試對初辦提要、修改提要及其判定標準予以探討。
《翁稿》所收三種提要稿,除去覆校稿即剩下初辦提要和修改提要兩部分。邏輯上說,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由于修改提要沒有明顯的標志,而初辦提要則有一定之規(guī)可尋,是以只要提出判斷初辦提要的標準,以之衡論,也就能夠判斷提要稿是初辦提要還是修改提要了。由于《四庫全書》提要編撰過程復雜,而現(xiàn)存相關資料又較少,是以要判斷具體某則提要為初辦提要或修改提要具有很大的難度。在此,筆者只能試提幾條判斷標準。
2.1 只關注所校版本信息、不符合《總目》標準者當為初辦提要
在校辦《四庫全書》之始,乾隆就對提要的內容作了規(guī)定,即需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2〕,但我們發(fā)現(xiàn)《翁稿》中頗有些只有關于所校書籍之版本信息,而無作者、內容介紹的提要。這部分提要很可能是初辦提要。
如“周易注并略例十卷”條曰:
《周易注》并《略例》,凡十卷,宋相臺岳珂刊本。每卷后有“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十字亞型方印。每頁末皆有“某卦”、“某篇”字,是倒折舊式也。每半頁八行行十七字。珂之自述謂,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略》,視廖瑩中世?堂本加詳。今世?堂本罕見,而岳氏此本之精善,應存以為校核之資。應先存此一部之目,以俟岳氏《九經》刻本匯于一處,而或刊、或抄之。纂修官編修翁方綱恭校。〔3〕
此條可視作翁氏對相臺本《周易注》最初的校閱意見,雖不符合提要之體例,但亦可視為初辦提要。《翁稿》中只關注版本信息而不符合提要體例者,蓋可視為初辦提要。
2.2 不必存目者必為初辦提要
翁方綱等分纂官在校閱書籍、撰寫《翁稿》時,需要對初辦圖書提出校辦意見,分為刊刻、抄錄、存目、不必存目、禁毀五種。因為《翁稿》是為纂修《四庫全書》而寫的,故只有刊刻、抄錄、存目的書籍需要不斷修改提要,使其日趨完善,而不必存目之書則無需修改。
當然,分纂官認為不必存目,而總纂官認為需要存目、甚至抄錄的書亦為數(shù)不少,如翁方綱認為《今易詮》、《周易旁注會通》等書不必存目,但《四庫全書總目》皆列為存目。但總纂官提出修改校辦意見后,必然需要重寫提要,而修改后的提要必不可能仍書為“不必存目”。是以,《翁稿》中列為不必存目的提要只能是初辦提要。
據(jù)此,《翁稿》經部所收的為《周易卦爻經傳訓解》、《易序叢書》、《易象解》、《顧氏易解》、《今易詮》、《周易旁注會通》、《十愿齋易說》一卷《易箋》一卷、《周易闡理》、《詩經六帖重訂》、《禮樂合編》、《春秋道統(tǒng)》、《左逸》一卷《短長》一卷合刻、《讀四書叢說》、《轉注古音略》、《石鼓文定本》、《七太天然窮源字韻》、《五經字學考》、《重訂馬氏等音外集》一卷《內集》一卷、《善樂堂音韻清濁鑒》等書所寫的提要稿當皆為初辦提要。
2.3 《翁稿》評價與《總目》相差甚大者或為初辦提要
翁方綱在校閱初辦書籍之后,需要在《翁稿》中對此書的價值提出自己的評價。而《總目》則是通過總纂官審定之后,最終確定下來的評價。此二者之間頗有不合者,甚至二者的評價恰處于兩極。
如《六書統(tǒng)》一書,翁氏以為:
是書獨患六書未備,窮源溯流,先以古文之正,次以古文之變,又次以古文之可疑者,而大小篆咸輯其中,蓋不以篆體之先后為主,而全以取形、取義、取聲之所自為主。如燈取影,而水赴壑,使天下之字一一得其所歸宿統(tǒng)紀,而有的可指,信乎許慎之功臣而字學之總萃矣。……若其書之有資于字學,則不待言耳。應刊刻傳之。〔4〕
而《總目》則曰:
以六書論之,其書本不足取。惟是變亂古文始于戴侗而成于桓。侗則小有出入,桓乃至于橫決而不顧。后來魏校諸人,隨心造字,其弊實濫觴于此。置之不錄,則桓穿鑿之失不彰。故于所著三書之中錄此一編,以著變法所自始。朱子所謂存之正以廢之者,茲其義也。〔5〕
翁氏對于《六書統(tǒng)》評價頗高,以其為“許慎之功臣”,而《總目》則是“存之正以廢之”,二者的評價可謂各處其極了。若翁氏所書非初辦提要,而是經總纂官審定初辦提要后重作的重修提要的話,翁氏定當考慮總纂官之看法,二者之間對此書的評價必不可能差距如此之大,是以此條當為初辦提要。
《總目》與《翁稿》差異甚大者,可能存在三種情況:第一,重修提要由原纂修官撰寫,分纂官按照總纂官之要求按不同原則重新撰寫提要,與原稿態(tài)度相去甚遠;第二,重修提要可能由其他分纂官而非原纂修官撰寫;第三,某種書籍由不同分纂官分別撰寫初辦提要,《總目》選擇其中一種,而此種與別種相差甚遠。是以,提要稿與《總目》之間評價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判斷某條提要是否為初辦提要的依據(jù)。但需注意的是,《四庫全書》提要處于不斷修改的過程中,對于書籍的評價也會不斷變化,其中甚或會有前后期差異甚大者。是以,提要稿與《總目》之間的差異只能作為判斷的參考,而不能作為完全確定無誤的標準。
2.4 《翁稿》與《總目》所收版本不同者或為初辦提要
《四庫全書》館所收書籍主要包括內府藏書、各省呈進書、私人進獻本和《永樂大典》輯佚書等部分,這四部分所具圖書多有重疊,同一種書可能包括多種版本。不同的版本,往往由不同的分纂官各自撰寫提要,是以一種書具有多種不同版本的提要稿。因為《四庫全書》及《總目》最終只選取一種版本及提要稿,是以其他版本的提要稿可能因其不為《四庫全書》及《總目》所用而不再修改。故《翁稿》中所保存的這部分與《總目》版本不同的提要稿當是翁方綱的初辦提要。
如《翁稿》有“《周易旁注》十卷《前圖》二卷”一條,其文曰:
《周易旁注》十卷,《前圖》二卷,明朱升著。升字允升,號楓林,休寧人。至正中鄉(xiāng)試進士,授池州學正,明初征為翰林侍講學士。升于諸經皆有《旁注》,而《易》有《前圖》,圖凡八,其第八圖卷內全載元泰和蕭漢中《讀易考原》之文,而系以邵子之詩與“三十六宮圖說”,可謂知本矣。《旁注》十卷,初用《注疏》本,其后程應明更定從《本義》本,于是上、下經與十翼分卷。此本即程應明所更定者也。其解經取訓詁文義,使相接觸而已。應存其目。〔6〕
而《總目》此條曰:
《周易旁注圖說》二卷(山東巡撫采進本) 明朱升撰。升字允升,休寧人。元至正乙酉舉于鄉(xiāng),授池州路學正,秩滿歸里。丁酉,太祖兵至徽州,以升從軍。吳元年拜侍講學士。洪武中,官至翰林學士,事跡具《明史》本傳。是書原本十卷,冠以《圖說》上下二篇,上篇凡八圖,下篇則全錄元蕭漢中《讀易考原》之文。萬歷中,姚文蔚易其旁注,列于經文之下,已非其舊。此本又盡佚其注,獨存此《圖說》二篇。漢中書已別著錄,余此八圖,僅敷衍陳摶之學,蓋無可取也。〔7〕
通過上文所錄《翁稿》、《總目》關于《周易旁注圖說》的提要可以發(fā)現(xiàn),翁方綱所校《周易旁注圖說》十卷全,并附有《前圖》二卷,而《總目》收錄者為只有《前圖》二卷之本,二者版本不同。同時比對二文可見,二者文字幾無相同,可知《總目》此則提要非翁氏所撰。翁方綱所據(jù)之版本較之《總目》本為全、優(yōu),何以《總目》舍此而取彼,為另一問題,另當詳考。但既然未被《總目》取用,則翁氏在撰寫此稿之后,當不會再次修改此則提要,則翁氏此稿當為初辦提要。
2.5 通過比對《翁稿》與進書提要、《總目》的關系判斷其是否為初辦提要
由于各省所進書籍皆附有簡單的提要,而分纂官所撰最初的提要稿很可能依據(jù)了這部分進書提要,是以進書提要與提要稿、《總目》的比較在一定程度上能為我們判定某則提要稿是否為進書提要提供幫助。現(xiàn)以《翁稿》所收《易領》一書為例,試說明初辦提要和后期修改后的提要的區(qū)別。
《翁稿》“易領”條收錄翁氏所撰提要兩則,為方便區(qū)分,名之易領甲、易領乙,錄下:
易領甲:
謹案:《易領》四卷,明郝敬著。敬字仲輿,京山人。萬歷己丑進士,官戶部給事中,謫知江陰縣。所著《周易正解》二十卷、《問易補》七卷、《學易枝言》二卷。是書專釋“卦序”之義。自序謂,冠以《卦序傳》,如衣之挈領,故以“領”名。其書雖主釋“卦序”,而于卦爻大意亦略舉其概,與所著《正解》有相發(fā)明者。其卷前標“山草堂集第二/內編”,蓋敬所著《九經解》皆入其全集,此書其集中之第二種耳。此本是從全集抽出者。卷末有闕頁。應存其目。〔8〕
易領乙:
謹案:《易領》四卷,明京山郝敬著。前有天啟乙丑敬自題辭,則又在所著《問易補》之后一年矣。止釋上、下經,每卦之首,冠以序卦,自謂如衣挈領,故以“領”名。應存其目。〔9〕
“易領甲”錄于影印本《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10〕第八冊第675頁,“易領乙”錄于第九冊第719頁,可知二者非同時所寫。對于“易領甲”、“易領乙”與《四庫全書總目》的關系,我們可對比《總目》和《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之提要:
《總目》:
明郝敬著。是書專釋“卦序”之義。自序謂,冠以《卦序傳》,如衣之挈領,故以“領”名。卷前標“山草堂集第二/內編”,蓋敬所著九經解皆入文集,此其集中之第二種耳。〔11〕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右前人撰。(筆者案:上《周易正解》條曰:“右明戶科給事中京山郝敬撰。”)每卦于彖、爻前冠以《序卦傳》,略加敷衍。自謂如著衣領,挈其領而前后襜如,故名。〔12〕
很明顯,《總目》之《易領》提要是刪略“易領甲”而成的,而“易領乙”則改編自《浙江采集遺書總錄》。是以,通過比較提要稿和進書提要、《總目》可以知道,“易領乙”當是初辦提要,而“易領甲”是修改提要。
上文所述《易領》是比較特殊的情況,因為《翁稿》中同時收錄了初辦提要和修改后的提要,故易于區(qū)分二者何為初辦提要,何為修改提要。但對于《翁稿》的大部分提要來說,一般每種書都只有一則提要,是以要區(qū)分其為初辦提要抑或修改提要甚為困難。只有深入比對《翁稿》和進書提要、《總目》之關系,才可判斷其是否為初辦提要。只能說與進書提要關系較為密切者是初辦提要的可能性較大,反之與《總目》較為接近者很可能是經過多次修改后的提要稿。
3 結語
《翁稿》作為《總目》研究最為重要的原始史料之一,只有在將其區(qū)分為不同類型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了解不同類型的提要稿在《總目》編撰中所處的不同時期,并進一步深入地發(fā)掘它所蘊含的價值,進而對《總目》編撰史作出科學、合理的探討。上文將《翁稿》之提要稿略分為初辦稿、修改稿和覆校稿三部分,并提出如何判斷初辦提要、修改提要之依據(jù)。以目前所具有的史料來說,這樣的分類和判定依據(jù)是較為合理、也是較易于付諸實踐的。但由于資料缺乏,要完全、精確區(qū)分《翁稿》中所包含的1093則提要稿的類型依然難以辦到,這仍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注釋
①張先生通過分析校閱單、提要稿內容、處理意見、分纂官之分工等,得出現(xiàn)存1093則提要稿中,初次校辦之書有972部,非初次校辦之書有121部。張先生并沒有將1093則提要稿何者為初辦提要、何者為覆校提要進行明確的說明,對于張先生對精確到個位數(shù)的對書籍類型的區(qū)分,筆者并不能接受。因為《翁稿》與《總目》的關系較為復雜,而張先生某些時候亦只是推測,如從分工看一節(jié),并不能將每一則提要稿都能完全明確地區(qū)分開來。
②因為分纂官在四庫館纂修提要時限于時間、資料等問題,對于館中寫完的提要必然需要修改、補充,這是難以避免的,這也不是筆者所說的修改提要。筆者所謂的修改提要是指經總纂官審定提出修改意見后再次重擬的提要稿,并非指常規(guī)修改。
〔1〕 張升.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構成與寫作〔J〕.文獻,2009(1):163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28
〔3〕〔4〕〔5〕〔6〕、〔8〕-〔9〕翁方綱,吳格.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1,119,352,25,34
〔7〕 〔11〕 永瑢.四庫全書總目〔Z〕.北京:中華書局,1965:50,60
〔10〕 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影印本)〔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
〔12〕 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采集遺書總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