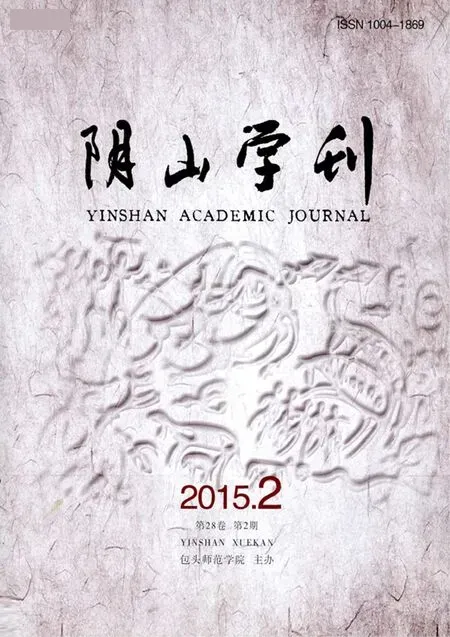公眾·社群·消費者:社會關系視野下的受眾研究*
徐 桂 權
(中山大學 傳播與設計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
公眾·社群·消費者:社會關系視野下的受眾研究*
徐 桂 權
(中山大學 傳播與設計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受眾研究是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從“受眾作為浮動的能指”的話語立場出發,大眾社會理論、自由民主理論、接受分析、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受眾經濟學五種理論話語建構了“大眾”、“公眾”、“社群”、“階級”和“消費者”等多樣的受眾觀念。與主流的、聚焦于個體態度、認知與行為的媒介使用與效果研究的話語相比,上述理論話語更關注社會關系中的受眾活動的意義,呈現出更廣闊的受眾研究的社會圖景,也為中國受眾研究拓展學術理論視野提供了參考的框架。
受眾;公眾;社群;消費者;社會關系
在歐美傳播研究中,受眾研究歷來是一個重要的子領域,形成了豐富的學術成果。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受眾”概念本身是媒介話語和學術理論話語建構的產物。正如麥奎爾所言:“媒介受眾是通過各種不同的‘邏輯’和話語而被建構和選擇性定義的”。[1](P143)卡彭鐵爾建議采用政治哲學家拉克勞和墨菲的話語理論[2],將“受眾”理解為一個“浮動的能指”,它在特定語境的不同話語中預設了不同的含義,并潛在地包含了不同的意識形態立場之間的領導權斗爭。[3]
沿著這一思路,本文擬從話語理論的角度對受眾研究的理論結構進行解析。有鑒于功能主義范式下的媒介使用與效果研究已成為受眾研究的主導話語、并將受眾個體的態度、認知與行為作為考察的重點[4],本文擬轉換視角,從大眾社會理論、自由民主理論、接受分析、傳播政治經濟學及受眾經濟學的話語梳理社會關系視野下的受眾研究,從而展現出“受眾”這一浮動的能指在社會關系諸話語中的多維表述。
一、 作為“大眾”的受眾:大眾社會的理論話語
大眾社會理論經常被視為傳播研究中第一個媒介——社會理論。在這個理論中,“受眾”被定義為脆弱的、原子化的大眾(mass)或聚眾(crowd)。“大眾社會理論”并不是一個嚴整的理論,而是一組社會學理論集合的標簽。大眾社會的理論話語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世紀的群體心理學對于大眾的理解。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著作《烏合之眾》被普遍視為大眾社會理論的路標。勒龐認為:“群氓”(crowd)指的是那些失去個性、理性和意志的人,他們可能帶來破壞性的危險。他就此寫道:“他們的統治總是無異于一個野蠻階段。文明需要穩定的統治—紀律,從本能狀態向理性狀態過渡,對未來的深謀遠慮,高度發展的文化——對于所有這些條件,群氓總是表現出:僅靠它們自己是沒有能力實現的”。[5](P19)勒龐并沒有在“群氓”與“大眾”之間做出區分,而是將他們等同起來。勒龐的著作反映了他對十八、十九世紀法國革命和歐洲社會運動的反思。他認為:大眾階級進入政治生活就意味著文明的終結,而只有精英能夠成功地完成社會管理的使命。
第二個階段是大眾傳播與宣傳席卷世界的20世紀上半葉。隨著媒介產業的擴散與戰爭宣傳的滲透,學者對大眾社會與大眾文化的批評變得更加尖銳。西班牙哲學家加塞特在他的《大眾的反叛》中追溯了“大眾人”(mass-man)的起源,并將“大眾人”在社會中的崛起視為高雅文化腐化的表現。[6]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宣稱:自由對現代人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從傳統權威中解放出來成為“個體”;但與此同時,他也變得孤獨無力地異化于自身,從而使他隨時準備服從于新的奴役。[7]在這個最糟糕的年代里,“大眾”無疑充滿了貶義,而“大眾社會”的理論話語也具有內在的批判性。
二戰之后,學術界出現了批判范式與實證主義范式并存的局面,這是大眾社會理論的第三個階段。批判的話語繼續對現代社會進行反思。里斯曼則在《孤獨的人群》中認為:戰后美國社會推動個體從“自我引導”走向“他人引導”的人格,大眾傳媒也在其中起到引導作用;而這種“他人引導”的人格可能導致大眾服從于意識形態與權力精英的操縱。[8]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中明確指出:美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精英已根據他們的利益構成了一個權力的聯盟,大眾傳播則是一個操縱人群的工具。[9]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經過數十年的建設,現代社會已經成為一個自由多元的民主社會。根據美國社會的調查結果,貝爾在一篇題為《大眾社會理論批評》的文章中認為:這種宏大的抽象理論以及對社會失序的模糊診斷是沒有意義的;這個國家的社會變化需要更仔細的考察。他的結論是:“大眾社會理論不再適合于描述西方社會,而不過是一種反對當代社會的、浪漫化的意識形態。”[10](P87)自上世紀60年代起,隨著功能主義成為社會學的主導范式,中層理論的建構成為學術主流,像大眾社會理論這樣的宏大理論則漸被拋棄。
盡管大眾社會的理論話語在戰后漸趨式微,“大眾”一詞卻已成為傳播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如“大眾傳媒”、“大眾傳播”和“大眾”本身。如今在傳播學論著中最經常被引用的“大眾”的定義來自社會學家布魯默的中性分析。作為芝加哥學派的一員,布魯默綜合了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觀點,認為“大眾”是現代工業、城鎮社會的新條件下的產物,尤其具有規模大、匿名和漂泊不定的特征。它通常是大量的、無附著的、彼此匿名的個體的集合,但對于個體接觸與控制之外的事物有共同的興趣。[11]這個“大眾”的定義是一個分析性的概念,沒有否定或肯定的判斷,因而在關于“大眾”的討論中更容易被接受。然而,到了網絡傳播時代,“大眾”的概念是否仍然具有意義,是當下涌現的又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
二、作為“公眾”的受眾:自由民主的理論話語
與大眾社會的理論話語相反,自由民主理論將人們視為民主社會中的“公民”與“公眾”。
在談到“公眾”的觀念時,李普曼和杜威是兩位經常被比較的政治思想家。在《民意》和《幻影公眾》中,李普曼認為:人們其實并不能直接認識“外在的世界”,而僅僅把世界作為“腦中的圖像”,因此他們對于“虛擬環境”的認識是扭曲的。由于普通公民無法理解客觀真實,并且民意僅僅是上層人士操作的刻板印象,李普曼認為參與民主是不能實現的,只有精英領導的代議制民主是可行的。[12]
杜威發表在《新共和》和《公眾及其問題》的評論并沒有否定李普曼關于專家制定政策的看法,但他主張民主不應限于管理者的啟蒙,而強調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公眾商議。杜威寫道:“我們不要求很多人都掌握調研的知識和技巧,但他們應具備判斷的能力,對其他人提出的共同議題做出評估。”杜威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因為公共商議要求受過更好的教育和組織化的公眾。他相信,民主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它總會朝著善治的方向進步。[13](P365)
李普曼—杜威的辯論集中體現了民主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沖突,已成為與傳媒和受眾研究相關的民主理論的經典敘述。然而,舒德森指出:實際上,李普曼與杜威之間并沒有真正發生過交鋒,而只不過是對于公眾及其經常出現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李普曼—杜威的“辯論”的敘述是在上世紀80年代和上世紀90年代建構起來的,當時的自由知識分子對于代議制民主的狀況感到不滿,并試圖尋找更多的民主參與,因而杜威的理念被視為復興公共生活的思想資源,而李普曼的理念則被抨擊為現行的官僚制度的依據。實際上,李普曼和杜威的話語都屬于自由民主的同一陣營,盡管他們各自宣稱不同程度的民主治理。[14]
二戰之后,美國的民主體制變得相對穩定,自由多元主義被廣泛接受為主流話語。這種樂觀的情緒也反映在預設了自由民主理論的輿論研究當中。例如,議程設置的研究發展了李普曼曾經提出的觀點,即新聞媒體提供的信息在建構我們對于現實的圖像方面發揮關鍵的作用。這個研究的貢獻在于,它解釋了“為什么某些特定議題的信息、而非其他議題的信息,對于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是有效的。”[15](P2)盡管議程設置研究聚焦于媒介議程、公眾議程與政策議程的具體關系,自由民主的理念已預設在研究當中,即新聞媒體應當成為輿論形成的平臺,并且政策議程應當對公眾議程作出回應。但是,通過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該研究把焦點從輿論與民主的規范理論轉移到關于新聞議題與受眾關系的經驗性考察。
三、作為“社群”的受眾:接受分析的理論話語
文化研究進路的接受分析通常被視為一種可與主流的媒介使用與效果研究相抗衡的替代性話語。對于接受分析,關鍵問題在于媒體建構現實的權力。正如威廉斯所言,“事實上不存在大眾,而只存在將人民看作大眾的方式。”[16](P289)在接受分析看來,受眾不應被看作無知的大眾,相反,他們作為意義的詮釋社群,對于媒介文本具有積極的解碼和抵抗的能力。
在接受分析中,霍爾的《編碼/解碼》被普遍視為一個開創性的研究。在這篇文章中,他批判了大眾傳播研究的“傳者—訊息—接收者”的線性模式,而以四個相關的環節取而代之:意義的生產、流通、分配或消費,以及再生產。每個環節都保持其獨特性,并有獨特的模態。這個思想受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關于商品生產與流通的論述的啟發,但在這里,霍爾將重點轉移到大眾傳播的話語形式,即電視節目作為有意義的話語的編碼和解碼過程。在受眾的一方,霍爾提出三個解碼位置的假設:主導解碼,即受眾對自然化和合法化的霸權觀點的認同;協商性解碼,即受眾接受過程中包含適從和爭議要素的混合;對抗編碼,則指受眾以完全相反的方式來解讀訊息。[17]
正如霍爾所指出的,解碼的假設需要經驗的檢驗和完善。在1980年出版的《全國觀眾》中,默利通過焦點小組研究,證實了階級立場與編碼之間的關聯。但是,默利并不把受眾的編碼簡單還原為階級立場。他寫道:“解讀總是分化為主導或對抗性意識形態的不同表述,以及聚焦于節目中不同的意識形態問題和話語模式”。[18](P266~267)在這個意義上,解碼分析要求更復雜的研究設計。
隨著大眾媒介的接受分析逐漸增多,這個研究領域的重點逐漸從編碼解碼模式的驗證轉向更多樣化的主題。默利在1986年出版的《家庭電視》中反思了《全國新聞》研究的局限:那些受眾研究不是在自然的家庭觀看環境中進行的;并且對于解碼的矛盾性的考慮也不充分。因此,家庭電視更關注觀眾在家庭環境中的電視使用和詮釋的深層結構,并且其分析更加靈活,而不再限于主導、協商和對抗解碼預設。[19](P28)這種從解碼到觀看語境的變化標志著這個階段的受眾民族志研究的重要發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一些學者開始反思受眾民族志的方法論前提。這種批評和反思提示了一種基于建構主義方法論的、關于受眾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的探索。這個階段的具體研究并沒有放棄受眾民族志,而是對跨學科和多元方法的探索持有更開放的立場,其目的在于將媒介、受眾與更廣闊的文化語境聯系起來。在這個建構主義框架之下,受眾的文化身份與文化消費成為重要的主題。阿伯克龍比和朗赫斯特認為:文化的商品化與“彌散的受眾”的形成密切相關:“一方面,所有的文化都成為商品,另一方面,所有商品都被審美化”;“這些過程產生的影響是受眾成為市場,而市場被建構為受眾。”[20](P98)在這個意義上,受眾作為詮釋社群是無處不在的,涵蓋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社會活動。近年來,受眾研究還涌現出其他多元化的研究議題,如文化公民身份與公眾參與, 兒童與青年的媒介素養,跨國受眾等,表現了受眾接受分析的持久活力,及其對媒介、受眾與社會之間的權力關系的持久關注。
四、作為“階級”的受眾: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話語
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通常被視為批判傳播研究的兩大陣營。對于傳播政治經濟學,其標志性的特征在于對階級權力的關注。與接受分析對象征權力的關注相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話語對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之間的相互建構給予了更多的關注,而“階級”則是政治與經濟兩個方面的話語節點。
作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斯麥茲的《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開創性地從階級關系的角度將“受眾商品”的概念帶入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認為:媒介工業生產的主要產品是受眾,因為媒介公司產生了受眾,然后將他們賣給了廣告商。[21]這個觀點將受眾視為階級權力控制下的商品和勞工,啟發了后來關于廣告受眾等諸多批判性的研究。莫斯可就此總結道:“受眾這個概念不像階級、性別、種族那樣是學術分析的范疇,而是媒介產業自身的產物。媒介產業用這個概念來識別市場,界定商品。”[22](P254)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努力是從階級的立場建構“公眾”的觀念。鑒于新自由主義在上世紀80年代西方媒介產業和媒介政策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認為,包括受眾研究在內的傳播研究應認真對待公民權與公共文化的議題。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概念被引入傳播政治經濟學之后,這個議題變得更加重要。韋斯特拉滕建議,公共領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不應限于制度架構和勞動過程,也必須將研究范圍從媒介訊息的生產延伸到接受與表意的政治經濟分析。[23]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接受分析的對話與調解仍在進行中。[24]
五、作為“消費者”的受眾:受眾經濟學的理論話語
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立場不同,媒介經濟學是在一個既定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中關注大眾傳媒的經濟面向。具體而言,媒介經濟學關注的是“媒介經營者如何以可資利用的資源滿足受眾、廣告商和社會的信息與娛樂需求”,以及“那些影響媒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因素”。[25](P7)根據這個定義,媒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兩個方面:媒介內容的生產,以及受眾對媒介的消費。而對于后者的分析即“受眾經濟學”的研究,在這里,“受眾”能指主要被建構為“市場”和“消費者”。[26]
沿著經濟學的邏輯,受眾細分是市場分析的必要環節。“市場上的消費者行為有千差萬別的個體偏好,但可以被假定為一些具有相似特征的群體或人口單位”,因此,“受眾研究試圖尋找和描述細分受眾的特征與其偏好的內容特征之間的關聯”。[27](P47)由于市場經濟是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受眾市場的分析也與社會經濟階層的范疇相關聯。所有消費者都可以通過若干種社會、經濟的方式來分類,并且受眾細分的有效性可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來進行衡量。
在受眾經濟學的話語中,作為商品的受眾變成一個中性的概念,并尤其通過讀報和收聽、收視率而典型地體現了媒介產業的經濟邏輯。米漢指出:“被生產和銷售的商品單單通過受眾評定來建構”;“交換的不是訊息、也不是受眾,而是收視率”。[28](P216)從這樣一個經濟視角來看,受眾不過是一組與市場有關的數字,而非具有獨特社會意義的人群。換言之,由于受眾經濟學將受眾還原為市場與商品,受眾作為社會行動者和政治參與者的意義都可能被經濟邏輯所遮蔽。
六、小結與討論
至此,本文已梳理了大眾社會理論、自由民主理論、接受分析、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受眾經濟學五種理論話語視野下的受眾觀念。與主流的、聚焦于個體態度、認知和行為的媒介使用與效果研究的話語相比,上述理論話語更關注社會關系中的受眾表現,包括其作為大眾、公眾、社會群體、階級和消費者的活動方式,從而呈現出更廣闊的受眾研究的社會圖景。
對于中國傳播研究者而言,上述多元的理論話語也為我們開拓中國的受眾研究提供了參考框架。經過三十多年的探索,中國受眾研究已取得豐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基于媒介使用與效果研究話語而展開的實證調查尤其引人注目。近年來,學界越來越意識到受眾研究需要更多理論維度的探索,尤其是對于公民、社會群體和消費者的多重意義的闡釋。因此,全面地理解西方受眾研究的理論話語,特別是社會關系視野下的受眾研究的脈絡,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打開學術視野,豐富中國受眾研究的發展思路。
[1]McQuail, D., Audience Analysis [M].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7.
[2]Laclau, E. & Mouffe, C.,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M]. London: Verso, 2001.
[3]Carpentier, N., ‘The Identity of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A]. Nico Carpentier, Caroline Pauwels & Olga Van Oost (Eds.) The Ungraspable Audience[C]. Grijpbare Publiek, VUB Press, 2004.
[4]O’Neill, B., ‘Media Effects in Context’ [A].V. Nightingale (Ed.) Handbook of Media Audiences [C]. Oxford: Blackwell, 2010.
[5]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M]. London: T. Fisher Unwin , 1909.
[6]加塞特.大眾的反叛[M].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7]弗洛姆.逃避自由[M].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
[8]理斯曼.孤獨的人群[M].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9]米爾斯.權力精英[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10]Bell, D., ‘The Theory of Mass Society: A Critique’. Commentary [J], 1956, volume 22 (1).
[11]Blumer, H. ‘The Mass, the Public and Public Opinion’ [A]. B. Berelson & M. Janowitz (Eds.) Reader in 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C].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3.
[12]李普曼.輿論學 [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13]Dewey, J.,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M]. New York: Holt, 1927.
[14]Schudson, M.,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and the Invention of Walter Lippmann as an Anti-Democrat 1986-199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 2008, vol. 2.
[15]Dearing, J. W., & Rogers, E. M., Agenda-setting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16]Williams, R.,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8.
[17]Hall, S., ‘Encoding/Decoding’ [A].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C]. London: Hutchinson, 1980.
[18]Morley, D., ‘“To boldly go…”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Reception Studies’[A]. P. Alasu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C]. London: Sage.1999.
[19]Morley, D.,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M]. London: Comedia, 1986.
[20]Abercrombie, N. & Longhurst, B.,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M]. London: Sage, 1998.
[21]Smythe, D. W.,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A]. Thomas Guback (Ed.)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C].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77.
[22]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 [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23]Verstraten,H. ‘The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 1996, Vol.11.
[24]Hagen, I. &Wasko, J. (Eds.), Consuming Audiences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in Media Research [C]. New Jersy: Hampton Press, Inc., 2000.
[25]Picard, R., Media Economics:Concepts and Issues [M]. London: Sage, 1989.
[26]南波利.受眾經濟學[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27]Gandy, O.H.,‘Race, Ethnicity, and the Segmentation of Media Markets’[A].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ition)[C]. London: Arnold and Oxford, 2000.
[28]Meehan, E., ‘Rating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 Third Answer to the Commodity Ques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J].1984,vol.1
〔責任編輯 韓 芳〕
Public, Social Group and Consumer:An Audience Study in the View of Social Relations
XU Gui-qua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udience research is a crucial area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Departing from the view of “audience as a floating signifier”, the discourses of mass society theory, liberal democratic theory, reception stud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audience economics articulate the audience’s identities as mass, pubic, social group, class and consumer. Such a broader landscape could be inspiring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audience research.
Audience; Pubic; Social group; Consumer; Social relation
2015-02-28
中山大學青年教師起步資助計劃“中外受眾研究的軌跡與趨勢”(17000-31121401)階段性成果。
徐桂權(1983-),男, 廣東廣州人,博士,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新聞傳播學研究。
G206.3
A
1004-1869(2015)02-0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