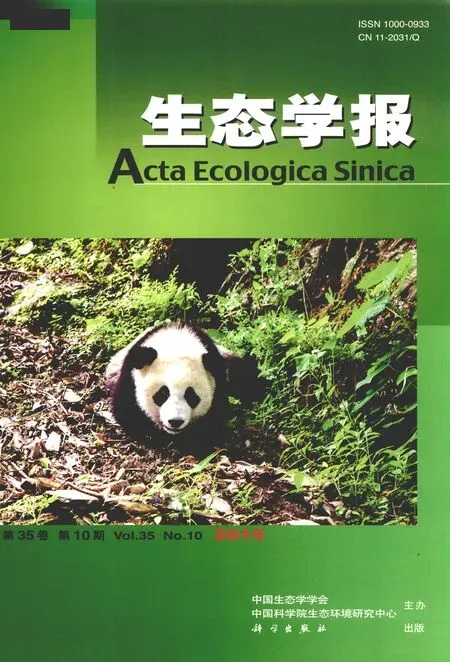烏蘭巴托—錫林浩特樣帶草地植被特征與水熱因子的關系
胡云鋒, 巴圖娜存, 畢力格吉夫, 劉紀遠, 甄 霖
1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 北京 100872 3 內蒙古自治區草原勘察規劃院, 呼和浩特 010051
烏蘭巴托—錫林浩特樣帶草地植被特征與水熱因子的關系
胡云鋒1,*, 巴圖娜存1,2, 畢力格吉夫3, 劉紀遠1, 甄 霖1
1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 北京 100872 3 內蒙古自治區草原勘察規劃院, 呼和浩特 010051
2012年夏季,研究人員對蒙古高原長約1100km的烏蘭巴托—錫林浩特草地樣帶開展考察,獲取了46個樣地的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等數據;基于全球GHCN(全球歷史氣象網絡)數據集,提取了樣帶夏季(6—8月)月均溫度和降水總量;繼而根據自然地理和行政區邊界,將草地樣帶大致分成北部(蒙古國烏蘭巴托—蒙古國艾日格)、中部(蒙古國艾日格—中國蘇尼特左旗)和南部(中國蘇尼特左旗—中國錫林浩特),開展了分析。研究表明:(1)樣帶夏季平均溫度的空間分布形態呈現明顯的倒“U” 型分布,南北兩端溫度較低,中部溫度較高;夏季降水量在空間上的分布形態則與之相反,呈現南北兩端降水量較高,中部降水量較低的正“U”型分布;(2)樣帶上植物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的空間分布形態均呈現正“U” 型分布,即在生態景觀類型為典型溫性草原的樣帶南部和北部地區,其生物多樣性、地上生物量明顯好于呈現為溫性荒漠草原、溫性荒漠景觀的樣帶中部地區。(3)相關分析體現了大尺度(高原樣帶尺度)上植被特征與水熱環境因子間的關系:植物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與夏季月均溫度均呈現負相關,而與夏季降水總量則呈現正相關關系。(4)偏相關分析反映了局地小尺度上植被特征與水熱環境因子間的關系:溫度和降水要素對于植物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均呈現正相關。
蒙古高原; 草地樣帶; 植被特征; 環境因子; 相關分析
草原植物的種屬、數量及生物量等指標是衡量草原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生產力和承載能力的重要參數,這些指標與環境要素間的關系是生態學家長期關注的問題。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上述草原植被特征對于環境變化的區域響應,更是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1]。蒙古高原是歐亞大陸上相對獨立的地理生態單元,總體上為典型溫性草原生態系統,也是我國北方重要的生態屏障。就蒙古高原草原植被特征及其與環境要素關系開展研究,對于探索蒙古高原區域生態系統分布格局及演化態勢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對于評估蒙古高原草地生態系統生態屏障作用具有重要實踐價值[2]。然而,由于地域廣大、國界分割、語言文字差異、野外工作環境艱苦等諸多原因,當前國內外研究人員對蒙古高原資源環境的研究并不十分透徹。
一方面,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內蒙古高原地區,對于蒙古國境內的研究相對較少。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大氣環流形勢、歷史氣候變化、沙塵天氣及一些特定植物物種區系分布、植物生理微形態學、種屬分支系統演化等[3- 7],此外還有一些關于高原植被生長和健康狀況分布格局、長時間序列植被參數對氣候變化響應、局地土壤風蝕速率測量、區域風蝕危險度評估等研究[8- 10]。總的來看,植物學家的分析常缺乏對蒙古高原總體分異規律的刻畫,而地理學家的大尺度分析則在第一手數據支持方面略顯不足。
其次,在目前大多數草原植被特征的研究中,由于生態系統的層次性和復雜性,特別是由于尺度推移效應,研究人員在不同地區、不同尺度上關于草原植物物種數量、生物量與環境因子間關系的認識并不統一[11- 15]。例如:白永飛的研究表明水、熱因子是影響內蒙古錫林河流域草原群落植物多樣性和生產力及主要因素[16- 17];胡云鋒、艷燕等的研究也表明:內蒙古東北—西南草地樣帶上,生物多樣性隨著水熱變化表現出明顯的梯度變化規律[18]。蔡學彩等根據內蒙古錫林河南岸大針茅草原樣地上的多年觀測數據分析,認為生物量與降水量的變化不存在顯著相關性[19];馬文紅等依據內蒙古高原113個樣地數據分析,認為降水是導致內蒙古溫帶草地生物量空間變異的主要因子[20];陳效逑等針對典型草原樣地開展研究,認為地上生物量對干燥度變化的響應非常敏感[21]。很多深入的研究還表明,環境因子中的降水因子在時間上的分布(季節分配、頻次、強度、間隔等)對于草地生產力有著重要影響[22- 28]。因此,在蒙古高原尺度上,草原植被特征與溫度、降水、干燥度等是否存在相關性?這有待于研究人員開展系統的采樣設計和分析研究。
針對上述科學問題,本文研究人員于2012年夏對蒙古高原烏蘭巴托—錫林浩特一線開展了野外綜合科學考察。考察采用樣帶調查方式,自西北向東南貫穿了整個蒙古高原。考察采用等間距采樣,對樣帶各點的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被、草地植物群落及農牧民生計等問題開展了綜合調研。本文即利用樣帶草地樣方調查成果,主要采用相關分析方法,對草地樣帶植被特征與水熱等環境因子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和建模。
1 研究區、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
蒙古高原以祁連山、賀蘭山和陰山山脈為南界,以唐努山、肯特山為北界,以阿爾泰山為西界,以大興安嶺山脈為東界;廣義的蒙古高原還包括陰山、黃河以南的鄂爾多斯高原。從行政區劃上看,蒙古高原大致包括蒙古國全部、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甘肅省北部、新疆自治區東部及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南部。由于四面遠離海洋,周圍為高、中山所環繞,蒙古高原呈現為山地與高原為主體的地貌格局,是亞歐大陸上一個相對封閉的內陸生態地理單元。
蒙古高原平均海拔1580 m,地勢整體自西向東、自南向北逐漸降低;除東部、南部少數地區外,其它地區年降雨量一般少于400 mm,是典型的大陸性干旱、半干旱區。本區土地荒漠化嚴重,沙塵天氣頻發,是影響我國華北乃至整個東亞的主要沙塵源區之一[29- 30];高原主要植被類型為草原,具體可分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和戈壁等幾個次級類型,并以典型草原分布面積最大。
1.2 樣帶設置

圖1 研究區及烏蘭巴托—錫林浩特草地樣帶示意圖
2012年8月20日至30日,研究組對蒙古高原烏蘭巴托、錫林浩特一線開展了科學考察。考察組成員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內蒙古草原勘察設計研究院、蒙古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草原監測站等單位。
野外考察起點為蒙古國烏蘭巴托市(Ulaanbaatar),終點為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市。在蒙古國境內,考察路線是沿著烏蘭巴托—二連浩特—北京國際鐵路沿線展開,在中國境內則是沿省道S101向東南方向展開。考察路線穿越了蒙古國中央省(Tov)、中戈壁省(Dundgovi)、戈壁蘇木貝爾省(Govi-Sumber)、東戈壁省(Dornogovi)以及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經過的主要城鎮包括:烏蘭巴托(Ulaanbaatar)、巴彥(Bayan)、喬伊爾(Choir)、艾日格(Airag)、賽音山達(Sainshand)、扎門烏德(Zanym-Uud),二連浩特、蘇尼特右旗、蘇尼特左旗、阿巴嘎旗和錫林浩特。路線全長約1100 km,海拔高程最低為887 m(蒙古國南戈壁省奧爾貢),最高為1650 m(蒙古國中央省巴彥)。
鑒于上述考察路線反映了蒙古高原氣溫、降水以及其它生態地理要素梯度變化的典型方向,因此該考察路線被定名為“蒙古高原烏蘭巴托—錫林浩特草地樣帶”(圖1)。進一步,根據自然地理和行政區分界,大致可以將上述草地樣帶分成北部(蒙古國烏蘭巴托—蒙古國艾日格)、中部(蒙古國艾日格—中國蘇尼特左旗)和南部(中國蘇尼特左旗—中國錫林浩特)。
1.3 數據獲取和預處理
針對蒙古高原地形坦蕩、生態地理單元尺度較大、生態景觀單一且連續過渡特點,考察采用等距離采樣方法,即沿著考察路線、每隔20—25 km開展一次踏勘采樣。植物樣方調查基本流程是:首先使用GPS測定經緯度和高程,使用數碼相機拍攝四至景觀及正下方草地樣方照片;而后在每個樣地做3個植物詳細樣方,記錄草地類型、草群高度、物種名稱、高度、蓋度、生物量等信息;最后在上述3個樣方周圍,隨機選取10個物種頻度樣方。經統計,共有46個樣地、近500個樣方,采集了約136份草地生物量樣品、2800余張相片。
氣象數據來源于美國NOAA網站所提供的GHCN(The Global Historical Climatology Network,全球歷史氣象網絡)數據集(http://www.ncdc.noaa.gov/ghcnm/)。溫度和降水數據的時間序列均為1950—2000年,其中降水數據來自全球47554個站點,溫度數據來自全球24542個站點;對上述觀測數據開展空間插值,最終形成了空間分辨率為1km、時間分辨率為1月的空間數據集。基于上述GHCN數據集,在ArcGIS環境中提取46個樣地所在格點的數據,得到各個樣地1950—2000年期間夏季(JJA:6—8月)逐月的溫度、降水數據。
1.4 分析方法
草地樣帶生物多樣性、生物量與水熱因子的關系主要通過事實描述和統計分析(簡單相關、偏相關和多元回歸)等方法進行研究。事實描述主要是基于氣象觀測數據、野外調查結果,通過簡單計算和制圖,在草地樣帶延伸方向上對各個樣地的物種數量、生物量以及氣候因子進行數據平滑、曲線擬合,說明其空間變化趨勢。統計分析是本文重點,研究中具體使用了簡單相關分析、偏相關分析以及多元回歸分析等3種統計方法。這些統計分析方法中所涉及的指標定義本文不再贅述,具體的統計分析工作是在SPSS(V17)的支持下完成的。
2 結果分析
2.1 氣候因子變化
夏季月均溫度在樣帶呈倒置“U” 型分布,而夏季降水總量在樣帶呈正的“U” 型分布,夏季平均溫度和降水總量在空間上的分布態勢正好相反(圖2)。

圖2 夏季平均溫度、降水總量的空間變化
樣帶北部,即蒙古國烏蘭巴托和蒙古國中央省地區,夏季平均溫度最低,為(16.3±1.5) ℃,樣地間的變異系數為9%;樣帶中部,即蒙古國東戈壁省賽音山達地區附近,夏季平均溫度最高,為(20.7±0.8) ℃,變異系數為4%;樣帶南部,也即中國錫林郭勒盟地區,夏季平均溫度較低,為(19.0±0.6) ℃,變異系數為3%。
與夏季平均溫度空間分布態勢變化正好相反,樣帶上夏季降水的空間分布則呈正的“U”型。即:樣帶北端夏季降水總量較高,為(166.8±27.0) mm,變異系數16%,樣帶中部夏季降水最低,僅為(94.9±12.0) mm,變異系數12.7%,樣帶南部夏季降水總量最高,為(167.7±17.0) mm,變異系數10%。
2.2 物種數量變化
樣帶上草原植物物種數在空間上大致呈現為南北高、中部低的“U”形分布(圖3)。
樣帶北部,即蒙古國烏蘭巴托和蒙古國中央省地區,平均每個樣地內有植物(21±4)種,樣地間的變異系數為18%;樣帶中部,即蒙古國東戈壁省賽音山達地區附近,平均每個樣地中出現的植物(13±2)種,其變異數為11%;樣帶南部,即中國錫林郭勒盟地區,平均每個樣地內有植物(20±3)種,其變異系數為14%。
上述事實表明,主要為典型溫性草原的樣帶南部、樣帶北部,其物種數顯著地高于呈現為溫性荒漠草原、溫性荒漠景觀的樣帶中部地區,樣帶北部和南部的生態系統更具生物多樣性。但是,從物種數量的局地空間差異(即樣地間的變異系數)上看,樣帶中部的荒漠草原和荒漠區的物種數量維持情況要比樣帶南北兩端的溫性典型草原區更穩定。
2.3 地上生物量變化
樣帶草地地上生物量在空間上的部分明顯呈現為南北高、中部低的“U”形(圖4)。
在樣帶北部,即蒙古國烏蘭巴托和蒙古國中央省地區,生物量較高,平均為(85±29) g/m2,樣地間的變異系數為34%;樣帶中部,即蒙古國東戈壁省賽音山達地區,生物量較低,平均為(62±31) g/m2,變異系數為50%;樣帶南部,即中國錫林郭勒盟地區,其生物量最高,平均約為(208±69) g/m2,變異系數為33%。
上述事實表明,主要為典型溫性草原的樣帶南部、樣帶北部,其地上生物量明顯高于呈現為溫性荒漠草原、溫性荒漠景觀的樣帶中部地區,樣帶南部和北部生態系統具有更高的地上部分生產力。并且,從地上生物量的局地空間差異(即樣地間的變異系數)上看,樣帶南部和北部地區的草原地上生物量穩定性要較樣帶中部更穩定;并且在同一區域上,生物量的空間變異程度明顯要比物種數量的空間變異程度要大得多。

圖3 樣帶物種數量的空間變化

圖4 樣帶地上生物量的空間變化
2.4 地上生物量與物種數量的關系

圖5 地上生物量與物種數量間的關系
據圖3和圖4,草地樣帶上地上生物量與物種數量遵循大致相似的變化趨勢,在空間上呈現南北高、中部低的“U”形分布。可以初步判斷,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針對樣地詳細樣方上的生物量—物種數量關系進行制圖(圖5),也可以清楚發現兩者之間存在正相關。但相關程度高低及是否能據此建立生物量—物種數量經驗模型,還需要進一步分析。
相關分析表明,在烏蘭巴托—錫林浩特草地樣帶尺度上,樣地地上生物量與物種數量程序顯著正相關(r=0.467,P=0.01),即隨著草地植物物種數量的增加,樣帶上草地地上生物量也會相應升高。但是,線性回歸分析得到的決定系數(R2=0.2174)并不大,即僅有22%的地上生物量變化可以通過物種數量變化來解釋,回歸模型的擬合程度相對較低。這也表明,決定樣地地上生物量的決定性因子可能并不是物種數量,而是具體的草地植物物種類型等其他因素。
2.5 物種數量與溫度、降水的關系
針對樣地上的物種數量及相應點位的溫度、降水因子開展簡單相關分析(表1)發現:樣帶上物種數和夏季月均溫呈顯著負相關關系(r=-0.363,P=0.013),即樣帶上物種數量會隨著夏季月均溫度的升高而減少。物種數與夏季降水量偏呈顯著正相關(r=0.462,P<0.01),即樣帶上物種數量隨著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多。
但是,對樣帶上物種數與溫度、降水做偏相關分析(表1)則發現上述關系發生了變化。樣帶上物種數量和夏季月均溫之間關系逆轉,呈現極微弱的正相關關系(r=0.057),但是這種正相關關系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P=0.709);而物種數量與夏季降水量偏相關系數依然為正相關,但相關程度略有降低(r=0.313,P=0.037)。
顯然,簡單相關分析結果符合圖 6、圖3和圖4所展示的表象規律,也是大多數前人草原生物多樣性研究的一般性總結,即干旱少雨不利于草地物種數量的提高[17]。偏相關分析從本質上揭示了物種分布及數量與溫度、降水等因子之間的機理。即在溫度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降水增加毫無疑問可以增加物種數量;但是在降水條件相同情況下,溫度提升對于物種數量的提高仍然存在有限的作用(弱正相關,且未通過檢驗)。事實上,在青藏高原等高寒地區,溫度就是影響植物物種分布的重要因子[31];但在蒙古高原這種典型溫性草原區,影響物種分布的關鍵因子為水分,溫度的提升對于典型溫性草原物種數量的影響非常有限。

表1 物種數量與夏季平均溫度、降水總量的相關性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es in summer
*在 0.05 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 在0.01 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2.6 地上生物量與溫度、降水的關系
針對樣地上的草地地上生物量及相應點位的溫度、降水因子開展簡單相關分析(表2)發現:樣帶地上生物量和夏季月均溫呈負相關關系(r=-0.199),但未通過統計檢驗(P=0.185)。地上生物量與夏季降水量偏呈顯著正相關關系(r=0.560,P<0.01),即表明樣帶上地上生物量隨著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多。

表2 地上生物量與夏季平均溫度、降水總量的相關性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in summer
*在 0.05 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 在0.01 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對樣帶地上生物量與溫度、降水做偏相關分析(表2)后發現上述關系發生了變化。樣帶上地上生物量和夏季平均溫度之間的關系逆轉,呈現為顯著正相關、且相關系數很高(r=0.615,P<0.01)。地上生物量和夏季降水總量之間則也呈現相關系數更高的顯著正相關關系(r=0.745,P<0.01)。
顯然,簡單相關分析結果符合圖 7、圖3和圖4所展示的表象,驗證了大多數前人對草原地上生物量研究的一般性總結,即干旱少雨不利于草地地上生物量的增加[17, 32]。偏相關分析則從本質上揭示了地上生物量與溫度、降水等因子之間的機制。即在溫度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降水增加毫無疑問可以增加地上生物量;而在水分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溫度的提升也依然有利于促進植物生長,有利于地上生物量的增加,這種規律突出地反映在青藏高原等高寒草原地區[31]。
2.7 多元回歸模型的建立
相關分析已經表明了蒙古高原烏蘭巴托—錫林郭勒草地樣帶上草地物種數量(SC)、草地地上生物量(AB)等2個因子與夏季溫度(T)、夏季降水(P)等環境因子有著顯著的相關關系。進一步考慮到溫度和降水因子之間交互作用,即濕潤度水平(可表達為P/T)的影響,可以在SPSS軟件支持下,對征草地植被特征(物種數量和地上生物量)進行非線性回歸建模,最終建立基于溫度和降水特征參數的回歸方程。
方差分析表明,在P=0.005的顯著性水平上,基于夏季平均溫度(T)、夏季降水量(P)因子建立草地物種數量的回歸方程有意義。具體的回歸方程為:
SC=-15.294 + 1.226×T-0.29×P+ 1.798×P/T
該回歸模型的決定系數(R2)僅為0.233,這表明僅有22.3%的物種數量變化可以由溫度、降水和濕潤度因子變化來解釋,模型總體擬合程度較低。
分析還表明,在P=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基于夏季平均溫度(T)、夏季降水量(P)因子建立草地地上生物量的回歸方程有意義。具體的回歸方程為:
AB =-339.625 + 8.521×T+ 4.447×P-42.337×P/T
該回歸模型的決定系數(R2)達到0.605,這表明有60.5%的地上生物量變化可以由溫度、降水和濕潤度因子變化來解釋,模型擬合程度相對較好。
3 討論
3.1 研究尺度所致的不確定性
由于研究區域位置、研究尺度不同,研究人員對于草原植被特征(生物多樣性、植被生產力)與環境因子(溫度、降水)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結論多有不同[17, 31, 33- 35]。總的來看,在局地小尺度(站點、小流域尺度)環境中,溫度與水分與上述植被特征呈正相關,或者關系過于復雜而呈現為沒有規律;在水分制約前提下(典型者如蒙古溫性草原區),大尺度(長樣帶、高原尺度)環境中溫度因子與上述植被特征呈負相關,而水分因子仍然與植被特征呈正相關;而在溫度制約環境下(典型者如青藏高寒區),大尺度(長樣帶、高原尺度)環境中溫度、水分與上述植被特征均呈正相關。這充分體現了地學研究中的尺度推移效應,即研究區域、研究尺度的變化導致了不確定性[36]。
在本文研究中,由于目標樣帶跨度長,包含了多個生態地理亞區(草地類型區),同時采樣間隔較短、每個生態地理亞區內均有足夠數量的樣地,這對于以綜合的視角將局地小尺度研究規律和區域大尺度研究規律聯系起來,具有一定優勢。在研究方法上,簡單相關分析展現了樣帶尺度上的生態地理變化規律,而偏相關分析則主要揭示小尺度環境中(特別是水分制約環境中)草原植物生長的環境驅動機制。這個研究有助于認識研究尺度變化所致的不確定性。
3.2 分析要素所致的不確定性
本文使用了草原植物物種數量絕對值作為衡量生物多樣性的指標、地上生物量絕對值作為衡量生物生產力的指標,使用了夏季月均溫度和降水總量作為驅動生態系統特征參數變化的氣候環境指標。顯然,尚有許多重要生態特征參數和地理環境參數還未納入評估范圍。事實上,分析要素數量的多少和具體要素的選擇差異,也將會給有關研究結果帶來不確定性[35, 37]。
一方面,環境要素的選擇對于評估模型的具體形態及模擬精度會有重要影響。在蒙古高原這一水分制約環境中,針對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這2個草地植被特征參數,如進一步開展包括水熱條件在內的更多的環境因子,如將海拔高度、局地地形地貌、土壤類型、土壤養分和水分、風場強度和風向、太陽輻照等要素納入進來;或者是在考慮總量基礎上,進一步考慮時間動態分布特征(如降雨的時間分布);或者是進一步考慮各要素之間的協同、耦合作用(如顯性地分析溫度-水分耦合要素,即濕度/干燥度因子)。毫無疑問,這些深入的分析工作,將可得到更加復雜,但相關性更好、決定系數更大、可信度更高評估模型。
另一方面,草地植被特征參數的選擇對于評估模型的構建也會有重要影響。例如,研究已經表明,不同地區草地群落地上地下生物量的比例有很大不同,在一些地區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呈正相關,而另一些地區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沒有明顯相關性,甚至是負相關[37- 38]。因此,如果單獨考慮地下生物量、或者將地上和地下部分生物量同時考慮,蒙古高原樣帶草原生產力與氣候因子的關系可能會發生很大變化。此外,對于其它重要生態系統特征參數,如均勻度指數、植被蓋度、植被營養元素和指示同位素(如δ13C)等,這些生態系統特征要素與環境因子的關系會更加復雜,需要更加細致和深入研究。
4 結論
以長約1100 km的蒙古高原烏蘭巴托—錫林浩特草地樣帶為研究區,本文描述了夏季溫度、降水、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等要素的空間變化規律,分析了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等草地樣帶植被特征參數與水熱因子之間的相關關系,構建了相應的回歸模型,并對研究區域、研究尺度和分析要素變化所致的不確定性進行了討論。主要結論有:
(1)蒙古高原烏蘭巴托—錫林浩特草地樣帶上的夏季降水總量、物種數和地上生物量,呈現明顯的“U” 型分布,夏季月均度則呈現明顯倒“U” 型分布。生態景觀類型為典型溫性草原的樣帶南部和北部地區,其生物多樣性、地上生物量明顯好于呈現為溫性荒漠草原、溫性荒漠景觀的樣帶中部地區。物種數量的局地空間變異性,是樣帶南部、北部劣于樣帶中部;地上生物量的局地空間變異性,則是樣帶南部、北部好于樣帶中部。
(2)應用簡單相關分析方法,可以得到蒙古高原烏蘭巴托—錫林浩特樣帶尺度上植被特征與水熱環境因子間的關系:植物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與夏季月均溫度均呈現負相關,而與夏季降水總量則呈現正相關關系。應用偏相關分析,可以得到小尺度上植被特征與水熱環境因子間的關系:溫度和降水要素對于植物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均呈現正效應,溫度和降水的增加從本質上有利于植物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的增加。
(3)由于尺度推移效應,在不同地理區域、不同研究尺度上針對植被特征與環境因子間關系的研究會有差異。本研究通過較長的樣帶考察、較密集的采樣計劃,將局地小尺度研究規律和區域大尺度研究規律聯系起來,有助于認識研究尺度變化所致的不確定性。此外本研究還指出,分析要素數量的多少和具體要素的選擇差異,也將會給有關研究結果帶來不確定性。
[1] 陳靈芝, 錢迎倩. 生物多樣性科學前沿. 生態學報, 1997, 17(6): 565- 572.
[2] 葉篤正, 丑紀范, 劉紀遠, 張增祥, 王一謀, 周自江, 鞠洪波, 黃簽. 關于我國華北沙塵天氣的成因與治理對策. 地理學報, 2000, 55(5): 513- 521.
[3] 劉桂香, 趙一之, 徐杰. 蒙古高原鴉蔥屬植物分類和地理分布研究. 中國草地, 2001, 23(2): 12- 18.
[4] 王鐵娟, 趙一之. 蒙古高原繡線菊屬植物區系地理成分及其生態地理分布規律的研究. 植物研究, 2001, 21(2): 245- 251.
[5] 燕玲, 宛濤, 烏云. 蒙古高原蔥屬植物種皮微形態研究. 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 2000, 21(1): 91- 95.
[6] 徐杰, 趙一之, 田桂泉. 蒙古高原天門冬屬植物分支系統演化的研究. 內蒙古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 2003, 24(3): 325- 329.
[7] 王菱, 甄霖, 劉雪林, Batkhishig O, 王勤學. 蒙古高原中部氣候變化及影響因素比較研究. 地理研究, 2008, 27(1): 171- 180.
[8] 張雪艷, 胡云鋒, 莊大方, 齊永清. 蒙古高原NDVI的空間格局及空間分異. 地理研究, 2009, 28(1):10- 18.
[9] Zhang X Y, Gong S L, Zhao T L, Arimoto R, Wang Y Q, Zhou Z J. Sources of Asian dust and role of climate change versus desertification in Asian dust emissio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3, 30(24): 2272- 2272.
[10] 劉紀遠, 齊永青, 師華定, 莊大方, 胡云鋒. 蒙古高原塔里亞特-錫林郭勒樣帶土壤風蝕速率的137Cs 示蹤分析. 科學通報, 2007, 52(23): 2785- 2791.
[11] Waide R B, Willig M R, Steiner C F, Mittelbach G, Gough L, Dodson S I, Juday G P, Parmenter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species richnes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99, 30: 257- 300.
[12] Mittelbach G G, Steiner C F, Scheiner S M, Gross K L, Reynolds H L, Waide R B, Willig M L, Dodson S I, Gough L. What is the obser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es richness and productivity? Ecology, 2001, 82(9): 2381- 2396.
[13] 劉先華, 李凌浩, 陳佐忠. 內蒙古錫林河流域植被多樣性特點及其與氣候因子的關系. 植物生態學報, 1998, 22(5): 466- 472.
[14] 王國杰, 汪詩平, 郝彥賓, 蔡學彩. 水分梯度上放牧對內蒙古主要草原群落功能群多樣性與生產力關系的影響. 生態學報, 2005, 25(7): 1649- 1656.
[15] 鄭曉翾, 靳甜甜, 木麗芬, 劉國華. 呼倫貝爾草原物種多樣性與生物量、環境因子的關系. 中國草地學報, 2008, 30(6): 74- 81.
[16] 白永飛, 張麗霞, 張焱, 陳佐忠. 內蒙古錫林河流域草原群落植物功能群組成沿水熱梯度變化的樣帶研究. 植物生態學報, 2002, 26(3): 308- 316.
[17] 白永飛, 李凌浩, 王其兵, 張麗霞, 張焱, 陳佐忠. 錫林河流域草原群落植物多樣性和初級生產力沿水熱梯度變化的樣帶研究. 植物生態學報, 2000, 24(6): 667- 667.
[18] 胡云鋒, 燕艷, 阿拉騰圖雅, 畢力格吉夫. 內蒙古東北-西南草地樣帶植物多樣性變化. 資源科學, 2012, 34(6): 1024- 1031.
[19] 蔡學彩, 李鎮清, 陳佐忠, 王義鳳, 汪詩平, 王艷芬. 內蒙古草原大針茅群落地上生物量與降水量的關系. 生態學報, 2005, 25(7): 1657- 1662.
[20] 馬文紅, 楊元合, 賀金生, 曾輝, 方精云. 內蒙古溫帶草地生物量及其與環境因子的關系. 中國科學C輯: 生命科學, 2008, 38(1): 84- 92.
[21] 陳效逑, 鄭婷. 內蒙古典型草原地上生物量的空間格局及其氣候成因分析. 地理科學, 2008, 28(3): 369- 374.
[22] Fay P A, Carlisle J D, Knapp A K, Blair J M, Collins S L. Productivity responses to altered rainfall patterns in a C-4-dominated grassland. Oecologia, 2003, 137(2): 245- 251.
[23] Fay P A. Precipitation variability and primary productivity in water-limited ecosystems: how plants ‘leverage’ precipitation to ‘finance’ growth. New Phytologist, 2009, 181(1): 5- 8.
[24] Heisler-White J L, Knapp A K, Kelly E F. Increasing precipitation event size increases aboveground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in a semi-arid grassland. Oecologia, 2008, 158(1): 129- 140.
[25] Zhang B C, Cao J J, Bai Y F, Zhou X H, Ning Z G, Yang S J, Hu L. Effects of rainfall amount and frequency on vegetation growth in a Tibetan alpine meadow. Climatic Change, 2013, 118(2): 197- 212.
[26] 白永飛. 降水量季節分配對克氏針茅草原群落初級生產力的影響. 植物生態學報, 1999, 23(2): 155- 160.
[27] 王玉輝, 周廣勝. 內蒙古羊草草原植物群落地上初級生產力時間動態對降水變化的響應. 生態學報, 2004, 24(6): 1140- 1145.
[28] 周雙喜, 吳冬秀, 張琳, 施慧秋. 降雨格局變化對內蒙古典型草原優勢種大針茅幼苗的影響. 植物生態學報, 2010, 34(10): 1155- 1164.
[29] Uno I, Wang Z, Chiba M, Chun Y S, Gong S L, Hara Y, Jung E, Lee S S, Liu M, Mikami M, Music S, Nickovic S, Satake S, Shao Y, Song Z, Sugimoto N, Tanaka T, Westphal D L. Dust model intercomparison (DMIP) study over Asia: Overview.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2006, 111(D12), doi: 10.1029/2005JD006575.
[30] Zhang X Y, Gong S L, Zhao T L, Arimoto R, Wang Y Q, Zhou Z J. Sources of Asian dust and role of climate change versus desertification in Asian dust emissio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3, 30(24): 2272- 2272. (本條文獻與第9條重復)
[31] 楊元合, 饒勝, 胡會峰, 陳安平, 吉成均, 朱彪, 左聞韻, 李軒然, 沈海花, 王志恒, 唐艷鴻, 方精云.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物物種豐富度及其與環境因子和生物量的關系. 生物多樣性, 2004, 12(1): 200- 205.
[32] 韓彬, 樊江文, 鐘華平. 內蒙古草地樣帶植物群落生物量的梯度研究. 植物生態學報, 2006, 30(4): 553- 562.
[33] 龍慧靈, 李曉兵, 王宏, 魏丹丹, 張程. 內蒙古草原區植被凈初級生產力及其與氣候的關系. 生態學報, 2010, 30(5): 1367- 1378.
[34] 馬文紅, 方精云, 楊元合, 安尼瓦爾·買買提. 中國北方草地生物量動態及其與氣候因子的關系. 中國科學: 生命科學, 2010, 40(7): 632- 641.
[35] 鄭曉翾, 趙家明, 張玉剛, 吳雅瓊, 靳甜甜, 劉國華. 呼倫貝爾草原生物量變化及其與環境因子的關系. 生態學雜志, 2007, 26(4): 533- 538.
[36] 李明財, 朱教君, 孫一榮. 植物對氣候變化生理生態響應的不確定性分析. 西北植物學報, 2009, 29(1): 207- 214.
[37] 鄢燕, 張建國, 張錦華, 范建容, 李輝霞. 西藏那曲地區高寒草地地下生物量. 生態學報, 2005, 25(11): 2818- 2823.
[38] 王長庭, 曹廣民, 王啟蘭, 景增春, 丁路明, 龍瑞軍.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物種組成和生物量沿環境梯度的變化. 中國科學C輯: 生命科學, 2007, 37(5): 585- 59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hydro-thermic factors along the Ulanbattar-Xilinhot Grassland Transect of the Mongolian Plateau
HU Yunfeng1,*, Batunacun1,2, Biligejifu3, LIU Jiyuan1, ZHEN Lin1
1InstituteofGeographicSciences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2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3InnerMongoliaRangelandSurvey&DesignInstitute,Hohhot010051,China
During August of 2012, the research team carried out a field exploration of the Ulanbattar-Xilinhot Grassland Transect on the Mongolian Plateau. The transect was split into three parts according to the physic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practical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the northern section (from Ulanbattar to Airag), the central section (from Airag to Sunitezuoqi), and the southern section (from Sunitezuoqi to Xilinhot). Along the 1100 km transect, 46 sample areas, 136 grass yield quadrats, and about 500 species-frequency plots were surveyed in detail and a series of species number data and above ground biomass data were then measured. Using GIS software and the GHCN datasets (The Global Historical Climatology Network), the historical meteorological data along the above transects were then extracted. The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s and total precipitation during the summer season (i.e., June, July and August)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data and hydro-thermic factor data, the correlation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were analy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stribution of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s in summer are presented as an inverted "U" pattern along the transect, i.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ections showing lower temperatures, while the central section maintained a high temperature level. Conversely, the distribution of total precipitation in summer is shown as an upstanding “U” pattern, i.e., high precipitatio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ections, with low precipitation in the central section; (2) the distribution of numbers of plant species and above ground biomass are both depicted as an upstanding "U" shape along the transect.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where the ecological type is typically warm steppe, both the bio-diversity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entral region, where the ecological type is usually warm temperate desert grassland or temperate desert; (3) simple correlation analysis normally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hydro-thermic environmental factors over large scales (for example, plateau transect). In this study, the numbers of plant species and above ground biomas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mmer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mmer precipitation; (4)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is inclined to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factors over a local scale (for example, small watershed). In this study, both the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factor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number of plant species and the ground biomass.
Mongolian Plateau; grassland transect;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 environmental factors; correlation analysis
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方向性項目(KZCX2-EW- 30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0971223); 科技部973計劃(2010CB950904)
2013- 08- 09;
2014- 05- 30
10.5846/stxb201308092051
*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huyf@lreis.ac.cn
胡云鋒, 巴圖娜存, 畢力格吉夫, 劉紀遠, 甄霖.烏蘭巴托—錫林浩特樣帶草地植被特征與水熱因子的關系.生態學報,2015,35(10):3258- 3266.
Hu Y F, Batunacun, Biligejifu, Liu J Y, Zhen 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hydro-thermic factors along the Ulanbattar-Xilinhot Grassland Transect of the Mongolian Plateau.Acta Ecologica Sinica,2015,35(10):3258- 3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