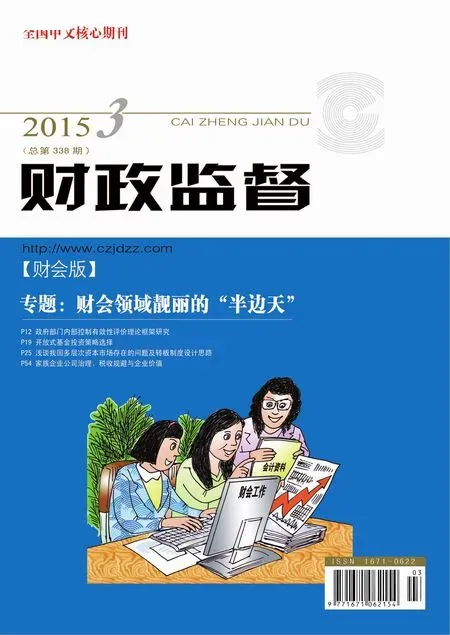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稅收規避與企業價值
——基于代理理論框架的分析
●浙江工商大學 顏淑姬
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稅收規避與企業價值
——基于代理理論框架的分析
●浙江工商大學 顏淑姬
本文基于代理理論框架分析家族上市公司稅收規避問題,首先從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了家族企業避稅偏好,實證發現家族企業存在一定的避稅偏好,但不顯著。接著從公司治理的三維:所有權結構、董事會結構、薪酬結構尋找影響家族上市公司避稅行為的因素。研究發現兩權分離度與避稅程度顯著正相關;兩職合一與避稅程度正相關但不顯著;股權分散、獨立董事與避稅程度正相關,說明并沒有發揮預期的權力制衡及監督的作用;董事會規模與避稅程度正相關,說明大規模的董事會反而導致監督乏力;高管高薪酬沒有發揮利益協同效應,長期機構持股及股票期權激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避稅程度。最后觀察了家族企業避稅與企業價值的關系,發現避稅程度與企業價值負相關,可能源于家族企業突出的代理問題。
家族企業 公司治理 稅收規避 代理理論
一、引言
對于企業而言,營業利潤的四分之一將作為稅收支出上繳給國家,是一項重要的成本開支,因此企業有強烈動機通過各種途徑去減少稅收支出。但是在我國,國有企業實現的利潤總額以及上繳的所得稅額均是高管業績考核的衡量指標,高管并沒有合理避稅的現實壓力;而對于家族企業而言,所得稅支出直接參與家族企業的財富分配,給企業帶來現實的現金流出,相比國有企業而言他們會有更強烈的動機去尋求避稅。國內外的一系列案例均已說明家族企業的避稅偏好。
貝因美屢次因非合理避稅被追繳稅款。2011年4月12日,貝因美以高新技術企業名義在中小板上市,同年9月披露因不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條件補繳稅款5892萬多元;2012年5月再次公告因前三年研發費用歸集不合理,補繳稅款2785萬元;同年還被查出存在銷售業務少繳稅收和會計核算不規范等問題,需補繳552萬稅款及滯納金。2011年8月15日據 《第一財經日報》報道青島亨達集團皮業發展有限公司在2007至2011這5年間假充外資企業享受“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據披露在2008至2010年期間涉嫌偷漏稅2631.38萬元。2008年韓國三星董事長李建熙因逃稅丑聞辭去董事長職務等。
避稅作為企業與國家之間的博弈活動,是財富在國家與企業之間又一次再分配過程,是以減少國家稅收收入為代價來獲得企業的節稅收益。而我國家族上市公司由于特殊的公司治理結構,導致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尤為突出 (陳德球等,2012;雷星暉,2011;賀小剛,2011等),避稅給企業帶來節稅收益的同時也會增加代理成本,如控股股東的尋租成本。對于控股股東而言,由于其較高的持股比例能分享更多的節稅收益,也因高控制權有能力利用避稅交易的復雜性及模糊性進行利益尋租,從而給廣大中小股東造成侵害。同時,由于控股股東的高持股比例、長持股期限及投資的非多元化使得其將承擔更多的因避稅失敗可能帶來的處罰、聲譽損失及股價下跌。理性的家族控股股東會權衡避稅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只有當邊際收益超過邊際成本時,才會采取激進的稅收行為。那么,家族企業避稅是否是普遍現象?是否比非家族上市公司避稅程度更大呢?家族上市公司不同的治理結構是否會導致避稅差異?是什么因素在影響家族上市公司的避稅行為?避稅到底是提升了企業價值還是減損了企業價值?本文試圖基于代理理論框架從公司治理角度探尋避稅動機的個體差異及避稅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及理論分析
(一)基于成本收益的避稅偏好分析。稅收是企業的一項重要的成本開支,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出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考慮,企業往往會聘請稅務顧問、進行外部稅務咨詢或內設稅務部門來進行稅收規避活動。避稅給企業帶來節稅收益的同時也會產生相應的成本,比如進行稅務咨詢的費用、制定籌劃方案的人力物力成本、籌劃方案可能產生的風險成本等以及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導致的非稅成本 (Scholes,Wolfson,Erickson, Maydew和Shevlin,2005)。但是對于家族上市公司而言,最大的還是因突出的第二類代理問題(陳德球等,2012;雷星暉,2011;賀小剛,2011等)而產生的非稅成本。
Desai等(2007)開辟了基于代理理論框架研究企業避稅行為的新紀元,其指出在稅務研究中考慮企業代理成本具有重大的理論及現實意義。是否避稅取決于企業對避稅產生的節稅收益與隱藏在其后的包括代理成本在內的非稅成本的權衡。對于企業而言,最大的收益在于節稅收益,控股股東因高持股比例可分享較多的節稅收益,控股股東還可能利用避稅交易的復雜性及模糊性獲取尋租收益。而非稅成本包括為避稅構造復雜交易的時間及努力成本,以及伴隨避稅交易的代理成本,避稅尋租被中小股東洞察而帶來的股價下跌成本,由避稅風險可能帶來的監管處罰成本及聲譽損失成本。
避稅主要通過對管理層尋租的反哺作用產生代理問題,引起代理成本。避稅交易因其自身的復雜性及模糊性難以被審計師和稅收監管當局發現,避稅交易越多,自利行為就越容易被掩蓋和實施,高管就能獲取更多的私利;而高額的尋租利益又會進一步激發高管層的避稅沖動。Dyrent等(2010)研究發現高管層一方面可以通過真實交易進行操縱性盈余管理來降低應稅收益,以達到減少稅收支出的目的;另一方面為降低應稅收益的交易背后可能隱藏著管理層的利益侵占行為。Desai等(2004)對Tyco公司、Cheng等(2005)對安然公司利用避稅交易操縱利潤進行了案例分析,均發現管理層確實通過避稅獲取了私利。
在一個有效的資本市場,當廣大中小股東發現高管層利用避稅進行利益尋租,則可以通過“用腳投票”來拉低公司股價,這對于代理沖突嚴重的家族企業也是致命的打擊,控股股東因高持股比例損失也將更大。控股股東持股期限長,投資非多元化,他們將為避稅風險長期買單,避稅如果被監管部門認定為違法,將帶來處罰成本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聲譽損失,這將影響企業的后續融資。因此,控股股東因避稅獲取高收益的同時也將承擔高風險成本,只有當邊際收益超過邊際成本時。避稅才是納稅人的理性選擇。
(二)企業避稅偏好的影響因素分析。公司治理會影響企業稅收行為(Desai等,2007),公司的管理和內部控制是稅收規避的重要影響因素(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影響家族上市公司的避稅行為呢?
所有權結構對避稅有重大影響 (Desai和Dharmapala, 2008)。Chen等(2010)研究發現家族上市公司由于股權高度集中,其避稅程度更為嚴重,因為其從避稅的節稅收益中分享的比例也更高,但同時也可能因高持股比例,長持股期限而承擔高比例的成本而降低避稅程度。Brad A.等(2013)研究發現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與公司避稅行為緊密相關,當所有權和決策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時,這些管理者會變得更加風險厭惡而不愿去投資于高風險的項目,而避稅活動往往存在很大風險,因此高股權集中度的公司稅收規避程度反而更低。機構持股會產生監管功能(Goergen和Renneboog,2001),但高的機構持股比例也會產生利益侵占行為(Hart,1995),機構持股是否會影響避稅行為則有待實證檢驗。
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家族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家族股東往往占有重要位置及比例,而家族控股股東往往又是決定避稅行為的重要人物,因此董事會結構必然會對公司避稅產生影響。Florackis(2008)認為獨立董事比例、董事會規模、兩職是否合一都會影響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關系。董事會規模對公司治理影響正反面結論都有,正面觀點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其所擁有的技能、經歷、資源就越豐富,越能發揮對CEO的監管作用。但是,大規模的董事會也容易導致溝通、協調、決策的低效率。Zahra和Pearce(1989)研究發現獨立董事因其自身的獨立性以及專業知識及經歷能發揮假設性作用,有助于緩解代理問題。Conyon和 Muldoon(2006),Haniffa和Hudaib(2006)基于社會網絡理論認為多席位董事會增強有效性,因為他們能接觸更多的社會資源,因在多處任職及多重背景容易帶來知識溢出。但是否會影響公司避稅有待實證檢驗。
薪酬激勵尤其是股票期權及績效工資將管理層的利益與廣大股東及公司的利益緊密聯系起來(Florackis,2008)。但是其是否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有待更多實證研究的進一步檢驗 (Fifth,Tam和Tang,1999)。只有 Desai和Dharmapala (2006)用非正常的稅會差異對績效報酬回歸后發現,在股東權益低及機構持股比例低的公司,兩者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因此,綜合文獻研究,本文從三個維度來衡量家族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分別是所有權結構、董事會結構、薪酬結構。所有權結構方面選擇股權分散度、控股股東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度、長期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來衡量;董事會結構方面選取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兩職是否合一來衡量;薪酬結構方面選取高管工資水平、是否實施股票期權激勵兩個指標來衡量。
(三)避稅與企業價值關系的研究。稅收負擔的減少就一定能提升企業價值嗎?按照傳統理論,避稅給企業帶來節稅收益的同時減少對政府的稅收支出,從而可以提升企業價值。但隨著委托代理理論被引入企業稅收行為研究,情況就變得更為復雜。高管層在進行稅收規避的過程中,為了不被稅務當局或審計部門發現,往往會采取一系列復雜的交易活動來掩蓋其避稅行為,在節稅的同時也由于交易的復雜及不透明性,加強了內外信息的非對稱性。這就為公司高管層利用信息非對稱性進行一些機會主義行為大開方便之門,比如:操縱性盈余管理、非公允關聯交易等等。在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的情境下,高管層不能完全分享籌劃所帶來的節稅收益,導致其開展稅收籌劃的動機并不與所有者完全一致。反倒激發了其利用稅收籌劃開展機會主義行為的動機(Chen等,2005;Desai等,2007)。從這一角度分析,稅收籌劃確實帶來了節稅收益,但也增加了代理成本。那么到底稅負的降低是提升了企業價值還是降低了企業價值,兩者關系并不明朗。理論上,只有當高管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得到有效抑制的時候,代理成本才會下降,稅收籌劃給企業帶來稅收支出減少的同時提升了企業價值;否則,過高的代理成本掩蓋了節稅收益,反而導致企業價值的減損。
Desai和Dharmapala(2009)基于美國資本市場的數據研究發現,平均而言,公司采取激進的納稅籌劃行為并沒有提升公司的價值,只有那些公司治理質量較好的公司,稅收支出的減少才提升了公司的價值。Halon和Slemrod(2009)的研究結論基本上與此一致,他們研究發現市場對企業激進的稅收行為反應顯著為負,只有在公司治理較好的企業中,這種負面反應才稍微緩和一些。
對于我國的家族企業而言,由于其特殊的治理結構導致其控股股東與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沖突比較劇烈,代理成本相對較高,節稅收益是否能超越代理成本,給企業帶來真正的盈利增長,尚有待實證的進一步檢驗。
三、樣本選取及避稅程度的衡量
(一)數據來源。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大部分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及色諾芬數據庫,重疊部分對兩者進行了比對檢驗。因避稅效果具有相對滯后性及較長期影響性,加上我國于2008年起實施新企業所得稅法,因此樣本選取為2008-2010年所有A股主板上市企業。剔除金融企業、PT和ST樣本、當年IPO或SEO的公司、當年凈資產為負及主營業務收入為零的樣本、數據缺失的樣本。共得到公司——年份的面板數據樣本2329個,其中家族上市公司(所選樣本家族上市公司其實際控制人均為家族自然人及其一致行動人)1364個,民營非家族上市公司(根據國泰安民營上市公司數據庫中去除自然人及家族控股以及國有控股)81個,國有上市公司884個。數據處理及回歸分析采用SPSS21.0統計分析軟件。
(二)企業避稅程度的衡量。根據Michelle Hanlon(2010)的綜述,主要有四種衡量指標:所得稅費用負擔率(ETR),現金所得稅費用負擔率(Cash-ETR),稅會差異(BTD),稅會差異的殘差項(residual-BTD)。
所得稅費用負擔率=所得稅費用/稅前利潤,該指標反映了稅會差異的永久性差異部分(如壞賬準備、優惠稅率等),但無法反映暫時性差異,比如固定資產折舊的加速折舊法,只是使稅負前后期轉移,總額是不變的,那么從較長期來考慮,是不會影響ETR的。
現金所得稅費用負擔率=現金支付的所得稅費用/稅前利潤,該指標同時反映了永久性差異和暫時性差異,不受應計制會計影響,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盈余管理的成分,避免前者對有效稅率的高估。
稅會差異是指會計利潤總額與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差異,應納稅所得額=(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資產增加額-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額)/名義所得稅稅率。隨著國內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額由于所遵循的法律依據不同,由制度差異帶來的永久性差異成分不斷擴大。稅會之間的差異除了有管理層避稅籌劃的部分,還包括了會計準則與稅法差異的制度性差異成分,以及管理層盈余管理的成分。用該指標來衡量避稅籌劃導致的操縱性差異存在一定的誤差。
稅會差異的殘差項是Desai和Dharmapala(2006,2009)提出的計量指標,其將稅會差異對總應計項目進行回歸,回歸的殘差視作無法被盈余管理行為所解釋的部分,當做避稅所導致的稅會差異部分,因此跟現金所得稅費用負擔率有異曲同工之妙。具體計算如下:應計項目總額(本文將會計利潤分為應計項目和現金流量,國外文獻中,常用的應計利潤計量通常借鑒Sloan(1996)等的 “折舊后經營利潤”以及Bath等(1999)的“非常項目前利潤”。本文借鑒上述第二種做法,根據數據取得的便利性,用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名義所得稅稅率作為非常項目前利潤)=非常項目前利潤-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非常項目主要包括減值、投資凈收益及營業外收支凈額。建立回歸模型,取值為回歸殘差項。
綜上,本文選取稅會差異的殘差項作為避稅程度的衡量指標,該指標越大,說明企業避稅程度越高。同時用現金所得稅費用負擔率做穩健性檢驗,與前相反,該指標越小,企業的避稅程度越高。考慮到避稅效果具有相對滯后性及較長期影響性,用后續三年平均值來加以衡量,即現金所得稅費用負擔率=3年現金所得稅費用之和/3年稅前利潤之和。
四、家族企業避稅偏好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從表1、表2統計結果可見,所得稅費用負擔率的均值及中位數都是家族上市公司最低,非家族民營上市公司其次,國有上市公司最高,符合預期。稅會差異及稅會差異的殘差項都是家族上市公司最高,其次是非家族民營上市公司,最低是國有上市公司,與預期一致。但在統計上均不顯著。說明在我國家族上市公司確實存在一定的避稅偏好,但是兩者差異不明顯。這跟Chen等(2009)研究結論相反,他們通過美國家族上市公司的樣本研究發現,美國的家族上市公司并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采取更為激進的稅收政策,他們更看重避稅遭受處罰帶來的家族聲譽損失以及由此帶來的股價下跌。這跟他們較完善的稅收征管體系及更為嚴厲的稅收處罰密切相關。而我國稅收體系尚在不斷完善過程中,執行不力、處罰不嚴導致企業避稅的非稅成本相對較低,而避稅收益較為豐厚,基于成本收益比較,才會有如此偏好。

表1 三類企業不同避稅指標比較表

表2 三類企業不同避稅指標的差異檢驗表
(二)基于公司成熟度的解釋。公司越成熟,對于所處行業越熟悉,對行業及相關法規政策的了解也越透徹,相對而言對稅收政策及法規的利用會更加自如,從而會采取更為激進的稅收行為,筆者將公司規模及公司年齡作為成熟度的代表變量,公司規模取公司總資產,公司年齡取公司自上市開始到樣本年間的年數。用稅會差異回歸應計項目的殘差項作為因變量,用上述家族上市公司樣本構建如下模型:

從表3回歸結果分析,模型(1)顯示公司規模與公司避稅程度顯著正相關,說明對于家族上市公司而言,規模越大,避稅越嚴重;公司年齡雖與避稅程度正相關,但統計上不顯著。模型(2)加入規模跟年齡的交乘項后發現,規模跟年齡均與避稅程度顯著正相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處于成長期的家族上市公司更偏好避稅,因為節稅帶來現金流的增加,而現金流的增加對于一個發展中的公司是何等的重要。但兩者的交叉影響卻是顯著負相關,說明規模越大公司年份越長的公司反而避稅程度越輕,可能這種處于成熟穩定期的家族上市公司更注重基業長青,會更多地去顧慮避稅失敗給企業聲譽造成的玷污及價值減損。

表3 成熟度解釋回歸結果
(三)CEO年齡對避稅的影響。新興起的關于CEO個人背景特征對公司政策影響的研究表明前者對后者存在重大的影響。比如有研究發現CEO越年輕,越傾向于選擇激進的企業戰略(Peng和Wei,2007)。Yin(2013)發現CEO年齡影響著企業并購行為。按此邏輯越年輕的CEO,可能更富有冒險精神,更偏向于采用激進的稅收政策,避稅程度會更嚴重。那么事實是否如此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0對老中青年齡界限的新劃分,44歲以下為青年人,45-59為中年人,60歲及以上為老年人。我們將上述家族上市公司根據CEO年齡老中青分成三類樣本,青年組樣本316個,中年組樣本865個,老年組樣本183個。
從表4、表5的統計結果分析,總體而言青年CEO所在家族上市公司的所得稅費用負擔率要比中年和老年CEO所在樣本公司來的低,而稅會差異及稅會差異回歸應計項目的殘差要比后兩者來的高,說明越年輕的CEO越偏好于采用激進的稅收行為,避稅程度相對較高。但三者之間差異不明顯,統計不顯著。

表4 不同CEO年齡樣本組避稅差異比較表

表5 差異顯著性檢驗表
五、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的家族企業避稅偏好影響因素分析
(一)模型設計及變量解釋。本文擬設立如下模型來觀測公司治理因素對家族上市公司避稅行為的影響:

股權分散度(SD):縱觀文獻研究有不同度量方法,國內研究者一般的分類方法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超過20%,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超過50%即為股權分散,反之則為股權集中(杜瑩、劉立國,2002;蘇武康,2003;劉運國、高亞男,2007等)。Jacquemin和Berry(1979)曾提出用熵的方法來測量高管團隊內部的股權分散度。繼之Kroll等(2007),陳闖、劉天宇(2012)等相繼采用過該方法。筆者也更偏向于用連續變量來度量股權分散度,因此借鑒后者來度量家族上市公司的股權分散度。該方法計算公式為:為股權分散度,Si為第i個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取前五大股東。股權越分散,越有利于權力制衡與民主決策,非合理避稅的概率會越低。
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CCD):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比率法,即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比值,比值越大兩權分離度越大;另一個是差額法,即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差,差值越大兩權分離度越大。本文研究中用CSMAR數據庫中的差值法。
長期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LIS):長期機構投資者作為有效的外部監管組織,能降低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Chen等, 2010)。
董事會規模(DS):董事會規模會影響公司治理效率,但正反結論都有。正面觀點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意味著擁有更多的資源、信息、技能及對CEO的有效監管,同時大規模的董事會也會導致溝通、協調、決策效率的降低(Florackis,2008)。
獨立董事比例(ID):鑒于董事的獨立性、專業知識及經驗會有效地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問題(Zahra和Pearce,1989)。
兩職是否合一(Duality):兩職合一容易導致權力壟斷,加劇代理問題。因而設立虛擬變量,兩職合一的為1,反之為0。

表6 變量描述表
高管工資水平(ESL):用CSMAR數據庫中金額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來表示,取自然對數。
股票期權激勵(SOI):股票期權激勵將決策層的利益與公司、股東的利益緊密相連,利益的趨同性有利于緩解代理問題,考慮到實施股票期權并非家族上市公司的普遍現象,樣本公司中有相當一部分未實施股票期權,因此用虛擬變量來表示,已實施的為1,未實施的為0。
另外根據相關文獻,為控制公司基本面因素,引入資產負債率(Lev)、公司規模(Size)(取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行業(Ind)作為控制變量。it表示第i個公司第t期的樣本數據。
(二)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統計。為控制異常值,所有變量均在樣本下1%和上99%分位數的位置做了極值截尾處理。從表7的描述性統計可見:稅會差異殘差項的均值及中位數分別為27535678元和6224215元,說明家族上市公司普遍進行了避稅管理,但低于均值的公司占多數,稅收激進的公司相對較少。從表8的皮爾森相關系數分析,因變量與各自變量之間高度相關,各自變量之間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變量選取合理。

表7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8 Pearson相關系數表
2.多元回歸結果及分析。從表9回歸結果分析,模型(1)擬合優度為0.326,且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股權分散度與稅會差異的殘差項成正相關,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與預期結果相反,說明股權分散并未取得預料的權力制衡及民主決策的效果,可能由于股權過于分散,導致各個股東都缺乏足夠的能力和動力參與企業的管理和監督管理層的行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投資者對管理層的監督乏力,反而助長了控股股東的機會主義行為,為控股股東提供尋租便利,當尋租收益大于代理成本損失時,強化了其避稅動機,從而使避稅程度提高。至于怎么樣的分散程度是合理的,有待后續實證的深入研究。
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度與稅會差異的殘差項正相關,且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說明控股股東僅憑較少的現金流權就能獲得絕對的控制權時,尋租將更加便利,在獲取控制權私利的同時因較少的現金流權而分擔較少的代理成本損失,因此容易采取更為激進的稅收政策,避稅程度更大。印證了Fama和Jenson(1983)的理論。
長期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稅會差異殘差項負相關,但統計上不顯著。說明長期機構投資者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監督功能,在抑制控股股東的機會主義行為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監督作用,降低代理成本的同時也大大降低了其可能獲取的尋租收益,從而使其避稅動機大大減弱,避稅程度也相對較低。支持了Goergen和Renneboog(2001)的觀點。
董事會規模與稅會差異殘差項正相關,且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說明對于家族上市公司而言,董事會規模越大,反而避稅程度越高,支持了Florackis(2008)的觀點:大規模的董事會會導致溝通、協調、決策效率的降低。最終反而容易成為控股股東的“一言堂”,起不到有效的監督和制衡作用,為控股股東尋租提供便利,增強其避稅動機,從而提高避稅程度。
獨立董事比例與稅會差異殘差項正相關,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獨立董事比例越高,反而沒有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在質疑獨立董事獨立性的同時也可能存在搭便車心理,沒有很好地履行監督職能,便利了控股股東的機會主義行為,方便其獲取尋租收益,增強其避稅動機,導致高的避稅程度。
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是否合一與稅會差異殘差項正相關,但統計上不顯著。說明兩職合一的家族上市公司避稅程度更高。公司引入董事會機制意在發揮監督總經理等經營層的職能,如果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就意味著自己監督自己,這會使董事會制度流于形式也不符合人的自利性假設。兩職合一只會使總經理的權力過于膨脹,也會削弱董事會監督高層管理人員的有效性,作為家族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往往擔任著董事長等要職,這就為其攫取私利大開方便之門,大大增強其避稅動機,導致其較高的避稅程度。
高管工資水平與稅會差異殘差項成正比,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與預期結果相反,高管薪酬越高,避稅程度也越高。說明“高薪并未達到養廉的效果”,因為對于家族上市公司而言,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并不是其主要問題,其主要問題在于控股股東與廣大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高管層很多都是家族控股股東,對于高管層的高薪激勵并不能起到緩解代理問題的作用。
是否實施股票期權激勵與稅會差異殘差項成反比,在10%水平上統計顯著。說明股票期權激勵在一定程度上捆綁了高管層與廣大中小股東及公司的利益,利益的趨同性使得他們會更加關注股價的波動。避稅存在風險,如因避稅丑聞導致股價下跌,在損害公司利益的同時也會影響到高管層自身利益。因此會弱化高管層的避稅動機,從而影響避稅程度。

表9 以稅會差異殘差項為因變量的多元回歸結果
用現金所得稅費用負擔率作為因變量做多元線性回歸,表9顯示的回歸結果與用稅會差異殘差項回歸的結果基本一致。只是股權分散度及是否實施股票期權激勵這兩個變量在統計上不顯著,進一步增強了結論的可靠性及說服力。
六、家族企業避稅與企業價值分析
(一)研究設計。本文借鑒已有文獻中廣泛應用的托賓Q值來衡量企業價值,Q=(每股價格×流通股份數+每股凈資產×非流通股份數+負債總額)/總資產。用上文分析的稅會差異殘差項(Residual-BTD)作為自變量。另外借鑒Chen等(2010),選取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作為公司基本面的控制變量,還選取股權分散度(SD)、長期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LIS)、獨立董事比例(ID)、兩職是否合一(Dualiry)作為影響企業價值的公司治理變量,同時還加入行業(Industry)作為控制變量,以第三部分選取的家族上市公司為樣本建立如下模型:

(二)回歸結果分析。從表10的回歸結果分析,稅會差異殘差項與企業價值負相關,但統計上不顯著,說明家族企業避稅程度越高,企業價值越低,避稅并未提高企業價值,反而造成價值下跌,可能在于過高的代理成本掩蓋了節稅收益。那么好的公司治理機制是否能夠提高企業價值呢?股權分散度、長期機構持股與企業價值正相關且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說明股權分散及機構持股改善了公司治理狀況,有效促進了企業價值。獨立董事比例、董事長及總經理兩職分離與企業價值正相關,但統計上不顯著,說明獨立董事及兩職分離有利于改進公司治理提升企業價值,但效果不明顯。資產負債率、企業規模與企業價值均負相關,且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說明負債水平越高,企業價值越低,并未發揮理論上的治理效應;企業規模越大,價值越低,可能源于規模遞減效應。

表10 避稅與企業價值回歸結果
七、總結及展望
本文將企業稅收規避的研究專門聚焦于家族上市公司,從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家族上市公司稅收規避行為,并結合代理理論將代理成本等非稅成本考慮進避稅決策,首先分析了家族企業的避稅偏好,將家族上市公司與非家族民營上市公司及國有上市公司比較后發現,家族上市公司較后兩者存在一定的避稅偏好,但差異不顯著。附加分析發現,成熟度影響家族上市公司避稅,處于成長期的家族上市公司較成熟期的家族上市公司有更強的避稅偏好。CEO的年齡差異對家族上市公司避稅也存在一定影響,總體而言CEO越年輕,該公司稅務行為就越激進,但統計上差異不顯著。
接著從公司治理的三維:所有權結構、董事會結構、薪酬結構探尋影響家族上市公司避稅程度的主要因素,研究發現,兩權分離及兩職合一導致避稅較為嚴重,股權分散及獨立董事未能有效發揮權力制衡及監督作用,高管的高薪酬并沒有發揮利益協同效應。長期機構持股及股票期權激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避稅程度。
最后分析了家族企業避稅的經濟后果,理論上認為節稅可以提升企業價值,但將代理問題引入稅務行為研究后發現,家族企業避稅程度越高,企業價值反而下滑,說明在家族上市公司中,企業避稅過程中的代理成本超越了節稅收益,也進一步突顯了家族上市公司嚴重的第二類代理問題,家族上市公司治理有待改進和完善。
基于以上研究發現,建議家族上市公司在所有權結構上股權應適度分散,增加長期機構持股以便更好發揮監督作用;董事會規模不宜過大,過大的董事會規模反而導致決策效率低下及最終壟斷,應提高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以便有效發揮監督制衡作用,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分離以達到權力制約;在薪酬結構上應更多地實施績效工資及股權激勵等方式,使高管層的利益與廣大中小股東及公司的利益捆綁以減少其機會主義行為。
本文豐富了家族上市公司稅務研究的理論文獻,將代理成本等非稅成本引入企業稅收決策,從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了家族上市公司避稅影響因素,為改善家族上市公司治理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證據。但本文未能有效區分合理避稅與非合理避稅的成分,有待后續研究的深入;什么樣的股權分散程度能更好地發揮權力制衡及民主決策的作用也有待后續研究的深入。另外,避稅是企業的內涵增長,而投資則是企業的外延增長,企業是否存在合適的投資機會、投資規模等都會對避稅決策造成影響,有待后續進一步研究。■
(本文受到國家社科重點基金 〈14AGL009〉“中國家族企業代際傳承的財務安排研究”的資助。)
1.陳冬、唐建新.2012.高管薪酬、避稅尋租與會計信息披露[J].經濟管理,5:114-122。
2.陳闖、劉天宇.2012.創始經理人、管理層股權分散度與研發決策[J].金融研究,7:196-206。
3.孫剛.2012.家族企業、稅收稽查治理與企業避稅行為[J].稅務與經濟,3:67-75。
4.王靜、郝東洋、張天西.2014.稅收規避、公司治理與管理者機會主義行為[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3:77-89。
5.吳淑琨.2002.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狀態的實證檢驗[J].證券市場導報,3:26-30。
6.曾燕芳、鄭家喜.2005.股權結構對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的影響[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5:75-79。
7.Andrei Shleifer,and Robert W.Vishny.1997.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Finance,2-52):P737-783. 8.Brad A. Badertscher,Sharon P.Katz,Sonja O. Rego,2013.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56:P228-250.
9.Chen S.,X.Chen,Q.Cheng.2010.Are family firms more or less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95(1):P41-61.
10.Desai,M.,Dharmapala,D.2006.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9: P145-179.
11.Desai,M.,Dyck,I.,Zingales,L.2007.Theft and tax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84:591-623.
12.Desai,M.,Dharmapala,D.2009.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firm valu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1:P537-546.
13.Hanlon,M.,Slemrod,J.2009.What does tax aggressiveness signal?Evidence from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news about tax shelter involvemen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3:126-141. 14.Hanlon,M.Heitzman,S.2005.A review of tax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50:P127-178.
15.Hanlon,M.2005.The persistence and pricing of earnings,accruals,and cash flows when firms have large book-tax differences[J].The Accounting Review,80:P137-166.
16.Jensen M.,Meckling,W.1976.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3:305-360.
17.Kroll M.,B.A.2007.W alters and S.A.Le,The impact of board composition and top management team ownership structure on post-IPO performance in young entrepreneurial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0:1198-1216.
18.Jeong-Bon Kima,1,Yinghua Lib,Liandong Zhanga.2011.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Firm-level analysi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00:639-662.
19.Scholes,M.,Wolfson,M.1992.Taxes and business strategy:A planning Approach,first ed Pearson Prentice-Hall,Upper Saddle River,NJ.
20.Wilson,R.2009.An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tax shelter participants[J].The Accounting Review,84:96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