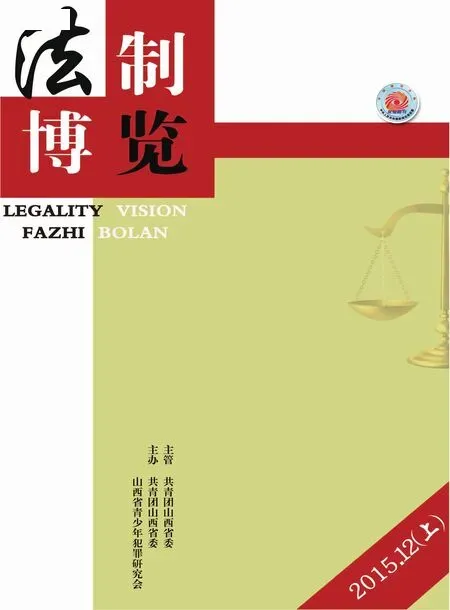論條約解釋中的善意原則
李佳佳
鄭州大學法學院,河南 鄭州450001
一、善意原則概述
(一)善意原則的含義
根據目前對善意原則的相關研究認為,一般認為善意原則起源于羅馬法的公共信用(Fides Publica)。而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解釋,“善意”一詞(good faith,bona fides)是指“存在以下情況的思想狀態:(1)在信念和目的上的誠實;(2)對其職責或義務的忠實;(3)在特定貿易或生意中遵守有關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準則;或(4)沒有欺詐或尋求過分益處的意圖。因此,這一解釋比較全面地展示了善意原則的基本內核,它首先要求締約方在締約之前、締約及履約過程中需要持有的善良和誠實的主觀狀態。
善意原則,即國際法中的善意原則是一項根本性原則,并派生出有約必守規則及其他不同于誠實、公平和合理的并與其直接相關的法律規則,這一規則在任何特定時間的適用,由此時施行的誠實、公平和合理的強有力的標準確定。或者正如沃爾多克所指出的:“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僅僅體現邏輯規則與善意,僅能幫助人們探尋體現在文本中的意圖。它們的適用是非自動的,而是解釋者認為就案子的具體情況而言適用它們是適宜的。”作為法律原則的善意原則似乎就是有其神而無其形,它就像陽光一樣,照耀、溫暖著眾多實體法律規則的生長,而無處不在,但卻不能完全獨立明確地存在于法律世界的具體法律規范和條文里。
(二)善意原則在國際法上的地位
首先,善意原則是一項古老的法律原則,也是國際法的一項普遍原則。被認為是國際法之父的雨果·格勞修斯更是強調說:“根據善意原則的要求,甚至與敵人包括海盜、反叛者和異教徒之間的條約也應當努力維持。”在國際法中,善意原則在條約法領域的實踐最為豐富。善意原則是舉世公認的支配國際法律義務創立和履行的原則。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序言第四段宣布各當事國“鑒悉自由同意與善意之原則以及條約必須遵守規則乃舉世所承認”。善意原則之所以被舉世承認,與它是支配國際法律義務創立和履行的基本原則分不開。國際法院在著名的“核試驗案”的判決中甚至指出,善意原則是支配法律義務創立和履行的基本原則之一。它應當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
其次,國際立法和司法方面,許多重要的國際法條約或公約都包括和體現著善意原則,在國際法院、WTO等國際組織的判決和爭端解決過程中,善意原則也得到了廣泛的適用。《聯合國憲章》第2條指出:“所有聯合國成員國都應該善意履行依照本憲章所承擔的義務。”《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也第26條規定:“每個生效的條約對締約國是有約束力的,而且締約國必須善意履行之。”第31條又規定,締約國有“善意解釋條約的義務”。二戰后,善意原則得到了更多的關注與實踐。如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善意原則在許多協定、義務的解釋和履行中及爭端的解決中得到了普遍適用,表明了它在當代條約實踐中的作用和地位。
(三)善意原則在條約解釋中的價值
首先,善意原則是條約解釋中的前提和基礎性原則。因為要使某一條約達到其訂立的目的與宗旨,必須在善意的指引下正確、合理、誠實、公平地解釋條約的內容。否則,任何歪曲的、包含欺詐與非誠信的解釋,必然導致條約履行的受阻和目的的不能。所以條約必須信守原則的實現,需要有條約必須善意解釋原則的“保駕護航”。《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條約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并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解釋之”。這是對善意原則在當代國際造法性公約里的直接立法規定。
其次,善意原則具有重要的評價功能。條約法中的善意原則具有雙重性的存在價值。即它既是對條約做出正確解釋的方法,同時對其他解釋性因素具有評價和衡量的一把“度尺”。雖然對公約解釋的因素與方法很多,且日臻完善,各方法均有其優長之處,但從某一具體公約解釋性因素出發,來解釋公約文本時,不免甚至難免做出與公約目的與本意相悖的結論。而將善意原則適用于條約解釋的過程中,能夠排除在條約解釋過程中導致明顯荒謬或不合理結果出現的可能。正是因為這種雙重價值的存在,善意解釋不僅構成整個條約法誕生的基礎,而且也是條約法其他解釋因素適用的基礎。
二、條約解釋中善意原則的具體要求
(一)不得違背國際強行法及習慣國際法
國際強行法(英文名:Jus Conges)是國際法上一系列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特殊原則和規范的總稱,任何條約或行為如與之相抵觸,歸于無效。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正式提出了“國際強行法”的概念。公約第五十三條規定: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指國家之國際社會全體接受并公認為不許損益且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質之一般國際法規律始得更改之規律。習慣國際法,是國際法的淵源之一,其構成要素包括國家的一致行為及法律確信。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規定,國際習慣是“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
介于國際強行法及習慣國際法的重要性及地位的不可撼動性,包括條約法在內的所有國際性立法,都理所當然地遵守國際強行法和習慣國際法的指引和約束,因此,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實例說明在國際社會中有哪一國家或國際性組織通過對條約的解釋對國際強行法及習慣國際法有所“冒犯”。
(二)不得做單方利己性解釋
如同國內法律沖突當時雙方一樣,在發生具體法律紛爭時,條約雙方有權利通過對條約的解釋,來維護自己正當存在于條約中所規定的可期待的利益,但是嚴重偏離善意原則的、不誠信、不公平、不合理的當方利己性解釋,是對條約的扭曲,對義務的逃避,對另一方依條約所應享有權益的侵害。典型的案件是中日“西松建設案”,案件中對于原告我國公民的訴訟請求,日本最高裁判所最終以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第五條,聲稱我國國家和公民已經放棄了所有關于戰爭賠償的權利,進而使原告敗訴。日本最高裁判所即以對《中日聯合聲明》的扭曲和利己性解釋,來達到逃避相關賠償責任的目的。
(三)不得“造法”、“修法”和“廢法”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第三十二條的規定了條約解釋的基本要求和方法。在條約的解釋過程中,條約解釋方擅自創造、擴大和引入條約約文語詞和概念,或者擅自擴大語詞及概念的其內涵與外延,即“造法”行為;解釋者通過改變約文中的語詞和概念或是利用其語義的多義性及歧義來改變條約約文本身所具有的含義,或者直接改變約文本身的行為,即為“修法”行為;條約當事方非基于條約的保留、退出及條約規定之情形,單方面通過立法、單方聲明等形式使條約無效而不受條約義務之約束,即為“廢法”行為。條約在假如和生效后,約文即被推定為是締約方意圖的真實和權威表述,并自愿、完全和無條件第接受條約約束的意思表示。因此,條約解釋的出發點應是闡釋條約約文的原本真實意義。而不為締約方日后利益只需要而妄加篡改。因此,條約的善意解釋理所當然地必須禁止“造法”、“修法”、“廢法”等任何形式的對約文的惡意解釋行為。
(四)不得損害條約的目標和本旨
條約法上的目的與宗旨原則確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國際法院的判例中,并于1969年被編纂進《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在《公約》中,目的與宗旨原則規定了條約生效前締約國所負的臨時義務,并對保留、解釋、修改、終止這四類條約行為的合法性與有效性起著規制作用。正是因為條約法上的目的與宗旨原則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在對條約進行善意解釋的過程中,要充分尊重條約本身所具備和所要達到的目的與宗旨。這就要求在解釋條約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務必使條約的目的與宗旨得以實現。這一要求尤其適用于諸如《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這種被稱作“憲法性條約”或“造法性條約”的公約。尊重和追求條約的目的和宗旨,嚴格遵守目的與宗旨原則,是條約善意解釋的必然要求和題中之意。
三、善意原則在條約解釋中的局限性
(一)善意原則的主觀性和模糊性
“善意”的主觀性和內容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善意原則同樣的非客觀性。善意解釋作為一項總的原則,要確定該原則的具體內容是很困難的,很可能找不到一個無可爭辯的“客觀的”獲得公認的衡量標準。因此《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規定的解釋因素以及其他非法典化解釋方法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這也意味著善意原則不是絕對的,而是有其界限與限制的。“善意”原則發揮作用的前提是條約文本規定不明。正如王澤鑒先生所言,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需先以低層次的個別制度作為出發點,必須在窮盡其解釋和類推適用后仍不能解決時,才能訴諸善意原則”。由此,善意的主觀性、模糊性可見一斑。
(二)解釋主體的多樣性及解釋結果的不確定性
在條約解釋的過程中,有權做出解釋的主體具有多元性。從而也就造成了條約解釋結果的不確定性。對于一個國際性條約,締約國或締約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條約監督機構對條約約文都可能具有解釋權,這種交叉性的解釋權的存在,極有可能造成解釋結果間的相互沖突、相互矛盾。而對于這種弊端,《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沒能從立法上做出解決,國際法委員也未能提出很好的解決辦法。因此,這種條約解釋主體的多樣性及解釋結果潛在的不確定性仍是困擾條約解釋的未解難題。也正因為善意原則的以上局限性,國際法院多次重申,善意原則不是本不存在的義務的來源,善意原則僅涉及現有義務的履行問題,即善意原則的普遍性、根本性不能替代現有義務。
四、結語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對條約的解釋做出了專門規定,但卻僅僅是條約解釋的一般性規則,而對其他條約解釋原則和因素并不排斥。從《公約》的規定來看,善意原則只是眾多解釋因素的其中之一,但是善意原則的地位和作用確實唯一的。條約的善意解釋是解釋條約的出發點,也是解釋條約的始終所要遵循的重要價值。但善意的局限也構成了對條約解釋的客觀障礙。因此,如何消弭善意原則在條約解釋中的重要性與局限性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如何進一步鞏固善意原則的地位與作用,如何破除善意原則天生的局限性,也成為我們不斷探索和研究的動力。
[1]鄭斌著,韓秀麗,蔡從燕譯.國際法院與法庭適用的一般法律原則[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08.
[2]李建.論條約解釋的原則[J].雞西大學學報,2011(11):2.
[3]宋杰.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關于條約解釋的再認識[J].孝感學院學報,2007,1(1):59.
[4]E.左萊爾.國際法上的善意原則[A].趙建文.國際法上的善意原則[C].當代法學,2013(4):2.
[5][荷]格勞修斯.論戰爭法與和平法[M].[美]A.C.坎貝爾,何勤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48.
[6]李伯軍.對條約在國際法中的地位、缺陷與發展趨勢問題的探討[J].時代法學,2004(3):6.
[7]鄭斌著,韓秀麗,蔡從燕譯.國際法院與法庭適用的一般法律原則[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08.
[8][荷]格勞修斯.論戰爭法與和平法[M].[美]A.C.坎貝爾,何勤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48.
[9]李浩培.條約法概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51-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