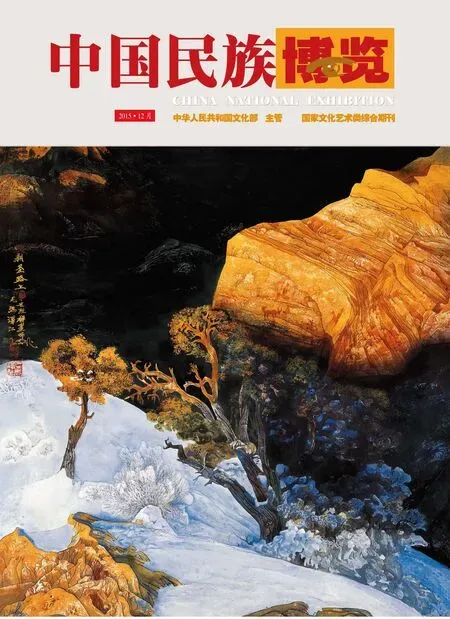《沉睡者》與觀眾心理
董建華
(江西省委黨校文史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沉睡者》與觀眾心理
董建華
(江西省委黨校文史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沉睡者》是1996年好萊塢最為轟動的影片之一。它沒有以宏大的場景、炫目的特技給觀眾造成視覺的沖擊,而是以其具有的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和古老的復仇主題打動了觀眾的心理情緒。然而,影片還因其表現的以惡制惡、以暴抗暴的復仇形式招致觀眾心理的不安與困惑。為此,影片又運用了某些藝術手段進行澄清與消解。
《沉睡者》;觀眾心理;影響;困惑;消解
《沉睡者》是一部長達150多分鐘的劇情片。 影片從情節內容方面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洛倫佐、邁克爾、約翰和湯米四個小伙伴在被稱作“獄廚”即紐約下等街區中的生活。他們在一個酷熱的夏天,制造了一場街頭惡作劇,結果意外地闖下了人命關天的大禍,因而被判關進男童院,生命的軌跡從此改變。第二部分描寫了他們在威健臣男童院的遭遇。他們在男童院遭受了諾克斯、費格遜、史泰勒、艾迪生四個警衛的欺凌、摧殘甚或性侵,這讓他們感受到了難以啟齒的恥辱和產生了莫大的仇恨。第三部分描寫了他們成年后復仇的故事,復仇中又纏繞著出于深厚友情的對“殺人犯”的救贖。由于影片所反映的內容既敏感尖銳又厚重豐實,它對觀眾心理的影響也是復雜而多樣。
一、《沉睡者》對觀眾心理產生的影響
(一)《沉睡者》以它所反映的社會重大而敏感的題材內容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
影片最引起觀眾關注的是第二部分情節內容即洛倫佐、邁克爾、約翰和湯米四個人被關進男童院后遭受獄警凌辱的經歷。男童院本是國家對犯有罪行或過錯的童囚進行教育和感化的地方。但是,教養所中的某些獄警卻把童囚當成濫施淫威的對象和發泄情緒及欲望的工具。因邁克爾和另一童囚在食堂打架,諾克斯強迫邁克爾四人吃倒在地上的飯食。在一次獄警和童囚比賽時,童囚們因沒有按照“慣常潛規則”輸給獄警們,結果黑人里素被活活打死,邁克爾四人在被痛毆后又被分別關進黑屋子并斷食。獄警們還有最惡劣的行徑是對童囚實行性侵犯。童囚們在晚上沒有屬于自己的安寧與清夢,而是要提心吊膽地承受被毆打和蹂躪的命運。
《沉睡者》這部分情節內容之所以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力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影片描述的成年男性對男童暴力性侵犯屬于極其惡劣的大事件:施暴者手段殘忍、行為無恥,被侵者則因過早處于恐懼和屈辱的環境中造成一生無法抹去的傷害。因而此類事件極易引起觀眾內心的正義感:對被侵者關切和同情,對施暴者憤慨和鄙棄。另一方面,此事發生在作為國家機器的男童院。男童院本應是教育感化并規訓未成年人的場所,盡管外表上看像是學校的模樣 ,實際上卻是制造罪惡和催生仇恨的人間地獄。這其中的巨大反差形成影片的強烈反諷意識,由此引發觀眾對所處現實進行理性地思考。總之,影片對此類題材內容的深度挖掘,帶給觀眾的除了情感的震蕩,還有思想的警示。
二、以古老的復仇主題挑動觀眾集體無意識
如果說《沉睡者》第二部分受虐內容使觀眾產生震驚,那么,第三部分復仇內容則讓觀眾感覺痛快。第三部分內容描述了四個獄警都得到了懲罰:或被槍殺,或被逮捕或被揭露。影片中洛倫佐等四人是成年后才實施復仇的,但復仇情結很早就植入在他們心中并伴隨他們的成長生根發芽。他們在年少時聽聞了長輩繪聲繪色地講述班尼復仇的故事:當年班尼被人打掉了門牙,隱忍八年后,他朝仇人兩條腿開了兩槍,從此聞名遐邇,并奠定了“獄廚”霸主的地位。洛倫佐在男童院時,就喜歡讀《基督山伯爵》。邁克爾則聲稱自己每天都堅持讀一點《基督山伯爵》。當四個仇敵都得到懲處,而約翰和湯米被無罪開釋時,約翰稱邁克爾就是基督山伯爵再世。《基督山伯爵》在影片中一再呈現,已然成為復仇的指代符號,也成為他們復仇的心理動力根源和支柱。
觀眾在觀看復仇的電影故事時總能產生一種審美的愉悅和替代性滿足。一方面,復仇情結猶如集體無意識存在于每一個人心中。復仇情結是遠古遺留的深層文化積淀,世界各地都有復仇的心理傳統及行為案例。而且,中外早期社會的倫理觀念也認同個人復仇的正義性。儒家經典《禮記·曲禮》有云:“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舊約全書》記載了古希伯萊人的法律原則:“以命還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日本武士道中,復仇被頌贊為“武士之花”。當觀眾觀看電影時,復仇故事因暗合觀眾的集體無意識帶來情感的共鳴和審美的愉悅。另一方面,“復仇主題迎合并適應了不平人接受視野中的 ‘先驗選擇模式’”[1],成為觀眾情緒宣泄和情感釋放的替代物。觀者在觀看影片時,把自己想象成了影片中的人物,享受報仇雪恨的暢快與愜意,即使心中沒有仇怨的人也可以借此發泄心中的種種積郁。此外,主人公為了復仇,必然要具備堅定的意志,堅強的信念和超出常人的膽識,而這些品質往往又能使觀眾產生敬佩和仰慕,從而獲得精神上的滿足。
二、《沉睡者》復仇主題又因偏離當下主流價值觀激起觀眾心理的困惑
(一)復仇手段的非正義性使觀眾產生心理矛盾
影片中邁克爾等人的復仇成功得力于暴力和陰謀。約翰和湯米在眾目睽睽之下連開了七槍殺死了諾克斯。此案交由法庭審判,而整個審案過程全由擔任副檢察官的邁克爾一人組織調度。洛倫佐找班尼的黑幫對證人進行恐嚇威脅,致使四個證人中的兩個避險而退。邁克爾一人分飾兩個角色,既是控方律師,又替辯方律師擬定好辯詞。他設法讓費格遜上法庭作證,逼使他回憶、反省并承認當年犯下的罪行。最后還迫使神父在對圣經宣誓后作下偽證。法庭最后竟宣判約翰和湯米無罪。在此,法律、法官、法庭審判員都被他或戲弄,或牽引,最終成就了一樁大錯案。影片另外一條復仇線索:班尼勸誘黑人小凱撒以還不起欠債為由槍殺安迪生為弟弟里素報仇,班尼外甥拿到洛倫佐交給他的材料控告和逮捕了貪腐的史泰勒。影片中邁克爾等人的復仇以勝利為告終,但是邁克爾等人復仇手段的非正義的性使觀眾產生矛盾糾結心理:壞人受到懲治,這是大快人心之舉,但是以惡制惡、以暴抗暴的手段與當下主流價值觀及法治精神不兼容,如果贊許之,則會擾亂社會秩序。而且,為了復仇,以犧牲誠實與信任作為代價,也勢必產生社會惡果。因此,評價影片良莠成為觀眾心理的難題。
(二)復仇主體的非純粹性使觀眾產生心理疑問
洛倫佐、約翰、和湯米、邁克爾因在男童院受到凌辱,帶來終生的創痛,然而,這四個被害人身份并不純粹,因為他們也是加害者。為了滿足一次口腹之欲,他們致使一個無辜的行路人重傷住醫院。邁克爾在男童院為了逞一時之強,鼓動想安分坐監的里素和獄警比賽時一決雌雄,終使得里素被活活打死。而邁克爾施展手法救下的約翰和湯米,是黑幫干將,犯有多條人命,本就死有余辜。正因為復仇主體并不是純粹受害者或無辜者,觀眾會質疑他們復仇的理由與動機。而同樣含有復仇內容的影片《肖申克的救贖》則不然。肖申克沒有殺人,他是被冤屈的,而他揭發徇私枉法的典獄長是為社會清除了毒瘤,屬于除暴安良的義舉。因而,觀眾對他的復仇只有贊賞沒有疑慮。
三、《沉睡者》運用藝術手段以消解觀眾心理 困惑
(一)通過刻畫人性引導觀眾共情
影片復仇手段的非正義性與復仇主體的非純粹性有可能削弱觀眾對復仇的認同度。為此,影片通過刻畫人性,使觀眾了解人物情感發展脈絡,繼而對人物行為產生認同。影片濃墨重彩描繪了復仇主人公在“獄廚”生活的貧窮但快樂的童年:他們有可以任意玩耍的街道,有形影不離的小伙伴,還有關心愛護他們的神父。他們雖常搞一小些小把戲,但不失純良之本性,如約翰本來的志愿是長大后做神父,邁克爾為了讓患癌斷腿的女孩高興,故意輸球。但他們進入男童院后,受到虐待,背負上屈辱與創傷,性格與心性因而發生改變。心理學上早就有論斷,童年和少年時期所經受的心理創傷會極大的影響一個人的性格發展乃至人生選擇。文藝理論家童慶炳也認為:“個人的童年經驗常常為他的整個人生定下基調,規定著他以后的發展方向和程度。”[2]邁克爾等人這段噩夢般的童年經歷,給他們帶來了永久的傷害,并制約了他們正常的人生發展。約翰和湯米自暴自棄、放蕩不羈且惡狠兇殘,最后都在二十九歲死于非命。邁克爾則把復仇當成必然使命,復仇后引咎辭職,以做木工度過余生,且終身未婚。而洛倫佐則把所有的精力和熱情投注于記者這一職業中。影片從人性的角度詮釋了他們復仇的心理依據,從而使觀眾認同他們的復仇行為并產生共情。
(二)采用了第一人稱敘事策略使觀眾成為共謀
影片是根據洛倫佐自傳小說改編,采用當記者的洛倫佐第一人稱敘事這被稱作 “人物直接表達感情最直接、最靈活的藝術形式”。[3]由于影片的內容是通過“我”傳達給觀眾,因而能使觀眾得到一種親切而真實的感覺。這就使得雖然 “我們知道一件想象的事并不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同時我們又把它當作幻想跟著它走”。[4]隨著影片情節內容的展開,觀眾仿佛緊跟敘述者的身影仔細聆聽他的講述。他向觀眾介紹他認識的人、他所熟悉的生活環境、他記憶中發生過的事件以及他在當時的心理活動。如同文學作品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者“我”與讀者“你”的交流使“讀者成為同謀”[5]一樣,影片中第一人稱敘事也使觀眾成為了同謀。觀眾與“我”共同經歷了童年的快樂和不幸,共同產生了復仇的欲望,共同體驗了復仇的快感。
[1]王立.復仇心態及中國古代文學復仇主題的審美效應[J].求索,1994(5).
[2]童慶炳,程正民.文藝心理學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張德林. 現代小說的多元建構[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4][美]艾·威爾遜.論觀眾[M].李醒等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
[5][英]巴特·穆爾-吉爾伯特等.后殖民批評,楊乃喬等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J9
A
董建華(1964-),女,江西贛州人,副教授、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