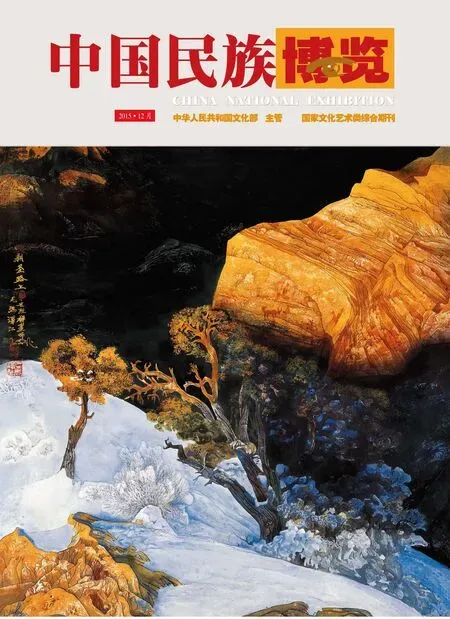馬克·吐溫小說種族敘事倫理分析
金 鑫,何婷婷
(1.云南經濟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304;2.云南昆明醫科大學海源學院,云南 昆明 650106)
馬克·吐溫小說種族敘事倫理分析
金 鑫1,何婷婷2
(1.云南經濟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304;2.云南昆明醫科大學海源學院,云南 昆明 650106)
馬克·吐溫是美國19世紀時期的現實主義作家,其小說所彰顯的理念,多為對資本主義社會弊端以及矛盾的批判,這種批判可以用《美國與美國人》中,斯坦貝克的言論來闡述,即少許憂慮、較多期望以及堅定自信。馬克·吐溫小說不僅對美國社會進行了整體批判,其還利用敘述技巧以故事話語的形式建構了一個獨特的倫理認知。我國相關學者在對馬克·吐溫小說進行研究時,往往將關注點集中于其所展現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理念,并沒有重視其批判倫理建構。而要想對馬克·吐溫形成全面的認知,充分感受到其小說中所體現的社會使命感與責任感,必須對這種倫理建構進行深入分析。
馬克·吐溫;種族敘事倫理;具體分析
馬克·吐溫在小說創作過程中,多以社會底層生活為素材,不僅深刻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社會問題,還對這種矛盾以及弊端進行了全面揭露,因此,其被稱為美國現實文學奠基人。本文先簡要闡述了敘事倫理理論,而后以馬克·吐溫小說中的印第安人素材為切入點,對其種族敘事倫理進行系統化分析。
一、敘事倫理理論
小說敘事特質主要體現為個體性,正是基于這種特質的影響,小說具有較強的自由性與虛構性,致使在敘事過程中,作者往往會融入大量的、自身對社會倫理的質疑與思考,以此體現自身的倫理構想。就某種程度而言,社會倫理表述與小說理念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簡言之,作者可以通過小說闡述自身的倫理價值觀念以及生命體驗。無論小說形態如何發展,這種關聯都是必然存在的,即使其逐漸演變的讓人難以察覺,但并不會隨著社會發展以及時間的推移而消失。而在后現代發展中,作者逐漸將自身的理念體現于小說敘事方式中,由此可見,敘事倫理即敘事中所蘊藏的倫理觀念,其也可以被稱之為倫理敘事,但其絕不是倫理與敘事的雙重疊加。而就敘事倫理本質而言,敘事倫理有機結合了倫理觀念、表述內容以及敘事方法,這種相互交融的形式,體現出三者之間具有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的關聯。敘事倫理并不是片面關注小說的敘事技巧或是故事內容,而是在明確認知二者重要性的基礎上,對二者進行了全面體現。查克里·紐頓對敘事倫理進行了權威概括,其認為敘事倫理共有三種形態:一是,倫理闡述;二是,倫理再現;三是,倫理敘述。本文主要對馬克·吐溫小說中的人物、情節以及敘事技巧進行分析,從而探析其所包含的倫理思維,進而推斷馬克·吐溫的倫理種族思想。
二、丑化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屬于美洲大陸的原住居民,其早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前,便于此繁衍生息,留有豐富燦爛的文學傳統,并形成了印第安文化。而在17世紀初期,英國清教徒開始陸續遷徙至北美大陸,導致北美大陸社會發展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白種人逐漸成為社會主流人群,社會發展日益繁榮;印第安人逐漸被邊緣化,社會發展極度落后。印第安人雖然屬于北美大陸的弱勢群體,但其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輻射美國的主流文化。正是基于這種背景,印第安人的形象塑造、印第安人與白人的關系一度成為作家的創作主題。馬克·吐溫自然不會例外,本文主要通過《苦行記》以及《湯姆·索亞歷險記》為例,對其所體現的種族敘事倫理進行分析。
(一)復仇者
馬克·吐溫在1876年出版了《湯姆·索亞歷險記》一書,作為其代表作之一,該書主要內容為湯姆為了解放個性,改變單調的生活,開始幻想自己所闖蕩的英雄事業。馬克·吐溫不僅在本書中對白人社會、宗教禮儀以及學校教育的弊端進行了充分體現,更是以湯姆的生存視角,塑造了一個具有復仇者形象的印第安人:印癲·喬,在小說中,其不僅極盡殘忍,還冷酷無情。例如,馬克·吐溫在小說的第九章中,以湯姆、哈克的視角,對喬進行了定位與總體評價:murderin half-breed,表示其連惡鬼都不如,將其于人類行列剔除,并以其因誤認為魯濱遜醫生對其不公正而殺害事件為切入點,對其復仇本性進行了印證。馬克·吐溫在小說中,通過敘述喬的種種行為,將其惡劣本性歸于印第安血統,由此可見,在馬克·吐溫的認知里,印第安種族便是十分邪惡兇殘的。
(二)掠奪者
馬克·吐溫在《苦行記》中,將印第安人歸于同動物一致的野蠻人,徒具人形外表,十分野蠻殘暴。通過分析《苦行記》的開篇內容可知,馬克·吐溫將印第安人等同于羚羊、犬鼠以及野牛等動物,而且在小說后序中,印第安人也總是以非正常人類的形式存在,其與白人之間天差地別,是徒具人形外表的、十分殘暴的野蠻人,并最后將其歸于郊狼本家。馬克·吐溫在該小說中,無處不在向人們傳遞一個觀念,即印第安人具有忍饑耐餓、懶惰以及不知疲倦的特性,是沒臉沒皮的乞丐。除了貶低印第安人的本性外,馬克·吐溫還通過構架情境,為印第安人塑造了燒殺掠奪、兇殘的形象。不難發現,在馬克·吐溫的認知里,印第安人與殺人犯基本等同,其以十分殘暴的方式制約著美國白人的英勇事業。
三、印第安種族的滅絕論
很多學者在鉆研馬克·吐溫著作后表明:馬克·吐溫骨子里便對印第安人充滿了仇視,這不僅僅是信仰的作用,還取決于其天性。其不僅想毀滅印第安人的身體,還想將其存活表象全部磨滅,這是一種靈魂毀滅。例如,在《湯姆·索亞歷險記》中,馬克·吐溫給喬設定的結局為:罪行暴露,被困于山洞,最終因饑餓而死。而其所藏財富最終也全部被哈克、湯姆占有。這種情景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將馬克·吐溫在印第安種族方面的倫理觀念體現的淋漓盡致。首先,在喬死亡情景上的設定,便體現了馬克·吐溫的仇視心理,恨不能將印第安人趕盡殺絕;其次,正如相關學者所言,白人在處理自身與印第安人的關系時,往往借助崇高名義掩蓋卑劣伎倆。白種人在北美大陸的發展均是以掠奪印第安人生存資源為基礎的,這種行徑與白種人口中所述的人道主義精神極其不符,必將成為美國歷史污點以及道義負擔,為了改變這種發展形勢,很多人都選擇通過文化手段,對自身種族的掠奪性行為進行美化與合法化。而在《湯姆·索亞歷險記》的結尾,馬克·吐溫設定由湯姆占有喬的財產,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便具有合法化自身種族掠奪行為的嫌疑。《苦行記》中,馬克·吐溫借助小說情形發展,界定了印第安人的食物鏈地位,即蟲子——蒼蠅——野鴨——印第安人——野貓——白人。并提出了:自然體系中,萬事萬物皆有適當的用處、地位以及職責,只有這樣,人類社會才能正常發展。基于這種界定而言,白人屠殺印第安人屬于自然體系的生態循環規律,無可厚非。由此可見,馬克·吐溫以生物進化論為切入點,對白人作用于印第安人身上的強暴行為,進行了合法化處理。
馬克·吐溫不僅在小說中,通過丑化印第安人闡述自身的種族倫理觀念,更是將這種觀念融入到其書寫方式中。例如,《苦行記》中,馬克·吐溫在寫印第安人時,總是會將他們與動物同等對待,除了上述的羚羊、犬鼠、野牛外,其還將印第安人等同于禿鷲、銀塊以及沙漠等,從這些寫作形式中,便可以發現,在馬克·吐溫觀念中,印第安人并不屬于人類,而是在禽獸之列,他們雖具人形,但卻是動物本家。赫爾德曾表明,語言是人類思維工具的同時,也是人類思維的內容與形式,因此,語言可以體現一個人的思維方式。以此延伸,詞語也可以體現人類的思維情感色彩。馬克·吐溫在小說中多用heathen、ignorance、slave of the devil、savage等詞形容印第安人,由此可見,其對印第安人存在強烈的歧視理念。《苦行記》中,馬克·吐溫更是站在道德角度,對印第安人進行負面評價,例如,savage、hostile Indian country、the most balefully interesting object、the stony-hearted liar以及half-breed等,極盡所能的貶低、輕薄、詆毀印第安人,通過這些詞語所顯露的情感色彩可知,馬克·吐溫非常敵視印第安人。
白種人在入主北美大陸后,往往將自身與印第安種族之間的矛盾沖突歸咎于印第安人,認為其本性便是燒殺搶掠、嗜血好戰。而將自身的侵略性行為歸為愛國主義。這種雙重評判標準在馬克·吐溫的《苦行記》中也有體現,該小說中含有大量的印第安人燒殺搶掠事件,卻從不提白人的殘害屠殺、非法掠奪行為,這種敘事內容充分體現了,馬克·吐溫自身便對印第安人存有嚴重的種族歧視、仇恨理念。
20世紀中葉,印第安人在北美普利茅斯石舉行了示威游行,并提倡以致哀日取代感恩節。由此可見,在印第安人視角里,白種人踏入北美的那一刻,便意味著印第安人的苦難史開始了。在社會生存方面,白種人通過燒殺搶掠,從印第安人手中搶奪了北美大陸的礦產資源以及土地資源,使其成為自身永久性財產,導致印第安人難以繼續生存,更遑論持續發展了。在社會文化方面,白種人通過文化作品,以殖民主義為基礎建構了一套話語體系,并以落后、原始等詞語界定印第安文明,對自身的侵略性行為進行合法化,并以高高在上的姿態,蔑視印第安種族,歧視思想觀念十分嚴重。隨著美國現實主義作品的橫生,印第安人逐漸淪為白種人社會發展歷史、藝術以及文學的產物。而馬克·吐溫作為現實主義發展的奠基人,其小說中所體現的思想觀念,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白種人殖民主義話語體系的重要部分。
四、結語
總體而言,馬克·吐溫的小說,在敘事話語、故事情節以及人物塑造方面,均可以體現出其對印第安人的仇視性偏見,因此,由馬克·吐溫小說所體現的種族倫理觀念而言,馬克·吐溫對印第安人存在種族歧視這一理念是毋庸置疑的。
[1]余純潔.《苦行記》:19世紀美國種族主義的文學鏡像[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14,4.
[2]李蓓蕾,譚惠娟.混血兒的身份隱喻——《傻瓜威爾遜》和《一個原有色人的自傳》的比較研究[J].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
[3]王建平.《夏威夷來信》中的“明確使命觀”[J].外國文學評論,2015,3.
[4]楊金才,于雷.中國百年來馬克·吐溫研究的考察與評析[J].南京社會科學,2011,8.
[5]溫振鳳.論馬克·吐溫兩部《歷險記》筆下的成人世界[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S4.
[6]呂沙東,李務專.試論《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兒童視角[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
[7]尹靜媛.從《哈克貝利·芬歷險記》管窺馬克·吐溫的生態倫理觀[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4.
[8]詹姆斯·費倫,肖向陽.《洛麗塔》中的疏離型不可靠性、親近型不可靠性及其倫理[J].敘事(中國版),2009.
[9]詹姆斯·費倫,尚必武.疏遠型不可靠性、契約型不可靠性及《洛麗塔》的敘事倫理[J].世界文學評論,2008,2.
I1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