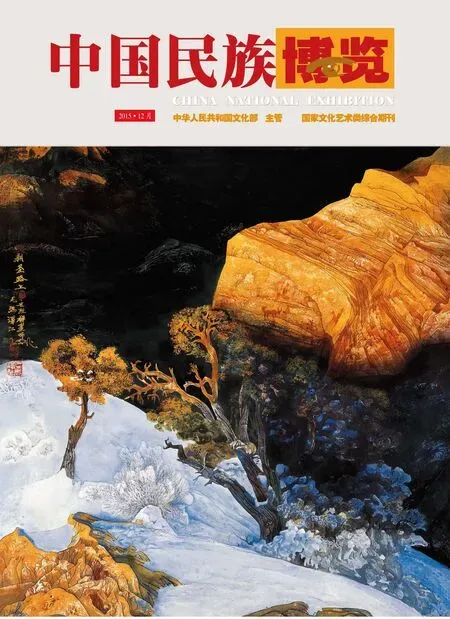歷代文史作品中的醫生形象
姜 媛 常存庫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歷代文史作品中的醫生形象
姜 媛 常存庫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醫生在人們心目中形象的文字記載主要來源于古典醫籍,本文從文史作品中提煉醫生形象,包括神秘型的巫醫;玄虛型的僧醫;正宗道德的儒醫;詭詐伎倆的民間游醫四種類型。剖析傳統醫生形象. 以此對新時期醫生形象的樹立提供歷史借鑒。
文史作品;巫醫;僧醫;儒醫;民間游醫
醫療是人類生活永恒的話題,醫生是醫療活動的主體。由于醫生和患者在醫療活動中的不對等關系,醫患矛盾隨處可見。醫生形象面臨危機。醫療實踐活動表明,醫生形象的好壞不僅影響醫療衛生行業的發展,更關乎于人們的健康生活和社會的安定。醫生形象具有繼承性,其產生脫離不了時代的印跡,我國古代社會對醫生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德不近佛不可為醫,術不近仙不可為醫”,“醫系人之安危死生,眷屬悲歡聚散,豈非天地間最重大之事”。[1]德與術兼備,不僅是醫者對病人的負責和對生命的尊重,更是對自我良心的安慰。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浸染出了大批優秀的醫家及優良的醫生形象。目前,文獻中關于醫生形象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從古典醫籍中分析、剝離。本文從文史作品中提煉出不同的醫生形象,對于全面認識古代文人筆下的醫生形象和樹立新時期醫生形象應有借鑒意義。
一、神秘型的巫醫
醫,或本源于巫,《說文·酉部》“醫,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醫。”“毉”同醫。明·徐春甫《古今醫統》“巫醫,以巫而替醫,故巫醫也。”[2]巫醫是一個具有雙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職醫藥,是比一般巫師更專業的醫者。由于對生老病死等自然規律認識的局限性,百姓對自然界產生了神秘和敬畏,遇到不符合認知的現象時不得不求助巫師。在這種背景下,雙重身份的巫師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僅從醫師角度出發,巫醫這一群體有著鮮明的形象特征[3]。
(一)巫醫群體扮演著醫師的角色,有起死回生之術
《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寙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4]。巫醫在操起死回生之術時,表現出強烈的神秘性,生動的詮釋出醫者對患者診治的同時,還附加了濃重的神靈色彩。
(二)巫醫群體還顯現采藥、種藥者的形象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4]。《山海經·大荒南經》“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入齋。黃鳥于巫山,司此玄蛇”[4]。展現出不畏艱險,為療疾苦而尋覓靈藥的形象。
(三)巫醫群體通鬼神療疾苦的形象
《山海經·海外西經》“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以上下也”[4]。《史記·封禪書》“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5]。巫醫療疾在形式上,用巫術營造一種神秘氣氛,形式上是宣示鬼神意志,對患者的具體治病上實質是通過心理上的安慰,達到一種精神支持的作用,或用藥通過藥理作用達到解除病痛的目標。
早期人類社會中,巫醫群體主要扮演著醫生、藥師、神職人員等多重身份。許多尚難用當時的科學文化知識所解釋的問題,巫是較好的求助對象。隨著科學技術和文化水平的進步,人們逐漸認識到疾病本身是一種自然現象,醫療行為方式亦是運用自然手段,而非利用超自然的力量解決。人類認知能力的提高和文化信仰的改變,使巫醫開始漸漸讓位于其他類型的職業醫生。
二、玄虛型的僧醫
兩漢時期, 佛教開始傳入我國,僧醫隨之而來。僧醫最開始是為方便寺院內部僧徒就醫產生的。在一段時期內,并不被我國人民所接受。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亂不堪,物質生活得不到保障,精神世界就需要寄托。這種情況之下,僧醫的出現就如救世主般拯救患病的民眾。僧醫既是僧人又是醫生,包括僧徒知醫和以佛法濟世救人兩層含義。他們身上最大的特點就是充滿了濃郁的佛教文化特征。
《魏書·藝術傳》“李脩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棄劉義隆于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眾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江南通志》“釋法蘊,以善醫,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多中。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一時稱藥王再現”。[2]
僧醫認為醫學是為人解除痛苦的一門學問,是自利利人之業。對僧醫來說,醫療行為是一種容易接近百姓,宣揚宗教信仰的有力工具。僧醫之所以被接受,一方面它產生了“好人”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與受眾群體在心理觀念上可達到契合。
《德興縣志》“釋普映,長居院僧,通究釋典,尤精岐黃術。元武宗取為太醫,除授僧祿司,在朝十三年”。[2]《德興縣志》“釋拳衡,燒香院僧,通釋典,善醫,投劑無不效。至治三年,皇后疾,拳衡獻藥有功,賜號忠順藥師,領五省採藥使”。[2]某些僧醫的社會地位極高,受到上層統治者的尊崇。僧醫一生都詮釋著行醫、宣教的兩大任務。
僧醫身份特殊,帶有一種濃郁的佛教文化色彩。僧醫在中國傳統醫學中所扮演的角色遠不止于醫學意義上使身體從非常狀態下轉變為常態,他們還負責處理“身體”與“信仰”的關系,即“肉體”與“精神”[8]。它的整個過程都是在宣揚醫學的控制力量與宗教的精神感動。
三、正宗道德型的儒醫
儒醫群體普遍存在中醫中,形成了一道特殊的中醫文化景觀。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儒家思想就成為統治思想,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這是其他思想無法比擬的。根深于本土的中醫學也深受其文化思想的影響,于是就產生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儒醫”。 醫稱儒醫,是對醫生的最高贊譽。儒醫,指儒生而行醫的人。廣義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識水平的非僧、非道的醫者;狹義指崇儒而習醫、業醫之人。
儒醫盛行于宋代,宋代以前人們以醫為小道,在士農工商中醫屬于工,處于社會末流,地位低下。儒醫階層的崛起,賦予了傳統醫學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
陳實功《外科正宗》“第一要即‘先知儒理,然后方知醫業’”。首先醫生必須有其深厚的儒家文化修養,其次有其精湛的醫術。宋徽宗二年詔諭“今欲別置醫學,教養上醫”。宋代將醫學納入儒學教育體系,醫生入儒學教育,才可稱為“上醫”即儒醫。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大學》“八條目”,儒醫在行醫過程中將其帶入醫學領域,成為醫生自身提升與治病救人的一個準則。
宋代張杲《醫說》曾記載“宣和間,有一士人,抱病經年,百治不瘥。有何澄者,善醫。其妻召至,引入密室中高之日‘妾以良人,抱疾日久,典賣殆盡,無以供醫藥之資,愿以身相酬’。醫正色拒之”。
“仁、義、禮、智、信”乃儒家重要的思想。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人們認為好的醫生不僅要有一顆仁愛之心,還要具備聰明才智。俞昌說:“醫,仁術也。”,“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韓非子》云:“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舊唐書·高宗傳》“時太宗患痛,太子親吮之,扶攆步從數日”。對儒醫來說,醫學不但醫治疾病,還要奉行忠孝之道。
《千金要方序》說:“余緬尋圣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
儒醫階層的興起為一些落魄的儒生提供了方便,所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對他們來說不僅僅是物質生活的來源,更是心理上的一種寄托。《古今醫統·醫部全錄》記載:“慶歷中,有進士沈常,為人廉潔方直,性寡合,后進多有推服,未嘗省薦。每自嘆日‘吾潦倒場屋,尚未免窮困,豈非天命耶?’乃入京師,別謀生計。因游至東華門,偶見數朝士,躍馬揮鞭,從者雄盛,詢之市人,何官位也?人日‘翰林醫官。’常又嘆日‘吾窮孔圣之道,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黃輩也?’始有意學醫。”[2]
儒家文化對傳統醫學的影響,通過儒醫漸漸地滲透到醫學領域,并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其中,無法撼動。
四、詭詐伎倆型的民間游醫
民間游醫由來已久,其稱謂多種多樣:“草澤醫”“走方醫”“鈴醫”“江湖郎中”等。他們讀書不多,用藥多是民間偏方,大多為謀生計。他們行醫具有很大的流動性,常常是走街串巷,足跡遍布社會的各個角落。手搖串鈴,背個布袋,叫喊包治百病是其典型的形象特征。
(一)民間醫生們是醫學經驗的代表: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藕皮止血起于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章太炎“取法東方,勿震遠西;下問鈴串,勿貴儒醫”。勞動人民的經驗為醫療活動積累了大量豐富且行之有效的醫學知識。
(二)民間圣手形象
《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507在:“嘉佑初,仁宗寢疾,藥未驗,下召草澤。始用針自腦后刺入,針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翼日,圣體良已,自稱其為‘惺惺穴’”[2]。《船窻夜話》載:“孝宗嘗患痢疾,眾醫不效,德壽尤之。過宮,偶見小藥鋪,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科’遂宣之。因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數服而愈。德壽大喜,以金杵臼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為金杵臼嚴防御家,可謂不世之遇”。[2]《明外史·盛寅傳》載:“初,寅晨直御藥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療寅,莫能應,一草澤醫人應之。一服而愈。問狀,其人曰:‘寅空心入藥房,卒中藥毒,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帝問寅,果空腹入。乃厚賜草澤醫人而遣之”。[2]民間醫生們獨特診療方式是國醫們不能比擬的,正所謂是“單方一味,氣死名醫。”“高手在民間”。
由此可以看出傳統中醫學在民間也是大放異彩,民間醫生能醫國醫不能治之疾,且用藥用方簡廉便驗,為廣大群眾所認可,雖然其中難免有些人是靠運氣發家,從而走上行醫賣藥的道路,某些人也不乏招搖撞騙之能事,這些人多沒有學術修養,但是很多經驗可貴,不應忽視。遺憾的是民間醫生沒有經過系統化、理論化的學習,診脈治病多出于經驗之談,經驗并不是百分百的準確,常常會出現誤差,造成醫療失誤也是不可避免的。
文史作品對人們的價值取向、審美取向、生活態度有積極影響。對樹立良好新型醫生形象有導向作用,有利于推動醫療活動的和諧發展。綜上而言,文史作品中我國古代諸多醫家形象,可為我們提供學習的榜樣,也可以提供反面借鑒。
[1]潘新麗.中國傳統醫學職業精神:仁、智、廉、不欺[J].醫學與哲學,2009,30(9):18-19.
[2]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點校本(卷501-卷520)總論及其他第十二冊[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50-268.
[3]鄭瑞俠.中國古代早期文學的醫師形象[J].東疆學刊,2004,21(2):65-73.
[4]史禮心,李軍.山海經[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157-216.
[5]漢·司馬遷.史記·中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5.1177.
[6]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7]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8]楊念群.再造病人[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38.
[9]清·趙學敏.串雅內外編[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
[10]李文彥,葉興華.德醫雙修精誠濟世-中國古代醫家醫德倫理思想分類舉要[J].醫史博覽,2012.
I206
A
姜媛(1989-),女,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醫史文獻專業研究生;常存庫(1955-),男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教授,研究方向:中醫學術思想與方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