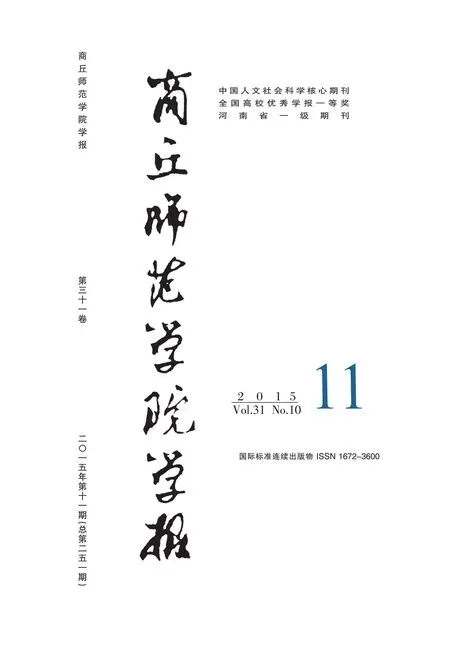《茶館》的“草珠項鏈”
——試談《茶館》幕前大傻楊的“數(shù)來寶”
董 克 林
(北京大學(xué) 教育學(xué)院,北京 100871)
《茶館》的“草珠項鏈”
——試談《茶館》幕前大傻楊的“數(shù)來寶”
董 克 林
(北京大學(xué) 教育學(xué)院,北京 100871)
老舍的話劇《茶館》以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矗立于世界文壇。其中,作者設(shè)計的幕前大傻楊“數(shù)來寶”帶著土洋結(jié)合的韻致,打著快板敘述表演,為“茶館”錦上添花。“數(shù)來寶”以20世紀50年代“雙百方針”出臺前后為背景,在劇中有聯(lián)結(jié)三幕、劇情化身和作為特殊“劇中人”的功能,同時具有音樂性、藝術(shù)張力及“假定性”的作用;收到了對時代背景映襯、與劇本語言風格遙相呼應(yīng)及對三幕劇串聯(lián)等藝術(shù)效果。
“數(shù)來寶”;民族元素;“劇中人”;串聯(lián)效果
老舍在《茶館》創(chuàng)作上用了“新招數(shù)”,他把解放前北京街頭乞丐所說的土得掉渣的“數(shù)來寶”串在了三幕話劇之前。大傻楊打著快板登上了話劇舞臺,是老舍將中國戲劇元素與話劇元素相結(jié)合的嘗試。大傻楊俗中有雅的韻致表演,像一串帶有濃郁京味的“草珠項鏈”,為悲愴的劇情譜出了歡快的音符,為苦澀的《茶館》涂上了一抹靚麗的色彩,為幕間增添了新穎的民族藝術(shù)形式和風格,為觀眾帶來了耳目一新的審美體驗。
一、土洋結(jié)合的“新招數(shù)”及其采用背景
(一)土洋結(jié)合的“新招數(shù)”
老舍說:“創(chuàng)作這個事就是大膽創(chuàng)造,出奇制勝的事兒,人人須有點‘新招數(shù)’,要勇于‘突破藩籬,獨出心裁,別開生面’。”[1]275他寫《茶館》遵循了話劇劇本基本格式,另在每一幕之前加一個附錄——大傻楊“數(shù)來寶”。老舍巧妙地運用敘述方式,讓大傻楊打著竹板在每一幕之前表演,將京味的快板書與話劇相結(jié)合,以話劇民族化的藝術(shù)手段,創(chuàng)造出國人喜聞樂見的曲藝藝術(shù)。楊迎平說:“老舍的‘新招數(shù)’是既要借鑒外來的演劇方法,又要繼承中國傳統(tǒng)的戲劇特點,布萊希特的戲劇觀正好融合了這兩個特點。”[2]295由此看來,“數(shù)來寶”登上話劇舞臺不僅是老舍踐行中國話劇民族化道路的一次嘗試,而且是中國戲劇與布萊希特戲劇理論相結(jié)合的成功實踐。
話劇劇本及幕(場)之間采用哪種結(jié)構(gòu)方式,用音樂、舞蹈,還是用字幕等其他方式,傳統(tǒng)的、民族的與現(xiàn)代藝術(shù)、西洋藝術(shù)怎樣結(jié)合,應(yīng)該取決于該話劇的題材、立意和作者開掘題材的藝術(shù)角度等因素。老舍在三幕話劇幕間添加的大傻楊“數(shù)來寶”,是民族化的一種形式,但并非唯一的形式,因為民族化元素滲透在中國話劇歷史發(fā)展進程之中,滲透在舞臺的每一寸空間。如曹禺的《北京人》中,曾文清吟誦陸游的《釵頭鳳》,《家》中的覺慧和鳴鳳背誦蘇東坡的《水調(diào)歌頭》等。而當年老舍為創(chuàng)新民族化藝術(shù),曾踐行在不同劇種之間,他“不僅寫過京劇,而且還改編過一些地方劇,從中感覺不同藝術(shù)形式的區(qū)別和舞臺藝術(shù)規(guī)律”[3]。他在《茶館》中添加的大傻楊的“數(shù)來寶”聯(lián)結(jié)了三幕,不僅延伸了全劇的完整性和統(tǒng)一性,而且與話劇內(nèi)容相映襯,與中國觀眾的民族化、地域化欣賞口味相契合,貼近大眾的審美心理,創(chuàng)造出了典型的土洋結(jié)合的“新招數(shù)”。
在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數(shù)來寶”和話劇各自的特點(參見表1)。“數(shù)來寶”表演形式為一人或兩人沿街說唱,用竹板或系以銅鈴的牛髀骨伴音。常用“三、三”七字、八字、九字句,句子押韻,朗朗上口,極富表演性,是民族曲藝藝術(shù)。話劇是“西洋劇”,20世紀初傳入中國,具有舞臺性、直觀性、綜合性、對話性,是一門綜合性藝術(shù)。

表1 “數(shù)來寶”快板書與話劇藝術(shù)要素對比簡表
相比之下,“數(shù)來寶”與話劇彰顯著各自的生命氣息和藝術(shù)光澤:西方的陽春白雪與東方的下里巴人,高雅的舞臺藝術(shù)與街頭的乞丐說唱。一東一西,一土一洋,一俗一雅。老舍大膽地將東方的“寫實主義”形式與“斯式體系”的“生活化”融為一體,他的“新招數(shù)”是一次在話劇舞臺上培育中國曲藝藝術(shù)元素的新嘗試。
夏穩(wěn)說:“中國話劇扎根中國的百年來也經(jīng)歷了從保持純凈的西方血統(tǒng),反對中國的戲曲文化到借鑒中國戲曲文化表現(xiàn)形式以至于最后話劇和中國的傳統(tǒng)戲曲文化相融合的這一顛覆歷程。”[4]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老舍創(chuàng)作大傻楊的“數(shù)來寶”的顛覆性具有兩個第一:第一次將曲藝藝術(shù)置入幕間,第一次將“數(shù)來寶”搬上舞臺。這種藝術(shù)首創(chuàng),說明了老舍不僅是當年“話劇的民族性”的實踐者,更是創(chuàng)新者,是當年顛覆話劇歷程的貢獻者。
(二)土洋結(jié)合“新招數(shù)”采用的背景
縱觀《茶館》前后的話劇民族化歷程,話劇的土洋結(jié)合是從1956年郭沫若的《虎符》開始的,還有《蔡文姬》《關(guān)漢卿》《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當時,西洋藝術(shù)被中國藝術(shù)民族化的形勢如春潮涌動,不僅在中國話劇舞臺上融合民族戲曲,而且為許多西方藝術(shù)中國化鋪墊了道路。當年,走中國民族化道路的文藝創(chuàng)作形勢給原本仰慕狄更斯并擅長潑墨京味小人物的老舍提供了嶄新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和機會。
20世紀初,搬到中國舞臺上的話劇演繹成“舶來品”,缺少民族之魂、藝術(shù)之美、人性之真,突出問題是缺少民族地方特色。針對這一問題,國內(nèi)出現(xiàn)許多導(dǎo)向性思想。特別是1956年全國首屆話劇觀摩演出后,在“雙百方針”指引下,話劇家們力求創(chuàng)新,紛紛獻劇獻策,糾正了話劇暴露出來的一些缺點,新劇本如《布谷鳥又叫了》《同甘共苦》《洞簫橫吹》等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框框,被劇作家劉川稱為“第四種劇本”。這些新作符合焦菊隱提出的“為表演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烘托環(huán)境氣氛和時代感,有利于突出主題思想”[5]。田漢先生也主張話劇不僅要接近真實生活,更要從真實生活中進行升華提煉,使其具有更高的藝術(shù)表達形式,更好地體現(xiàn)出其民族性。他主張在現(xiàn)代話劇與民族戲曲之間,駕起一座互相溝通的橋梁。當時,周恩來指出:“我們的話劇,總不如民族戲劇具有強烈的民族風格。中國話劇還沒有吸收民族戲曲的特點,中國話劇的好處是生活氣息濃厚,但不夠成熟……”[6]如此種種話劇創(chuàng)作民族化信號與老舍土洋結(jié)合的創(chuàng)作理念一拍即合,話劇的時代民族性與老舍自身的民族藝術(shù)細胞存量為老舍提供了不竭的創(chuàng)作源泉。
老舍為了采用中國戲劇的表達方式,增強中西文化藝術(shù)融合后話劇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他審視西方、中國、自己和他人的話劇作品,悉心尋找“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新套路。早在1953年,他在話劇《龍須溝》中,塑造了瘋子“數(shù)來寶”片段,創(chuàng)作《茶館》時,他再次將“數(shù)來寶”鑲嵌在三幕之前,超越了東方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二元對立思維,超越了“舶來品”話劇的格調(diào),也超越了老舍自己。他摒棄的是在創(chuàng)作藝術(shù)上照抄照搬,創(chuàng)新的是將民族藝術(shù)元素奇妙地融進話劇舞臺。老舍說:“格調(diào)欲高,固不專賴語言,但語言貧味,即難獲得較高的格調(diào)。提高格調(diào)亦不耑賴詞藻。用的得當,極俗的詞句也會有珠光寶色。”[7]611可見,“數(shù)來寶”這根寶鏈既不是偶然之筆,也不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而是作者在民族化道路的春潮中,在語言上精雕細琢,才得以將有血有肉、鮮活欲出的民間曲藝之寶呈現(xiàn)出來。這根寶鏈堪稱中國話劇史上的草根變珠寶之藝術(shù)絕版。
老舍設(shè)計大傻楊“數(shù)來寶”,還有以下這些原因:一是劇情需要,劇中有些演員要一人演三幕,換幕化妝時間較長,為使幕間連貫,需要“新招數(shù)”。二是老舍出身原因,老舍是在京味胡同里長大的作家,在北京民間藝術(shù)中過篩子,是情理之中的事。三是聽取了專家學(xué)者的建議,陳白塵在1957年12月19日座談老舍的《茶館》時提出:“不妨請老舍同志寫個幕前詞,向觀眾解釋一下。假設(shè)能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更好。”[8]935還有人出主意,可以說段“數(shù)來寶”讓觀眾等待。這種建議與老舍的創(chuàng)作天才相撞擊,產(chǎn)生火花。這也恰遇老舍關(guān)注平民視角之所好,正中老舍善于駕馭俗詞俚語之擅長。四是符合話劇舞臺表演的動作性,“寫劇本應(yīng)盡量多找動作,用動作來代替對話,記住!在臺上用一個真實的動作,比用一車子的話表述心情更有力量”[9]。從曹禺這句話里,也能看到大傻楊打快板的力量之所在。五是符合布萊希特主張的話劇舞臺表演的娛樂性。事實上,這種娛樂性包含著老舍與布萊希特同時追求的寓教于樂的演劇觀。當然,時代背景和老舍本身致力創(chuàng)新話劇民族化形成了作者內(nèi)因與外因的有機結(jié)合。在時代的召喚下,老舍既博采眾長借鑒外來的和現(xiàn)代的戲劇藝術(shù)方法,又苦心孤詣地探索繼承民族傳統(tǒng)藝術(shù)之途徑,促使他又一次捕捉到了“出奇制勝”的良機。
二、土洋結(jié)合的“新招數(shù)”的運用
(一)賦予大傻楊“劇中人”的角色
老舍在《茶館》附錄中寫道:“……故擬由一人(也算劇中人)唱幾句快板……”[10]323按照老舍給大傻楊“劇中人”的定位,“劇中人”指的是幕與幕之間的那個人,是特定的一個角色,與劇中的角色人物不同。楊迎平說:“‘大傻楊’是戲外之人,與劇中人是間離的。”[2]296雖然,“劇中人”與“戲外之人”文字不同,但意思同指幕間的這一特殊角色。布萊希特提出的“間離方法”(陌生化方法)要求演員與角色保持一定距離,演員要高于角色、駕馭角色、表演角色。雖然,大傻楊沒有完全按照布萊希特的陌生化方法來完成角色定位,遵循的是老舍給予的民族角色設(shè)計,但是,在這個“劇中人”身上,仍然具有布萊希特戲劇元素的“間離”性。從《茶館》舞臺演出來看,老舍的“間離效果”與布萊希特的“陌生化效果”不盡相同,可“數(shù)來寶”最終的“間離效果”與布萊希特的“保持距離”方法仍然存在藝術(shù)近似的地方,達到了既要讓觀眾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效果,達到了揭示社會本質(zhì)、引起觀眾聯(lián)想與深度思考的效果。因為,老舍式“間離”不為假定性而假定性,拉近戲與人的距離,意在拉近幕與幕之間的距離,拉近幕間與觀眾的距離,拉近觀眾與劇情的距離。
大傻楊的“數(shù)來寶”所擔當?shù)慕巧珣?yīng)該是一種特定“旁白”,但它與一般“旁白”在藝術(shù)形式、表現(xiàn)內(nèi)容等風格迥異。通常,“旁白”多用書面語,或有音樂伴音,多為描寫、說明、闡述性文字,用朗誦介紹劇情。而“數(shù)來寶”有竹板伴音,多用擬聲詞、擬態(tài)詞,用表演說唱介紹劇情。
盡管“數(shù)來寶”與“旁白”有明顯差別,但“數(shù)來寶”登上舞臺后,其“劇中人”的角色還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它承上啟下。大傻楊以介紹者身份出現(xiàn),角色自由、直接,既簡述劇情,又穿插一些與劇情有關(guān)而又無法在劇本中無法表現(xiàn)的內(nèi)容,使相對獨立的三個幕次連綴成一個整體。這種角色嫁接是跨疆域的思想文化結(jié)合,是中外藝術(shù)的融匯,是中華民族審美精神的滲透,體現(xiàn)了戲曲傳統(tǒng)美學(xué)與話劇美學(xué)的基因互補,有機嫁接。人性對光明、美好的追求具有共通性,其文化藝術(shù)嫁接后更容易成為有價值的文藝空間。老舍為三幕話劇烙上的北京色彩的鄉(xiāng)俗符號,實現(xiàn)了一次東方美學(xué)與話劇的詩化“聯(lián)姻”,在話劇史上塑造了一個帶有民族鄉(xiāng)俗符號的可以永久享用的“劇中人”。第二,它是劇情化身。大傻楊擔當了作者和劇情的化身,說出了作者授意的話語。正像老舍說的:“人物出場的先后既定,情節(jié)的轉(zhuǎn)折也有了個大概,作者似乎便把自己要說的話分別交給人物去說,張三李四原來不過是作者的化身。”[7]609可見,作者設(shè)計“數(shù)來寶”,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劇中人”僅僅是化身、話筒的作用,放大了幕間的敘事張力,這種難以用文字和價值來衡量的大傻楊身后的角色藝術(shù),拓展出更多的化身空間和敘事空間。第三,它是典型“劇中人”。《茶館》人物表上有名有姓的人物有50人,傻楊名列其中。作者給了大傻楊土洋結(jié)合的角色定位,賦予了這位“土老帽”代替“旁白”的新的表演方式和敘述方法。老舍說:“寫小說和寫戲一樣,要善于支配人物,支配環(huán)境(寫出典型環(huán)境、典型人物)。”[11]548大傻楊的典型在于他以乞丐身份登上了話劇舞臺,開國人話劇另樣“旁白”之先河,成為三幕話劇幕間的典型人物。
(二)“數(shù)來寶”在三幕話劇中的作用
歐陽予倩曾說:“中國戲曲、曲藝的演唱,與中國的語言結(jié)合得很緊密而又富有表現(xiàn)力。無論是大鼓、相聲、單弦,比京劇更接近現(xiàn)實生活的口語,這種民間的曲藝,始終與人民的口頭語言保持著最緊密的聯(lián)系,適合話劇和新歌劇演員借鑒。”[12]歐陽予倩對漢語言民間曲藝的認識與老舍使用京味語言技巧習慣是一致的,“數(shù)來寶”就是從街頭巷尾走出的民間曲藝,這種草根曲藝形式,在話劇舞臺中富有民族化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力。老舍認為,快板與詩是相通的,“我們須在寫快板的時候,也要抱著把它寫成詩的愿望……形式可以不要,語言的美麗與音樂性卻非要不可,因為中國詩之所以成為中國詩必定因為它是中國語言的精華,這也就是民族風格的所在”[13]305-301。老舍視中國詩為漢語之美麗象征,把快板書當成詩詞來創(chuàng)作,讓快板書富有詩意,具有民族風格的音樂性。從老舍的文藝民族化創(chuàng)作理念中,讓人們看到大傻楊在《茶館》中擔負的作用至少有民族化用意、詩詞化用意和音樂化用意。
把握一臺話劇的基調(diào)非常重要,喜劇則歡快流暢,悲劇則深沉壓抑,歷史劇則折射時代特色,懸疑劇則神秘莫測,而《茶館》劇情基調(diào)則是悲喜交融,使人笑后而悲憫,旨在突出埋葬舊時代的主題。老舍設(shè)計幕前大傻楊,用明快的形式直觀地傳達劇情,引出對即演幕次人物、事件的闡釋。這種創(chuàng)意和用意,正如老舍對三個“幕前”所述:“幕與幕之間須留較長時間,以便人物換裝”;“或者休息時間可免過長”;“同時也可以略略介紹劇情”[13]305-307。這幾點互為依存,不可偏頗,應(yīng)該是老舍創(chuàng)作“數(shù)來寶”的部分初衷。而從實際演出效果分析,還能看到它更多的藝術(shù)作用。
其一,具有音樂性。從戲劇舞臺上的背景音樂方面來說,有一層含義是環(huán)境音樂,大傻楊“數(shù)來寶”表演了舞臺京味“音樂與音響”。按照老舍對快板書語言的闡釋,快板書原本就是一種通俗藝術(shù)形式,它既有詩的本質(zhì),又有音樂語言之美。例如:“哪位爺,愿意聽,《轅門斬子》來了穆桂英。”“王掌柜,大發(fā)財,金銀元寶一起來。”[17]305-307句中有明快的音節(jié),有押韻的字詞,加上快板“伴奏”,有吟詩之意境,有歌唱之歡樂,這些表現(xiàn)手法創(chuàng)造了幕間舞臺環(huán)境音樂。
其二,具有藝術(shù)張力和表現(xiàn)力。快板書似說似唱,通過說、唱以敘事和抒情,其說唱藝術(shù)獨具唱詞押韻方法以及聲響合一的表演形式,使“幕間戲”具有藝術(shù)張力和表現(xiàn)力。老舍曾說,快板書“字句容易調(diào)動,可以容納地道白話”[18]305-307如第一幕前,從表現(xiàn)茶館生意興隆到表現(xiàn)“戊戌變法”所用的唱詞:“這件事,鬧得兇,氣得太后咬牙切齒直哼哼。”第二幕前,表現(xiàn)軍閥混戰(zhàn)所用的唱詞:“為賣炮,為賣槍,幫助軍閥你占黃河他占楊子江。”“老百姓,遭了殃,大兵一到糧食牲口一掃光。”[10]324-325第三幕前,表現(xiàn)外敵入侵和國軍進京“國民黨,進北京,橫行霸道一點不讓日本兵。”[10]324-325其中的順口溜都是大實話、大白話,不僅交待了小茶館與個人、與民族、與國家命運為一體的黑暗世道中的種種怪象,而且充滿詩意,以藝術(shù)張力和表現(xiàn)力突出話劇主題。如溫靜君所言:“傳統(tǒng)說唱藝術(shù)的音樂旋律與當?shù)氐姆窖月曊{(diào)密不可分。中國話劇植根于漢語言的節(jié)奏韻律基礎(chǔ)上發(fā)展,所以傳統(tǒng)說唱藝術(shù)的節(jié)奏韻律直接影響著中國話劇的語言表現(xiàn)力。”[14]老舍把語言藝術(shù)張力和表現(xiàn)力當成一種作品趣味,這種運用趣味、表現(xiàn)趣味的目的,是挖掘小舞臺大社會的歷史和處在三個黑暗時代的人心,挖掘時代和文化,挖掘真知和真理。“數(shù)來寶”發(fā)揮了渲染時代悲哀、澄清事件曲直、表現(xiàn)人物命運、抓住觀眾心靈的作用。
其三,具有“假定性”。把大傻楊“數(shù)來寶”看做一種“旁白”,“旁白”也具有假定性。《茶館》反映了“裕泰”50年三個時代的變遷,一人演三幕的演員年齡需隨時代跨度而變化。如:茶館掌柜王利發(fā)在第一幕里,正值青春年華,年富力強。到第三幕時,他與同病相憐的另兩位悲劇主人公秦仲義、常四爺亦是老態(tài)龍鐘,垂垂老矣。“數(shù)來寶”形式上的歡快,與三位老人自撒紙錢的悲涼形成強烈反差。諸如此類演員的角色跨度之大,人物表演難度之高,都與人物化妝和幕間舞臺布景有密切關(guān)系。大傻楊承擔了消除觀眾因等待而可能產(chǎn)生的空檔感及不耐煩情緒的作用,充當了“劇中人”,這種“假定性”作用,增加幕與幕、人物與人物、時空與時空之間的鏈接,烘托出詩一般的意境,增加了舞臺空間的靈動飄逸之美。
三、土洋結(jié)合的藝術(shù)效果
大傻楊“數(shù)來寶”是用“表演生活化”和“生活表演化”有機統(tǒng)一來獲得觀眾認可的民族化嘗試,“將原本高于觀眾——需要觀眾仰視的舞臺降到與觀眾一致,甚至低于觀眾的平面上”[15]。拓展了舞臺視野,賦予劇本以外更大的經(jīng)緯空間,使原本甘甜中的苦澀余味無盡。老舍說:“要考慮讓觀眾聽了發(fā)生共鳴,讓他們也去想。……這樣觀眾不僅聽得懂,還會引導(dǎo)他們?nèi)ハ耄透辛α俊!盵1]258大傻楊的“數(shù)來寶”不僅產(chǎn)生了與觀眾共鳴的效果,而且啟發(fā)觀眾思緒,獲得了許多意料之外的厚重的藝術(shù)效果。
茅盾說:“文學(xué)作品的民族形式的主要因素是在民族語言基礎(chǔ)上加工的文學(xué)語言。”[16]從話劇創(chuàng)作藝術(shù)角度來看,大傻楊的“數(shù)來寶”最大的效果是使具有民族語言特色的曲藝符號恰如其分地鑲嵌在話劇劇場之中,成為三幕話劇之間珠聯(lián)璧合的“草珠項鏈”。《茶館》中有一只深層結(jié)構(gòu)之手在暗處點撥,使全劇貫穿著一條無形的悲愴主線。與這條主線交相輝映的是大傻楊的“數(shù)來寶”,它穿針引線,連綴起三幕戲,呈現(xiàn)出一條表層彩線。主線與彩線一主一輔、一明一暗、一粗一細、一悲一喜,彩線串連主線、闡釋主線、調(diào)味主線,強化作品內(nèi)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使深邃意境與獨特結(jié)構(gòu)達到完美融合。作者的用意“是為了加深讀者觀眾對50年社會變遷的理解,獨創(chuàng)性地用他的‘數(shù)來寶’來作見證,但卻與全劇結(jié)構(gòu)珠聯(lián)璧合,引人深思”[2]12。
(一)“數(shù)來寶”與三幕時代背景的映襯
珠聯(lián)璧合體現(xiàn)在“數(shù)來寶”對每一幕的“映襯”上。“數(shù)來寶”濃縮了劇情,向觀眾介紹即將上演的內(nèi)容。第一個幕前,448個字,22句“臺詞”。“那時候的政治黑暗,國弱民貧,洋人侵略……戲中的第一幕,正說的是頑固派得勢以后,連太監(jiān)都想娶老婆了,而鄉(xiāng)下人依然賣兒賣女,特務(wù)們也更加厲害,隨便抓人問罪”[17]753,映襯出晚清必亡的主題。第二個幕前,290個字,17句“臺詞”。“這一幕里的事情雖不少,可是總起來說,那些事情的所以發(fā)生,都因為軍閥亂戰(zhàn),民不聊生”[17]753,映襯出兵荒馬亂,民國不國的亂象。第三個幕前,219個字,14句“臺詞”。“第三幕最慘,北京被日本軍閥霸占了八年,老百姓非常痛苦,好容易盼到勝利,又來了國民黨,日子照樣不好過,甚至連最善于應(yīng)付的茶館老掌柜也被逼得上了吊。什么都完了,只盼著八路軍來解放”[17]753。映襯出黑暗即將過去,象征著民族新生的曙光就要到來的寓意。
這種映襯取得了用“數(shù)來寶”內(nèi)容切換時代背景的效果。如第一幕前“數(shù)來寶”:“官人闊,百姓窮,朝中出了個譚嗣同。”[10]323-325帶有清末內(nèi)憂外患、國弱民貧和戊戌變法的時代符號。第二幕前“數(shù)來寶”:“現(xiàn)而今,到民國,剪了小辮還是沒有轍。”[10]323-325帶有改朝換代后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民國符號。第三幕前“數(shù)來寶”:“自從那,日本兵,八年占據(jù)老北京。”“(哼)國民黨,進北京,橫行霸道一點不讓日本兵。”[10]323-325帶有國土八年淪陷,抗戰(zhàn)勝利,國軍又來騷擾的符號。老舍把對三個舊時代的憤恨聚焦在這九百多個漢字的字里行間,形成了一幅濃縮的歷史畫卷,道出了三幕話劇主題:晚清至民國一步步走向崩潰的中國。但第三幕前“數(shù)來寶”詞句“小姑娘,別發(fā)愁,西山的泉水向東流”[10]323-325,預(yù)示了黑暗的歷史就要結(jié)束,東方的天就要亮了。
話劇舞臺對時代背景的映襯方法有音樂、燈光、布景、語言等切換。在《茶館》之前,作者曾嘗試過用民間藝術(shù)來達到對舞臺時空切換的方法,如話劇《駱駝祥子》一啟幕,劇場就響起了京腔說唱叫賣的音樂,這種京腔以民族藝術(shù)形式、民族地域氣息將觀眾帶入了規(guī)定的時代場境中去。京腔叫賣聲和“數(shù)來寶”兩種民間藝術(shù)形式,在話劇劇場里都是以說唱表演來達到對時代背景映襯的。
(二)“數(shù)來寶”與劇本語言風格的遙相呼應(yīng)
珠聯(lián)璧合體現(xiàn)在“數(shù)來寶”與幕中語言風格遙相呼應(yīng)。這種以戲外局部語言呼應(yīng)全劇的藝術(shù)風格與布萊希特式戲劇有相通之處,在“陌生化效果”戲劇學(xué)派形成的過程中,布萊希特繼承和革新自身民族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借鑒了東方戲曲藝術(shù),吸收了希臘悲劇元素,把一些表面上不相通的戲劇元素相結(jié)合,轉(zhuǎn)變成布式戲劇。而老舍將中國民間戲曲元素巧妙地“化”在了話劇舞臺上,把京味俚語優(yōu)勢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實現(xiàn)了跨疆域、跨民族的藝術(shù)元素之間優(yōu)勢互補,使得快板書與三幕劇相得益彰。“數(shù)來寶”拓展了話劇幕間銜接全劇的藝術(shù)空間,呼應(yīng)了全劇的時代元素、思想元素和諸多藝術(shù)元素。《茶館》全劇沒有貫穿全劇的事件和情節(jié),沒有揪心的懸念和激烈的沖突,取而代之的是獨特的典型化人物及其生動的個性化語言。快板書過于“自然化”的設(shè)置點綴突破了戲劇常規(guī),融合了民族藝術(shù)元素,創(chuàng)新了老舍式民族曲藝元素與話劇舞臺相結(jié)合的藝術(shù)形式,
一是與劇本里的語言風格相呼應(yīng)。如第三幕出現(xiàn)的小劉麻子語:“柳葉眉,杏核眼,櫻桃小口一點點”;賣雜貨的老楊語:“美國針、美國線、美國牙膏、美國消炎片。還有口紅、雪花膏、玻璃襪子細毛線。箱子小,貨物全,就是不賣原子彈!”“美國針、美國線,我要不走是混蛋!”[18]304-307幕中出現(xiàn)了與“數(shù)來寶”相同的快板書,形成了“數(shù)來寶”與舞臺演出的民族語言風格的“同聲”呼應(yīng)。“我們不能叫劇本中的每一句話都是這樣的明珠,但是應(yīng)當在適當?shù)牡胤竭@么獻一獻寶 ”[19]539。老舍極其吝嗇筆墨,惜墨如金,但在他的筆下一字一句都鮮活傳神,極富魔力。將“數(shù)來寶”與幕中的句子在語言棋盤里變成“同聲”明珠,是老舍的語言智慧,也是他舉棋尋道的藝術(shù)追求。
二是通過語言風格的呼應(yīng)進而對全劇相呼應(yīng)。“數(shù)來寶”言簡意賅地提煉了三幕時代、事件、人物命運等主題元素,用輕松、歡快的娛樂形式,表演了劇本內(nèi)容、主題思想、時代背景,形成了對全劇的呼應(yīng)。布萊希特說:“我們把劇院當做一種娛樂場所,這在美學(xué)里是理所當然的。……‘戲劇’就是要生動地反映人與人間流傳的或者想象的事件,其目的是為了娛樂。”[2]301老舍的“數(shù)來寶”藝術(shù)創(chuàng)造并超越了劇場娛樂,呼應(yīng)了舞臺演出的藝術(shù)要素和主題思想,在喜中有悲的劇場氣氛里,傳遞出詛咒黑暗時代的深邃意境。
(三)“數(shù)來寶”對三幕話劇的“串聯(lián)”效果
珠聯(lián)璧合體現(xiàn)在“數(shù)來寶”對三幕話劇的“串聯(lián)”效果上。“數(shù)來寶”與三幕話劇可視為一種雙線式結(jié)構(gòu),因為它借鑒了“間離效果”藝術(shù)手法,像一種拼圖,使觀眾靠近“劇中人”,更多地對主題及人物命運進行思考,讓觀眾在“接縫”中清醒頭腦,釋放出理性判斷。“數(shù)來寶”作為彩線輔助三幕主線發(fā)展劇情,實現(xiàn)了幕間與話劇演出的“虛”與“實”的結(jié)合。這種有主有輔、有明有暗、有喜有悲的雙線波浪式劇情發(fā)展,產(chǎn)生了明顯的藝術(shù)效果。
其一,彩線“串聯(lián)”主線。其“串聯(lián)”不是盲目的鏈接,而是故意在時代跨度的幕間,在看似松弛的彩線中,起伏著笑中含淚的樂曲,把三個時代、若干事件和相關(guān)人物“串聯(lián)”得天衣無縫,使得整場話劇似綿延、曲折、高潮迭起的完美樂章,與深層結(jié)構(gòu)交織成內(nèi)在聯(lián)系緊密的渾然整體。其二,彩線闡釋主線。其闡釋是演唱、是表演、是介紹,使觀眾既能走出劇情,又能走進劇情,始終跟隨時代、社會、人物三位一體的動態(tài)脈絡(luò),更多地關(guān)注小茶館所反映的主題,關(guān)注黑暗時代必然產(chǎn)生的悲慘的人物命運,為觀眾留下更多的理性思維空間。其三,彩線調(diào)味主線。正如老舍所說:“觀眾要求我們的話既有思想感情,又鏗鏘悅耳;既有深刻的含意,又有音樂性;既受到啟發(fā),又得到藝術(shù)的享受。”[1]243而“數(shù)來寶”散發(fā)出濃郁的生活氣息,烘托出熱烈的、親切自然的舞臺效果和劇場效果,為觀眾帶來了強烈的藝術(shù)感染,可謂特殊的“氣氛道具”。“數(shù)來寶”構(gòu)成了“幕間戲”與舞臺畫面的故事鏈條,給觀眾帶來觀“戲”的新的思維和視覺沖擊,讓觀眾在落寞與悲愴的劇情中真切地看到一縷光束。而歡快其表、悲慘其中的基調(diào)又讓觀眾輕松進入劇情,仿佛置身北京街頭,快板書引發(fā)人們開口一笑,又被劇場籠罩的一層既可加重又可釋放似悲劇情緒的灰色面紗帶進了復(fù)雜心境之中。
顯然,是大傻楊這一典型人物創(chuàng)造了典型環(huán)境,才得以融劇情一起助推觀眾波動的心境的。這種典型人物和典型環(huán)境應(yīng)該說又是一種藝術(shù)效果。《茶館》劇中有許多典型人物,他們以群體形式突出了全劇的典型性,而大傻楊則是以獨特的“劇中人”身份成為極具性格化和動作性的典型人物,并用快板說唱表演出了幕間的典型環(huán)境,創(chuàng)作了獨特的環(huán)境藝術(shù)之美。
眾所周知,北京人藝和焦菊隱對《茶館》的二度創(chuàng)作,在國內(nèi)外經(jīng)久不衰,其巨大成就應(yīng)當歸功于劇本作者、話劇導(dǎo)演和演員共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同時,大傻楊的“數(shù)來寶”在幕間嫁接中所起到的畫龍點睛的作用,也成為茶館里的一道亮麗風景。盡管它的文藝嫁接作用是輔助性的,但對三幕話劇增光添彩的作用遠遠超出了老舍當初的設(shè)計預(yù)期。它堪稱中國式話劇的帶有珠光寶氣的“草珠項鏈”,永久性地成為茶館里的一串京味藝術(shù)之花。
[1] 老舍:老舍的話劇藝術(shù)[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82.
[2] 楊迎平:老舍的精神世界與文化情懷[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3] 馬云:老舍的話劇創(chuàng)作與舞臺視野[J].文藝研究,2006(11).
[4] 夏穩(wěn):談中國話劇藝術(shù)的民族化和表現(xiàn)力[J].戲劇之家,2014(4).
[5] 方堃林:舞臺燈光與音響效果在創(chuàng)造上的配合[J].演藝設(shè)備與效果,2008(1).
[6] 鄭彥清:話劇藝術(shù)創(chuàng)新談[J].藝術(shù)教育,2010(5).
[7] 老舍.話劇的語言[M]//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
[8] 吳懷斌,曾廣燦:老舍研究資料(下)[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
[9] 張彩琴:淺談曹禺話劇舞臺說明的特點[J].山西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0(5).
[10] 老舍.〈茶館〉附錄[M]//老舍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
[11] 老舍.人物、語言及其他,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
[12] 賀鍵.記歐陽予倩和羅常培、老舍談話劇臺詞課[J].文藝研究,1982(1).
[13] 老舍.詩與快板[M]//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
[14] 溫靜君.論話劇臺詞藝術(shù)中的傳統(tǒng)說唱因素[J].齊魯藝苑,2008(5).
[15] 郭暉.“生活表演化”與“表演生活化” [J].藝 海,2010(8).
[16] 譚霈生.“話劇民族化”意味著什么?[J].:人民戲劇,1982(6).
[17]老舍.談茶館[M]//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
[18] 老舍.〈茶館〉第三幕[M]//老舍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
[19] 老舍.戲劇語言[M]//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
【責任編輯:郭德民】
2015-09-15
董克林(1958—),男,河南商丘人,北京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碩士,商丘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副院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xué)研究。
I206.7
A
1672-3600(2015)11-00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