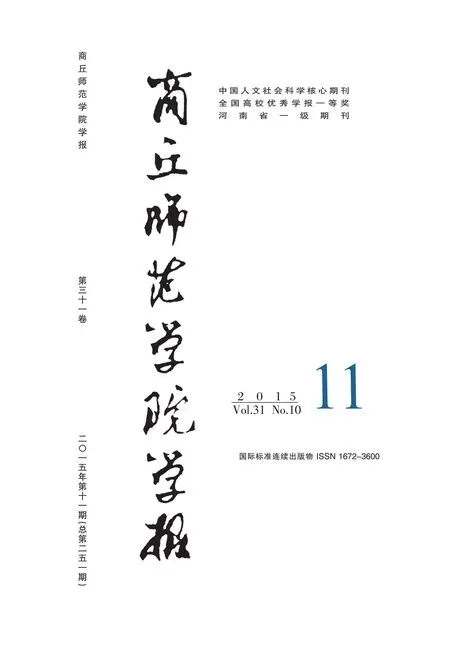當前國內敘事學文本批評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以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理論為例
楊 洪 敏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當前國內敘事學文本批評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以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理論為例
楊 洪 敏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當前國內敘事學文本批評中存在一定問題,如不加以澄清,對敘事學研究大有影響。以最常用的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理論為例,發現存在對該理論表述上的準確性問題、對理論本身的誤讀以及機械套用現象。由于西方敘事學與中國敘事學的對接問題仍比較突出,因此,如何實現兩種知識體系的有效通約性是當前敘事學研究需要完成的任務。
敘事學;文本批評;符號矩陣理論;問題
在西方敘事學中國本土化過程中,國內學者運用敘事學理論解讀具體文本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具有個別性,有的則具有普遍性。為了對這些問題加以澄清,下面以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理論的運用為例加以詳細說明。之所以選擇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理論,是由于當前國內敘事學文本批評中,根據筆者的統計,最多的是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和行動元模式。
一、對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理論表述的準確性問題
筆者所講的表述準確性問題,是指在目前對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理論中關于邏輯項之間關系的表述上,國內學者使用了多種表達,有的甚至多有含糊之處,極容易引起誤解。為了直觀說明,首先列出符號矩陣圖(圖1):

圖1 符號矩陣圖

圖2 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理論英文表述圖
在該圖中,三種關系分別表述為“relation of contradiction”、“relation of contrariety”、“relation of complementarity”。顯而易見,國內學者在理解“contradiction”和“contrariety”上存在一定問題,從而對讀者造成了一定困惑。如一些國內著名學者的如下論述(參見圖3):“格雷馬斯……提出了解釋文學作品的矩陣模式,即設立一項為X,它的對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還有與X矛盾但并不一定對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即A與B、-B與-A之間屬于對抗關系,A與-B、B與-A之間是互補關系,A與-A、B與-B之間是矛盾交叉關系。”[2]49

圖3 國內一些學者表述矩陣模式圖
上面論述中很容易引起歧義的是:既然X的“對立一方是反X”,說明兩者的關系是“對立”,后面又講“A與B、-B與-A之間屬于對抗關系”,這里顯然對橫軸關系使用了“對立”和“對抗”兩種表述。而根據格雷馬斯的理論,兩者本質上相同,應規范為一種表述。而“對立”和“對抗”在漢語中的意義明顯是不同的,“對抗”比“對立”程度更嚴重。對于對角線關系:“有與X矛盾但并不一定對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A與-A、B與-B之間是矛盾交叉關系。”顯然實際上使用了三種表述:“矛盾但并不一定對立”、“矛盾”、“矛盾交叉”,這里的問題除了應規范為一種表述外,主要是“矛盾但并不一定對立”的表述本身在邏輯上講不通,因為按照對“矛盾”的解釋,矛盾即“非此即彼”,“矛”與“盾”兩者一定是“對立”的。“矛盾交叉”這一表述也不太嚴謹。此外,還有著作[3]204將橫軸項表述為“對立”,將縱軸項表述為“無關系”。
為了厘清上述表述,我們不妨著眼于格雷馬斯的理論本身。“格雷馬斯文學符號學理論中最著名的是‘符號矩陣’,它源于對亞里士多德邏輯學中命題與反命題的詮釋。”[2]49為此,讓我們引入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方陣”:下圖(圖4)[4]65-66所示為表示A、E、I、O之間四種真假關系的“邏輯方陣”。

圖4 邏輯方陣圖
顯然該圖對各邏輯項分別表述為“反對關系”、“矛盾關系”和“從屬關系”。筆者認為可以此為依據翻譯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因為這就實現了與邏輯學知識的通約性。另外,鑒于當前學者已經使用的方便(如《論意義:符號學論文集》一書[5]使用“反義”和“蘊含”的表述),筆者認為“反對”和“反義”、“從屬”和“蘊含”可以通用,其余表述則一概不采納。這樣也就基本符合格雷馬斯 “relation of contrariety”、“relation of contradiction”、“relation of complementarity”三種關系的含義。
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還要從邏輯上細致區分“矛盾關系”和“反對關系”的差異。筆者下圖(圖5)舉例分別直觀表示兩者的區別:

圖5 矛盾關系與反對關系對比圖
明顯看出,矛盾關系中雙方構成全集,非此即彼;而反對關系中雙方處于排斥,但對于全集而言,不是非此即彼,存在不屬于兩者的第三種情形。以交通信號燈為例:“紅燈”與“綠燈”構成反對關系,因為還有“黃燈”狀態;而“紅燈”與“非紅燈”構成矛盾關系。
二、對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理論的誤讀
除了上述所論及的表述的準確性問題外,對理論的誤讀也是值得引起重視的一個方面。如果說準確性只是翻譯造成的,而誤讀則直接導致理論的錯誤。最明顯的來自于朱立元主編的《當代西方文藝理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中對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的解釋說明。鑒于該書的重要學術地位,有必要對之進行澄清。下圖是該書中使用的符號矩陣圖:

圖6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使用的符號矩陣圖
書中作者說明了圖式的四項:“在格雷馬斯看來,文學故事起于X與反X之間的對立,但在故事進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從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當這些方面因素都得以展開,故事也就完成。”[6]253在該圖中,明顯可以看出,圖中X項的對角線應為非X,反X項的對角線應為非反X;而書中將兩項顛倒了,將X項的對角線設為非反X,將反X項的對角線設為非X。
為了詳細說明,書中還特別引用了美國文論家杰姆遜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中對中國古典小說《聊齋志異·鴝鵒》運用該理論進行的解讀,并列出了以下圖式(圖7):

圖7 《鴝鵒》解讀圖
仔細比較二圖,很明顯杰姆遜的圖式是正確的。這一點已引起一些細心讀者的注意,指出該書中提供的圖式“影響廣泛,很多文學理論書籍都采用了這一圖式。但是這里明顯存在一個矛盾,在這個圖式中第一項為X,第二項為反X,第三項為非反X,第四項為非X。而在杰姆遜所作的分析中,第三項為非人,第四項為人道,也就是反人的矛盾項,即非反人。若將人再抽象為X,則第三項為非X,第四項為非反X。所以在第三項和第四項的位置安排上正好是顛倒的。綜上所述,《當代西方文藝理論》所引圖式,一方面與所引用的杰姆遜的論據是不相符合的。”[7]
值得說明的是:上述錯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國內類似研究的誤區。如有學者[8]在研究斯坦培克的《菊花》時,首先按照人物關系得出了以下分析圖(圖8):

圖8 某學者的《菊花》人物關系圖
在該圖的基礎上,該學者從意義角度按照“女人”和“反女人”進行了深層分析,認為“伊莉莎的女人性和亨利的反女人性因素之間的二元對立是故事的基本線索,菊花和補鍋匠是故事發展中引入的輔助因素,菊花的非女人性是故事發展的支撐點,而補鍋匠的非反女人性則是故事發展的催化劑。這四個義素相互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兩個義素群之間的對立關系、各義素群內部的統一關系以及義素的動態發展變化使故事產生了豐富的內涵”[8],從而得到以下圖式(圖9):

圖9 某學者對《菊花》所作的深層分析圖
顯然,該圖中的三、四項是顛倒的,“女人”的對角線應當是“非女人”,“反女人”的對角線應當是“非反女人”,這和《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一書中提供的矩陣圖的錯誤是一樣的。
三、對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理論的機械套用現象
機械套用是當前對西方敘事學理論運用中出現的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國內很多研究熱衷于引進一個理論模型,然后將一個中國文本進行一一對應,而對于理論深層的意義挖掘不夠。對格雷馬斯符號矩陣模型的套用現象是十分明顯的,筆者搜索了關于格雷馬斯的研究文章,大多均屬于這種情形,最突出的是尋找作品中的某一人物進行四項對應。如在研究《彼得堡》時,往往將“杜德金”、“參議院”等人物地名進行簡單對應,從而可以得到以下圖式(圖10)[9]:

圖10 國內套用格雷馬斯符號矩陣模型研究《彼得堡》圖
這種圖式是目前國內研究的主要形態,這對文本的分析固然是必要的,但有必要進一步深化。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然而在很多用此模式的文本批評中卻存在生搬硬套、墨守成規、亦步亦趨的教條傾向。其表現為將一文本斷章取義,抽出四個人物形象,然后將此四人與符號矩陣中的四項做簡單的對應,然后進行分析……雖然有一定的意義,但并不是符號矩陣的精髓所在。”[7]
那么,符號矩陣的精髓是什么呢?顯然是為了呈現文本深層的意義,因此應當將矩陣中的四項進行意義賦值。當然,如果人物符號能代表一種價值時,這種對應也是正確的,但是不再從意義的角度使用人物符號,而僅僅以人物符號滿足四項時,這種分析則是膚淺的。這里還以杰姆遜對符號矩陣具體實踐為例,他對《聊齋志異·鴝鵒》中的分析圖式中運用了“主人”、“鳥”、“王爺”等人物,其實杰姆遜是在“金錢”、“權勢”、“友誼”等意義角度使用人物符號的。為了說明意義賦值的重要性,再看杰姆遜對康拉德的《吉姆爺》的分析,他使用了“價值”和“行動”,行動是做事取得成功, 價值是體現在朝香客的被動性中的意義,從而得到以下圖式(圖11)[10]130-131:

圖11 杰姆遜對《吉姆爺》的分析圖
可見,在該圖中,深層的是意義分析,人物符號處于第二層面。也就是說,人物只是意義的體現者:“非價值與非行動的結合是坐在甲板座椅上的人, 非行動和價值的結合是朝香客, 行動和非價值的結合就是虛無主義的冒險家, 而價值和行動的結合則是作者找到的吉姆爺。”[7]而國內學者大都習慣于人物層面的賦值,比如在對《祝福》的分析中,就將X項賦值為被壓迫者祥林嫂,反X項賦值為壓迫者魯四老爺,非X項賦值為非壓迫者柳媽,非反X項賦值為幫手“我”。對立項是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階級斗爭,這樣的分析在符號矩陣的面紗下依然是我們熟悉的社會學批評。
有學者從“問”的角度進行分析,得到以下圖式(圖12)[7]。

圖12 某學者對《祝福》的分析圖
這種研究將意義研究放在首位,在此基礎上進行人物分析,而不是僅僅進行人物關系的簡單對應和歸類,這是國內研究需要提倡的。
四、對當前國內敘事學文本批評中存在問題的思考
最后值得說明的是,不僅僅對于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理論存在上述現象,對格雷馬斯的行動元模式、普洛普敘事功能的分析也存在類似的問題,特別是機械套用情況:往往在文本中尋找主體、客體、幫助者、發送者進行對應;總是習慣于套用序列并尋找類似的敘事功能。這種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更應在此基礎上思考這些方法中蘊含的深層意義。
本文分析雖然是以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理論為例,但是揭示出文本批評中存在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就目前而言,西方敘事學本土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還包括:過多依賴熱耐特的術語,其中又以敘述者、敘述視角、敘述人稱和敘述時間為主;對敘述聲音、敘事層次、敘述進程關注很少;鮮有將敘事話語和故事結合,提煉出有效敘事規律;多采取靜態的角度,未將闡釋語境納入到文本解讀,等等。
上述問題從本質上講是一個文化對比和影響研究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從表面看是翻譯的問題,而從深層看,則是如何對待西方話語中心主義的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放棄對中國文人根性的本土化探求而求助于簡單嫁接西方理論是無法深入澄清問題的。影響研究在此成了低級的形式邏輯游戲。平行研究的意旨雖然是一種開放式的交流,但長期以來其范式和框架都追隨西方,這套結構背靠著抽象的普遍性的形而上假設和演繹邏輯和形式理性的思維根子。”[11]尤其值得說明的是,由于西方敘事學與中國敘事學的對接問題仍比較突出,因此如何實現兩種知識體系的有效通約性,這是當前敘事學研究需要完成的任務。
[1]Martin McQuillan.The Narrative Reade[M].London:Routledge,2001.[2]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杰拉德·普林斯.敘述學詞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4]南開大學哲學系邏輯學教研室.邏輯學基礎教程[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
[5]格雷馬斯.論意義[C]//符號學論文集.吳泓緲,馮學俊,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
[6]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7]康建偉.對“符號矩陣”在文學批評實踐中的反思[J].中北大學學報,2008(1).
[8]姜淑芹,嚴啟剛.簡析《菊花》的敘事結構[J].外國文學研究,2005(2).
[9]管海瑩.《彼得堡》的多元敘事結構[J].俄羅斯文藝,2011(4).
[10]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1]上官儒燁.對弗朗索瓦·于連的漢學研究的研究[D]. 成都:四川大學, 2006.
【責任編輯:郭德民】
2015-08-12
楊洪敏(1981— ),女,內蒙古烏海人,講師、博士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
I0-03
A
1672-3600(2015)11-006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