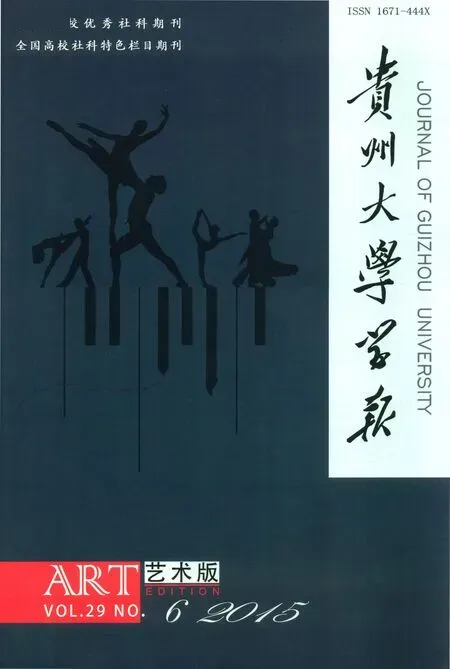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當代重構
許 艷,廖明君
(廣西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6)
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縣地處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帶,生活著壯族、漢族、苗族、仡佬族等民族,其中隆林彝族現有人口五千多人,主要居住在德峨、新州、豬場、者浪等鄉鎮的十幾個村屯。
隆林彝族自云南遷來,最早的一支在當地生活已有一千多年歷史。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改革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隆林彝族文化遭遇了嚴重的破壞,不但經書被燒掉,畢摩不允許做法事,鮮艷、華麗的民族服飾也被禁止制作與使用,使得彝族服飾藝術一度陷入斷裂與消亡的危機之中。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增強,隆林彝族文化開始復興,隆林彝族服飾藝術也重現了生機,彝家女孩火紅的百褶裙、閃亮清脆的銀飾、端莊美麗的瓦片帽,男子英俊瀟灑的“查爾瓦”、威嚴莊重的“天菩薩”,成為了一年一度彝族火把節的火把場上最靚麗的風景線。
一、隆林彝族服飾藝術變遷歷程
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變遷歷程,大致經過了傳統社會形態下的沿襲與承續、民國前后的涵化與整合、1949-1978年間的斷裂與消解三個階段。
(一)傳統社會形態下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沿襲與承續
彝族服飾藝術作為一種物質文化,它的產生發展、衍變,反映了本民族的歷史變遷、地理環境、社會形態和經濟生活。[1]據考證,彝族先民與西北氐羌族群有淵源關系,與其他各族不斷融合而形成今天的民族共同體——彝族。彝族是活躍在我國西南邊陲的民族共同體,長期以來靠放牧生活;明清以前,滇東、黔西的彝族與今四川涼山彝族服飾大致相同,服飾藝術的發展變化速度也很緩慢,到了改土歸流以后,各地彝區人民在中央政權和強勢文化的雙重壓迫下服飾習俗漸漸有了較大的變化。
歷史文獻對隆林彝族的記載著墨不多,然而通過其遷徙的時間與地域來看,改土歸流以前,隆林彝族服飾與云南東川、會澤、曲靖、沾益、興義、安順、冊亨等地的服飾大致相同。如光緒《東川府志》上記載說:“黑玀玀披氈戴笠,壯者青藍布裹頭,短衣長褲,女則衣裙皆長,跣足。營長火目家多用鍛帛,……白玀玀,麻衣麻裙。”[2]光緒十一年《沾益州志》云: “白玀玀之種二,而男耕女織習尚簡樸,衣冠禮儀一如漢人,惟彝語尚未盡改,居山者,男子裹頭跣足,以草束腰,女彝耳帶銅環,披羊皮,事耕鑿 (鑿),于諸彝中向化最先,蓋其質性原與漢人不相遠也。……黑玀玀……衣短青衣,髻向前,以布繞其髻,出入配短刀,性嗜酒……女長裙細褶……蠻娘能在織連錢錦貝,飾花裙百褶”[3]。咸豐四年所修《興義府志》上也記載:“倮儸男子服色青白布,女人辮發用青布纏之首,戴梅花,耳垂大銀環,衣長,裙以二十一幅布為之”[4]。咸豐《安順府志》說: “倮儸,男子服青白布,女人辮發。用青布纏首。戴梅花。耳垂大銀環。衣裙皆長,裙以二十余幅布為之。”[5]此外,《皇清職貢圖》、《冊亨縣鄉土志》[6]、《安南縣志》[7]等均有關于彝族先民 “倮玀”穿著習俗的記載。
根據上述文獻記載可知,此時彝族婦女尚能自制衣服,且內部有著嚴格的等級區別:黑彝服飾可用鍛帛等高檔面料,白彝只能用麻料;黑彝尚黑,白彝尚白。其服飾藝術的總特征為:男子椎髻向前,以布纏髻,戴 (左)耳環,出入佩刀,女子上衣長,束腰,下穿百褶長裙,赤足 (土司及統治者穿鞋),男女皆披氈或羊皮,喜用銀裝飾身體,如銀耳環、銀花額貼、銀鏈等。而到了清中期以后,白彝已有不同程度的漢化,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衣冠禮儀一如漢人”[8]的情況。
(二)民國前后隆林彝族服飾藝術涵化與整合
民國前后,隆林彝族服飾藝術主要呈現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與周邊民族的服飾藝術風格與裝飾手法日益相近,二是吸收了滿清及漢族民間服飾藝術的成分,整體處于不斷的涵化與整合之中,進而發展出了獨特的服飾藝術風格。
一)鮮明的地域特色
經過累世的生活勞作,隆林彝族不僅適應了桂西北高寒山區的自然地理氣候,也通過族際間的交流不斷吸納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形成了該地區特有的服飾藝術風格。如民國時期雷雨在《西隆苗沖紀聞》中說:“住于苗沖者,尚有果羅及來子二種人,通常亦被曰為苗子,然除言語之外,他固無以異于漢人也……苗族雖以服裝而異,但苗男之服裝,并無差異,即與一般客人,土著,及果羅,來子諸族,亦無二致。其服裝多好藍,白,青,黑諸色,與他族無大差別”[8]。可見,當時隆林各族男子服裝已基本相同,而女子服裝除苗族之外,皆“無以異于漢人”。
不僅服裝款式結構基本相同,隆林各族民眾的織造技術、用色習俗、配飾及裝飾手法等方面亦存在許多的共同之處。如各族民眾大多自己種青蔴織布,但也有人從市場上買回棉花自己織布,織好的布用藍靛經浸、染、洗、曬等步驟將白布染成藍色或黑色。隆林德峨的阿稿寨至今還保留有8個彝族人曾經使用的染布池,苗族、壯族的許多村寨里也還保留著類似的傳統染織技術和染布池。由于隆林盛產野靛草,各民族傳統服飾中上衣以藍色、藍黑色等為主體色彩體系,下裳以黑色、藍黑色為主要表現色彩,服飾品中的鞋子以黑色為主,而選用一些較亮的紅、藍、綠等色繡上花葉、蝶鳥等圖案做點綴,裝飾都集中在襟口、下擺、袖口、褲腳及圍腰頭、鞋頭等位置,裝飾技藝多以刺繡為主,輔以剪貼、鑲緄等手法。而在配飾方面,女性雖愛銀、飾銀,但卻不求華麗繁復,裝飾得恰到好處;新生兒滿月或周歲時都有外婆送背帶的習俗,背帶形制以深色或紅色等棉料為底料,配上六塊、八塊或十二塊背帶芯及貼花彩布背帶柱組成。此外,鞋墊、荷包等裝飾也有許多共同之處。
二)滿漢之風盛行

圖1 清末隆林彝族馬面裙 (藏于隆林民族博物館)
民國前后,社會動蕩不安,地處偏遠山區的隆林彝族社會不僅受到了當時整個社會環境變革的沖擊,還因當地種植、交易鴉片的影響,對外經濟文化聯系空前繁榮。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隆林彝族服飾又吸收、融入了滿清及漢族服飾的成份,出現了“叮當檔”裙、馬面裙、琵琶襟坎肩、長衫馬褂等具有典型漢族及滿清風格的服飾。
1.“叮當檔”裙
清末以后,隆林彝族女子裙裝款式變化較大,早期風行鳳尾裙,咸豐同治年間“魚鱗百褶裙”深受婦女喜愛,到光緒時又出現過一種名為“叮當檔”的裙裝,其裙上十數條劍狀飄帶,端系金屬小鈴鐺,動則發出悅耳的叮當聲響。筆者在田野考察期間多次聽當地老人描述一種類似的“叮當檔”裙。住在德峨街上的95歲老人黃阿妹說:“這種裙子只有少數有錢人才穿,裙子很長,差不多快到地了,裙子上面掛滿了鈴鐺,都是銀做的。走路叮叮當當的響。”①受訪人:黃阿妹,訪談時間:2014年1月18號13點,訪談地點:德峨黃阿妹家中。彝族畢摩王文魁說:“我很小的時侯,記憶中有見過這種裙子,叮叮當當的,很有節奏,好聽極了。”②受訪人:王文魁,訪談時間:2014年1月14號22點,訪談地點:德峨黃阿妹家中。
2.馬面裙
馬面裙是中國漢民族傳統裙裝中很重要的一種,是明清女子裝束經久不衰的典型搭配。馬面裙是以數幅整幅緞面接合而成的長裙,前后各有20-27cm的平幅裙門,這個平幅裙門俗稱“馬面”,在平幅裙門和裙擺上繡有各種精致的繡花花邊或鑲、緄、拼貼工藝裝飾。“馬面裙”整體呈現平面的圍式造型,側縫不縫合,兩頭分別用兩根腰帶維系于腰間達到重合以形成閉合的裙裝效果。據隆林彝族老人介紹,馬面裙在建國以前在隆林彝族村寨還比較盛行,一開始可能只是貴族婦女才能穿,以表身份。后來,平民百姓也開始效仿,但主要是在婚禮等喜慶場合穿著,且需要“向別家借來”,婚禮時8人 (可能是伴娘)圍坐一桌,兩兩穿不同顏色的衣裙套裝,有粉色、綠色、黃色等。現隆林民族博物館存有兩件馬面裙,材質華貴,工藝精美 (圖1)。

圖2 琵琶襟坎肩

圖3 清末隆林彝族長衫馬褂
3.琵琶襟坎肩
如圖2所示的服飾是照片中的老人根據前人的描述及自己的記憶仿制的一套仿古服飾,于2011年制作,由頭衣帽子、上衣的襖、坎肩和下裳褶裙組成。圖中,老人身上穿的坎肩具有明顯的滿清服飾風格,從中仍能窺見當時服飾藝術交融的盛況。
4.長衫馬褂
長衫馬褂是清末民國時期男子最普遍的服裝。長袍為右衽大襟,狹窄直身,長至腳踝上兩寸,袖長與馬褂齊,多為藍色。馬褂通常作為正式場合的一種禮服形式與長袍搭配,衣長及臀圍,有琵琶襟、對襟、右衽大襟多種,紐扣有5、7、9顆不等。今德峨阿稿彝寨保存有一張彝族地主楊廷鳳③楊廷鳳生于清朝末年,卒于1949年。的照片,如圖3所示,照片中的楊廷鳳頭戴西式寬沿圓禮帽,身穿直領對襟深色外衣——馬褂,前胸門襟處有7顆盤扣,內穿淺色長衫,長衫下配長褲,與當時漢區流行的禮服幾乎一致。據當地老人說長衫配馬褂的著裝風格在隆林彝區流行了很久,有的在長褲的外面只穿一件右衽大襟的長衫衣,腰間系一根同色布腰帶,衣服通常為黑色粗布制作。
由上觀之,這一時期的隆林彝族服飾已與改土歸流以前有了很大的區別,一方面在與周邊各民族共同相處、融合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地域特色的服飾風格,另一方面又跟隨時代風氣吸納滿漢服飾之精華,可謂兼收并蓄,博采眾長,在涵化、整合中不斷地發展變化。
三)1949-1978年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斷裂與消解
1949-1978年,在鄉村改造運動以及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組織體系和權利網絡的全面建構下,逐步開始了對于傳統文化的“破舊立新”式改造,使得民族傳統文化從形式到內涵、從表象到根基之間逐步趨于分離甚至斷裂的境況,尤其在“文革”十年期間,所有的傳統思想、行為、文化、藝術都受到了極大的沖擊。這一時期,隆林彝族服飾藝術也同樣受到影響,變化的速度異常迅速。

圖4 20世紀60年代隆林彝族服飾

圖5 王秀珍縫制的彝族服飾
住在新洲、團石等地的彝族老人告訴筆者:“那時候我們都挨抓去剪短發,以前用的耳環、手鐲、項圈全都要上交,衣服上有花花不能穿……要是被紅衛兵發現,就要被批斗。”因此,隆林彝族群眾只能穿著凈黑或凈藍色土布衣褲,除了實用功能外,幾乎無其他裝飾,而傳統的女子繡花服飾也都難以見到,圖案和裝飾技藝也基本失傳。

圖6 1989年第一次大型火把節上的彝族服飾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隆林彝族服飾藝術在結構形式上較以前變化不大,但卻存在以下問題:第一,服裝款式單一,傳統的女子盛裝服飾逐漸消失。第二,服飾色彩減少,不管男性還是女性的服飾,普遍使用黑、深藍、灰色等顏色,很少運用其他鮮艷的顏色;第三,飾品配件等從逐漸減少到徹底消失,服飾成為了評判人的政治信仰和思想觀念的外在標志,經濟、實用的服裝要符合“革命”時期的風尚。于是,隆林彝族服飾藝術逐漸走向衰落,面臨著斷裂與消解的危機。
從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發展的軌跡來看,其經歷了從“羊皮披氈”、“絲綢盛裝”到“粗陋布衣”的巨大演變,服飾制作面料也從古代牛羊皮、植物根莖到現代工業合成面料的過程。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功能也從防寒護體的基本物理功能上升為象征地位、財富與身份標志的文化功能,在1949年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又淪為政治意識形態的載體。上述巨大變遷,不僅展現了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演變歷程,記錄了隆林彝族整體的社會的發展階段,也折射出了隆林彝族民眾思維觀念和心理行為的變化。
二、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當代重構的文化進程
盡管隆林彝族仍然傳承著本族群的歷史與文化記憶,保持著本民族的語言、族群稱謂、風俗習慣等,但由于隆林處于彝族文化的邊緣地帶,且長期與境內其他民族混雜而居,在歷經了民國至“文革”結束后幾十年的文化解構歷程之后,其傳統服飾藝術的傳承與發展面臨著巨大的危機。然而,不容忽視的是,民族文化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國家對于民間傳統文化的自上而下的取締與否定,并不能徹底切斷人們心理意識深處的信仰,一旦來自于國家權利的政治意識形態控制有所松動,長期蟄伏在民眾心中的傳統便有可能復蘇,并通過不斷調適、重組而使民族文化煥發新的生機。隆林彝族服飾藝術正是經歷這樣的重構歷程。
(一)時代背景
“文革”結束后,國家重新修正了有關民族傳統文化的政策,開始重視保護和挖掘民間傳統文化遺產。1979年以后,國家多次下達搶救、搜集整理和研究彝族歷史文獻的文件,全國各地彝區紛紛成立或恢復彝語文和彝文古籍整理、翻譯機構。1983年6月5日,國家民委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談會,隆林彝族應邀派出代表參加。這次會議第一次正式將川、滇、黔、桂四省 (區)的彝族同胞聚攏到了一起,因而也成為了隆林彝族文化當代重構的起始。此后,隆林彝族多次派出代表赴云南、貴州、四川參加相關會議,考察學習這些地區彝族文化傳統的復興與重構。
改革開放之后,國民經濟實力及生活水平均得到了較大的提高,經濟社會水平的改善為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隆林彝族涌現了一批具有“民族文化自覺”意識的知識分子,他們充分認識到本民族的文化處境,心系民族未來,迫切希望為民族的發展作出貢獻。
同時,現代化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進一步席卷全球,傳統文化生存的土壤逐漸縮小。民間的信仰體系趨于瓦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適應的素來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10],傳統社會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與規范不斷接受著新型社會環境的考驗。一方面,民眾被動接受或主動追求著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試圖在現代化進程當中保留或挖掘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一切能夠成為民族認同符號的文化表達由此獲得了重構和再造的內在契機。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自20世紀80年代起,包括服飾藝術在內的隆林彝族傳統文化藝術在歷經了民國前后的涵化、整合及解放后至“文革”期間的斷裂與消解之后,逐漸走向了復興與重構之路。
(二)傳統文化的復興
一)舉辦彝文古籍整理、畢摩培訓班與彝文培訓班
1984年4月,在隆林各族自治縣政府的支持下,隆林成立了彝文翻譯組,參與者有黃國政、王文魁、韋定富等人。他們搜集了隆林、西林彝族村寨傳承下來的彝文古經書,聘請彝族老畢摩王文輝先生傳教彝文。后來,又派代表到貴州畢節學習彝文翻譯工作,并整理出了《隆林彝文單詞》一書。此后,隆林又舉辦了短期的畢摩培訓班,教授彝族畢摩文字、祭祀儀式流程等內容。
二)改彝式神壇、取彝名
隆林德峨阿搞寨現有王、楊、李、吳、郭、黃、韋共七個漢姓,每一個彝族漢姓都有與之相對應的彝族“涅益”家支。傳統上,每個家族的男子從小就要背誦本家支的系譜,但后來由于彝族人口較少,且平時與壯族、漢族等接觸較多,使用漢姓更為方便,因此就逐漸丟棄彝族傳統家支制度。到了20世紀80-90年代,隆林彝族畢摩王文魁等人根據畢摩經書的記載及民間的記憶,尋根問源將各姓彝族的漢姓與彝族“涅益”家支一一對應起來,具體為:“額伯涅益稀”(替仆)——韋,“荻撮碑羅西”——王,“荻切碑羅西”——黃,“日K仆”又 (古西涅益西)——楊或李,“渣洲涅益西”——吳或郭,并在“涅益”家支的基礎上將各村寨彝人的漢式神壇改為彝式神壇。如1963年6月廣西民族學院歷史系實習組的調查,那地寨黃世福家的神位文字為[11]:

此神壇樣式與當地壯族、漢族無異,這說明在解放初期,隆林彝族文化受周邊漢族影響已相當之高。但在20世紀80-90年代以后,當地彝族的神壇文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筆者僅摘錄其中之一作為對照①此神壇文字抄寫自德峨鎮阿搞寨李景林家。:
接著,當地部分知識分子還為自己起了彝名。如韋革新的彝名是“替仆支不”,楊義杰的彝名是“古西烏沙”,其中“替仆”、 “古西”是彝族“涅益”家支的簡稱,“支不”、“烏沙”則是名。這種現象在新一代年輕人中則更為普遍,如楊強的彝名是“古西西措”,其二哥楊堅彝名為“古西阿格”,楊玉婷的彝名是“古西依婷”,吳海飛彝名為“渣州詩洛”,其姐姐吳海清則取名為“渣州詩薇”,“渣州”也是彝族“涅益”家支的簡稱, “詩洛”、 “詩薇”是名。
從漢式神壇、漢名到彝式神壇、彝名的變化,不僅反映了隆林彝族文化的發展過程,還折射出隆林彝族文化心理的變遷軌跡。“彝味”濃郁的彝式神壇、彝族名等都是隆林彝人傳承、重構本民族文化的文化行為。
三)傳統節日的重構
隆林彝族如今主要過三個民族節日,即“火把節”、“祭送布谷鳥節”和“彝年節”,但這三個節日“恢復”舉辦的時間也都是在1980年代末以后。
1.火把節。“火把節”是彝族最具代表性的傳統節慶,因具有集體狂歡的特征而被譽為“東方的狂歡節”。但是,歷史上彝族并沒有“火把節”這個稱謂。那么,隆林彝族在歷史上是否有舉辦“火把節”的傳統呢?根據現有文獻資料所見,并未發現有關于隆林彝族“火把節”的記載,筆者在田野調查中也曾多次對“火把節”進行求證,得到的答案幾乎都是否定的,唯有一個“六月六”的日子與火把節的內容頗為接近。
案例1:黃靈芝家人等訪談錄①訪談時間:2014年1月20號,訪談地點:黃靈芝家,文中材料根據錄音材料整理。
1982年,我組織過的火把節,那是第一次,82年以前也過火把節但是規模不大,改革開放以前,以前沒有火把節的時候就過“六月六”,點燒火把、殺牛、祭祖,還搞一些娛樂活動。以前大年初一、初二我們也燒火把,規模不大,后來才統一到六月二十四號。1989年在阿搞那邊舉辦了大型的“火把節”,各村各寨的人都去參加了。
顯然,當地人也認為“六月六”與火把節有一定關系,只是火把節在農歷的六月二十四舉辦,開始過火把節以后,“六月六”的節日也就取消了。
而隆林彝族畢摩王文魁則說:“我們彝族傳統上是在每年的豬月豬日過火把節。”畢摩是彝族傳統歷史文化知識的集大成者,雖然隆林彝族畢摩經書已經失傳,但因口傳而留下了不少寶貴的資料。王老先生的這句話似乎又說明隆林彝族原來就有火把節,現在只是重新恢復了。總之,可以肯定的是,隆林彝族原來就有燒火把的習俗,只是時間在農歷的六月六,內容主要是殺牛、祭祖、娛樂活動等,與現在的火把節內容形式差不多。
2.“祭送布谷鳥節”。該節由“祭送布谷鳥儀式”發展而來,廣泛流傳于廣西隆林各族自治縣和西林縣的彝族村寨。關于該儀式的由來,隆林彝族民間主要流傳有兩則故事:其一,布谷鳥是彝族祖先神,它佑護著彝族人民從遙遠的他鄉遷徙到隆林這片土地,祭祀布谷鳥寄托了隆林彝民的思鄉之情。其二,布谷鳥是催春的神鳥,每年初春萬物復蘇時節就會來到人間催促人們耕種,它夜以繼日地關心人民生產,以致操勞獻身,人們感謝它,于是在每年豐收之時送來食物與之共享。當地還廣泛流傳著《布谷鳥歌》,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祭送布谷鳥節”的本土性。[12]
但是,筆者翻閱了各種文獻也沒有查找到有關于祭送布谷鳥節的記載,隆林彝人也都說以前沒有這個節日。筆者在翻閱2003年編撰的《隆林彝族》一書時,發現當時彝族人過一個叫做“嘗新節”的節日,“嘗新節”與“祭送布谷鳥節”均有“豐收之后,請布谷鳥嘗新”的習俗[13]。現在, “嘗新節”是當地仡佬族最大的民族節日,而彝族已不再過“嘗新節”。因此,很有可能隆林彝族祭送布谷鳥節是在火把節與“布谷鳥嘗新”的結合下被建構出來的新的節日。現在的“祭送布谷鳥節”與“火把節”同一天過,于2014年申報為廣西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3.“彝年節”的回歸。按照彝族十月太陽歷,一年共有十個月,每個月36天,剩下的5-6天為“過年日”,即“彝年節”。過去,彝年節是隆林民眾休閑玩樂、殺豬祭祖等活動的時間,但因為長期與漢族相處,就與漢族同胞一起過起了春節。隨著與滇川黔彝族的交流,隆林彝族逐漸意識到本民族節日的文化內涵,開始重視彝年節。隆林彝語稱彝年節為“戈西”,時間在每年的冬月三十一 (農歷臘月初一)。彝年節除了殺豬、雞、鴨外,還要在年節當天凌晨雞叫三聲時舂糯米粑,然后將一塊直徑約45公分的大粑粑和米豆、米豆水擺在神臺上供神,并舉行祭祖祈福儀式。
“火把節”、 “祭送布谷鳥節”和“彝年節”幾乎都是在傳統儀式、節日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民族傳統節日是本民族傳統文化觀念、民族文化心理等的集中反映,通過民族節日可以全方位的向外界展示民族傳統服飾、歌舞、飲食、宗教儀式等民族文化藝術,傳統節日的回歸與重構對于增強隆林彝族文化自信、增強民族凝聚力、樹立良好的對外形象等都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民族服飾藝術的重構
伴隨上述一系列傳統文化的復興與重構,隆林彝族民眾對民族服飾藝術提出了新的要求,建構一套能體現本民族身份與精神風貌的服飾,已成為時代賦予隆林彝族人的使命。
繼1979年第一次彝文古籍工作會議之后,20世紀80-90年代是隆林彝族廣泛與川、滇、黔彝族同胞交流學習的時期,在這期間,隆林彝族知識分子和機關干部等發揮了重要的紐帶作用。其中,隆林彝族詩人韋革新 (替仆支不)是將涼山彝族服飾帶到隆林的第一人。筆者找到了當時參與新式彝族服飾“設計”的彝族干部王秀珍,試圖還原當地彝族服飾藝術重構的全貌。
案例2:彝族干部王秀珍訪談錄①受訪者:王秀珍,訪談時間:2014年1月18日上午,訪談地點:古城村往隆林縣城的車上。
筆者:現在這種紅色的盛裝衣服是什么時候開始有的?
王:(20世紀)八幾年的時候。
筆者:是怎么來的?
王:韋革新從涼山帶回來的嘛,他那時候去涼山,回來給他愛人帶了一套,大家都覺得好看,就開始效仿。
筆者:具體的經過可以說一下嗎?
王:那時我剛來縣里參加工作,正好遇上要設計新的民族服裝。我們德峨的彝族人還成立了一個工作組,專門討論傳統文化恢復的事情,主要是火把節和火把節服裝。火把節的時候,涼山那邊給我們寄來達體舞的資料,我們一群人跟著寄來的錄音磁帶學達體舞。89年火把節的時候,各個村寨的人都來了,殺豬、殺羊……好熱鬧。說到火把節的服裝,那時候我家隔壁是裁縫,我請她裁好后,自己一針一線開始縫,那是我第一次做衣服。后來大家統一以我做的那套服裝為標準,這套服裝后來被百色市博物館收走了。
德峨鎮阿搞寨的“寨老”楊合明也說現在的隆林彝族服飾是以涼山彝族服飾為樣板制作的,時間是在1980年,韋革新從涼山進購過來幾件,穿起來大家個個喜歡,于是就開始仿制。
但也有人說,隆林彝族新式的民族服飾是根據隆林彝族過去的服裝改制的,他們認為,過去隆林彝族婦女也是穿裙子,只是到了近代才改穿褲子。
案例3:王文魁 (70多歲)訪談錄②受訪者:王文魁,訪談地點:隆林縣城王文魁家火塘邊,訪談時間:2014年1月14號下午10點。
我小的時候見過我母親穿裙子的,那時候的裙子褶子很大,跟涼山那邊的很像,不像現在 (機器壓的)這么細,大大的褶看起來很大方。那時候的裙子顏色也比較深,一般是黑色的,上面掛上銀制的鈴鐺,走起路來叮叮當當的響,好聽極了。
案例4:黃阿妹 (95歲)、王阿灣 (90歲)訪談錄③受訪者:黃阿妹、王阿灣,訪談地點:德峨黃阿妹家中,訪談時間:2014年1月18日下午1點。
以前,我們結婚的時候還穿過裙子,后來不多見了。像是帽子、衣服、裙子這樣的全身搭配很少見,有的也是在結婚的時候穿,有人要辦喜酒了,就去向別家借來穿,久不久見到一兩套,慢慢的就全都不見了。
此外,隆林民族博物館館藏的兩件彝族“古裙”也成為當地彝人對于過去穿裙這一傳統的有力“物證”。顯然,在涼山彝族服飾的“啟發”、當地老人的“記憶”以及實物依據等多重因素影響之下,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當代重構順勢在開展,并通過1989年的火把節、1993年的縣慶活動正式宣示了新式隆林彝族服飾的合法性。
1989年,隆林彝族在德峨街舉辦了第一次大型火把節,各村各寨的人都趕來參加,大家穿上統一的民族服飾、圍著火把跳起達體舞。火把節不僅為新式民族服飾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而且還成功的塑造了一個團結和諧的民族集體形象,包括周邊其他民族、游客、縣領導及媒體在內的所有人均對此舉表示贊賞。
1993年,適逢隆林各族自治縣成立40周年,縣里要求境內的每個民族派出81人的代表穿著民族服飾參加縣慶,彝族代表以一身艷麗、喜慶的新式民族服飾亮相,驚艷了縣內外來客。如果說火把節上穿著新式民族服飾使得這種服飾在內部贏取了隆林廣大彝族同胞認可的話,參加縣慶活動則是正式向外界宣示了隆林新式彝族服飾的“合法性”。
此后,隆林彝族民眾不管是參加當地還是外地的民族活動,都身穿民族服飾以新的民族形象展示在人們面前。20世紀90年代,新型的隆林彝族女裝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舉行的滇、川、黔、桂四省(區)彝族服裝展中獲得一致好評,其中被賦予了典型文化內涵的“五色百褶裙”、“鉤連紋”的隆林彝族服飾還在此次展評中榮獲一等獎。[14]
三、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當代重構的價值與意義
隆林彝族服飾藝術在當代社會中的重構,不僅僅是穿著形式的改變,還意味著民族文化的重塑,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文化意義。
(一)成為民族文化展示、宣傳的重要媒介
每個民族都有一系列與服飾藝術相關的民俗活動。隆林彝族日常生活中與服飾相關的民俗活動眾多,從歲時節日、婚喪嫁娶、祭祀儀式到各種形式的族內族外的文化交流與交往,尤其是歷次對外活動,如“第一屆中國藝術節”①1987年于北京開展,參展的隆林彝族代表有王雪芳、王文魁、韋斌。、 “ 中國彝族十月太②1992年,云南召開,韋革新、王文杰兩位同志參加。、 “③2014年5月,隆林派彝族代表參加。、 “陽歷學術研討會” 那坡跳弓節活動” 第四屆云南民族服裝服飾文化節”,以及縣市及省內外的各種民俗比賽活動等,新式的隆林彝族服飾往往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大亮點。在每年的火把節期間,各地游客都因隆林彝族火紅熱烈的“百褶裙”、威武颯爽的“查爾瓦”而慕名前來,年輕的隆林彝族姑娘穿著整套彝族服飾大方自信地在游客面前展示。鮮艷耀眼、美麗大方的隆林彝族服飾給族內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種視覺上的好感是認識和了解隆林彝族歷史與文化的內在動力,統一的民族服飾為隆林彝族建構了一幅民風淳樸、熱情好客、團結友愛的畫卷。
(二)促進民族文化的繼承與創新
在任何時代,文化變遷都是傳統之“舊”、現實之“新”以及在有條件的時候加上外來之“異”三者激蕩的結果,傳統、現實、外來這三者形成層疊、交融、并列,方能產生當下狀態的文化。[15]從表面上來看,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當代重構不過是重新建構了一身美麗的衣飾裝扮,但實際上卻反映了隆林彝族傳統文化的傳承、重組與創新之道——在全球一體化浪潮的沖擊之下,世界各民族都面臨文化急劇變遷的問題,許多文化在這個過程之中徹底消失,而隆林彝族服飾藝術則通過調適、重構而獲得新生,如從傳統服飾中繼承了“上衣下裙”、 “右衽百褶”的基本結構形式,以及裝飾、縫制手法,又從現實社會和外來文化中吸收了“鮮艷濃烈”、 “上窄下寬”、“上短下長”、“凹凸有致”的服飾藝術風格。既保持了本民族的傳統特色,同時又與時俱進,可謂“傳承蘊含創新,創新源于傳承”,二者互滲互融,不斷地豐富、發展本民族文化,與“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的理念不謀而合。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被使用,服飾藝術一方面承載民族文化意蘊,另一方面還是物質消費品,應該穿在人的身上,而不是一成不變地存放在博物館中,只有被人不斷使用的服飾才具有生命活力。20世紀80年代以前,隆林彝族許多人穿上了工人裝,著裝形象與漢人無異,男性更是幾乎沒有人再穿傳統服裝,現在則是幾乎人人都有一套民族服裝,隆林彝族民眾愿意穿著民族服飾并以此為豪。擁有、穿著傳統服裝人群的增加,客觀上有利于隆林彝族文化傳統的繼承,更還可以擴大彝族文化的影響力,促使其走近大眾,走向世界。因此,民族服飾藝術的重構對隆林彝族傳統文化的傳承、保護與發展起到難以估量的作用。
(三)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話語權
對于隆林彝族來說,統一式樣且異于周邊族群的民族服飾,可讓人一眼就識別出穿著者的身份,引導、培養族人的民族情感,進而強化民族成員的共同體意識,其所蘊藏的內在精神力量激勵著族人去發掘、維護、承繼、發展本族文化,并給人以文化的認同感和民族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正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正如華梅教授所言:“以服飾來表明集團的整體性,就意在以可視形象增強集團內部的凝聚力,使所有成員在集團內感受到規范的約束,在集團外又確立不同于其他集團的獨特形象。”[16]隆林新式民族服飾還喚起和深化了民族成員的共同意識,自覺將原來不同階層 (黑白彝間等級森嚴)、分布零散 (西林、隆林各村屯)的族人聚合在一起,共同維護民族的集體利益,共同維持民族內部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共同傳承、發揚民族傳統文化。
此外,新式民族服飾的重構對于提升隆林彝族的話語權也有一定積極的作用。長時間以來,無論是在隆林境內還是在川、滇、黔、桂四省 (區)彝族群體內部,隆林彝族這一支“弱小的”群體都未曾真正擁有過話語權。而當隆林彝族同胞以一身洋溢著和諧、喜慶、熱烈、時尚又不失古樸、端莊氣質的民族服飾出現在大眾眼前時,周邊的各族朋友們是羨慕的,筆者在考察時問過當地苗族人對于彝族服飾的看法時,他們都毫不掩飾對于這種民族服飾的羨慕與欣賞。
在各地彝區的文化交流交往中,隆林彝族通過積極參加各地彝族活動,并邀請外界彝族同胞加入到隆林彝族文化建設中來等舉措,逐漸得到了各地彝族同胞的認同和贊賞。在出席對外活動時,隆林彝族民眾必定要穿上本民族的服飾,而本就融入了涼山彝族服飾元素的隆林彝族新式民族服飾,讓外地的同胞們一眼便能識別出這是彝族。從服飾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通過服飾上“隨大流”以換取團體“合群”的肯定進而立足于群體之內,是著裝者著裝心理的典型表現。正因為如此,隆林彝族能夠很快融入彝族大群體之中,并逐漸獲得了一定的話語權。近年來,每逢全國性的彝族活動,都會邀請隆林彝族的代表參加,如隆林彝族畢摩王文魁就多次參加了涼山、畢節、昭通等地的畢摩大會及畢摩文化研究會議等,彝學會負責編纂彝族文化資料等也會邀請隆林彝族同胞參與,彝族大學生交流會自第一屆(2012年)舉辦以來一直都邀請隆林彝族大學生參加,隆林彝族在四省 (區)彝族中越來越被重視,逐步融入彝族主流文化圈,實現了由“邊緣”向“中心”的過渡。
四、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當代重構的文化思考
縱觀隆林彝族服飾藝術重構的文化歷程,呈現出如下一些特征:一是伴隨民族旅游而興起,從感官上打造“異文化”的新鮮感;二是對傳統服飾做加法或減法,增加的是一些容易引起視覺好感的配件,或增加已經失傳了的民族服飾,而減法則是指傳統的整套民族服飾被簡化或剔除;三是色彩濃重、視覺沖擊強,多為舞臺盛裝;四是以女性民族服飾的重構為主;五是體現了民族精英的理想。
民族服飾藝術在當代社會重構的過程中,隆林彝族也出現了諸如服飾禮服化、服飾成衣化、涼山彝族服飾“泛化”等值得思考的現象。我們知道,“民族文化在特定的地域空間中形成,因為其適應特定的生態環境而具有外來文化無法取代的生命力。”[17]彝族服飾藝術在特定的自然地理、人文社會環境中產生,千百年來逐漸形成了本民族的獨特文化,是一種獨特的優勢文化資源。隆林彝族服飾藝術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理應得到足夠的重視,合理的保護與開發并促進其多樣發展是當務之急。當然,重視和鼓勵民族或族群間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并非不遺余力地倡導和促進因為這種“交流”所帶來的某一文化的“泛化”。那樣的話,喪失的不僅是某一民族或族群的文化遺產,“還將喪失我們最有競爭能力的發展空間和發展領域,更為嚴重的是其發展的最終結果將導致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退化和喪失。”[18]
總之,隆林彝族服飾藝術作為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體現了物質文化的一般特征,又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當代重構,體現出了民族傳統服飾藝術在當代的適應性問題。隨著當代社會發展以及國家政策調整、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服飾藝術處于不斷地變化與發展之中,我們希望通過分析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當代重構,揭示這種重構背后的文化內涵與機制,進而揭示出我國少數民族在現代化語境中其傳統文化藝術發展、變遷的一般規律,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挖掘、保護與開發提供一定的經驗與理論。
[1] 馮敏.彝族服飾考[J].思想戰線,1990(01).
[2] 梁曉強校注.東川府志·東川府續志·戶口(卷8)(校注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93.
[3] (清)陳燕,韓寶深修,荘致和等校.沾益州志·風俗(卷2)[M].沾益縣文物管理所復印,光緒十一年重修本:209-210.
[4] (清)張鏌修,鄒漢勛,朱逢甲等纂修.興義府志·苗類(一)(卷41)[M].貴陽文通書局據刻本鉛排本,民國三年:389.
[5] (清)常恩修,鄒漢勛,吳寅邦纂.安順府志·風俗(卷15)[M].咸豐元年刻本:14.
[6] (民國)羅駿超纂.冊亨縣鄉土志略·風俗(第九章)[M].冊亨縣檔案館藏鉛印本,冊亨縣政府編印.
[7] (清)何天忂修,郭士信等纂.安南縣志·輿圖·風俗(卷1)[M].貴州圖書館(雍正九年稿本,據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復制油印本),1996.
[8] (清)陳燕,韓寶深修,荘致和,馬文忻等校.沾益州志·風俗(卷2)[M].沾益縣文物管理所復印,光緒十一年:209.
[9] (民國)雷雨.廣西西隆縣苗沖紀聞[M].廣西民政廳秘書處出版,民國八年:36,33.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11]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編.廣西隆林縣德峨區彝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Z].1964:32.
[12]許艷.隆林彝族“祭送布谷鳥節”傳承現狀考察[J].攀枝花學院學報,2014(05).
[13]《隆林彝族》編寫組.隆林彝族(內刊)[M].隆林:廣西隆林各族自治縣印刷廠,2003:85-86.
[14]《隆林彝族》編撰委員會編.隆林彝族[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13:249.
[15]朱炳祥.“文化疊合”與“文化還原”[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0(05).
[16]華梅.人類服飾文化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16.
[17]覃德清.壯族文化的傳統特征與現代建構[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268.
[18]楊昌儒.民族文化重構試論——以貴州布依族為例[J].貴州民族研究,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