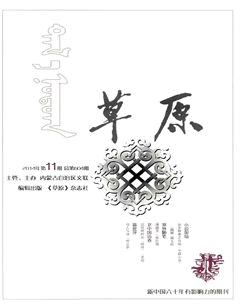軟筋軟筋的河套油糕
劉秉忠
油糕是與河套人有生死之緣的美食,吃油糕曾經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老農民說:“人這一生,要吃三頓糕:過滿月一頓,娶老婆一頓,進棺材一頓。”猛一聽覺得怕人,細細想來,不無道理。因為吃油糕必定和人生許多大事有關聯。
再窮的人家,每逢大事,也要吃頓油糕,哪怕借上黃米借上油。再窮的村子,也有一副兩副搗糕用的碓臼碓杵。小時候,每逢看到有人肩扛碓杵趾高氣揚招搖過村,大家就知道,這家人有喜事了。不信你問問。回答果然是“孫子過滿月了!”“新女婿上門了!”“娘舅家來人了!”……
村里有老年人去世,不說死,說“吃了糕啦”。既文明又不失幽默。
特別是過大年之前,整個鄉村,做油糕好比轟轟烈烈、全民動員的一場戰役。一進臘月,搗糕聲震得地抖房搖,炸油糕的香味兒滿村飄蕩。泡上一斗黃米,吃到正月十五,二斗黃米吃到二月二。每天一頓豬肉粉湯軟油糕,吃得歡歡喜喜。
很多時候,吃油糕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并且暗示著某件大事的結果。河套人風俗,男女相親,男方頭一次到女方家接受面試,回家后老人第一句話就要問:晌午吃的甚?如回答是燉雞肉炸油糕,老人就樂了,有八九成的勝算。回答是烙餅,多半沒戲,再回答是酸粥,那就徹底酸了。
軟筋軟筋的油糕,是河套美食的靈魂。小時候聽村里人唱過一首酒曲兒:“一條扁擔軟溜溜,擔上黃米到蘇州,蘇州愛我的好黃米,我愛蘇州的好閨女。”野心還不小!我沒有考證過河套人與蘇州是否有過黃米和美女的交易,但我佩服老農民的品牌意識,這些幾乎目不識丁的莊戶人,居然把河套的油糕和蘇州美女放在一個檔次上,想其不是空穴來風。
再說黃米。黃米乃黍子脫粒而來,也有品質之分,軟則為上,硬則為下。硬的做出糕來和窩頭無異。同一黍子,在這一村種上是軟的,在那一村種上則硬。紅泥地一個樣,砂土地又一個樣。故農家樂此不疲串換黍種,從而保證了油糕的質量。一年之計在于春,一年之糕在于種。
農村人飯量之大,人所共知,但吃油糕之量大,更讓你大開眼界。村里人,一頓飯吃掉一升黃米(3斤)油糕的人比比皆是。有回在村里上事宴,一位親戚和人挑戰,他說,我吃一片油糕,你喝一盅白酒。無人敢應。原來,這位老兄可以吃二十多片糕,還能喝兩碗粉湯。他對我說,他在城里開過三年炸油糕店,一天三頓油糕沒有吃膩。他還說,一斤黃米做糕,捏大了是七片,捏小了是八片,所謂“七大八小”。我聽后大吃一驚,原來“七大八小”的成語由此而來!
然而,吃油糕遠遠不止紅白喜事。蓋房子,有“上梁饃饃壓棧糕”一說。上梁只是一道工序,壓棧乃為竣工慶典,可見油糕的地位遠在白面饃饃之上。還有“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九遭”的說法。不吃糕還有這多麻煩,你一年搬上九回家試試。貧困時期,娶媳婦兒這天,除去雙方議定的彩禮及其他物品,男方還要另帶一份“離娘饃饃離娘糕”,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甚至前功盡棄……
“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十里的豆面餓斷腰。”你看這油糕多耐餓! 一個農村人想彰顯自己的影響力,他非常含蓄地對人說的一句話是:你背上二斗黃米訪一訪我的名聲。二斗黃米做成油糕,可夠一個人吃半個月,半個月可走方圓百十來里路。那意思即周邊地方沒有說他壞話的人。
曾幾何時在農村,除了種好大宗的糧食作物之外,每個生產隊都要種上一些黍子加工黃米,分給農戶做油糕。每年春播時隊長征求農民意見,總有人說,其他的我們不管,甚不甚種上幾十畝黍子。如果一年吃不上油糕,這個隊長十有八九就要下臺。記得有一年,隊里頭關場門(莊稼收完慶豐收),由隊里開支吃了一頓粉湯炸油糕,我們鄰居二板頭家少分了兩片子油糕,二板頭老婆和分油糕的保管員結下了“梁子”,罵了好幾天。后來二板頭才告訴老婆說,那兩片是他在路上偷吃了。賊不打三年自犯。
有一個河套人講的故事,說廟里住著大小兩個和尚,老和尚愛吃油糕,在門前的地里種了一片黍子。小和尚怕干活,對老和尚說:種不種吃不上。老和尚有道行,不計較他。鋤地的時候,小和尚又說,鋤不鋤吃不上。之后每一個生產環節,小和尚總要說一回“吃不上”。老和尚多次寬恕。最后一天,老和尚把糕蒸好坐上油鍋,要小和尚去抱柴火炸油糕,小和尚邊走邊說,炸不炸吃不上!老和尚終于忍無可忍,拿起燒火棍去追打。漏了一個空,進來幾只貓把案板上的素糕叼走了。最后,老和尚把小和尚趕出了山門。因為一頓油糕沒吃上,老和尚壞了幾十年苦苦修來的寬容忍讓的道行……
星移斗轉,時光荏苒。碓臼碓杵早已放進了博物館,成為河套飲食文化的見證。但吃油糕的習俗卻始終不改變,估計沒有人能改、也沒有人敢改。
呵呵,軟筋軟筋的河套油糕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