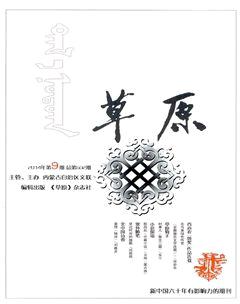舟已遠 劍還在
陳慧明
孔子請弟子言志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論語·公冶長》)
時差2443年的上世紀60年代。而立老師請花季學生言志:說說理想。學生答:當大夫當警察當火車司機當售貨員……
時針又滑過了半個世紀:耄耋老師問花甲學生曰:經過了“文革”又經過了改革,你們現在活得怎么樣?學生答:拼過了,但拼不成當年的理想。日子還行吧,不像孔子形容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雖不至于“一簞食,一瓢飲”,但有幾成“愿車馬、衣輕裘”?
生活是戲劇的,歷史是荒謬的。社會是變化的但歲月是刃人的。一天就是一天,如同刻舟求劍,劍雖在,舟已遠。
彈指一揮半個世紀。想我們這些曾經的莘莘學子,布衣粗食卻志向遠大,簡單幼稚卻正氣凜然。當我們搖著撥浪鼓似的腦袋背誦“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時,我們恰好同學少年,我們正值風華正茂,我們真有書生意氣,我們揮筆指點江山。看窗外,朝陽燁燁藍空遙遙,清風徐徐燕雀恰恰。雞冠花開如雞冠,喇叭花開如喇叭,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實可信,怎能不懷疑我們的未來功成名就、飛黃騰達?
舊事斑駁,老景已去;純真時代,尚可憶否?
1962年秋天,一幫子出自農家白屋的花季少年涌進了臨河市第二中學,時為我們執教的,有畢業于清華、南開的優秀教師,師資力量可謂雄而厚之。但師尊們不遺余力地往我們的大腦里灌輸知識之后,卻看到了滿目的蒼涼,“文革”只一個流彈便將我們師生共同搭建的希望之塔擊得片瓦無存,塵埃落定。
我們是新中國的開國嬰兒,幸運的我們本不該不幸運地跌落在文化的斷層里,但是,正如《飄》的作者、才貌雙絕的米切爾被一名醉酒的司機開車稀里糊涂撞死那樣,既不敢相信又確鑿屬實。
我們來不及思考自己有沒有被白熱的激情焚毀,就被時代的大潮給卷走了。待驀然回首,我們好像從花季少年直接穿越到六十花甲,中間歲月呈現了迷蒙而又身不由己的狀態,所以,欲說還休。
2010年“六一”前夕,幾個同學在聚會中戲言:我們為什么不能過個兒童節?
導火索很短、感情線很長。從娘胎里帶來的澎湃激情并未在十年動亂的野蠻狂呼中耗盡,激情勝過礦藏能源用盡了還能再生。六十花甲子們的感情一下就被引爆了!是啊,我們怎么就不能過上一個“六一”呢?我們也曾一身陽光地戴著紅領巾、一臉陽光地唱著“準備好了么?時刻準備著”,一片陽光地度過兒童節啊,我們寧愿相信那片陽光,還在!
命運就像從潘多拉的盒子里跳到了多米諾骨牌的牌桌上一樣,六六老三屆們與“六”這一數字有著天干地支的機緣巧合:我們和祖國同時走過了60大壽,同時從六六年的“文革”走到了七六年的變革,同時從16歲的花季走到了60歲的花甲——如果我們硬要把這個感覺歸入唯心論,誰能把我們怎么樣?
我們有過十五六歲的少年花季,我們也有過十七八歲的青春雨季。那些太陽般的時光,那些月亮般的心靈,本該播種星星般的知識。但我們卻統統被冠上了“老三屆”這樣一個怪誕的名分,而且從此像一串干茄子那樣灰不溜秋地掛在了中國現代史上。
從事思想史工作的、具有“尋蹤癖”的朱學勤先生曾苦苦尋找過十年浩劫中曾有過一段思想蹤跡的我們,他希望把我們的思想載入大陸思想史中。他中性地稱呼我們為“六八年人”。在他看來,我們當時是一群有著旺盛體力、貧弱學力、但時刻都在思考著的群體,但這個群體后來卻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請了一批曾上山下鄉的老三屆撰寫《苦難與風流》一書,朱學勤先生便把自己回憶老三屆這個群體的文章做成了一個“尋人啟事”。他寫道:“他們理應還活著,之所以隱匿不見,是不是也因為功名利祿的腐蝕才失蹤了呢……那是一代人買櫝還珠的悲劇。”
朱學勤感慨“六八年人”不是知識分子卻更像知識分子,只是這些知識分子們太“短命”了,大多數人的思想未老先衰,提前進入暮年狀態。他感慨這一代思想者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那一邊的黑暗里,都沒有引起思想長河的一聲嘆息!
痛惜也,悲乎哉?
買櫝還珠——在10年前那個流火的7月,闊別40多個春秋已是白發為冠的班主任高峰來到我們中間,他痛心地說:你們這一代人太可惜了……
高老師只說出這么一句話便突然哽咽,舉杯的手劇烈地顫抖起來,酒至唇邊怎么也喝不進嘴里,將一大半淋灑在胸襟之上!
高老師手執教鞭40余年,他說他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們這一屆,所以在古稀之年從異地趕來看看我們是怎么活著的。
我們都年過“花甲”了,當年臨河二中的栽桃育李者尚存幾人?我們努力地聯系到了四位老師,而其中兩位師尊已行動不便,但他們表示一定要來參加,因為與諸多的主義相比,此時最重要的是在場主義!
等待當年兢兢業業而被無情批斗的敬愛的老師們,我們理應程門立雪!
一位老師慨嘆道:你們那一屆“攛胎學生”都很厲害啊!
在浩大的國學史上,獨我們老三屆才能享譽“攛胎學生”這一植物性稱號:中考前擱淺,退回去搞兩年革命——嗟,來領初中畢業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歲月如風轟然吹過,而今我們都“耳順”了。東晉李充說: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宋代計有功說:手挼六十花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
而我們卻決定要做一次年齡的反叛,身為文人雅士的蘇老夫子都要找回少年狂,我們為什么不能?
我以《老夫聊發少年狂》為題寫了一篇夸夸其談的文字發表在當地報紙上,以游說1966年畢業于臨河二中(校址狼山)的同屆同學,大家都來歡度“六一”!
在市區居住的同學們很快就聯系到了,而如同珍珠般散落在鄉野田疇的同學卻無從查到電話號碼。你們看到報紙了嗎?你們會因當午之鋤禾而拒絕“六一”嗎?endprint
務農是春種秋收,而非晨鐘暮鼓。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學友們,我們有著共同的基因那就是農家子。你們現在菜畦內外、麥壟前后嗎?那就別換衣服了,直接帶著莊稼地里圣潔的黃土,帶著田間鄉野阡陌獨有的清風,帶著說不清道不明的付出與獲得,來吧!
蘇軾老夫子的《聊》文很放達,所以我們姑且剽竊之,姑妄篡改之:老夫聊發少年狂,著紅裳,攜酒缸。倜儻風流,傾倒太平洋……
扯起“六六老三屆六十花甲聚會六一兒童節”的橫幅后,大家從四面八方千鄉百里趕來了。
幾十年來,除屈指可數的一些同學有機遇達到“愿車馬、衣輕裘”外,絕大多數老三屆們都處于沉默之中,或荷鋤扛犁沉默在農田里,或趕牛牧羊沉默在山腳下,或小買小賣沉默在風雨中。
是的,大家都花甲了,兩鬢都斑白了,更有鄉下同窗們的皺紋因披星戴月、晨耕夜鋤有著更深的刻度和更僵的曲線;牧區學友們的白鬢由于高原干旱、戈壁風雨,表露著更加明顯的歲月銹斑。
能來的都來了,大家初見之下只是互相抓住手,竟不知該從哪年哪月說起。兩位年近80高齡的老師坐在我們中間如舉父母高堂;我們的班主任高峰遠在千里之外、坐在輪椅上咬著不真切的字眼祝福我們聚會成功!很多同學不能到位,但他們在電話那頭嘶喊著前所未有的遺憾。
這是一種有別于世上任何情感的特殊情感:甲子情愫!
臺上的同學有歌有舞,臺下的同學忙著說話。每個與會者都有排解不完的激情訴說不盡的言語。那就說吧說吧,大家本就沖著說話來的,說老師說同窗說輟學說家庭說婚姻說兒孫說命運說人生說現在說未來說……42年的顛覆人生,一個聚會能說得清嗎?
初中文化的我們特別不喜歡“白丁”這個名詞,所以我們回避了“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只談論“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我們回避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只認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為了像一群兒童那樣簡單快樂,我們屏蔽了很多想說的話,40多年的靜水深流潛在于美麗的浩渺煙波之下!
我曾這樣描寫過自己的心情:太陽落下去我就等著月亮,哪怕等到了月食;月亮落下去我就等著太陽,哪怕等到了日食——我不知道這段兼有著積極和消極的文字是否適合此時此地同窗們的心情。
六十花甲子轟轟烈烈地度過了“六一兒童節”,同學們分手時互相囑托:大家都老了,所以下次聚會不能時隔太久。我們可以過“六一”也可以過“八一”!
所以四年之后,我們再度相聚于“八一”。
聚會當晚我發了一條微博:我們半個世紀前的老三屆師生73人大聚會,老師八人,最大的83歲;學生65人,最小的63歲。師生不辭勞苦地來自京城更來自農村。上午在宴會廳載歌載舞,下午包大巴去看黃河大橋。想我們經歷了那么慘淡的人生,竟還能拿出如此激情,嗚呼感慨!
美麗端莊而又善良的女同學,不美麗了但依然端莊而又善良;瀟灑熱情而又睿智的男同學,不瀟灑了但依然熱情而又睿智。歲月奪走了一些,卻奪不走另一些。
激情不說年齡,熱血只在性格,午餐后,我們包了一輛大巴,浩浩蕩蕩地去看浩浩蕩蕩的黃河。路上,我們唱著當年的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想著當年的事:提著糨糊桶和刷子到處張貼大字報;說著當年的話:世界歸根結底是我們的。20多分鐘的車程,我們一路年輕一路張揚,直到站在波濤洶涌的黃河邊上。
舟雖遠,劍仍在。
這只是版圖的黃河現實的黃河,而我們經歷中的黃河、命運中的黃河呢?那不也是九曲十八彎嗎?
這條華夏的古河,它奔流過一萬年的歷史,曾發生過1500次決堤,26次改道。布衣百姓口中所謂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指的就是炎黃中國的這種生命之湯湯,它充滿著唯心的詛咒和詭異,也寫照了一個歷史時段的滄海桑田。所以我們不會離開黃河,我們來了。
不見黃河心不死,見了黃河心會死嗎?
不會!我不能代言但我能代筆:雖然一些在野的史記會把我們視作淪落于文化斷層中的遺珠散石,但國家無權忘記我們,因為我們經過了十年的出位終將歸位了,而且處在各自命運的夾角里也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奉獻。
此時,當萬里黃河的驚濤駭浪來到我們面前時,我們說,我們不再發泄怨言了,我們的怨言在“六一兒童節”那次聚會中說完了。我們會繼續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但卻是有益的事情,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故鄉、對得起歷史、對得起社會。
我們的步伐十分一致,已經整體從花甲邁向古稀了,這中間最重要的也是最關鍵的,是我們的心態日漸平和,因為隔著兩條天塹般的代溝,我們親眼目睹了孫子輩不會再像我們那樣度過他們的花季青春、而立不惑,他們擁有櫝珠同在的人生舞臺,絕不會遭到流彈的襲擊而轟然坍塌。只要付出足夠的耐力和毅力,他們都會成功。
我們曾度過了彼此無法聯系的隔膜歲月,那是一萬年太久,我們再次預約了五年后的聚會,卻是只爭朝夕。
古稀之年的2118同學會,那是一個恢弘的乾坤大挪移,但愿我們全體師生一個不少、全數到位!
子路曰:“愿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責任編輯 ? 楊 ? 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