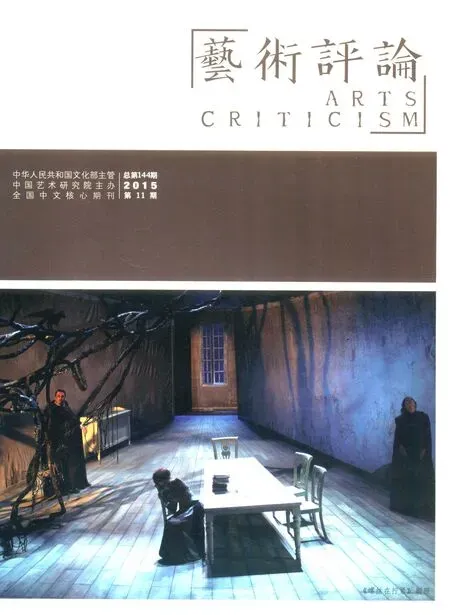論中國電影對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
陳旭光
論中國電影對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
陳旭光
20世紀的中國藝術是近代國門打開之后,在中西文化沖突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自20世紀以來,藝術領域中西沖突或現代化與民族化的糾葛就一直是個揮之難去的問題。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實踐和具有大眾文化性的新型藝術門類,電影藝術更有其艱難的歷史與復雜的形態。不夸張地說,一部現代中國電影藝術的歷史就是一部如何處理現代化與民族化、西化與本土化關系的歷史,是這幾種趨向的矛盾、悖離、糾葛或融合的歷史。
在21世紀的文化大發展和媒介大交融的新語境下,傳統在電影藝術中如何繼續存在和發展?中西文化在銀幕藝術世界中如何交融?電影藝術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是“西化”還是“民族化”,是革新尚“今”、還是“守舊”崇“古”等,都是20世紀迄今我們仍須面對的電影藝術發展的重要問題。
毫無疑問,“傳統的現代轉化”是一種文化理想也是一種文化實踐。20世紀以來有識之士都在思考并實踐這樣的命題。而在藝術領域,在21世紀的當下,這個問題尤為重要也更趨復雜化。傳統不是靜止不變的。而現代的生活自然呼喚著與之相適應的藝術表現風格和形態。傳統的內核與精神也許是穩定的、不變的,但豐富的多姿多彩的外在的表現、再現形態是會百花齊放的。也就是說,傳統的“現代轉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傳統文化只有在轉化中才能得以承傳和傳播,不然就僅僅是束之高閣、徒有其表而功能盡失的文化“遺形物”。當然,關鍵的問題,也是難題,則是——如何轉化?
我們以電影藝術的實踐為個案來探討這個問題。
一、傳統文化現代轉化的前提、條件或語境
討論傳統文化、傳統美學、藝術精神在銀幕影像世界中“現代轉化”的問題,首先應該充分考慮到這個問題發生的前提、條件和當下語境。
(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要尊重電影自身的本體語言特性
中國電影對傳統的現代轉化,主要是通過獨特的電影語言(而非文字語言)與文化傳統發生關聯的。因此要尊重電影自身的本體語言特性。
電影是一種以影像(當然還有聲音,合稱視聽語言)而非以文字語言為其本體語言的藝術。法國先鋒電影人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曾經宣稱一個“攝影機如自來水筆”時代的來臨。而這只是一種比喻性的說法——攝影機自然與自來水筆不同,電影語言也與文字語言有根本的差異。它們在根本上就是兩種藝術媒介,也是兩種文化或文明的主因性載體。毫無疑問,在電影這門“視覺藝術”中,作為對白或畫外音的語言的重要性比之于文學這樣的以文字語言為本位的藝術要弱得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認為印刷文字是維系作為一個民族的“想象的共同體”的重要媒介,因為“印刷語言是民族意識產生的基礎”。但我認為,電影產生以后,作為一種新媒介也加入到這一建構“想象的共同體”的過程中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們現在常說的電影的國際傳播、電影具有國際文化形象建構功能等等,都指涉這一問題。當然電影不是以文字語言、印刷語言的方式,而是以動態的影像敘事、符號表現的方式,以畫面、聲音、鏡頭、蒙太奇、長鏡頭等電影語言,完成這種建構和傳播的。
現代傳播學有一個關于“文化貼現”或文化折扣(culture discount)的原理,即認為在從一種文化向另一種異質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文化會發生變形、磨損等現象,傳播效果是會發生變異的。循此原理,電影以影像的方式對原來蘊含于語言文學、美術、音樂、戲劇戲曲、舞蹈等藝術門類中的藝術精神、意蘊、倫理觀、價值觀等進行現代轉化,是不是也會出現類似的“文化折扣”現象?在我看來,答案是肯定的。電影是一種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阿諾德·豪澤爾曾不無輕蔑地認為“電影可以說是一種能夠適合大眾需要的,無須花多大氣力的娛樂媒介,因此,人們稱電影為‘給那些沒有閱讀能力的人閱讀的關于生活的連環圖畫’”。這話雖然過于尖刻,但還是抓住了“電影閱讀”的某些特性。因此,從經典、高雅的文化媒介(語言文字)通過影像向通俗文化、大眾文化、群眾文化、視覺文化的轉換必然會有變異與磨損,也可能是難免的稀釋、淺顯化,甚至于文化的扭曲、變形和混雜。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這也許是一種新文化形態的重構和創生?在這一過程中,傳播內容的深度也許降低了,但傳播的廣度卻無疑大大拓展了。
(二)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必須考慮到電影的大眾文化性
電影無疑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我們世紀最富有群眾性的藝術”和“具有最大影響力的現代藝術”。從文化性質的角度看,我們說電影是以大眾文化為主導定位的,是具有龐大受眾數量的大眾文化形態、大眾傳媒和文化產業。
在當代社會,大眾文化借助于現代傳播媒介和商業化運作機制,不僅事實上已不容置疑地成為當代社會文化的主潮,而且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與閑暇活動本身,改變了當代社會的結構和文化的走向。正視大眾文化的崛起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必然結果。隨著大眾文化觀念的逐漸被認可,中國電影也經歷了一個由原來的藝術電影、商業電影、主旋律電影而向大眾文化轉化的“大眾化”的過程,當然,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化”。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大眾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差異,高雅與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壇,通俗文化步上臺階,向主流靠攏,共同在經濟、政治、科技、商業與文化的全面滲透中互相交融。中國當下文化發展的現實,已經逐漸發展成具有中國本土的獨特性的大眾文化。
(三)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必須考慮其當下語境
探析傳統文化在電影中的“現代轉化”應該考慮當下語境即全球化背景、“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力、合拍片的大量增多和電影中的文化融合等問題。
在當下“全球化”“全媒介”“互聯網+”的時代文化語境中,好萊塢電影文化的全球影響力是極大的。至少在目前中國與美國的文化交流和傳播就還不是完全對等的。美國電影大片對中國年輕幾代觀眾的觀影趣味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力甚至是某種“控制力”。因為美國是電影大國和電影強國,占據全球90%以上的電影市場。百余年來一直強力輸出電影也輸出美國文化。而中國則是美國最大的海外市場,在近年中國電影總票房強勢上漲的形勢下,美國電影的票房仍可占到將近一半。
而在電影生產的層面上,合拍片的比重在電影生產中也逐步提高。兩岸三地乃至多地、跨國的合作拍片方式漸成趨勢并越來越普遍,局限于一地的封閉式拍片方式無論數量還是影響力都漸趨衰落,兩岸三地乃至部分海外的電影開始進入一個跨越區域、國家、甚至民族疆界而互相滲透、合作、融合的狀態。因而在合拍片中,異質、跨地文化的多元融合必將成為一種常態。
這也是我們不能不面對的“現實一種”。
二、傳統文化現代轉化的幾種類型
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博大精深,風格表現亦頗為多元豐富。例如,藝術美就不僅有錯彩鏤金的美,也有清水出芙蓉的美,既有文人畫式的飄逸清高、抒情寫意,也有民間年畫的色彩濃艷、工筆寫實。因此,不同形態的傳統文化或傳統美學、藝術精神,在今日中國電影中的轉換和呈現也各有不同。
(一)傳統寫意性美學與文人文化的現代轉化
寫意與寫實相對。“寫意性是中國傳統美學的一種重要精神,并表現于詩歌、書法、繪畫、戲曲等藝術門類。概而言之,這種藝術精神重神輕形,求神似而非形似,力求虛實相生甚至化實為虛,重抒情而輕敘事,重表現而輕再現,重主觀性、情感性而輕客觀性,并在藝術表現的境界上趨向于純粹的、含蓄蘊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界。”

電影《城南舊事》劇照

電影《小城之春》劇照
在中國電影史上,《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東流》《早春二月》《枯木逢春》《巴山夜雨》《小街》《城南舊事》《春雨瀟瀟》等影片,以其緩慢、凝重、抒情的風格,文人逸趣、空鏡頭的比喻和象征,移步換景的鏡頭語言等,一向被標舉為傳統美學在電影中現代轉換的典范。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古典繪畫的空間意識和畫面結構等傳統藝術精神,的確曾經影響過上述電影的影像結構、鏡語組成和風格樣態。最近的《刺客聶隱娘》又續上了這一傳統,而且這一承續是在當下商業氣息濃厚的氛圍中以極端的方式進行的。《刺客聶隱娘》畫面極為細膩,意境頗為深遠高古,對話精簡,情節高度濃縮,表現極為含蓄,意味格外清新雋永,體現了中國古典美學精神之一種,這是一種文人化了的、書卷氣很濃、很中國化的文人情懷、歷史倫理觀和詩意雅興。不妨說,上述影片對傳統寫意性的意境美學精神的轉化是比較“原汁原味”,甚至是形神俱佳的。但這樣的原汁原味在今天卻陷入“小眾化”的票房窘境。
中國電影中還有另一種寫意美學的“現代轉化”,這可以以香港導演王家衛的電影為代表。他的《重慶森林》《東邪西毒》《一代宗師》等影片的影像語言和藝術表現方式均具有鮮明的寫意性特點。在其電影中,透過動感十足、燈紅酒綠、眼花繚亂的鏡頭畫面,甚至是不無扭曲和夸張變形的影像狂歡,呈現了一種強烈的視覺感官化特征,我們能夠感覺到一種抒情的風格化、寫意化的美學表現。但濃郁的都市生活氣息、快節奏的生活、絮絮叨叨的獨白,又使得這種寫意性美學不再是那種寧靜圓融的境界和緩慢抒情的風格。不妨說,這是一種“現代寫意”,也可以說,作為傳統美學精神的“寫意性”在王家衛電影里已發生了“現代轉換”。漂泊不定的人物、燈紅酒綠的浮華世界、“動態”的影像與畫框的不斷被打破,使得這種在傳統藝術表現中寧靜、均衡、飄逸的舊文人式的詩情畫意,變成了現代人生的喧鬧、繁雜、浮囂與躁動不安。
(二)傳統藝術意境美學的現代轉化
宗白華曾經在《中國藝術意境的誕生》一文中反復論述過中國藝術的意境美學精神及其表現:“‘情’與‘景’(意象)的結晶品”,“——以宇宙人生的具體為對象,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借以窺見自我最深心靈的反映;化實景而為虛境,創形象以為象征,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意境’。藝術境界主于美。”新世紀以來,一些“古裝電影大片”的藝術實踐,則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對中國古典之意境美學的追求和影像表達,體現了另一方向的傳統文化精神之“現代轉化”。
作為現代大眾傳播媒介和新型藝術門類,古裝電影大片對中華文化的影像化轉換,是寫意性、表現性美學的影像再現和符號化表現。這類“古裝”題材電影本身就因其與現實、當下的疏遠而別具詩性和文化符號性,別有一種超現實美學和東方美學的意味。如《英雄》極為重視對“場景”的凸顯,常常以開闊的、高遠的航拍鏡頭,取開闊的大遠景、全景畫面,體現出超現實的意味,形成一種色彩與構圖的大寫意風格。特別是無名與殘劍在張家界湖面上飄逸飛舞、點到輒止的打斗,以及對于影調、畫面和視覺風格的著意強調,使得這些場景具有了一種中國意境的味道,是一種有東方文化“意味”的“形式”或“符號”。不難發現,張藝謀的畫面表現得頗為大氣,營造了一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物我兩忘,離形去智”的精神浩氣,有時則是一種“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式的恬靜從容、沉靜闊達。這是一種獨得中華文化藝術精神之精粹的意境的影像化表現。宗白華說過:“一切藝術都趨向音樂的狀態、建筑的意匠”,“‘舞’是中國一切藝術境界的典型。中國的書法、畫法都趨向飛舞。莊嚴的建筑也有飛檐表現著舞姿”,“中國的繪畫、戲劇和中國另一種特殊的藝術——書法,具有共同的特點,這就是它們里面都是貫穿著舞蹈精神(也就是音樂精神)。”我認為張藝謀電影也有明顯地趨于對“樂”和“舞”的境界的追求,以中國特有的中國武術、中國功夫營造出了一種“武之舞”的武術境界和藝術韻味。
另外,張藝謀在《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影片中還營造了一種繁復奇麗、錯彩鏤金、濃墨重彩、裝飾性效果很強的美。從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角度看,這種在中國古典美學形態中并不占有主導地位的繁復奇麗、錯彩鏤金的美,既是民間工藝美學之美的“現代轉化”,更成為了一種當下大眾文化背景下兼具艷俗和奢華的雙重性的“新美學”。這種新美學表明,在此類視覺化轉向的電影中,色彩與畫面造型的視覺快感追求被發揮到了極致。
(三)傳統“邊緣文化”“亞文化”或“次文化”的現代轉化
近年來,中國的妖魔鬼怪題材或玄幻魔幻類電影頗受歡迎。早幾年票房平平的《白蛇傳奇》《畫壁》《倩女幽魂》,今年創新并打破票房紀錄的《捉妖記》《大圣歸來》(動畫電影票房),以及《九層妖塔》等,均與中國古代民間傳奇、傳說有著千絲萬縷聯系。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妖鬼仙魔的傳說歷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奠定中華文化心理原型的孔夫子就頗為排斥(“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漢后的儒學文化更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里的百家自然也包括雜家、陰陽家等。就電影而言,作為電影類型的玄幻電影或魔幻電影在內地一直付諸闕如。雖然在中國電影史上,一些武俠電影(如從《火燒紅蓮寺》開始)有一定的玄幻、魔幻元素,香港武俠武打電影中更是常常有奇幻色彩,但在中國大陸,由于主流文化的禁忌(如唯物主義的原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要求)等復雜原因則一直“失語”。妖仙神鬼故事往往被貶為封建迷信、糟粕(如20世紀60年代昆曲《李慧娘》的遭遇)。但在1949年前和香港電影里,則仍然有不少表現。香港鬼片堪稱發達。有關白蛇、倩女幽魂等聊齋民間傳說故事就經歷了多次翻拍,不乏經典作品(如《畫皮》《倩女幽魂》)。這些妖鬼仙魔題材電影借助高科技手段,在視覺奇觀表達、特效等方面強化玄幻色彩,以奇觀化的場景、服飾道具人物造型等營造出一種有別于好萊塢魔幻、科幻大片的東方式的幻想和奇詭,把人性、愛情、人與動物、人與妖、人與自然等的原始情感推向幻想世界進行某種“詢喚”,完成大眾對魔幻和超驗想象世界的超驗想象和奇觀消費。
《畫皮Ⅱ》把此類“中國式魔幻電影大片”提升到一個高度。影片在把狐妖鬼魅的文化“大眾文化化”的過程當中,又結合了很多西方魔幻電影的類型要素。影片中的場景設計、畫面構圖、色彩渲染,往往并非純中國的,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還有來自西方。因此影片頗具文化融合特征。實際上,除了“狐妖”這一角色的原型來自中國民間的志怪妖仙文化外,電影與原著《聊齋志異》的聯系并不緊密。這部映射諸多當代話題(也是一種“接地氣”)的魔幻電影中雜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號,并以精美奇絕的視覺效果呈現。在文化取向上,《畫皮Ⅱ》既有自己的堅守,也有開放和吸收。它表現出了具有東方文化氣象的意境、境界,營造了很中國化、很詩意化的影像風格造型,如在青藏高原拍攝的高遠遼闊的天空湖泊,那種純潔天藍、山水一色的影調等,就總體風格意境而言,無疑是東方化的。這也符合影片主創方的定位和追求:一種“東方魔幻大片”。
此外還有徐克導演的《狄仁杰》系列(《狄仁杰之神都龍王》是徐克繼《狄仁杰之通天帝國》之后的又一力作)。在拍這兩部之前,徐克早年在香港拍的《蜀山》系列、《倩女幽魂》系列、《東方不敗》系列已經頗有妖魔玄幻的神秘色彩。在影片中,徐克的想象力頗為豐富,造型、細節、橋段,奇門遁甲、怪力亂神、天馬行空而匪夷所思。在徐克天馬行空、甚至大巧若拙、拼貼游戲性的想象力之外,還能發現徐克以本土文化為底蘊對其他文化的融合發揮,發現他對東方文化的情有獨鐘。徐克在電影中表現了某些在中國儒家文化主導下不入流、邊緣化的“亞文化”,或者如監制陳國富所稱的“神秘次文化”(陳國富說,狄仁杰系列的亮點之一就是古代的各種神秘次文化)。徐克還巧妙地把這些“神秘次文化”與現代科技進行大膽接合,創造出許多既科技又玄幻的奇觀。《神都龍王》里,古代文化中神秘的“蠱”術變成了現代生物基因突變、生化危機。這些細節常常讓我們想起《侏羅紀公園》《異形》《食人魚》等科幻片或災難電影。《狄仁杰之神都龍王》是一種中國文化本位的玄幻電影,但呈現了極為多元復雜的文化融合。

電影《大圣歸來》劇照

電影《捉妖記》劇照
這種亞文化轉化和融合的意向同樣見諸于《捉妖記》。由“怪物史瑞克之父”許誠毅導演的《捉妖記》,接近童話,更像動畫片。影片從中國傳統志怪中汲取了靈感和精髓,但又明顯融入了導演駕輕就熟的美國動漫電影造型的特點,小妖王胡巴領銜的妖怪的造型頗為美國化(人稱是“怪物史瑞克”“小黃人”“大白”等動畫人物的同父異母兄弟),也顛覆了中國傳統妖怪恐怖、冷艷和猙獰的形象。從某種角度看,中國人的“妖鬼情懷”本質上是中國人對于自然、對于“道”的情懷的變相表達,這是對正統儒家文化禁忌的一次心靈的放假和想象的“還鄉”,是對自由、浪漫、返璞歸真人生境界的向往,是“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境界的理想表達。更重要的是,影片表達的這種萬物平等、人妖和諧的美好理念超越了單一文化,表達了一種普適性的普世自然觀。
鑒于中華文化的精深渾厚和駁雜多樣,也由于文化大繁榮時代人民群眾的精神與娛樂的雙重需要,我們應該大力發展具有中國特色、具有中國文化傳統淵源的魔幻玄幻電影,我們要把中國傳統文化中邊緣性存在的民間民俗志怪文化、道家哲學等與高科技支撐下的影像奇觀結合起來,開發新的生產力。這些文化的影像化——當然是經過改造的——實際上折射了真正的文化大繁榮。我們就應該有這樣的文化胸襟,讓各種類型的傳統文化,只要是大眾喜聞樂見的,都成為當下影像文化再生產的有機源泉。
(四)《大圣歸來》:經典的再造
文藝“經典”,泛指在歷史上頗為優秀的,得到公認的,具有一定權威性、公信度和美譽度的文藝作品,是傳統文化精神的重要凝聚。不用說,《大圣歸來》是經典小說《西游記》的“現代轉化”。《西游記》、孫悟空,都是一個大IP,一直以來都有“現代轉化”。但2015年的動畫片《大圣歸來》卻別有特色。
《大圣歸來》雖以《西游記》故事為依據,但孫悟空這個形象卻有創新。不難發現,影片對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在立足于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大膽拿來的。這部動畫電影的造型及孫悟空的形象,和以往的動畫形象不太一樣。它似乎不那么純粹、輕盈、空靈、靈動,也不再扁平化。影片對孫悟空這個形象的內心世界頗有新的開掘,使其不再只會打妖怪。《大圣歸來》中的孫悟空更像一個現代版、互聯網時代的“哈姆雷特”:猶豫彷徨、不自信,在虛名和實際本領的虛榮和反差中,在尷尬窘困中迷茫憂憤、自怨自艾,等待來自江流兒自我犧牲的逆向“拯救”。
在美學風格和文化表意方面,《大圣歸來》頗為多元化。一方面,它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有效地化用了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中華文化符號;另一方面,又向“美系”“日系”動漫風格借鑒。影片較好地融合了兩種造型風格:“美系”動漫的形象造型風格偏陽剛、粗獷、強悍、霸氣,是超人式、英雄化的(大圣形象最為集中明顯);日系動漫的“治愈系”,乖巧、叨嘮、善良、聰慧(包括江流兒和土地公、山妖等的造型)。這兩類形象造型在影片的敘事中形成了一種剛柔相濟、張弛有度的戲劇性效果。
就此而言,我認為《大圣歸來》是對傳統文化的一次成功的“現代轉化”,影片主創有一種開放的文化建設心態,對大圣形象進行全新的改造,讓在美系、日系動漫電影的浸潤下長大的幾代青少年在接受“大圣“這樣的中國形象時增強了親切感和親和力。
三、結語:問題、原則與立場
美國文化學者費斯克曾指出:“我們生活在工業化社會中,所以我們的大眾文化當然是一種工業文化,我們所有的文化資源也是如此,而所謂資源一詞,既指符號學資源或文化資源,也指物質資源,它們是金融經濟與文化經濟二者共同的產品。”的確,傳統文化、傳統藝術精神和形態,不正是我們今天文藝創作的“符號資源”“文化資源”嗎?轉化利用好了,它還能轉化成為“物質資源”,成為“金融經濟與文化經濟二者共同的產品”。
不妨說,在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中,轉化生成的是顯文本,而傳統則是“潛文本”。西方影視文化學者認為這種“互文參照性”是大眾文化時代媒介文化敘述的重要特征。它并不是對原有的東西進行汲取和簡單的轉換,而是一種再創造,因為它可以賦予原來的文本以完全不同的文化意義。在大眾文化的意義上,正如柯林斯所言:“這種互文指涉是后現代大眾文化具有高度自覺意識的標志:一種對于文本本身的文化狀態、功能、歷史及其循環與接受的高度自覺意識。”對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經典的再度闡釋、再生產顯然是今天我們文藝生產的重要方式。
毋庸諱言,電影中傳統文化“現代轉化”過程中會出現很多問題,如無法規避的文化“貼現”或“折扣”,融合的不和諧性,還有經不起考據的“文化錯位”、歷史挪用或過于荒謬的“時空穿越”:《夜宴》中中國武士像日本武士那樣切腹自殺,《黃金甲》中日本“忍者”式的怪異造型和打斗武器,《英雄》中羅馬士兵似的盔上紅櫻和羅馬式的大軍團列陣,《大圣歸來》中孫悟空形象不中不西的奇特造型,《捉妖記》里明顯更多源于美國動畫形象造型的萌萌的“胡巴”……
但我們要寬容,畢竟在全球化時代,文化的原汁原味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何況中華文化一直是在重構中發展的。文化不能僅僅停留在典籍上、鎖在深宮博物館里,而是要進入文化傳播場域,也不能過于無視觀眾和市場。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傳播為王,效果第一。沒有觀眾,沒有票房,再好的東西也是單向度的,無法進入有效傳播。文化傳統、美學藝術精神這些典雅高貴之物,與其在神殿上供奉千年,不如借助現代傳播媒介“飛入尋常百姓家”。作為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電影對文化的承載、轉換、傳播,必然會有文化的變異,適度的娛樂化、大眾化,一定的文化交融雜糅,也是難免的。當然,要有度,要有底線。而最重要的底線是,中華文化要占主導地位,或者說,總體風格情調氛圍境界上,應是中華性、東方化的。
在當下的文化態勢中,我們身處其中的已經不是西方與東方簡單對峙的階段,而進入互融、互包、互惠、互利、在競爭中尋找生機的階段。我們殷殷期待藝術工作者:既要有對傳統文化的尊重和敬畏,又要在藝術的再創造中秉持開放多元、有容乃大的從容心態,在堅守的前提下有對外來文化的大膽吸取、借用。我們敬畏傳統但不是拘泥于傳統。在立足本土的立場上,我們完全可以大膽拼貼,融合,創意制勝。唯有如此,新型、和諧、富有生機與活力的世界文化才會在沖突與融合的必要的張力中健康和諧地發展。
注釋:
[1]如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M].北京:三聯書店,1988.
[2][法]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 攝影機——自來水筆:新先鋒派的誕生[J]. 世界電影. 1987(6).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匈]阿諾德·豪澤爾. 藝術社會學[M]. 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274.
[5][匈]貝拉·巴拉茲.電影美學[M]. 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3.
[6]參見陳旭光. 大眾、大眾文化與電影的“大眾文化化”——當下中國電影生態的“大眾文化”視角審視[J].藝術百家. 2013(3).
[7]參見陳旭光. 藝術的意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153.
[8][9][10]宗白華.藝境[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159;167;289.
[11][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33.
[12][英]吉姆·柯林斯. 電視與后現代主義.載林少雄,吳小麗主編.影視理論文獻導讀(電視分冊)[M]. 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5:249.
陳旭光: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副院長
責任編輯:雍文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