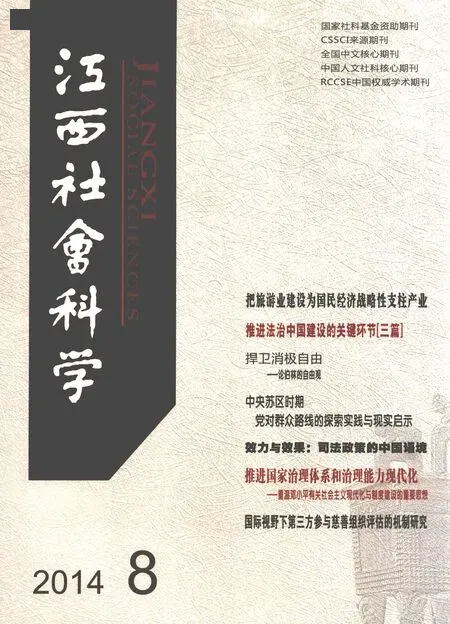都市寫作的困境——以晚生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型為例
■葉祝弟
在20世紀(jì)末的文壇上,晚生代作家已經(jīng)廣為人們所關(guān)注。所謂晚生代作家,主要是指20世紀(jì)60年代出生,90年代登上文壇的青年作家群體。關(guān)于晚生代一詞的由來,陳曉明在其主編的晚生代叢書的前言中提及這件事情,在描述20世紀(jì)80年代先鋒派思潮中,他首用這個概念,用以命名85新潮之后的小說家,后來這一名稱用來指20世紀(jì)90年代之后登上文壇的更為年輕的作家,如韓東、邱華棟、朱文、林白、陳染、畢飛宇等,還有一些評論家將衛(wèi)慧、棉棉、魏微等一批70后的作家也囊括在內(nèi)。雖然文壇對這批作家的命名是斑駁而模糊的,評論家們試圖用各種時間性的詞語,命名這批寫作風(fēng)格存在差異的作家,但是總體相似的文學(xué)背景和文學(xué)理念,使得他們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某種共性。在創(chuàng)作上,他們的作品可以被概括為個人化寫作、對宏大敘事的逃離;在精神氣質(zhì)上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反抗傳統(tǒng)的文學(xué)觀念和現(xiàn)存的文學(xué)秩序。總體來說,晚生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在直面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生活,以個人化寫作姿態(tài)關(guān)注個體生命的真實體驗,強調(diào)創(chuàng)作的個體性和自我意識。[1]
然而,以標(biāo)榜個人化寫作和都市欲望生活寫作為價值立場的晚生代作家,在凸顯個人生存的本相的時候,卻往往是以虛化歷史維度和收縮社會視角為代價的,文學(xué)中理應(yīng)被反應(yīng)的社會問題和時代命題,便懸置在文學(xué)之外,而難以進(jìn)入個人化寫作的視野。這種寫作視野的天然缺陷,反應(yīng)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就是普遍缺乏廣泛的生活題材和寫作對象,無法對生活做出明確的價值判斷;普遍缺乏對生活能力的把握,建立不起宏闊的文學(xué)追求和宏大的敘事氣象。這種創(chuàng)作的頹勢引起了一些批評家的關(guān)注,有些批評家看到晚生代作家正在陷入創(chuàng)作的畫地為牢中,許多晚生代作家的反抗性正在明顯萎縮;如有的批評家認(rèn)為,“我們有理由期待一種清晰的、透明的歷史感的寫作”。正是在這種不滿與期待的復(fù)雜心境中,在21世紀(jì)初,晚生代作家中的一批中堅開始了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型,比如林白的《婦女閑聊錄》、韓東的《扎根》、畢飛宇的《平原》、李洱的《石榴樹上結(jié)櫻桃》等作品,將目光從人們喜愛的都市空間轉(zhuǎn)向熱氣騰騰的鄉(xiāng)村,寫作風(fēng)格也呈現(xiàn)了別樣的氣象,對這些作品的分析和總結(jié),有利于窺出晚生代作家群體的創(chuàng)作的新變,也有利于蠡測當(dāng)前都市創(chuàng)作的問題和走向。
一
從一開始,在都市里從事寫作的晚生代作家們,選擇了一種拒絕與主流話語合作的邊緣者的姿態(tài)。出于對中心意識形態(tài)的恐懼,他們選擇了邊緣性的位置,扛起個人化寫作的大旗,在經(jīng)驗和立場上力圖成為獨特個性的“那個個人”。晚生代作家的都市小說里,出現(xiàn)了一大批游離于主流的小人物,他們是都市的流浪者和遺棄者。晚生代作家塑造了都市里漂的一代,并以此為隱喻,傳達(dá)出晚生代作家在既定的社會秩序里面的殘缺感和邊緣感。
第一,邊緣立場。陳染、林白、海男、韓東、朱文等一批作家,似乎一登上舞臺就在個人化的生活經(jīng)驗、日常化的生活氣息中表達(dá)他們對生活的看法。他們自認(rèn)為是“時代的孤兒”(東西)。這種身份的自覺,使得他們天生以與生活平行或者低于生活的姿態(tài)進(jìn)行寫作。
這種邊緣化的立場是晚生代作家能夠安身立命的真正的要素。他們從中心退回內(nèi)心,從集體書寫退回個體言說,挖掘個體一己的經(jīng)驗,在日常生活狀態(tài)中言說,使他們的小說有了新的美學(xué)意味和生命意味。晚生代作家無一例外地流露出回到個人內(nèi)心寫作的愿望。如有人認(rèn)為“內(nèi)心是作品的長相”(畢飛宇);有人認(rèn)為,“如果不從自己最深切的這種痛感入手,那么我覺得這種寫作就沒有意義”(韓東);“我的全部作品都來自我的生命”(林白),正是這樣的立場,他們獲得了比前代作家更加自由的表述空間,使得他們所提倡的游離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外的個人化寫作得以大行其道。
第二,邊緣人物。晚生代作家塑造了一大批生活在時代邊緣的人物,她們要么是同性戀者,如倪拗拗和禾寡婦(《私人生活》)、二帕和意萍(《瓶中之水》);要么是自戀、戀父者,如《子彈穿過蘋果》、《回廊之椅》中的朱涼、《無處告別》中的黛二小姐;要么是生活在城市邊緣的無業(yè)游民,三個百無聊賴的朋友(《三人行》)。他們的小說里充斥著失意的詩人、自命不凡的天才、招搖過街的騙子、深夜不歸的酒鬼以及毫無羞恥之心的妓女和嫖客。
第三,邊緣心態(tài)。通讀晚生代作家早期的作品,似乎所有的作品里面都散發(fā)出那種壓抑、猥瑣、迷惘、狂放的氣息,這些人物的精神永遠(yuǎn)在流浪。在路上奔跑,是他們的人生狀態(tài),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酒吧到另一個酒吧,從一個臥室到另一個臥室,在這些不同的場景中他們疲于奔波,靈魂無處安家。
人格的裂變是他們的普遍的心理狀態(tài),幾乎所有的人物內(nèi)心都是分裂的,他們在生活的縫隙中生存,他們掙扎在愛與痛的邊緣,他們默默體驗著孤獨的苦酒。傳統(tǒng)的英雄或者梟雄與他們都沒有關(guān)系,他們只不過是正常人中的一個,只是比正常人要壞一些,要遲鈍一些,要曖昧一些;匪夷所思是他們的行動狀態(tài),他們總是在恐懼和懷疑中生存,他們對世界充滿了不信任,道德的沖突和陣痛在他們身上體現(xiàn)得那么自然,那么栩栩如生。這是一種典型的頹廢心態(tài),正如魏微所說,“人們喪失了理想,然而內(nèi)心是慌張的,在這個太平盛世里,我們失去了內(nèi)心的平和,這是個無依無靠的時代,與前后都斷裂了,成了時間之外的一個獨立,人都是小人,也是無依無靠的,簡陋,可憐。”
魯羊的中篇《九三年的后半夜》,可以被看作是晚生代作家眼中的時代圖像和背景。九三年應(yīng)該是一個時間的隱喻,舊的秩序正在被破壞,新的秩序還沒有形成,晚生代處在這個黑夜和黎明交替的夾縫中。這樣的后半夜,就是這樣一種時刻,“人類或僅僅是個人的真正境遇在此刻顯示出來。無家可歸者在此處更加無家可歸了。狂歡達(dá)到了高潮,并且開始疲乏;街頭巷尾站出來許多面孔和嘴巴。他們紛紛說,我是流氓我怕誰,并且我比你更流氓”,在這樣一個無所適從的時代,我,蘇軾(戲仿了宋朝的大知識分子),在一個大草垛上無所適從,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無法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一個漂泊的人。
與蘇軾同樣出于尷尬地位的,還有朱文小說中一再出現(xiàn)的小丁,拖著殘缺的身軀在城市的邊緣游走,整天無所事事,一種刻骨銘心的無聊感威逼著他。為了消除無聊,他不得不做出各種無聊的事情,編造各種無聊的故事去抵抗無聊。在《我愛美元》中,他和父親大肆談性,性成了生活唯一的目標(biāo);在《五毛鐘的旅程》中,打電話消磨無聊的時間,他們甚至興奮地以詆毀自己為樂,稱自己為“垃圾”。
第四,邊緣語言。與晚生代作家筆下的邊緣人物相呼應(yīng)的,晚生代作家的語言也是一種典型的邊緣語言。在晚生代作家那里,語言呈現(xiàn)出粗糙、質(zhì)樸的形態(tài),既沒有形式上的刻意創(chuàng)新,也沒有藝術(shù)上的雕琢。方言、口語和生活語言泥沙俱下,在晚生代作家的筆下活靈活現(xiàn),呈現(xiàn)著爆炸而又粗鄙的一面。在朱文的小說中,總是回蕩著一種粗野的激情。欲望的狂歡與粗鄙的語言紐結(jié)在一起,流露出一種強烈的挑戰(zhàn)一切、顛覆一切的意味,流露出都市邊緣人的率真和下層人的流氓氣。
林白在《我的全部作品都來自于我的生命》中寫道:“我80 年寫詩過來的,我想嘗試一種粗礫、有點臟,但很生動的語言風(fēng)格,多塞幾個他媽的進(jìn)去。”
到了《萬物花開》、《石榴樹上結(jié)櫻桃》、《平原》、《婦女閑聊錄》,都市邊緣人退場,或者回到農(nóng)村,原來在晚生代筆下被遺棄的鄉(xiāng)下人,開始占據(jù)了文本的中心位置。
《萬物花開》通過一個腦子里長瘤的大頭的獨特視角,觀察活躍在鄉(xiāng)村里的人物:殺豬的二皮叔、賺錢的王大錢、跳開放舞的女孩、偷情如家常便飯的鄉(xiāng)村男女。具有至高無上權(quán)力的禾三叔(可以和村里的任何一個女人睡覺);鄉(xiāng)間的、城市的順口溜、民謠在這里交匯;貧窮、懶惰、生育、死亡都在他們身上呈現(xiàn)出狂歡的精神。這里的每一個人都生活在自由自在的狀態(tài),他們生生死死。人們對外面的世界保持了一定的寬容,對于發(fā)廊女三躲把性當(dāng)成謀生的手段,三丫、四丫用肉體換取男人的錢財?shù)男袨椋麄儾]有太多的譴責(zé)。
王榨的鄉(xiāng)村人,不僅對人類保持著寬容的態(tài)度,而且對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滿懷敬畏。大頭與一頭叫妞兒的母牛的結(jié)合,完成了性的啟蒙,他小小的年紀(jì)就看透生死——“瘤子既使我通向死亡,也使我通向自由,它是我的雙刃劍。”
二皮叔殺豬是給豬放生,讓豬重新獲得做人的權(quán)力。二皮叔對生死有特別的理解,性和死亡連在了一起,死亡是新生命的開始。在王榨人看來,“萬物平等,萬物有靈”,連茄子花、豆角花,也因為豐腴茂盛而有性的象征。
在《婦女閑聊錄》中,王榨人另類是天生的,另類就是他們自由自在、最本真的狀態(tài)。他們并沒有像城市的敘述者那樣蔑視農(nóng)村、蔑視一切。他們笑看人生,在他們看來,苦難并不被認(rèn)為是苦難,鄉(xiāng)村也不再神奇和浪漫,但是他們按照自然而然的本相生活,渾身上下洋溢著狂歡的力量。
在扉頁中,林白說:“無論如何,我就是大頭。”在后記里,林白又說:“原先,我小說中的某種女人消失了,她們曾經(jīng)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優(yōu)雅,也魅惑,但現(xiàn)在她們不見了。”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那些潮濕的沙街、月光、青苔、鏡像、冷艷絕倫的女人,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肥沃的土地、牲畜、花朵、瘤子,狂野恣肆的鄉(xiāng)民。青瓷般幽冷孤寂的林白世界,轉(zhuǎn)而充斥著濃郁的泥土氣息。……王榨鄉(xiāng)村及其萬物生靈的鮮活,閱讀中我們心靈的震顫,確證了林白生活在別處的意義。”[2]
二
當(dāng)下寫作,相對于過去時寫作,它是一種現(xiàn)在時的寫作,是晚生代作品的敘事背景。晚生代作家對當(dāng)下生活日常狀態(tài)保持持久的興趣和熱情,他們通過個人的視角寫正在發(fā)生著變化的人和城市的關(guān)系。他們的欲望化敘事,一方面表達(dá)的是都市人在城市化過程中所享受到的某種自由,另一方面又流露了某種失控。他們潛入日常生活,感受日常生活的庸常、無聊、無力。
林白、韓東、東西的很多作品都是面向當(dāng)下的現(xiàn)在時的寫作,而不是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對歷史有著狂熱的迷戀。這種現(xiàn)在時寫作有著自身的必然性。90 年代人們普遍對歷史表示了某種冷淡,對與歷史相對應(yīng)的宏大敘事表示了嘲諷和不屑。作家們對社會的歷程作非歷史化的處理,他們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個人經(jīng)驗進(jìn)行創(chuàng)作,用身體感悟外在的世界,用感性的語言描摹外在的世界。依靠感官而不是大腦寫作,使得他們的作品熱衷于表現(xiàn)某些轉(zhuǎn)瞬即逝的感受。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讓晚生代作家們更加傾心表象化、平面化的世界描述。
表面上看,林白是擅長用過去時寫作的作家。她關(guān)于廣西北流的故事的講述很多就是用回憶的筆觸來展開的。林白的小說不是以故事取勝,而是以那些曖昧不清的混沌詭異的意象營造的氛圍取勝。在回憶中,故鄉(xiāng)的沙街總是以一種若有若無的面目出現(xiàn),呈現(xiàn)出斑駁不清的模態(tài)。她通過回憶,營造了一個“美麗動人、欲望勺勺、命運叵測的女人們”的世界。這些女人在沙街猙獰血腥的透著死亡和腐爛的空氣中掙扎、毀滅。林白對這些女人投去的是悲憫的目光,并且不時要跳出來對這些女人指手畫腳,她通過這些女人的塑造,“意在對女性隱秘、苦難經(jīng)驗反思和現(xiàn)實中女性欲望重新喚醒”。林白對她的女人們是一種愛憐的心態(tài),同時又是居高臨下的,她通過那些無所畏懼、在高低之間尖叫著飛翔的女體;通過美麗潮濕的雨季,賦予她的女子獨特的女性個人氣質(zhì)。李萵、姚瓊、冼小英無不是生機勃勃而神秘莫測地生活著。
這些女人詭秘的內(nèi)心世界傳達(dá)的正是身居異鄉(xiāng)的林白的個人生命體驗。她們雖然身在北流,但是與林白的個人現(xiàn)實世界是同構(gòu)的。在漆黑詭異的黑夜,林白通過回望北流沙街來塑造另一個現(xiàn)時的自我,以驅(qū)逐孤單靈魂的束縛。她通過自說自話實現(xiàn)自我的拯救。當(dāng)然林白是非常清醒的,這種回望的姿態(tài)并不能解救自我,靠陷入自我的想象、做虛幻的夢來拯救自己,其結(jié)果只能陷入更深的夢境中無法自拔。
在《婦女閑聊錄》中,林白擺脫了過去自我回望的那種敘事方式,林白學(xué)會了傾聽,她成了一個虔誠的聆聽者。她記下了中年婦女木珍的口述,進(jìn)行了一次拯救自我、解放自我的行動。這是另一種回望式的寫作,與林白以前的封閉式的回望式寫作不同。如果說以前的回望寫作是為了對現(xiàn)實生活的逃避,那么現(xiàn)在的這種回望式寫作更多的是一種對現(xiàn)實生活的熱情的驅(qū)動。回望寫作是一種雙重思維的寫作,一方面寫作者有著豐富的當(dāng)下經(jīng)驗,另一方面帶著這些經(jīng)驗再回望逝去的那些經(jīng)歷,就有了一種別樣的色彩和韻味。
《婦女閑聊錄》創(chuàng)作了一種閑聊體。《萬物花開》是林白的寫作由“個人化”全新風(fēng)格的過渡,《婦女閑聊錄》無論題材還是形式,都展示了林白從未有過的風(fēng)格。書中以第一人稱,散碎而又鮮活地還原了農(nóng)村婦女“木珍”的生活記憶,看似零亂而口語化,卻具有一種平靜中的文字力量。
當(dāng)敘述人處于一種閑聊的狀況時,她的內(nèi)心不會受到來自現(xiàn)實的壓力,她可以把現(xiàn)實的任何煩心的東西拋到一邊,全心全意陷入東拉西扯的閑聊中。她的這種回憶,因為有了距離而獲得了別樣的體驗。木珍“回望”的不是屬于一個婦女的個人內(nèi)心小世界。她展示的是一幅中國鄉(xiāng)村的典型的全景圖,是一個農(nóng)家婦女個人的歷史、家庭的歷史、自己所生長的鄉(xiāng)村風(fēng)土人情世故。在木珍的眼里,通過她的回憶,鄉(xiāng)下的那些風(fēng)物都擁有無限的溫情。她可以原諒一切,她可以容忍任何的困境,她甚至對自己的情敵冬梅也是充滿了某種理解和熱愛。
木珍鮮活的記憶帶給了林白別樣的生命觸動,木珍的那種幾乎是超脫了個人情感糾葛的人生態(tài)度影響了林白,讓林白感觸很深,走出了房間,找到了都市寫作和鄉(xiāng)土寫作的關(guān)系,評論家多有討論,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寫作中,人們對都市寫作和鄉(xiāng)村寫作存在的誤解也影響了晚生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型。
三
在現(xiàn)代化的版圖上,城市意味著文明,意味改變命運的機會,更意味著一種優(yōu)越的生活方式和現(xiàn)代化的生活形態(tài)。進(jìn)入大都市成了人們普遍的夢想。但是當(dāng)他們通過考試、上大學(xué)、工作來到城市,他們便像候鳥一樣遷徙到城市,或者歸隱到某個單位,或者自愿遠(yuǎn)離現(xiàn)有體制的控制,采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進(jìn)行創(chuàng)作。農(nóng)村的經(jīng)驗在他們身上烙下了深深的腳印。當(dāng)他們以闖入者的身份來到城市,因為沒有城市底層的經(jīng)驗和記憶,他們的寫作題材很容易狹隘在酒吧、高級場所這樣的中產(chǎn)階級生活的地方,或者城市邊緣地帶、地下場所這些同樣是與普通的城市居民隔膜的地方。
在晚生代作家的作品里,幾乎都是都市公共空間的場景,并施展想象。對一個城市的弄堂——一個城市最基本的單位結(jié)構(gòu),幾乎沒有什么正面的描寫。根本原因就在于以經(jīng)驗化寫作的晚生代作家,沒有城市生活的天生的經(jīng)驗,喪失了言說的可能性。比如在林白的作品中,主人公總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自怨自艾。
猶如自言自語一樣。這樣的寫作方式面臨著很大的問題。比如交流和理解的問題,一個人不可能完全在自己的空間里過著童話鏡子里一般的生活,這種幽閉的生活只能導(dǎo)致人生更大的虛無,對外界生活的拒絕,也就意味著個人的淪喪。
晚生代在城市是沒有根的,他們沒有深厚的城市底蘊。他們是在城市想象城市。他們只能在都市的邊緣從事生存和都市的雙重漂泊。比如,林白90 年代來到北京,她的前期所有的作品幾乎都是在北京創(chuàng)作的,然而卻沒有一部作品是反映北京的現(xiàn)實生活的,反而到了北京,在她的作品中主人公總是回望家鄉(xiāng)北流。北京,雖然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體現(xiàn)為權(quán)力意志,權(quán)力跟文化結(jié)合以后,往往就會構(gòu)成一種很特殊的文化圈。但林白基本上是排除在這樣一個文化權(quán)力機制以外的作家。
另一個原因,在于晚生代作家并沒有找到真正講述的都市語言。隨著方言的潰退,以及文字的演變,都市作為一個另面的“風(fēng)景”被發(fā)現(xiàn)了。《子夜》等一大批都市小說的面世,標(biāo)志著中國的都市文學(xué)進(jìn)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中國近百年來的文學(xué)長了一副極不對稱的體格——鄉(xiāng)土小說四肢發(fā)達(dá),都市敘事頭腦簡單。造成這樣的結(jié)果,不僅僅與作家的價值立場有關(guān)——我們是一個農(nóng)業(yè)文明傳統(tǒng)極其深厚的國度,我們一直以為農(nóng)業(yè)文明代表著正義和詩意,代表美和善,而都市文明是惡之花,代表著狡詐、欺騙、虛偽和萬惡——還與我們的都市經(jīng)驗表達(dá)的方式的貧乏有關(guān),相對于發(fā)達(dá)的鄉(xiāng)村書寫體系,我們無法找到適合都市書寫的方式。
一直以來,中國的作家認(rèn)為都市只適合用精雕細(xì)鑿的文字(歐化語言,白話文) 來表達(dá),而對用聲音為主的都市方言視而不見。甚至他們認(rèn)為都市只存在著公共語言,而方言只存在于邊遠(yuǎn)的鄉(xiāng)村。其實不然,事實上,在中國任何一個都市都有屬于自己的方言,這些方言產(chǎn)生于弄堂里巷,產(chǎn)生于瓦肆?xí)^,流傳在市井小民之間,他們是鮮活的,他們上不了廳堂,但是就像河邊的水草一樣,生命力旺盛,相對于普通話為代表的文字,它們才最大限度地承載了一個都市的記憶。
然而在現(xiàn)代性的思維模式下,都市方言也被壓抑了。我們總認(rèn)為雄偉的高樓、時尚的酒吧(對應(yīng)的是普通話為主的文字) 才是都市,那些或隱或藏的里弄 (對應(yīng)的是方言為主的聲音) 不是都市。我們的作家總以為只有規(guī)范的文字才是表達(dá)生活的最有效的手段,卻對都市里的方言沒有多加注意。他們在表達(dá)都市經(jīng)驗的時候,放棄了對都市方言的采用,而鐘情于干巴巴的文字。盡管他們殫精竭慮,從古典文學(xué)中汲取營養(yǎng),無奈植根于農(nóng)耕文明之上的古典詩詞對電話、電梯等現(xiàn)代詞匯一籌莫展,從西方文學(xué)中汲取營養(yǎng),對市民生活的描摹方面卻又是手足無措,他們一片茫然,于是他們開始懷鄉(xiāng),他們逃到對鄉(xiāng)村的書寫中去。中國都市書寫的失敗,我認(rèn)為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價值觀立場的偏見——如把都市描繪成為誘惑、沉淪、幼稚、虛偽的人間地獄,而是表達(dá)方式出了根本的問題——都市書寫中文字中心主義代替了語言中心主義。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敘事中,一直存在貶低城市、抬高鄉(xiāng)村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從茅盾的《子夜》到周再復(fù)《上海早晨》,城市幾乎等同于墮落、惡魔,而農(nóng)村則象征著詩意、溫情。中國一直存在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而鄉(xiāng)村生活中的苦難生活場景,風(fēng)俗人情中的倫理觀念,更容易產(chǎn)生深層的歷史感。在當(dāng)下社會,隨著城鄉(xiāng)交流的逐漸擴大,農(nóng)村社會的各種傳統(tǒng)道德的瓦解更容易被發(fā)掘和書寫。在都市寫作中,文字中心主義的寫作理念是對語言中心主義的戕害,事實上這樣的后果是非常嚴(yán)重的。都市書寫的失敗后,一大批中年作家錯誤地以為寫都市是沒有出路的,寫鄉(xiāng)村才能復(fù)活真實的經(jīng)驗世界。這種思維邏輯也同樣影響了一大批晚生代作家——這些都市之子。他們最初以寫都市聞名,尖叫著飛翔于文壇。從現(xiàn)在的情況來看,他們的都市書寫是失敗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深入到都市的方言中去觀察生活,表達(dá)生活。
這一批晚生代作家其實是虛偽的都市之子,他們并不是天然的都市人,他們的血脈里殘留著鄉(xiāng)村的思維因子。這一批作家大多童年生活在農(nóng)村,通過讀書考上大學(xué)進(jìn)入都市的經(jīng)歷,注定了不可能用徹底的都市思維去觀察都市,去深入都市的肌理進(jìn)行考察。他們要么用出生地方言(農(nóng)耕文化) 的邏輯來觀察都市,得出一個欲望、虛偽、做作的都市;要么用普通話的經(jīng)驗邏輯來描述城市,進(jìn)而遮蔽了那些生活在里巷弄堂的都市生活經(jīng)驗。他們的這種“隔”的身份割斷了他們與都市的最深刻的經(jīng)驗連接的可能,從而得出一個片面的、不成功的都市印象。在都市寫作失敗之后,他們最終又不約而同地逃向了對鄉(xiāng)村經(jīng)驗的書寫,逃回到那個最初最熟悉的世界里。
晚生代作家均不約而同地表示了對城市的失望和恐懼。其他的晚生代作家,表示出對鄉(xiāng)村的迷戀,視鄉(xiāng)村為自己的精神紐帶,如東西:“隨著三伯的過世,田氏家族中父輩的最后一雙眼睛從我的身上消失,也就是摸過我腦袋,看著我長大的那一代田家人已經(jīng)全部入土,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和故鄉(xiāng)就切斷聯(lián)系呢?”這種邏輯的后果是,中國的都市文學(xué)一直處于被壓抑被丑化的狀態(tài)。因此,一個作家如果要復(fù)活出鮮活的都市經(jīng)驗,就必須轉(zhuǎn)移自己的視線——從那些會堂、廣場、酒吧、游樂廳等公共性的領(lǐng)域轉(zhuǎn)向,轉(zhuǎn)到里弄、亭子間、閨房等都市最私密性的場合——用聲音(都市方言)而不是用文字(普通話標(biāo)準(zhǔn)語)來描述。其實,好的文學(xué)圖景不是都市寫作和鄉(xiāng)村寫作誰高尚誰低劣的問題,而應(yīng)該是都市寫作和鄉(xiāng)村寫作共同發(fā)展的狀態(tài)。可惜的是,大多數(shù)的晚生代作家都不可能熟練操作兩種題材的寫作。
[1]張鳳琴.大陸新生代小說創(chuàng)作研究述評[J].理論與創(chuàng)作,2004,(6).
[2]叢坤赤,俞春玲.對《萬物花開》意義與敘事立場的一種解讀[J].山東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