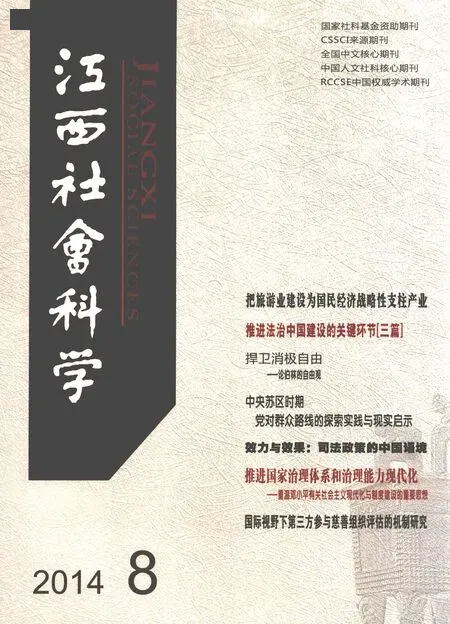“十七年”文學中新民歌的審美表征與反思
■戴 勇
作為一場由全民積極參與的詩歌生產活動,1958 年的新民歌運動所引發的詩歌生產現象,無疑是奇特而又令人震驚的。因為無論是詩歌的生產數量,還是創作者的數量,都是空前的。關于這段歷史的描繪,已有不少學者作出理性的剖析。①在眾多對“十七年”新民歌分析中,卻很少有人從詩歌內部藝術特征著手來分析,學界仿佛更加偏愛對“十七年”新民歌的外部歷史進行描述。本文試圖從新民歌的概念辨析入手,分析其審美特征,并反思新詩在當代的發展道路。
一、新民歌的源流梳理與概念辨析
中國早期民歌以描寫人們的日常生活場景為主。如最早的民歌《彈歌》寫的就是遠古人們的狩獵情形,而對后世影響最深的無疑是《詩經》中的《國風》。《國風》中許多民歌反映了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疾苦以及對統治者的血淚控訴,如《七月》、《伐檀》、《碩鼠》、《君子于役》等。這些民歌成為后世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七月》、《碩鼠》等詩篇在內容上表達了下層勞動者的心聲;在詩歌形式中出現了四言、五言的句式;在音韻上有押韻、和韻與對仗,這使得《國風》流傳最為廣泛,也最具影響力。《詩經》之后,中國民歌的發展呈蓬勃態勢,至秦漢,更產生了專門采集詩歌的官方部門——樂府,漢代出現了由官方編纂的《漢樂府》,其中漢樂府雙壁《木蘭詩》與《孔雀東南飛》則把古代民歌的敘事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唐代較有影響的民歌是詩人劉禹錫模仿巴蜀民歌“竹枝詞”所創作的《竹枝詞九首》。宋明清以來,有影響的民歌集如馮夢龍的《山歌》、李調元的《粵風》以及華廣生的《白雪遺音》、黃遵憲的《客家山歌》等。
從以上對中國民歌源頭的簡要梳理,可以見出中國民歌的起源是和勞動人民生活密不可分的。在古代民歌中,諸如日常勞作、豐收慶典、對暴政統治的揭露、對美好愛情的向往成為其表達的主要內容。所以可以這么理解,中國古代民歌指的是在民間流傳的、反映廣大勞動人民心聲且具有韻律特點的詩歌。古代民歌是中國傳統詩歌的一種重要表現方式,其與正統的精英詩人寫作的雅歌既相聯系又有差別。傳統雅歌更注重語言的書面化,更講究聲律的規則,而民歌則不避俗字俗語,更口語化。譬如明代末期北京廣為流傳的一首民謠:“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這首民歌語言樸實,讀起來朗朗上口,集中體現了當時下層勞動者的心聲。
如果說以《國風》、《漢樂府》為代表的古代民歌反映了廣大勞動者的民間疾苦的話,那么新民歌在內容上則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新民歌的最初設想源于毛澤東1958年3 月22 日在成都召開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面都要提倡學習,結果要產生一個新詩。現在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1](P124)毛澤東所說的民歌與古典結婚所產生的第三個東西指的就是新民歌。這在周揚于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所做的《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的發言中可以得到印證。周揚認為:“新民歌是毛澤東提出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創作方法的范例,它開拓了民歌發展的新紀元,同時也開拓了我國詩歌的新道路。”[2]
毛澤東、周揚的講話透露出兩個重要信息,即中國詩的出路在于古典與民歌嫁接,而作為“五四”文學革命產物的新詩主流位置則遭到否定。毛澤東對新詩的態度,引起了一大批精英詩人的極大憂慮與不安,代表者有何其芳、卞之琳、力揚等。何其芳認為“民歌體的體裁是有限的”,主張“批判地吸收我國過去的格律詩和外國可以借鑒的格律詩的合理因素,包括民歌的合理因素在內,按照我們現代口語的特點來創造性地建立新的格律詩”[3]。卞之琳也主張學習民歌要“結合舊詩詞的優良傳統,‘五四’以來新詩的優良傳統,以至外國詩歌可吸取的長處,來創造更新的更豐富多彩的詩篇”[4]。詩人力揚的觀點則更為激烈:“為什么有將近四十年的歷史,并為很多讀者所接受的新詩,就不能成為詩歌的新的民歌形式之一,不能成為詩歌的發展基礎之一? 這首先是粗暴地抹煞了中國詩歌發展的這段歷史,也是從不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民族形式的問題。”[5]
何其芳、卞之琳、力揚與毛澤東、周揚產生分歧的焦點是關于新民歌發展基礎的問題,后又擴大延伸為對詩歌民族形式、詩歌發展道路的大討論。盡管何其芳、卞之琳、力揚等詩人極力證明新詩的價值和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有著近40 年歷史的“五四”新詩資源在“十七年”文學中處于整體滑落的尷尬處境。“五四”新詩資源被遮蔽的根源在于“十七年”文學中以政治立場為核心的批評思維。這種批判價值尺度早在1955 年臧克家編選《中國新詩選》(1919—1949)所作的《“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代序)》一文中就初露端倪。在該文中,臧克家總結了新詩發展的兩條道路,一條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文藝派,另一條是以郭沫若、殷夫、蒲風、艾青、田間等為代表的革命浪漫派。以胡適、徐志摩為代表的具有鮮明精英意識的詩人顯然是不符合臧克家編纂詩選要求的。以胡適、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派”和李金發為代表的象征派被批判否定就不足為奇了。[6](P14)在排除了資產階級文藝派的新詩資源后,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革命浪漫派的資源照理是應該大行其道、枝繁葉茂了。然而事實上并非如此,按照毛澤東對新詩主要是新民歌的創作方法的定義,則此時的新民歌在發展基礎上既拒絕了胡適、李金發等作詩的歐化、西化的“主觀唯心”的新詩資源,又態度模糊地排斥了左翼詩人的寫實傳統。
新民歌倡導者主張從民間尋找資源,在內容上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統一,形式上是古典與民間的統一。由是,我們可以如此判定新民歌的概念,即指的是反映社會主義時期新的生活面貌與風尚、以古典詩歌創作方法寫作的詩歌。1958 年的新民歌運動把新民歌的創作推向了頂峰,而經由郭沫若、周揚編選的《紅旗歌謠》②則是這場新民歌運動的結晶。這部被譽為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國風”、“新詩三百”的新民歌集,彰顯出了新民歌在社會主義時期改革創作的實績。不過在新民歌的實際成型過程中,許多浮夸的因素逐漸取代了詩歌創作的基本規律,尤其是1958 年的“大躍進”,在“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盛行的年代,新民歌的創作呈現一片繁茂的態勢,尤其是在數量上達到了驚人的數目。據統計,“全國省以上出版社出版的民歌集子種數達700多種,至于地委、縣委、區、鄉乃至社出版的民歌集子,那更是無法計算,以四川省來說,僅141 個縣、市的統計,到十月份為止,已出版了民歌3733 種”[7](P4)。顯而易見,新民歌的創作逐漸異化,而這與古代民歌的自發自主的寫作大相抵牾,并且在審美形式上又顯現出詩歌創作主題精神的滑落與變異的重大弊端。
二、新民歌的審美表征
新民歌在題材選擇上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反映社會主義時期人們的生產勞動與精神面貌。如《紅旗歌謠》中描寫“大躍進”時期人們生活狀況的“農業大躍進之歌”、“工業大躍進之歌”;反映人們精神風貌的“黨的頌歌”、“保衛祖國之歌”。新民歌經常用一些公共意象作為抒情載體,來表達人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的豪邁熱情。在抒情主體上常常是以集體的“大我”的形象出現,而“小我”在新民歌文本中難覓蹤跡。
(一)公共意象的集體塑造
所謂公共意象指的是在詩歌創作中頻頻出現被創作者用作相同或相近情感抒發載體的藝術形象。公共意象大都表現為一種實物,如古典詩詞中經常出現的月亮、香草、楊柳、孤雁、飛燕等等。這些意象代代相傳成為人們廣泛認同的情感表達載體。新民歌中出現頻率最多的公共意象是“太陽”、“毛主席”和“黨”。以《紅旗歌謠》為例,59 首“黨的頌歌”中出現“太陽”意象的民歌達15首,出現“毛主席”意象的達28 首,出現“黨”的意象達11首。“太陽”是具體物象,象征著光明和力量。“毛主席”是具體人物,在象征意義上具有與“太陽”意象同質同構的隱喻意義。“黨”的意象不是一個具體實物,其在新民歌公共意象的塑造中暗含一種精神的象征。“太陽”、“毛主席”和“黨”三個公共意象既具有各自獨立的象征取譬,更多地又表現為意義的重構和疊合。換言之,這三個基本公共意象在文本的實際生成過程中是相互交叉、互為補充的。如四川簡陽有首民歌《四川出現雙太陽》:“陽春三月好風光/四川出現雙太陽/青山起舞河歡笑/人民領袖到農莊。”[8](P15)這首新民歌的中心意象是太陽,雙太陽的隱型譬喻暗示人民領袖為另一個太陽。湖北民歌《歌唱毛澤東》中更是把毛澤東直接比喻為“不落的紅太陽”,四川康定藏族民歌《那不是天上的太陽》也把“天上的太陽”比喻成“毛主席的光輝”等等。
“太陽’意象是和“黨”的意象有同一指稱內涵的,如甘肅武山的民歌《好不過人民當了家》:“牡丹花開象繡球,石榴花開結子稠;向日葵朝著太陽轉,人民跟著共產黨走。”向日葵與太陽及人民與黨,構成了兩相對應的對比意象。
新民歌中的另一重要的公共意象是“紅旗”,紅旗的所指是黨旗,能指卻異常豐富。如長沙民歌《紅旗是燈塔》:“紅旗插上山/山變萬寶箱/紅旗插上地/遍地長棉糧/紅旗插水中/紅河發電光/紅旗插心里/渾身有力量/紅旗是燈塔/前進有方向。”[9](P6)在這首民歌中“紅旗”意象隱喻指代社會主義總路線,這樣的新民歌在當時是比比皆是的。
“黨”、“毛主席”、“太陽”、“紅旗”為代表的公共意象的塑造是新中國前期中國文學新民歌創造的特有景觀,這種公共意象的集體塑造反映了當時文學思潮的走向,也顯現出當時新民歌意象生成的單調。
(二)抒情個體的集體失落
新民歌創作主體的身份多元,有革命干部、知識分子,但更多的是以農民、工人為代表的廣大勞動人民。新民歌的情感抒發主體有一個共同模式,即拋棄個體的小我,表現為公共集體的大我情懷。新民歌的這種情感抒發模式和20 世紀40 年代中國詩歌會的詩歌創作極為相似,抒情主體都彰顯出對民族大業及對祖國蓬勃發展的極大熱忱與關注,在新民歌大我情感抒發濫觴的同時,代表個體“小我”的私有情感整體消失。
新民歌的這種大我情感抒發與初期的白話新詩注重表現個體情感不同,新民歌的創作者無疑把自身設定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員,“我”變成了“我們”,這在《紅旗歌謠》所選錄的新民歌中表現最為集中。在300 首新民歌中,文本主體無一例外或抒發對社會主義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的歌頌,或描寫人們在農業、工業等勞動中的沖天干勁,或歌頌保衛祖國的戰士。比較而言,諸如惆悵、思念、愛情、鄉愁這些在古典詩歌中頻頻出現的情感則成為真空。由是,新民歌抒情個體的唯一性就泛化為集體性,個體的聲音淹沒在集體的洪流中。
新民歌抒情個體的失語癥,一方面源自于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需要,用集體的“大我”表達充分顯示出勞動人民的團結一心,另一方面又折射出當時的政治。
(三)民間口語與民間形式
與“五四”新詩的半文半白歐化傾向的詩歌語言相比,新民歌用的是純粹的口語,有的詩歌還夾雜了方言俗語,表現出濃郁的鄉土色彩。如“樹上喜鵲喳喳的叫,老漢咧咀忍不住地笑。……放近耳邊聽一聽,莫不是毛主席的說話聲?”(江蘇民歌《指路明燈》)日常用語入詩,明白如話,有口語化、大眾化特點。
云南哈尼族民歌《哈尼人唱躍進歌》描寫了哈尼族人高漲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及對黨的歌頌,詩中諸如火把節、打野豬、獻地神、祭龍等極富民族地域色彩的活動成為詩歌描寫的主要對象,地域色彩濃厚。
畬族民歌中常出現“俺”、“哥”、“妹”的人稱代詞,這些代詞的運用使得詩歌在傳誦中讀來十分親切。如《俺家住在南山下》:“俺家住在南山下,門前有株芙蓉花,情哥若到俺家去,俺請哥哥吃杯茶。泉水是妹親手挑,茶葉是妹親手摘,親手泡茶親手送,聽妹說句知心話:畬家若無共產黨,黃連樹上哪有花。”
從新民歌的詩行來看,創作者們充分吸收了中國民間歌謠創作的特點,并融會貫通成為新民歌的表現形式。其中快板、信天游、山歌、兒歌是新民歌運用最為廣泛的形式。快板本是中國民間曲藝中的一種似說似唱的表演形式,其特點是節奏感強,采用兩兩對應的韻文加以襯托,讀來朗朗上口,極易流傳。農民出身的王老九創作的新民歌就帶有鮮明的快板色彩,如其流傳最為廣泛的作品《想起毛主席》:“夢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陽起/種地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氣/走路想起毛主席/千斤擔子不知累/吃飯想起毛主席/蒸饃拌湯添香味/墻上掛像毛主席/一片紅光照屋里/開會歡呼毛主席/千萬拳頭齊舉起/中國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飄紅旗/中國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換拖拉機。”[10](P5 -6)這首新民歌共八節,每節兩句。在每節的第一句都用“想起毛主席”作為后綴,前后呼應。從節奏上看,每節三個拍子,三個拍子分別由兩個二字拍和一個三字拍構成,所以誦讀起來極富節奏感,讀來鏗鏘有力,這與快板的節奏異曲同工。
老舍的《“五一”快板》直接以快板為題描寫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蓬勃氣象,詩歌以“歌五一、唱五一”起興,下句分別連接著一個五字句和一個七字句,形成對仗,五字句和七字句的尾字押韻,體現出快板的快節奏和自由轉韻的特點。
信天游是流傳在我國西北黃土高原的一種民歌形式,其特點是曲調高亢,用二句體形式,前后兩句又常用比興,形象生動,極富感染力。收錄在《紅旗歌謠》中的新民歌《想起了公社忘不了你》就采用信天游的方式,表達了陜西米脂人民對領袖毛主席的感恩。“一朵朵紅花山頂頂開,辦起了公社幸福來。”第一句形成預設,第二句構成興,成為詩歌表達的重心。兩句又形成對照比興,結構完整,極富西北民歌色彩。
兒歌又是新民歌民間形式構成的一種重要方式,《紅旗歌謠》收錄了全國各地的兒歌有4 首,分別是湖南兒歌《新嫂嫂》、河北兒歌《荷花葉》、四川南充兒歌《好姑姑》、河南登封兒歌《新媳婦走娘家》。這些兒歌豐富了新民歌的表現形式,語言活潑,意象清新,充滿了童趣。
山歌是人們在日常勞作生活為了排遣煩惱、鼓足干勁以自娛自樂的一種民歌,主要流傳在高原、丘陵、山寨的貧瘠地區,主要表現形式有船歌、漁歌、牧歌等。在《紅旗歌謠》中出現了大量的山歌,如江西的《摘茶子山歌》、北京的《放水謠》、河北泊頭的《水田姑娘唱旱田歌》等。這些山歌描寫了當地勞動人民日常田間勞動的情形,具有濃郁的鄉土色彩。
三、對新民歌發展道路的反思
毛澤東對新民歌的展望是古典加民間,其中隱含的主題是詩歌創作要順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要為廣大勞動百姓所接受,為當時的“三面紅旗”搖旗吶喊。這種思想是與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脈相承的,即文學如何為政治服務的問題,所以文學的大眾化就勢在必行。
不可否認,誕生于“十七年文學語境中的新民歌確實成了當時一道別樣的風景,新民歌能在當時廣為流傳除了政治干預以外,新民歌的大眾化審美表征功不可沒。由于新民歌的大眾化特點,使得其在傳播方式上能被廣大讀者接受,并能成為當時宣傳國家政策的重要工具。所以,新民歌尤其是1958年的新民歌“有的時候,僅指一種具體的詩體樣式;而從更大的方面看,則是當代激進力量創建文化和文化運動方式的重要試驗”[11](P82)。新民歌以文化運動的形式、以集體生產的模式創造了中國詩歌總產量的神話,在當時就遭到評論者的嘲諷。青年作家吳雁指出:“說是一天寫出三百首七字句的東西就叫作‘詩’,我寧可站在夏日炎炎的窗前,聽一聽樹上知了的叫聲,而不愿被人請出作這類‘詩篇’的評論家。我唯一佩服的只是‘三百’這個數字。”[12]
從吳雁的批評文章不難看出,其對新民歌創造藝術規律的質疑,及對新民歌大眾化生產方式的否定。吳雁的嘲諷自然在當時語境中受到猛烈批判。不過,這對我們重新認識新民歌作為詩歌藝術的本身特點,有良好的啟示。
如果就詩歌藝術的本體而言,新民歌無疑是越走越遠。而從新民歌的整體審美特點及其作為中國新詩的發展道路來看,在詩歌傳統、詩歌藝術、詩歌功能上值得反思。
(一)“綁架”的詩的大眾化
純詩與大眾化是新詩發生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從胡適的白話詩肇始,到徐志摩、聞一多為擺脫白話詩散文化缺乏詩味弊端而創作的新格律詩,到李金發突破新月派受格律束縛為代表的象征詩,直至艾青的革命現實主義詩歌。這些精英詩人都在詩歌的形式與表現方式上進行了有效的探討。而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圍繞大眾化的三次討論,把文學的精英化與大眾化推向高潮。大眾化即文學的普及化,文學的普及化勢必拋棄創作主體所謂的“精英意識”,而在文學語言上呈現的是公共“我們”的集體意識,那么代表詩歌個人化、私語化的特質就自然而然被棄置。換言之,新民歌語言失去了詩歌創作主體作為標識的個人色彩,公眾的主題也消解了個人描寫的豐富性,在通俗易懂、淺白直接的詩歌語言描述中,摒除了詩歌語言的晦澀、精細與深邃。但凡沾染上西化的個人主體私語情感的語言,都被視為異端。所以肇始于“五四”時期的作為文學多樣表現的“五四”新詩,發展至新民歌就變成一場單一狹義的運動,“千篇一律的新民歌字里行間夾雜著大量的政治詞匯,在這場狂熱的全民詩歌運動背后隱藏著一個宏大政治烏托邦”[13]。這個宏大的政治烏托邦規定了新民歌的創作主題,所以與其說新民歌是新詩發展到“十七年”的一次文學選擇,不如說是一次政治的規約。新民歌作為新詩發展道路的目標,就變成了政治運動的手段。而新民歌的大眾化因此而變得異常扭曲,“大眾內涵不斷被抽空、壓縮,大眾和我們的界限泯滅了,我們消融到大眾的視野當中,我們不見了,最終真正的大眾也從所有的文學視野里隱退”[13]。新民歌的大眾化就這樣被綁架,不斷被抽空、隱退,而真正的大眾則在現實中沉浮,繼而被遮蔽。
(二)古典詩歌傳統曖昧不清
民間和古典是新民歌的兩個核心創造資源,但是在新民歌的實際成型中,民間的因素表現得更加充分,如快板、信天游、各種山歌的形式成了新民歌詩行的重要載體,并由此形成了新民歌歌謠化的民間特色。相較而言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卻曖昧不清,尤其是丟失了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精華——意境。眾所周知,意境營造是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一個核心命題。王國維就把意境的有無作為判定詩歌優劣的重要標桿,最好的詩是“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意境的形成離不開意象的有機合成,眾多意象的組合生發才能產生“虛實相生”、“韻味無窮”的審美效果。新民歌中雖然也出現了眾多的意象,但這些意象僅僅表現在詩歌語言的顯性表層,而缺乏意象連接的隱型象征。新民歌出現的意象群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托物言志”的傳統,然而在具體詩歌創作中,新民歌僅圍繞一個意象抒懷,缺乏意象之間的綿密性,因而就達不到意境所形成的基本條件。由是,意境的缺失則成為新民歌整體創作的一大短板。表面上看,在民間與古典兩結合的新民歌生產方式下,民間的資源可以為廣大勞動人民所喜聞樂見,古典的資源又可以彌補新詩發展的不足,實際情形卻是新民歌是在拐著腿走路,對民間的重視超過了古典傳統。就古典傳統而言,新民歌僅僅剩下對古代詩歌詩行的工整和對仗的模仿。
(三)詩藝的萎縮
新民歌在強大的政治口號和全民的參與下,呈現出批量生產、簡單復制的寫作浪潮,尤其是在數量上恐怕是空前絕后的。盡管在新民歌運動結束后產生了一些藝術水準較高的詩篇,如陸棨的《重返楊柳村》、沙白的《水鄉行》等。但整體而言,新民歌尤其是1958 年的新民歌在詩歌藝術上,走上了一條街頭詩、報刊詩、口號詩的老路。不可否認,新民歌的政治意義得到了極大彰顯,但其詩歌本身特質逐漸萎縮,最終走向一條極其狹窄的發展道路。毛澤東曾在新民歌運動結束后說:“新詩改革最難,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條大家認為可行的主要形式,確是難事。”[14]從毛澤東對新詩發展道路的反思中,不難看出中國新詩在“十七年”文學中的發展困境,中國新詩要走上一條獨立健康發展的道路,除了更多地繼承中國古典詩歌資源及民間傳統之外,也應該容納“五四”新詩的新傳統及西方世界文化資源,這或許才能使中國新詩有個更好的未來。
注釋:
①參見:謝保杰《1958年新民歌運動的歷史描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1期)和巫洪亮的博士論文《“十七年”詩歌研究》。
②《紅旗歌謠》有兩個版本,分別是《紅旗》雜志社1958年版和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本文討論的版本為后者。
[1]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2]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J].紅旗,1958,(創刊號).
[3]何其芳.關于新詩的“百花齊放”的問題[J].處女地,1958,(7).
[4]卞之琳.關于新詩發展的幾點看法[J].處女地,1958,(3).
[5]力楊.生氣勃勃的工人詩歌創作[J].文學評論,1958,(3).
[6]臧克家.中國新詩選(1919—1949)[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
[7]天鷹.1958年中國民歌運動[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
[8]郭沫若,周揚.紅旗歌謠[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9]中共湖南省委辦公廳.湖南大躍進歌謠[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
[10]王老九.王老九詩選[M].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4.
[11]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2]吳雁.創作,需要才能[J].新港,1959,(8).
[13]張桃洲.論“新民歌運動”的現代來源:關于新詩發展的一個癥結性難題[J].社會科學研究,2001,(4).
[14]臧克家.毛澤東同志與詩[J].紅旗,19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