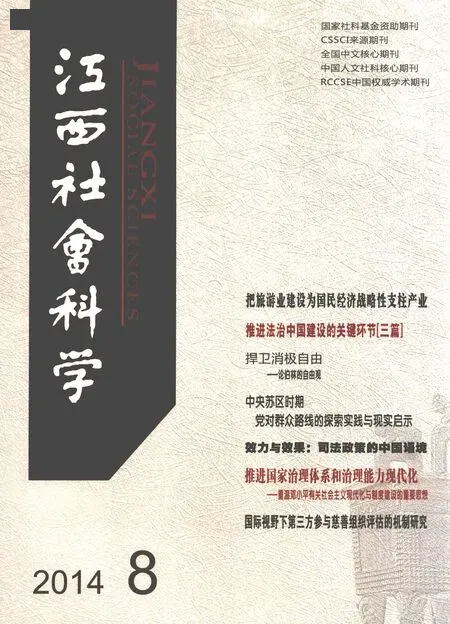西方實踐哲學傳統(tǒng)與馬克思實踐觀的革命
■孫樂強
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是當代西方學術界攻擊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漢娜·阿倫特,她重新回到西方實踐哲學的傳統(tǒng)來批判馬克思的勞動和實踐概念,企圖從根基上顛覆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然而,這一思路恰恰忘記了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正是從這一傳統(tǒng)中脫胎出來的。因此,在此背景下,細致梳理西方實踐哲學傳統(tǒng)的形成和演變過程,清晰界定馬克思的實踐觀與西方實踐哲學傳統(tǒng)的內(nèi)在關系,不僅具有至關重要的學術意義,同時也能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理解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革命意義提供有益借鑒。
一
在西方哲學史上,亞里士多德最先提出了實踐哲學問題。他把人的思想和活動分為三類:一是理論沉思,即通過理論思考來達到對世界不變本質(zhì)和原理的認識,它涉及的是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二是實踐,主要包括倫理和政治行為,它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主要是通過對倫理和政治行為的研究,使人達到至善的境界;三是創(chuàng)制,主要指勞動和技藝活動。[1](P118 -119)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理論和實踐都以自身為目的,而創(chuàng)制則以他物為目的,因此,在歷史地位上,前兩者遠遠高于后者。不過,前兩者又存在一定的差異:理論是對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研究,它不以人的意志和行為而改變;而實踐則受到人的行為和選擇的制約,無法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基于此,亞里士多德將理論視為人的最高層次的活動,接下來是實踐,最后是創(chuàng)制。
如何評價亞里士多德的這一思想呢?首先,他將實踐從理論活動中解放出來,將其詮釋為以自身為目的的倫理或政治行動,并賦予其獨特的理論地位,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chuàng)見,開啟了西方實踐哲學的傳統(tǒng),對后世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其次,亞里士多德將理論與實踐界定為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忽視了二者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同時開創(chuàng)了理論高于實踐的邏輯先河。再次,就實踐與創(chuàng)制的關系而言,前者是自由人從事的倫理或政治活動,而后者則是奴隸從事的低級活動,二者在內(nèi)涵和歷史地位上完全不同,開啟了貶低勞動的理論先河。總而言之,亞里士多德的三重劃分是與當時的奴隸社會相適應的,雖然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畢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價值訴求,對后來的西方哲學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到了中世紀,原本清晰的實踐范疇遭到誤用,出現(xiàn)一種“跨界”現(xiàn)象。康德指出:“迄今為止,在以這些術語來劃分不同的原則、又以這些原則來劃分哲學方面,流行著一種很大的誤用:由于人們把按照自然概念的實踐和按照自由概念的實踐等同起來,這樣就在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這些相同的名稱下進行了一種劃分,通過這種劃分事實上什么也沒有劃分出來(因為這兩部分可以擁有同一些原則)。”[2](P5 -6)結果,兩種不同的實踐都被冠以實踐哲學的名稱,導致實踐范疇的嚴重錯位。也是在此基礎上,康德重新界定了實踐范疇的內(nèi)涵:“如果規(guī)定這原因性的概念是一個自然概念,那么這些原則就是技術上實踐的;但如果它是一個自由概念,那么這些原則就是道德上實踐的;而由于在對理性科學的劃分中完全取決于那些需要不同原則來認識的對象的差異性,所以前一類原則就屬于理論哲學(作為自然學說),后一類則完全獨立地構成第二部分,也就是(作為道德學說的)實踐哲學。”[2](P6)以此來看,康德明確區(qū)分了兩種不同的實踐:一是“按照自然概念的實踐”,它完全基于自然因果性行事,因此,康德又將這種實踐稱為“技術實踐”,它只是理論哲學的“實踐部分”,不可能納入真正的實踐哲學。二是“按照自由概念的實踐”,它完全“基于某種超感性的原則”[2](P7),目的是使人類意志擺脫自然因果性的限制,達到真正的自由,因此,康德又將這種實踐稱為“道德實踐”,它已經(jīng)越出了理論哲學的范圍,構成了一個獨立部分,即“作為道德學說的實踐哲學”。
與亞里士多德相比,康德至少做了以下推進:第一,他明確區(qū)分了兩種不同的實踐概念。他在堅持亞里士多德倫理實踐的同時,將后者的創(chuàng)制活動納入技術實踐范疇,取消了“創(chuàng)制活動”的獨立地位,將其視為理論活動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沉思與創(chuàng)制活動的人為分割,揭示了二者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前者是理論,后者是理論的技術實踐,它們都遵循自然因果性。第二,康德進一步完善和發(fā)展了亞里士多德的道德實踐哲學。后者始終認為,道德實踐只是對特殊或具體行為的研究,不可能像理論那樣達到最高的普遍性,更無法推導出一種普遍適用的道德律令,這也是亞里士多德將理論沉思視為高于道德實踐的重要原因。而康德則摒棄了這一觀點,認為道德實踐實際上也像理論一樣存在著普遍法則,并從根基上證明并解決了這一問題,建立了自己的道德律令學說,實現(xiàn)了他所謂的“哥白尼革命”。第三,他顛覆了亞里士多德“理論高于實踐”的觀點,突出了實踐理性的優(yōu)先地位。康德關注的根本問題始終是人的問題,因此,他更注重與人的道德活動相關的實踐理性,而不是與自然或知識相關的理論理性,“在純粹思辨理性與純粹實踐理性結合為一種知識時,后者領有優(yōu)先地位……我們根本不能指望純粹實踐理性從屬于思辨理性,因而把這個秩序顛倒過來,因為一切興趣最后都是實踐的,而且甚至思辨理性的興趣也只是有條件的,惟有在實踐的運用中才是完整的”[3](P166 -167)。由此,他顛覆了亞里士多德理論高于實踐的哲學傳統(tǒng),開啟了實踐高于理論、道德高于知識的新視點。最后,康德區(qū)分了兩種不同的自由:一是消極的自由,即人可以任意選擇的意志自由;二是積極的自由,即在普遍的道德原則指導下的自由。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雖然康德將勞動和物質(zhì)生產(chǎn)納入技術實踐,開啟了對實踐范疇的新理解,但他并沒有真正揭示這種技術實踐與理論之間的辯證關系,而只是簡單地將技術實踐視為理論的具體運用,忽視了技術實踐的獨立價值和社會歷史意義,更沒有揭示技術實踐與道德實踐或自由的內(nèi)在關系,而是像亞里士多德一樣,把后者限定在純粹的主體領域,割裂了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的內(nèi)在關系,導致了現(xiàn)象界和本體界的二重劃分,這也為后面的發(fā)展埋下了伏筆。
二
與康德不同,黑格爾認為,真正的自由既不是對外在客體(自然必然性)的簡單認識,也不是從主體角度假定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道德自律),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實現(xiàn)的主客體統(tǒng)一。因此,黑格爾強調(diào),要想實現(xiàn)真正的自由,就必須縫合理論與實踐的分裂,因為這是達到主客體統(tǒng)一的前提條件。那么,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黑格爾的答案是:實踐。正是借助于實踐,絕對精神才不斷揚棄自己的外化形式,回歸自身,達到主客體的統(tǒng)一,最終實現(xiàn)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踐就是精神不斷揚棄外化最終回歸自身的歷史活動,而勞動和倫理實踐則是它的不同形式。正是勞動改變了奴隸與物的關系,確立了奴隸在自然面前的主體地位;同樣,也正是勞動顛覆了主人與奴隸的關系,使后者獲得一種自為的存在意識,成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獨立的自我意識(個人主體)。[4](P131 -132)更為關鍵的是,正是借助于勞動,自我意識才打破了相互分離的境界,確立了它們之間的相互認同和內(nèi)在統(tǒng)一性,使其發(fā)展為理性的自我意識。[4](P234)一旦達到了這種自在自為的狀態(tài),理念也就不再是純粹的理念,而是轉(zhuǎn)化為“實踐的理念,即行動”[5](P522),它必然要超越純粹的主觀性,實現(xiàn)主客體的內(nèi)在統(tǒng)一。
以此來看,真正意義上的實踐絕不是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理解的那種純粹主觀性的道德實踐,而是實現(xiàn)主客統(tǒng)一的具體活動。比如,在康德那里,“善”始終被理解為一種彼岸的“應然”狀態(tài),而良心也只是一種原則上的普遍性,完全被限定在純粹的主觀領域之中,缺少現(xiàn)實的支撐,因此,他理解的實踐只是道德原則的主觀實踐,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實踐。與此不同,黑格爾認為,善的實踐絕不是停留在主觀領域中的抽象行動,而是走出主觀性,實現(xiàn)與客觀內(nèi)在統(tǒng)一的過程,因此,善不是主觀領域中的“應然”狀態(tài),而“是同時在自由統(tǒng)一形式中的客觀的東西和主觀性”[5](P523),“善就是被實現(xiàn)了的自由”[6](P132)。也是在此基礎上,黑格爾提出了兩個重要命題。一,實踐包含理論。“理論的東西本質(zhì)上包含于實踐的東西之中。這與另一種看法,認為兩者是分離的,完全相反。”[6](P13)這一觀點從根基上揚棄了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缺陷,實現(xiàn)了理論與實踐的內(nèi)在統(tǒng)一。二,實踐高于理論。實踐“不僅具有普遍的資格,而且具有絕對現(xiàn)實的資格”[5](P523),因此,它在現(xiàn)實活動中必然高于理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黑格爾的貢獻首先是將勞動納入實踐范疇,充分挖掘了它的積極意義,顛覆了過去貶低勞動的哲學傳統(tǒng)。亞里士多德完全把勞動視為低級的奴隸活動,忽視了它的人類學意義。康德雖然將勞動納入實踐范疇,但仍只認為勞動是一種低級的技術實踐,沒有看到它的積極意義。在古典經(jīng)濟學的影響之下,黑格爾最先將勞動從西方哲學傳統(tǒng)中解放出來,將其上升到人的本質(zhì)高度,揭示了勞動在現(xiàn)代主體產(chǎn)生過程中的歷史作用。“黑格爾的《現(xiàn)象學》及其最后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chuàng)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chǎn)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非對象化,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zhì),把對象性的人、現(xiàn)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勞動的結果。”[7](P101)以此來看,黑格爾第一次從哲學高度揭示了勞動的人類學意義,顛覆了過去貶低勞動的理論傳統(tǒng),將勞動哲學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其次,黑格爾將實踐理解為實現(xiàn)主客體統(tǒng)一的中介活動,進一步豐富了實踐概念的內(nèi)涵。這一界定既超越了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的道德實踐哲學,也有效縫合了勞動和倫理實踐的二元分裂,將它們視為絕對精神在不同發(fā)展階段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前者是現(xiàn)代自我意識確立以及推動自我意識向理性發(fā)展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后者則是理念超越主客分離最終達到至善(自由)的中介活動,在絕對精神的主導下,實現(xiàn)了二者的辯證統(tǒng)一。
再次,黑格爾把實踐范疇引入認識論,提出了“實踐包含并高于理論”的命題,實現(xiàn)了本體論與認識論的辯證統(tǒng)一。“黑格爾通過人的實踐的、合目的性的活動,接近于作為概念和客體一致的‘觀念’,接近于作為真理的觀念。極其接近于下述這點:人以自己的實踐證明自己的觀念、概念、知識、科學的客觀正確性。”[8](P212)在黑格爾這里,實踐不僅是實現(xiàn)主客體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活動,而且也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重要標準,實現(xiàn)了本體論與認識論的辯證統(tǒng)一,既縫合了理論與實踐的外在分裂,也進一步強化了實踐對理論的優(yōu)先性,將實踐哲學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最后,黑格爾全面深化了對自由的理解,彌合了必然與自由的二元分裂,實現(xiàn)了二者的辯證統(tǒng)一。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黑格爾的整個實踐觀是建立在唯心主義之上的,他雖然看到了勞動實踐的積極意義,但究其實質(zhì)而言,黑格爾所說的勞動實踐只不過是精神和觀念的活動,而不是現(xiàn)實的人類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并沒有真正縫合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客體、自由與必然的二元分裂。
在黑格爾之后,費爾巴哈再次顛倒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他站在客體的角度來理解實踐,把它理解為一種骯臟的利益買賣活動,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猶太人的活動,“直到今天,猶太人還不變其特性。他們的原則、他們的上帝,乃是最實踐的處事原則,是利己主義,并且,是以宗教為形式的利己主義。利己主義就是那不允許自己的仆人吃虧的上帝。利己主義在本質(zhì)上是一神教”[9](P163),即金錢。基于上述邏輯,費爾巴哈指出:“如果人僅僅立足于實踐的立場,并由此出發(fā)來觀察世界,而使實踐的立場成為理論的立場時,那他就跟自然不睦,使自然成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實踐利己主義之最順從仆人。這種利己主義的、實踐的直觀——在它看來,自然自在自為地便是無——之理論上表現(xiàn)便在于它認為:自然或世界,是被制造出來的,是命令之產(chǎn)物。”[9](P161)這種實踐的卑污性,必然會玷污理論直觀的純潔性,使理論限于狹隘之中,淪為利益的囚徒。因此,費爾巴哈極力贊同理論直觀,反對實踐活動,由此顛覆了康德和黑格爾確立的“實踐高于理論”的邏輯。費爾巴哈之所以會得出這種觀點,根本原因在于他無法站到更高的層次上,看到實踐活動孕育的革命性力量,而只是依據(jù)具體形式來把握實踐,最終扭曲了它的科學內(nèi)涵。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質(zhì)》中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于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xiàn)形式去理解和確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10](P54)這一批判直接刺中了費爾巴哈的要害。在此后不久,馬克思從物質(zhì)生產(chǎn)出發(fā),揭示了實踐的科學內(nèi)涵及其哲學意蘊,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觀,實現(xiàn)了對整個西方實踐哲學傳統(tǒng)的變革。
三
馬克思的科學實踐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jīng)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學生階段,馬克思曾在康德和黑格爾的意義上使用過實踐概念。到了《1844 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已經(jīng)摒棄了二者的理解,開始基于工業(yè)生產(chǎn)來改造實踐范疇。在《神圣家族》中,他已經(jīng)明確指認了封建社會與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重要差別:前者的基礎是土地(自然),后者則是工業(yè)實踐。此外,通過對鮑威爾等人的批判,馬克思形成了獨特的社會認識論:歷史根源于塵世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只有從現(xiàn)實生活中的物質(zhì)實踐出發(fā),才能真正認識某一歷史時期。這就意味著,如果不從現(xiàn)代工業(yè)實踐出發(fā),就不可能真正認識現(xiàn)代歷史。而到了《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jīng)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馬克思已經(jīng)明確區(qū)分了工業(yè)的兩種不同尺度:一種是工業(yè)的客體尺度,即從工業(yè)所處的環(huán)境和現(xiàn)實的狀況來看,工業(yè)完全陷入買賣利益的異化形式之中,這是資產(chǎn)階級的工業(yè)形式;另一種則是主體尺度,即從“人的發(fā)展”、“人類歷史”的主體視角來看待工業(yè),這樣它就不再被視為買賣利益的異化形式,而是被看作為“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的對象化活動。馬克思明確指出,一旦以第二種尺度為立腳點,廢除工業(yè)目前的存在形式、把工業(yè)從買賣利益的羈絆中解放出來的時候就到來了,憑借工業(yè)這種“感性活動”創(chuàng)造的力量,就能真正揚棄資產(chǎn)階級私有制,為人類的全面發(fā)展奠定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這些觀點到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最終被確立為科學的實踐觀,成為馬克思哲學革命的邏輯起點。
通過上述梳理,以及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具有兩個特征。第一,它絕不是單純哲學演繹的結果,而是奠基于現(xiàn)代工業(yè)生產(chǎn)之上。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物質(zhì)生產(chǎn)活動只不過是對自然材料的選擇和加工,而人類主體只不過是這個過程的被動客體,這注定了當時的人們不可能從感性活動的角度來理解客觀世界,而只會將其視為單純的客體和感性對象。這正是法國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不理解實踐本質(zhì)的原因所在。而在現(xiàn)代工業(yè)生產(chǎn)中,自然界已經(jīng)成為人類支配的對象,人們周圍的感性世界已經(jīng)不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yè)和社會狀況的產(chǎn)物,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10](P76)。馬克思看到,人類實踐絕不是一種被動的消極活動,而是一種變革世界的、能動的、革命的批判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恰恰是對現(xiàn)代工業(yè)生產(chǎn)的哲學提煉,是對社會歷史生活總體的科學概括。[11](P359)第二,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絕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學范疇,而是始終與具體的社會關系聯(lián)系在一起。正是這種客觀的、現(xiàn)實的歷史規(guī)定性,將他的實踐概念同過去的一切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界劃了開來,成為他超越亞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爾的真正偉大之處,更是將其與切什考夫斯基和赫斯的實踐哲學劃清了界限,后兩者實際上只是康德、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雜合物,本質(zhì)上仍是一種唯心主義。
馬克思很快發(fā)現(xiàn),實踐只是一種總體性的規(guī)定,一旦進入真實的歷史,便存在一種最基本的活動,即物質(zhì)生產(chǎn),于是馬克思在邏輯上實現(xiàn)了由實踐的總體規(guī)定向物質(zhì)生產(chǎn)的具體轉(zhuǎn)變,這主要體現(xiàn)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之中。那么,為什么說物質(zhì)生產(chǎn)是最基礎的實踐活動呢?首先,它是人區(qū)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其次,它是一切人類得以存在的根基;再次,它是一切歷史得以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2](P56)。在馬克思看來,物質(zhì)生產(chǎn)包括兩個方面的內(nèi)涵。一是物質(zhì)資料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過程,是人改造自然的活動,它構成了人類生存發(fā)展的永恒基礎。從這一過程中,馬克思引出了“生產(chǎn)力”的重要規(guī)定,它是指人對自然關系的歷史實踐力量,“表示著人對自然力的控制、駕馭和調(diào)節(jié)能力,所以,單就生產(chǎn)力本身來說,代表了人的利益,具有人類學的意義,是衡量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準”[13]。二是社會關系的生產(chǎn),人們在進行物質(zhì)生產(chǎn)的同時,也生產(chǎn)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馬克思從中引出了交往關系和生產(chǎn)關系范疇。以此來看,物質(zhì)生產(chǎn)過程不僅是物的生產(chǎn)過程,而且也是社會關系的生產(chǎn)過程,二者共同構成了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由此出發(fā),馬克思建立了一種全新的實踐觀和歷史觀,實現(xiàn)了對西方實踐哲學傳統(tǒng)的根本變革,這主要體現(xiàn)在四個方面。
第一,實現(xiàn)了對實踐概念的歷史唯物主義改造。亞里士多德和康德將真正的實踐理解為單純的倫理行為,黑格爾則將其理解為實現(xiàn)主客體統(tǒng)一的精神活動,而費爾巴哈則把它理解為骯臟的買賣活動,所有這些都沒有真正理解人類實踐活動的本質(zhì)。馬克思通過對現(xiàn)代工業(yè)生產(chǎn)的研究,將實踐理解為一種改造世界的、能動的物質(zhì)生產(chǎn)活動,揭示了一切個體和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物質(zhì)基礎,實現(xiàn)了對實踐范疇的歷史唯物主義改造,為我們科學認識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奠定了客觀基礎。
第二,實現(xiàn)了實踐與創(chuàng)制的融合。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是一種以自身為目的的倫理活動,而創(chuàng)制則是以他物為目的的外在活動,由此,將后者視為低等活動排除在實踐之外,并將二者對立起來。康德雖然將勞動或物質(zhì)生產(chǎn)納入實踐范疇,但在他看來,這種活動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實踐活動,而只是一種低等的技術實踐,從而將其劃入理論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講,康德并沒有縫合創(chuàng)制與實踐的分裂。在這方面,黑格爾又往前邁進了一步,將勞動和倫理實踐視為絕對精神在不同階段采取的不同形式,有效縫合了二者的分裂,但他的這種縫合是建立在唯心主義之上的。馬克思從人類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出發(fā),將創(chuàng)制標識為人類實踐活動的本質(zhì)規(guī)定,實現(xiàn)了“勞動的實踐化”和“實踐的生產(chǎn)化”[14]轉(zhuǎn)向,縫合了創(chuàng)制與實踐的分裂。
第三,揭示了創(chuàng)制與自由的內(nèi)在關系。在亞里士多德和康德那里,創(chuàng)制和自由完全分屬于兩個異質(zhì)領域(“實然”和“應然”),他們既沒有揭示二者之間的內(nèi)在關系,又都將創(chuàng)制理解為手段性的低等活動。在這方面,古典經(jīng)濟學開啟了一條縫合這兩個領域的新思路,他們認為,生產(chǎn)勞動與自由并不是兩個對立的領域,而是內(nèi)在聯(lián)系在一起的,隨著前者的不斷發(fā)展,自然會產(chǎn)生一個普遍豐裕的自由社會,由此提出了“自由放任”政策,反對國家干預。而黑格爾則顛覆了上述兩種觀點:一方面,他揭示了勞動在現(xiàn)代主體產(chǎn)生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顛覆了以往貶低勞動的哲學傳統(tǒng);另一方面,他既反對亞里士多德和康德將生產(chǎn)勞動與自由對立起來的做法(自由在生產(chǎn)勞動之外),也反對古典經(jīng)濟學將生產(chǎn)勞動與自由直接等同起來的行為(自由在生產(chǎn)勞動之中)。他指出:“自由并不單純是抽象的否定性的自由,而反倒是一種具體的積極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出,認自由與必然為彼此相互排斥的看法,是如何地錯誤了。無疑地,必然作為必然還不是自由;但是自由以必然為前提,包含必然性在自身內(nèi),作為被揚棄了的東西。”[15](P323)自由既不是與必然性分離的理想狀態(tài),也不是必然性的簡單延續(xù),而是將必然性揚棄在自身之內(nèi)所達到的全新狀態(tài),勞動和實踐就是實現(xiàn)這種狀態(tài)的中介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黑格爾在一定程度上縫合了必然性與自由的缺口,但又不得不承認,這種縫合由于其唯心主義的實踐觀而成為一種虛假的縫合。而馬克思則揚棄了黑格爾的這一缺陷,將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轉(zhuǎn)變,奠基在現(xiàn)實的物質(zhì)生產(chǎn)之上。他指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自然必然性的限制,人類必須要與自然抗爭,才能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于是,勞動被迫降低為一種生產(chǎn)物質(zhì)資料的手段性活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人類物質(zhì)財富獲得了巨大發(fā)展,但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的強制性,使勞動又淪為一種生產(chǎn)剩余價值的雇傭勞動。所有這些都是人類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面臨的人與自然、人與人內(nèi)在矛盾的結果,而物質(zhì)生產(chǎn)又是解決這些矛盾的工具。當財富生產(chǎn)已經(jīng)超越了自然必然性和匱乏的限制時,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降低為工具性存在的時代將會終結,屆時,“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fā)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16](P929),“勞動已經(jīng)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7](P23),“成為吸引人的勞動,成為個人的自我實現(xiàn)”[18](P616)。于是,原來作為手段性活動的勞動,將成為所有人的生活目的,成為人的生命的本質(zhì)體現(xiàn)。以此來看,馬克思基于科學的實踐觀,系統(tǒng)揭示了物質(zhì)生產(chǎn)與自由的內(nèi)在關系,詮釋了作為手段的勞動與作為目的的勞動的辯證法,實現(xiàn)了對西方實踐哲學傳統(tǒng)的變革。
第四,真正解決了創(chuàng)制、政治倫理實踐和理論的關系問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三者是分割開來的。康德將創(chuàng)制納入理論,視其為理論哲學的延續(xù),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理論與創(chuàng)制的分割,但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康德仍然堅守亞里士多德的二元分裂。黑格爾則以絕對精神為基礎,將它們分別視為理念發(fā)展的不同環(huán)節(jié),打破了三者的人為分裂,實現(xiàn)了三者的大一統(tǒng),并提出了“實踐包含并高于理論”的命題,積極推進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然而,在他那里,這種統(tǒng)一的基礎卻是非法的。而馬克思則在科學實踐觀的基礎上,真正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實現(xiàn)了三者的辯證統(tǒng)一。他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chǎn)中發(fā)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力的一定發(fā)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chǎn)關系。這些生產(chǎn)關系的總和構成了社會經(jīng)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xiàn)實基礎。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9](P412)因此,作為物質(zhì)生產(chǎn)的創(chuàng)制活動從根基上決定了政治活動和上層建筑(包括法律、道德、哲學等意識形態(tài)體系)的性質(zhì)和方式,并影響著亞里士多德和康德意義上的理論即自然科學活動,從而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將三者有機地統(tǒng)一了起來,實現(xiàn)了對以往哲學觀的歷史變革。另一方面,康德只是簡單地將創(chuàng)制活動視為理論(自然科學)的具體運用,完全忽視了前者的獨立價值和社會歷史意義。而馬克思則將它從理論的牢籠中解脫出來,賦予其獨特的歷史地位,同時又克服了亞里士多德將二者對立起來的做法,充分揭示了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首先,自然科學是人類物質(zhì)實踐活動的歷史產(chǎn)物。“如果沒有工業(yè)和商業(yè),哪里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于工業(yè)和商業(yè),由于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10](P77)在這里,馬克思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重新確立了實踐對理論的優(yōu)先性。“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xiàn)實性和力量”[10](P55),“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10](P56)。其次,自然科學也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物質(zhì)生產(chǎn)的發(fā)展。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現(xiàn)實財富的創(chuàng)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nèi)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chǎn)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而是取決于科學的一般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這種科學在生產(chǎn)上的應用”[19](P100)。后者的不斷發(fā)展將為人類沖破資本的限制,最終實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奠定巨大的生產(chǎn)力基礎。
總之,從亞里士多德提出人類活動的三重劃分開始,經(jīng)過了兩千多年的發(fā)展,最終由馬克思科學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后來毛澤東在馬克思觀點的基礎上,又將這三種活動統(tǒng)稱為“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即物質(zhì)生產(chǎn)實踐、階級斗爭實踐和科學文化實踐[20](P282 -283),最終在實踐的名稱下實現(xiàn)了三者的大一統(tǒng),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的實踐概念。
[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2](德)伊曼努爾·康德.判斷力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3](德)伊曼努爾·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4](德)格奧爾格·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上)[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5](德)格奧爾格·黑格爾.邏輯學(下)[M].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6](德)格奧爾格·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7]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列寧.哲學筆記[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9](德)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M].榮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張一兵.回到馬克思[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3]孫伯鍨,張一兵,陳勝云.從“實踐”轉(zhuǎn)向“物質(zhì)生產(chǎn)”的邏輯過渡[J].江蘇社會科學,1997,(1).
[14]徐長福.勞動的實踐化與實踐的生產(chǎn)化——從亞里士多德傳統(tǒng)解讀馬克思的實踐概念[J].學術研究,2003,(11).
[15](德)格奧爾格·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0]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