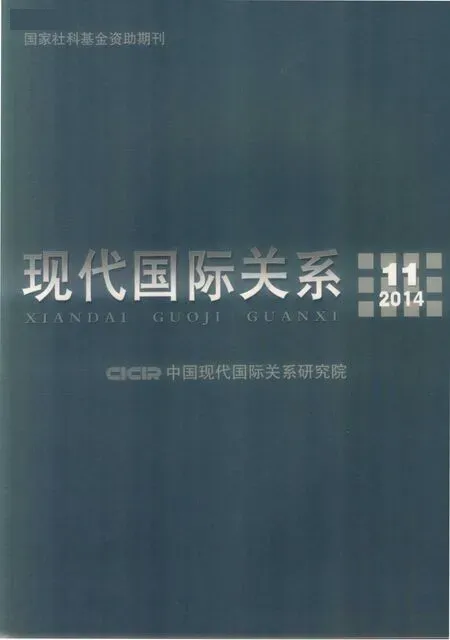中國新一輪改革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袁 鵬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新一輪改革的號角,其意義堪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的第一次改革開放相比。中國的第一次改革開放不僅創造出經濟超高速發展的“中國奇跡”,而且也推動中美關系“超出想象的”大發展。那么,中國新一輪改革與新時期中美關系是將延續以往“同步發展”的正相關關系,還是會出現某種新變化甚或是具有顛覆性意義的大轉折?這是決定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乃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性問題。
一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設定了“兩個百年”的戰略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描繪了“第一個百年”所應實現的分目標及300多項具體改革任務,這些任務或目標匯聚成一句話,就是習近平主席反復強調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既然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不是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①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求是》,2014年,第1期,第1頁。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一句話,這將是一場全局性、全面性、根本性的改革,不是小改,而是大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內外不少人士將此次改革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的第一次改革開放相提并論,稱之為中國的“二次改革”。②參見:“本輪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訪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經濟參考報》,2014年9月23日;David Shambaugh,“China at the Crossroads: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October 1,2014,http://www.brookings.edu/~ /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4/10/01/20%china20%crossroads.html(上網時間:2014年10月20日);另,《經濟學人》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召開的2014年中國峰會主題即是“中國,二次改革”。
中國推進新一輪改革的范圍和領域之廣,改革決心和改革力度之大,從近期陸續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等組織機構設置中,從中央以空前力度鐵腕反腐從而為深化改革掃清障礙中,以及從新領導集體積極進取、全面布局新時期對外戰略中,均可見一斑。
新一輪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其階段性或核心目標則是“十八大”確立的“第一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屈指一算,從現在起到“第一個百年”的2020(或2021)年,只剩下六七年時間。要在六七年時間內落實全面深化改革的300多項任務,建成惠及13億多中國人的較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會,談何容易!且不論國內各種利益藩籬的牽絆,新一輪改革要獲得成功,必須以“四個繼續保持”為前提。
一是繼續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曾使中國經濟保持30多年年均10%左右的超高速增長,這被稱為“中國奇跡”。未來中國繼續保持超高速增長看來“做不到、受不了、沒必要”,因此中央提出換擋回落、保持7%-8%左右中高速增長的新目標,并以所謂“新常態”概括之。“新常態”的積極意義在于,將推動中國經濟優化結構,倒逼中國經濟尋找新動力,從而實現中國經濟全面轉型升級。但毫無疑問,“新常態”之下的中國經濟也將同時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和不確定風險,尤其是將面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疊加”的挑戰。如何在底線思維即“憂患心”和戰略思維即“平常心”中保持平衡,①相關觀點主要源于《人民日報》2014年8月5日、6日、7日連載的三論中國經濟“新常態”文章:“經濟形勢閃耀新亮點”、“經濟運行呈現新特征”和“經濟發展邁入新階段”;另,關于中國經濟“新常態”,還可參閱《人民日報》經濟周刊“新常態,平常心”之系列報道,分別是2014年8月4日“新常態,新在哪”、8月11日“新常態,辯證看”、8月18日“新常態,新應對”。繼續保持經濟穩中有進,是關系中國新一輪改革成敗的重大考驗。
二是繼續保持政治社會基本穩定。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一條,是在保持經濟超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保持了政治社會總體穩定。中國不僅避免了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蘇聯解體的歷史悲劇,而且也成功應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同樣階段政局動蕩的難題,各式各樣的“中國崩潰論”、“中國改造論”不攻自破,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迸發新的活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等“三個自信”應運而生。但在中國新一輪改革的新階段,一系列新問題、新矛盾愈發復雜難解,誠如有學者所概括的,公共需求的日益多樣化與政府組織的有限容量之間的矛盾、經濟高速發展與改革目標全面性之間的矛盾、威脅國家安全穩定的因素越來越多與責任主體的相對單一之間的矛盾,等等,②參見鄭言、李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2期。日益突出,全面沖擊著中國的政治、社會穩定。以“東突”暴力恐怖主義為標志的新安全威脅,以互聯網為平臺的新輿論環境,以群體性事件為特征的新民眾訴求,等等,全面考驗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維穩能力。
三是繼續保持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社會活力,都必須落實到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來”。③鄭必堅:“鄧小平打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新戰略道路”,《人民日報》,2014年8月21日。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引下,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迅速進入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廣大人民群眾實現了溫飽,進入了小康,這正是中國政治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然而,經濟總量世界第二與人均GDP排名90多位以后之間的落差,區域、城鄉、貧富之間日益累積起來的差距,民眾對“中國夢”的美好預期與客觀現實之間的差距,等等,使得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如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更高層次的——包括物質的、環境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追求,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四是繼續保持國際與周邊環境總體穩定。中國的“第一次改革開放”以實現中美關系的正常化開局、以塑造和平穩定的國際與周邊環境為條件、以對外開放以及學習一切有益于現代化的成功經驗為取向。面對國際與周邊局勢復雜多變,中國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設、全心全意謀發展,始終堅持韜光養晦、斗而不破等基本原則,始終把握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善于抓住并運籌各種戰略機遇,終于使中國和平發展爬坡過坎兒達到新的高點,中國也由此步入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央和國際政治舞臺的前沿。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實力地位的提高與戰略利益的擴展,中國面臨的國際與周邊形勢從未像今天這么復雜,內外兩個大局也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纏繞。中美博弈日益加劇,中日僵局一時難解,中越、中菲爭端此伏彼起,國際安全問題熱點頻發,加之國際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和國際能源形勢的不穩定性,均考驗新時期中國的戰略智慧、戰略意志、戰略能力與戰略定力。
上述“四個前提”交互影響、系統聯動,而對于領導新一輪改革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還將長期面臨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外部環境等“四大考驗”。“四個前提”加上“四大考驗”,足見中國新一輪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如果說其中多數方面主要取決于中國自己的主動作為和積極進取,那么能否繼續保持和平穩定的國際與周邊環境,則主動權不完全操之在我,顯得尤為關鍵。而在其中,惟有中美關系不僅能夠全方位影響中國的外部環境,也能實質性影響中國的內部發展,因而尤需高度重視和精心維護。
二
回顧歷史可知,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與中美關系的正常化可謂相輔相成、互為因果。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吹響了新時期改革開放的號角;三天后,12月16日(華盛頓時間15日),中美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兩天后,也即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后十天,1979年1月1日,中美對外正式宣布建交;四周后,也即1月29日至2月5日,鄧小平歷史性訪美。中美關系正常化與中國改革開放啟動在時間上的高度契合絕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內在邏輯性和歷史必然性。誠如有學者所言,“鄧小平是將處理對美關系同中國選擇現代化模式結合在一起思考的,它將建立穩定和積極的中美關系視為中國實現富強的首要外部條件,改革開放與中美戰略關系是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①牛軍:“‘聯盟與戰爭’:冷戰時期的中國戰略決策及其后果”,《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6期,第88頁。可以說,沒有中美關系的正常化,就沒有中國全方位的改革開放;而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面啟動,中美關系的正常化也難以順利地展開。這種良性互動形成了一種極其特殊的結果,即中美關系不僅全面影響中國國際與周邊戰略環境,而且深刻影響中國國內經濟政治社會狀況以及發展進程。
自此以后的35年,中國改革開放日益深入,中國和平發展成就斐然。2013年,中國經濟總量比1978年擴大了25倍,占全球GDP的份額擴大了4倍(從不足3%躍升至12%),②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13.并連續超越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躍居世界第二;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制造業產值、外匯儲備、鋼、煤、水泥、棉布等20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國科技進步有目共睹,軍事現代化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更加引以為傲的是,中國擺脫百年來積貧積弱的面貌,從1980年全球最貧窮的30個國家之一到2013年進入世界中等收入國家行列。③Nicholas R.Lardy,Markets Over Mao: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September 2014,p.1.按照國際貧困標準,從1978年到2010年,中國共減少6.6億貧困人口,開創了人類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④“人類減貧史上的偉大實踐”,《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7日。一句話,中國實現了初步的崛起。
與此同時,中美關系也保持“波浪式前進”的總趨勢,取得了“超乎想象的”大發展。經濟上,中美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24.5億美元發展到2013年的5210億美元,這一數字幾乎接近中國與歐盟28個國家貿易額的總和,超過中國與東盟10國貿易總量,更是中俄貿易額的6倍。⑤1976年美國對華貿易總額為3.36億美元,是美國對臺貿易的1/10。參見[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29頁。中美兩國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并已連續10年成為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兩國雙向投資也超過1000億美元。由此,兩國經貿關系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賴格局。政治上,兩國對話溝通管道日趨完備,包括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等在內的90多個對話與合作機制,其數量之多、所涉及領域之寬,在當今國際關系中實屬罕見。社會文化上,兩國已建立起41對友好省州和201對友好城市關系,每年互派留學生達10萬人,每天超過1萬人往返于兩國之間,100所孔子學院遍布美國。戰略安全上,從朝核、伊核問題到蘇丹、敘利亞問題,從氣候變化到能源安全,從反恐合作到抗擊埃博拉,從兩軍交往到網絡對話,中美之間保持著全天候密切溝通。
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與中美關系之所以同步啟動且并行發展,最根本一點,是過去35年兩國對彼此戰略的總趨勢是相向而行的。從美國方面看,其對華戰略幾十年未變的一個基本思路或邏輯是: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以體系的力量約束或規范中國的發展方向,進而塑造、改變中國或中國自我改變的環境。中國對美戰略幾十年堅持的一個大方向,也是在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在參與、融入改革既有國際體系而不是打破這一體系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擴展自身利益,實現和平崛起。實踐證明,在這樣一種特殊的相向而行的狀態下,中美關系雖沖突摩擦不斷,但總體保持既競爭又合作,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格局。用基辛格的話說,“盡管兩國的出發點迥異,八位美國總統和四代中國領導人在處理微妙的雙邊關系時卻顯示了驚人的連續性。雙方始終盡力維護這一實質性的合作關系,使之不受歷史糾葛和各自國內考慮的干擾。”①[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序,第 VI頁。
但細加考察可知,過去35年美國對中國的“接納”,實際上是有條件、有目的、深謀遠慮的戰略布局。首先,它是在中美實力極不對稱的前提下,美國以一種君臨天下的姿態對國力相對落后的中國的開放,既旨在借中國之力遏制蘇聯擴張,又尋求敲開中國的市場、改變中國的政治,進而將中國吸納進美國主導的“自由市場+自由民主”的西方體系,服務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②這一判斷見諸美國政府歷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例如,即使在發生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美國依然強調,“我們尋求避免將中國與外部世界全部隔絕。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不僅具有全球與地區意義,而且對中國重新走上經濟改革與政治自由化道路十分關鍵”(1990年)。以后美國歷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均重申這一觀點,如,“同中國保持協商和接觸以免加劇其掩蓋鎮壓的孤立狀態將是我們政策的主要特征。中國的變革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我們同中國的聯系必須是持久的”(1991年);“我們正在發展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廣泛的接觸,這種接觸既包含我們的經濟利益又包含我們的戰略利益”(1995年);“中國納入國際法規和準則體系除了將對它與世界其余國家的關系產生影響之外,還將對它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產生影響”(1997年);“讓中國更充分地融入全球貿易體系顯然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1999年)。其次,美國對華戰略從來都是兩手并用。以2005年9月21日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為標志③Robert B.Zoellick,“W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Remerks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Gala Dinner,September 21,2005.,過去35年的美國對華戰略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可稱為“接觸+遏制”(engagement and containment),接觸旨在改變中國,遏制旨在搞垮共產黨政權。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改變論”在這一時期甚囂塵上、此伏彼起,不是偶然的。然而事與愿違,歷史的發展正好走向美國預期的反面。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強勢崛起;中國共產黨不僅未被改造,反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與活力。面對現實,佐利克提出“利益攸關方”論,主張美國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務實面對中國崛起以及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現實,學會跟一個崛起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和平共處。因此,自此之后的美國對華戰略可稱為“融合 +牽制”(integration and hedging)。即,努力將崛起的中國塑造成為美國的“利益攸關方”,變體制外的約束為體制內的整合,并輔之以必不可少的防范和牽制,以求規范中國崛起的速度和方向,使崛起的中國依然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這一時期,形形色色的“中國崛起論”、“中國責任論”、“中國搭便車論”紛紛揚揚,蓋因如此。
從中國方面看,鄧小平以高超的戰略膽識同時啟動改革開放與中美關系正常化,也是在開啟一盤中國現代化的大棋局。一方面,面對蘇聯、越南北南兩線的雙重安全威脅和戰略壓力,盡快推動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改變國際和地區安全環境,符合中國戰略利益;另一方面,拯救瀕于崩潰的國民經濟,全面啟動改革開放,更繞不開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和市場。鄧小平這種“微妙而又大膽的策略”,在他歷史性訪美的行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根據基辛格的描述,“鄧小平訪美是做給別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嚇蘇聯。鄧小平在美國為期一周的訪問既是外交峰會,又是商業訪問,外加巡回政治演說,還有為對越作戰進行心理戰”。①[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357頁。自此之后,中國一直將對美外交置于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經歷了學習美國、防范美國、追趕美國等不同階段,奉行“以兩手對兩手”的策略,既合作又斗爭,既學習又防范,既追趕又自制,較好地保持了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大局,由此才確保中美關系在起伏不定中始終保持螺旋式上升的總體方向。
一句話,過去35年中國改革開放與中美關系幾乎同步發展,總體都是成功的。今天,中國站在下一個35年的新起點,在爭取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段,中美關系還能延續以往的軌跡嗎?新時期的中美關系將何去何從?
三
站在前后兩個35年的歷史交匯點,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發現,中美關系已經或正在出現有別于過去35年、具有一系列新特點的重大甚或根本性變化。
首先,兩國實力對比出現重大變化,大體處于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以來的10余年,美國深陷兩場戰爭、一場危機,經濟低迷、社會動蕩、政治極化相互影響,軟硬實力遭到重創,過半美國人認為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而中國抓住“戰略機遇期”,一心一意謀發展,綜合國力出現重大飛躍。以經濟總量而論,2001年中國 GDP僅為美國的12.8%,2011年則已達到48.5%,2013年超過55.2%,②根據美國商務部給出的統計數據,2013年美國名義GDP總額為16.7997萬億美元,中國為56.8845萬億元人民幣。按照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6.1242∶1換算,中國2013年GDP約合9.2885萬億美元。據此計算,2013年中國GDP規模相當于美國的55.29%。這種追趕速度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的。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到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意味著屆時中國經濟總量即使超越不了美國,也將極大接近美國的規模。這一規劃同國際多個權威機構普遍預測中國GDP超美很可能在2020-2025年之間大體吻合。經濟實力雖只是綜合國力的一個指標,但誠如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史家尼爾·弗格森所言,“一個國家如果首先獲得了經濟實力,然后就會獲得相應的地緣政治實力”。③[美]亨利·基辛格、尼爾·弗格森、法里德·扎卡利亞、[中]李稻葵著,蔣宗強譯:《舌戰中國:21世紀屬于中國嗎?》,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7頁。更重要的是,自19世紀80年代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后,美國再沒有遭遇過一個擁有比自身規模更大的經濟體的潛在戰略競爭。④[美]阿倫·弗里德伯格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新華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3-4頁。事實上,到2012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貿易大國,中國在航空航天等科技能力和軍事現代化方面也都有長足發展。美國戰略界在認識和評估中國時,看到的其實遠不只是經濟崛起,而恰恰是中國有別于前蘇聯的“復合型”實力。⑤有學者研究后發現,“在1960年蘇聯占美國的財富達到大約50%以后,直至蘇聯解體,蘇聯財富達到極限時大致只是美國的一半”,參見:金燦榮、趙遠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條件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3期,第60頁。更重要的是,中美實力對比的拉近與西方世界同新興大國力量對比發生歷史性變遷的國際大勢產生共振,更放大了兩國實力差距縮小的態勢。其結果,中美關系從以往一般意義上的“超”-“強”關系變異為特殊意義的“老大”-“老二”關系,美國對華戰略也由應對“中國崛起”轉向思考如何應對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新時期中美關系中競爭、博弈面明顯增強,且更多地涉及地緣政治、軍事安全、發展模式等深層領域,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兩國戰略態勢出現重大變化,亞太地區愈益成為兩國競合博弈的“戰略場”。從中國方面看,奧巴馬政府正在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是美國全球地緣戰略的一次重大轉向。如果說上世紀末美國的戰略重心在歐洲,新世紀頭10年美國戰略重心在中東,那么,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甚至更長的時期,美國的戰略重心已明確轉向亞太。美國這一戰略轉軌從克林頓執政后期已現端倪,小布什執政之初本欲實施,無奈“9·11事件”突發延滯了這一進程。因此,奧巴馬啟動亞太“再平衡”與其說是在謀劃“后反恐時代”的美國對外戰略新格局,不如說是在承接“后冷戰時代”美國的地緣戰略大棋局。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亞太“再平衡”不是一次簡單的戰術性“再平衡”,而是一次兼顧歷史與現實、涉及內政與外交、連接軍事安全與政治經濟、得到兩黨共同支持的全局性的戰略重心東移。奧巴馬總體外交在美國國內雖頻遭詬病,但美國兩黨及重要戰略界人士幾乎都認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任憑烏克蘭變局和中東亂局的干擾,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大基調似乎不為所動,只是策略手法略為調整而已。美國這一重大戰略轉向雖非全部沖著中國而來,但其力量布局、戰略投入及各種造勢,對中國已經構成軍事、外交、經濟、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全方位挑戰。①關于美國亞太“再平衡”對中國影響的具體內容,可參閱: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編:《中美亞太共處之道——中國、美國與第三方》,時事出版社,2012年。而從美國方面看,中國對外戰略也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近年來,美國有關中國正在放棄“韜光養晦”、對外更加“強勢”、更加突出軍事實力等論調不絕于耳。概而言之,美國認為中國正在有條不紊從陸地走向海洋、邁向太空,從亞洲走向非洲、走進拉美,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經濟與軍事建設并重,凡此對美國的亞太主導地位甚至全球領導地位形成挑戰。在這種認知基礎上,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被認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借釣魚島爭端強化東亞軍事部署,進而逐漸將美國排擠出“第一島鏈”;中國加強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建設則被描繪為另起爐灶,打造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經濟安全體系。②Ashley J.Tellis,“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China”,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2013.總之,在美國看來,如果說美國的全球戰略呈收縮之勢,那么中國的外交則在全面擴張。而事實上,美國所謂“收縮”更多體現在戰略重心轉向亞太,中國所謂“擴張”也僅意味著在亞太地區捍衛主權、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意志更加堅定。這一局面導致的結果,就是中美百年來首次在亞太地區“短兵相接”,展開正面的、全面的博弈,彼此既未做好完全的戰略和心理準備,又缺乏現成的規則和路線圖,能否在亞太地區長期和平共處,成為考驗兩國關系最突出也最緊迫的戰略性課題。
再次,兩國戰略基礎出現重大變化,支撐中美關系的既有戰略基礎逐漸松動,而新的戰略基礎尚未確立。穩定的戰略基礎是中美關系發展的主要條件。20世紀70、80年代,中美關系的戰略基礎是共同對付蘇聯;冷戰后10年,是全球化大潮下的經濟合作;本世紀頭10年,中美關系發展順暢,則得益于經貿合作與反恐合作“雙引擎”。現在,這兩大基礎同時出現松動。一方面,美國雖仍然強調恐怖主義是頭號威脅,但從其全球戰略布局看,從反恐轉向應對新興大國一面愈益凸顯。另一方面,隨著中美雙方同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美經貿關系傳統意義上的互補性在減弱,競爭性在增強。奧巴馬強調“出口倍增”、“制造業回歸”,中國則倡導自主創新、對外投資。對于中美各自經濟發展戰略的新變化如果應對不當,就有可能使經貿關系從中美關系的“壓艙石”變成沖突點或摩擦源。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大規模的對美反向投資潮,如2012年萬達收購AMC娛樂控股公司,2013年雙匯收購史密斯菲爾德公司,2014年中國安邦保險集團收購紐約華爾道夫酒店,乃至2014年阿里巴巴在紐約證交所創造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上市活動,等等,美國既樂見其成,又心態復雜。兩國近年有意嘗試在氣候變化、新能源等領域展開合作,以及在廣泛的地區和全球議題上加強溝通、協調,但這些一時難以成為中美關系的新基礎。舊有基礎松動,新的基礎待建,給中美關系未來發展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
最后,兩國決策環境出現重大變化,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和脆弱性明顯增大。從外部環境看,中美關系越來越被所謂“第三方因素”所干擾甚至“綁架”。近些年中美之間的地緣戰略博弈,多涉及日本、菲律賓、越南、朝鮮、蘇丹、伊朗、緬甸、烏克蘭、俄羅斯,等等,中美與上述國家之間的關系往往引發彼此深度猜疑,而與它們之間的矛盾或過節也往往最終演化為中美之間的戰略摩擦,這是中美關系超越雙邊而越來越具有全球性意義的新特征所決定的,在以往兩國關系史上并不多見。換言之,中美關系如何發展,有時不完全取決于中美自身。從內部環境看,高層決策往往受制于國內利益集團、網絡媒體、民意輿論。美國政治極化與社會保守化趨向愈演愈烈,經濟民族主義與社會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在這種背景下,一向支持中美關系的工商界對華態度也趨于消極。中國國內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等因素對決策的掣肘也成為顯而易見的另類“新常態”。
上述四大變化加在一起,表明中美關系與過去35年已大不相同,曾經成功指引或規范中美關系發展的既有框架(大體包括三個聯合公報及1998、2009、2011年中美之間簽署的三個聯合聲明)已難以完全適應新時期兩國關系的發展。如何迎接這一新變局?兩國戰略界和官方都在思考和探索。其中,美國戰略思想界提出了種種構想,較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大體有三類:一類以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阿什利·特利斯等為代表,主張對華強硬,其中前者以其“進攻性現實主義”一貫的簡單思維,認定中國難以和平崛起,①米氏咄咄逼人地質問:“我們憑什么期望中國會與美國的戰略選擇不同?難道中國的領袖們比美國領袖更有原則?還是他們的道德更高尚?抑或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沒那么嚴重?或根本對國家生存漫不經心?當然不!中國定會效仿美國,試圖成為區域霸權國”。參見:John J.Mearsheimer,“Say Goodbye to Taiwan”,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say-goodbye-taiwan-9931.(上網時間:2014年11月17日)主張美國應聯合盟友提早對華進行戰略圍堵;②John J.Mearsheimer,“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上網時間:2014年11月17日)后者主張美國奉行一種從未嘗試過的“沒有遏制的平衡”,包括“剝奪中國參與全球貿易體系的機會、使中國的鄰國融入到反對北京的一個統一聯盟體系之中、制定反對中國的集體防務戰略,以及發動意識形態攻勢,旨在剝奪中國國家及其政權的合法地位”。③Ashley J.Tellis,“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China”,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2013.一類以前副國務卿斯坦伯格為代表,主張中美加強危機管控,彼此進行“戰略再保證”,確保兩國關系長期穩定。④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一類以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為代表,主張順應時勢,以大胸襟和大手筆展開中美合作,共創未來。前者主張中美雙方“共同進化”,進而共建“太平洋共同體”;⑤[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515-518頁。后者繼提出“中美共治”(G2)論后,近期又倡導中美兩國正式簽署“太平洋憲章”,以此為基礎帶動他國共建世界新秩序。⑥參見:《布熱津斯基:太平洋憲章——大棋局的嬗變》,http://www.guancha.cn/bu-re-jin-si-ji/20141113285884s.shtml.(上網時間:2014年11月15日)以上三類聲音在美國各有市場,迄今仍在爭論中。相較而言,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更多是上述主張的折衷,體現為遏制、規制、接觸、防范、競爭、合作等多方面因素的有機統一,更像是應急性、反應性的政策拼盤,而尚未形成一套有別以往的新的對華戰略框架。個中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國疲于應對經濟復蘇、政治內斗和國際危機,無暇思考長遠對華戰略,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國囿于霸權邏輯,無法擺脫遏制、接觸等慣性思維窠臼,因此也就難以提出符合新時代條件和中美關系新特點的新的對華戰略思想。
相較而言,中國戰略界、學術界對未來中美關系雖也提出過引人注目的新思考,如前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的“中美利益和利害共同體論”、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的“中美兩超論”、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的“西進論”等等,但總體看,均尚未形成對中美關系未來發展較成體系的新論述。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12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提出構建“前無古人,但后啟來者”的中美新型合作伙伴關系倡議,⑦參見:2012年2月24日習近平副主席訪美期間在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午餐演講。“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Biden and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Luncheon Benjamin Franklin Room”,State Department,February 14,2012.令人眼前一亮。這一思想隨后在一系列場合被反復提及,最終形成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基本輪廓。關于其從提出到逐漸豐富的過程,已有學者作過細致研究,⑧可參見:倪世雄:“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推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載黃平、倪峰主編:《美國問題研究報告(2013)》,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9-11頁。在此不擬贅述。值得關注的是,美方對“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提法的認識,大體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12年習近平副主席提出到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召開,美方總體反應冷淡或不積極,盡管期間舉行的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主題即采用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提法,但仍未能充分調動起美方的熱情。唯一例外是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該概念提出后一個月即作出了積極回應,⑨希拉里·克林頓2012年3月7日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發表的紀念尼克松訪華40周年的講話中談到,要為“老問題”尋找“新答案”,被普遍視為是對習近平提出“新型大國關系”的積極回應。參見: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m.但并未直接提及該概念。第二階段,從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到2013年底,美方開始全面重視并態度積極。一方面是因為“十八大”報告正式采用了這一提法,另一方面則因為美國意識到這可能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對新時期中美關系的戰略謀劃。這一年,先有即將卸任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3月在美國亞洲協會演講中全面闡述美方態度,并首次公開使用“中美新型關系”提法①Thomas Donil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Remarks delivered at Asia Society New York on March 11,2013,http://asiasociety.org/new-york/complete-transcript-thomas-donilon-asia-society-new-york,(上網時間:2014年11月17日),再有6月習奧“莊園會晤”就此達成初步共識,最后是11月新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在喬治城大學首次闡釋其亞洲政策時,明確表示要尋求踐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operationalize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②Susan E.Rice,“America’s Future in Asia”,Remark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Washington,D.C.,November 20,2013.第三階段,從2013年12月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到2014年11月北京APEC會議,美方態度趨于消極。既因為美方對中國劃設防空識別區的強力反彈,也因為中美圍繞美表示將助日協防釣魚島問題上的緊張對立。但這一階段,美國智庫、學界反而掀起了單獨或者與中方聯合研究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新高潮。③這一時期,美國主要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和平研究所、大西洋理事會、美國進步中心等都開展了相關研究。第四階段,從2014年11月北京“習奧會”拉開帷幕,美方態度轉趨積極、理性、務實。經過過去兩年多的觀察、研究、磨合,中美雙方終于在新的起點上重新思考如何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習近平主席強調,要以“積水成淵、積土成山”的精神,不斷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奧巴馬總統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共同為此作出努力”。④“習近平同奧巴馬在中南海會晤”,《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2日。至此,中美高層就新時期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再次“對表”,為下階段務實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指明了方向。
四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從2013年6月“莊園會晤”到2014年11月中南海“瀛臺會晤”,在中美關系復雜變異的大背景下,中美兩國元首最終就“在務實合作與管控分歧的基礎上推動新型大國關系建設持續取得實質性進展”方面達成重要共識。⑤“中美元首北京會晤主要共識和成果”,新華社,北京2014年11月12日電。這一成果著實來之不易。與此同時,包括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多尼隆、哈德利等多位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內的美國戰略界人士,也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理念更加認同,給予很高評價并寄予期望。⑥如基辛格表示,“我相信中國和美國有機會建立一種新型大國關系。這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而是現代技術發展的必然需要,也是我們共同面對諸多問題的客觀要求。”參見:“中美關系或迎來新的‘分水嶺’——專訪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參考消息》,2014年11月10日。另見:Thomas E.Donilon,“Keynote Address:Obama in China:Preserving the Rebalance”,November 5,2014,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14/11/05-obama-in-chinapreserving-rebalance.(上網時間:2014年11月12日)接下來,誠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我們不能讓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滿足于早期收獲,還要繼續往前走”。⑦“習近平同奧巴馬在中南海會晤”,《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2日。這條前無古人的道路如何繼續往前走呢?
首先,它需要兩國領導人始終高瞻遠矚,持之以恒,加強引領。回顧過去35年中美關系所走過的路,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把握大勢和大局,控制枝節和末流。迄今為止,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與其說是一張現成的路線圖,不如說是一個目標、一種愿景,是用以規范兩國關系新階段發展方向的一種精神原則,是中國新領導集體對新時期中美關系的新思考、新期許和新承諾。對于中美兩國目前存在的將其庸俗化、狹隘化的趨向,唯有通過高層的引領才能正本清源,保持航向。這就要求兩國在任何時候都“不為一事所惑,不為一言所擾”;⑧習近平:“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在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的致辭”,《人民日報》,2014年7月10日。“一時的感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養一種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仍能持續的行為模式的能力”。⑨[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517頁。這考驗兩國高層能否在錯綜復雜的局勢中和風云變幻的環境下,保持戰略定力,擁有寬大胸襟,加大戰略投入,發揮引領作用。對于深受國內政治環境變動的奧巴馬政府而言,尤其如此。
其次,它需要兩國戰略界、理論界、學術界群策群力,加強合作,為“新型大國關系”這座大廈提供理論支撐,增添豐富內涵。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同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是一脈相承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能否走得通和平發展道路。現有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對此顯然缺乏足夠的解析力,而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上尚在形塑過程中,這其實為從理論上探討“新型大國關系”提供了絕好的契機。中美兼具經濟相互依賴、核與金融恐怖平衡、多元一體民族的相近性、無主權領土爭端、都有大國抱負和“例外論”情結等特質,有數百年大國崛起的悲劇作教訓,也有35年中美關系發展的成功經驗作借鑒,更有全球化、多極化、信息化等新時代條件作背景,如何從學理層面將其歸納提煉,轉化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理論基礎,有賴于中美兩國學界沉下心來精誠合作。畢竟,“一個巴掌拍不響”,共同的事業需要共同的責任和擔當。
第三,它需要兩國具體的實踐去檢驗和修正,從而實現從理論到實踐再到理論的良性循環。經過多輪互動和兩度“習奧會”,中美在“新型大國關系”上取得的一個重大進展,就是不再拘泥于這一概念本身,甚至不太在意是否一定用這個提法,而更注重把握其避免沖突、發展合作的精神實質,都希望通過實實在在的合作去體現“新型大國關系”之“新意”所在。2014年11月奧巴馬訪華期間兩國共同發表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以及兩國國防部簽署關于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的諒解備忘錄和關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的諒解備忘錄等,就是解放思想、以實際行動踐行“新型大國關系”的有益嘗試。展望未來,通過共建亞太自貿區(FTAAP)從而破解TPP與RCEP平行推進的難題,進而構建中美利益共同體;①相關方面的最新成果,參見 C.Fred Bergsten,Gary Clyde Hufbauer,Sean Miner,“Bridging the Pacific:Toward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October 2014.通過搭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構”從而打破亞太兩套不同安全機制之間的障礙,進而構建中美安全共同體;②相關方面的最新成果,參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課題組:“太平洋足夠寬廣——關于構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構’的思考”,《現代國際關系》,2014年,第10期,第1-9頁。通過加強應對埃博拉、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的合作從而沖淡兩國地緣戰略博弈,進而構建中美責任共同體,都是大有可為的方面和方向。
第四,它需要兩國更加主動地塑造內外環境,從而為“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掃清不必要的障礙。從內部看,中美兩國在未來幾年都面臨深化改革的重任,如何培育健康、健全的民族心態,善于相互學習與借鑒對方,而不是簡單夸大威脅、有意渲染矛盾,從而使中美關系為各自的國內發展服務,造福兩國人民,是必須盡快提上日程的大事。近期雙方在旅游和商務簽證問題上的合作,就是非常有前瞻性和建設性的舉措;從外部看,若干“第三方”因素將繼續從不同角度影響中美關系的發展,如何擺脫冷戰思維的干擾,用合作共贏的精神和開放包容的姿態建構“中美+X”的新型三邊合作框架,是未來值得大力嘗試的外交方向。
最后,它需要兩國加深理解彼此的發展道路和歷史文化。在“瀛臺會晤”期間,奧巴馬總統表示,經過深入交談,“進一步加深了我對中國的情況以及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執政理念的了解。我更加理解中國人民為何珍惜國家統一和穩定”。③“習近平同奧巴馬在中南海會晤”,《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2日。這種認識,對于未來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設實在難能可貴。這正是真正做到“相互尊重”的前提。如何創新文明對話及人文交流的方式方法,加深兩國執政者與民眾之間的相互理解,是一項必須堅持不懈的工作。
總之,歷史的演進將中國新一輪改革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再次聯系起來。較之過去35年,新時期的改革任務更艱巨,難度也更大;新時期的中美關系更復雜,也更脆弱。但未來似乎在召喚:中國新一輪改革勢在必行,志在必得;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也是中美關系繼續前進的唯一選擇,舍此別無他途。④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基辛格寫道:“新型大國關系是規避歷史上大國競爭悲劇的唯一道路”。參見: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Penguin Press,2014,p.367.也正因此,我們相信,中國新一輪改革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構建,將再次創造中國崛起與中美關系又一個35年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