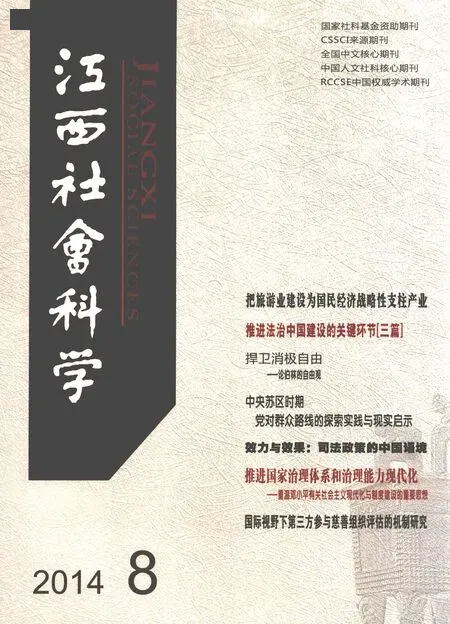強制性追隨:內涵與本質
■曹元坤 祝振兵
一、引言
正如Avolio 等所言,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領導力的研究成了組織行為學研究中的“香餑餑”,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1]。而在這些關于領導力的文獻中,研究者更青睞于建設性的、有效的領導者行為,構建了一個又一個“建設性的”、“積極的”和“正面的”領導模型,如魅力型領導、變革型領導、愿景式領導、真實型領導等。領導與追隨是一對共生的概念,有領導者必然有追隨者(追隨者是指那些不具備其上級權利、權威或影響力的下級[2],所以本文中追隨者和下屬、員工同義;領導與上司、主管同義)[3]。與“建設性的”領導者相對應,絕大多數與追隨者有關的文獻關注的是“積極的”、“主動的”追隨和積極的情緒體驗。比如,魅力型領導風格有利于激勵員工的創新性行為[4];變革性領導對追隨者的積極情緒和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5];愿景式領導對于追隨者的工作積極性、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6]。
但現實生活中,追隨者的行為并非都是積極的,還存在一些相反的現象。比如,在網上所公開報道的“三聚氰胺毒奶粉”、“染色饅頭”等令人發指的事件中,我們很難相信那些一線員工都是心甘情愿地接收此類指令并從事這些敗德行為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被迫的,所以才有個別員工因為實在無法忍受良知的煎熬,冒風險“曝光染色饅頭潛規則”。此外,Zapf 等所做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工作場所中,有約5%~10%的員工經常遭受上司的恐嚇、威逼等辱虐對待[7]。我們很難說在上司的高壓、辱虐之下,員工的追隨行為也都是積極的、主動的,而不是被強制的、非自愿的。所以,只關心追隨者的積極、主動的行為對于全面理解追隨是有失偏頗的,要把握追隨的真諦,也應該關注追隨者的非自愿性行為。可喜的是,最近已有部分研究者在這一方面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比如Vigoda-Gadot 對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進行了反思,認為工作場合中的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并不總是自發的、主動的,有時也是被迫的,并據此提出了強制性公民行為(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的概念[8][9]。但強制性公民行為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和發展的方面,如,其研究的目的只是試圖對組織公民行為概念進行拓展,強制性公民行為所涉及的只是對組織有益的角色外行為(比如幫助他人),而沒有關注到角色內行為(如領導明確要求的行為)等。本文在這些現象和已有文獻的基礎上,試圖對員工的強制性行為做進一步的探索。一是探索性地提出強制性追隨的概念;二是辨析和比較強制性追隨與強制性公民行為、服從、強制性說服理論、從眾和被動追隨等概念的區別與聯系;三是對強制性追隨理論未來的研究進行展望。
二、強制性追隨概念的提出
嚴格來講,強制性追隨的思想并非我們的首創,此前一些文獻中已存在零星的論述,只是尚未有學者進行深入、系統、明確的闡述和研究。如Kelley 特別關注追隨者的自愿依從。為了更好地說明這種自愿的依從,Kelley從“獨立思考程度”和“主動程度”兩個維度將追隨者劃分為五類,即疏離型追隨者、模范型追隨者、守舊型追隨者、被動型追隨者、實用型追隨者。模范型追隨者和守舊型追隨者屬于自愿的追隨者,疏離型追隨者和被動型追隨者屬于非自愿的追隨者,這些非自愿追隨者無疑依賴于領導的監督或強制。Kellerman 也意識到了這種強制性追隨的存在,并在其影響至廣的《追隨力》一書中簡短地表達了這種思想:“一般情況下,追隨者可能會為了追求安全感、為了尋求歸屬感的群體或者為了找到歸屬或意義而自愿去追隨領導者;但有時候追隨者的順從并非是自愿的,有時候,領導者迫使他們這么做。”[2]從詞源上講,根據《現代漢語辭海》和《韋伯斯特詞典》的解釋,“追隨”可理解為跟隨或接受權威指導指令而行動的行為[10]。所以就追隨這一行為來講,可以是個體自愿實施這一行為,當然行為主體的這一行為也可以是被迫的,如員工被迫加班。
上述學者在一定意義上都觸及了強制性追隨的思想,但并沒有由此進行專門的探索,更沒有進行明確的定義。基于以上有關論述(尤其是Kelley 的自愿依從的思想),我們嘗試給強制性追隨下一個初步的定義:“強制性追隨(Compulsory Following)是指在領導者非正當的直接或間接要求下,追隨者被迫表現出的一種角色內行為。”為了進一步澄清強制性追隨的概念,需特別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非自發性
非自發性是指個體行為的實施是來自領導者指令,即非自發行為。一方面,就指令的發出主體而言,這種指令的發出者是能夠直接干預追隨者工作的領導者,其領導身份是組織正式認可的,而非基于其他身份的個體,如基于“專家身份”發出指令的個體等;另一方面,就指令的表達方式而言,這種指令可以是領導直接明確表達的,也可以用間接暗示或授意的方式表達,當然,這種暗示或授意必須能夠被員工感知到。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可能通過授意或暗示的方式發出指令的情況并不少見,如,網上曝光的領導授意員工做假賬,授意員工偽造病歷等可能皆屬此列(這些事可能會讓員工面臨極大的法律和道德風險,往往不是他們自發的)。
(二)非正當性
指令非正當性是指員工感知到領導者的指令是非正當性指令。指令是否正當的判定是基于追隨者的一種主觀認識,當領導者的指令與追隨者的行為準則(價值觀、信念等)相抵觸時,追隨者就會體驗到這種指令的非正當性。這種主觀性具體可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于同一個指令,由于不同追隨者所持有的價值、信念等標準的不同,追隨者之間對指令是否正當的感受可能不同。“主動型追隨者”對于領導的指令的正當性會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如果感覺正當就努力執行,否則不去執行甚至掀其下馬[2];其二,對于不同的指令,甚至相互抵觸的指令,同一追隨者對其是否正當的感受也可能會相同,如“頑固型追隨者”可能對領導的任何指令都認為是正當的。
(三)非自愿性
非自愿性是指個體實施行為是與自己的意愿相違背的,被強迫做的。行為的非自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追隨者所處的環境無法讓其對行為進行自由選擇,或者說要自由選擇就需付出極大代價。例如,有些企業為了獲取高額利潤,不擇手段,要求員工非法操作(如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員工由于擔心自己被辭退,即使不情愿也可能會按指令行事,因為被辭退可能會導致全家衣食堪憂。其二,當個體實施這些行為時往往會體驗到不安、焦慮等內心沖突。如,前文所提及的一線員工因為體驗到饅頭染色行為與其道德良心的巨大沖突,而主動揭發行業黑幕事件。
(四)角色內行為
員工的角色內行為(In-role)和角色外行為(Extrarole)是組織行為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也是備受爭議的焦點。那么,何為角色內行為,何為角色外行為呢?Van Dyne 等對于兩者的劃分提出了一個標準,他們認為角色外行為有三個特征:其一,沒有被角色描述提前指定;其二,沒有納入正式的報酬系統;其三,如果不做也不會受到懲罰[11]。反之,那些被要求要做的,與報酬體系聯系(如工資等)在一起的行為屬于角色內行為。Morrison 認為:組織中的角色很少是固定的,對角色的認識是在追隨者和領導者就工作范圍問題的協商中不斷演變的。也就是說,內、外角色是一種主觀建構,具有個體性、主觀性、變化性而非固定性[12]。我們認為,Van Dyne 所指的“角色描述提前指定”和“納入正式報酬體系”的標準,所指的是角色內和角色外行為的客觀穩定性,“會不會受懲罰”是指兩種角色的存在性;而Morrison 所質疑的只是角色內和角色外行為的穩定性,而對于這兩種行為的動態存在性(不做會不會受到懲罰)并沒有否認。所以結合這兩種觀點,強制性追隨中所講的角色內行為滿足兩個條件:其一,領導直接或間接要求的行為;其二,執行可能會受到獎勵,拒不執行會受到懲罰或擔心受到懲罰。
三、與相關概念關系的辨析
為了進一步明確強制性追隨的內涵和本質,我們試圖從“非自發性”、“非正當性”、“非自愿性”和“角色內行為”四個方面,將強制性追隨和與之內涵有交集的幾個概念進行比較,即比較“強制性公民行為”、“服從”、“強制性說服理論”、“從眾”和“被動追隨”與強制性追隨的聯系與區別(見表1),并分析強制性追隨概念的獨立性。

表1 強制性追隨和相關概念的區別與聯系
(一)強制性公民行為
強制性公民行為最早是由Vigoda-Gadot 明確提出的一個與組織公民行為相對立的概念,指的是“員工因感知到來自主體、客體及環境的壓力,而被迫表現出的一種非自發的公民行為”[8]。強制性公民行為最突出的三個特點表現在:追隨者感受到行為的非自發性、角色外行為和對組織的有益性(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有益的,如幫助他人等)。在“非自發性”、“非正當性”維度上,兩者有相似之處,強制性公民行為也是強調在外來的壓力下員工被迫實施的非自發的行為,并且這種感知到的外部要求和內在標準不一致。但與強制性追隨相比,外來壓力的來源可能不同,強制性公民行為在壓力的來源上并不只限于領導的指令,其也可以是組織的氛圍,如組織的加班氛圍。強制性公民行為認為,員工會出于印象管理的需要而從事強制性組織公民行為,即通過奉承、自我推銷、作秀等方式操縱觀眾對于自己所希望展現的形象的認知,比如通過實施強制性公民行為,博得領導好感[13]。此時,員工出于工具性的目的做這些事情,雖然可能認為這些行為指令是非正當的,但仍會自愿去執行。當沒有印象管理的動機時,員工會認為這些行為指令是非正當的,會非自愿去執行。所以,在“角色內行為”維度上,強制性追隨明確定義為一種角色外行為,強制性公民行為存在差異。除表1 所列區別外,兩者不同還體現在行為后果對組織是否有利這方面。強制性公民行為所指的是對組織有益的行為(至少領導者主觀認為是有益的),而強制性追隨所指的行為未必對組織都有益。比如Einarson 等人提出的反組織型(Anti-organization)領導,他們有可能會要求員工做出一些違背組織正當利益的行為(如虛報業績)[14]。所以,強制性追隨還有可能是對組織不利的行為。
(二)服從
社會心理學中有三個詞意思比較接近,即遵從(conformity)、順從(compliance)和服從(obedience)。所謂遵從是指追隨者對群體有強烈的認同感,會內化群體的規范或指令,并借以指導他們的行為。遵從不僅僅是在行為上同指令的要求相一致,而且在思想和態度上與指令也高度統一。順從是為了滿足他人的要求,個體暫時的、表面上的行為和態度的改變,其真實的態度和想法并沒有發生改變。與遵從相比,順從需要外力的監督。比如,在我們忙得不可開交時,有人求助,而礙于面子我們又不好拒絕他人的請求,這時順從就可能會發生。服從是順從的一種形式,兩種都是指行為和真實的態度不一致,但順從是因為對提出請求者的喜歡,或為了博得對方的好感而主動為之;而服從是命令發出者基于權力要求個體去執行(當然這個權力可以是獎賞權也可以是懲罰權,甚至其他,如專家權)。關于服從,比較經典的研究要數耶魯大學教授Milgram 所做的權威服從(Obedience to Authority)實驗。Milgram 通過海報宣傳招募志愿者,佯稱參加學習能力和記憶方法的研究(實則是權威服從研究),并承諾對愿意參與者給予十分誘人的經濟報酬。實驗的目的是檢驗在權威命令的情況下,被試是否會做出違背自己一直所遵守的道德規范的行為。實驗結果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近65%的被試違背了自己的真實態度,服從了權威的要求[15]。所以,服從是指令性行為,因而具有行為發動的非自發性,并且由于追隨者持有的信念和權威的要求不一致,這些指令也是不正當的。但由于這些行為是被明確要求或說明的(如在Milgram 的實驗中,實驗前對被試的工作進行了事前說明),所以這些行為屬于角色內行為。可以看出,在“非自發性”和“非正當性”維度上,服從與強制性追隨相似。但在“非自發性”維度上,由于強制性追隨專指來自于有正式權力的領導,而服從也可以是來自專家等的權威,所以后者外延要更廣泛。在“非自愿性”維度上,服從不一定具有強制性。比如,在Milgram 的實驗中,“被試是完全自愿地服從權威的命令”[15],或者說即使不服從,也不會受到懲罰,被試可以自由選擇隨時退出實驗。在“角色內行為”維度上,由于服從的指令不一定來自于正式的領導,并且如果不執行指令個體也不會受到懲罰,所以其行為可能屬于角色外行為,也可能屬于角色內行為。
(三)強制性說服理論
強制性說服理論(Coercive Persuasion Theory)是社會學、心理學關注較多的一個理論。Ofshe 等將強制性說服視為一種社會影響的手段,通過運用強制的方式(比如,壓力、勸說、權力、人際影響以及基于群體的影響),從而使追隨者產生行為或態度的改變[16]。一般認為,強制性說服包括四個主要階段:依靠強烈的人際和心理沖擊動搖個體原有的自我感,促進服從;同伴群體或領導對個體施加人際壓力;使用人際的壓力促進個體的遵從行為;通過對個人所處的整體社會環境的操縱控制,強化或鞏固新形成的態度或行為[8]。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發現,強制性說服理論雖然也涉及個體的主觀感受,但該理論更關注于運用一系列的步驟策略,使追隨者的行為或態度達到實質性的改變。即從最初的非自發性到自發性,從最初認為行為指令非正當到后來認為正當,從非自愿執行轉變為最后的自愿追隨。強制性追隨和強制性說服理論的交集只是發生在強制性說服理論的第二個階段,并且即使在這一階段,兩者也仍是不完全相同的,如在行為的要求上,強制性說服理論中還包含了同伴施加的壓力,而強制性追隨只是指領導的壓力,并且同伴壓力下的行為并非角色內行為。所以,強制性說服理論和強制性追隨只是“貌合”,兩者實質相去甚遠。
(四)從眾
Asch 曾進行過一系列從眾實驗。在其實驗中,被試被分為若干組,每組均由6 人組成,其中只有1 人為真正的被試,其他都均為偽被試。主試先讓所有人看一根直線,然后又給出3 根直線型,讓被試從中選擇,哪一根與最初看到的直線等長。根據實驗的預先安排,5 名偽被試都會選擇一個相同但錯誤的答案,并且均先于真正的被試給出此答案。最后,真正的被試宣布自己的答案。結果發現,大部分真正的被試都跟隨了群體的選擇,而沒有接受親眼所見的明顯證據[17]。從眾同樣是個體受到了外部的壓力,但從眾行為所關注的只是同等地位成員行為對個體行為的潛在影響,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個體的這種行為具有非自發性,但這種非自發性并非來自于更高地位成員的影響,所以,從眾沒有來自領導的行為指令。從眾研究中,真正的被試是基于“多數人是正確”的原則做出判斷的,因此“非正當性”維度上是否定的。此外,個體是處于一種印象管理的動機實施行為,并且個體即使選擇不從眾也不會受到正式的處罰,所以在“非自愿性”和“角色內行為”維度上也與強制性追隨明顯有別。
(五)被動追隨
如前述,Kelley 依據追隨者的思考能力和主動性兩個維度對追隨者進行了分類,根據其分類模型,被動追隨者的特點為: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同時沒有主動性,其行為需要持續的監督。被動追隨也是領導要求的行為,不執行也要受到懲罰,所以在“非自發性”、“角色內行為”維度上和強制性追隨相似。在“非自愿性”維度上,雖然被動追隨者如果不按照指令行事也會受到懲罰,但追隨者并不是因為害怕懲罰才去行動,而是因為指令給了他行動的方向,沒有指令他們不知道如何行動;而在強制性追隨中,追隨者是由于害怕懲罰而不得不按指令行事。在“非正當性”維度上,由于被動追隨者缺乏思考能力,或者說“腦子是空的”,所以,在被動追隨者中,追隨者沒有評判是否正當的標準,故無所謂是否正當。
上文從四個維度對相關理論進行了比較。但由于這些理論或概念并非都來自于對企業組織行為的研究(比如服從、從眾來源于心理學研究),將這些理論統一在企業組織的框架進行對比,可能在某些維度異同地辨析上會有些牽強(比如服從屬于角色內還是角色外等),但總體來講其區別或聯系是存在的。
四、小結與展望
瑪麗·帕克·福列特指出:“要求下屬無異議地遵從那些未獲認可或理解的命令是一種糟糕的管理方式。”[18]但現實生活中此類強制性追隨事件層出不窮,如“員工被迫加班”、“被迫做假賬”等。基于這種對現實生活的觀察,以及有關文獻的分析,我們嘗試性地提出了強制性追隨的概念——“強制性追隨是指在領導非正當的直接或間接要求下,追隨者被迫表現出的一種角色內行為。本文重點強調了這一行為的“非自發性”、“非正當性”、“非自愿性”和“角色內行為”的性質。此外,我們對強制性追隨和一些相近的概念進行了區分,分析了可能引起強制性追隨的因素,以及強制性追隨可能導致的后果,但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今后進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第一、強制性追隨概念的進一步明確和澄清。雖然我們從理論上闡釋了強制性追隨概念,但我們并不認為這是對強制性追隨內涵最精確無誤的表達,像組織公民行為在研究中內涵不斷清晰的演進歷程一樣[19],強制性追隨概念的進一步明晰和澄清有待今后不同研究者之間進行思想的碰撞。對于強制性追隨是否獨立于其他一些相近概念(包括但不僅限于上文提到的強制性公民行為、服從等),有待于今后對強制性追隨測評工具的開發,并通過實驗和調查的手段,獲取較為客觀的數據以檢驗概念的獨立性。此外,用實證的手段探討強制性追隨的前因和后果變量也是未來極有價值的研究方向。其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澄清強制性追隨的概念邊界,而且是考驗強制性追隨概念獨立性和其存在價值的重要方式。
第二、強制性追隨對組織的意義。本文對于強制性追隨的整個論述是建立在“負面的”、“消極的”基調之上的。那么,強制性追隨一定是不好的嗎?在一個信息驟增、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變革在企業中似乎已成為了常態。而變革就意味著要打破既有的平衡,這必然會遇到技術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等方面的阻力[20],有時還需要強性推進,繼而導致強制性追隨的出現,這種強制性追隨也是消極的嗎?某些強制性追隨對某些個體可能是消極的,但也許對組織的長期成長也具有積極意義。因此,今后研究中對區分導致強制性追隨的指令的性質是有意義的。
第三、關于強制性追隨研究的現實意義。在企業責任正逐漸引起廣泛關注的時代,企業的責任不只是為自身創造短期的經濟利益,更是要實現企業內部的和諧、員工的滿意,甚至對整個社會發展的積極貢獻[21]。對于“被加班”、“被迫造假賣假”等強制性行為的探索,不僅有利于深入了解企業中影響員工身心狀況的因素,而且對于如何實現企業和員工的和諧共生,如何推動企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總之,本文探索性地界定了一個新的概念——強制性追隨。雖然,在概念的建構中存在很多缺憾和不足,但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是對非自愿行為研究的又一次拓展,在一定意義上豐富了組織行為研究的內容。并且,其與現實生活相連,解釋了一些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現象,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1]Avolio B J,Walumbwa F O,Weber T J.Leadership:Current Theories,Research,and Future Direction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9,(60).
[2](美)Kellerman B.追隨力[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3]Vugt M V.Evolutionary Origins of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2006,(4).
[4]Conger J A,Kanungo R N,Meno S T.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Follower Effect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0,(7).
[5]Shin-Guang L,Shu-Cheng S C.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 Task Performance:the Role of Susceptibility to Positive Emotions and Follower Positive Emotions.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12,(28).
[6]Kantabutra S,Avery G C.Follower Effects in the Visionary Leadership Process.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s Research,2006,(5).
[7]Zapf D.Einarsen S E.Hoel H.et al.Empirical findings on Bullying in the Workplace.London:Taylor &Francis,2003.
[8]Vigoda-Gadot E.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Theorizing Some Dark Sides of the Good Soldier Syndrome in Organizations.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06,(1).
[9]Vigoda-Gadot E.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of OCB?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Compulsory Extra-role Behavior in the Workplace.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07,(3).
[10]許晟,曹元坤.“追隨力”三概念探析[J].江西社會科學,2012,(1).
[11]Van Dyne L,Lepine J A.Helping and Voice Extra-role Behaviors:Evidence of Construct and Predictive Valid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1).
[12]Morrison E W.Role Defin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the Importance of the Employee's Perspectiv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2).
[13]彭正龍,趙紅丹.強制性公民行為研究述評[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0,(6).
[14]Einarsen S,Aasland M S and Skogstad A.Destructive Leadership Behaviour:a Definition and Conceptual Model.Leadership quarterly,2007,(3).
[15](美)Milgram S.對權威的服從[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16]Ofshe R J,Singer M T.Attacks on Peripheral Versus Central Elements of Self and the Impact of Thought Reforming Techniques.Cultic Studies Journal,1986,(3).
[17]李維.社會心理學新發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18]瑪麗·帕克·福列特,劉俊生.論命令的發布與服從[J].領導科學,2013,(5).
[19]Organ D W.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It’s Construct Clean-up Time.Human Performance,1997,(2).
[20](美)Ott S,Parkes S J,Simpson R B.組織行為學經典文獻(第三版)[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
[21]Pless N M,Maak T.Responsible Leadership:Pathways to the Futur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