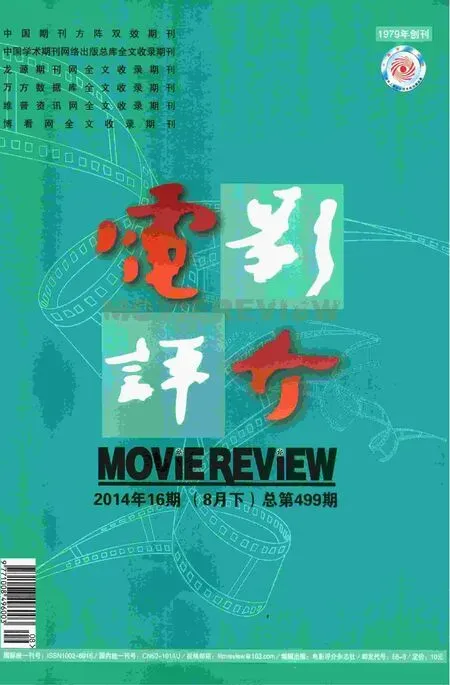從電影的形式和內容談“電影感”
胡 南
從電影的形式和內容談“電影感”
胡 南
一
電影作為一種語言,和音樂、文學等藝術形式一樣,是技巧、風格和美學的結合體。電影感同文學感和音樂感一樣,不僅表現在形式上,也體現在內容中。電影是運動的,是一門時間藝術,又是一門空間藝術。一部有著充沛電影感的電影,必然是時間維度上不失私己化表達,空間層次上又有足夠密度的作品。
電影的語言、音樂、燈光、構圖、攝影機運動、鏡頭的組接等,都是在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上,使畫面獲得一種電影感。時間層面上的電影感,更多地體現在運動上,包括畫面的運動,敘事過程的節奏和戲劇性,因此形成了各種各樣的鏡頭剪輯和敘事觀念。而空間層次上的電影感,使得影像更為立體。最為常見的,是通過畫面轉換來建立空間層次。
二
斯坦利·卡維爾曾指出,因為知道現在同過去不可兼容,同時自己又孤立和脫離于現在;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產生了對攝影尤其是對電影的向往。因為電影能夠提供一種“特殊的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同時感”,這樣的審美感受也僅有電影能夠滿足。[1]讓·米特里也強調了影像的“虛構性”和“主觀性”。因為攝影畢竟經過一定的處理,因而必然包括明顯的主觀性。影像揭示的,是一個被自我感知和主觀表現后的現實,而不是一個原原本本的或者完全超驗的現實,人類賦予影像的美學意義也基于此。[2]讓·米特里表示,電影的主要魅力就是使實在事物變成了非實在事物,或者說被改觀了的虛構事物。也就是說,它一方面似真,一方面似幻。正因為此,影像里具有明顯美學效應的現實要比其原貌更完美。因此,內容層面來講,電影感就是真幻一體。也就是說,真是存在的,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其為真,反之亦然。如果追求的純粹是現實中真的一面,你發現的只能是缺憾和索然,而且變化不居。沒有幻的現實,其實是一種假的真,不存在的真。真幻合一在電影里通常表現為寫實性與抒情性的統一,從而帶來一種更為潛在也更為高級的電影感。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物象層面。作為電影畫面的基本元素,人和物是表現“真幻一體”的電影感的最基本層面。導演在創造審美意象時,首先根植于生活,通過“象”與“意”的相互契合,相伴相生,從而呈現出一種審美的、詩化的情緒。影片《蘇州河》里的美人魚,既是美美的生存狀態的化身,也投射著馬達對牡丹的想念。在喧囂、陰郁的城市背景下,它是一種美麗而又疏離的存在。《那山那人那狗》中翠綠的山與人化的狗,也是父親性格的映照,而父親在風中追逐的信,也將父親對郵政事業的執著詩化。
第二,視聽造型層面。通過視聽元素的巧妙結合,實現寫實性與抒情性的交融,從而既帶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又富有扎實的生活質感。電影《洗澡》中用歌曲《心太軟》暗示老劉的柔弱品質,用澡堂里高歌一曲《我的太陽》來表現東西方文化的融合。《菊花茶》里,馬建新與同事開著機車載著李衛華在鐵路上行進,汽笛聲與人聲交融在一起,并伴以抒情性的音樂。這些視聽造型都充分宣泄了積蓄在男女主人公內心的種種情愫。一部電影要實現觀眾的價值認同,乃至更廣范圍的傳播,離不開在創作中注重非文字符號的運用,尤其是視覺和聽覺符號的表達。高度視聽化的敘事策略才能增強電影的影響力,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強勢”。
第三,敘事層面。好的作品往往既于生活的自然流淌中凸顯生活的“真”,又能在“幻”的潛微滲入后,保持一定的戲劇張力,使影片在對環境、事件和人物的處理上,宛如生活的本來形態又不失觀賞性,給觀眾即真實又夢幻的感受。
電影《洗澡》里,在澡客們的各種沖突中,影片將生活動作轉化為戲劇動作,以增強戲劇效果。同時,澡堂空間本身就有戲劇性,像是一個不斷上演著人生戲劇的大舞臺。姜武飾演的二明,沖人傻笑、與父親賽跑、給胖子澆水,這些莫名其妙的戲,別有一番況味,都是生活與戲劇的融合、真實與夢幻的交織。《陽光燦爛的日子》里,老莫里在開生日宴會,馬小軍為了米蘭與劉憶苦起了沖突。馬小軍打破酒瓶去捅劉憶苦,但鏡頭一轉,碎瓶子竟然復原,暗示他們那天晚上什么事也沒發生。在許多觀眾看來,第二次敘事才是真的,而之前所謂的打斗不過是馬小軍腦海中壯志未遂的豪邁。這種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幻中有實的敘事手法,讓人絲毫不覺得突兀,甚至是沉醉其中。誰不是在現實的逼仄下進退維谷,誰又不是把最隱秘的幻想留在記憶深處。
第三,情節的非線性延展后,形成的某個“特殊時間”層面。托爾斯泰說過,人的真實生命存在于瞬間之中。而虛實相生,真幻交融的電影感也往往存在于某個瞬間。高明的導演就是發現這樣的瞬間。觀眾也只能在這樣的瞬間里才得以發現真實和永恒。后現代主義認為,真實瞬間的存在是曖昧的,堪疑的。但是這種瞬間卻可以被攝影機“直擊”和“破譯”。最為經典的一個例子,應該是安東尼奧尼《夜》的最后七分鐘:你開始看見一些東西,而且也意識到自己正注視著那些東西的存在。漸漸地,我們與時空面對面,無所多余,也無所缺少。同時,它們也回視我們,而我們的存在因它們變得空茫,這一切讓人驚懼,又讓人解脫。在一個個真實的瞬間里,電影表達的可能性剎那間無窮無限。
第四,心理想象填充在真實場景,形成的某個“特殊空間”層面。徐玉蘭和王文娟的《追魚》,作為一部老舊的地方戲曲片,里面卻有著令人想象不到的電影感。有一場戲,張珍跟魚美人去看花燈,在一個巷口里面停下來。此后影片并沒有表現真正的花燈,而只是讓紛紛走過的燈影疊在墻壁上面,影影綽綽,兩人就那么唱起來。這種空間里,你看不到邵氏電影里以往的那種浮華,別有一種似真似幻的風致。《太陽照常升起》里也有類似的場景。陳沖冒雨趕來向黃秋生傾訴衷腸,臨走時,黃秋生愣愣怔怔地走到病房的窗子旁。此時,貼窗的雨水汩汩而下,整個房間水汽彌漫,仿佛漂浮在五彩斑斕的光中。這個場景無論是視覺層面還是心理層面,都一種如夢似幻的真實感。
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熱衷的表達方式,有的注重形式,有的注重內容。兩者雖沒有高下之分,但就電影感的體現層面,是重在姿態還是重在態度而言,還是有區別的。前者更多地體現于形式,乃至往往流于俗套,徒有其表;后者則更多地蘊含于內容,潛在幽微,極見本心。畢竟形式上的感官愉悅不會太長久,只有內容上非一般的敏感,才能讓人深深明白影像表現力的強大和微妙。那些微妙的“神來之筆”,仿佛上帝代替藝術家蓋下的手印,仿佛幻覺,一如夢境,讓人困惑、恍惚,又格外真實、迷人,使電影變得如詩歌一般美好。
三
中國電影,尤其是在資金方面乏力的中小成本電影,應該以經濟的方式表達現實的美感,同時,以真切的方式去觸摸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將嚴肅和動人作為首要標準,依靠影像的文化力量來打動觀眾。其實對于作者式的中小成本影片,觀眾對電影語言的要求不高,只要在表情達意上,與他們形成不那么干澀的交流,就行了。而現在的導演,較少往這方面發展,更多的是對市場方面的考慮,而不是從個性出發、從作品出發來對待電影。中國的基礎電影,在這點上做得實在不夠。每年生產的影片里,90%都屬于看不見的影像。
在電影的表達上,我們不妨試著回溯那種具有獨特“電影感”的電影風格,懷揣這樣一種獨特的電影世界觀——既是真實的,又不是真實的。一個人可能不懂什么推拉搖移,但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感覺去掌控鏡頭,言之有物,在光影流瀉后,讓一些信息從影像表達中蕩漾開去。拍出的電影,依然可以具有充沛的電影感。很多藝術形式相通的地方就是存在一個原始的沖動,這是超越所有東西的,是不需要技術層面的經驗的。導演應該做的,就是從影像本體出發,尊重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回到原初的感動,表達他們自己。電影的關鍵,是對影像語言的感覺,這跟文學語言一樣,是一種能力,是可以培養的。正是那些有著特殊電影感的、讓人感動的地方,才使得我們長期被影像侵淫的心慢慢激活,逐漸回暖。這也是一部電影,一個導演的價值所在。只有具備面對自我的誠意和勇氣,對經常視而不見的生活懷揣著詩意和深情,我們才能對得起自己和這個時代。
[1]斯坦利·卡維爾.看見的世界——關于電影本體論的思考[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0:51-53.
[2]讓·米特里.電影美學和心理學[M].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53-60.
胡 南,男,河南濮陽人,鄭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當代影視評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