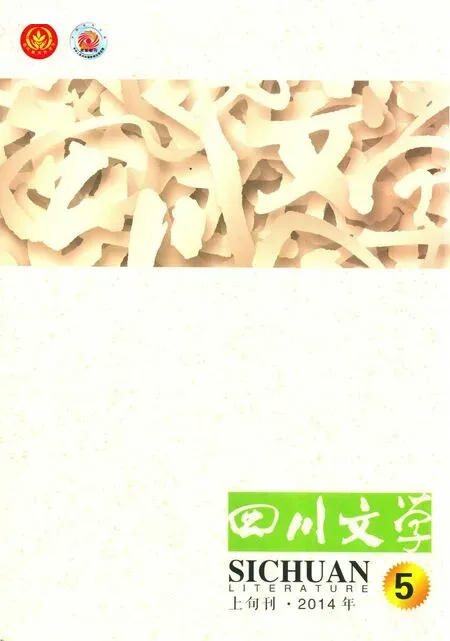讀永勝作品兼談小小說創(chuàng)作
2014-11-18 11:38:37楊輕抒四川
四川文學
2014年5期
/楊輕抒(四川)
讀永勝的小說,讓我想起一個比方:一個小姑娘眉眼長開之前,就一咸菜疙瘩,等到春暖花開,眉眼伸展了,咸菜疙瘩就成一破殼而出的美女了。而這個美女如果還有一份智慧與知性,就有大氣了。永勝的小說就是一大氣美女。
把小說拿美女來比方,跟小說的題材、語言無關(guān)。要說題材,這三篇都是農(nóng)村題材,土;說語言,永勝顯然是故意把我們習慣了的順溜的語言截斷,弄得結(jié)結(jié)巴巴的,同樣土里吧嘰。但是,永勝的小說在敘述過程中的那種從容自在、揮灑自如狀態(tài),的確見功底。如果拿一幅畫來比方,永勝的小說就是水粉畫——色彩雖成片而氣韻流淌,構(gòu)圖雖不闊而舒展大方。因此,忽然有點小感想:寫小小說,選擇什么題材不重要,采用什么語言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骨子里的那份現(xiàn)代意識——一個破衣爛衫的教授依然滿腹經(jīng)綸,一個西裝革履的富二代未必就不是禽獸,世態(tài)萬千,唯理不變。
三篇小小說從氛圍來說,第一篇 《皮狗》最沉重。這種沉重首先來自于永勝在小說場景、人物、故事情節(jié)設置的簡約:一是場景布置簡單,僅僅局限于韭菜地與院子之間;二是人物設置簡單,只有村主任皮旦、農(nóng)民皮狗以及皮狗的兒子皮大三個;三是矛盾沖突簡單,講村主任皮旦要睡農(nóng)民皮狗的老婆,而皮狗想反抗卻無勇氣。這種處理方式類似于歐洲古典戲劇所遵循的 “三一律”,就是把原本可以長篇制作的故事故意壓縮在一個小小的空間里,給人營造一種十分壓抑的感受。……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散文詩(青年版)(2022年4期)2022-04-25 23:52:34
都市(2022年1期)2022-03-08 02:23:30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8期)2019-09-23 02:12:2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46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百花洲(2014年4期)2014-04-16 05:5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