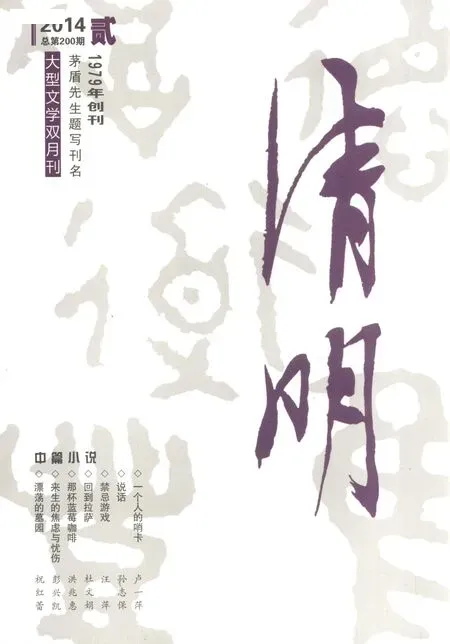目光穿透荒原
目光穿透荒原
宗利華
1
一只山雞從我右上方飛走。
它逃得太快,我根本沒看清它什么樣子,也不知道此前它悄無聲息躲在何處。撲棱一聲響,就把寂靜的氣流撞破,把我沉甸甸的回憶嚇跑了。我想起了母親的話。她說:“真是怪事兒,現如今,野山雞越來越多,螞蚱啦蝎子啦倒越來越稀罕,難不成都叫山雞給吃了?”
山下的槐花兒早就敗了,半山腰一簇簇荊棵上細細密密的花卻還沒綻開。一蓬野酸棗上,挑著一個褐色鳥窩,拳頭般大小,迎著風絲絲顫抖。鳥窩里邊的幾顆干酸棗兒已經變成黑紅色。我小心翼翼伸過一只手去,穿越密密麻麻的尖刺,用拇指和食指捏出一顆,放在手心里搓一搓,慢慢塞進嘴里。頓時,一股子酸澀在牙齒周圍驟然擴散!
我不由得發出嘶嘶的聲響。
頭頂上方突然起了聲音,肯定是荒原上的老四。我聽見他手中羊鞭的聲響,以及他的歌兒。他一定在我的上方,聽起來,卻像是在我身下的谷底。兩山之間的回音太虛空,聽不清他唱什么。
我站到一塊稍稍探出的石板上,看遠處融為一體的天空與山巒,看山谷對面錯落排列起伏不定的崖石,看身體下方清幽的山谷,看一只竭力舒展開翅膀在兩山間悄無聲息滑翔的鷹。我閉上眼睛,模仿那只鷹的樣子,使勁將雙臂向兩邊伸展,伸展。在想象中,我把雙臂伸得無限遠。
那感覺很奇異,既興奮,又害怕。
夕陽打在老四的臉上,他輕飄飄的目光投向荒原邊兒,好像那兒正鮮活地蹦跳著三兩只小羊羔的剪影。他的頭發像搽了油,臉上膚色黝黑,眼里閃著光。他的兩片厚嘴唇緊緊相扣,好像使勁兒憋著,憋著,才能不讓一個莫名其妙的笑聲從嗓子里冒出來。
我鼓動他再唱一首山歌聽聽。
“我不唱,把羊嚇跑了咋辦?”老四嘟囔說,“我哪里會唱啊?”
“我上來的時候,你明明在唱,還甩著鞭子,啪啪,伴奏著。”
老四嘴角稍稍一動,露出半絲微笑:“那個啊,不能守著人唱。”
“這荒原上就咱弟兄倆,我還是外人?”
“可你是文化人。”
“要不這樣,你先來一個大實話。”
“大實話?這行。”老四正正身子,咳一下嗓子,雙手擊打著膝蓋唱起來,“太陽出來喲照個西墻,孩子哭了嘛抱給他娘。弟兄倆走路當哥哥的大,當嫂子的呢肯定是個娘們家。”
我嘴里的一口水差點兒噴出去。“咦,我就奇怪,先前那個,老四你為啥不愿意唱?”
老四搔搔頭皮:“那個有點兒不正經,沒人的時候唱行。”
我笑了:“我滿臉的皺紋都成一道道褶子啦,啥不正經的沒聽過?”
老四猶豫片刻,吧嗒一下嘴:“也是,你兒子都這么高啦,再說,男人女人夜里那點兒破事兒,你比我還在行,我連個老婆都沒有。”他站起來,一邊拍著屁股上的塵草,一邊歪著腦袋,去看那一群個頭不一顏色不一的羊,似乎擔心會被它們聽到。可羊們根本沒在意他剛才唱的大實話,都在忙自己的,啃草的啃草,吸奶的吸奶,頂角玩兒的頂角玩兒。
老四清清嗓子,唱道:“姐兒喲今年剛滿十八,胸脯脯鼓呀,屁股也大,白天晚上想男人啊,還瞞著俺爹和媽。”這種小段兒,我小時候也聽過,有個放牛的半大老頭兒,一張口,全這個。我兩只手掌一拍,念一句白,給他墊腔:“妮兒,你還小啊。”老四接口:“秤砣小哎能壓千斤,胡椒粒兒小能辣死個人,姐兒我雖小——”
他咔嚓一下頓住。
“咋不唱啦?”我笑瞇瞇地看他。
老四嘿嘿直樂:“太流氓啦!”
我也哈哈大笑。
笑過后,我一本正經:“老四,你想女人啦?”老四彎著腰,瞪著眼睛盯著我,虛張聲勢。這說明,他此刻很興奮。“你四哥我都這把年紀啦,夜里連個通腿兒的都沒有,又不是塊石頭!你個沒良心的,飽漢子不知道餓漢子饑。要不是你哥小時候淘氣,爬墻上屋的,自己把腿弄成這樣,我還愁找不上老婆?”
“咦?俺九叔一直給你托媒人。是你自個兒逞能,不愿意,怨誰呀?”
老四哼一聲:“不是啞巴,就是聾子,要不就拖家帶口,還讓我倒插門兒。我能去受那個罪呀?”
那個夜晚,我和老四坐在石板屋前的小院兒里,喝下半斤地瓜老燒,眼看著距離荒原邊緣處不遠的地方,月亮小心翼翼一探,一探,跳了上來。
小院子里頓時一派清澈,荒原上一片空茫。
老四搖搖晃晃站起來,提著褲子,去院子一角撒尿。我也跟去。即便是白天,除了老四,除了一群羊,除了遠遠近近伏在草叢里、窩洞里的山禽野獸,原上的其他活物很少,何況,是在寂靜的月夜?我們可以無所顧忌。
老四的一線尿柱在月色下閃著細碎的光,越過樹枝柵欄,撒向外面的荊棘叢。“還行,是不是?”他很自豪。我很不屑:“小時候比誰尿得遠,你就從沒贏過我。”老四大手一比劃:“再比一盤兒么!”
怪得很,我不如他尿得遠。
老四哈哈地笑:“你看,你累著它了吧?”
重又坐回后,我跟他說正事兒:“你都快四十歲的人啦,還真想在這荒原上住一輩子?”老四卻反問:“住一輩子有啥不好?這原上啥東西沒有?就我過的這份日子,你在山下有嗎?你在城里有嗎?”
我承認山下的確沒有:“但是山下有的,你這里也沒有。”
老四說:“上次咱倆喝多了酒,躺在那塊石板上,你跟我說,城里什么都快,快得來不及讓人眨巴眼睛。”
我點點頭:“是啊,城里是快。”
“這里慢啊,慢得每一天每一年都不重樣的。剛才,我是跟你開玩笑,要真有個女人和我在這里,我還受不了呢。現在,我一走下這片山坪,一到山下,就渾身不得勁兒。在水泥公路上我不知道先邁左腳,還是右腳。屌毛沒長全的小屁孩子,摩托車騎得跟飛一樣的快,我真怕他們撞死我。你看我現在和你絮絮叨叨,一到山下我就說不出話來。就是到城里,到你家去,我照樣也是沒話說,你懂我意思不?”
我嘟囔說:“你跟個原始人差不多啦。”
2
“人這輩子,說慢哪,很慢,說快可真快。”
九叔的臉上似乎永遠是一派淡然。他這份感慨,是我舅爺惹起來的。也就是我奶奶的親弟弟。那個老頭兒,從查出肺癌到咽下最后一根蠶絲樣的氣息,只花掉一周時間。
“你真行,”九叔拍打著舅爺花花綠綠的鞋面嘿然而樂,“不給兒女們添麻煩呀。”
舅爺被擺放在干燥的堂屋地面的一張葦席上。一束陽光掠過草苫子做的半門,沉甸甸地落到他的頭頂。光束里頭,有數不清的細微塵末,正悄然飛舞。在那道陽光的對比下,其他地方,就顯得有些昏暗。舅爺臉上蒙著張黃表紙,胸口上放著一只粗瓷碗,碗里,是紋絲兒不動的一抹清水。
我隔著幾個腦袋伸過頭去,想看一眼舅爺那張臉,卻什么都看不見。
九叔點上一支煙,緩緩升騰起來的煙霧繚繞在臉上,原本還算清晰的皺紋,一時也縹緲起來。看得出來他有些累,他也是真老了。何況,他剛剛做完的那套活路,很考驗一個老頭兒體力的。
細一想,那還不僅僅是體力的事兒吧?
當時,我跪在一個角落里,目光輕輕掠過面前的一片白。我不能跪在前邊兒,如果不是鄉間的習俗日漸開明,我都不能跪在那間屋子里,因為我不屬于舅爺的家族,或者說我跟舅爺家族里的人,并無直系血緣關系。屋子里的每一個人,都清楚自己應該跪在哪兒。那一片白是舅爺家的人,我的長輩們。他們的頭頂,用老粗布做的孝帽各有兩個尖角。我不能戴那樣的帽子,也不能穿白袍子。
看不到前面長輩們的臉,但能想象到,他們并不十分悲傷。舅爺算是老喪啦!所謂老喪,就是無疾而終,自然死去。當然,鄉間對于已足夠老的人,除去自殺,不管何種緣故死去的,都稱作老喪。老喪儀式上,孝子孝孫們是可以輕松,甚至開心一點兒的。
九叔不著重孝,只在左臂肘彎上方纏一細條白布,以示自己也是晚輩。若躺著的那個人跟他毫無親戚關系,則連臂上這白布條兒也省略。因為,這一天,他身兼著要職,鄉下人稱作禮相。喪葬過程,從頭至尾每個環節,都由他來指點。鄉下的紅白喜事有很多講究,很少有人扯得清。
九叔扯得很清。因此,他在鄉間還算受人敬重,尤其受老人敬重。何況,九叔這禮相,比其他人還多一道程序——給離世者凈身。
最初我感覺這事兒很恐怖。年輕時的我,根本不敢進九叔家屋子,事實上常去他那間屋子的人也不多。平日見了他,我都忍不住打量他的一雙手。慢慢地,我不害怕了,開始覺得好奇,這老爺子干嗎要干這個啊?瘆人不瘆人!而現在,我已經能夠理解他了。
因為這個,九叔在方圓一帶很有些知名度。別人沒做這個的,或者不敢,或者不愿。當然九叔也不是對每個離世的人都做凈身,而是根據死者家屬要求。比如我舅爺這樣的老頭子去世,沒什么可忌諱的。要是早夭的年輕人,就得看家人的意思。不過女人離世不管年老的還是年輕的,家里人都不會請九叔做凈身的。即便請,他也絕對不肯。
對于為死者做凈身的每個環節,我都很感興趣。
我請求跪在那間屋子里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看到傳說中的那個過程。
九叔左手位置有個小盒子,核桃木做的,油光可鑒。盒頂有個蓋子,可以輕松打開來。打開后你會發現那很像老女人的針線笸籮,真是有針線、剪刀、指甲刀、錐子等物件。他的右手位置放一個粗瓷的開口盆,盛滿清水。水盆旁邊,擺兩塊四四方方潔白的毛巾。九叔先在另一個盆內凈一下手,輕輕甩一甩水珠,才慢慢地抓起毛巾,泡進清水里,再提起來,雙手輕輕一擰,讓毛巾略干。接下來,開始擦拭舅爺身體了。從頭頂開始,一直到腳心。他的動作很緩,很輕,但很嫻熟。那副身子上的每一道褶褶皺皺,或者能夠藏污納垢的細部,比如耳孔、鼻孔、腋窩,甚至兩腿之間,他一寸都沒放過。九叔上嘴唇向內,緊緊扣著下嘴唇,鼻尖上掛著一滴小小的汗珠兒。光從右側一面打過來,他的面部輪廓就有些不清晰,恍惚之間,我覺得那輪廓邊緣有一重隱隱約約的光暈。屋子里一片靜,似乎喘息聲都聽不到。
偶爾,九叔擰動毛巾,水珠滴落進盆內,清幽無比。
擦洗完畢,九叔伏下身子,抱起舅爺,要為他穿壽衣,就顯得有點兒吃力。他扭頭沖著舅爺的大兒子——我的大表叔——喊:“老哥,搭把手吧?”大表叔故意地問:“這個能行嗎?不合規矩吧!這是你的事兒。”九叔齜牙一樂:“他可是你親爹。”
于是,我的兩個表叔,一前一后,膝行向前,幫著九叔給舅爺換衣服。
舅爺的身體有些僵硬,看上去卻像一片樹葉那么輕。
“嘖嘖,這身衣裳真新鮮啊!老頭兒,我敢保證你這輩子是頭一回穿!”九叔樂了。
給舅爺穿上鞋子,他緊繃的身子一下松馳。九叔拍拍舅爺的一只鞋尖:“你可把我累壞啦。你這輩子喝那么多酒,身子倒還是不輕。”他稍稍前傾,爬行一截,抓起旁邊一張黃紙,即將覆蓋在舅爺臉上時,突然說:“老舅,外甥給你挑個小毛病吧?你瞧——”他伸出一只手,指著房頂。所有人迷惑不解,都抬起頭,順著他的手指頭去看。九叔說:“那個字兒,四十年前我就說你寫錯了,你就是改不過來。”房梁上的確有四個字,寫在紅紙上。彌經歲月,紅紙早就變成灰黑。四個大字是“上梁大吉”。在我的位置看去,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上梁”兩個字,“大吉”在另一面。我擰著腦袋去瞧,果然,那兩個字兒有些不對。
“那個吉字兒,老舅你寫錯一輩子。”九叔笑得滿臉核桃紋。
舅爺寫的“吉”字的上半部分,前一橫比后一橫短。舅爺讀過私塾,寫得一手好字兒,村里凡帶毛筆字兒的東西上,多是他的手筆。
屋子里頓時歡快起來。幾個表叔開始互相遞煙,聊起家常來。
后來,我跟九叔有過一次私下里的對話。
我問九叔:“你怎么想起來去干這個的?”
九叔笑:“你不覺得挺好玩兒嗎?”
這個答案,當然滿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是說,怎么想起要給過世的人擦洗身子?”
九叔眨巴眨巴眼睛,認真地看著我:“以前,我這么想,咱莊戶人來世上走這一遭,其實最簡單。下生的時候在土里,走的時候直接鉆進土里,是不是?你想過沒有,這世上的任何東西,根兒都在土里。現在,人都爭著搶著到城里去,住高樓上,鉆到鋼筋水泥里,到頭來還不一樣,還是到土里去。”
我咦了一聲:“九叔,你是高人哪!”
九叔擺手:“對農村人來說,有比泥巴更干凈的嗎?活一輩子,走的時候身上就這點兒土,有必要洗巴干凈?可后來我聽收音機里說,城里人死了,整得那一套很復雜。電視上有個給死人修臉的,說了句話我覺得在理兒,說是要讓一個人走得干干凈凈。城里人能那樣,鄉下人為什么不行啊?我想明白了,下生的時候身上沒臟東西,走的時候也洗干凈才好。要我說啊,人死了,連衣服都沒必要穿,光溜溜地來光溜溜地走,多好?”
九叔的這番話,引起我的另一個問題,他對人的死亡這事兒,怎么看?他做了多年的鄉村遺體美容師,算是一個經常跟死神對話的人吧?會不會偶爾也會思考這問題?
九叔似乎稍稍一愣:“你啥意思?”
或許,是我的表達太不明確。“也就是說,人這一輩子,生,死,你怎么看這兩件事兒?”問過后,我還是覺得這命題太大。生,還有死,誰能琢磨清楚?一直生活在鄉下的九叔,怎么能回答得出來呢?
果然,九叔搖搖頭:“你這話問得,叫人摸不著后腦勺。但你說的這倆字兒都很簡單。生,人哇的一聲,睜開眼睛,到這個世界上來!死,眼睛一閉,兩腿一蹬,人沒啦!”
我頓時無語。片刻過后,九叔幽幽地補充一句:“不過,中間最長的那段兒,是很受罪很受罪的,那就是活著啊!”
3
“有些事兒,他沒跟你說。”母親說。
母親坐在生滿綠苔的那盤老磨旁邊的棗木馬扎上,目光蟬翼一般飄過院子一角老杏樹的樹梢。日頭已半隱在遠山肩膀后面,樹梢上的葉片嘩啦啦散著光,幾粒原本泛黃的杏子,變成幾點模糊的白,在葉片里或隱或現。
母親講了關于九叔的一段舊事。
九叔這輩子曾經為唯一一個女人凈過身,那是我的九嬸兒。
九嬸兒死于饑餓。
“人,是最不撐餓的東西。”母親說,“餓到狠處,不是瘦得皮包骨頭,倒像是發面一樣鼓起來,眼前的東西都在飛,整個身子輕飄飄的,走路的時候啊,十根腳趾頭得使勁兒摳著地,要不一陣風就能刮跑了。餓壞了的人都不敢走山脊梁,要從溝底下走。”
我的九嬸兒,老四的母親,怕就是被風刮起來,茅草一樣翻滾在半空的吧?那過程中,天空中肯定還塵土飛揚。因為在母親的描述里,她渾身上下就像一個土人,頭發里、臉上、衣服的褶皺里、露著腳趾頭的布鞋里,到處是土。
我母親背著九嬸兒。準確地說,背著九嬸兒的尸體。我的大娘,拄著一根棍子,攙扶著她倆。三個討飯歸來的女人,站在九叔家光禿禿的院子里時,日頭正敞亮地掛在頭頂。她們的影子被踩在腳下,快要看不到。
九叔弓著腰從屋里鉆出來,耀眼的日光刺得他睜不開眼。他兩只手像搭涼棚一樣,擋在眉毛上方,呆愣好一會兒才飄進院子,飄到三個女人跟前。他不說話,艱難地彎下腰,要母親把九嬸兒放到他背上。
母親卸下重負,身子差點兒癱倒在院子里。
眼前的九叔九嬸兒抖成兩張疊加的樹葉。兩個女人的目光輕飄飄地注視著九叔背著他的女人進了屋子。期間,有一整個冬季那么久。炎炎烈日下,兩個臉頰上流著汗的女人,卻不約而同感到半空中飄起雪花兒。九叔把九嬸兒輕輕放到門口位置,一只手摟著她的脖子,慢慢地把她的腦袋平放在地面上。母親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九嬸兒野草一樣的頭發,隨即,兩扇門緩緩關閉。門臉兒上,是一副顏色泛白的春聯。
“你九叔沒哭,從頭到尾,他都沒哭。”母親說,“那時候,人不興哭,不興笑,也基本上不說話。”
黃昏的時候,院子里聚了好多人。土人一樣的女人,蝦一樣弓著身子的男人,但沒有一個人發出聲響。過了很久,有一聲渾濁的開門聲撞開沉寂。
九叔兩腿分開,站在門口,頭發直豎著,兩只眼睛像兩個黑洞。
九叔沖著院子里一拱手,嗓子沙啞:“老少爺們,進來看看吧!”
“你九嬸兒被你九叔拾掇得,就跟當新娘子那時候一樣!”母親說。
那也是九叔第一次為離世的人凈身。
4
老四的整個童年,基本上是遠離荒原的。因此我一直猜不透,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重又返回去。當我從母親那里得知九叔的一段往事后,曾一度猜想,是否這個對老四產生了某種影響?九叔為九嬸兒凈身的那個下午,五歲的老四在哪兒?會不會他就站在屋子里的陰影中,食指塞進嘴巴,靜靜地打量著眼前的一切?
總之,老四在二十一歲那年的某個清晨,拖著他十二歲時生活賜給他的一根瘸腿,沿著一道山脊梁,重回荒原——他的出生之地。而許多年前,他的和我的父輩們,沿著同一道山梁,拖家帶口,挑著鍋碗瓢盆,搬到了山下。
下山,是為了接近繁華,上山是為了什么呢?
許多年過去,某個午后,當一縷陽光穿越云層,穿越城市上空,穿越我家窗戶的玻璃,打落在坐在藤椅上的我的臉上時,我恍然頓悟!二十一歲的老四,已經看透人生本相。以前,我還一直認為,荒原上的老四在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重復著毫無意義的日子,他在緩慢的歲月里等著自己慢慢老去,他在荒原上重新搭建起的那座石板房就是為自己造的墳墓。可那一刻,我突然不那么看。他是找到了一種度過自己漫長人生的方式啊。而我,在四十九歲這年的一個午后,才突然看清了自己,突然發現生存空間的逼仄,突然看到原來未來的好多種可能,已經對我關掉大門。也就說,你這一輩子已經別無選擇。
我縮在藤椅中間的身子,如此渺小。
“在那塊石板上,我坐了差不多一個上午。”老四指著柵欄外頭的一塊青石板,輕飄飄的目光似乎正端詳二十一歲的自己。然后,那時的他站起了身子,朝自己手心里吐口唾沫,兩個砂紙一樣的掌面擦出一陣脆響,隨后攥緊一把鐮刀,走向荊棘叢。
“好,咱們開始吧!”
我母親曾嘟囔過一句話:“草比人力氣大,人斗不過它。人只要一走,房子身上啊,立馬就會長滿草。”這話可真對!偶爾我會想,人尋找家園建設家園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跟草做斗爭。跟現實中的草,跟思想罅隙里的草。人確實斗不過草,人沒法把雜草從這個世界上、從自己的身體里徹底清除干凈。正如,人類自身也在生生不息。
荒原的腹地,曾經有個干干凈凈的小村子。
那種干凈,是屬于人的。哪怕連接幾戶人家的小道上那一坨坨雞糞、一粒粒羊糞蛋兒,哪怕用青石板或木柵欄圍成的一個簡單的羊圈,哪怕飄渺在村子周圍房子周圍那種黏稠的氣味兒。然而,當老四站在那個村落的邊緣時,曾經被踩得堅硬發亮的小路早已被荊棘、雜草的根攪拌得很松軟,互相纏繞的拉拉秧、野葡萄、爬山虎,幾乎覆蓋掉所有的石頭屋子,曾經茅草鋪設的屋頂,已完全變成芨芨草、竹節草、狗尾巴草們的天下。似乎它們以一種氣勢洶洶的姿態,來慶祝領土失而復得。
“人造一個村子,要幾十年,甚至幾輩子。”老四指指院子周圍,“它們,用不了兩三年,就給你全蓋住。”
四十多歲的老四看著掛在石板墻上的一堆蓬勃的竹節草問我:“你能看出來,它們是裝在一個籠子里的嗎?”
當年,二十一歲的老四把一蓬割下來的鮮草,胡亂塞進一個荊條籠子。他在面朝陽光的一面石板墻壁的縫隙間,砸進一根槐木楔,將籠子挑在上面。我想,他這么做只是一時心血來潮,或者,是想在寒冷的冬天順手扯下一把來塞到爐膛里引火。總之,老四認為,一籠子野草早已經被烈日曬得脆干。也就是說,它們已經在夠不到泥土的地方緩慢死去。然而第二年夏天的一場小雨過后,他坐在清新的院子里,正打量滿原活潑潑的綠意,一扭頭,突然發現墻上也掛著濃濃的一簇綠色。
那荊條籠子周圍,竹節草正活潑潑地探頭探腦!
接下來的數個冬去春來,老四的目光肯定不止一次打落到那個籠子上。那一籠子的草,老四決定在有生之年都不再去動它們,他要看看那蓬挑在墻壁上的圖騰一樣的野草,究竟能長成什么樣子。在帶著輕飄飄的欣喜的目光注視下,一籠子的草以一種貌似懶洋洋卻執拗的、肆虐的姿勢,完全盤踞了那面墻上的一塊空間。有年夏天,他在屋子里盯著墻面的時候,突然吃驚起來!墻外面一籠子草的草根,穿透了石板與石板的縫隙,已經鉆進屋里。“要是樹根呢?會怎么樣?”老四問我。我沉默半天后說:“會把整座房子撐開。”
5
皚皚的雪,覆蓋了荒原差不多整整一個冬季。
我站在荒原邊沿,打量那間石板房頂一動不動的一抹青煙。我的四周,閃著耀眼的光芒。所有一切都靜止不動。
大雪覆蓋下的荒原上,根本沒有道路。對我來說這并不是困難。我熟悉每一條上山的路,也熟悉原上每一道堤堰、每一蓬草叢、每一個坑坑洼洼。這很奇怪是不是?我出生不久就被父母帶下荒原,沒有足夠多的荒原記憶。在山下村子里我度過了童年,在二十公里之外的鎮上我讀完了中學,然后,進入城市讀大學,畢業后,在三十公里外的縣城教書。
畫了這樣一道弧線后,我居然發現最讓我魂牽夢繞的,還是我的出生地——荒原上一間石板作壁茅草封頂的小屋子。
而那個地方現在一絲房子的痕跡也找不到了,積雪把它蓋得嚴嚴實實,即便沒有雪也找不到。老四說得很對,草根啦,樹根啦,早在數年之前就很輕松地把一間石頭房子拆得四分五裂。荊棵、酸棗樹、灌木、蠟條、野桑樹、野香椿,它們的根布滿整個荒原表層,深深地循著土壤的脈絡,扎入地下石板層的哪怕一丁點紅土。它們把荒原表層弄得越來越松軟,甚至風雨還會幫著它們,讓一堆亂石在歲月緩慢的步伐中移動位置。
住在城里的我偶爾會想,荒原上的老四,如何度過大雪封山的日子啊。
整整一個冬季,他不會下山。像冬眠動物一樣,在春夏秋三季積蓄熱量,冬季進入蟄伏狀態。山下人很少到荒原上去,也就猜不透,老四怎樣驅逐嚴寒。事實上也基本沒人會去猜。老四像個野人,根本無法納入山下人的視線。
我站在雪地里,站在凝固不動的冰冷氣息里,繼續向四周看去。
到處都完全一樣,潔白,清澈,干凈,靜止。
我看到老四笨拙的身軀鉆出屋子。他的嘴里呼出鮮活的熱氣。起初,老四沒有看到我,或許,他根本就沒朝我站立的方向看。他的體態臃腫,像一只黑熊。走起路來像是在爬行,蹣跚,緩慢。掛在擔杖鉤上的兩個鐵皮水桶,倒是偶爾鮮活地發出聲響,豐富一下荒原上的色調。
“冷不冷啊?”老四終于遠遠地瞧見了我。
我正走向他,隨口嘟囔兩個字:“廢話。”
我們在離小屋子不遠的一洼泉眼邊上會面。那洼泉水長年地存在于原頂,簡直就是個奇跡。若沒有它,我簡直難以想象老四怎么存活。泉邊放著一根鐵鍬,老四抓起來,咔嚓咔嚓,敲開凍得結結實實的冰面。不一會兒,夾雜著冰塊的水,滿了兩個水桶。
“讓我試試?”在老四抄起擔杖時,我說。他瞧我一眼,慢悠悠地反問:“你身子還能行?”
兩桶水,讓我的肩膀感到沉甸甸的壓力。走到屋子門口的時候,我呼呼直喘,身上卻分明暖和了些。屋子里倒沒我想象得那么冷,紅彤彤的爐火戰勝了凜冽的寒風。
“從入秋開始,我就沒讓爐子里的火滅掉。”老四說。
是的,在荒原上只要有火,有水,就死不了人。
顯然,老四一個人在喝酒,爐灶上擺著兩個小碟,一碟是花生米,一碟是三五只螞蚱和蝎子。他從灶旁摸出另一個酒盅,順手抓起小桌子上的一塊毛巾擦擦,倒滿酒遞過來。
我仰起頭,一飲而盡,一股子辛辣在身體內輻射開來。
“我是叫你下山的。”喝了兩口,我說,“九叔走了。”
老四看我一眼,稍稍沉默,輕飄飄地問:“啥時候的事兒?”
“今天凌晨。”
老四又慢悠悠地給我倒上一盅,突然齜牙一笑:“還有幾天就過年啦,你說他著什么急呀?”
6
依照鄉下代代傳下來的規矩,每一輩的男人都要按年齡排個順序,這叫排行。我們家族的人,父親的那一輩,已經所剩無幾,我跟老四這一輩倒還齊整,二十一個。父親輩上總共是十一個,現在,只剩老六和老十一。老六,我的六叔,在大雪來到的第二天就倒在炕上,據說咳嗽聲像是在擂牛皮鼓。所以,老九,我的九叔,駕鶴西去,家族里的掌舵者是十一叔。十一叔比我大哥——我們這一輩里年齡最大的一個——年紀還要小一點兒。在整個過程中有些掰扯不清的事兒,他還要請教我大哥。
幫工的村里人很多,活兒就顯得少。宰豬、擔水、劈柴、燒水、蒸饅頭、洗菜、燒菜,這些雜事兒都有人搶著干。這些人的父輩或爺爺輩,有去世的,都曾麻煩過九叔。即便不是如此,逢著誰家有紅白事,鄉下人也是聚到一起的。我們這些孝子不必干這個。這支龐大的隊伍,得待在靈堂。來吊孝的親朋正從周邊的村子,從四面八方的大公路上、山梁上,慢慢地往一個地方匯聚。每個人到來,身著白衣頭戴白帽的我們,都要在十一叔率領下,分作幾行幾列,跪在地上答謝。老四站在前排,九叔的親兒子里他最小,所以,就排在最末。
自始至終,他一聲不吭。但神態悠閑,看不到幾許悲傷。
不過,老四做了一件事兒,對我來說不啻是狠狠地一擊。我想,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們這些兄弟姐妹,以及村子里所有人,都將會牢牢記住荒原上的老四了。
那是他下山后的第一個夜晚。所有人都在守靈。院子里的積雪,白天被踩踏成泥地,還不到傍晚,就成了冰,外邊的人踩出咔嚓咔嚓的聲響,屋子里的人卻寂靜無聲。
或許,一個很多人已經想到卻不愿第一個提出的問題已經擺在面前。那就是,要不要給九叔凈凈身子?
從聽到九叔過世的那一瞬起,這問題就纏著我不放。照慣常思維推理,九叔生前肯定希望有人為他洗一下身子,才好騎到那只大鶴的后背上。問題是,誰給他擔任禮相?誰為他凈身?九叔沒有帶出弟子。現在哪有人學這個?找個禮相不難,但找個像九叔如此專注、如此嫻熟而又如此有敬畏感地為死者洗身子的人,實在不容易。
即便是自己的子侄,哪一個愿意去做呢?
我逼著自己垂下腦袋。盡管那問題揮之不去,但我還是強迫自己不要開口。我已經問過自己,你,能不能干那件你親眼目睹過的事情?結果,內心經過一番廝殺,有個聲音無奈地作了回答,不能!
許多天后,我對自己當時的這個不能做過辯解。或者說,總算找到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你不能,是因為你不敢面對死亡。此刻我不能不提到,當時九叔揭開一張黃紙后,我終于看到的舅爺那張臉。正是那張臉才促使我詢問九叔關于生與死的問題。盡管,他的回答還沒那么讓我滿意。
我在舅爺臉上看到一絲恐懼!是的,對死亡的恐懼!
舅爺的臉形有些扭曲,有些變形。我理解為,在生命的最后一秒,在跟死神握手的時候,他渾身顫抖!
是的,我垂頭看著地面的時候,地上的確是舅爺那張臉,和那個糾纏了我很長時間的神色。同時我又回想了一下,那天九叔為舅爺凈身的時候,他的那張臉。那是一張閃著光亮的臉哪!
此刻,躺在屋子中央的九叔的臉,會是什么樣子?
他會不會對死亡也有恐懼?
一個輕微的聲音響起。從我身邊走過一個人。我抬起頭,看到老四一瘸一拐的背影從坐著的跪著的人群縫隙間,輕飄飄地走過去。他肯定是憋不住尿啦。我甚至想,他會酣暢淋漓地用尿柱在冰面上化開一個黑洞。過了好一陣子,他回來了。我有點兒吃驚地看到,他肩上搭一條潔白的毛巾,手上端著一個嶄新的冒著熱氣的盆子。他沒有回到自己該待著的位置,卻直接在九叔旁邊兒蹲下身子。他把瘸了的那條腿緩慢地攤開,另一條腿挪動著跪了下去。
屋子里所有人都在瞧他,沒一個人說話。
“老頭,咱洗洗身子吧?”老四前傾著上身,臉幾乎要貼到九叔的鼻尖。他的臉上帶著一絲微笑,“你看,我給你打了熱水,一點兒都不冷。”說著,他慢慢地把右手探到九叔那張臉的上方,慢慢地揭開覆蓋的那張紙。
于是,我看到了九叔的臉。他神態安詳。
責任編輯 苗秀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