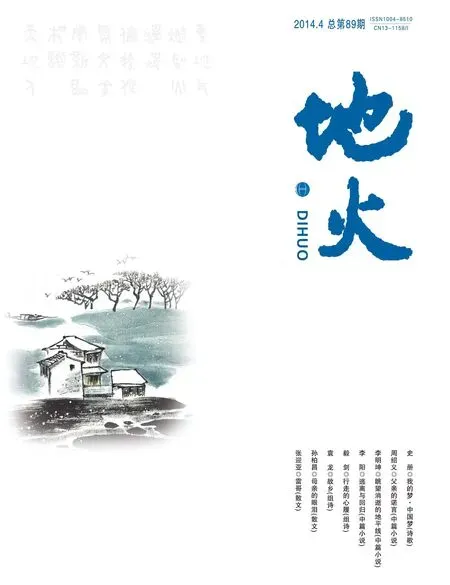行走的心履(組詩)
■毅 劍
行走的心履(組詩)
■毅 劍
遠方以遠
很小的時候,他就望見了那個地方
隨后的幾十年里他一直朝著它走
多少次走近了才發(fā)現依然很遠
一棵樹用怎樣的姿勢才能長成一棵樹
一匹馬用怎樣的奔跑才算得上馬的速度
一只騰空的鳥,該如何伸展雙翼飛翔
最終,才能抵達一只鳥的高度
一座山熟悉自己的每一株草、每一塊石
而從不曾與另一座山相遇
擁擠中他看清了許多人卻忘掉了自己
他總是夢到遠方并成為最亮麗的風景
不同的山、不同的水、不同的風和云
他常為自己的夢想亢奮而不安
但腳下的路,依然的泥濘和擁擠
一些花開了敗,一些風來了去
一些老枝新芽,驚奇中愈發(fā)地深感陌生
他想象著遠方的天空,博大、深邃
佇立在遠方的峰巔之上,俯視著
一條通向他腳下的路,神秘而彎曲
那些驚人的相似,甚至讓他分辨不出
他走過的是哪一條?獨一無二的路徑
但現實是他還在路上,并一直會在路上
在遠方以遠,依然有著無處安放的思念
這終于讓他有機會看到另一些人
另一些猶如雕像的光芒,另一些的
最終抵達的同一片山林或墓場
那些,原本就光亮和灰暗的相似命運
只是,明白了這一切,他已到了晚年
現在能夠做的,只是偶爾想起后的苦笑
顫巍巍地與人講述后的莫名失落
身后,那些曾經年少的激情和沖動
這結果,顯然與最初的想法不同
有一個地方
許多的雨打過,許多的風吹過
許許多多的路和許許多多的時光
一一遠離、一閃而過
總是說都過去了,可還是想起
總是說早遠離了,卻恍若如昨
一條河,一座城,一片天
一串背后的影子晃動著久遠的思念
許多年了,你要去的地方
他總是先期到達。你準備要去的地方
他早已兜了個圈子,憑借輪回
他又折返,你正要啟程的始點
那一刻,你總有點心猿意馬
一種熟悉的陌生讓你手足無措
那一刻,你看到遠處的自己
不知是左胸還是右胸就開始陣痛
歲月留給你的晴朗總是越來越少
生命的冬天一日日不再遮掩
而他依舊年輕,那個將你一天天
活老了的地方,總是鮮亮著
吹在他身上的每一場冷風,不偏不倚
像早年一樣,吹在你的心上
該來的終會來,該去的也終會去
這原本,就是沒有辦法的事
一生說長,也很短,痛并快樂地活著
繁世煙云中放棄了過多的隱忍和熱愛
你最終沒有放下的,還是有一個地方
像久治不愈的心病,靈魂深處的歌謠
總是——不停地,一直吟唱
偶爾回首
沒有預兆。只是一個不經意的動作
心,就忽然的一下子收緊了
從腳下的某個點迅速地向身后散去
一串腳印,似曾相識的一些影子
閃亮,抑或跳動著的都鮮活起來
像一個秋天,嶄新地將自己打開
一生的路,注定還沒有走完
你去年穿越的那片林地,一些樹
已開始落葉。曾驚飛的一些鳥
還在另一些樹上叫著,你聽不懂
她們一直都在說的什么,但知道
你走過,曾無意地驚動了她們
看不清的跳躍和飛翔,最終構成
記憶,以及深處的一些韻腳和線條
一些笑散盡了,一些傷還在路上
如果生命可以重來,你會不會
剪掉那些原本就不該長出的枝葉
繞過泥濘、崎嶇及形形色色的誘惑
會不會只保留春天,保留河流和道路
保留遠方那個聲音,持久地傳唱
如同春天的花帳,覆蓋著眾多的仰望
回憶是安全的,但活著,你必須轉身
更多地關注腳下的路和未知的遠方
一些風已先你前去,一些枝條
穿過冰封,憔悴中已透出春意的欣慰
那么還是走吧,在新的征程中
找回更加完整的自我。花開花落
都最終,無愧于轟轟烈烈的一生
靜靜走過
從一朵蕾到一樹花,這只是一種過程
反常也正常的舉止在枝杈之間游走
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細節(jié)漫過日子的沉重
靈魂中存在的一切,那些仿佛和曾經
都靜靜走過。這小村,瓦舍,窄窄的田埂
這遠遠近近,熟悉與不熟悉的一些面孔
土路和小橋,返青的麥子及漸深的草叢
一串又一串腳印在黃河灘的深遠里走失
永不回頭的碎裂在河岸的空曠里蕩動
能夠聽得見什么?又能夠聽得懂什么
響過鈴鐺的,是自行車老掉牙的鏈條
一頭拉上屠場的老牛發(fā)出最后的長鳴
靜靜走過,這遲來的春雨,晚來的風
燦爛著一路綻放的煙花,發(fā)霉的陳年舊事
飄飛的灰燼,還有早已斷了線的風箏
小地方總是趕不上外面的大世界
前年的一本老皇歷還記著今天的日子
嘀嗒,嘀嗒,總是給自己畫圓的破鐘
每個早晨最先睜開眼睛的小村長者
枕邊的一小塊濕痕,來自傷心的夢境
靜靜走過,這滑到嘴邊又咽進肚子的詞語
比方言還方言的話,比土地還土的手勢
家長里短,三大姑八大姨們的親情
靜靜走過,看花開著開著就謝了
鳥飛著飛著就遠了,水蛇般的時光
一恍沉沒在田里,再一恍,又隱入水中
太陽照著酷夏,也同樣照著隆冬
蝶的痛苦嬗變,不經自己同意就死的生命
也同樣的,不經自我允許就可以降生
靜靜走過,這微露的晨曦,河流與山巒
大地和天空。箭一樣逃命的野兔和一只鷹
它擊穿了天堂,還在不停地飛啊飛的鷹
同樣的,一直就在生活或命運的掌中
你回來了
你回來了,她卻走了
好多年前,隔著半截短短的矮墻
她喊你。一條通往校園的鄉(xiāng)村土路
在時光深處沉沒,也像那枚
你投出的瓦片,濺起的一串水花
心頭驟然泛起的星星點點
只有村頭的河水,依然流著
像一條線,縫合著眼前和遠去的昨天
還有一些燕子,高低不平地飛著
似曾相識。那些年的小橋、柳樹
還有房屋、小院和一些熟悉的面孔
你只能猜測、想象和虛構
老屋不在,那位檐下佇望的人呢
遙遠的叮嚀,也像徹底走遠了的牛車
只有風聲,熟悉而又陌生
視野更遠了,而腳下卻更加擁擠
除了記憶,沒有什么留得住
時間和愛,一代又一代的親人
沒有墳頭的祖墓地,你轉了三圈
也沒能找到祖母的墳塋
一地柳絮,卻沒有柳笛聲聲
你繞到碑前凝視,一串名字的亮光中
一個個親人開始走動,你試圖
拉住他們的衣襟,握住他們的手
你伸出的指尖,觸碰到的
卻只是那塊從不言語的石頭
一個似曾相識的地方你把它叫作故鄉(xiāng)
一個一生念道的名字你把它視為親人
而最終相識的,也只有那些燕子
它們還是那么輕快完美地,高低飛著
像穿過你和她身體的空靈和虛無
從不管,你是不是來了,真的回來了
她走了,是不是——永遠地也就走了